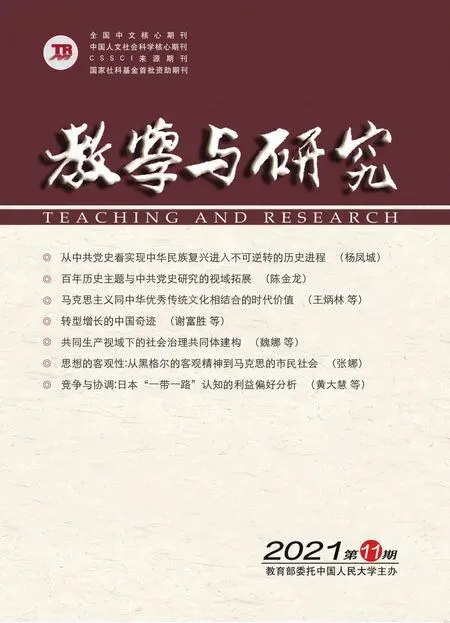贫困如何产生: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认知差异
——从《法哲学讲义》到《哲学的贫困》
田书为
贫困,是迄今为止人类尚未解决的重大难题,近代以来,人们一直苦苦思索贫困产生的原因。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产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1)[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页。黑格尔是启蒙时代之后的大哲学家,对贫困问题有着持续的探讨。(2)梁燕晓:《黑格尔:个体与共同体冲突的成功和解者?——基于市民社会中贫困问题的考察》,《哲学分析》2018年第4期。马克思更是思想史上的伟人,终其一生关心贫困者的境遇。所以,分析他们对贫困成因的认知及其差异,对于理解当时甚至当代社会的贫困问题、寻找摆脱贫困的路径,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黑格尔对贫困成因的认知
黑格尔认为,在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市民社会由两个原则构成:第一,“特殊性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3)第二,“形式普遍性原则”,“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197、211、58、58页。所以,个体都以满足自身需要为劳动目的,不过,这却要通过与他人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才能实现。
在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秉赋是不同的,即特殊方面,他们发展起来,并且通过这种发展呈现出差异”,(5)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3,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p.1328,p.1328,p.1328,p.1328,p.961.而“秉赋”来源于“自然”,“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197、211、58、58页。所以,“不平等”随即被赋予了天然的合法性。在“秉赋”存在差异的自然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现存的普遍财富,但这是有条件的。”(7)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3,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p.1328,p.1328,p.1328,p.1328,p.961.“第一,通过他直接拥有的,即资本,它可能来自于继承或者积累……第二,通过技能和才干……第三,通过他人的任性”。(8)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3,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p.1328,p.1328,p.1328,p.1328,p.961.这说明,当他人没有“任性”地在与劳动者交换劳动产品时破坏市民社会原则,劳动者分得财富的不平等,就是源自其自然条件的不平等,因而是合法的。这样,认为“一切人应该有足够的收入以满足他的需要……象一般单纯的善意愿望一样,它缺乏客观性”。(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197、211、58、58页。个体获得财富的不平等反而体现出市民社会充分尊重了个体的自然属性,包容了个体的差异,使每个人都按照其自身特点各尽所能,为整个社会劳动继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即便财富分配多寡不等,我们似乎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按照市民社会的“形式普遍性原则”,个体即便获得较少的财富,却也仍旧能够从社会中获得生活必需。在“抽象法”阶段中,黑格尔曾指出,“人们当然是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即在他们的占有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意义说,每个人必需拥有财产”。(1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197、211、58、58页。的确,人格的实现必须要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且以得到市民社会的承认与肯定为重要标志,因为“市民社会是个人与群体的特殊性被承认的领域”。(11)Sybol Cook Anderon, Hegel’s Theory of Recognition: From Oppression to Ethical Liberal Modernity, Continuum, 2009,p.8.所以,个体所依赖的私有财产必需存在一个“最小限额”,(12)Dudley Knowles, Hegel and the Philosophy of Right,Routledge, 2002, p.126.使个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完善自身,以致有能力融入市民社会的分工体系,过有“尊严”的生活。由此观之,黑格尔一方面承认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合法性,同时也为市民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即相对贫困,划定了底线。可以说,个体只有具备一定数量的财产,才有能力融入市民社会;当个体处于市民社会的分工体系之中时,意味着他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
但是,黑格尔马上发现,相对贫困的成因不仅在于主观因素,社会分工同样引发相对贫困。“当初产生分工……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1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通过分工,市民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并远远超越了自然的最初给予。黑格尔声称,“自然是富饶的,但却是有局限的……与之相对……人类通过劳动生产的财富,能够无止境地增加”。(14)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3,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p.1328,p.1328,p.1328,p.1328,p.961.但是日久年深,“人们从事越抽象的劳动,他们就越被一种严格的纽带紧紧地束缚在一起……开始,分工似乎从优势出发,即通过对具体的分解,劳动获得了普遍的形式,才智在这种抽象中得以保存。但是,人的依赖性增强了,在这种片面性中的技能,对一个具体事物而言则是笨拙”。(15)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3,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p.1328,p.1328,p.1328,p.1328,p.961.的确,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法单独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自身的需要,只能通过交换的手段满足自身的需要,所以个体只能从事一种劳动,随着分工的细化,必然存在相当一部分群体从事着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抽象的劳动,这使得他们对其他领域的劳动愈发无知,对于理解、把握、生产某种更加具体的事物愈发无能为力。于是,个体带入市民社会中的诸多自然要素在市民社会分工体系的作用下走向了“匮乏”,而以“匮乏”为条件分得的“特殊财富”势必日益减少。这样,相对贫困的产生,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困”(16)在商务版的《法哲学原理》中,“Noth”被译为“匮乏”,“Armuth”被译为“贫困”,“Mangel”被译为“缺乏”或“匮乏”等。实际上,这三个词都有“不足”“缺失”“贫穷”之意。不过在黑格尔那里,“Noth”总体上指个体的能力、素质、情感、意志等主观因素的相对缺失;“Armuth”包含“Noth”的内涵,并侧重指个体参与普遍财富分配后,私人所得的相对缺失;“Mangel”指更一般意义的“缺乏”。问题逐渐凸现出来。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与以弗格森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思想存在着明显差异。首先,弗格森看到了在分工条件下,个体所从事劳动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商人的民族由那些除了自己的特殊贸易以外,对全人类事务一窍不通的人组成。……士兵除了服兵役以外,并不关心其他事务”。(17)但是,他并不强调社会分工能够使人堕入“匮乏”这一负面意义,而基本关注社会分工能够增加普遍财富、完善劳动产品这一积极作用。“通过技艺和专业的分工,财富的源泉被打开了……每种商品都在最丰富的意义上被生产”。(18)依据这样的观念,弗格森认为市民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和基础”,(19)并将之归因于“天赋与性情的差异”“个人在不同工作中养成的习惯”(20)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73,p.173,p.179,p.175.等主观因素。所以,相比于弗格森,贫困问题对于黑格尔而言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实际上,贫困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贫困贱民”问题密切相关,而“贫困贱民”标志着市民社会原则在现实领域中的崩溃。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2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44页。“贫困贱民”就会产生。1824—1825年《法哲学讲义》直接引述了《法哲学原理》中的上述原文。(22)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3,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 p.1390.很明显,“贫困贱民”所具有的贫困特点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因为他拥有的“特殊财富”已经低于“社会成员所必需”的水平之下,他已经没有物质能力进行自我完善以融入社会的分工体系,而被抛出市民社会之外,成为市民社会原则的对立面。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发现,“长期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导致了:低收入,缺乏财产所有权,没有储蓄,家里没有食物储备,并且长期缺乏现款。这些条件减少了他们有效参与到更大的经济体系的可能性”。(23)Oscar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On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ed.Daniel P.Moynihan, Basic Books, 1969, p.189-190.刘易斯这里指出的贫困现象,实际就是黑格尔“贫困贱民”思想反映出的社会现实,二者所处的时代虽然相去甚远,但得出的结论却具有高度一致性。
按照《法哲学原理》和1824—1825年《法哲学讲义》的行文表述,黑格尔在讨论社会分工造成相对贫困这一问题以后,直接把讨论聚焦在“贫困贱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上。这样的文本安排似乎表明,绝对贫困是由相对贫困的加剧导致的,因此,市民社会分工体系的发展就要为“贫困贱民”的产生直接负责。但实际上,在市民社会分工体系的条件下,相对贫困逐渐加剧这一量变过程,无法发生向绝对贫困转化这一质变结果。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过程中,劳动所有权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改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中的个体,始终是市民社会的一员,为市民社会贡献劳动,同时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身所需,市民社会与个体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相互承认的状态。个体始终具有一定数量的财富,以满足他融入市民社会的需要。所以,即便由于分工的发展,“广大群众”的私人所得越来越少,但它就是个体成为社会成员实际需要的最小值(“社会成员所必需”),单纯从市民社会分工体系出发,绝对贫困不会产生。
那么,如果从客观性出发理解“贫困贱民”成因的道路行不通,就只有从主观性出发了。黑格尔在论及相对贫困时指出,它使贫困者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化。因为,相对贫困发生以后,贫困者会生发出一种渴望“技能和财富”得到“平等”分配、“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得到“平等”提升的情感。但是,贫困者的这种渴望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市民社会“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24)贫困者的这种诉求,在黑格尔看来因此只是“任性的特殊性”,而且这种“任性”在持续蔓延。随着相对贫困的加剧,贫困者“丧失了……受教育和学技能的一般机会,以及司法、保健,有时甚至于宗教的慰藉”。(25)这时,贫困者的情绪从渴望平等逐渐转变为“嫌恶劳动……邪僻乖戾”,与市民社会原则的对抗性日趋尖锐,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情绪现实化以后所产生的“其他罪恶”,即逃避劳动,不再通过劳动获得生活所需,正面与市民社会原则对抗。贫困者本来已经处于市民社会的边缘,当他“主动”脱离市民社会分工体系以后,便无法从市民社会中获得生活所需,他的生活就更加得不到保障,绝对贫困也就这样产生了。如黑格尔所言,“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2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1、243、244、244页。这一句中的两处“贫困”都是指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至于那种“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情绪,在贫困者还是市民社会成员、面对相对贫困时就已经内在地形成了,并一直延续到他成为“贫困贱民”之后。
二、黑格尔贫困成因思想的特点及其困境
黑格尔的贫困思想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认为相对贫困是个体的自然差异与社会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用一系列真实的数据与案例,为世人呈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工人阶级“骨瘦如柴,毫无气力……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老得快,死得早”。(27)针对英国利物浦各阶级平均寿命情况的调查显示,“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曼彻斯特郊区“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28)而且,“英国医生收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不得不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服用那些从长远看来弊大于利的假药”。(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8、420、417页。如果把这一事实拉回到黑格尔的思想语境,那么工人阶级的遭遇则是工人自身的自然要素以及社会分工共同造成的,并且这会使“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3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1、243、244、244页。所以,黑格尔清楚地看到了分工的负面意义乃至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化。伊尔廷(Ilting)在编辑《法哲学讲义》时,甚至将《法哲学原理》第243、244节,直接分别命名为“阶级对立”和“工人与资本家”。(31)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Band 2, Frommann Holzboog, 1974, p.682-683.蒲鲁东曾宣称,“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提到了分工规律的益处和害处,但是他们过分强调了前者而忽视后者……什么是财富增长与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的首要原因呢?就是分工。造成精神衰退和文化贫乏的首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也是分工”,(32)[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4页。并认为只有萨伊和自己认真对待了分工的消极因素,这显然低估了黑格尔的贫困思想。
黑格尔贫困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认为“贫困贱民”是贫困者的“任性”直接造成的,黑格尔将之称为“贫困者的不法”(33)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14,1, Felix Meiner Verlag, 2009, p.192.。商务版(商务印书馆出版)《法哲学原理》将第241节中的“ihres Unrechts”译为“他们所遭受的不法待遇”,这是一处不小的错误。因为若按此理解,黑格尔似乎认为社会分工成为了一种“不法”,贫困者的负面情绪反而具有了合法性,这恰恰与黑格尔的原意背道而驰。英译版《法哲学原理》将“Gefühl ihres Unrechts”译为“sense of wrong”,更符合黑格尔本意。(34)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Allen W.Wood, trans.H.B.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65.虽然,黑格尔很清楚,相对贫困不仅来自贫困者的自然要素,同时也来自社会分工。他甚至承认,“这种不法是强加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3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45、245页。不过即便如此,黑格尔也仍旧坚定地声称,“没有人能主张权利与自然相违背”。(36)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Suhrkamp Verlag, 1970,p.390.在商务版《法哲学原理》第244节补充中,“gegen die Natur”被译为“对自然界”,语法上虽然无误,不过依据《法哲学原理》第200节,译为“违背自然”其实更妥。因为贫困者无视自然这个“不平等始基”(市民社会维护并发展了这个“不平等”),“任性”地提出了“平等”的诉求(违背自然),以致堕入“不法”,沦为“贫困贱民”(第241节的“ihres Unrechts”也表达此意)。若把“gegen”译为“对”,则无法凸显这个内涵。英译版《法哲学原理》将“gegen die Natur”译为“against nature”,更符合黑格尔本意。(37)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Allen W.Wood, trans.H.B.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65.不难发现,黑格尔极大淡化了社会分工摧残贫困者这一客观事实,而把贫困者沦为“贫困贱民”主要归因于他的主观“任性”。所以,相对贫困是黑格尔默许甚至支持的,但“任性”及由以造成的绝对贫困(“贫困贱民”)却是黑格尔坚决反对的。
可以说,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超出弗格森等人对贫困成因的理解方式。弗格森认为,“在每一个商业国,尽管人人都要求得到平等权利,但是,抬举了少数人肯定会压制多数人”。而贫困者“是很无知的。对于尚未得手的财富的向往成了嫉妒或奴性之源。……实现贪欲而犯下的罪孽都不是无知的例证,而是堕落和卑鄙的例证”。(38)[英]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弗格森虽然没有明确区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罪孽”“堕落”等贫困者的不幸境遇,归因于“嫉妒”“奴性”等贫困者的主观“任性”。黑格尔呈现出了与之非常接近的思路。如果把这种理解贫困成因的态度推向极端,那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必然产生。马尔萨斯认为,“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这两条法则……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39)另外,“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数比率增加的”。(40)所以,物质财富的供给远小于对它的需求,贫困及由之引发的“苦难与罪恶”必然产生。这时,理性“出面加以干预,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若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41)[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10、13页。现在,连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即繁衍,都成了一种需要被限制的“任性”。很明显,马尔萨斯对现代社会贫困成因的判断是错误的,蒲鲁东曾专门对此予以说明,“50年来,法国的国民财富增长了五倍,而人口却只增加不到一半……可是,为什么贫困并没有成正比地下降,却反而增长了呢”。(42)[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41页。黑格尔也认为,“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4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45、245页。所以,黑格尔不会同意马尔萨斯的想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理解贫困成因的思路有着高度契合。
其实,黑格尔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现实,他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资本家把市民社会原则“置之度外”,不从事劳动却与工人进行着“以无换有”的交换,“寄生在生产阶级身上”。(44)[英]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3-54页。在1821—1822年的《法哲学讲义》中,黑格尔认为,“富裕贱民同样存在”。(45)当大部分劳动者随着分工发展愈发严重地陷入相对贫困时,整个社会的“普遍财富”便会更多地向“少数人”聚集,贫困者(工人)与富人(资本家)的阶级分化逐步形成。资本家分得的“特殊财富”与整个社会创造的“普遍财富”在量上越来越接近。于是,他狂妄地认为,他的“特殊财富”就是“普遍财富”,工人所应得的“特殊财富”成了他的给予。因此,资本家“视大部分人的生活资料为它的掌中之物,将自身视为他们的匮乏及其诸多权利的主人”;(46)认为自身是“凌驾于法之上的……通过这种情绪的存在……在自身中随即采取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人们亦可将之称为堕落,即富人认为一切都是被允许的”。(47)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2,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 p.754,p.754,p.754.当这种情绪外化以后,资本家必然会在没有交换对等劳动产品的基础上,剥夺工人的“特殊财富”,破坏以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原则。鲁达(Frank Ruda)认为,贫困贱民的形成“取决于他是否使自己成为贫困贱民”,不过,“如果制度之外存在财富的偶然性力量,那么富裕贱民不得不产生”。(48)Frank Ruda, Hegel’s Rabb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ontinuum, 2011, p.54.可是,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可知,财富之所以具有偶然性力量,恰恰是资本家“任性”的结果,所以鲁达在判断“富裕贱民”的形成根据时倒果为因了。看上去,黑格尔似乎解释了前述社会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资本家与工人进行不对等交换,工人所得的“特殊财富”将少于他维持自身工人身份所需的财富值,况且工人本身已经处于市民社会的边缘,资本家的掠夺将使工人的财富低于“社会成员所必需”,工人将随之失去融入市民社会分工体系的客观条件,沦为“贫困贱民”。因此,资本家的“任性”掠夺,带来的不会是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有序”生产,而是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虽然黑格尔对此没有过多说明,但能够从他的整体思路中得出上述结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这样概述黑格尔遭遇的难题:从市民社会中“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按照市民社会原则,无产阶级仍旧从属于分工体系,本应享有相应的权利、发展自身的特殊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黑格尔的逻辑无法解释的。所以,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原则在现实中逐步走向了自我矛盾。哈德曼(Michael O.Hardimon)指出,“认为黑格尔比马克思更早地意识到贫困是一个异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50)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黑格尔看来,贫困是生发于市民社会结构自身的罪恶……贫困导致人们失去有意义地融入社会的市民和政治生活的必需方式”。(51)Hardimon Michael O, Hegel’s Social Philosophy: The Project of Reconcili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46,p.236.在此,哈德曼忽视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逻辑界限。相对贫困虽然来自于“市民社会结构”,但不会导致绝对贫困,所以黑格尔不会认为它能够引发“贱民”乃至“无产阶级”等“异化”问题。哈德曼此举虽然拉近了黑格尔与马克思贫困思想的距离,但却高估了黑格尔贫困思想的理论水平,与事实不相符合。
三、马克思对贫困成因的认知及其超越
市民社会如何产生出一个不享有“任何特殊权利”的工人阶级?这是《巴黎手稿》急于回答的问题之一。首先,马克思延续《导言》中的思路,仍旧从市民社会原则出发考察现实社会。“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52)而这种联系,依赖于“交换”,因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5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170、175页。当然,以上种种,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实现的。所以,“每个主体都依赖于一种特定的补充,这样所有的主体就都相互通过承认的关系而连接在一起,他们各自都在他们的劳动中相互得到证实”。(54)[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84页。很明显,马克思这里坚持的正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则。其次,工人阶级之所以不享有“任何特殊权利”,是因为存在着“异化劳动”。“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即资本家。这样,工人就无法通过劳动从社会中换得自身所需。所以,工人遭受的“不公正”不在于个体间自然要素的差异,而在于被彻底排除在市民社会原则之外,处于普遍的无权利状态。最后,即便如此,为了“利己的需要”,即“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5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170、175页。工人不得不屈从于整个社会的奴役。
不过,黑格尔已经表明:第一,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在“异化劳动”发生以前就存在了;第二,在这样的前提下,资本家掠夺工人合法所得,只能使工人失去维持其阶级身份的必要财富。所以,工人虽然主观上要维持生存,但客观上不具备继续成为工人的能力。因此,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直不能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澄清“异化劳动”究竟如何从市民社会中产生,无法解决黑格尔遗留的难题。这里的马克思与布雷(又译“勃雷”)很相似,布雷也承认市民社会原则对社会发展的作用,“1.必须要有劳动。2.必须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资本。3.必须要有交换”。(57)而资本家“凭着骗人的不平等交换制度,天天在工人身上榨取”。(58)至于这种榨取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也只能含混地说一句,“我们姑且不管我们的社会何以会有了现在这样的状态……只管它在被发觉时就已如此,并且是可以改造和修正的就好了”。(59)[英]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5、53、23页。所以,马克思与布雷、弗雷格、马尔萨斯等人的差异在于,放弃从贫困者“任性”的角度出发解释贫困成因。但是,他们却又误判了“富裕贱民”(资本家)“任性”所能产生的现实影响,继而面临难以克服的理论障碍。
很快,马克思认识到,要想真正理解现实社会为何存在阶级压迫、为何源源不断地制造贫困,必须放弃市民社会原则式的历史解读路径。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找到了推动历史演进的真正物质基础,即“阶级对抗”。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是依据“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并把黑格尔意义上“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的市民社会,称为“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所依托的基本经济结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持这样的观点,“‘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作为这样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61)Marx-Engels-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p.115.本文将“als solche”译为“作为这样的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译法不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在本句中,前两个“市民社会”指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三个“市民社会”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仅实现了资产阶级,而非全体市民成员的发展。
这时,马克思真正超越了黑格尔解读贫困成因的基本范式,并与蒲鲁东、布雷等人划清了界限。蒲鲁东认为,“‘这个阶级(消费阶级)是由一切阶级组成的,它的幸福就是公众的幸福,就是一个国家的繁荣。’不过,萨伊应该加上一句,就是生产阶级也是由一切阶级组成的,它的幸福也是公众的幸福”。(62)[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4、100页。而整个社会则是通过分工与交换发展起来的,个体在市民社会原则的作用下,彼此都是互相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个体,不存在经济关系层面的结构性对抗。按照这样的理解,蒲鲁东的确可以“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135、148-149、196-197、154页。将社会抽象成一个“普罗米修斯”。整个社会就表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路径:“普罗米修斯开始劳动了……第一天,他的产品、即它的财富和福利便等于10。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了分工,他的产品便增加到100。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都发明一些机器……”。(64)[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4、100页。能够看出,他与布雷和早期马克思一样,都接受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则。若延续这样的逻辑,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必将最终被还原为个体间矛盾,而对工人阶级现实境遇的把握,亦将回到黑格尔的理论困境中无法自拔。所以,马克思犀利地指出,“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135、148-149、196-197、154页。那么黑格尔、蒲鲁东、布雷的市民社会原则从何而来?或者说“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135、148-149、196-197、154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该原理”来自思想家对资产阶级社会运行方式的误解,是“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到此,马克思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难题。因为,当“阶级对抗”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性原则并主宰着全部个体的意志与行为时,“压迫”便不是资本家以“任性”的方式施于工人,“被压迫”也不是工人以“任性”的方式能够摆脱。“压迫”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本质;“被压迫”使工人成为工人,是工人阶级的本质。如果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语言概括,那就是,“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指劳动能力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工人“被压迫”的经济条件,是“工人”概念的核心内涵;“赤贫”则是“工人”概念的直观表达。黑格尔的逻辑无法澄清资产阶级社会如何从市民社会中产生,而马克思则宣告,市民社会其实不曾实现过,有的只是从古至今的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社会也是从前一个阶级社会演变而来,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135、148-149、196-197、154页。“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135、148-149、196-197、154页。望月清司曾尝试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之前,加入一个市民社会阶段,“促使共同体发生变化的是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和交往体系,它们却在‘市民社会’中披上了私人所有的外衣,转变成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资本家社会(市民社会的转变形态)又以‘广泛的分工’即‘大工业’的形式开花结果”。(71)[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即便暂且不对马克思的复杂文本进行细致讨论,单从黑格尔的理论困境及马克思对他的扬弃便可发现,望月清司的判断值得商榷。
那么,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如何发生呢?马克思发现:“利润”和“工资”分别是资本家和工人取得收入的方式,不过他们却共同地来自工人的劳动,这正是资本家可以在不付出劳动的情况下就获得财富(“压迫”)的经济原因。布雷认为,在交易中,“资本家和业主们对于工人的一星期的劳动,只付出了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在一星期中所获得的财富的一部分。(72)[英]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2页。从字面上看,布雷似乎与马克思得到了非常类似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工人付出了一周的劳动却没有获得对等的回报,而只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部分劳动成果,以“利润”的形式被资本家据为己有。当然,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清晰地指出,工资实际是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73)而“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7、618页。超过的部分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过,与马克思不同,布雷意义上的剥削仍旧立足于资本家的“任性”,而非对资本家阶级身份的揭示,所以他没有达到《哲学的贫困》的水平,更无法企及《资本论》的高度。
当马克思以“阶级对抗”的立场认知贫困问题时,贫困者精神意识的变化,便不再如黑格尔所言,经历从“正直、自尊”到“贱民精神”(75)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2,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 p.994,p.753-754.的过程,而发生着从“利己主义”到“阶级意识”的演进。马克思认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76)因为,“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工人只关心各自的私利,反抗资本家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77)他们仍旧被“利己主义”精神支配,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委曲求全。但是很快,工人在大工业的发展中逐渐联合起来,面对资产阶级日益深重的压迫,“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6、196、196页。工人把斗争的矛头自觉指向了资产阶级,形成了“阶级意识”,(79)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对自身历史生成和时代使命的客观把握。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8页。成为了“自为的阶级”。对这一历史进程,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予以清晰概括,“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黑格尔之所以把贫困者对市民社会原则的反叛情绪称为“任性”,究其根本在于,他认为贫困者没有看到市民社会承认并发展着他的个人利益,误解了市民社会原则的本质。在1821—1822年的《法哲学讲义》中,黑格尔指出,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在医院中找到。……如果大量群体低于这一尺度,贱民就会产生”。(81)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2,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 p.994,p.753-754.黑格尔或许认为他已经把“社会成员所必需”这一标准降得很低,不过亦如他所言,“为特异化了的需要服务的手段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也细分而繁复起来了……至于无穷”。(8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6页。所以分工的发展是没有界限的,贫困者的私人所得在持续降低的过程中势必要低于医院所能给予的财富值。基于生理、心理等正常的生物学反应,贫困者沦为“贱民”具有很大程度的必然性,“贱民精神”也因而真实呈现出市民社会分工体系对劳动者的摧残。维尔埃克(Wilfried Ver Eecke)认为,黑格尔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即贫困大量存在,并且来自于个体能掌控范围之外的偶然现象”。(83)Wilfried Ver Eecke,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conomy,Springer Verlag, 2008, p.172.不过,恐怕是出于保护市民社会原则的需要,作为对市民社会的反叛,“贱民精神”的合理性始终没有被黑格尔承认。
可以这样概括:黑格尔虽然声称市民社会尊重人的特殊性差异,承认人的独立地位,但默许了市民社会对贫困者的压榨;马克思虽然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建立在对贫困者剥削的基础上,但也因此为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改变人类命运,寻找到坚实的物质根基。事实往往是血淋淋的,令人难以接受,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终究不是田园诗式的,而是在阶级斗争中诞生、发展,并把所有人裹挟其中。当然,分析贫困成因远不是目的本身,只有在此基础上指明人类摆脱贫困的路径,才能真正以思想引领现实,而那将是一个更复杂且更富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