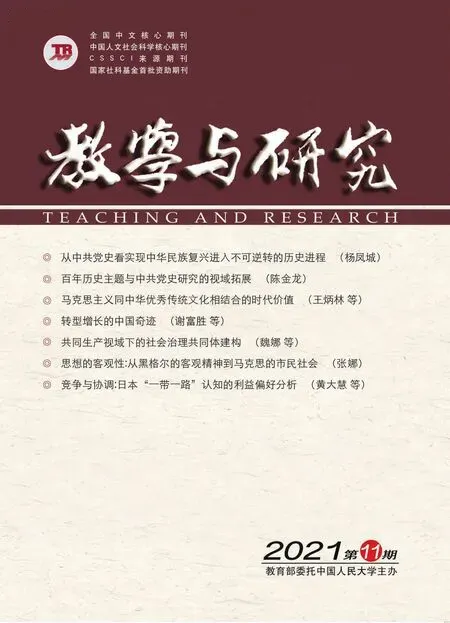竞争与协调:日本“一带一路”认知的利益偏好分析*
黄大慧,赵天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变革国际关系与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既获得了来自沿线国家的欢迎,也逐渐得到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与肯定。日本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以及亚洲与全球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也在各个层面对“一带一路”给予了高度关注,“一带一路”一时间在日本成为高频词而被广泛提及。尽管如此,日本对“一带一路”的高度关注却未能转化为积极认知,从政府、学界到社会都弥漫着对“一带一路”的警惕与担忧。直到2017年,日本才对“一带一路”展现出一定的接触姿态。
关于日本的“一带一路”认知,既有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纵向性”整体认知,这类研究占了绝大多数,主要梳理了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认知的阶段性变化,同时聚焦于安倍政府的反应或应对;(1)“纵向性解释”的研究参见: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卢昊:《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日本学刊》2018 年第 3 期;杨伯江、张晓磊:《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转变动因与前景分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3期;等。二是集中于日本经济界、媒体、学界等非政府力量的“横向性”认知,此类研究有别于将日本政府作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研究,反映出日本各界对于“一带一路”认知的多元性及其对政府认知的反作用力。(2)“横向性解释”的研究参见: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顾鸿雁:《日本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其影响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朱丹丹:《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解读及应对》,《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2辑;吴淑招:《从朝日新闻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重大转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13日,http://www.cssn.cn/gd/gd_rwhn/gd_ktsb/gjydylpxhzgyxpz/202008/t20200813_5169256.shtml;等。
本文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尽管学界有不少文章论及日本政府与各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情况,但对于这种认知的形成原因及其转变艰难性仍缺乏更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利益偏好决定国家认知”的解释路径阐释日本的“一带一路”认知问题,而非仅仅是对认知的历史演变或是对不同行为体认知进行事实梳理。
一、解释路径:基于利益偏好的分析
认知(Recognition)是指双方对彼此的意象,它由利益(Interest)决定。国家利益的构成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从“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的本体论角度出发,国家利益的形成不仅是天然的物质性存在,也可以通过规范等理念性因素建构。在此基础上,国家对利益的不同偏好(Preference)构成了国家对外认知的来源。
首先,权力竞争重视物质的相对收益。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都强调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竞争,尤其在后者看来,以“无政府状态”为国际政治的假定条件,国家更看重相对收益,而不会满足于绝对收益,国际合作也因此难以实现。(3)尚会鹏:《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权力竞争更容易发生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双方都十分看重物质收益的孰多孰少,这种结构性矛盾会使得获取利益的过程变得更加激烈。崛起国与守成国还会根据自身利益偏好来设计与推进地缘战略,因此在某一重合的地理范围内很容易造成地缘权力竞争。
不论从经济权力还是地缘权力的视角来看,日本对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地位更替十分敏感,日本并非不愿意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获益,而是担忧这种获益会更有利于中国。(4)袁伟华:《权力转移、相对收益与中日合作困境——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为例》,《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尤其自2010年日本GDP排名被中国超越之后,日本与中国展开权力竞争的趋势愈发明显,日本全方位对华制衡显著增强。甚至在西方学者看来,日本已经从维持稳定的国际战略的“现状国家”开始向“怨恨的现实主义”转变,公开对华采取“软硬”两手制衡。(5)[英]克里斯托弗·休斯:《“怨恨的现实主义”与日本制衡中国崛起》,《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卷第4期。在冷战结束之后,日本不仅在争夺东亚贸易与投资市场方面与中国竞争激烈,在围绕“东亚”“亚太”等地区主导权方面也与中国展开了广泛的竞争。
其次,制度合作注重物质的绝对收益。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利益是物质性的,但对于国际合作抱有期待,并不过分强调争权夺利的竞争色彩,而是提出制度的理性安排会使得行为体倾向于合作,以获取物质的绝对收益。合作性是制度强调的重要方面,制度的实践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现实情况中,国家实力的结构性变化、相互认知以及彼此采取的外交政策等因素,往往会导致制度既可以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可以作为制度领导国或参与国的权力制衡工具,国际制度间的竞争并不鲜见。(6)关于“制度制衡”与“制度竞争”,贺凯和李巍分别提出了“制度现实主义”与“现实制度主义”,两种理论虽然在分析层次、研究问题等方面各有侧重,但是都强调了制度具有现实主义属性的“竞争性”,而非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的制度与合作之间存在的高度关联。尽管制度权力既视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工具,也将其作为权力竞争的组成部分,但很明显的是中日两国之间后者占据了主导性。参见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
中日在东亚制度格局中形成了长期竞争局面,两国都希望更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方案成为地区合作的主导方案,为此双方曾围绕“10+3”和“10+6”机制展开过激烈的制度竞争。(7)在地区合作的制度偏好方面,中国属于内向型,而日本属于外向型的。例如中国更愿意通过在东盟主导的“10+3”制度框架内发挥更大的话语权,而日本更倾向于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三个与日美友好的域外国家,以“10+6”制衡中国实力,推动合作进程。参见孙忆:《竞争者的合作: 中日加强经济外交合作的原因与可能》,《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尽管如此,两国仍然通过中日韩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机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地区协调。在这种局面下,一方面,中日两国的制度协调经常存在制度导向不一、外部力量强势介入导致合作龃龉的困境,制度的竞争性淡化了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制度合作性;另一方面,东亚的大国协调基本处于可控的范围,中日两国能够在地区合作中寻求相关契合点,以获取绝对收益,并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由此可见,虽然制度间竞争是主流,但中日仍可以通过政策协调改变收益预期,达成竞争者之间的合作。
最后,规范塑造国家利益。国际规范作为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核心,是指国际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约束和塑造国家的对外行为及其互动。(8)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国际规范理论指出,不同于物质的利益观,国家利益既不是外部威胁的结果,也并非国内需求驱动,而是各国共享的规范和价值塑造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认定和行为选择。(9)章远:《话语权、国际规范和国家利益——重读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8日。国际规范作为 “一个行为集体拥有的关于适当行为的共享期望”,塑造了相似行为体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西方国家倡导的规范在自身容易扩散且接受程度较高,这不仅与西方国家相似的国内制度与文化较匹配,也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需求。基于“国以群分”的身份政治逻辑,规范竞争导致零和博弈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同的因果推论,西方国家以容易传播的“好规范”来定义西方规范,而将“非西方规范”定义为不享有国际合法性与传播性的“坏规范”,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竞争与对立形态。(10)何银:《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对外政策具有经济务实主义特性,但在保持与西方国家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集体一致时,仍然遵循利益逻辑而非义务逻辑。尤其是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之后,面对中国倡导的规范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扩散,日本针对中国“规范遏制”的趋势愈发增强。在各种国际场合,安倍政府频频抛出“价值观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反对以实力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海洋法治三原则”“基建建设标准”等排他性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试图联合规范认知相近的国家一同构建遏制中国崛起的“规范层面”均势。(11)日本学者汤川拓将“均势”概括为“政策层面的均势”“体系层面的均势”“规范层面的均势”,认为“规范层面的均势”并非完全现实主义式的均势概念,而是对于实现国际社会共同体共有利益或成员一般利益而形成的规范性和集团性体制。参见湯川拓:「国際社会における規範としての勢力均衡とその存立基盤」,『国際政治』2014年3月第176号。
基于上述分析,对“物质的相对收益”与“规范塑造的国家利益”偏好构成了日本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性”认知,对“物质的绝对收益”偏好则构成了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协调性”认知,前者为主要,后者为次要。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既有竞争也有协调,这不仅符合日本长久以来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为判断未来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走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性”认知
在“竞争性”认知中,“物质的相对收益”偏好,是指日本将“一带一路”视作日本地缘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的威胁;“规范塑造的国家利益”偏好,则是指日本认为“一带一路”严重挑战了西方倡导的价值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一)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
地缘利益既包括地缘经济利益,也包括由地缘经济扩展形成的地缘政治利益。地缘经济通常被视为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经济手段(Economic Statecraft)。(12)Blackwill, Robert D. &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在日本看来,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成为“一带一路”扩展地缘经济利益的重要目标,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不仅局限于交通基础建设,中期来看,也包括构建以人民币为基础货币的地区经济圈。”(13)浅野亮:「『一帯一路』の論理と性格―経済と安全保障の両面から―」,『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号,第32頁。日本各界对于AIIB的关注程度颇高,在机构初创时期,日本对于AIIB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这侧面反映出日本在处理AIIB问题上利益取舍的复杂心态。面对中国首次主导创设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日本将其视为对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巨大挑战,担心传统的亚洲基建市场会落入中国手中。与此同时,即使日本深知“不参加获益便为零”,但参加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经济权力的制度化安排,并与全球金融体系的传统主导国美国相忤。因此,日本对AIIB抱有相当程度的警惕,本质上是抗拒中国可能主导未来地区与全球基建的融资话语权,从而使日本的获益受损。
不容否认的是,日本曾长期扮演着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建设者角色,积极开发地区经济走廊,实施政府开发援助、调动民间资本一直是日本获得巨大基建市场的主要手段。面对“一带一路”的基建布局,特别是中国企业雄厚的资金实力,日本企业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强,日本政府也开始积极为本国基建市场寻求出路。在2015年5月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日本宣布在未来5年内与ADB合作向亚洲国家提供1 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个数字恰好比AIIB的法定资本金多出100亿美元,这无疑展现了日本对于相对收益的极度敏感,与AIIB的竞争性姿态不言而喻。(14)「第21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餐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外務省,2015年5月21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521speech.html.2013年5月,日本制定了“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立下了到2020年基建订单达到30万亿日元的雄心壮志。(15)「インフラシステム輸出支援」,外務省,2020年9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 092742.pdf.在“一带一路”重点布局的沿线区域,日本政府除了频频签下高额的基础设施订单之外,安倍晋三等政府官员也是不遗余力地充当起本国基础设施的“超级推销员”,以挤占中国的基建市场,在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区与中国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16)例如,仅在2017年,安倍等其他日本政府官员亲自作为“超级推销员”的基建订单成果合计194件,包括印度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速铁路项目、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口开发项目,俄罗斯的邮政系统项目等。
日本警惕“一带一路”可能危及自身地缘政治利益,将中国构建“一带一路”的动机视为“秩序修正主义”,认为中国对现今国际利益格局所处位置不满。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认为“‘一带一路’就是要以经济权力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17)川島真:「一帯一路構想と海運事業―海運·海洋強国を目指す中国の動き」,『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号,第98頁。此外,诸如“海洋强国”“军事港口”“新朝贡体系”等概念频频出现在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对“一带一路”认知的现实主义逻辑,即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中国“试图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18)「第3章 国益と世界全体の利益を増進する外交」,『外交青書』,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chapter3_01_06.html.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认为“中国创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背景就在于中日两国在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陷入对立局面;在东亚合作构想受挫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协调对象开始从太平洋向西亚、南亚以及欧洲与非洲拓展,从而构建一个宏大的经济圈,并以此为基础构筑明显具有强烈政治含义且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势力圈。”(19)天儿慧:「政治から読み解く『一帯一路』-パックス アメリカーナへの挑戦と難題」,『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号,第39頁。
日本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在于中美对立博弈的国际格局。日本认为中国正在力图打破美国为霸权的国际秩序,打造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决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动机有二:一是美国难以接受构建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二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出台。(20)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日本学者多提出较为消极的看法,认为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始终保持着极为慎重的回避姿态,“互相尊重核心利益”成为美国难以解决的首要问题。有日本学者指出,2013年之后,随着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中美在南海与西太平洋的摩擦与网络攻击加剧,奥巴马政府基本不愿再提及“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参见神保謙:「新型の大国関係 米中外交の行方を左右」,キャ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2019年9月28日,https://cigs.canon/article/20150929_3309.html;高原明生:「中国の内政と日中関係」,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9月28日,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R01_China/01-takahara.pdf.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认为,美国无法接受中国与自己的对等地位,难以默许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无法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因而一个中美利益共存的国际秩序恐怕很难形成;此外,TPP则是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开展的实质性围堵。在高原明生看来,由于中国向东的利益空间扩展明显受阻,中国开始将对外战略由“美国第一主义”转向“欧亚大陆第一主义”,“一带一路”就是这一转变的实际举措。(21)高原明生:「アジア地域の安全保障と日本の課題」,佐倉国際交流基金,2016年8月6日,http://www.sief.jp/21/2016/bundai201612.pdf.尤其是TPP战略可谓赌上了日本的“国运”,但缺少美国的TPP使得日本的对华“软制衡”严重受挫,转而积极谋划构建“印太”战略,矛头直指“一带一路”,与中国展开新一轮地缘竞争战略。
(二)价值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日本将“一带一路”视为与所谓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等对立的“异质化”存在。安倍政府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尽可能营造一个广泛对抗中国的“价值观”阵线,这是在日本相对实力衰落事实下所采用的“软制衡”手段。(22)早在2006年第一次执政期间,安倍晋三就针对中国推行“价值观外交”。参见黄大慧:《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安倍政府刻意强调所谓共同价值观,在外交场合言必称“自由、民主、人权”,极力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日本的标牌。(23)《揭开安倍政权“价值观外交”虚伪面纱》,《人民日报》2013年6月14日。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寻求这种价值观利益的另一层用意在于拒斥带有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日本对美国庇护下的国家秩序始终抱有一种依赖感,这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为日本提供了自身稀缺的安全保障与经济赖以生存的自由贸易体制。川岛真将“一带一路”形容为“与欧美依据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基本理解完全不同的新型国际关系试验场”,是一种“完全不以民主主义为前提,基本上只是重视经济关系,以利益分配构筑‘双赢’,凭借伙伴关系相连的世界命运共同体。”(24)川島真:「一帯一路構想と海運事業―海運·海洋強国を目指す中国の動き」,『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号,第97-98頁。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也提出,“一带一路”既是为了阻止美国回归亚洲对华形成包围圈,也是为了阻止向世界输出“民主”的美国构筑的价值观围堵。(25)遠藤誉:「習近平主席訪英の思惑―『一帯一路』の終点」,yahoo news, 2015年10月9日,https://news.yahoo.co.jp/byline/endohomare/20151019-00050601/.
面对“一带一路”的新理念与主张,日本开始积极以“印太”为抓手,与西方国家组建群体性力量牵制“一带一路”。日本首先利用2016年第6届“东京—非洲国际发展论坛”(TICAD)的机会提出了“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紧接着,同印度、美国与澳大利亚领导人紧急确认了这一战略规划。(26)「第1章 2017年の国際情勢と日本外交の展開」,『外交青書·白書』,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s10201.日本的战略方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与中国存在地区争端的印度纳入“价值同盟”,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封堵。日本不止一次地寻求与印度确认“基于价值的伙伴关系”,开创“拥有共同普适价值与战略利益的‘日印新时代’”,称赞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27)「日印共同声明 自由で開かれ,繁栄し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外務省,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90053.pdf;「岸田外務大臣によるモディ·インド首相表敬」,外務省,2016年11月1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80.html;「日印ヴィジョン2025 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と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の協働」,外務省,2017年12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8.html.另一方面,日本突出与印太地区中小国家,特别是向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的国家施加“海洋法治”规范,借价值观之名,行安保合作之实。日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扩大该地区遏制中国的安全合作,并为“印太”地缘构想的顺利实施增强合理性,与沿线各国共同对“一带一路”设置障碍。
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倡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符合西方的高标准,强调构建“高质量”建设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包括“经济性、安全性、应对自然灾害的强韧性、考虑环境与社会、以及对当地社会和经济的贡献”,之后固定为“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的“四大条件”。(28)「第21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餐会」,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2017年5月21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521speech.html.安倍晋三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在满足‘四大条件’的前提下才可考虑与‘一带一路’的合作”,却又明确表示“并非认可‘四大条件’,就一定代表与‘一带一路’合作”。事实证明,中国的基建模式在注重质量的同时,兼顾平等协商的原则,充分考虑对象国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体现了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的内涵。日本学者也承认,与日本追求“高质量”的精细化方式不同,“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通过精简项目的审批手续,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与资金能力在短时间内高效率推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从而对接次区域各国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9)Fumitaka Furuoka,“Japan Is Putting more Quality over Quantity in the Mekong”, East Asia Forum, September 27,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09/27/japan-is-putting-quality-over-quantity-in-the-mekong.除了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建规则标准,日本政府也加紧利用2016年在伊势志摩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7)与2019年在大阪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等国际场合,进一步在西方国家之间扩散对国际基建规则标准的规范认同,试图扩大自身在全球基建领域的话语权,以排除“一带一路”在规则与标准方面的影响力。(30)「質の高いインフラ分野をめぐる国際潮流」,外務省,2020年11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bunya/infrastructure/index.html.
三、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协调性”认知
虽然“竞争性”认知是主要方面,但在“协调性”认知下,日本也可通过制度合作得到物质的绝对收益,具体包括“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主义”“聚焦‘印太构想’的经济合作性”以及“探索务实合作模式”三个方面。
(一)全球性体制认同:维护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
特朗普政府动摇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主义架构,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过度竞争,与“一带一路”展开一定的接触姿态。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表态转变与特朗普政府上台带来的日美关系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给日本造成了强烈冲击。在这种变局下,安倍政府可谓是“不安倍增”,自由贸易体制与地区经贸制度事关日本国家利益,一旦倾覆,后果不堪设想。在美国因素的“助推”下,日本逐渐意识到与中国继续展开竞争无益于维护国际秩序,也无益于彼此利益,而“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促进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的地区倡议,这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寻求中日关系由“竞争”到“协调”的突破口。2017年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显示出了一些灵活调整的迹象,对“一带一路”的表态开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日本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向外界传递对“一带一路”的改观,采取了较为“谨慎的积极”,一面表示“‘一带一路’是具有潜力的经济构想,中日合作可以满足亚洲巨大的基建需求”,另一面又指出“在认同公平公正的亚太发展理念、透明开放的招标方式和经济回报性高、债务可偿还的前提条件下参加‘一带一路’建设。”(31)「第23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餐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首相官邸,2017年6月5日,https: //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第3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対話(日中CEO等サミット)歓迎レセプション」,首相官邸,2017年12月4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1712/04taiwa_kangei.html.
对于AIIB,尽管日本政府至今仍未表态加入AIIB,但是与AIIB的接近值得瞩目。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指出“虽然日美同盟是不可撼动的根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仅仅依靠美国就可以描绘日本未来的剧情已不复存在,中日通过ADB与AIIB共同为其他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是符合现实的。”(32)寺島実郎:「大中華圏で捉える『一帯一路』」,『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号,第28頁。2019年7月,日本派出了此前负责国家财政与基建的两位重要官员出席在卢森堡召开的AIIB年会,被日本媒体看作是日本政府对AIIB的积极信号。(33)「中国主導のAIIBになぜ接近?日本の深謀遠慮の背景」,朝日新聞,2019年10月30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BQ462BMBQULZU00B.html.除此之外,2020年1月,AIIB也雇用了一位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BIC)的日本籍雇员,日媒评价说“此人具有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丰富经验。”(34)「中国のアジア投資銀、日本人登用」,西日本新聞,2020年1月14日,https://www.nishinippon.co.jp/item/o/575445/.日本综合研究所的AIIB动态分析报告也指出AIIB关注经济回报性,在选择项目投融资方面较为谨慎,与ADB的合作比较广泛,在机构运营上也具备很高的专业性,而非具有较强的中国政府色彩。报告建议“日本应当考虑加入AIIB,并为日本企业谋求更大的基建利益。”(35)佐野淳也:「AIIBの現状とわが国の関わり方」,『アジア·マンスリー』,2018年8月号,https://www.jri.co.jp/page.jsp?id=33071.2017年以来,AIIB连续两年获得标普、惠誉、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最高Aaa评级,穆迪则在2019年率先给出AIIB的Aaa评级,认为其“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日益巩固”。(36)《亚投行连续三年获得穆迪Aaa评级:前景稳定》,2019年4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2732.由此可见,尽管日本想要改变对“一带一路”的固有认知仍存在现实困难,但在AIIB保持良好绩效的事实面前,日本将来是否会选择加入也未可知。
(二)区域性制度协调:聚焦“印太构想”的经济合作性
不同于美国以竞争为目的的“印太战略”,日本既不愿看到“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形成过分的地缘竞争,也并不完全排除潜在的制度协调。不能否认,在构思和推行“印太构想”的过程中,日本始终秉持国际权势斗争的固有逻辑和对华指向性。(37)宋德星、黄钊:《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机理及其战略效能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1 期。毋庸置疑,“印太”的诞生就是为了与“一带一路”争夺地缘的相对收益,但现实主义的利益逻辑很难保证己方的利益所得一定会多于彼方,双方往往会因为争夺相对收益过于惨烈而陷入安全困境。尤其像日本并不能如同美国凭一己之力即可主导战略走势,也难以保证自身战略意志与战略能力是否可以与战略目标相匹配,因此日本需要考虑除对冲、制衡的传统战略手段之外与新兴崛起国的接触(Engagement)策略。接触政策要求尽可能通过与新兴崛起国的互动来取得经济利益,提高收益预期,这也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绩效支撑政治合法性前提下的必要做法。(38)菊池努:「インド太平洋」の地域秩序とスイング·ステーツ『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ースイング·ステーツへの対応ー』,平成26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総合事業)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4年,第3頁。
日本非常清楚,如果将自身绑定在美国对抗中国的“战车”之上,很容易陷入中美大国博弈的“断裂带”,最终失利的只能是日本自己。在2018年的国会施政演说上,安倍晋三提到“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与中国也可以合作,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的庞大需求”。在2019年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安倍晋三则直接将“战略”更名为“构想”,也并没有像2018年一样沿用“与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共有的国家联手”这样的表述。(39)「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8年12月2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2019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安倍晋三表明“‘印太构想’是不排除任何国家的。”(40)「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9年12月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从现实情况来看,印太地区的国家对中国存在很高的经济依存度,日本也深知自身无法给予这些国家所需的所有公共产品,因此在承认“一带一路”作为印太地区主要公共产品供给方的基础上,避免“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的过度竞争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日本战略学者神谷万丈指出“日本的‘印太构想’中具有对华竞争与对华协调两种特性,对于实现竞争战略来说,协调战略也同样重要。”(41)神谷万丈:「『競争戦略』のための『協力戦略』―日本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の複合的構造―」,SSDP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研究会,2019年2月,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26.html.未来日本继续贯彻这种作为矛盾体的“印太构想”是可以确定的,但是这种正相反的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如日本所愿,恐怕并非日本一己之力可以左右。
(三)探索务实合作模式: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行为体的增加可以改变收益的未来预期。日本国内经济界的逐利动机迫使日本认真思考一味竞争的后果可能是双输局面,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折中的机制协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日本经济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暧昧,一是出于对倡议本身的不了解,二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消极应对,并没有营造出日本企业参与的有利氛围。但是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逐步清晰,日本经济界出现了要求考虑参与“一带一路”的声音,至少日本社会已经隐约意识到不参加“一带一路”可能导致的失利,并会削弱日本产业竞争力。(42)苗吉:《多元中的演进:日本视野中的“一带一路”倡议》,《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6卷第1期。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方针稍有变化,日本的经济团体就会顺势而动。经团联前后两任会长榊原定征、中西宏明对“一带一路”抱有很高的期待,他们多次率团来华访问,寻求在“一带一路”下加强中日两国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商机。(43)「中国首相『日本と自由貿易を擁護』経団連会長らと会談」,2018年10月10日,https://www.sankeibiz.jp/macro/news/181010/mca1810101921018-n1.htm.历史屡次证明,日本国内经济界充当压力团体推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这背后是日本经济界希望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的利益动机。
利益认知决定行动策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日本政府落实中日企业合作的具体机制。“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特点在于弱化政府的介入角色,强化企业的主体性,突出两国企业在第三国展开具体项目选取与合作的经济利益。日本一方面仍不愿以政府与“一带一路”签署任何官方的合作协议,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一种折中方式为本国企业搭建一个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机制平台。“第三方市场合作”被看作是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背景下,两国对“务实合作”的探索。在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下,中日两国开始为“第三方市场”制定具体实施步骤,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是在2018年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召开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但需要指出的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然会受到日本相对收益思维的掣肘,中日之间似乎对这种合作模式本身存在温度差。从合作的现实情况来看,被寄予厚望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高铁合作项目,也因为日本企业退出投标,从中日泰的“三方合作”变成了中泰的“两国合作”。(44)赵天鹏:《从“普遍竞争”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动向》,《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失为一种中日现阶段经济合作的有效路径,但仍需要稳定的中日政治关系来保驾护航。
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一带一路”认知走向
2020年8月,安倍晋三辞任日本首相后,日本政治进入“后安倍时代”。首先是菅义伟作为过渡性人物,在担任继任首相期间依旧延续了安倍时期的外交路线,特别是对美与对华政策。时隔一年之后的2021年9月,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在选举中胜出,成为第100任日本首相。虽然仍无法预判日本新政府会存续多久,但是在“后安倍时代”的背景下,日本的 “一带一路”认知在承袭安倍政府后期“竞争为主,协调为辅”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变数。
首先,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或将更加置于“印太”视域之中,强调地缘利益的相对性,进而突出“印太”的战略性而非构想性。菅义伟政府时期,日本在外交领域的重点方向可以归纳为 “印太”外交, 特别体现在 “印太”频繁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外交议程中。2021年4月16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将同盟关系的定位表述为“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并表示“深切关注中国在该地区违背国际规则的活动,包括使用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烈反对中国在东海与南海单方面破坏地区现状的行动”。(45)「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8.pdf.尽管为了规避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对于“印太”的战略敏感性,安倍晋三执政后期将“战略”替换为“构想”,但种种动向表明,日本近期似乎更加强调“印太”的战略诉求,力图发挥日本自身谋划力,极力推动非正式的“四国安全对话”向正式的“四国联盟机制”转变,并以此作为“印太”构想的主体构架,进一步加强对华战略博弈。
其次,日本将以拜登政府的“价值观与规则同盟”形成共振为前提,以美日印澳四国的群体收益为战略基础,从而扩展“印太”对“一带一路”的规范遏制。伴随“四国安全对话”时隔10年之后于2017年的再次重启,美日印澳四国之间在三年多时间里形成了定期的双边、三边与四边的互动机制,除了强调“印太”应具备“自由”“开放”之名外,还进一步冠以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包容”,以寻求四国及“印太”地区东南亚国家的价值观共性,但却是以“包容”之名,行“排他”之实。除价值观之外,四国将“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的四大标准”等设置为主要议题,矛头直接指向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在该地区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46)陈庆鸿:《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进展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6期。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首先举行了视频会议,在巩固与深化“共有价值观、基于法治的开放和自由的国际秩序、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国际海洋法、航行与空中航行自由”等规范领域达成共识。(47)「日米豪印首脳テレビ会議」,外務省,2021年3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_000939.html.之后不久,在于日本举行的美日双边外交与国防长“2+2”会议上,两国罕见指责中国“行动与地区秩序不符,在东海与南海试图用单方面改变现状”等。(48)「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2+2」)(概要)」,外務省,2021年3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st/page1_000942.html.9月24日,首次线下召开的四国领导人会议共同声明提出要建立“美日印澳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为“印太”地区“提供高标准基础设施”,并重视“对‘蓝点网络’计划(49)2019年11月4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执行总裁大卫·博吉安在于泰国曼谷举办的第35届东盟峰会系列会议“印度—太平洋商业论坛”上,提出了“蓝点网络”计划。该计划由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三方共同发起,旨在“统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参见苏浩、熊栎天:《透视“蓝点网络”计划》,《环球》2020年第2期。的继续参与。”同时还特别指出,“要支持债务可持续与责任追究在内的国际标准与公正、开发、透明的贷款惯例,要求所有债权人都要遵守这一规则”。(50)「第2回日米豪印首脳会合」,外務省,2021年9月2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38176.pdf.在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新强调美国要做“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日本以巩固西方规范性利益为前提,积极向以东盟为中心的“印太”国家扩散“共有价值”“地区规则”与“基建标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规范遏制。
最后,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将会继续基于制度协调以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在拜登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的战略回旋空间将大大受限。尽管遭受了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2020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展却逆势而上,在非金融类投资领域实现了自倡议提出以来的最大增幅,绝大多数基建项目也复工复产,“一带一路”继续彰显着自身的韧性与可持续性。(51)《“一带一路”在疫情挑战中前行》,《光明日报》2021年1月4日。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共有超过3 164个项目与“一带一路”有关,项目总估值约4万亿美元。(52)Refinitiv: BRI Connect: An Initiative in Numbers, 8 December 2020, https://www.sgpjbg.com/baogao/23668. html.面临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极大不确定性,日本政府无法实现经济层面的“去中国化”,2020年11月,日本宣布加入RCEP就是寄希望通过超大型FTA获取巨大经贸红利的最好例证。未来,在 RCEP框架下的中日经贸合作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韩自贸区的进展,以及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将是检验日本是否继续选择对华制度协调的试金石。但令日本心态愈发复杂的是,尽管拜登政府不会同特朗普政府一样在经贸问题上施行极端政策,但在利用“印太”地缘工具制衡中国方面,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相差无几,对中国采取安全与经济双重围堵的战略决心已成定局。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反建制主义政策已是过去式,但如若中美战略竞争加速升级,日本对“一带一路”或将不得改变协调性认知,很有可能延续安倍政府前期的对华制衡战略。
结 论
综上所述,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具有非常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日本十分重视在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方面的物质相对收益,以及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与国际标准方面的规范性国家利益,这使得其难以根本转变对“一带一路”固有的“竞争性”认知;另一方面,日本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也并非一味竞争,日本认识到通过制度协调获得物质的绝对收益是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日本与“一带一路”在维护全球性贸易体制、地区制度协调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存在合作的空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RCEP的签订也为日本寻求与中国在上述相关领域的协调提供了机会。
从长期来看,特别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及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国际格局之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对待“一带一路”,仍会以“竞争性”认知为主导,“协调性”认知将进一步受限。历史证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安全议题上升的情况下,日本突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加强“携美制华”的倾向会明显上升。尽管日本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客观存在,但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华的竞争战略,再加上拜登当选总统意味着美国将重拾传统的“同盟外交”,与盟友对共有“威胁”进行制衡。拜登政府设想与G7国家推出替代“一带一路”的“绿色清洁倡议”就是典型例证。(53)Bloomberg: G7 Set to Back Green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gram, June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6-01/g-7-set-to-back-green-rival-to-china-s-belt-and-road-program.不出意外,日本新政府仍将忠实地追随安倍时期的外交路线,但是孤立中国的政策是不现实的,仅靠包围相互敌对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关系出现调整,日本的战略选择将十分被动。(54)《“对抗和共生”都应是焦点》,日本《每日新闻》202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