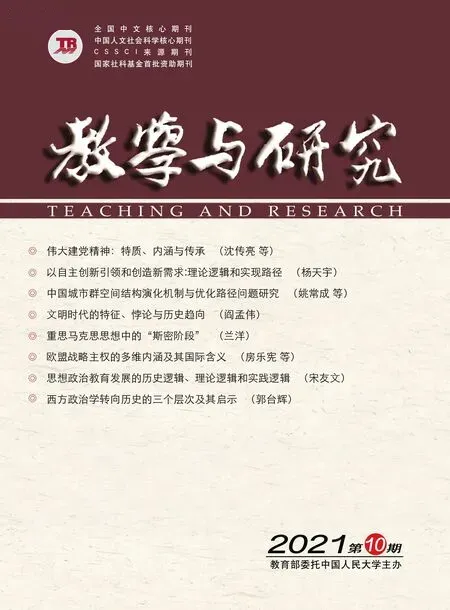现代性的超越*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启示
林 钊
犹太人的苦难固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和公元70年的圣殿焚毁,但犹太人解放之问题却完全是一个现代问题,正是启蒙运动开启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才使犹太人的被压迫变得不可忍受。解放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而“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关键却是,犹太人是同化为“人”,还是作为犹太人而获得其解放?一个文化独特、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如何在以世界主义、普遍主义、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里获得其本质存在?犹太人问题既是特殊的,又如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所说是普遍性的。它以相同的方式提给了正在奋力谋求复兴的中国人,同样是文化刚健、历史深厚、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现代政治世界里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中国人而获得解放(复兴)?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回答犹太人如何在现代社会里获得解放,反倒给出了一个“答非所问”的方案:犹太人的解放在于社会的自我解放。与其说马克思的回答“不得要领”(2)[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29页。,毋宁说他发现犹太人问题在现代性框架下是无解的。马克思方案对现代中国人的启示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充分掌握现代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辟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
一、鲍威尔的同化主义方案与马克思的回应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犹太人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隔都”生涯。隔都是强制性的种族隔离,犹太人被要求必须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居住区内,并承受税赋、婚育、就业、教育、迁徙等多方面的政策歧视。隔都于1516年起源于威尼斯,也就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发生地。莎士比亚曾借夏洛克之口说出犹太人的控诉:“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亏了本,挖苦我赚了钱,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报仇呀。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3)《莎士比亚全集》,第1卷,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31-432页。犹太人的屈辱显而易见,但对抗和复仇肯定不是弱小的犹太人的可行出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给犹太人带来了解放的曙光。法国《1791宪法》在欧洲率先赋予犹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随着拿破仑征服欧洲,隔都纷纷拆毁。即使拿破仑失败后复辟浪潮再起,犹太人和进步的自由派的平权呼声已不可阻挡。犹太人在要求平等的同时,必须面对新的问题,即平等意味着什么?
两百多年隔都生涯对犹太人的禁锢是双重的,它既加剧了基督徒对犹太人作为“异类”和“他者”的排斥,让犹太人失去了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和分享文化科学大进步的机会,又强化了犹太人“特选子民”的民族意识,使得原教旨的塔木德主义大行其道,让犹太人“自觉地”隔离于万民。外在的、内在的隔都让犹太人“成为了精神上的变态者”(4)张倩红、艾仁贵:《犹太文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现代性对犹太人的解放也是双重的,既要拆除围墙和政策的隔阂,也要卸下犹太人内在的宗教和文化上的自我防卫。在大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犹太人表现出了巨大的融入现代世界的热情。当相对保守的普鲁士在新皇帝威廉四世1840年登基后颁布大开倒车的《内阁敇令》草案,作为激进派领袖的布鲁诺·鲍威尔发起“犹太人问题”大论战,重擎启蒙大旗。鲍威尔的方案简言之就是一种同化主义、人道主义的方案,即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同化为“人”以获得平等和解放。在这里,平等和解放是同义的,就是说,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要摆脱宗教的特殊性、排他性、对抗性,而成为共同致力于普遍人类利益的同质化的人。鲍威尔既反对犹太人对基督徒的“皈依”,因为这只是让无权的犹太人变成享有特权的基督徒;也反对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让步,因为这是在鼓励新的特权,是另一种意义上对犹太隔都的重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是对普遍人性和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现代共和国的抵触和威胁。应该说,鲍威尔的立场并不讨喜,他左右开弓,两面树敌。他既支持犹太人的解放,又批评那些支持犹太解放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摆脱特权的狭隘偏见。“拥护犹太人解放的人陷入了特殊的困境,他们为反对特权而斗争,同时又赋予了犹太教不可改变、不容侵犯以及没有罪责的特权。”这些拥护者其实是最敌视犹太人的敌人,他们“还没有把犹太人的事业变成真正广为人知的事业,还没有变成一项普遍的人民的事业。”(5)同时鲍威尔也鞭笞那些歧视犹太人的基督徒,正是他们的压迫使犹太人孤立,斩断了犹太人通向真正伦理和公共生活的道路。“压迫把(犹太人的)私人德性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对自己私人事务的关心”,使他们无法感受到“普遍的人的感觉”。(6)鲍威尔自认为他拆穿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抗的实质,指出双方两千年来的相互嘲笑、讥讽、折磨,其实只是宗教牢笼里两个同样可怜的囚徒的困兽犹斗。他们都不敢成为“人”,不敢争取作为人的“自由普遍的自为本质”,却把人道主义看作“对他们的特权的冒犯”。(7)[德]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载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34、42、99、106页。所以,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需要和渴望获得解放。解放的出路便在于,让公民消灭宗教,让人权消灭特权,让国家消灭等级。鲍威尔展示了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家的意识形态:人权万岁、国家至上、民主化解民族(宗教)。
鲍威尔在大讨论中写下题为《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论文,可以说他在现代性框架中给出的方案完全是证成的。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其实也就肯定鲍威尔方案在现代性范围内的正当性。但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他把“现代犹太人如何获得解放”的问题转变为“为什么犹太人在现代无法获得解放”,问题的焦点从犹太人变为现代性,而答案则变为:犹太人只有在现代社会之外才有获得解放的可能。
鲍威尔的同化主义事实上是启蒙自由派和认可“哈斯卡拉运动”(即由门德尔松所推动的犹太启蒙运动)开明的犹太人都接受的方案。但绝非保守主义者的马克思并不赞同这个方案,他的理由独特、“怪异”,却显示了超越性的视野。概括来说,理由有三:其一,同化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冲突;其二,政治解放并不需要文化同化;其三,资产阶级社会事实上正在实施同化,但同化其实是异化。
先看第一条理由。马克思批评鲍威尔虽然大谈特谈“人”:人权、人性、人的本质等等,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人,他把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把国家对宗教的摆脱、建立世俗民主国家看作人的自由的达成,把宗教排他性的消除等同于人的普遍性的获得。马克思对鲍威尔有一个看起来有些“莫名奇妙”的嘲讽,他嘲笑大力进行宗教批判、甚至由于激烈批判宗教而被解除教职的鲍威尔为“名副其实的神学家”。(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其原因就是他无论是被称作“批判的神学家”还是“神学的批判家”,他念兹在兹都是宗教对立。鲍威尔确实说过:“如果要结束公民等级和特权以及政治等级和特权,必须消除、结束宗教偏见和宗教隔离。宗教偏见是市民偏见和政治偏见的基础……”。(9)[德]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载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34、42、99、106页。尽管鲍威尔不忘强调宗教偏见是市民偏见和政治偏见造成的,但他并没有分析后两者。对马克思来说,宗教不是现实隔阂的原因,相反,历史的、现实的隔阂才是宗教冲突的原因所在,宗教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投射。就算教徒同化为人,冲突就消失了吗?马克思阐发了那个著名的论断:人权只是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私权利的表达。市民的自由权利“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0)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只是宗教的延续。宗教把普遍性留给天国和彼岸,却把冲突性留给了现实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政治国家把普遍性留给“公民”,却把冲突性留给市民社会的成员。无论哪一种,都保留了“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11)政治解放甚至比宗教隔阂更可怕,因为它以解放之名遮蔽了社会冲突,似乎同化、扬弃了社会冲突之一的宗教就化解了社会全部的冲突。
再看第二条理由。马克思强调,“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0、27页。马克思区分了当时德国、法国、美国的犹太人状况。德国没有完成政治革命,所以依然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问题依然表现为宗教冲突;法国是君主立宪国家,算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美国是共和制国家,可算完全的政治解放。但在后两者那里,“犹太人”并没有消失。在法国,关于制定16岁以下法定休息日的法律提案里,休息日按天主教习俗定在了星期天,而没有按犹太人安息日惯例定在星期六。马克思从中再次看到政治解放的限度,如果犹太人和基督徒真的是平等的,那为什么基督徒的礼拜日会在全体法国人的法律中得到体现,而号称与基督徒平等的犹太人的安息日却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犹太人事实上还是作为“特殊者”承受着牺牲和歧视。而美国则提供了与法国相反又相同的例证。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美国,已没有了国教,没有了一种礼拜对另一种礼拜的优势,人们可以自由地信仰宗教。换言之,在美国你可以堂而皇之保留自己的犹太宗教;而事实上,美国也是犹太人最主要的移民地。法美状况相反,却共同说明特殊性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与政治国家并行不悖。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实则是同义的,政治解放不就是以宗教自由为旗帜保护公民享有(而非剥夺)多元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自由吗?
最后再看第三条理由。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一个激烈批评,是指责文中第二部分马克思表现出的“犹太人的自我憎恶”(Juedischer Selbsthass)。马克思宣称犹太人是财迷的民族,犹太人的神就是金钱,那些饱含犹太民族自尊心的批评者无法容忍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居然这样侮辱自己的民族身份。必须承认,马克思的言辞并不友善,这正是他青年时期写作风格的典型表现。但还要注意到,“Judentum”一词在德语中既指商贩,又指犹太主义。马克思批评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辩护者也一再强调马克思“憎恶的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家。”(14)[美]威廉·布朗沙尔:《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载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与鲍威尔纠结于犹太人与基督徒无法同化为无神论的公民不同,马克思看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正在事实上制造着同化,它把欧洲人都同化为了Jude(犹太人),或曰商人。政治解放释放了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以利己主义为根本原则,既然反犹主义者都把犹太精神贬斥为唯利是图,那马克思略带反讽地宣布: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犹太人”的社会,一个“犹太精神”实现普遍统治的社会。这里所谓的“犹太精神”早已不是摩西五经和塔木德的信仰,而是现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经商牟利的热情和欲望。在马克思的语境里,那个被反犹主义鄙视的“犹太精神”就是现代性。桑巴特回应了这一说法:“犹太人和统治者并肩走过历史学家所谓的现代。对我来说,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兴起的象征,继而是现代国家兴起的象征。”(15)[德]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页。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所有拥有古老传统的民族都不得不面对以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的洗礼。马克思预先宣告了后来被尼采称为“虚无主义”、被韦伯称为“祛魅”的世界命运,那就是“伟大、严肃、崇高的东西越来越让位于平俗、日常、无精打采的东西”。(16)刘森林:《物与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所有传统的、超验的、神圣的价值都在坍塌,人们被世俗化、庸俗化为利己的商人——即使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也是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人们被普遍同化为商人,也意味着人的异化的普遍化,人与伦理自由所要求的普遍交往、与类生活之间的疏离反而加剧。鲍威尔的理想实现了一半,即宗教对抗消除了,但和平并没有到来。金钱的普遍性扬弃了宗教,却把宗教生活中的排他性、封闭性转移到世俗生活中来,把民族间的对抗和战争延伸到每个人之间。当马克思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他清楚表达的是,不超越现代性,就没有实质的自由和整全的解放。
二、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和文化的
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对同化主义的批判只在少数犹太知识分子和激进青年中产生影响,同化主义事实上仍然是19世纪犹太解放运动的主流。以启蒙理想为主旋律的1848年欧洲大革命延续了1789年开始的犹太人解放进程,一方面,资本主义迎来了狂飙突进的黄金年代,另一方面,欧洲社会的主流朝着统一、民主、开明、融合的方向继续迈进。被赋予公民权的犹太人抱着同化融合的美好理想进入公共生活,他们热情参军保卫国家,凭借天赋在自由的商业、工业、金融业中收益丰厚,欣然接受异族通婚,大量进入公开的中学和大学学习且成绩优异,还有不少人积极从政甚至进入国家内阁。按照研究者的考察,“欧洲犹太人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接连胜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18)张倩红、艾仁贵:《犹太文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曾经争论不休的犹太人解放之问题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的议题。
本次收集的所有数据录入到SPSS21.0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用b±c表示记录资料,采用t检验组间比较,用m(%)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组间比较。
然而,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打破了犹太人同化的美梦。法国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在明显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被裁判为间谍罪,比审判不公更让犹太人惊慌不已的是法国人群情激昂的“犹太人该死”的呼声。该事件发生在犹太人最早实现政治解放的法国,发生在人权宣言发表一百年后,而且当事人德雷福斯甚至愿意以反犹主义的姿态来谋求同化。这正印证了半个世纪前马克思的判断:政治解放的同化主义方案无法实现犹太人解放。阿伦特也是这个看法,她说:“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世俗化和消失。”(19)阿伦特详细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她注意到反犹主义是极权主义源起的一部分,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为犹太人正是作为市侩、富有的暴发户阶级而受到普通民众的厌恶和憎恨,他们“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20)[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42、38页。可见,现代性确实没有化解种族主义,相反,种族歧视却由于不断加剧的阶级敌对而愈加深化。
作为反犹主义的反动,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犹太复国主义可追溯到马克思青年好友摩西·赫斯。赫斯于1862年写作《罗马与耶路撒冷》,他认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或可摧毁犹太宗教,但无法消解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在这本书里他重申了20年前青年马克思的洞见,即同化主义的现代性解放方案绝非犹太人的真正出路,但又为犹太人问题增添了马克思绝不会认可的民族主义。“如果犹太人解放于流亡与犹太人的民族性确实不可兼容,那么犹太人有义务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21)Moses Hess,Rome and Jerusalem,A Study in Jewish Nationalism, Dover Publications, 1988, p.31.赫斯认为社会主义才是犹太人解放之道,但他的犹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影响甚微。而他反对“解放于流亡”,便是强调犹太人的解放必须是返乡复国,这一主张在犹太解放运动中反响巨大,赫斯由此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在赫斯之后,犹太复国主义从理想走向实践,其中两大主流是政治复国主义和文化复国主义。政治复国主义以西奥多·赫茨尔为代表。赫茨尔是记者出身,深受德雷福斯事件的刺激,写下《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尝试》一书。他直言不流血的压迫无处不在,同化主义没有出路,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即使它有时采取诸如此类的形式。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民族问题。”(22)[奥]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肖宪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页。既然犹太人在世居的土地上仍被当作外国人,既然强权仍凌驾于公理之上,那么犹太人的出路就只有一条:为犹太民族寻找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工业化的、富裕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为此,他多方奔走,既向罗斯柴尔德等犹太富商呼吁,又向英德等欧洲列强求助,还和土耳其、埃及斡旋谈判,先后提出过“阿根廷方案”“乌干达方案”等计划,最终确定,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才能重建以色列国。文化复国主义以阿哈德·哈姆为代表。阿哈德·哈姆出生于正统犹太教家庭,深受正统犹太文化影响。在他看来,政治复国主义虽然把复国梦推到实践阶段,但它忽视了犹太文化的基本问题。让犹太人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反犹主义,而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犹太精神自身的动摇。他批评赫茨尔道路带来了“去犹太化”的危险:“因为赫茨尔设想的正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先进和文明的国家,那里虽然住着犹太人,但不是具有犹太人特征的国家。”(23)[美]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芳、阎瑞松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165页。从文化复国主义角度说,犹太国的复兴首先要完成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如果犹太人接受了现代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把自己的传统当成要医治的疾病,如果犹太人都自愿割舍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核,纵使拥有了耶路撒冷,也永远告别了以色列。
政治复国主义和文化复国主义各执一端,各有道理,也各有难以克服的弊端。政治复国主义无疑更具现实性,它让流散两千年的犹太人意识到,他们应该也可能拥有自己的政治实体。列奥·施特劳斯就很赞赏赫茨尔这一点,他说:“赫茨尔的天才在于将犹太民族政治化。”(24)[美]列奥·施特劳斯:《犹太哲人与启蒙》,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85页。没有独立、强大的政治主权,犹太人立足于现代民族之林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们无法反抗歧视、排挤和迫害,更不用去奢谈权利和解放。这是后来的历史向犹太人一再证明的事实:正是依靠一次又一次取得中东战争的胜利,在弹丸之地立身的以色列从二战中被屠杀的可怜人一举转变为受世人瞩目的“大国”。政治复国主义遭受的批评则在于,它勾画的图景既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唯独不是犹太主义的,它让犹太民族现代化,却也让犹太国成为了万国之一。如果说反犹主义厌恶的是犹太人的格格不入,那么从反—反犹太主义出发的政治复国主义却实现反犹主义:那个“特选民族”终于同化得和所有民族一样了。
文化复国主义对民族的本质存在的认识比政治复国主义更深刻,它捕捉到的现代性危机也比后者更深远:犹太人问题不在政治危机而在文化危机。它试图重建的不是犹太人的政治实体而是精神实体。在这里,犹太人的解放不是谋求平等,而是对犹太性的保持和传承。这种主张也吸引了马丁·布伯、约瑟夫·布伦纳等一代犹太思想巨匠。然而,文化复国主义试图在政治解放的大潮中去政治化,无疑是逆流而动,它对物质生活仿佛视而不见的强烈的唯灵论色彩也使之失于浪漫空想。更致命的是,它还是无法化解现代性框架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背离,重拾自信的犹太人依然在以对抗的姿态面对基督徒和穆斯林。其实可以说,文化复国主义和政治复国主义一样,都是反犹主义镜子照出的另一个倒像。
我们无意在此详细比较政治复国主义和文化复国主义的利弊,它们也并非只有争论而无融合。后来魏兹曼正是合两方所长促成以色列1948年复国。但是,以色列的重生不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曾以“犹太精神”来指代市民社会精神,并指出犹太人——以及所有人的真正的解放在于超越市民社会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但是,犹太复国只是战争的开始,犹太人的命运被复刻了,只不过这一次基督徒换成了犹太人,被驱逐和流散的换成了巴勒斯坦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换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犹太人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变得强大,但马克思所要求的人的解放,人的普遍性的实现,即人能够“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的那种状态,依旧遥遥无期。
三、从“犹太人问题”到“中国人的解放”
重思犹太人问题,要旨终在“中国人的解放”。这里所谓“中国人的解放”,不仅指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而且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的根本内涵是中国人获得自身的本质规定,中国人作为中国人而实现自身的本质存在。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多有不同,但二者的现代遭遇却有一定相近之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命运多舛,在同一性的现代性浪潮中坎坷寻求解放和复兴。犹太民族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先贤马克思对同化主义的批判教诲,最终以复国主义的方式成为被现代性所捕获的民族国家之一。作为马克思的精神的传人,现代中国人需要记取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答非所问”所开启的新视野,需要比犹太人的复国之路走得更远。一言以蔽之,现代中国人的解放,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既是对现代性的把握与实现,又是对现代性的扬弃与超越。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同化主义、政治复国主义、文化复国主义等方案,都可以在“全盘西化”“富国强兵”“中体西用”等口号中找到它的中国版本。于五四运动百年后回看,作为被资本主义侵轧后的应激性反应,五四运动中所谓“救亡与启蒙”的分歧并未走出对现代性的简单复刻,无论哪一条似乎都无法达成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之解放,如同张志扬先生所论:“归根结底‘救亡—启蒙’就是把中国从传统中拔出来转向西方道路指示的‘现代性’。不转向,中国亡;转向,中国同样亡,即同化尾随于西方——名存实亡。”(26)萌萌学术工作室编:《“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三联书店,2011年,前言第4页。在“救亡—启蒙”的现代性叙事里,“中国人”消失了。
对于20世纪初中国激进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对甲午失利后的国家衰败,深感器物落后的实质是这个古老民族在政制、伦理、文化等方面与世界潮流的格格不入。他们看到国人的落后与麻木时的心情,与最早的犹太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面对“隔都”时的焦虑颇有相通。从梁启超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大批现代派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要求兴办洋务、变法革制,也主张批孔反儒、更新文化,从伦理道德甚至语言文字都全面西化。同化主义成为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人的普遍期待。他们写了大量比较中西文明的长篇短论,其要旨都是将“中国”看作中国人解放的最大障碍。这种同化主义方案的前景可在后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得以窥见:“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27)蔡乐苏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0页。这种担忧与犹太的文化复国主义的论调亦如出一辙。
当1918年一战落幕,中国现代派知识分子的同化主义美梦破产,作为榜样的欧洲并没有实现“同化”,在现代文明圈外的中国也没有被平等接纳。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的“双轮”(“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必然通向幸福,标榜和平、平等的自由主义民主革命没有消除民族争斗,素被推崇的工业革命又带来了更惨烈的杀戮。另一方面,欧美民族国家內部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并没有扩及西方文明以外的民族,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仍然以殖民主义霸权为原则。于是乎,在中国启蒙派这里,先有陈独秀看到中国在“巴黎和会”被耍弄,悲愤于“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幻灭,痛言“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28)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0-91页。陈独秀之悲愤,与赫茨尔惊恐于德雷福斯遭遇正有几分相似,而他不得不接受的“公理”面具下尽是“强权”的觉悟也正是青年马克思对人权的剖析。再有梁启超西游战后欧陆,看到曾经艳羡的繁华欧洲而今满目疮痍,开始理解西人对现代化的反省:“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29)继而重新审视进化论、个人主义、科学主义这些西方现代性核心原则的限度和负面。梁启超也不再将中国文化视作中国进入新文明的障碍,而强调“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49页。当梁启超呼吁化合新文明时,他回到了民族传统,发觉中国古老的天下主义中已经暗含了“全人类大团结”的理想,蕴藏着超越对抗性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由此不难理解欧游回国的梁启超从西方现代性的热烈追慕者扭头变为先秦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并一再指出接受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的新天下主义才是中国人解放之道。梁启超大概不知道马克思的犹太人之论,但新天下主义与马克思所言的“类存在”或“人的解放”至少在理论方向上是一致的。
于新文化运动未散去的喧嚣声中,中国共产党呱呱坠地。五四运动就其历史性意义而言,最终使中国从现代启蒙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从此发生了本质性转变:以救亡应对帝国主义,以启蒙应对封建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应对“中国人的解放”。如何理解这个“新中国”,毛泽东做出了精准的阐释:“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1)如何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强调,必须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71页。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的论述里,新中国,也即中国人真正的解放,既要完成建立民族国家和思想启蒙的现代性任务,也要在社会主义革命里完成超越现代性的任务。只有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才能完成特定民族的解放,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者的指示,也是同为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马克思对自己两个母国的提醒。马克思既要求犹太人摆脱现代利己主义商业精神,也警告德国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马克思确实描绘过东方从属于西方、“野蛮”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的历史图景,但那只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4)而绝非历史的终结形态或唯一形态。相反,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后,特定民族才能获得解放。“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50页。遗憾的是,他的两个母国都遗忘了他的告诫,德国人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开始迎来复兴,却最终遭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犹太人复建“新以色列”,却同样陷入半个多世纪的民族战争。
“新犹太国”不是“新中国”的好榜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基于狭隘现代性的“解放”之路正是中国人要避免重蹈的覆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承担着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中国绝不是对英美德等帝国主义的复刻,而是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36)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当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化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那正是马克思期待的普遍的人的解放在一种中国式方案中得到开显,在这里,中国人的解放和人的解放达成了最终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