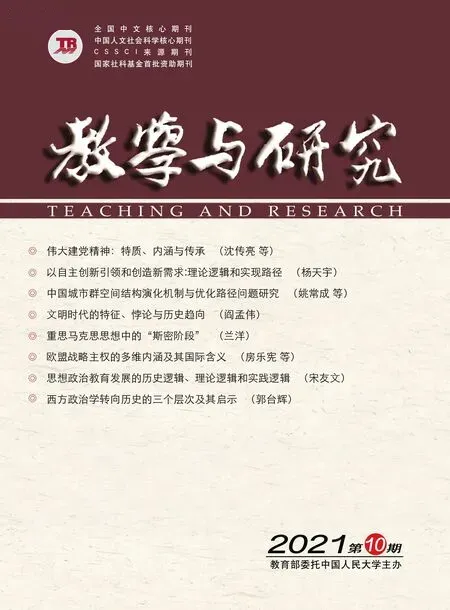西方政治学转向历史的三个层次及其启示*
郭台辉
恰逢新时代提倡“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参见《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社会科学界对此积极响应,形成一股“转向历史”的潮流。社会学界“初兴”历史社会学,法学界“复兴”历史法学,(2)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 《学海》2018年第3期;许章润:《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而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尝试发展“历史政治学”。(3)徐勇、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张树平:《改变生活的政治与改变政治的生活:一种历史政治学分析》,《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杨光斌:《以中国作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同时,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要求政治学供给新的知识产品,包括新思维、新概念、新话语、新视野,而中国政治学人也开始意识到,充分挖掘自身传统的知识资源与本土经验,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滋养。长期以来,虽然中国政治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建制化形式,但总体上依赖于苏联与美国两大相对峙的政治学科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因此,中国政治学在新时代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对苏联阶级中心论与美国行为中心论两种外来话语体系的长期依赖,力图发展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走出抛弃历史意识的美国政治科学阴霾,重新接上政治学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的学科传统,回到中国自身。转向历史是政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立足于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历史反思,关注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结合方式,归纳出三种层次性的关系及其缺憾,并基此提出对于中国政治学转向历史的几点启示。第一种结合方式是把历史视为方法,历史研究为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更丰富的论证材料,这种实证主义的理解遭到来自阐释学传统的批判;第二种结合方式把历史作为一种意识、认知和思维,政治学的研究议题置于历史过程的具体阐释,对政治学理论、概念与命题的知识生产施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性条件,但带来知识碎片化和历史想象力的诟病;第三种结合方式是把历史视为本体的存在,而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是论证普遍历史进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或手段,这恰恰为世俗化的后形而上学传统所抛弃。我们尝试发展历史政治学,需要合理定位历史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联机制,尤其需要为第三种理解提供中华文明连续统一的历史观念,使之成为前两种结合方式的前提假设与哲学基础。
一、历史作为方法
在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上理解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结合,意味着历史研究为论证材料之“用”,服务于政治学研究之“本”,旨在探索与发现在现实政治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概念、理论、命题等知识范畴。把历史研究视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始于19世纪前期由孔德奠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但正式进入现代西方政治学学科的方法范畴,却源于二战后一部分学者不满结构—功能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因此,从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来理解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结合,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把历史视为经验事实的文献材料,可以直接或间接拿来论证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基本命题、因果规律和法则;其二,政治学与社会学和经济学一样,成为实证社会科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对应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划分政治、社会、经济领域,而政治学的任务是探索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领域,解释当下国家正在运行的政治现象与规律。但这两个前提条件并非同时发生,各有不同的形成时间与方式。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之所以“体”“用”结合,得益于一部分政治学者不满政治科学的既定研究状况而转向历史方法,为当代政治学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同时打开政治研究的历史视野。
其中,历史研究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得益于两个基础。其一是哲学基础。笛卡尔开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之先河,他不满于传统的历史研究,(4)[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页。认为历史材料需要有利于当下知识生产的论证,因当下问题的解决而探讨过去,即“以古观今”是为了达到“以今观古”的现实主义目的。同时,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叙述应该言之有据,经得起怀疑、考证和批判。这被柯林伍德称为“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5)[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0-64页。并成为19世纪德国史学“兰克学派”的哲学依据,把编纂与整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料视为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其二是社会科学基础。孔德在笛卡尔基础上,进一步把历史与观察、实验、比较并置为科学研究方法,旨在通过过去发生的里氏事件来检验当下的结果,“对人类不同状态的历史比较,不仅是新兴政治哲学的手段,也是这门科学的真正基础”(6)Auguste Comte,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Vol.II), translated by Harriet Martineau, Bell,1896, p. 251.,因此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最本质、最广泛的证据。结果,消除其唯心主义影响的德国“兰克学派”迅速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在法国发展成为“实证史学派”以及后来的“历史学方法论派”,并且到19世纪后期的涂尔干时代,史料编纂的历史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发现“社会事实”的主要场域与论证材料来源。(7)“史学方法论派”的代表作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历史研究导论》,李思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史学方法论派可谓是“半吊子”的兰克学派,只接受兰克主张对政治史和档案材料的精确与客观考证,但抛弃其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从此,以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剔除“历史学家部落的三个偶像”(8)即“政治偶像”、“个人偶像”、“编年史偶像”,参见英文版Francois Simiand, “Historical Method and SocialScienc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985,9(2):163-213.为标志,奠定了历史研究为“用”、社会科学为“体”的结合关系结构。
然而,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三门学科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来说,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更晚接受历史方法。尽管政治学有着漫长的学科史传统,但在近代之后一直与道德哲学、神学、经济学等纠结在一起,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出美国政治科学之后,才独立建制为一门现代学科。但历史成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抵制美国以功能论和系统论为主导范式的政治科学。美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的历史转型期之后,政治与社会开始进入常态化和平稳期,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分道扬镳,研究重心从制度转向行为、历史转向当下、共和转向自由、集体转向个体,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意识形态假设从美国“例外论”转向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化”,而进化论、结构论与功能论成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框架。全新的政治科学全然关注当下政治过程与生活,尤其是选举与投票的政治行为与心理,采用问卷调查、定量和数理模型化的实证分析,寻找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硬科学”规律。这成为战后世界各国政治学发展的主流范式。同时战后兴盛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与社会史,把社会科学关注的生活领域诸多议题带入历史领域,也催生了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跨学科潮流。到60年代后期之后,这些历史转向逐渐上升到政治领域,从而使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如国家、政府、民族、战争回归其历史变迁的过程意识。虽然主流的政治科学依然强劲地追求数理模型和理性选择,但一批非主流的社会学家率先以“历史社会学”为名,在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上行使“历史政治学”之实,复兴19世纪政治研究传统的关键议题。
在这个时期,历史社会学与历史政治学之所以难分伯仲,在于两个原因。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学研究过于局限于微观行为与“中层理论”,而宏观领域及其变迁禁锢在进化论、系统论和结构—功能论等静止的经验主义或宏大抽象理论,不关注动态的、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变迁问题。同样,政治科学的宏观思维与问题也受制于结构化的政治系统论与稳定的控制论,全然抛弃19世纪之前政治学研究关注的军事、国家、民族、制度、帝国、阶级、反叛与革命等广泛议题。因此,一批充满反叛精神的社会学家如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斯考切波重新启用19世纪之前的政治知识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传统的现代性问题,结合到史学界的比较历史方法,尤其是吸收“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并集中于“历史社会学”的头衔。然而,社会学转向历史的浪潮并没有影响到政治科学,后者继续追随经济学的定量与数理结构模型,只有极少例外,比如政治学者西德尼·塔罗与裴宜理早年受到查尔斯·蒂利的影响,前者终生关注抗争政治,后者始终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反叛与革命,而李普塞特则是当时较少关注历史与社会冲突的知名政治学家。同时,一大批“左翼”与比较史的史学家参与推动这股跨学科的研究浪潮,比如汤普森、艾森斯塔特、本迪克斯等,他们走出“兰克学派”的编纂史学路径,主动要求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化、结构化与理论化思维。因此,当今政治学需要寻找那段时期转向历史方法的知识资源,进而接驳在19世纪之前的学科传统,必须关注相邻学科的学术史,尤其是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亲密结合。
在这段时期,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们主要是坚持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把历史视为一种研究方法,用来收集和整理经验材料,以论证不同于主流范式的理论解释。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巴林顿·摩尔等人虽然反对线性进化论假设,但依然集中“现代化”主旋律,重新探讨19世纪经典作家关注的现代性议题,关注传统至现代的断裂与转型;其二,他们充分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围绕冲突与变迁的重要政治议题,进行跨时间、跨空间与跨语言情境的大范围比较,试图为大转型提供结构主义的合理解释,或者重新解释宏大历史的帝国与文明过程(艾森斯塔特),或者分析具体主题的因果关系机制(如斯考切波比较社会革命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其三,很少像查尔斯·蒂利对待《旺代》那样,既充当历史学家,亲自收集充分的一手档案史料,又扮演社会学家,对数据统计进行量化分析,对具体研究的问题提供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更多的社会学家宽容二手历史文献,直接运用本土历史学家整理的历史数据,甚至利用翻译的二手历史文献,进行历史案例比较的定性研究(如斯考切波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或者对财政、经济、人口等“硬”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如格尔斯通关于近代世界五大帝国的人口增长与帝国转型关系),进一步宏观比较、理论提炼和因果关系分析。
对于转向历史的政治学来说,从作为方法来理解历史,在研究实践上最容易操作。编纂史学大多是政治史文献,重大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史料相当丰富,都是关注政治学基本命题在具体历史情境的细节变化。社会科学家在确立研究议题之后,大量收集历史学家关于该时段的相关文献,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与结构化思维,创新相关理论或概念,并提炼为合理的命题或解释模式。然而,历史作为方法的政治学也最容易遭到诟病。其中,这种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研究,需要经受来自史学的批评,比如柯林伍德批评这是“剪刀加浆糊”,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史料派理解的历史可能丧失历史个体的生命体和主体性,况且这种唯政治史的历史掩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多面性与复杂性。因此,转向历史方法的社会科学普遍得不到史学界的认可。同时,主张历史方法的政治学往往以超历史的理论问题先入为主,试图发现一个所谓外在于历史自身的非历史命题。从实证主义的“硬科学”标准来说,运用历史材料所佐证的社会科学命题没有重复性,无法在不同时空中得到科学检验。因此,他们难以进入到那些运用当下数据并追求普遍解释力的主流社会科学视野,只能挤压于历史特殊性与理论普遍性的夹缝之间。结果,转向历史方法的政治学研究如果不是被政治学的主流范式所抛弃,就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严格遵循主流学科传统的标准建制,成为其中一个独特的子学科或研究领域,自娱自乐,自谋发展。
二、历史作为认知
在认知层次的历史研究看来,历史不能仅仅看成是发生在过去的各种痕迹,随意用来作为论证材料。相反,历史有其本质的规定性,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唯一具体性,不可复制,必须严格遵循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安排;其二,历史过程充满偶然性与复杂性,并没有超越时间次序和历史情境的命题、概念、理论和普遍发展规律;其三,历史上的人物、制度、事件及其发生过程都是整体涌现的,并且同时在各领域、各层次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造成不同后果。这意味着,历史整体是被人为划分并建构为局部不同的领域史,而再现真实的历史需要一个整体的历史意识和具体的关联机制。相应地,在历史认知层次上来理解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其任务有三:其一,政治学的所有概念、理论、命题必须受制于时间次序与历史情境的条件约束;其二,政治学当下关注的任何议题与问题都必须有其历史形成和路径依赖的意识,现实的政治生活与制度带有历史痕迹,是历史过程渐变或突变的延续或结果;其三,政治学转向历史,其任务不仅是阐释与分析历史过程中的关键发生机制,而且需要关注推动其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以及结合机制。换言之,历史认知层次理解的政治学转向历史是在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双方都需要同时反思,之后的再结合才得以可能。
在当代西方学术史上,认知层次的历史研究是在反思与批判方法层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突出贡献是充分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而这恰恰是最大的缺憾。斯考切波为了有利于结构化变量的比较,把三个国家的革命发生置于同一个时间序列过程,忽视其处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还把阶级和国家抽离其具体文化场景,忽视不同历史过程的复杂情境。这是为了理论的普遍性而有意忽视历史的特殊性。(9)John H.Goldthorpe,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1,42(2):211-230.同时,编纂史学的正统历史研究主要围绕历史人物和事件而叙事,而社会科学是以分析性的语言展示社会结构与因果规律。转向历史方法的社会科学为了达到理论建构的目的,只能人为裁剪历史材料,运用社会科学“讲道理”的语言替代并重组历史学“讲故事”的语言,这既违背历史重现的真实性,又不符合社会科学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标准。历史研究必须“按其真实发生的方式来叙述的历史”(10)C.Camic,“The Utilitarians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85(3):516-550.,因此,“真实发生”(时间次序)与“叙述”(叙事语言)构成为社会科学转向历史时必须面对的两个前提条件,相应也迫使“政治学转向历史”之“历史”从历史方法层次上升到历史认知层次,之“政治学”能接受叙事语言的表现方式。
因此,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既反思实证社会科学自身的“硬科学”范畴,又充分吸收历史学的传统特征,超越历史方法的层次,把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在认知上结合在一起,并且充分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语言上采取分析性叙事,性质上以过程阐释取代因果解释,严格遵循时间的先后次序来理解历史;时间序列上遵从历史原本真实发生的起因与结果;重视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过程的整体涌现性与后果的不可预料性。用历史学家小威廉·H·休厄尔(William Sewell)的话来说,是用具体历史中“充满事件的时间”取代宏大理论导向的“目的论时间”和实验观察思维导向的“实验时间”。(11)William H.Sewell Jr,“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2,98(1):1-29.这意味着社会科学从“硬科学”到“软科学”、解释到阐释的让步,不仅在认知上接纳历史研究,而且也解放了社会科学自身。阐释型社会科学追求受历史情境条件限制的“弱结构”或“弱逻辑”,使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更容易结合,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从此走出了僵化的比较历史分析和教条式的结构分析、因果解释和普遍法则。社会生活领域涉及的几乎所有议题,从微观到宏观领域,如疾病、卫生、福利、身份认同、社会网络,甚至气候变迁和艺术绘画等都纷纷转向各自的历史过程,并且都可以在现代性框架下得以解释,完全模糊了现代主流学科建制的清晰边界。
当然,在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潮流中,政治学学科比较滞后,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追捧经济学,以“理性人”为研究假设,建构“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等高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模型,以“历史的终结”为口号,自信或自傲地关闭历史的面向。但苏东剧变并没有带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所想象的价值观全球化,反而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历史研究的“春天”。然而,政治科学即使转向历史,也存在三种明显缺陷。其一是“历史即研究往事”,为政治史中的特定结果提供经验性的因果解释;其二是“历史是收集例证性的材料”以证明普遍命题;其三“历史是产生案例的场所”,利用小样本展示大命题。(12)[美]保尔·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黎汉基、黄佩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页。这三种或经验性或策略性的历史转向,只是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主”“仆”关系的结合。相反,如果真正重视历史时间,政治学不仅要弱化命题的普遍解释力和概念的普遍适用性,还要完全受制于历史条件限制,尤其是时间次序和时间变化的节奏及其对政治结构、行动、过程、议题等的决定性机制。对于规范研究的政治理论来说,当代政治学领域诸多解释性概念,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人权,形成规范价值的一套“组合拳”,却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价值预设。惟有回到原初历史场景的“毛坯”生产场域及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期待,并且展示其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或缓慢或迅速上升到普遍命题的形成机制,才能揭示自由主义普遍世界的“幻觉”。(13)[英]雷蒙德·戈伊斯:《政治中的历史与幻觉》,黎汉基、黄佩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导论部分。换言之,从一个据于历史和社会的事实描述性概念,上升到一个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价值规范性概念,或者从一个普遍的价值预设回溯其历史场景,清晰展示其历史形成脉络,这是政治学在历史认知层次转向历史的重要标志。
对于经验研究的政治科学来说,政治学转向历史主要是突出时间维度,把时间作为影响政治结构、制度与行为的关键要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从行动中心论转到制度中心论,进一步强调制度设计的偶然性及其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并且在时间次序中展示因果关系的社会机制。制度领域把分析层次定位在中观层次,既不同于宏观层次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单位,也异于微观层次的行动领域,但却可以同时兼顾并打通宏观—微观之间的壁垒。因此,“历史制度主义”是政治科学转向历史在历史认知层次的最好代名词。历史制度主义可以重新关注曾受诟病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并广泛运用于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国家形成与构建等领域,把大结构、长波段、理性选择理论、因果推论以及普遍理论等,糅合原本对立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在于历史制度主义强化时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路径依赖”,运用中层理论的社会机制,重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在同一时空过程中的因果关联性,强调历史语境条件对结构与行动及其所形成的理论和命题的限制性;另一方面表现为“路径偶然”,突出关键事件、关键节点以及关键性要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使历史认知层次的时间次序作为关键变量,落实到政治科学的具体操作中。
的确,社会科学意识到历史认知层次的重要性,并高度重视时间意识,具体落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主题,使社会科学突破了实证主义的范畴,历史也从方法层次中解放出来。这种“双重解放”使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相融共生,彼此结合在传统主流学科之间获得自我发展的生命力。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乎所有议题都可以转向自身的历史,而时间意识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找到独特的应有位置,从而使过去与当下、特殊与普遍、微观与宏观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动态联系。
然而,在历史认知层次上理解的政治学研究也面临问题。其一是知识碎片化问题。不同领域不同主题都以自己的方式纷纷转向各自的历史时,必然形成不同的历史形成路径,产生多元化的时间意识,由此确定斑驳琉璃的政治理解、历史阐释以及因果关系机制,所生产的政治学知识或历史知识不仅缺乏共识,而且导致专业知识的碎片化和再“部落化”(14)参见[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其二是历史成为想象。当社会科学几乎所有议题都转向历史时,历史就成为反思现实的一种感知,社会科学失去其追求普遍理论的“初心”与“使命”,受制于历史经验约束的社会科学知识成为“地方性知识”,既无法解释宏观大结构变迁,也无法建构超时空的宏大理论。其三,打破传统主流学科的霸权地位。当所有研究议题有着时间意识,相应也找到自身的历史合法性,无须从母体学科寻找知识资源的支持,也不为母体学科增强解释力和知识创造力,传统主流学科难以有新的生命力。简言之,政治学从认知层次上转向历史,既缺乏普遍历史的基础性支撑,又作为政治学传统学科体系的离心力,带来研究议题的泛化与知识构建的主观化。
三、历史作为本体
历史本体论是对历史意识与观念的普遍假设,假定历史整体作为一种生命体,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一种本质、普遍的统一关联机制,任何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现象甚至自然现象都源于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普遍历史规律。因此,所有因学科建制而分化的知识探索与建构只是学术分工的不同,而且是具体、局部地“窥探”历史整体,旨在证成或展示某种历史观念的自洽性、普遍性与规律性,反过来,历史成为“上帝之手”,为具体、差异、个体、局部、片面的知识探索与理性建构奠定统一的普遍基础。显然,历史本体层次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恰恰是历史方法层次上的关系“倒转”,即以历史研究为“本”,政治学研究为“用”。惟有在历史本体层次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和基本导向,后者才能具有统一的研究指南与明确方向,即使诸多研究之间可能主题迥然不同,或方法千差万别,但都殊路同归,指向历史普遍意识的发现与证成,看似碎片化的知识背后恰恰有统一假定的结构性基础。历史的本体层次可以在历史认知层次为学科建制的知识壁垒找到历史观念的普遍共识,避免走向知识的相对主义与历史的虚无主义。然而,历史研究分歧最严重的层次恰恰是历史的本体论问题。因为这种“何为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处于历史观念领域的最高层次,属于人之理性不能把握的信仰范畴,却是知识建构与理性论证之先验预设。虽然西方社会科学有五种时间性的理解(15)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但西方的历史观念传统主要是循环论与进步论两种竞争性的历史本体论假设,各自对政治学研究的历史本体论有着决然不同的影响。
历史循环论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近代的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至现代的斯宾格勒与汤因比,都把人类文明视为生命周期循环的兴衰历史。修昔底德从人性不变的假设出发,认为所有外在社会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是内在人性的反映,因此历史必然周而复始地循环发展。这为古希腊史学奠定观念基础,与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政体循环论相一致,即君主专制—民主选举—贵族共和之间的政体更替成为历史循环式变迁的决定性机制,而历史研究以“实用”为目的:“假如我们从历史中移除掉何以、如何以及为何每件事会被进行,以及这结果是否我们可以合理期待,那我们所剩下的不过是描写技巧的单纯展现,而非道德教训;这些技巧虽然可以暂时讨好读者,但对未来却没有永恒的价值”。(16)[古希腊]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
到近代之后,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复兴古希腊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从人性不变的假设出发,把人类历史视为政治史,并从政治经验领域总结出对当下现实有直接效用的历史教训。马基雅维利把追求专制政体的《君主论》视为其追求共和政体的《论李维》的手段。这种“实用主义”主导的历史循环观念传统在孟德斯鸠关注治国艺术的《罗马帝国兴衰原因》和《论法的精神》中有充分体现。当然,不同的是,以往的历史循环论归结为政体的循环与兴衰,但孟德斯鸠把外在于制度的气候、环境、文化等因素都纳入历史进程的因果联系,从而突破政治史对人类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后来的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则从文明史比较的更大视野来强调历史循环论,试图以悲观笔调来超越乐观自信的进化论。
孟德斯鸠重视经验分析,延续古希腊至马基雅维利的经验—实用历史观念传统,为现实政治的君主制国家提供治国艺术,旨在发现政治与道德领域共同的正义标准及其制度落实。这意味着孟德斯鸠不仅仅停留在特定语境条件的实用主义史观,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范畴,探讨推动历史变迁与社会运转的“原因之原因”,即更为稳定的普遍法则。为此,涂尔干把孟德斯鸠视为社会科学的先驱。这恰恰是遵循培根开创的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认为历史材料是逐步提炼客观知识的基础,而知识“金字塔”顶端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普遍法则,通过“一列通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17)[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由特殊和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升到普遍的规范哲学。从此,自然法的理性主义与感性现实的经验主义两种哲学传统达成统一,与其说终结了古希腊以来据于实用主义原则的政治史,不如说历史循环论在18世纪之后受制于历史进步论。19世纪兰克的贡献恰恰是开创性地把政治史契合到德国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预设。一方面他主张完全据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官方文件,考辨各种客观经验“直观”的一手档案史料,另一方面视之为通向普遍历史的“直觉”基础,试图发现背后“上帝之手”的普遍历史进程。
当然,进步论在近代西方之后成为一种强劲的历史观念,恰恰是始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上帝神学假设。近代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把人的理性精神抬高到上帝位置,确立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但中世纪的共相/殊相、人/自然等二分法假设依然有效,只是表现为历史进化论、发展主义、现代化等方式。奥古斯丁确立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信仰体系,把“圣父”“圣子”“圣灵”视为“三位一体”不同“位格”的整体,(18)[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统一解释永恒上帝与普遍历史的存在,形成神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假设,共同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普遍进程。然而,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三“位格”对世界、上帝、历史的解释出现分歧,逐渐形成理性神、自然神、意志神三种世俗化的神学假设,奠定近代西方不同的历史哲学传统,尤其是从意大利维柯到德国赫尔德以降的历史主义传统和法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虽然英国并没有明确提出经验主义的历史哲学,却依然坚持普遍历史进步的普遍假设。“对诸如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本性以及人与认识对象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给出或假设了确定的回答”,(19)[美]艾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张卜天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年,第18页。从而形成三种新的形而上学传统和“现代性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指出:“一切历史哲学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神学”。(20)[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4页。
当然,历史本体论假设在近代西方由进化论取代循环论,三种世俗化的神学假设以科学与理性精神之名义,实现上帝的普遍意志。不同的是,培根的经验哲学与实验科学方法把人、自然、历史、社会纳入自然神假设的统一整体与时间序列进程,当然,到洛克之后的经验主义史学则是否认自然神的假设,更重视长期积累的感性实践与经验知识,而休谟把历史研究视为整理感性记忆和记录的历史材料,旨在形成因果关系链条的论证过程。但法国以理性神假设的历史哲学传统以理性精神为核心,旨在发现理性精神在人类历史普遍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众多具体、偶然、个别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本质性存在的普遍规律与永恒法则。因此,普遍性的命题需要历史作为论证材料,同时也是解释复杂历史进程的关键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从伏尔泰、孔多塞、孔德对宏大变迁的人类文明进程都划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人类精神不断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普遍历史进程。但源于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意大利—德国历史主义传统恰恰抵制法国笛卡尔—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人内化了神的力量,是有灵的意志性存在,而历史内蕴了价值、想象与信仰,是人类获得确定性知识的唯一来源,因此不能仅仅作为无生命体活力与进程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传统要求探索人之本质性存在的具体性、独特性及其生命意义,以此“直觉”到人类历史整体的生命有机体存在及其普遍进程。
到19世纪之后历史进步论大获全胜,虽然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在19世纪末走向衰落,但进化论和发展主义依然是西方主导性的历史本体论假设。本体论假设以承认上帝的实在和启示为前提,历史才获得整体性、目的论、进步性、阶段性、自我完满性的普遍特征和人类兴衰存亡的自我意识。在基督教上帝退位的现代世界之后,无论是认识论层面的培根、笛卡尔、维柯,还是后来方法论层面的孔德、兰克、韦伯等人,都依然保持对“上帝犹在”的神秘感与敬畏感。但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上帝的唯一权威性和实在论不同的是,圣父、圣子、圣灵把个体、自然、理性、科学、历史、意志,甚至是现世的政治人物,都推到上帝的神坛位置,由此制造出彼此冲突的实在论。一旦确立了上帝的世俗化替身之后,关于历史的本体论假设随即重新生效,历史整体及其所具备的普遍特征犹如灵魂附体,再次获得生命力,只需重新理解和调整历史整体的进步观念及其方向、阶段、动力和目的的完满性。进入20世纪,历史进步观念蜕变为现代化理论、趋同论、依附论、历史终结论等,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念。
但是,历史进步观念的根本问题在于,带基督教神秘色彩的历史观念有着强烈的目的论、宿命论与终结论,假定了人类历史普遍趋同的未来,忽视文明进程的多样性,容易为各种意识形态所操纵,进而陷入诸如19世纪后期所构建的“种族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以及帝国/殖民等霸权话语,对差异的不宽容,最终诉诸种族屠杀、文明冲突与世界战争。此外,统一时间进程的历史进步观念带来虚幻的、浪漫的、盲目的乐观主义,缺乏对人类生活的忧患意识与自我反思。(21)对历史进步论的更具体批评可参见[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2009年;查尔斯·蒂利也批判发展主义源于19世纪的八项“有害假定”,参见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risons, Russull Sage Foundation, 1984,pp.11-12,并认为:“我们必须坚持19世纪的问题,但是放弃19世纪的学术路子”(p.59)。沃勒斯坦在批判方面走得更远,认为“发展”是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最关键、最有问题的概念,参见[美]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三联书店,2008年,导言第2-3页。
四、结论与启示
无论从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还是从某区域国家的局部历史来看,当社会政治环境处于和平繁荣与陷入混乱之间的历史过渡期,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都高度关注历史,只有在完成过渡期而进入社会平稳期时,才可能专注当下现实而遗忘历史。其中,在走向繁荣的时期,现实需要获得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历史资源,掌握通向当下与未来的历史解释主导权,而在混乱时期则是需要寻找历史教训和因果关联,摆脱当下的危机与困境,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提供历史方位。在19世纪之后,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一直充满争议,在转向历史过程中存在三个层次的性质差异,即历史作为方法、作为认知与作为本体。其中,历史作为方法立足于当下,历史作为认知把过去与现在关联一体,而历史作为本体是放眼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贯性。
首先是历史作为方法。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糅合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认识论传统,一方面,历史成为可以观察感知和经验归纳的“试验场”,另一方面,感性、具体、复杂、具体的历史现象背后有着本质性存在的因果联系与普遍规律,因此历史可以作为方法和材料服务于社会科学研究。其次是历史作为认知,对于关注过去的历史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二者从来都是相容为一个整体而不可分离,“以古观今”与“以今观古”都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旨在共同理解当下问题的历史成因与历史变迁的当下后果。最后是历史作为本体。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彼此平等融合并非稳定不变,历史在本体层次上的价值或信仰预设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自身的意义,还关系到社会科学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其中,价值与信仰体系的预设决定了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及其之间普遍关联的判断,成为历史观念与历史编纂的共同基础,而社会科学成为论证这种普遍历史关联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西方社会科学转向历史过程中之所以充满争议,根本原因是在三个层次之间出现认知上的断裂和行动上的任意选择。
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现象,但每一种文明形态的转型方式、时间跨度、过程、结果与未来走向并不一致。中国有着连绵而悠久的历史、成熟文明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在晚清被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的方式,暴风骤雨地被拽入现代世界体系。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停滞不前,甚至用西方文明来替代或改造自身文化传统,进而以其标准衡量现代中国,并在其框架下定位中国的未来。然而,随着现代中国的转型时代进入尾声,传统中华文明意识与历史意识开始复兴,并与政治意识紧密结合。三种意识落实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集体书写,旨在争得话语解释的主动权与领导权,并通过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实现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意识崛起。在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并非仅仅理解为方法、认知或本体,也不能在其间选择或切割,而是需要把三者融为一个统一体,使历史成为中国人进行自我精神认知、形象塑造和价值呈现的内在品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相互融合必备的共同时空意识与价值导向,以此摆脱西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所谓的价值中立,抛弃实证史学所谓纯粹的史料整理与编纂。其中,历史本体为历史认知铺陈的普遍基础,使历史认知不至于走向碎片、浪漫、虚构与想象,而历史认知恰恰为历史方法注入真正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
然而,对于历史的理解,中国与西方的文明体系之间有很大不同。中华文明体系理解的历史观念没有超越性的、先验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因此不同于基督教文明体系的历史哲学传统与线性进化史观。相反,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基础,即“六经皆史”,这种历史是有生命史的严格时间限度和次序安排,而历史的无限性恰恰是有限历史连绵不断的结果,是以一种完全世俗的、经验的历史意识来克服西方先验的、超越的形而上学问题。正如赵汀阳所言, “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意味着“六经皆史”“经史一体”与“事道一体”,其中,“经”与“道”为“史”与“事”提供精神支柱,而“史”与“事”为“经”与“道”提供活力。历史不需要西方形而上与形而下先验与经验的二分法预设,也不存在其间的张力,而是二者的合体,并且都在经验的真实世界得到理解。(22)赵汀阳:《历史、山水及鱼樵》,三联书店,2019年,第1-30页。
因此,当中国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起转向中国自身的历史时,首先要理解中国精神世界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质世界之变迁,而不能割裂历史作为方法、认知与本体之间的有机整体,更无必要寻找其背后所谓先验性、终极性、超越性的历史假设。同样,中国社会科学也需要把社会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政治学只是作为社会局部的知识领域和理解社会世界的一种视角。这种社会世界以整体的形态进入历史世界,并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社会、历史与精神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较之西方传统,中国政治学转向历史的独特意义在于,把社会、历史与精神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理解多重世界之间的关联性及其运转机制。
同时,这种作为中国精神世界的历史意识为历史方法提供指导原则,使历史材料成为无穷意义与无限问题的言说链条,以文字化、事件化的方式让历史意识充满历史活力而时刻在场。换言之,历史方法是历史意识的表征、表象与具体化。中华文明传统一直充满历史意识,在于官方与民间社会都高度重视客观记录历史,包括朝代更替年表、地方史志、家族繁衍以及历史事件的时间次序与兴衰过程,文字记录复活了历史和还原现场,但严格受制于社会礼仪规则系统和道德规范系统。因此,转向历史的中国政治学需要超越西方实证史学意义上的史学方法,从历史文本材料中发现并遵循作为中国精神世界的历史意识,而具体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路径。其一,在宏观结构的长波段大范围变动中重新探索传统国家政权的运行特征以及皇权与官方权力确认的礼法及典章制度,考察其运行规则与兴衰变化规律,评估其国家治理绩效以及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对照古今制度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稳定与变动机制。其二,在中微观层次整理地方史、家族史以及个体生命史,重新发现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体系的“礼”“法”“俗”及其传播、实践与现代转化的历史变迁,探索宏观权力向下渗透与微观层次的回应方式,使之作为社会个体行为规则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意识的确认与分类。
总之,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是转向历史方法、历史认知与历史本体,三个层次之间是断裂的,因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而形成转向历史的不同社会科学群体和知识生产类型。与此相对照,中国政治学在转向历史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反思西方知识界的内在分途,而且需要回到自身的文明传统,从此,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已经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转向”(turn),而是研究对象与价值主体意义上的“回归”(return)。作为精神世界的历史意识,不仅是历史本体与认知的合体,而且成为历史方法的指导原则,从而是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成为内在关联的统一体,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学与历史研究的真正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