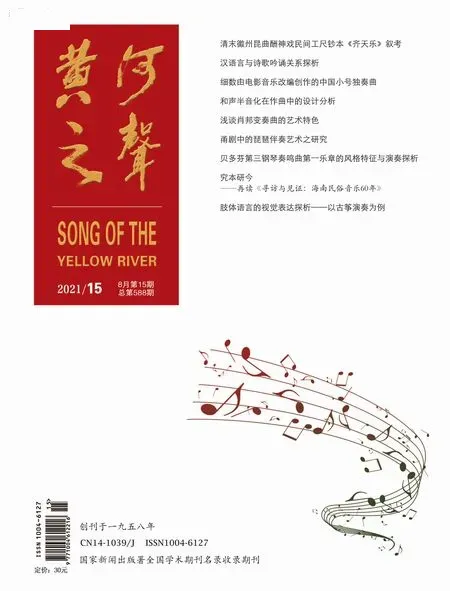汉语言与诗歌吟诵关系探析
刘小凡
引 言
中国古代诗、词和文皆可以吟诵,因诗,文体出现较早,所以吟诵方法是其他文体吟诵方法发展之源头。诗歌按照汉语言的声调、腔调和节律而构建吟诵之法,词由诗发展而来,但不及诗歌句式整齐,其参差错落,并且用韵也较宽松,所以它在依据由语言声调、腔调和节律构建的吟诵方法之上,还会根据句子的长短进行节奏和旋律的变更。词最初的形态,在唐五代时期(907-960),被称为“曲子词”,“曲子”指音乐的曲调,“词”指歌词,从它诞生以来,本是配乐而歌唱的,所以属于唱曲,如后来的宫廷燕乐或民间清歌等形式,词的吟诵之法是歌曲与格律诗吟诵调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不及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更近。文的吟诵之法相较于前二者而言,在旋律和节奏的编配方面更自由,不似诗词按照文字平仄声调抉择曲调升降,依据语言节律划分节奏,而是通过判断句中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而高下升降旋律线条,节奏随文势之急缓而变化。文之吟诵规则难循,诗词吟诵之法有一定规则可循,诗词相较,诗又为其根本。诗歌之吟诵与文字的声调、腔调和语言节律关系密切,汉语言的形态决定了诗歌吟诵音调的创作方法。
本文之所以从这三个方面论述,是因为诗歌的吟诵调与欧洲传统音乐体系不同,不能从以动机、和声、调式和节拍这几个方面的乐音体系进行问题的讨论。东西方对于音乐的感知不同,主要由语言而决定,从其最小基本单位,形成音的过程样式思考整体,片面性的论断整体只能代表外在样貌,深入不到问题本质,外在的分析又会回归到“西体中用”的中国音乐理论刻板印象的模式之下,吟诵音调的形成主要由深层结构,语言方面的声调、腔调和节律所决定。
一、汉字声调之形态
音乐从语言中诞生,又受制于语言,二者都为传文达意,抒发内心情志而服务。吟诵为主要传达诗歌纹理内容,于读书、赏析和交流之用,其旋律音调脱胎于文字声调之形态。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为声调型语言,通过语言声调的高低和升降来区别汉字之意,吟诵音调的走向与声调相符合才能做到最基本的传文达意之要求,做到吟诗“字正腔圆”的“字正”。“字正”就是指言语读准汉字的平、上、去和入四类声调,每个声调都有自己的调值,表示音节的相对音高。现代标准汉语皆是由单音节构成的文字,一个音节通常会对应好多个不同的汉字,声调的作用是辨别这些相同音节的汉字之意,一个汉字的读音,包含音节和声调两个要素。吟诵以包含音高序列的语调曲线构成旋律,具有结合语言和音乐两个方面属性的特点,与唱曲偏重达意的方式不同。
汉字声调为组成吟诵旋律最根本的要素,但古时声调形态与现在大不相同。中国古代上古时期、中古时期和现代汉语的语言声调,每个时期汉字的声调与调值都不同,但是大致为“平、上、去、入”四类。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认为《诗经》时代只有三个声调:平、上、入声,没有去声,去声与入声合为一类,直到魏晋时期,才分裂为去入二声。换言之,在古体五言和七言诗出现之前,四言诗的时代没有去声调。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王力认为上古时期的声调有四个,原因是现代中国各地方言都保存着四声的痕迹。例如北京平声分为两个阴平和阳平,入声归入平、上、去三声;大部分的吴语平、上、去、入四声各分为二,唯有一些地方的阳上归入阳去。如唐调吟诵和常州吟诵,二者都属于吴语,具体调值不同,但都是平声低于仄声。
当代吟诵学研究者徐健顺认为“从魏晋到隋唐,汉语的字音声调,存在着明显的音高关系,由低到高分别为平、入、上、去。这种声调结构,属于音高型声调,即各个声调之间存在高低关系,调值基本互相不交叉。”徐健顺提出了从魏晋时期开始,文字声调的调值可考。他提出古体诗“四声对五音”的吟诵方法。意思是平、上、去、入四声对应宫、商、角、徵、羽五声。平声有阴平和阳平之分,音高由低到高分别为阳平对应宫音,阴平对应商音,入声对应角音,上声对应徵音,去声对应羽音。具体的调值数没有文献记载,但是四声的音高排序可考。之所以上古时期的文字会形成这样的吟诵方法,是因为音高型语言不通过声调的调值来辨义,而是以相对音高来辨义,所以音高型语言,主要通过音符唱出文字调值高低关系便可做到传文达意。
唐朝之后的中古汉语一共有八个声调,是“平、上、去、入”四声调的阴阳之分。这八个声调在后世的演化中,中古音的平声字被平分为现代标准汉语的前两个声调;上声字变为现代的上声和去声两类;入声字消失,分别归类到阴声韵的平、上、去三声中,这种变化被称作“入派三声”,意思是平声不分阴阳,如果按照标准汉语阴、阳、上、去四声分类,也可称为“入派四声”,中古汉语的具体调值没有文献可考。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认清古代四个声调的音高形式,但对于语词属于哪个声调种类还是清楚了解。
现代标准汉语一共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调值名称依次为高平、高升、降升和全降调。运用现代语言学对汉语语音做出较为具体、精确的描述可以形成对声调的平仄与高低建立起更为清晰的认识。现代汉语四声常用“五度调值标记法”,用1-5五个数字表示单字的读音。阴平为55调,阳平为35调,上声为214调,去声为51调。调值1-5表示具有“相对音高的五级音格式”:1指“低音”,2指“半低音”,3指“中音”,4指“半高音”,5指“高音”。重读字音才有声调,也有无调字音,叫做轻声音,有些有声调的字是多音字。另,上声的后面如果有停顿,它是完整的214调。但是当在阴平声、阳平声、去声、轻声前时,变为21调。当在上声前时,变为24调。
汉字声调的调值可以决定音乐的长短和高低,但是不能决定强弱。由于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文字声调的调值缺乏文献参考,所以现今除方言吟诵外,基本上都是依着现代标准汉语的调值来构建吟诵旋律。中国语言属于单音独体字,一个汉字之内不会存在轻重音节,只有字与字之间会根据语气和文意形成轻重缓急之势。“平、上、去、入”四类声调会根据调值被分为“平、仄”两类,“平”就是平声一类,阴平55调,阳平35调,起伏平缓。其余三声合并称“仄”一类,“仄”意为“倾斜、不平”,相对于“平”声,“上、去、入”三声的调值都有升降,其共同点就是“不平”。在吟诵唐朝之后的近体诗时就会出现“平低仄高”、“平高仄低”和“平长仄短”的法则。也就是平声吟长,仄声吟短,平声的音高唱高,仄声的音高唱低。在方言中平声比仄声调值低的,会遵循平声唱低,仄声唱高的原则。
在吟诵诗歌时,由于加入了旋律发展,所以每个字都会拖长了吟诵。但是相比较于平声字,仄声是升降调,一拖长,无论是上行发展还是下行发展都不完全合理,平拖又倒字。另外,虽然入声字已经“入派三声”,但是在吟诵诗歌的时候,需要把入声字识别出来,尤其对格律诗而言,有些入声字刚好在格律字位置上,易造成歧义。入声字的韵尾是塞音韵尾,读音短促,所以在吟诵时,都会在入声字后紧跟一个休止,入声吟拖不长。相较而言,平声字可以更好地进行拖长发展。音调拖长了的旋律发展一般主要是在汉字的韵母部分发展,由于汉语言文字单音独体的特点,在进行旋律发展的时候可以根据创作者的需求随意延长也不会改变文字本意,这种旋律的发展被称为腔调的吟诵方法。
二、腔调吟诵之方法
音,从西方音乐的角度来解释,音的形态基本上是直线状的,音乐持续感的来源是由不同长短时值的音,通过不同的组合而带来的,如音与音之间级进或跳跃的关系。但是从中国传统音乐的角度讲,中国音乐有“音腔”论。沈洽解释音腔为音乐持续感来源的直接表现,是一种音过程的特定样式,一种整体结构。音腔所包含的音成分的变化是“音自身的变化”所带来的持续感,并非是西方音乐“不同音的组合”构成的持续。在西方音乐中,一个音具有四个性质:音高、时值、音色和强弱。因为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无声调,从语言韵律学的角度来讲,这些语言每个音节的高度都是一定的,不可变的,也就是没有音高变化的语言。但是,在读汉字的过程中会存在一种从高音滑向低音,低音滑向高音的升降感,中间会经过一些过渡的阶梯。不像弹奏钢琴时,每一个音都是颗粒状的发出,单个音不具备音高升降的感觉,每个音之间升降感觉的形成是需要音与音之间的组合才能够形成。沈洽所谓中国传统音乐“音自身的变化”形态,从弦乐演奏的角度讲更能说明这一原理,如古筝演奏者们采用“推”的手法得到一个音高向上滑动的变化音,他们认为这样奏出的每一个音是一种“音高变化的音”,也就是通过使用方法,在一个音的时值内产生其自身具有变化感觉的音的形态,而非通过多个音之间的组合形成这种变化之感。
这种自身具有变化形态的音便是中国传统的音乐形态,通过对腔体本身无限趋向圆满的发展而得到。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分为音头、音腹与音尾三部分结构的腔体,因这一发音腔体与汉字本身的发音方式不谋而合。汉语的发音结构,也就是一个音节本身,有头、腹和尾的结构之说。字头是发音的起始阶段,它包括声母和韵头;字腹由韵母的主要元音充当;字尾一般由辅音构成,它是一个具有字头、字腹、与字尾三部分结构的腔体。根据这三种成分的不同结合方式,可以获得持续感长短不同的音腔。音腔的结构可以分为:完全结构音腔,即有头有尾的音腔;不完全结构音腔,即有头无尾的音腔或无头有尾的音腔;单体结构音腔,即无头无尾的音腔。
一个汉字由声母加韵母拼读而成,韵母由元音组成,有一个、两个和三个元音的情况。字头是发音的起始阶段,它包括声母和介音(韵头)两个音素;字腹是发音的中间阶段,它由韵母的主要元音充当;字尾是发音的收结阶段,一般由韵母末尾的元音i和u或者由韵尾的鼻辅音n和ng充当。不是所有的音节都是“头、腹、尾”齐全的,有的只有字头和字腹,而没有字尾,如“家”(jia),ji是字头,a是字腹;有的只有字腹和字尾,而没有字头(即所谓“零”声母字),如“哀”(ai),a是字腹,i是字尾;还有的只有字腹而没有字头和字尾,如“啊”(a)。所以,就会出现完全结构音腔、不完全结构音腔和单体结构音腔的形态。不同结构的音腔在实际吟诵中所形成的单个音的发展空间不同,也就是该音持续的长短不同。
与西方音乐通过音之间的组合而带来的持续感相比较,“音腔”——作为微观表层的单音波动形式,只可能定性为单音而不可能超越到单音之上的“结构”层面;这种单个音的“变化”,始终囿于其自身性质所决定的音级定位——逻辑关系上限定了的层面,只能在该层面所限定的范围内予以解释。也就是说音腔的发展,如果记谱,所呈现的主要是级进式音的发展,不会有跳进式发展,并且有些音并不一定能够通过记谱写出,十二平均律之外的音需要用微分音记谱法标记,然而这些在古代根本没有出现。所以诗歌的吟诵调在古时几乎考证不到乐谱记载,一种原因,吟诵在古代是约定俗成的读书方式,其二就是音腔的发展具有创作者的主观性和即兴性成分在其中,有些吟诵者在熟记了诗歌的旋律骨架音之后,不需要乐谱视唱,看到文字便可以吟出音调,现今就算有记谱,一般记写的也都是骨架音。
音腔吟诵这种独有的带有即兴性特点的表达,使之明显的区别于诗歌的歌唱方式。歌者在重复同一首歌时唱同一种曲调,固定的曲调可以由某个作曲家特意为之谱曲而成,或者直接取自传统,并产生出一种或可能几种替换的变体。吟诵的调子可以是即兴的调子,即看到文字的声调便可以吟出基本的旋律,吟诵者可以根据各自审美标准加入音腔的发展形态,作为主旋律的一部分或者不算在主旋律的时值内,作为装饰音。赵元任认为这种夹带了装饰音声调的效果使“咬字”更为清晰,因为音位的声调是语词构成成分的一个部分。赵元任所谓的这“一个部分”就是指的韵母,“咬字”更为清晰是指字的腔调更饱满,也就是“腔圆”。
声调决定了吟诵每个文字的主要旋律音,把发音的用力点放在开始部分的字头上,以此带动后面的字腹和字尾,字腹为音腔的主体部分,负责进行音时值上的变化发展。字尾根据该汉字于诗中所在位置而抉择尾音是否持续发展,如在韵尾处就需要增加尾腔来吟诵,如果该字本身为入声字就需要结束得坚决而果断,还可以根据文字在诗歌中表达的情绪而判断吟长还是吟短。汉字以声调型语言的特点,其本身发音的运行方式就带有高下升降的旋律线条,根据由声调和腔调所形成的语调曲线构建吟诵调,形成“依字行腔”的吟诵之法。
但是吟诵调的旋律形成不仅仅由“依字行腔”这一个方面决定。赵元任认为中文语言的实际音高进行是声调和语调的代数之和。那么吟诵调旋律的音高进行也会受语调的影响。这里所指的语调便是语言学中所指的,由说话时轻重、缓急所配置而成的语调。也就是说语调和情绪相关,可以通过诗歌中描绘的场景和用词来推断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绪,从而判断每个字、词和句的语调,也就是“依义行调”之意。声调决定吟诵音高的高低,音腔决定音的时值长短,音的强弱则从语言的节律方面进行判断,节律就是诗歌吟诵的节奏规律,对诗歌吟诵节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诗歌表达的含义和语调的轻重急缓。
三、语言节律之辨析
现代所呈现的古典诗歌中的标点符号,在古时本不存在,除随诗歌文意判断节奏急缓之外,文字本身的语言节律才是形成诗歌吟诵节奏的根本因素。依据汉语言的自然节律所形成的一种节奏格式来划分节奏。“诗歌节律是一种语言节律,它是由各种语言特征的对立要素(如音的高低、长短和轻重)通过有规律的重复变化构成的。”语言的节律结构是指语流的轻重音结构,就是语流中轻重音按一定的规则交替出现形成的一种语言特有的节奏规律。近体诗所体现的语言节律最明显,因为近体诗的平仄格律本身就是一种有规律的重复变化的节律,并且诗歌的吟诵具有“平长仄短”和“平低仄高”这样的对立关系。因为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只在第二、四和六字上体现,第一、三、五字不论平仄,所以可以根据格律的分配对诗歌的节奏进行分割。五言诗的节奏划分可以表示为XX/XX/X,七言诗可以表示为XX/XX/XX/X。最后一个单独的X是韵尾字。每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单位,两个字是一个节奏单位,或者称为节律单元。
根据五、七言诗的节奏划分可以截取出三种基本节律单元:双音节段:XX(1+1),三音节段:XX/X(2+1)和四音节段:XX/XX(2+2)。三音节段从句法上看有两种可能:1+2或2+1,但从节律上来看,排除了1+2的可能。也就是说,无论在句法上是1+2还是2+1,事实上按节律都念成2+1。因为1+2的结构打破了双音节韵律的规则。也有单音节自成一个节律单元的情况。吴为善将节律单位称为音步,认为双音节为“标准音步”,三音节为“超音步”,单音节为“弱音步”。按照汉语语言发音习惯对诗歌进行节奏划分,基本都是两个音节为一个节奏单位,所以双音节才会被称为“标准音步”。因为汉语是双音节韵律,后重,就是后一个字读得重,这是汉语的特点,一三五字读长就不是后重了,违背汉语的习惯,所以只有二四六字的平声字和韵字是读长的。而从声学原理来看,一个音节拖长加重了,它的声调特征就变得显著,这正是汉语节律构成的依据。所以若是两个字组成的词语,一般都是后一个字读重。
诗歌的吟诵调首先是从语言的节律方面来考虑,其次是从音乐的角度看,那么就会主要依照语言的韵律规则来确定节奏点的划分位置。吴为善认为所谓的节奏点就是节奏单位中声音扬的位置,吟诵时要拖长加重的音节。拖长加重的音节在“标准音步”中就是第二个字,对应扬,第一个音节就是抑。这样就组成了声音一抑一扬,一轻一重的对立要素。近体五言诗句有三顿,七言诗句有四顿,最后一个字曼声长吟,等于或超过前面每两个字音的长度。所以五言近体诗的节奏结构一般是2+3,或者2+2+1,七言近体诗的节奏结构一般是2+2+3,或者2+2+2+1。如五言律诗,杜甫《春望》开头两句:仄仄/平平/仄,国破/山河/在,平平/仄仄/平,城春/草木/深。如七言律诗,王翰《凉州词》开头两句:平平/仄仄/仄平/平,葡萄/美酒/夜光/杯,仄仄/平平/仄仄/平,欲饮/琵琶/马上/催。除韵尾字一般是单音节音步之外,都是优先每两个字为一个音步,第二个字要比第一个字读重拖长,也就是说在配吟诵调时,若第二个字是平声字则拖长吟诵,并且会有一个音腔上的发展;若第二个字是仄声字,则会有一个短的停顿。这样就形成了“抑扬顿挫”的感觉,“挫”指的是旋律的变调或者转调。
根据轻重的相对韵律格式,一般扬格位置的字音会吟诵得音更高、更强或者更长,以此来区别抑格位置的字音。其与西方音乐中强、弱、次强、弱的节拍划分不同,对于吟诵调的记谱惯用“散板”来标记,如此便不会形成小节式的“匀拍值”形态,而是具有模糊性的自由发挥式的节拍形态。由于腔音发展和即兴吟诵的特性,诗歌的每一句吟诵音调的时值划分不具备“匀拍值”标准,每拍所占时间长短无法准确定论,所以速度不可以用一分钟有多少拍来表示。大体上都是一句为一个小节,以散板作为拍号标记,时值根据实际吟诵创作情况而发展。
这主要是由于汉语为单音节结构,词语中没有重音,而印欧语系大多数为多音节结构,以欧洲各种语言写成的诗歌,单词重音存在规律性地出现,成为构成诗歌韵律的主要因素,与重音密切相关的音乐要素就是节拍,从而形成了欧洲音乐中强弱交替很有规律的节拍体系。汉语的单音节结构中没有轻重相对音节,也就没有节拍重音,不存在节拍体系和小节概念。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板”和“眼”是衡量音乐时值的基本单位,并非所谓强弱,所以从汉语言本身节律结合诗歌格律方面分析吟诵抑扬,或称强弱音方面的解读更合理。由此看来,由于无节拍、无小节的限制,吟诵音调对于强弱音的体现并不是非常明显,音的高低和时值的长短为最主要的两个元素,其吟诵音调的强弱方面主要还是跟随诗文之义和表达情绪之急缓而决定。
结 语
汉语言的声调、腔调和节律包含了吟诵基本旋律的构建之法,古代诗、词、文皆以此为发端。诗歌以其句式整齐,结构有规律可循,作为论述吟诵旋律与语言相关因素的典型代表。汉语言以其声调型语言的特点,使得吟诵音调脱胎于文字声调之形态,汉字声调的调值可以决定旋律的高低起伏。另,汉字本身具有运用腔体发音的特点,其结构由字头、字腹和字尾形成腔体,于主要发音部分字腹进行吟诵旋律上的变化性发展。由于汉字单音独体的特点,创作者可以随意延长腔音的时值发展也不会改变文字本意,于是就得到了一个自身具有变化属性的音的形态,达到腔圆饱满的目的。以上两点决定了组成吟诵旋律的音的高低和时值变化,但是音的强弱方面主要取决于语言节律。以近体诗为代表,其格律安排本身就属于一种语言节律,以此来解释轻重韵律格式,判断诗歌节奏划分规律。但是汉语言为单音节结构,单个音节之内没有轻重音的存在,所以除近体诗之外,其他体式的诗歌类型,其吟诵音调对于强弱音的体现并不是非常明显,也会根据诗文之义和表达情绪之急缓而判断轻重音。吟诵调中的重音位置主要通过吟诵得音更高、更强或者更长来体现。本文从这三个方面论述吟诵音调与诗歌纹理内容的相关性,从语言结构形态入手,解读吟诵音调的成因,构造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