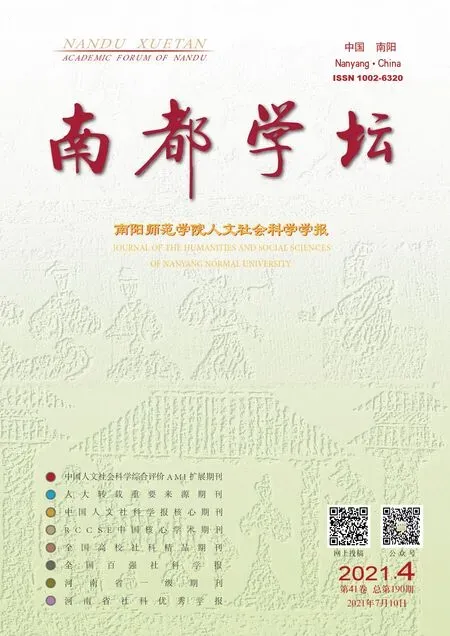非遗影像史记录的转型与实践研究
刘 东 亮
(国家图书馆 社会教育部,北京 100081)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目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一般简称非遗,特定语境下不简称)影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阐释其文化功能和社会意义。影像媒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让非遗最大化地实现了学术“本真性”的要求。1994年12月在日本通过的《奈良文件》肯定了本真性的意义所在,称本真性是“定义、评估、保护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原则”[1]。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创作,非遗影像记录兼有学术伦理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关怀的社会功能。影像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可以使非遗的“本体”更加直观地展现出来,同时又能涵盖物质媒介、文化空间、社会历史环境等关联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非遗影像的记录内容及方式进行研究。
一、非遗记录方式的转型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确定了“非遗”的概念与内涵,其中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2]。
(一)口头传统的演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最初是口头文本的讲述,这是传统社会存储和建构人类文化与记忆的基本方式。对于没有文字的族群来说,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靠非物质的形态延续下来的。尤其对于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而言,口头传承就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大多是以口头相传的方式来记录和保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以人传人、代传代的媒介模式,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生礼仪、器乐、服饰等各种文化事项的记忆保存下来,并以“记忆内容—语言—形式逻辑”的方式完成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
口头传承是“非遗”的一个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口头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特定演述形式和传统技艺实践环境的知识,比如在民间文学中讲一个故事,表演艺术中演唱一首民间歌曲等,这种讲、唱都是一种在特定文化空间中的艺术表达形式,具有比较强的“规范性”。另外,编渔网、建房子、织绣、铸造等技艺,是在具体劳作过程中传下来的,属于文化实践中有关生存技能的知识。第二类是既有特定的演述形式,又有特定应用场合的知识。比如人生的重要仪式中,出生礼、成人礼、婚礼这些生命过渡仪式,都需要特定场合才能讲述。其他比如少数民族有很多的禁忌和避讳,例如普米族巫师为病人举行的“送替身”“退口舌”等仪式,必须在某一个特定的民俗文化事项里才能够应用。第三类是一般性的知识,在人与人的交谈、聊天等各种场合中讲述的,不需要有明确的时间、场合、形式上的规定,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二)影像书写——新媒介的产生
在传统的社会中,图画和图形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性手段,可以弥补口头传播中因记忆和理解力而出现差异的缺陷。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非遗的记录方式。随着摄影技术的兴起,对于包括口头传承在内的非遗来说,其记录手段无疑更加丰富了。影像记录可以满足非遗动态性保护的需求,“数字化音视频设备能够实现高保真、高清录音与摄像,加之多机位拍摄技术、多媒体呈现技术等,非遗的动态性在数字资源中的实现程度越来越高”[3]。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拍摄的《佤族》《凉山彝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等十几部民族志影片,用镜头记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场景、风俗习惯、节日仪式、宗教信仰等内容。依靠影像化的手段,可以真实地记录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语言与文字无法完全展现的言外之意,如人的姿势、神态、动作等记录下来,使传统非遗文化真正成为立体性的活态文献。
二、非遗影像中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自觉
面对这些活态的文化艺术形式,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视觉化的方式完整地展现出项目的核心价值,发挥影像传媒的中介作用,拓宽非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以创新发展的方式赋予非遗更强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影视媒介,则是可供开发的原材料、新的艺术创造的源泉,更不失为传播传统文化、张扬本土色彩、坚守‘文化版图’的有效策略。”[4]在这一情况下,非遗的影视书写有了双向的发展策略。
(一)集体记忆:文化的标志物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分析了人类的社会交往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在记忆理论的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命题。他们把“日常的集体记忆形式称为交往记忆。它的最大特征是时间的有限性”[5]。实际上,这种交往记忆的典型例子就是非遗的代际传承。集体的知识在历史的演进中产生,但是它会随着文化传承者的消失而与现代社会产生某种断裂,从而衍生出一种新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强调非遗的影视记录重视传承人的原因,“人亡艺绝”现象的出现正是代际记忆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表征之一。文化记忆正是在日常交往转换为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实现的。它需要有固定的时空节点,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得以存在,并且还保留于节日、仪式、故事、歌曲、文化遗迹等各种载体之中。这些“记忆的形象”,通过系统化的集体实践与互动得以延续和传承。
传说是最早的口头叙事文学之一,如北京的永定河传说是典型的地名传说类型。这就牵涉到集体的场所记忆了。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建立了“建筑现象学”的理论,提出了“场所”的概念。在舒尔茨看来,场所是“人们通过与建筑环境的反复作用和复杂联系之后,在记忆和情感中所形成的概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建筑与特定的人群相互积极作用并以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整体”[6]。现今关于永定河的传说有30多个,其中大多与日常生活习惯有关。比如永定河边栽杨柳树的由来、如何治理永定河等,都是当地人以一种程式化的方式记忆历史,在不断讲述传说的过程中,附会上某一个权威人物或有意义的事迹,来阐释传说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进一步强化这种集体性的认同。
(二)个体意识与文化自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人”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以人为主,所以,社会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非遗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充分唤醒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文化自觉,形成大众对于非遗保护重要性的共识。对于非遗的保护来说,在倡导传承人“文化自觉”理念的基础上,要充分保障传承人的“文化权利”。具体来说,文化权利“需要考虑个人和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个人和群体非常珍视它,而它又决定了他们的集体特征”[7]。在 2005年10月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法罗公约——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遗产权”的概念,其主要规定有“人人都有单独或者集体享有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以及为丰富文化遗产作出贡献的权利;人人都有单独或者集体承担如同自身遗产一样尊重其他文化遗产的义务”[8]。简而言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障传承人自由开展文化活动,使其文化利益更好地得以满足,同时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发展及个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但是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都市文化流失现象严重,逐渐呈空心化的趋势。近年来,由于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普及,大众媒介娱乐化的倾向也日益显著。在这一过程中,激化了传统与现代这两者之间的文化冲突,加剧了都市文化的变异现象。由此使人们形成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非遗是一种“不合潮流”和“落后”的文化现象,这种心理暗示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非遗传承人的文化焦虑感。
三、影像记录非遗的工作方法
(一)对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和传统技艺实践的记录
口头作品典藏。对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影像记录最主要的方式是录制其代表性的作品。通俗来说,就是在传统的表演场合里,以其应有的表演形式,对其代表作品进行记录,重点是要体现出传承人的语言特色、表演技巧、即兴能力、互动能力,记录与作品相关的信仰与禁忌等。对于传统音乐的记录,应选取传统性、代表性的作品录制,侧重于他们的演唱、演奏技巧,所记录的音乐作品保留了其传统的表演环境和表演方式,并且要详细记录与音乐相关的仪式。对于传统技艺实践的记录,具体的工作方法是全程记录传统技艺流程、制作步骤和方法。其中注意不要遗漏原材料及其加工方式、特殊工具的制作等内容,并且还可以记录与之相关的口头知识、传统行规、师训、行话等。
(二)对民俗活动的记录
对于民俗活动进行影视学的记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整记录民俗活动从筹备、活动准备、活动呈现、活动结束及循环规则等的全过程。比如对于传统年节及大型祭典等习俗,要记录年节及祭典活动的全过程,重点记录其中的核心仪式和艺术表达,如敬天、祭祖,这些都是严肃的精神活动,在仪式中的集体歌唱、舞蹈带有娱乐表演的性质。对于民间信仰习俗,要完整记录整个仪式的过程,如迎春、神诞、禳灾、还愿等,以及传承人对相关信仰仪式的解释说明,并且还要着重记录和民间信仰有关的口头表述,如各类说辞、经文等内容。
对于生产生活习俗,则要完整记录该项习俗的全部环节。记录依托在生产生活习俗上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窗上的剪纸,宴席上的祝词、歌曲,劳作时的民歌、号子等。这种生产生活习俗是民族传统观念的外化,不仅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而且规范了族群的道德伦理观念,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对于民俗活动的记录应该在当地的日常环境中进行。
(三)口述史访问
口述史的工作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科所接纳。因此口述史访谈工作基于相关的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展开。对于文化事项的持有者和非遗传承人的访问,可以依据四级非遗传承人名录,以此为参考,确定访谈对象。因为大量的口头传统内容是分布在非遗十个大类里面,蕴含着民众的生活传统和经验,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采访者要熟悉传承人所属项目的历史源流、发展变迁及传承情况,初步编写传承人年表、传承谱系表及访谈提纲。访谈结束以后需要将口述史访谈的内容转录、校对、编辑,做成口述文字稿。口述文字稿完成以后,请受访人审稿并在纸质文本上签字确认;如果有不予公开或暂时不予公布的部分,则在纸质文本上标记。
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相关传统村落的专题口述史访问。口述史的方式可以有效弥补有些村落文字书写的不足,将传统的口头遗产如农耕知识、祭祀仪式、节日庙会、婚丧习俗等内容由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社群和民族群众讲述或表演出来。
(四)已有文献的收集
从图书馆的本位工作出发,对相关的社会组织、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和传承人个人记录的非遗影像资料进行收集,可以通过接受捐赠、购买、交换、复制、数字化、网络下载等方式获得相关的文献。对于已获取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均应通过签署《文献收集与使用授权书》等方式明确使用权限,避免可能引起的法律纠纷。
四、结语
在当下的时代,我们对于非遗的影像记录不能仅仅停留在项目这个单一主体上,而是应该回到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将视角转向传承人的动态实践活动,以及与文化传承者的集体互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将非遗的核心内容用影像记录下来,从而形成对非遗的立体性保护。
非遗从来不是一种静态的文化事项,它的发展和传承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紧密相关,所以在文化空间和社会互动中理解非遗就显得尤为重要。非遗影像对于传承人和项目的记录,不是让其作为“标本”保存,而是在动态的项目实践和传承教学中保持其发展的活力,同时了解这个项目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未来前景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对非遗影像进行整体性的诠释和理解。另外,非遗影像还应该坚持对人的描写。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表演艺术、节庆活动与人生仪礼,这些是非遗项目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非遗价值的集中体现。如何将传承人头脑中的知识与技艺外化出来,才是影像记录的难题所在。
影像在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进行记录之时,也应对人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以及项目背后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阐释。因为浅层次的文化记录容易走向追求新鲜感、时效性与娱乐化的误区。当我们把传承人与一系列的文化事项联系在一起时,就形成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文化研究文本。我们通过影像的方式对非遗进行分析和描写的时候,就更容易阐释其中的文化蕴含。
——围棋
——新一代江格尔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