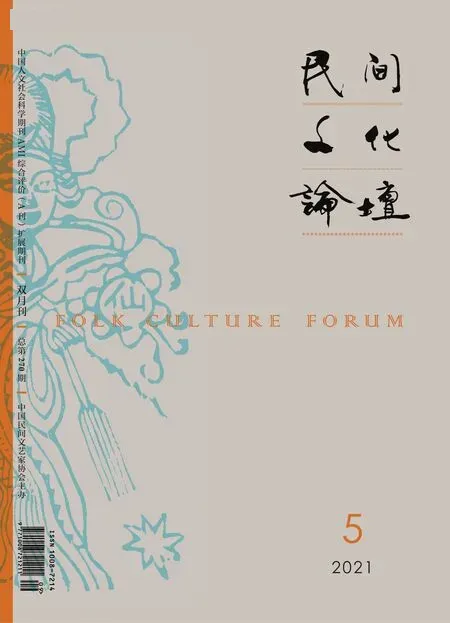日常空间:现代民俗学关注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
李向振
日常生活转向,是近年来国内民俗学者讨论学科研究领域拓展与纾解学科危机时采取的表述策略。a李向振:《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在国内民俗学领域,高丙中较早地将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领域。b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经过近三十年的讨论,目前民俗学领域围绕此概念的讨论已经形成较成体系的知识谱系。从学科知识演进脉络来看,国内民俗学者讨论日常生活大体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从胡塞尔哲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世界”出发,将民俗学研究领域扩展到生活文化,以探寻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性;二是从卢卡奇、列斐伏尔到赫勒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日常生活”与“再生产”的讨论出发,意在拓展民俗学研究对象并探索民俗学新的研究范式。
日常生活既是个复杂的学术概念,又是个难以厘清的社会事实。在阿格尼丝•赫勒看来,日常生活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c[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衣俊卿更加明确了个体再生产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定义,“一般来说,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的各种活动的总称。”d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尽管我们可以说民俗学研究的最终旨趣是对日常生活及行动者意义世界的整体关照,但落实到个案和实证分析,我们又不能不对整体的研究领域进行裁分,以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生活世界进行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在赫勒这里,日常生活并非总是表现为抽象概念,还表现为其确定的行为及知识、确定的行动主体、确定的组织架构等形成的图式。正如伯格所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一个由我与他人分享的世界”e[美]彼得•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日常空间是日常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空间。a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第19页。日常空间不仅是社会生活展开的竞技场,也是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对于生活实践而言,时间和空间都具有社会建构性。b参见[英]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美]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黄春芳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美]德雷克•格利高里、[美]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等等。时间与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日常行动的时空场域,其本身也参与到一切人类行动的意义建构之中。转向日常生活的现代民俗学,需要重新审视日常时间和日常空间的民俗特性。
一、日常空间的边界与建构
社会生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空间性。日常生活总是和个人的“此时此地”相联系。这里的“此地”就在最广泛意义上代指了“日常空间”。日常空间是个人经验结构化的重要维度。承载日常生活意义的空间结构必然是有边界的,因为边界本身总是确证空间存在的标志。
(一)空间的边界
爱德华·雷尔夫说,“事实上,村落的空间形式都是在不自觉中被组织起来的,整个过程所依据的是主导社会的信仰与劳作实践:每一名成员都能意识到村落里各种空间要素的意义,且能严格遵守。”c[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1页。从现实经验来看,人们构建空间边界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物质形式,比如一堵墙、一个篱笆、几个石头、一座庙宇、一个神龛,等等;二是时间形式,比如一炷香的距离、打个盹儿的距离、一小时的车程等;三是观念形式,比如神圣的天堂、充满鬼魅的地狱、“天地三界十方真宰”等。
日常生活中,作为度量单位,时间与空间总是相互指涉、相互对照。一方面,人们往往爱用时间来理解和度量空间。比如田野中问起某位农民,某某村多远时,他极有可能回答,十分钟路程或半小时路程。另一方面,空间距离的变化,也会经由时间来表达。比如高铁开通之前,北京到武汉的距离被表述为“火车十几个小时”,高铁开通火车提速,这段距离又被表述为“高铁四个半小时”。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用空间来表述时间,比如人们常说“日上三竿了”“日落西山”等都属于这种情形。这些表述,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人们如何通过时间长短来感知空间远近,又如何通过空间远近来表述时间的长短。
对于民众而言,无论是将空间远近转化为时间长短,还是将时间长短转化为空间远近,都不是简单的表述策略问题。实际上,这种转化背后,蕴含着人们对时间和空间基本属性的深刻认识。从现实经验来看,人们用时间来表述空间多于用空间来表述时间的情形,原因在于时间更具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日常时间的确定性让人们在做出选择时往往优先考虑时间维度,时间是否允许,决定了可以到达的空间远近。比如对每天都无所事事的人来说,花十几个小时出趟远门旅游,可能并不会觉得遥远,但对于非常忙碌的人来说,花几分钟去办公楼下取趟快递,可能都感觉非常遥远。这便是时间的确定性带来的空间边界性。
在日常话语中,“长”和“短”既可用来表示时间又可用来表达空间。这是日常生活赋予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当人们说空间距离长或短时,实际上是与到达那里所用的时间进行对比后做出的判断。到达那里,是人们对空间的行动性表达。人们之所以要到达“那里”,因为“那里”有与“这里”(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的生活形态。从时间线上看,“那里”是未来的生活或过去的生活,而不是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只属于空间上的“这里”和时间上的“当下”。
对于未来的生活,人们擅长将现在的空间边界,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明确,并尽可能地将自然时间划分为确定的时段,以保证未来生活的可控性。对于过去的生活,人们往往依靠回忆和叙事将其释放出来,过去的生活大都不需要明确的空间边界,因此,在民间叙事(比如神话、传说、故事等)中,如果不是赋予空间以特别的意义,那么在讲述的文本中“过去的空间”总是被忽略掉。比如,人们总是爱用“从前,有一个地方……”作为故事的开头,这里的“有一个地方”就是不确定边界的空间。而对于现在的生活来说,人们则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确定空间的边界,因为一切关于当下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在特定的边界范围内组织完成。
在乡村社会中,边界经常是个模糊的概念。尽管耕地有明确的界线、村庄有明确的轮廓、行政村有明确的领地、家庭庭院有明确的围墙,但从村民社会关系与心理认知层面来看,这些边界在日常生活领域并非总是有意义。不过,在重要的公共事件或集体行动时,这些边界会迅速成为各种共同体制作的重要资源,从而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力量。同时,在这些事件中,边界还被赋予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工具。尽管在边界两边看来,这些互动可能更多是消极的背离运动,但在各自边界内部区域内,互动和行动的目标将更加明确,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凝聚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力量。
虽然边界经常由物质载体和空间界线构成,但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实际上真正的、纯粹的具有边界的实体在历史上或许就从未长久过。”a[美]迈克尔•赫茨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问题是边界形成的逻辑是什么呢?蒂利认为,“边界过程的参与者接受那些影响他们追求边界内关系、跨边界关系和边界区域陈述的奖励或惩罚……边界维持动机的变化一般导致边界的变化。”b[美]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许多情况下,边界的设置在事实上再生产了村落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公共事件场合,现实可见的边界为村民建起一座“安全岛”,“岛”内意味着安全,这无疑会增强边界内群体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表现在“对抗”外部世界的“他者”时,往往会迸发出极大的威力。“边界可以稳固社会关系。它区分了居民与流浪汉、邻居与陌生人、陌生人与敌人。”c[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因边界设置而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并非完全是基于情感和关爱的自发组织,更可能的是,它原本就是对共同的外部世界带来的风险的防御机制,同时,边界内部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本身也形成一种与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集体机制,“由于村落内部人际关系亲密,交往相对频繁,来自外界的重要信息却可以迅速传播而由村民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外界联系不便的缺憾”d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二)空间与乡愁
在日常实践中,空间的边界划分,在区隔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现。城市和乡村之间拥有一条人为的但又不易打破的边界。居住在城市和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各自组织着彼此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品味。
在现代社会之前,城乡间的不同可能仅仅是体现在职业分工不同,但在现代社会,这种职业分工不同正在被阶层和生活风格与文化形式的不同所替代。现代以来,城市和乡村被视为时间序列上的前后关系,城市代表文明,乡村代表野蛮;城市代表进步,乡村代表保守;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等等。诸如此类对立的二元词汇,被嵌入在各种描绘城市和乡村的著作中。在这些研究中,人们总想着按照城市标准去改造、拯救、甚至消除乡村。我们很难说,这到底算不算文化霸权,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现代社会,人们在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社会形态中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将城市和乡村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生活空间。
这种来自现代性的区隔,塑造出了一种被称之为“乡愁”的生活状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向往乡村,因为在其观念中,乡村是承载乡愁的最佳空间。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即便出生地是城市,也会倾向于认为唯有乡村才能寻觅到乡愁。这很具隐喻意义。乡愁成为了特定空间的文化符号。这一特定空间被命名为“乡村”。
当然,乡愁也不只是包含了空间意义,它还具有时间意义,即乡愁是过去或传统生活的现代遗存。人们将空间上远离城市的乡村,想象成为时间上的过去。在时间线上,乡村被认定为城市的过去,城市则被视为乡村的未来。时间和空间在此刻统一于乡愁之中。
善于制造乡愁的现代社会,从来也不缺乏满足乡愁的方式。比如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或有线电视,通过各种以乡愁为主题的节目,让身处现代城市的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缓解乡愁之苦;或者各种交通工具带来的生活便利,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到空间上更远的乡村寻觅乡愁。寻觅乡愁变成了一种与空间上“遥远”相关的游戏。仿佛越是远离城市,越是远离人类聚居点,就越能接近乡愁。这是人们对空间的文化想象。
从传统民俗学研究路径来看,研究者更倾向于将“乡村”作为展开研究的主要生活空间,而且关注的主要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也大多与乡村直接相关。正如刘铁梁所言,“村落作为农业文明最普遍的景观应当成为我们民俗学调查所把握的基本空间单位。”a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尽管关于都市民俗研究的呼吁和实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俗学发轫之时即已有不少相关学术作品,但真正将都市民俗研究置入现代民俗学日常转向问题进行讨论,则是近十几年的事情。b李向振:《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的几个关键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现在看来,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民俗学,是时候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这两种被人为建构起来的概念和社会现实的合法性问题了,而且需要在审视中,思考二者的空间建构性是如何体现在各种类型的民俗事象与民俗实践之中的。
二、日常空间的类型与民俗生活
空间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合适的场所。日常生活领域可分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与之相应,空间也可以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对待这种两种生活空间的态度,也构成了乡村与城市最为直观的区别。
(一)私人空间与私人生活
在乡村社会中,私人生活空间是半公共性的,尤其是院落,经常会汇聚一些妇女坐在庭院里聊天或做家务事,她们边干活边闲聊,她们所关注的往往都是村落里的公共议题。
院落与村落其他公共空间的区别在于时间性,村落公共空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村民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整个白天和黑夜在公共空间闲聊、游戏或者开展其他活动而不会影响到其他村民生活。然而,过去院落是以天黑为标准的,在没有电的年代,人们休息得很早,即使有串门的,也会在主人关灯休息之前离开。从乡村生活来看,村里接通电的最大好处是延长了作为私人空间的院落的公共性时间,人们可以闲聊更长时间,或者一起看电视或者做其他事情。
传统乡村地区,纯粹的私人空间极少存在。人们的生活空间从院墙内延续到院墙外,院墙的意义不是在公共空间隔离出一个私人生活空间,而是防止牲畜、坏人来搞破坏。对于日常生活而言,院墙只是一个家的范围的象征,并不影响人们之间的交往。
城市的生活空间相对来说私密很多,城市设计者通过种种方式将生活区域与其他空间区隔开来,而在生活空间中,又通过各种“门”来限制其他不属于该区域的人进入,小区有小区的门,家户有家户的门。虽然这些“门”也是为了维护住户与家户不被人为破坏,但从日常生活实践上看,这些门切切实实地阻隔了邻里间的日常交往,无论是下班回来,还是遛弯、买菜回来,在门口遇到的邻里间礼貌性的打过招呼后,就将厚厚的防盗门一关,人与人之间就这样被区隔开来。
(二)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公共空间对于乡村或城市社区的意义不言而喻。人们在这里组织起日常生活,人们在这里讨论着关于他人、关于社会、关于国家的议题,这里充满乐趣、充满活力。人们可以在这里娱乐、休闲,也可以在这里完成手头上的活计,最主要的是在这个空间中,人们讨论的话题是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尽管很多流言蜚语也是从这些地方传播出去。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公共空间都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对乡村社会来说,非正式公共空间就是如前所述的邻里交往的日常空间,其正式公共空间则表现为一些固定的场所。比如在没有自来水之前,村子里的水井周围就是村落公共空间,每日午后,都会有村民到水井旁打水洗涮衣物,在洗涮衣物的同时,他们互相交流共同关心的话题或村里的公共事件,所涉及的内容往往很庞杂,正如俗话所说,“张家长李家短七个鼻子八个眼。”
村里的闲话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属于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形式。闲话中心往往是一种非制度性约束力量,很少有村民在闲话中心褒扬某种集体行为,他们更多的是通过闲言碎语等非正式惩罚机制,规范和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
另外,村里的庙宇、宗祠等也属于公共空间范畴a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无论是庙会或祭祖期间,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借助这些神圣空间,解决各种事关村落集体或村民个体利益的公共议题。
不过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进入,大多数村落已经能够吃上自来水,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使用洗衣机,在这些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村里的水井周围开始变得冷落起来,甚至许多村子里的水井四周都已经荒草丛生,或者干脆被掩埋了。洗涮衣服这样一件在过去看来属于公共生活领域的事情,退回到了家庭内部成为个体生活的一部分,与之相关的公共生活也随之丧失。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政府统一建设的村广场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公共空间,这些都应该成为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民俗学所要特别关注的空间议题。
城市社会中,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一般表现为街头巷尾,比如成都地区的茶馆,老北京地区的胡同、“杂吧地儿”,现代城市里形形色色的酒吧、餐厅、咖啡馆等。王笛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文化时说道:“中国茶馆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中国茶馆也是一个人们传播交流信息和表达意见的空间。”b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26—427页。岳永逸在关注老北京“杂吧地儿”时指出,“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可能生存的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行的动力与助力。”a岳永逸:《“杂吧地儿”: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一种方法》,《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城市中这些非正式公共空间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往往难以截然分开,一个顾客或一个看客的私人事务,很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并迅速以话题的形式成为公共事务。
与非正式公共空间不同,城市中正式的公共空间往往具有较为确定的边界,它们往往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如“广场”。在现代城市社会,广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更多的公共空间以城市公园、小区健身器材置放区、棚式或露天菜市场等形式出现。这些公共空间,是人们表达地方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地方,是人们组织日常生活的场所。
(三)神圣空间与神圣体验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将空间结构置于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民俗事象、文化设置、生计策略、劳作模式等社会现实同等的地位来考虑,但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划分,也不难看出,空间结构与上述社会现实存在着深刻内在的关联。
比如传统社会,民间盖房上梁时,会在承载整个屋脊重量的木梁上贴“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字样,以宣示此木梁所涉及的建筑空间已经被“太公”(即姜子牙)所保护,具有了神圣意味,任何妖魔邪祟都不得侵扰生活于该建筑空间的人们。此时,普通的建筑空间就具有了神圣性。在世俗的生活空间内制造出神圣空间,一方面用来确定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们处理神圣与世俗事务的行为边界;另一方面用来确定人与人的关系。b岳永逸:《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所有二元划分的空间都是一种相对存在,比如世俗空间只有与神圣空间进行对照时,才能显示其社会意义。
范热内普说,“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唯一用来对此社会划分的分水岭便是对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亦即世俗与神圣之区分。”c[法]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根据生活体验和生活诉求,日常生活可分为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与之对应,日常空间也可分为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
人们最初在日常空间中分化出神圣空间,也许正是认定这些空间有助于神灵显现。从逻辑上思考清楚神祇显灵的原因并不容易也无必要,人们往往从直观的时间、空间、建筑、身体、仪式等出发,通过重复这些可知可感的因素,以还原神显的原始情境,从而获得新的可重复的神显。正如雷尔夫所言,“神圣空间是古代人的宗教体验,并由各种符号、神圣中心与充满意义的事物分化出多种多样的形式。”d[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第25页。此时,时间、空间、建筑、身体、仪式等,都具有了神圣性。
神圣空间并非简单地与世俗空间进行隔离,而是在诸多要素共同作用下,为人们提供某种神圣体验,使得人们相信进入且只有进入这些空间,才具有和神灵沟通的可能性。此时,神圣空间成为人与神进行沟通的场所,成为信仰的地域中心,比如某座庙宇以及某个神龛或某座神像所在的空间。神圣空间是人们为满足宗教情感而创造出的社会空间。比如村落中存活了数百年的古树,人们一旦认为其具备了神性,那么这棵树连同周边的空地,便都具备了神圣性。更进一步,人们可能会在该树附近建一座神庙,增加其神圣性。这样,一个原本属于自然界“无机”的物理空间,变成了社会生活领域“有机”的神圣空间。
神圣行为需要在神圣空间举行。因为在人们的生活观念里,人与神的交流非比寻常,它需要一种与日常和世俗并不相同的社会情境,其中神圣空间是隔绝日常与世俗的必备条件。比如,进入神圣空间时需要跨越一种有形的门槛,这无疑使得进入其中的人们具有了某种边界意识,即从世俗走入神圣,从日常进入非常,从人与人的关系进入人与神的关系。
俗话说,“世上至理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之所以“僧”要占“名山”,一方面与其远离人世有助于静心修行有关;另一方面,将庙宇建在深山老林或山势险峻之处,也有助于维护神灵的神圣性,这是吸引民众信仰的重要因素。信众登顶圣山或建有神庙的山顶,便远离了世俗的生活从而接近了神圣的中心,在最高平台上,不仅从视觉上产生“一览众山小”的神圣感,更从心理上产生“恐惊天上人”的神圣感,人们会在烟雾缭绕的香火、栩栩如生的神像和各种早已深植内心的口头传说等诸多元素影响下,进入另一个境界,超越于世俗空间,从而进入一片“净土”。比如有“五岳独尊”的泰山,因其东岳大帝信仰和历史上的皇帝多次封禅而被视为圣山,对不少信众来说,一步步攀登上 “十八盘”而进入“南天门”是表达虔诚的一种方式,在信众看来,这样做才有机会得到神灵照应。
神圣空间是人们为满足宗教情感而创造出的社会空间。对于民俗学而言,我们在关注信仰、仪式等民俗事象时,不能忽视神圣空间的相关论题。比如神庙、宗祠等,这些神圣空间本身在完成神圣仪式或祭祀等职能外,有时也会承担公共空间职能。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议题,比如邻里或族内纠纷的处理。因此,观察这些神圣空间的位置、构造、历史变迁及其象征意义,对于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观念和意义世界都有裨益。
结 语
日常生活转向是现代民俗学学术视域拓展和学科自觉的选择。对于民俗学学术视域而言,日常生活是一切民俗事象和民俗实践的寓所,它既是我们观照民俗事象和民俗实践的语境,又是我们通过民俗事象和民俗实践进行观照的对象。简言之,日常生活拓展了现代民俗学的关注视域。对于民俗学学科来说,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民俗事象和民俗实践不断式微,与此同时,新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实践又没有合适路径进入民俗学研究视域。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理论给民俗学学科注入了活力。日常生活理论要求研究者在关注生活世界及其意义图景时,要特别注重关乎“人的再生产”的个体或集体的行动。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就是要特别关注个体或集体的行动及其意义的再生产,这也是当前实践民俗学讨论的基础问题之一。
日常生活并非海市蜃楼,它不仅是一种哲学概念,更是一种有着现实意义的实体存在。日常生活是个体维系再生产以及由此实现社会再生产的一切行动和观念的总和。由此,日常生活表现为社会个体或社会集体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和交流活动和日常观念体系及其实践。同时,日常生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它还是贯穿人们整个生命历程的现实存在。
民俗学关注日常生活,不仅要从哲学层面对其内在逻辑进行阐发,还要从其现实层面进行讨论。事实是,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节点,从来都是民俗学的重点关注对象。前者主要表现在通过各种岁时节日的讨论,探究民众的日常时间观念,后者主要表现在通过各种人生仪礼的讨论,探究民众对于生命过程及生命意义的理解。除日常时间和生命历程之外,日常空间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民俗学在关于空间的讨论方面,尽管也有所建树,不过,总体来说,还比较薄弱,而且没有形成较成体系的研究范式,而这应该成为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民俗学所应特别注意的学术议题。
——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