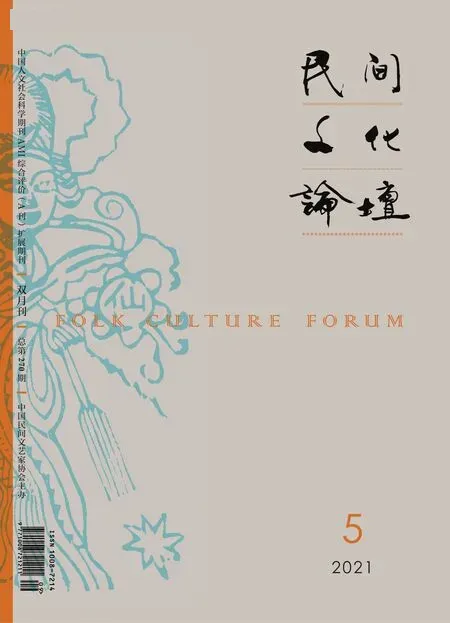试论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历史起源与现代演变
范宗朔
《玛丽亚•莫列夫娜》是一个在俄罗斯广为流传的民间童话故事,这则童话故事也被收录在阿法纳西耶夫编著的《俄罗斯童话》中。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关注到了这则故事,并从形态学意义上对这则民间童话故事内部的功能项以及故事回合进行了详细的划分a[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2页。,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历史起源的角度对这则故事进行系统的发生学层面的追溯。在结构层面,这则故事是一个具有多回合并涉及多个功能项的复杂故事;在内容层面,这则故事也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本文主要从普罗普对于民间故事的历史研究出发,结合故事发生学及流传学等不同视角,从故事情节、叙事焦点等方面详细解读这则故事文本的前世与今生。
一、普罗普与民间故事的历史研究
民间故事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载体,其发生与演变并非在一个独立的体系内完成的,而是始终与社会历史文化密不可分。普罗普认为,通过联系远古时代初民的宗教、信仰、仪式、习俗等探求民间故事的起源与演变应是故事研究的旨归,这一观点也将民间故事的研究从单纯的故事文本扩大到了社会历史层面。因此若想研究俄罗斯童话故事《玛丽亚•莫列夫娜》的起源与演变问题必定离不开历史的方法。
关于民间故事的历史研究,似乎是一个无需说明的概念,但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历史的内涵却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普罗普所倡导的历史研究作出学理性的解释。贾放在《普罗普的故事诗学》一书中总结道:“在俄罗斯历史学派眼中,故事中的‘历史’是编年史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故事文本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做考证索引工作,还未将历史分析看成是一种方法。”b贾放:《普罗普的故事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因此,寻找故事材料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对应与考证就成了历史学派研究故事的主要任务,但普罗普明确宣称,他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派的方法并不相同。他说:“起源研究就其需要和性质而言永远是历史的,但它跟历史研究不是一回事。起源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现象的产生,历史则是研究现象的发展。起源学先于历史,它为历史开辟了道路。”a[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页。在这个层面上,民间故事与历史事实并不是直线对应的,民间故事有其特有的发生规律和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并不能够直接从故事中找到真正的历史。在普罗普看来,故事历史研究的重点并非从故事中寻找真正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历史往昔。普罗普认为,故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既受到当时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跳出了经济基础的限制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换句话说,故事起源的问题应当在历史中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但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因此不能直接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去寻找故事的起源历史,因为故事中直接对于生产活动的描述是非常罕见的,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故事的各个单独母题及所有故事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被创作出来的,因此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应该成为故事发生学研究的重点。
然而社会制度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无法与具体的故事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普罗普在其著作中又将社会制度具体化为社会法规与宗教法规。就社会法规而言,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总是去远方寻找未婚妻而不是在自己的身边寻找,这一常见的情节在普罗普看来有可能是外婚制的反映,因此从发生学的层面来看,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故事中出现的婚姻形式并找到在这种形式背后的确存在过的那种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普罗普认为并非所有的故事在起源时都与社会法规有关,有些故事情节母题与社会法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普罗普又将着眼点转移到了宗教法规的层面,具体来说就是从仪式、习俗以及宗教中寻找故事的起源,尤其是故事与仪式的关系成为普罗普对于故事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他认为故事中保留着大量的仪式痕迹,许多母题只有通过与仪式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相应的解释,但故事与仪式的关系是多样的,在有些故事中存在与仪式的直接对应,但更为常见的一种模式是故事对于仪式的重解和转化。在普罗普寻找到的诸多故事源头中,他认为成年礼和死亡观念是故事起源最主要的源头。在《玛丽亚•莫列夫娜》这则故事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氏族社会成年礼仪式的痕迹,但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笔者发现这则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其所传达的基本内涵随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更替可能又发生了相应的演变。
二、《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历史起源
(一)神圣的陌生世界
在《玛丽亚•莫列夫娜》中,故事的最初情境是伊万的父母去世,伊万和三个妹妹在一起生活,接下来故事中出现了三只动物分别娶伊万的三个妹妹为妻的情节,伊万由此感到孤独便开始离开家寻找妹妹。故事开端的情节在笔者看来是成人仪式在初始阶段的一种反映。在故事中,伊万在无形之中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当中,而在氏族社会的成人仪式中,首先需要将授礼者从其熟悉的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中,这个陌生的异域空间在仪式过程中是一个独立的神圣空间,它与世俗的生活世界是断裂的,且往往带有“巫术—宗教”的特性。因为神圣与世俗的二分或对立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观念,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历史早期,神圣意志贯穿于世俗世界中。赫尔兹曾指出:“占据原始人精神世界的最基本的一组对立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对立。”a[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吴凤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8页。在故事文本中,伊万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陌生的田野中,至此在这个故事中开始有了第一次的空间转换,但具体的空间移位例如伊万如何走到田野里、走了多久以及走了多远的距离,在故事当中并没有展开叙述,可见伊万在故事中并非平面地行进,而是跳跃式地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中。这种行为带有一种超时间性和神秘性,而正是这种神秘性恰恰可以说明伊万进入的空间与日常的时空是不同的。在成人仪式中,这种时空转换就象征着被授礼者从世俗空间到神圣空间的过渡。在神圣空间中,个体的行动天然地就具有了“神圣—宗教性”。因此故事开端时空转换的象征意义,可能就是使主人公首先完成与现实世界的分隔,进而为其接下来的仪式过程做好准备。
接下来伊万在田野中遇到了玛丽亚•莫列夫娜,并在她的白色帐篷中住了两晚,随后便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结了婚。这一情节也带有明显的成人仪式的痕迹。一方面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推测伊万进入的田野很可能就是氏族社会举行成人仪式的神圣场所,而在田野中出现的白色帐篷便有可能是通往另一个世界入口的象征。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认为:“准确地说,对于普通住宅,门是外部世界与家内世界间之界限;对于寺庙,它是平凡与神圣世界间之界限。所以,跨越这个门界就是将自己与新世界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也是结婚、收养、神职授任和丧葬仪式中的一项重要行为。”b[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页。作为个体的伊万在进入帐篷前后的状态是不同的,进入帐篷之前伊万独自生活成长,但进入帐篷之后伊万便与玛丽亚•莫列夫娜成婚,随后便同玛丽亚•莫列夫娜一起回到了她的国家。除此之外,伊万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婚姻在这则故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这里出现的是伊万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第一次婚姻,但他们的这次婚姻在故事文本中是一件很突然与模糊的事情,结婚的前因后果在故事中交代得并不明确,而正是这种神秘性恰恰也能够说明伊万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结婚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婚姻,而是伊万通过田野中的帐篷进入神圣的仪式世界之后与另一世界居住者的婚礼,其目的可能是使得主人公与神圣的仪式世界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进而更好地完成主人公的成人仪式。
(二)神圣世界中的考验
主人公通过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分离进入到了神圣的仪式世界当中,但在仪式世界中,此时的主人公本身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生命状态,游离于新旧世界边缘。范热内普认为:“凡是通过此地狱去另一地狱者都会感到从身体上与巫术—宗教意义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一种特别境地:他游动于两个世界之间。”c同上,第15页。他把这种境地称为“边缘”。在《玛丽亚•莫列夫娜》中,伊万从失妻到寻妻这一过程标志着成人仪式的正式开启,而在这一阶段,主人公通常将在神圣的仪式时空中完成难题考验。范热内普将这一阶段称之为“阈限礼仪”。在故事中,伊万寻妻的整个过程就是成人仪式中难题考验的一种变体,也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情节。普罗普也曾指出,在民间故事中,孩子们被送到或者被驱逐到森林里、被妖怪劫走、小木屋、碎尸与再生、获得宝物与神奇的帮手等母题都是源于成年礼的授礼仪式,在这一阶段,伊万的暂死与再生以及妖怪科谢依、老妖婆以及感恩动物们的出现,都与授礼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故事文本中,伊万打破禁忌,释放了妖怪科谢依,导致玛丽亚•莫列夫娜被劫走,伊万再次出发寻妻并被科谢依杀死砍碎,这一故事情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科谢依要劫走玛丽亚•莫列夫娜?在劫走玛丽亚•莫列夫娜之后科谢依为什么没有逼迫与之成亲或加害于她,甚至在故事中科谢依竟然告诉了玛丽亚•莫列夫娜如何才能获得拯救自己的神马?笔者认为,种种细节表明,科谢依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加害者与被加害者的关系。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科谢依”的意思是不死的老头,而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名字中也带有死亡的含义,再结合相关的故事情节,笔者推断在这则故事中,科谢依有可能是作为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父亲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劫走玛丽亚•莫列夫娜在本质上其实是对主人公能否获取婚姻权利甚至是王位继承权的一种考验,并且在考验过程中对伊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和引导。例如,在故事文本中,科谢依将伊万杀死并且剁碎,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很残忍的行为,但在仪式世界中,被授礼者需要死去和复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被授礼者可能会获得一种魔力。在萨满教中,身体被砍碎撕碎是一个人成为萨满之前所必备的条件。因此科谢依杀死伊万实际上是对伊万的一种帮助。除此之外,科谢依还对主人公顺利完成考验进行了引导,间接告诉了伊万需要到老妖婆那里获取神马才能拯救玛丽亚•莫列夫娜。伊万在渡过火焰河寻找老妖婆的路上遇到了鸟、蜜蜂、狮子等三只动物,这三只动物告诉伊万不要吃它们的孩子,它们就会帮助伊万获取神马。伊万并没有吃掉这些动物,普罗普认为,这些不该吃且后来会提供帮助的动物是作为图腾祖先存在的。因此这三只感恩的动物有可能是作为主人公已故的祖先而存在的,它们在仪式世界中代表着主人公的图腾归属。图腾归属对于部落氏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凝聚部落的结构秩序,而举行成人仪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被授礼者重新建立与图腾祖先同一性的认同,因此原始氏族部落往往会在仪式中重新巩固这种认同感。这些动物在故事文本中能够为主人公提供帮助,还原到仪式过程中就相当于把氏族的图腾神话传给被授礼者。在故事中,主人公就如同仪式的被授礼者一样通过图腾祖先建立起了对于氏族图腾的同一性认同。
在主人公的考验过程中,老妖婆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事文本对老妖婆居住的房子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老妖婆房子的周围竖着12根杆子,其中的11根杆子上挂着人头骨,只有1根空着。这一细节对于推断老妖婆与仪式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故事文本中,对于老妖婆房子构造的描写与仪式中男性公房的特点是极为相似的。男性公房是氏族社会所特有的一种产物,“它的产生取决于狩猎作为物质生活生产的基本形式,取决于图腾崇拜作为该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在农业生产刚刚兴起的地方,这种制度还存在着,但趋于退化,有时形式上还会发生一些畸变。男性公房的功能五花八门且不固定。完全可以断定,在一定的时候,一部分男性即那些进入性成熟期又尚未结婚的青年男子已经不与父母合住,而是要搬到专门为此而建的大房子里去,这些屋子被称为‘男人的屋子’‘男性公房’或‘单身汉的屋子’,他们在此过着特殊的公社式的生活。”a[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第133页。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普罗普列举了男性公房的几大特征,分别是:(1)房子坐落在树林深处,也可能不是;(2)它以庞大为特点;(3)房子有围墙环绕,有时还装饰以骷髅头;(4)它建在木桩上;(5)入口是一架梯子或柱子;(6)入口和其他的洞孔都被遮挡关闭;(7)里面有几个房间。b同上,第137页。不难发现,故事中保留了极其鲜明的氏族社会男性公房制度的痕迹。但在这个故事中,老妖婆作为一个女性形象为什么会居住在男性公房里参与男子的成年仪式?因为人和妇女等通常是被禁止参与进来的。笔者推断,老妖婆这一形象在故事文本中虽然是作为加害者出现的,但在仪式过程中,老妖婆可能是仪式过程的主持人。因为在普罗普看来,女性、老太婆、母亲、女主人等形象是最早的“神性的赐予者”,正是由于她们自身的神性色彩,成年礼授礼仪式的主持人总是与主人公的妻子或母亲等女性形象沾亲带故,而与男性形象并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状况与后来“历史形成的男性权力发生了冲突”,而摆脱这种冲突的方式之一便是仪式的主持者改头换面扮成女人,因此笔者推断,老妖婆在仪式世界中有可能是一位装扮成女性的男性祭司或仪式主持人参与到仪式进程中。
(三)伊万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的两次婚姻
在《玛丽亚•莫列夫娜》故事中,伊万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在故事的起始阶段,伊万在田野中第一次遇到玛丽亚•莫列夫娜并与之结婚,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判断,伊万的第一次结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而更多的是为了主人公能够更顺利地进入成人仪式并完成相应的考验而做的前提准备。在故事结尾,伊万在考验中完成老妖婆的难题并得到老妖婆的神马,借助神马的力量,伊万与玛丽亚•莫列夫娜最后终于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故事的结尾可以说是伊万第二次婚姻的一种变体,是真正的结婚。在第二次婚姻的过程中,神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神马,普罗普认为,在魔法故事中主人公以马为坐骑能够说明这则故事反映的历史与成年礼有关。
在《玛丽亚•莫列夫娜》中,伊万通过喂养赋予马神奇的力量,使马具有了像鸟一样飞行的神力。在这里马与鸟发生了一种同化现象,会飞的神马其实就是鸟马合一。在仪式当中,马作为一种骑乘用的动物通常为死者陪葬,普罗普认为,主人公骑马飞行反映的其实是骑鸟飞行的另一个阶段:飞往冥国。但在《玛丽亚•莫列夫娜》故事中,神马是在伊万完成考验之后出现的,马在故事中作为一种骑乘动物的功能没有变化,但目的地在故事中发生了转变,它并非飞往冥国,而是作为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载体存在的。在这里出现了整个故事的第三次空间移动。这次的时空转换代表着主人公完成了冥国之旅,需要重新返回现实世界。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再一次从现有状态中分离出去,只不过这一次伊万所分离的那个世界是仪式的世界,而主人公从仪式世界中分离出来重新进入日常世界的方式,就是通过再次举行婚礼或重新确认婚姻关系来实现的。据此可以判断,故事最后伊万救出玛丽亚•莫列夫娜并与之一起回家才是正式婚礼的一种变形。
“返回家中”这一行为本身便是从神圣的仪式空间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象征,但此时的现实世界已不同于故事的最初情境。一方面,主人公自身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年轻少年变为成年男性;另一方面,婚姻也促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结婚成为从一社会地位到另一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过渡,因为至少婚姻一方需转换家庭、家族、村落或部落,有时新婚双方还需建立新居处。”a[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第87页。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民间故事大多都以婚姻作为结尾,因为这种结局既不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幻想,而是指涉了一种仪式的真实。故事最后的婚礼往往是幸福圆满的,这与主人公真实婚姻是否幸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只是代表着主人公完成了仪式并成功返回了日常世界。故事结束也象征着成人仪式的结束,通过这一仪式,主人公完成了从青年到成年人的过渡,并获得了参与社会事务的资格,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结婚的资格。
(四)小结:男性的成人仪式
综上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可能并非简单的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成人仪式色彩的故事,而成人仪式也可能涉及了这则故事最初的起源。
这则故事首先通过伊万离开家寻找妹妹、被科谢依杀死等方式来实现被授礼者与现实世界的剥离,从而能够进入到一个神圣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在仪式中往往是死人的王国,是神灵的王国,是与现实世界相断裂的另一世界。在故事中出现的田野中的帐篷以及有着禁忌的房间可能就象征了进入另一世界的入口。但是仪式中的被授礼者一定要违反禁忌、打开禁忌之门,因为如果不打开禁忌之门就无法完成仪式。在仪式过程中,主人公通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与挑战,但在这期间,主人公会得到图腾祖先以及仪式主持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包括赠与主人公法宝或传授本领等等,以帮助主人公解决难题进而完成仪式任务。完成仪式后,主人公通过最后的婚礼以一个新人的身份重新进入日常世界,正是在这种从离开到回归的整个仪式过程中,主人公废除了旧有的社会属性,以一个新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到社会中。经过这个仪式,故事主人公被赋予了新的属性和新的地位,他可能从一个普通人转变为祭司或者巫师的继任者,或者成为部落的正式成员,这些转变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
虽然这则故事可能最早诞生于成人礼仪盛行的氏族社会中,但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变迁,这则故事流传到今天,故事中的一些细节也显示了当下对于这个故事关注焦点的转变,其关注点已经不再是远古时期的成人仪式,而是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三、《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现代演变
(一)故事题目的焦点转换
如果单纯从内容上来看,绝大多数读者会认为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伊万王子以及他多次历险的爱情故事,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伊万身上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这则故事的题目被定为“玛丽亚•莫列夫娜”而非“伊万的故事”。当然就这则故事的题目而言,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最早是谁在什么历史时期添加的,但就这则故事的不同异文来说,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名字确是这则故事中的不变因素。除此之外,对照这则故事的不同异文,我们也会发现全文只有玛丽亚•莫列夫娜一人是有名有姓的,并且在故事中总是用她的姓名全称来讲述她,而在故事中出现的其他大部分人物的名字都是不完整的,有的角色有名无姓,比如伊万、科谢伊等,甚至还有些角色连名字也没有,比如故事开始出现的雕、老鹰和渡鸦以及后来帮助伊万的三只动物。很显然,在今天流传的这则俄罗斯童话故事似乎在向读者透露一个信息,即玛丽亚•莫列夫娜可能是这个故事叙述的主要人物,读者需要关注的应该是玛丽亚•莫列夫娜而并非是伊万。
经过这样一个焦点的转换,故事的内涵以及所要传达的意义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玛丽亚•莫列夫娜作为主要人物在故事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一场战争之后,她率领着军队打败了敌人。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出场及种种行为并不符合传统故事中的女性性格特征,勇猛、富有权力以及领导力是玛丽亚•莫列夫娜带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而伊万在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的对比中也呈现了与传统男性并不相符的特点。他在与玛丽亚•莫列夫娜结婚后竟然选择离开家前往妻子的国家生活,这并不符合父权制文化中妻子通常会住在丈夫家里的传统。从这几点来看,笔者以为,在故事中玛丽亚•莫列夫娜与伊万这对夫妻可能存在着一种性别互换的关系,或者说是角色互换的关系。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伊万的形象可以被理解为是玛丽亚•莫列夫娜内心的一部分投射,也就是说伊万是玛丽亚•莫列夫娜身上存在着的男性倾向的一种体现,而这也正是荣格所认为的“阿尼姆斯”原型。阿尼姆斯原型指涉的是女性心理中的男性一面,包括刚性、侵略性、好斗等特质。
倘若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这则故事流传到今天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既不是有关男性成年的故事,也并非民众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具有“阿尼姆斯”原型投射的女性故事。
(二)被父亲的阴影所劫持
在荣格看来,阿尼姆斯原型是无意识的一部分,而无意识的内容总是要通过禁忌与打破禁忌体现出来。禁忌在神话或民间故事中通常以食物或者房间作为象征物,并且在心理学上禁忌通常代表着压抑,告诉人们不可以去看、去接触,因为里面的东西是人的意识不愿意接触的。而一旦碰触了,那些被意识排斥、抗拒的东西会从潜意识里释放出来,但是人为了要走向自我成长的历程,必须要去打破禁忌。
伊万打破了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禁忌,在密室中发现并释放了科谢依,这就相当于玛丽亚•莫列夫娜内心抗拒的那一部分无意识被释放了出来,科谢伊象征着她童年不愿触碰的阴影。荣格认为,“对于女人的阿尼姆斯产生决定影响的是她的父亲,父亲赋予他女儿一种独有的特征,赋予她种种无以争辩的、令人确信不疑的‘真实’信念——永远将女人作为真实自我的个体真实性排除在外的信念。”a[瑞士]荣格:《潜意识与心灵成长》,《荣格作品集》,张月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86页。如果带着荣格的结论再回到故事文本中,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父亲应该对她阿尼姆斯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关键的影响。但在故事文本中并没有玛丽亚•莫列夫娜父亲的相关叙述,所以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科谢伊本身就是玛丽亚心中对于父亲的阴影。按照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解读科谢伊劫走玛丽亚•莫列夫娜的情节就代表着玛丽亚•莫列夫娜被父亲的阴影所劫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谢依在劫走玛丽亚•莫列夫娜之后并没有对她实施任何的加害行为。
而玛丽亚•莫列夫娜之所以会被父亲的阴影所控制,笔者推断是由于在这之前玛丽亚•莫列夫娜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多次率军外出征战,做出了一系列不符合传统女性特征的行为。当她被科谢依抓起来之后就象征着失去了自由,这与父亲对试图冲破束缚的女儿的惩罚极为相似。因此科谢依在故事中劫走玛丽亚•莫列夫娜的目的可能就是强迫她从一个阿尼姆斯人格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掌控者回归为传统的女性形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她从一个女王转变为一个公主。从这个层面来看,玛丽亚•莫列夫娜被科谢依劫走实质上是玛丽亚•莫列夫娜从阿尼姆斯人格向传统女性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三)玛丽亚•莫列夫娜的转变与成长
玛丽亚•莫列夫娜在被科谢依劫走之后,整个故事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伊万拯救玛丽亚•莫列夫娜的过程其实就是玛丽亚自身的转变与成长的过程。
伊万在寻找老妖婆的路途中遇到了三只动物,这三只动物与故事开始出现的雕、老鹰和渡鸦不同,在这里出现的三只动物都是母亲的形象,并且作为感恩的动物给予伊万帮助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不要吃它们的孩子,除此之外,这三只动物并没有让伊万去完成很复杂的任务,这一情节在这个故事中实质上体现了母亲对于孩子的一种舐犊之情,而这也正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感情。
除此之外,蜂后让伊万选择一匹长着癣的马帮助他逃跑这个细节也值得注意。为什么要选择一匹长着癣的弱马,而不是选择一匹强壮的马帮助他逃跑?故事下文给出了答案。伊万在喂养了这匹长着癣的小马之后,它变成了一匹会飞的神马,而如果一开始就选择一匹强壮的骏马,那么接下来伊万可能就需要去控制、制服这匹马才能带他逃走。所以这一情节暗含了传统女性的特质更多的体现为关爱、培育而不是去制服和控制。
故事最后,蜂后帮助伊万避免被老妖婆杀死,这说明了在这个故事中强调和认同的是蜂后等三只动物母亲所传递的信息,而并非老妖婆身上所传达的信息。因为老妖婆代表的是一种扭曲、极端、负面的女性形象,而三只母性动物的形象则象征着对于女性真正的肯定。所以这一部分情节讲述的其实就是玛丽亚•莫列夫娜从科谢依的囚禁下得到拯救的办法,这三只母性动物所传达的信息就是玛丽亚•莫列夫娜恢复自由与成长的关键。
(四)小结:女性的自我成长
《玛丽亚•莫列夫娜》这则俄罗斯童话故事自诞生以来流传发展到今天,其承载的内涵与外延随着社会制度更替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总的来看,这个故事在今天更多的是围绕玛丽亚•莫列夫娜这个女性形象展开,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女性如何自我成长的故事。在这个层面上,荣格提出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能够为这则故事在当代所传达的意义做出一个自洽的说明。在荣格看来,“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的功能是以性别互补的方式缓解了两性对立,表达了一种两性心理互补现象。在这个故事中,玛丽亚•莫列夫娜自身“阿尼姆斯”人格原型存在的功能可能就是,向那些富有权力的女性呈现如何实现自身人格的和谐或平衡这个在当今很容易忽略或被遗忘的问题。
四、结 语
通过分析这则广为流传的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我们既能够在《玛丽亚•莫列夫娜》故事文本中找到成人仪式与故事起源之间的联系,又能够感受到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在现代社会中的演变。在故事的叙事层面,故事时空的转换是成人仪式的直观表达,从世俗到神圣再到世俗这三次时空转换分别对应成人仪式中三个不同的阶段,从而展现出主人公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不同状态。在故事的内容层面,叙述的焦点随着故事的流传而不断发生转变,在今天,整个故事围绕着玛丽亚•莫列夫娜的成长与自由而展开。但无论故事讲述的是神圣的成人仪式还是女性的自我成长,这则故事自产生之日起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关怀与探索,并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以多样的方式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