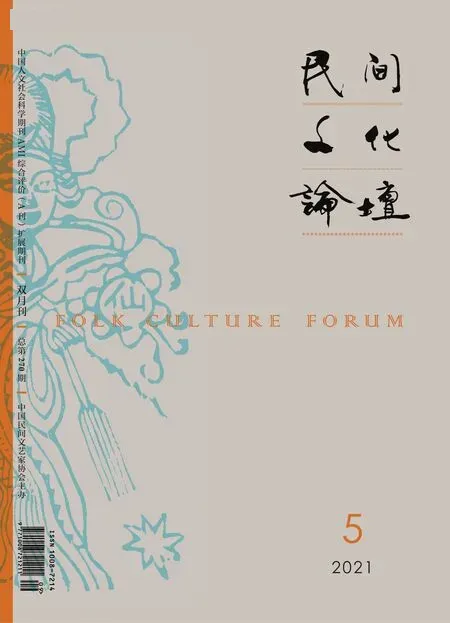与日本“中国民话之会”及相关学者交流印象记
陈勤建
最早,我得知日本有个“中国民话之会”,是1979年夏天,在北京师范大学红楼钟老——钟敬文教授寓所书房里,从他老人家对我学术训导中获悉的。
那一年,华东师范大学主持中文系工作的徐中玉教授,破格指派留校不久的我,为同一文艺理论教研室退休刚回聘的民间文艺专家罗永麟先生当助手。罗永麟先生是中国首先命名四大民间传说——《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民间文艺学专家。为了更好地发展中文系的文艺学,徐中玉先生认为,学科的内涵要丰富,拓展文艺学——民间文艺学是一个不可缺失的方向,同时,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内容也要多彩。为此,徐中玉先生就亲自修书一封,委派我前往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处,参加由中国教育部批准、钟先生主持的首届中国高校民间文学骨干青年教师暑期讲习班进修。因为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研室经过一段中外文艺理论的熏陶,初接触民间文学,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学习期间,对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常有一点“胡言乱语”,其中,可能也不乏尚不成熟的新见。不料由此引起了在课堂研讨旁听的钟先生的关注,课后他勉励了我,并邀我早晨陪他在操场上散步谈话,去他家聊天,这使我有机会零距离地倾听钟先生的教诲。
进修结束回上海后,罗永麟先生认为民间文学是活在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要搞好民间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一定要到社会实践中去。于是,他推荐我前往正在市文联筹建中国民研会上海分会(国内先于中国民研会,首个更名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以下简称上海民协)的任嘉禾先生处工作,参与社会的民间文学活动。自1980年初参与上海民协工作开始,至1998年底,前后18年,我成了中国民间文艺界奇特的“双面人”:一面是大学老师,一面在协会工作,并从一个协会的志愿者,逐步兼任了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以及协会主办的中国第一家民间文学作品刊物《采风报》编辑、副主编、主编,学术理论刊物《民间文艺季刊》副主编。1990年起,全面主持上海民协以及两个刊物的日常工作。《采风报》,主要刊登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人士民间采集的各类民间文学以及“新故事”和民间风俗。《采风报》创办,为中国民间文艺界递送了一股清新刚健,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艺新风,赢得中国广大民众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爱戴,每天全国民间自发投稿量之多,上海邮电局不得不派两大卡车搬运。发行量节节攀升,最高每期达180多万份,畅销全国。协会主办理论刊物《民间文艺季刊》是全国公开发行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兼有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性专业刊物,每期二十余万字,也是自筹资金,由《采风报》盈利资金支撑它的出版、发行与作者的稿费。它的面世,为中国高校及各省市学界提供了专业研究阵地,质量上乘,影响很大。同时,其学术影响力传到海外,中国新华书店每期订购上千册,远销全球。
上海民间文学一报一刊的创办出版发行,得到了中国民协各级机构和兼任中国民协领导职务的贾芝先生、钟敬文教授和后来主持工作的刘锡诚先生及刘魁立老师的大力鼓励支持、关心指导。因上海民协和报刊工作的需要,我也有了更多机会,进京到中国民协汇报交流,每次也必然去北师大钟老寓所执弟子之礼,向老人家请教。而钟老总是不厌其烦,详细了解上海协会、刊物和大学民间文学工作、教学和研究状况及其他熟悉的学人故友的现状,激励我排除万难,主持好上海协会、刊物的同时,搞好大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是一项光荣与伟大的事业,国际学界也在关注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他指出,除了日本学界有以中国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机构——“中国民话之会”,美国、苏联等外国学者也在关注它,并教导我在搞好国内专业的同时,要关注国际学人之间的学术交流。
1976年以后,中国迎来了文学艺术繁荣的春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民间文学事业得到大发展。在独立创办民间文学一报一刊公开发行后,海内外声誉剧增,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纷至沓来,寻求合作采风,交流研究。首先是上海的近邻浙江省与江苏省的同仁。上海地处 “吴尾越角”,在文化源流上与浙江、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文学更是如此。在首任上海民研会主席的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二任主席姜彬先生挂帅下,任嘉禾先生主办,我协办联络,江浙沪二省一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很快就成立了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联合展开吴歌、四大传说等民间文艺专题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等,一时搞得轰轰烈烈,影响巨大。海外学者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闻讯前来洽谈或展开研究交流事宜。上海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的经济文化大都市,历来就是国际各界人士来往中国的重要门户,另外,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得以快速地恢复和发展,上海民协又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和雄厚的学术力量,因故,上海民协八九十年代接待任务很重。期间,与美国、日本、苏联、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相关研究机构或个人或团体有交流。如首访中国的美国著名中国民间故事学专家华裔学者丁乃通,美国及世界民俗学会前主席阿兰•邓迪斯,他们都是由我机场接机并全程陪同接待交流的。但是,我记忆中首次接触参与接待国外合作研究交流的是日本民间文学界——日本口承文艺学会。
1980年12月10日至16日,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以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臼田甚五郎先生为团长的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民间文学代表团访华。臼田甚五郎教授是日本的国学大师,为日本全国规模的学会——歌谣学会创立者与会长,也是日本口承文艺学会的会长。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民间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当时,中国民研会要求上海民研会后两天接待臼田甚五郎教授一行,进行短暂学术交流。上海民研会会长(改名上海民协后,会长称主席)赵景深先生身体欠佳,由常务副会长姜彬先生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任嘉禾先生接待。我虽然刚到民研会协助工作不久,但因日方团长臼田甚五郎教授要求拜访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老专家罗永麟先生,我本来就是罗先生的助手,学会就指派我与翻译陪同他前往华东师大罗先生寓所交流。罗先生青年时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过。我们进门,罗先生即用日语表达欢迎之意,臼田甚五郎教授一脸惊喜。双方寒暄过后,就民间歌谣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研讨中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普遍不以为然没加以深究的事,臼田甚五郎教授却特别“顶真”。他反复问道:中国为何将民歌又称为山歌?山歌是否是山区的民歌?上海和苏南及杭嘉湖平原没有山或山不多,当地唱吴歌,为啥也称“唱山歌”?
那时,我不知道首次陪同的以臼田甚五郎教授为团长的日本民间文学访华团,是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以下简称民话之会)借口承文艺学会名义组团访华的。民话之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会,他们是日本一群爱好和关注新中国民间文艺的学者的群体。为了更好地和中国交流,所以请了本学科最有代表性的臼田甚五郎教授任会长的口承文艺学会出面,而中国方面根本没介意。
80年代开始,中日民间文学交流日益兴旺。日本学者与上海进行学术交流者甚多。如姜彬先生和我应邀与时任东京大学教师的田仲一成教授、丸尾常喜教授、大木康副教授、学习院大学的诹访春雄教授等有过多年中日合作研究。日方学者一般没有介绍自己在日本属于什么学会,而我们也只认专业,从来不主动询问对方归属何种学会。期间,常有熟人介绍来上海顺道访问交流的。
因为是熟人介绍,所以更不探究,几乎闹出笑话。80年代中期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埋头在上海巨鹿路675号上海民协办公室兼《采风报》编辑部审稿。突然,一个带有中国南方口音的女孩低声问道:“陈勤建先生在吗?”我应了一声“在”,抬头一看,两个穿戴青春时尚女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姑娘,一脸腼腆羞怯看着我。从未见过,谁啊?我一愣。上海民协报刊影响日增,日常来访者不少,见多不怪了,就随口问道“有事么?”“钟敬文先生介绍我们向你请教。”一听是钟先生介绍,我忙停下手中的活与她们聊起来。看着俩人的模样,我估摸着她们是从广州方向过来的,她们说“是”。所以进一步自以为她俩是钟先生当年工作的中山大学的学生。那里有钟先生1966年前招收的最后一位研究生叶春生先生当教授,是当代中国高校民间文学的教学研究的重镇,故就更不探问,而直接谈起当代中国民协系统和高校民间文学以及采风、《民间文艺季刊》的发展成绩和不足之处。她俩谦虚地恭听着,偶尔插话提些问题。谈了一会,我突然发现,领头的小姑娘戴了结婚戒指,便随意问了一句:“你结婚啦?先生什么工作?”“日本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我一听,一脸惊讶,怎么回事?看出我的尴尬,她忙解释道:“您开始也没问,我们都是日本人,我在钟先生处读过研究生,叫中原律子,她也是研究生毕业,从事相关研究,名为冈崎由美。”她俩年轻俊俏,一口中国话,我竟然一开始就误认为她们是中国人了,真不好意思。后来我知道中原律子(即广田律子)教授是民话之会的成员,我俩事后的二三十年间,保持着学术的友好交往,多次合作田野考察研究。她对我及我国与日本学界学人密切联系、合作交流帮助极大。1998年,她向宫田登先生引荐,并由宫田登先生推荐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赴日本京都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参加日本分子人类学(生命科学)发起主办的“从环太平洋看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起源”全球性国际会议。在大会上我作了《关于中国江南稻作鸟(日)传说信仰在日本传播衍化》的主题报告,受到很大的鼓励。21世纪初,我的博士生尹笑非在神奈川大学研修,又是她主动当导师,悉心关照。一次雨雪,尹博士一时没合适的鞋,又是她自己掏钱给她买鞋穿。这一切终身难忘。
熟人推荐顺道与上海民协进行学术交流的民话之会的成员,印象深刻的还有加藤千代女士等。她们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过程中,对中国的新故事发生浓厚的兴趣。上海是中国新故事的策源地,又有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公开出版物《故事会》,到上海交流,也是当然的事。出于友好交往,我与协会多次接待她们,安排人员座谈,组织交流。我们侧面听说加藤千代与她朋友在日本国内一度境遇有点困难,但是,却在中国一头扎在学术研究中,令人佩服。
臼田甚五郎教授顺访回国后,经乌丙安教授牵线,上海民协正式邀请日本臼田甚五郎教授、小岛美子教授等日本歌谣学会三人团,前来上海及苏南地区进行吴地吴歌的考察研究。1988年下半年,臼田甚五郎教授以日本歌谣学会(学科上与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一个系统)会长的名义,邀请我们上海民协主席姜彬、副主席任嘉禾、王文华和我四人赴日回访考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学术考察交流,有几件事印象极为深刻。
一是富而不奢。抵日后,臼田甚五郎教授一行举行日本料理晚宴为我们洗尘,席间双方相聚甚欢。餐后多余的料理,日方全悉打包,没有一点浪费。有一双多余的公筷,没想到酒酣微醺的臼田甚五郎教授见了,微笑说了一句日语,意思是不要浪费,随手打开高档时髦西装,把它放进里侧插钢笔的口袋。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一幕至今还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8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民生富庶,然富而不浪费一点可用之材,深深打动了我。我回国后至今,在外用餐等,多余必打包而归。
二是传统与现代的密切融合。现今,我国对此的认知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当初却有一些人包括学者认为,现代化必将把那些土得掉了渣的传统文化扔掉。没想到,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在西风吹拂下,衣食住行、礼仪交往等细微末节处处留有日本传统的模式和印记。饭后,随坐臼田甚五郎教授私家车送我们去宾馆。车路经其家,我们请他先回家,推辞不了,他下了车。我转眼望去,一个草木簇拥的日式小庭院,往里一座精致的小木屋。随着汽车喇叭声响,木屋的木格栅条移门打开,一位穿着日式和服的老太太俯身跪着迎接臼田甚五郎教授进门,而微醉的臼田甚五郎教授,似乎不及应诺,却嚷嚷着他的助手,要好好送我们回宾馆。原以为只应在电影或小说里才能见到的场景,没想到在现实中出现了。
三是日本高校文学研究者对民间文学价值学识、学理上的认同和重视。80年代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统文化再一次受到严重的冲击。虽然民间文学界自身在努力恢复发展,一度颇为兴旺,但是另一方面,整个文学界成“两张皮”,特别是搞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研究者,却对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学予以否认与排斥。其间一些搞理论的学人,言必称欧美某某主义,倡导“纯文学”。有一国内名校著名古典文学教授公然宣称,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与民歌没有关系,全是文人创作的纯文学。臼田甚五郎教授邀请我们访日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参加日本歌谣学会的全国大会。进会场前,我以为就是民歌手及爱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不料,在双方寒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不少是日本大学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博士教授。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阿部教授,在大会主题演讲中,洋洋洒洒地解读了日本古典《万叶集》和歌与日本民歌的密切联系,并热情洋溢唱起了日本的民歌,把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会后,我在住宿地偶遇一位我国在日公派生,谈起会议情况,他看了我与会过程中日方学者赠送的一张张名片,兴奋地在床边一蹦三尺高,羡慕地说:“陈先生,你真好运气,遇到了这么多日本博士教授。”我不解,他解释道:据他了解,到当时为止,“全日本高校有博士学位的文学教授,不到百余位,我来了三年,才见到几位,你怎么一下见了几十位呢?”是啊,一个民间歌谣学会,引来这么多古典国学名教授参与,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啊。
四是学识学术上的共同推进。受国内80年代多学科交融、学术创新思潮的影响,身在中文系从文艺学转向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我,力图在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创出一条新路,提出了“文艺民俗学” 的理论路径,经评审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申报的中国文学研究八五规划唯一的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成为其中一个子项目。当时,我已大致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初稿。然而,毕竟是第一次做国家课题,也不知道国外类似的研究,心中总有些不踏实。交流中发现日本学界有类似的研究,在小岛美子教授的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工作室,研究歌谣的她正在撰写一本《音乐民俗学》,形式上真是不谋而合。后来我的文艺民俗学研究成果以专著形式公开出版了,8年后被教育部评为中国高校第二届中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受邀出席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世界民俗学大会,并作了文艺民俗批评的专题报告。澳大利亚电视台为此还对我作了专访在国际频道播放。
随着与民话之会及日本相关研究者交往的深入,学术交流由学习吸纳为主转向一定的传播交流。我多年的研究成果,中国远古江南稻作生产引发鸟(日)崇信文化的缘起及在国内外特别是在日本的衍化传播,得到日本等国际学者的关注。为此受邀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作相关议题的报告。2000年初春,我正应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樱井龙彦教授的邀请,在该校做国际交流项目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民话之会骨干新潟大学桥谷英子教授闻讯我在日本,便联络商定请我赴东京,为民话之会和研究关注中国文化的相关教授和研究人员做一次讲座,时间是3月18日。讲座原定由会长饭仓教授执掌,后来先生有事,临时由铃木健之教授主持,伊藤清司教授致辞,都立大学何彬副教授做现场翻译。何彬从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本科毕业后,投奔于钟敬文教授门下,为钟老的得意门生。硕士一年后,钟先生推荐她进入中日“联合培养”,到日本留学受教于福田亚细男教授。因经常为钟老做翻译,她早就认识了民话之会会长饭仓教授以及加藤千代、曾士才、铃木健之、桥谷英子、中原律子等民话之会的成员。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到日本进一步深造发展,经考核,进入都立大学原饭仓教授退休空缺的教师岗位,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说自己也是钟敬文教授生前钟爱(有点自卖自夸了,不好意思)的旁门弟子。因钟先生关系,我和何彬在国内就很熟悉。我到日本交流,经常得到她的关照。另外她作为中日共同培养的研究生,受过双方大师的学术熏陶,业务能力强,自然也成了中日民间文学、民俗学交流的桥梁。
讲座在东京政法大学内一个中型的会议室,从日本各地赶来听讲座的学者,大约有七八十人,有的好像不是民话之会的成员,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菅丰教授,也赶来捧场。我此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江南稻作生产的发生与鸟信仰传说崇信的缘起关系》。这是我八九十年代,对中国浙江、江苏、上海在内的中国长三角等地广泛深入调研,以及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相关研析,经过田野作业、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的爬梳三重论证得出的思考。讲座的素材,一些来自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福田亚细男教授主持,我参加的“中日环东海农耕民俗”十余年的调研。讲座的材料准备是比较充分的。
整个讲座用了一个下午。我感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国际学术交流。记忆中我讲了约2小时,听讲的学者们,提问讨论约2个半小时。会场气氛十分活跃。讲到中日双方学者在中国江南稻作区实地调研中稻作生产引发鸟(日)崇信的一些案例,非亲历者难以翻译时,桥谷教授就站起来,以一起调查的亲身所见,用日语作进一步的介绍。我讲座中所涉及一些主要资料的来源、观点的佐证等等,日本学者都要加以辨析。记得其中一幅蚩尤图,我用的二手资料,伊藤清司教授可能一眼看出来了,追问我它的实际出处。幸亏此事前,我在国内早去实地考察过实物(只因保存此物的博物馆不让拍照,只好沿用二手资料)。所以,如实做了解答,得到了伊藤清司教授的认可。会后,铃木健之教授等几位民话之会干部一起请我用晚餐。席间交流,发现席间有的教授不需要日本式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礼俗,原来他们访问中国,顺道停留上海,我还匆匆接待过。人多事杂,见面时才又想起来。此时,双方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晚宴后,由桥谷英子教授安排,坐八点多的新干线赶往新潟,次日由她与福田先生的已毕业在日工作的女博士生陈玲陪同下赴佐渡考察。我与桥谷英子(即马场英子)教授,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环东海农耕民俗”考察的合作研究中。她与她的几位挚友都是民话之会的忠诚会员。在中日民俗联合考察中,她专门调研民间文学,我也是,所以田野作业时,我们两人经常分在一个组。在中国上海郊区,浙江乡村,我主动联络地方调研对象,在日本,她全程帮我询问解惑。在上海松江乡间,我们共同发现了明代冯梦龙采集过并传承至今的民谣和谜语,我帮她解读方言校阅中文。在日本新潟,桥谷英子帮我找到了鸟崇信的物证——鸡的神社。我俩的学术合作十分融洽愉快。
佐渡,据说是日本国学大师柳田国男先生当时展开乡土研究的起点,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有一个很好的规定,每个客座研究员教授每月另有一小笔科研经费,供其游学与购买工作所需的小型电子器材。游学地我首选新潟大学与相邻的佐渡。桥谷教授欣然帮我实现这一愿望。在她的精心安排下,我如愿到达佐渡,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疲劳,在渡船中,经不住海浪的颠簸,我晕船了,原计划不能完全实现,还给桥谷教授和陈玲添了大麻烦,真不好意思。不过,也遇到了有趣的事,在我们看来,佐渡就是一个大的海岛,但是佐渡人不认为自己的居住地是个岛,而是大陆。另外,因为佐渡有金矿,在古代日本统治者眼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地。二十余年过去了,当初的佐渡之行,仿佛还在眼前。
我年届七十时,正式退休。现家中正在重新装修,书柜等全部封存,凭记忆,回顾与民话之会及相关专家学者学术交往的点点滴滴,浮想联翩。我的学术生涯,与日本学界有过颇多的交往,上述是其中的一部分。期间,受益不浅,借此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