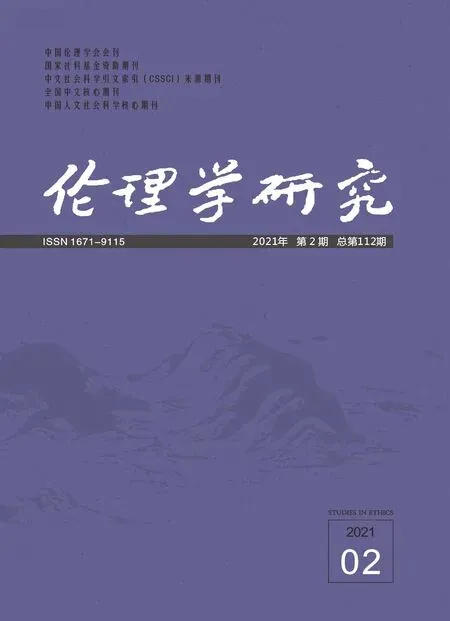中国特色集体协商的和合伦理基础及权利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集体协商是企业方与职工方就工资报酬等劳动条件签订集体合同,协调集体劳动关系,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中国特色制度。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的工作中,集体协商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但如何完善集体协商权利体系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对该问题的思考可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可概括为“传统劳权论”,即以传统集体劳权为核心展开研究,借鉴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的设置设计集体协商制度中的各项权利[1]。第二种思路可概括为“困境应对论”,即以集体协商工作中的困难出发,分析如何完善权利(力)义务设置。如认为职工方难以与企业抗衡,则建议完善政府监督保障权[2];认为企业抵制协商的行为难以纠正,则建议完善诚信谈判义务和强制性协商义务以保障协商权[3][4]。这两种思路为集体协商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对策,但集体协商制度中的权利设计应基于我国特殊国情,难以直接借鉴西方理论。针对集体协商工作实施困难,可产出一系列的实用性对策,但难以描绘集体协商权利体系的整体框架。
当前对集体协商权利设计的研究尚未对中国特色集体劳动法律关系的伦理基础给予足够关注。而伦理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在运行机理,是介于他律的法律规范和自律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规则,是法律关系和法律规范形成的基础[5]。“无论是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而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6](P162)忽视伦理基础的法律设计,不仅难以得到社会环境的接纳,更难以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集体协商权利体系的完善,还应基于中国特色的劳资伦理基础。构建在中国社会的劳资伦理关系之上的法律制度,方能发挥协调劳动关系的作用。和合伦理是中华传统伦理秩序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特色劳资伦理的重要基础,它对丰富集体协商理论内涵、构建集体协商制度体系以及完善集体协商权利设计具有重要意义[7]。
一、中国特色集体协商的和合伦理基础
和合伦理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和”“合”二字的书写。和,原指音律相和,后来发展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合”,原指唇齿相合,后来发展为社会关系中各主体的合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8](P295-296)各主体相互合作,达成社会关系和谐的和合伦理规则,在集体劳动关系治理中有重要的运用价值。在和合伦理基础上,企业方与职工方同舟共济、相互合作,达成合作发展、利益协调,形成和衷共济、和谐和睦的集体劳动关系。集体协商需建立在和合伦理的基础上,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完成劳资沟通,形成“劳资合作”,有别于西方集体谈判中劳资双方或对抗或妥协从而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劳资博弈”。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追求协商目标协调、协商行为配合、协商收益均衡,基于和合伦理中和合共生、和善诚信、和衷共济的伦理规则。
1.协商目标协调的“和合共生”伦理基础
集体协商强调协商目标的协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认为“劳动关系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2020 年5 月2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集体协商工作的通知》强调,开展集体协商,“寻求双方利益平衡点,妥善解决受疫情影响劳动关系的突出问题,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9]。集体协商中,企业方更看重经营利润,职工方更看重劳动收益,但两者的协商目标是一致的,均追求企业有序发展下的职工劳动收益的提高。如果没有企业的有序发展,职工的劳动收益也是无本之木。反之,没有职工劳动收益的保障,企业难以具备凝聚力而提升生产经营效益,经营利润的产出终成无源之水。
企业方与职工方协商目标的协调,基于“和合共生”的伦理基础。《国语·郑语》有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事物的和谐共生,才能相互促进、不断发展;如果万事万物皆相同,则难以发展。集体劳动关系中企业方、职工方追求不同但有目标调和,才能在双方各司其职中,通过企业方对生产经营事项的合理安排和职工方对劳动收益的有序谋求,建立和谐稳定的集体劳动关系治理秩序,达成企业发展和职工收益双重目标的协调和实现。因此,在劳动关系各方协商目标的协调中,职工的社会主体地位得到保障,通过集体协商表达诉求;企业具备契约意识和担当意识,正确对待职工诉求,积极对待集体协商,企业与职工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和合共生”的伦理秩序是共建集体劳动关系的基础。
2.协商行为配合的“和善诚信”伦理基础
集体协商需要协商主体协商行为的配合。集体劳动关系调整,需在企业方、职工方相互配合,精诚合作下完成。集体劳动关系一方的协商意愿,需得到另一方的充分尊重;一方在协商中的合理要求,需得到另一方的充分回应。协商双方在诚意合作、互商互量的和谐氛围下完成集体协商。
企业方与职工方协商行为的配合,源于“和善诚信”的伦理基础。儒家“仁爱”思想,丰富了“和善诚信”伦理秩序的内涵,“仁”字,即是多主体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爱护之意[10]。《论语·雍也》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公孙丑上》有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沿袭了孔子“爱人”的思想,说明了与人为善、善待他人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体间的交往中,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所思所想,尽量回应和配合他人的合理要求。在集体协商中,企业方与职工方应相互尊重,避免激励的冲突对抗,在诚信公平、相互配合的氛围下完成集体劳动关系的构建。我国追求的共治劳动关系,不仅保障各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途径,更要求各主体的治理行为的配合,保障治理效果。在集体协商中,工会组织职工方合法表达诉求,企业通过集体协商优化管理策略,避免劳动条件的企业单方决定和劳动者对过高诉求不计结果的坚持,而实现多方满意的协商结果。
3.协商收益均衡的“和衷共济”伦理基础
集体协商强调企业方和职工方的利益共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要求“企业和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实现“职工工资合理增长”[11]。2020 年1 月24 日下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12]。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中实现利益共享,需职工方与企业方共同分享和谐劳动关系下双方创造的收益,共同面对生产经营的风险,实现协商收益的均衡。
企业方与职工方协商收益均衡,来源于“和衷共济”的伦理秩序基础。《尚书·皋陶谟》中有“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同寅协恭,和衷哉”的表述,将“和衷”描绘为百工同僚相互协作、同心同德、合作共事。《管子》有中“合则强,孤则弱”,《荀子·王制》中有“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的表述,说明了各社会主体共担风险、同舟共济的强大力量。中华传统伦理秩序,还强调团体内部经济收益分享的合理均衡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13]。因此,集体协商是防止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合理地压低职工工资的协调企业收益分配的制度,同时集体协商并不片面追求劳动关系某一方主体收益的增长,而为创造收益设立协商双方的行为规范,为分担风险设立预备方案,为分享收益设立分配标准和激励措施。在集体合同内容中,不仅有劳动条件的约定,还有合同双方的行为规范。集体合同的条款,不仅体现工资福利的“增长”,也会适时体现工资福利的“增减”。
二、现有集体协商权利体系对和合伦理秩序的维系
集体协商立法包含了协商团体形成权(组成职工方和企业方并产生协商代表的权利),集体协商权(协商要约权,协商商谈中的建议权、否决权、陈述权),政府介入请求权(请求政府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拖延协商的行为、向另一协商方提交不实资料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政府监督请求权和请求政府对集体协商中发生的争议进行协调处理的政府调处请求权),职工方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集体合同草案的权利)。而协商团体形成权实现集体协商团体的成立,集体协商权促成协商团体的合意,政府介入请求权、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保障集体协商权的行使。
这不同于传统集体谈判制度中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的权利体系。传统集体谈判制度以集体行动权保障集体谈判权的行使,集体协商未设计集体行动权,而以政府介入请求权和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促成集体协商的有序开展和协商结果的合理性。集体协商权是核心,协商团体形成权是集体协商权行使的前提,政府介入请求权是集体协商权行使秩序的保障,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是集体协商权行使效果的保障。
中国特色的集体协商权利体系体现了对和合伦理秩序的维系。
1.“和合共生”伦理秩序的维系
“和合共生”的伦理秩序,需要外部环境的尊重和维持,当集体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局面面临打破的风险时,需要党政居中调和,维持“和合共生”的伦理秩序,促成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政府介入请求权是协商目标协调的关键,政府监督保障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的行使,促成集体合同的签订,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6 条所规定的集体协商“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14]的目标。政府介入请求权包括政府监督请求权和政府调处请求权,具体表现在如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53 条规定,政府部门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协商的行为,向另一协商方提交不实资料的行为进行处罚[1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4 条规定政府部门可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集体合同规定》第49 条规定,集体协商中发生争议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书面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协调处理申请”[16]。
通过政府介入,保障协商目标的协调,维系“和合共生”的伦理秩序,是集体协商与西方集体谈判的区别。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作用,也是西方集体谈判理论的追求。但西方集体谈判中,“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工会力量减弱,企业影响力增强,工会与企业力量平衡的破坏,阻碍了社会主体治理能力的有序发挥,而政府态度“超然”[17]。德国、美国等国政府提供基本规则,由劳资双方自主谈判;而英国等国采取自愿主义,政府对集体谈判缺乏保障措施,甚至不鼓励集体谈判的开展[18](P22-51)。这使得集体谈判特别是行业集体谈判,不再如昔日一般发挥着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6 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合同覆盖率平均值,从1985 年的45%降到了2017 年的32%[19](P15)。
我国追求的共建集体劳动关系,不仅激发社会主体对劳动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调党和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引导,协调职工方、企业方对劳动关系的治理目标,保障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和合共生”的秩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领导协调机制”“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11],即是要求从党委领导的角度,保障集体协商秩序。
2.“和善诚信”伦理秩序的维系
企业方、职工方表达自身态度和诉求有多种可能的途径,协商双方的协商行为可能表现为激烈对抗,这时就需要制度规范予以干预,以维系“和善诚信”的伦理秩序。
集体协商对“和善诚信”伦理秩序的维系,也是集体协商区别于西方集体谈判之处。西方集体谈判制度中有集体行动权的设计,当雇主拒绝工会诉求时,工会有罢工权;当工会拒绝雇主的要求时,雇主有闭厂权。集体行动权的设计,使劳资争议以外放的、冲突对抗的形式得以解决。集体行动权的设计根植于西方的争议解决传统,以美国为例,其罢工权的设立基于上百年的大规模罢工对抗实践。而在我国,职工方与企业方若有争议,倾向于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沟通予以解决,或通过政府、地方总工会、各界社会力量的介入参与得以调解。因此,在集体协商权利设计中,我们并未借鉴西方集体谈判的集体行动权,而是在《集体合同规定》第5 条对集体协商原则作出“相互尊重”“公平合作”“不得采取过激行为”[16]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27 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14]
3.“和衷共济”伦理秩序的维系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励的环境下,一些企业会有牺牲职工利益、片面追求企业利润的倾向。这就需要制度规范对合乎秩序的行为予以倡导,对违反秩序的行为予以纠正。
集体协商对“和衷共济”伦理秩序的维系,也是其与西方集体谈判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3 条规定,“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15]。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赋予了职工方对集体合同草案的表决权,可有效平衡企业方的强势地位,监督集体协商权的行使,防止出现不利于职工方的集体合同,确保集体合同内容呈现利益共享的要求。西方集体谈判,没有谈判结果的干预机制则显现了谈判结果失衡的迹象。现有集体谈判正在转向“管理者偏好”[20](P263-282),现今管理者往往追逐自身的短期利益,不再追求各主体平衡发展的长期利益[21],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欧盟,劳动者生计危机和贫富差距的加大已在多国出现[22]。在美国,贫富差异也愈加明显,“最富有的1%的人获得了65% 的收入,而低层90% 的人只有12% 的收入”[23](P126)。
三、和合伦理基础上集体协商的权利完善
伦理规则是规范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秩序,指导各类社会关系,超乎于个人主观见解之上的强大现实力量[24]。法律制度基于伦理秩序,是法律制度正当性、合理性的保证[25]。中国劳动立法中的权利义务设计,应建立在中国特色劳资伦理秩序的基础之上,同时维系和促成劳资双方的伦理责任意识,实现伦理规则的内化[26]。在和合伦理基础之上,产出集体协商权利体系的完善建议,更能适应中国社会关系的特征,也更具可行性。
1.完善政府介入请求权
党政领导是维系“和合共生”伦理秩序,保障集体协商有序开展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广集体协商时,片面注重集体协商覆盖率的数据和集体合同中工资增长的结果,而未引导职工方与企业方真实开展沟通协商,以完成国家集体协商覆盖面考核为目的对集体协商实行指标管理。集体协商推行不顺时,人社部门会联合其他政府部门给企业施加压力,企业若不开展集体协商,就会面临种种惩罚,以外力推动集体协商的开展。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集体协商,协商过程受政府的强制干预,协商结果服从地方政府的要求,政府主导是弥补工会与企业协商能力与意愿欠缺的途径,也导致了协商过程形式化的现象,集体合同中体现双方意见交流的条款较少,难以达到协调劳动关系的最佳效果[27][28]。
地方政府迫使企业开展集体协商的外在激励诱导下的集体协商推广方式,难以推动企业方和职工方自觉主动地运用集体协商维护自身权益,难以实现伦理秩序的内化。在地方政府调整推广策略,由地方总工会培养企业方和职工方在集体协商中的胜任感、自主感、成就感,通过内在激励推动集体协商开展的同时,法律制度应该对职工方和企业方获取政府介入提供合理途径和有效规范,确保政府介入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目前现有的立法中政府监督请求权规定不明,政府调处请求权存在行使障碍,协商目标协调机制的实践与立法预期存在偏离,应在立法中明确政府监督请求权和政府调处请求权,并明确行使主体、行使情形、保护措施,以及政府部门对政府监督请求权的回应义务,以实现地方党政对协商双方协商目标的协调。
2.完善协商团体形成权和集体协商权
在“和善诚信”的伦理基础上,企业方和职工方应积极维持协商团体内部的秩序,积极回应协商要约,共同商量完成集体协商。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的行使,是职工方与企业方“和善诚信”地平等开展协商的关键,是协商行为协调的关键。但目前现有的立法中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规定不清。其一,职工越过工会表达诉求的情形还缺乏制度回应。其二,集体协商要约权是否对应应约义务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3 条[1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51 条规定,“可以”开展集体协商,未设定强制性协商义务。实践中,一些企业据此不同意开展协商。其三,集体协商权是否对应诚信协商义务不明确。哪些行为属于违反诚实守信的行为缺乏基本界定。
集体劳动法立法应在劳资合作的伦理观念下,明晰企业方和职工方的权利义务,为协商双方的协商行为提供具体的规范指引。协商行为配合的要求以及冲突对抗方式的摈弃,是基于“和善诚信”伦理秩序的方向选择,但还需要细化协商行为的行使规则,指导协商双方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和善诚信”伦理秩序的内化。因此,应对职工越过工会表达诉求的情形予以积极回应,可规定一定比例的职工要求发起集体协商时,工会必须发出协商要约;明确一定情形下,协商要约权对应强制协商义务;明确集体协商权对应的诚信协商义务,细化诚信协商的具体要求和保障措施。
3.完善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
“和衷共济”伦理秩序中,职工方与企业方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在立法中,以职工方的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保证集体合同内容的合理性。但具体实践中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行使缺乏支持。首先,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行使缺乏有效保障。虽然立法规定,集体合同草案的决议权在职工方,但实际上,企业方往往是集体合同内容的决定者,有的企业拒绝向劳动行政部门报送不符合企业方要求的集体合同。其次,判断“共享”的依据缺失。集体合同草案是否体现“共享”,需依据工资分配的相关信息。但一些地方政府发布的诸多信息,如最低工资标准、高温补贴等,缺乏集体协商的针对性。企业发布的信息有较强的专业性,而职工方往往缺乏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职工方难以判断集体合同草案的合理性。
推动企业方和职工方践行“和衷共济”的伦理秩序,还需要法律提供细化的行为规则,对相关权利提供保障。应完善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工会监督和政府监督。在该权利受到侵害时,工会有权要求纠正。政府部门在审查集体合同时,可要求提交完整的职代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集体合同草案的材料,督促该权利的落实。同时,完善信息共享规定,以助于职代会或全体职工对集体合同草案的评价。政府应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业态,发布工资分配的相关参考数据。集体协商法规中列举的协商双方可要求交换的资料,应更具体,更符合行业特点和业态特点。职代会或全体职工大会中,应有对信息的专门讲解。
结语
集体协商的权利设计应基于和合伦理秩序的基础,同时应细化和合伦理秩序的规则,通过有效可行的权利设计,推动企业方和职工方主动践行和内化和合伦理规范。完善集体协商权利设计,有多种思路,但基于和合伦理基础的权利完善,更能确保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社会接纳度和运用效果。只有企业方和职工方主动运用集体协商,才能真正发挥集体协商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