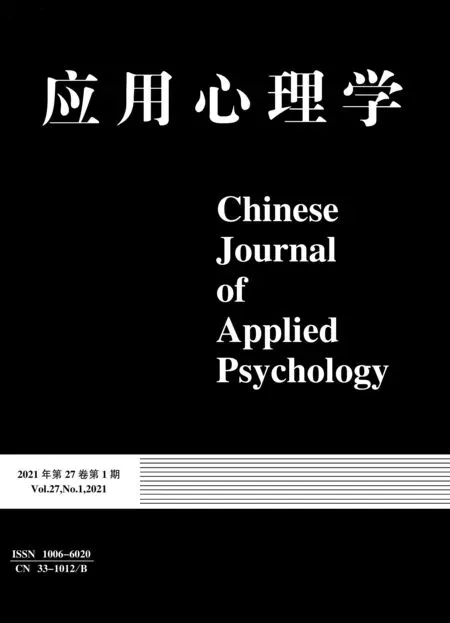支付效应的理论机制及影响因素*
于艺凝 李 欧 汪 蕾*
(1.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杭州 310058)
1 引 言
在购买商品时,消费者既可以使用纸币结算,也可以使用借记卡、信用卡以及手机支付等方式结算。消费者使用何种支付方式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最早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是Hirschman(1979),他发现当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支付时,他们的消费金额以及消费频率都要显著高于只持有现金时。由此,研究者开始关注支付方式对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系统性影响(Feinberg,1986;Soman,2003)。
有关支付方式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由于70年代后具有“先买后付”特征的信用卡在美国盛行(Kaynak & Harcar,2001),因此早期研究集中于比较现金与信用卡,它们之间存在的消费行为差异也被称为信用卡效应(credit-card effect)(Feinberg,1986)。后续研究进一步包括同属卡片式,但为“先付后买”特征的借记卡(Thomas,Desai,& Seenivasan,2011)、礼品卡(Yao & Chen,2014)等。这些支付方式的特点都是手持信用凭证或卡片完成交易而无须现金参与,因此又被称为非现金支付。新世纪以来,随着通信技术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支付(mobile payment)逐渐普及(Dahlberg,Guo,& Ondrus,2015)。但无论是卡片式还是移动支付,它们都不是直接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因此可以称为间接支付方式。而移动支付的发生要更加间接,并且其用于购买的货币已经被抽象成一种电子货币形式(Dahlberg et al.,2015)。
支付方式对消费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心理变量”与“行为变量”两方面内容:在心理变量上,研究主要关注满意度(Liu & Mattila,2019)、感知属性(Boden,Maier,& Wilken,2020;Shah,Eisenkraft,Bettman,& Chartrand,2016)以及解释水平(Chen,Xu,& Shen,2017;Yao & Chen,2014)等因素;在行为变量上,相关工作聚焦在购买意愿(Boden et al.,2020)、过度消费(Hirschman,1979;Soman,2003)、健康饮食(Bagchi & Block,2011;Park,Lee & Thomas,2020;Thomas,Desai,& Seenivasan,2011;Zeballos,Mancino,& Lin,2020),以及捐赠行为(Kelting,Robinson,& Lutz,2019)上。虽然该领域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证据,也有多种可供解释支付效应的作用机制,但仍缺少系统性综述。特别地,美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eMarkter的预报显示,中国在2019年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Stern,2019),然而与之不匹配的是国内学界对支付方式研究的关注度仍较低,只有少数研究者跟进(Chen et al.,2017;Xu,Chen,& Jiang,2019;Yao & Chen,2014;杨晨,王海忠,钟科,付佳,江红艳,2015;张美萱等,2018)。因此,对支付方式相关的研究进行综述,不仅有助于归纳、提炼该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还有助于国内同行了解该领域的动态并启发更多立足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研究。其次,支付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与决策任务无关的决策外因素;理性的决策要求决策者尽可能少地受决策外因素干扰,而将决策证据累积过程完全基于任务本身。因此,相关主题综述有助于深入理解支付方式发生干扰的原因和其潜在的影响因素,进而能为纾解这种“非理性”决策因素的干扰提供政策建议和指导。最后,移动支付正在世界范围内急速发展,eMarkter预报显示到2023年移动支付全球用户数将达13.1亿人(Enberg,2019)。因此,对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支付方式研究进行综述,有助于研究者抓住市场发展动态并为日后开展满足市场现实需求的研究做好铺垫。
接下来文本将梳理支付方式与消费行为的理论机制及影响因素,并在总结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指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2 支付方式影响消费行为的理论机制
2.1 条件理论(Conditioning theory)
Feinberg(1986)基于经典的联结主义学说(Thorndike,1898),提出了解释支付效应的条件理论:个体在日常消费经历中会逐渐建立信用卡与消费之间的联结关系,因此信用卡的出现会成为激活消费的线索。在Feinberg(1986)最初进行的四项实验中,信用卡线索都有效提高了被试的支付意愿与捐赠意愿。自条件理论提出后,一些研究者尝试对信用卡效应进行重复,却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尽管Nakajima和Izumida(2015)成功复制了Feinberg(1986)的结果,但其他重复研究中的多数都未能验证信用卡效应(Hunt,Chatterjee,Florsheim,& Kernan,1990),甚至出现了逆转的现象(Lie,Hunt,Peters,Veliu,& Harper,2010)。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文化背景不同,本地居民在信用卡与消费之间建立了有区别的联结关系。如果联结对多数消费者而言是积极的,那么信用卡的出现会促进消费;反之,信用卡则会成为控制预算、抑制消费的线索,表现出支付效应逆转的现象。如果某一群体内,建立了积极或消极联结的人群比例相当,则信用卡对消费的正向和负向作用会相互抵消,表现为零效应。最近一项关于移动支付的研究为支付与消费的联结方向对信用卡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者发现移动支付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受移动支付使用频率的调节,即对使用频率高的消费者而言,移动支付才能刺激他们的购物意愿(Meyll & Walter,2019;Sharma & Pandey,2020)。这可能是因为移动支付使用频率高的人已经适应(adoption)了新的支付方式,并在记忆中建立了支付与消费的积极联结,使得移动支付成为激发其购买意愿的线索(Boden et al.,2020)。尽管如此,当前研究对条件理论的合理性与稳健性仍存在着较大争议(Pornpitakpan,2012)。因此,后续研究者分别从消费者的情绪体验与心理账户的视角切入,对支付效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2.2 支付痛感理论(Pain of paying theory)
支付痛感是消费者在为其消费(购买)付出成本时所经历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Prelec & Loewenstein,1998)。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为支付痛感提供了生理层面的证据。例如,在Ceravolo,Fabri,Fattobene,Polonara和Raggetti(2019)进行的脑成像研究中,被试分别观看使用不同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的短视频,结果显示直接支付会激活右侧脑岛(insular);而脑岛一般被认为负责消极情绪加工,说明直接支付相较其他支付方式引起了个体更高的消极情绪体验。Chan(2020)的最新研究通过操纵身体痛感进一步证明了支付痛感的存在。他们发现身体痛感能够缓解支付痛感,这是因为身体的疼痛占据了人们加工消极情绪所需的认知资源,从而减弱了人们对支付痛感的感知。
不同支付方式的主要差异在于支付透明度(payment transparency)不同,由此能引起不同程度的支付痛感。支付透明度是指支付的易察觉程度,取决于支付方式在形态与数量上的显著性(Soman,2003)。形态显著性是指消费者感受到金钱流失的难易程度,而数量显著性是指消费者追踪自己消费金额的难易程度。某种支付方式在形态与数量上的显著性越高,那么该支付方式的透明度越高,其引起的支付痛感也越强。一方面,从形态上说,由于间接支付是使用非实体货币,它让消费者在支付时较难体验到金钱流失的感觉。另一方面,从数量上说,由于间接支付无须进行货币清点,具体交易金额难以在消费者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故而支付的间接程度与支付透明度和支付痛感成反比。支付方式的功能多样性亦会影响支付透明度。支付媒介的非支付高频功能,如多功能卡片的身份识别功能(Gafeeva,Hoelzl,& Roschk,2017)和智能手机的娱乐、社交功能,会稀释消费者对其支付功能的感知,弱化消费者花钱的感觉,从而降低支付透明度及支付痛感。
消费时除了有付出金钱成本引起的支付痛感外,还会有因成功购买带来的愉悦感,因此只考虑痛感显然是片面的。后续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补充,并提出了平衡痛感与愉悦感的双通道理论。
2.3 双通道理论(The double-entry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消费者会在无意识中以多个心理账户对不同来源收入进行管理,并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对它们适用不同的支出准则(Thaler,1980)。Prelec和Loewenstein(1998)在心理账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通道理论,即消费者的心理账户中存在两个通道:一个是记录从消费中体验到的快乐,另一个则记录付款时感受到的痛苦。心理账户的总效用值等于两个通道的效用值之和,若购物的快乐大于支付的痛苦,人们会产生“买值了”的积极体验;反之,人们会产生“买亏了”的消极体验(李爱梅,郝玫,李理,凌文辁,2012)。认知神经科学为心理账户中双通道的存在提供了生理层面的证据。Knutson,Rick,Wimmer,Prelec和Loewenstein(2007)的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实验表明,消费过程会同时激活与快乐、痛苦相关的两部分脑区。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会激活与奖赏有关的伏隔核(NAcc),而过高的价格则会激活与生理痛和经济损失有关的脑岛,这些脑区的激活水平能共同预测随后的购买决策。
支付和消费的联结程度(coupling),即购买决策与付出金钱之间联结的紧密程度,是影响双通道心理账户中快乐与痛苦所占权重的重要因素(Prelec & Loewenstein,1998)。支付与消费的联结越紧密,快乐(vs.痛苦)账户所占的权重越低(vs.高)。间接支付通过去联结(Decoupling)的方式,削弱了消费者在购买时的支付与消费的联结程度,使消费者的心理账户暂时由快乐主导(Prelec & Loewenstein,1998)。去联结的方式有两种:先付款后消费和先消费后付款。先付款后消费通过预付款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分离了支付与消费环节。预付款是指支付发生在消费之前的支付方式(如储值卡和代金券),它通过预存或预付的方法让消费者提前为日后的消费买单,从而剥离了付款与消费环节(Ding & Zhang,2020),让消费当下的快乐主导了消费者的心理账户,让消费者更容易跨越“是否要买”的阶段而直接进入“要买什么”的阶段(Yao & Chen,2014)。一次性付款是指消费者一次性付清购买商品所需的全部费用。在支付行为发生之后,消费者对支付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化,对付款成本的淡忘使快乐通道逐渐主导了他们的心理账户(Tatavarthy & Mukherjee,2019)。与之相反,先消费后付款的方式则通过延后付款的方法来分离支付与消费环节。比如,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付款的当下并没有实际支出,这大大削弱了双通道账户中痛苦账户所占的比重,消费者在快乐账户的主导下更容易发生计划外的冲动性消费。
双通道理论是对支付痛感理论的有益补充: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不仅受到支付痛感的影响,还受到消费愉悦感的影响,消费者对购物的整体感受是这两种影响加总的结果。
3 支付方式作用于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
3.1 内生性因素
影响支付效应的内生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性与文化两方面。首先,在个体特性上,依据对支付痛感的敏感程度可以将消费者分为挥霍者(Spendthrifts)与节俭者(Tightwads)两种类型(Rick,Cryder,& Loewenstein,2008)。挥霍者喜爱消费,较少因花钱感到焦虑;相反,节俭者则会因花钱感到焦虑,他们常节制消费以进行更多的储蓄。Thomas等人(2011)最早发现,挥霍者因为对支付痛感不敏感,因此使用现金并不能有效控制他们对不健康食物的购买冲动,使得支付效应在挥霍者身上并不显著。然而,新近一项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支付效应在节俭者身上才不存在(Wong & Lynn,2019)。这两个研究的矛盾结论可能是由于使用的刺激材料不同所致。Thomas等人(2011)使用的材料中既有享乐产品也有实用产品,而Wong和Lynn(2019)只考虑了实用产品。由于实用性消费情境能减弱支付痛感(Friedman,Hauser,& Dhar,2019),因此在Wong和Lynn(2019)的研究中可能存在地板效应,并使得支付方式对支付痛感的影响在节俭者和挥霍者身上均不显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挥霍者倾向于建立信用卡和消费的联结,而节俭者倾向于建立信用卡与债务的联结(Wong & Lynn,2019),因此信用卡分别成为了挥霍者促进消费和节俭者抑制消费的提醒物,使得支付效应在节俭者身上消失。除此之外,Duclos和Khamitov(2019)还发现个体的聚焦方式会影响人们对暂时与金钱分离的痛苦,从而影响支付效应。这是因为持预防聚焦(vs.促进聚焦)的个体对负面(vs.正面)结果更为敏感,因此加剧了他们对支付痛感的感知,这种天花板效应使得支付方式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消失。
其次,在文化上,早在1990年Feinberg面对信用卡效应不可重复危机时便对文化因素对支付效应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支付效应的重要前提是,人们在过往的使用中已经建立了信用卡与消费的积极联结(如便利性、应付流动性等);而如果建立的是消极联结(如高额利息、负债等),那人们在持有信用卡时的购买意愿甚至还要低于现金。例如,Lie,Hunt,Peter,Veliu和Harper(2010)在新西兰居民中发现了逆支付效应,也即与以往结果相反的“现金支付意愿 > 信用卡支付意愿”。逆支付效应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新西兰居民的负债较为普遍,政府也一直在宣传债务的危害并致力于消除个人债务危机。因此新西兰人更多地与信用卡建立了消极的心理联结,因此在使用信用卡时会出于控制预算的目的而降低购买意愿。同样地,Kamleitner和Erki(2013)也发现亚洲学生大多将信用卡视为一种投资或负债(消极联结),因此他们中也不存在支付效应。现有支付效应的研究多使用单一群体作为样本,鲜有研究探讨支付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的激增使支付效应的跨文化研究展现出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同时招募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群体,以探究支付效应的文化差异。
3.2 外生性因素
影响支付效应的外生性因素主要包括支付金额与“支付-体验”间隔两方面。首先针对支付金额,现有研究关注了支付金额对支付效应的影响(Ceravolo et al.,2019;Shah et al.,2016)。来自fMRI的证据显示,相比小金额消费,大金额消费(150欧元 vs.10欧元)会显著激活编码消极情绪的脑岛及编码自我控制的扣带回(Cingulate cortex)。但是支付金额对支付效应的影响仅存在于现金支付条件下,在信用卡、移动支付等间接支付条件下该影响消失(Ceravolo et al.,2019)。张美萱等人(2018)在行为层面上也得到了相似发现,他们的研究表明个体在使用间接支付时会表现出对消费大(100元)/小(10~40元)金额的不敏感性,而非如现金支付时那样对大额消费进行自我控制而对小额消费不重视。这可能是由于间接支付低透明度的特点使得消费者对不同金额区别的感知变弱(Soman,2003),因此导致他们的购买意愿较难受商品价格的影响。然而,Shah等人(2016)在交易后商品评价中却没能发现金额与支付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他们的实验中,无论是消费10美金还是20美金,现金相比于间接支付都能增加产品的心理价值进而提升消费者忠诚度。这可能是因为无论10美金还是20美金,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心理价值都较低(张美萱等,2018),因此支付金额的调节效应并没有得到体现。该结果表明只有在支付金额足够大时,消费者才会在现金条件下对消费进行有意识控制。
其次针对“支付-体验”间隔,即从完成支付到体验商品之间的难易程度或时间间隔。在有关支付方式与健康饮食的研究中,Thomas等人(2011)发现消费者在使用现金(vs.信用卡)时会减少购买不健康食品,然而Baghi和Block(2011)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使用信用卡才会降低消费者对不健康食品的购买意愿。Baghi和Block提出矛盾可能是由两项研究的情景差异引起。Thomas等人的研究采用的是延迟消费情境,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并不会马上体验商品;而Baghi和Block的研究采用的是即时消费情境,该情境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后会立刻进行体验。因此,可能是对不健康食品的延迟体验使得其难以补偿花钱带来的支付痛感,才使得在Thomas等人的研究中出现“现金抑制不健康食品购买”的结果。这两项研究表明“支付-体验”间隔可能会逆转支付效应的方向。此外,“支付-体验”间隔还会调节支付方式对购后体验的影响。在电子商务领域,缩短配送时长是优化客户体验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近期一项研究发现,较长的配送时间反而会提高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降低退货率(Sharma & Pandey,2020)。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支付-体验”间隔的变大,支付贬值(Payment depreciation)(Tatavarthy & Mukherjee,2019)现象使消费者逐渐淡忘了付款时的痛感,从而导致在收货时其心理账户由消费的快感所主导,进而提升了满意度。
综上所述,内生性因素主要是通过个体差异,以及建立支付方式与消费之间积极或消极的心理联结来影响支付效应;而外生性因素则主要通过与消费有关的情境信息放大或舒缓支付痛感来影响支付效应。
4 未来研究展望
4.1 基于移动支付的新特点,构建解释支付效应的新视角
截至2019年6月,我国移动支付用户数达6.2亿,移动支付使用比例高达73.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9)。然而移动支付的研究却相对落后,目前研究仍是聚焦在直接支付与间接支付方式的差异(如现金支付 vs.信用卡支付)上,少见将新型间接支付方式与传统间接支付方式相比较(如移动支付 vs.信用卡支付)。基于移动支付的大好前景,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挖掘移动支付的新特点,丰富和补充支付效应的理论机制。
4.1.1 移动支付改变了消费者的决策方式
决策方式可分为基于直觉与启发式的情感型决策方式和基于理性与分析式的认知型决策方式(Metcalfe & Mischel,1999)。研究发现,在使用移动端购物时消费者的决策方式倾向于向情感型决策转变(黄敏学,王薇,2019),进而导致享乐偏好等下游效应(如Shen,Zhang,& Krishna,2016)。那么,移动支付是否也会启动消费者的情感型决策方式,从而导致其消费行为的变化呢?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来观测消费者在使用移动支付时大脑情感活动的变化。
4.1.2 移动支付加深了消费者的情感依恋
除了支付功能,手机、电子手表等移动支付工具也是我们生活中情感相连、密不可分的物品,“手机依赖”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曲星羽,陆爱桃,宋萍芳,蓝伊琳,蔡润杨,2016)。Pisani和Atalay(2018)发现,消费者感受到的支付痛感随他们对移动支付工具情感依恋(attachment)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对“手机依赖”问题严重的消费者而言,移动支付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否会消失?此外,“商业+社交”模式的兴起和微信支付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支付平台尝试将社交生活融入商品交易,如定位于熟人支付市场的P2P支付(peer to peer payment)(Huang,Ghosh,Li & Ince,2020)。支付与社交的融合可能会在消费者记忆中建立起支付与社交的联结,进一步加深消费者对支付工具的情感依恋,进而削弱甚至逆转支付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针对该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4.1.3 移动支付增强了消费者的风险感知
移动支付为消费者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套路贷、网络诈骗、隐私泄露等安全问题。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增加了消费者对其风险性的感知(Shao,Zhang,Li & Guo,2019),进而降低了他们对移动支付工具的使用意愿(Ardiansah,Chariri,Rahardja,& Udin,2020)。因此,与其他间接支付方式相比,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强风险感知是否会泛化到其风险决策行为上,并表现出更高的风险规避?为了减少移动支付的不良影响,支付宝、微信钱包等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官方资质保证、加强用户隐私保护等方式降低了用户对移动支付的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移动支付的高风险性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de Kerviler,Demoulin,& Zidda,2016)。未来研究可以聚焦在如何减轻移动支付风险问题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上。例如,有研究发现个体对移动支付的使用经验和熟悉程度能够降低其对移动支付的风险感知(de Kerviler,Demoulin,& Zidda,2016)。基于此,针对移动支付低频用户可以通过相关知识科普教育、熟人宣传推荐等方式提高用户熟悉度与用户黏性,以削弱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风险感知。
4.2 从移动支付到刷脸支付
技术进步推动了货币形态与支付方式的变革,作为近两年兴起的一种新型高科技支付方式,刷脸支付(face scan payment)仅通过面孔识别即可完成支付,其间接程度更高、支付透明度更低的特点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支付痛感。Liu和Mattila(2019)发现,在获得成功服务体验的前提下,移动支付会提升消费者对服务的满意度;这是由于移动支付作为一种高科技支付方式,被消费者视为身份阶层的象征。刷脸支付拥有更高的科技含量,那么消费者从刷脸支付中感受到的高科技性、创新性和新鲜感是否会成为支付效应新的解释机制?消费者在使用刷脸支付时感知到的创新性是否会蔓延到其对创新产品的偏好中?刷脸支付的上述影响又是否会随着消费者对新技术的逐渐熟悉而减弱(Fryer,Ainley,Thompson,Gibson,& Sherlock,2017)? 未来研究可以聚焦于以刷脸支付为代表的高科技支付方式及其对支付效应的影响上。
4.3 打破聚焦于主流支付形式的思维局限
目前,研究者大多聚焦于支付形式(如现金、银行卡、手机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较少关注支付来源(如信用账户、储蓄账户、现金账户等)(Runnemark,Hedman,& Xiao,2015)如何影响消费行为。与支付形式不同,支付来源通过作用于消费者的心理账户来影响其消费行为。例如,消费者信用账户的购买意愿显著大于其储蓄账户的购买意愿,这可能是因为信用账户的支出被放在了未来的心理账户中,从而减缓了当下支付的痛感(Thrane,2015)。同种形式的支付方式会因其支付来源的不同而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Sarofim,Chatterjee和Rose(2020)的研究发现,虽然使用商店卡和银行卡消费会带来相同程度的支付痛感,但是使用商店卡消费的金额会被存储在与商店有关的心理账户上,这会导致消费者很难再次使用该账户进行消费,从而降低了他们对同一商店的重复光顾意愿。随着“花呗”等消费信贷产品的普及,使用同种支付形式的消费者可能由于其支付来源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未来研究应同时考虑支付形式和支付来源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此外,未来研究可以跳出现有支付形态的限制,通过对支付方式的间接性、便利性等特点进行直接操纵,从根源上探究支付方式的不同特点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支付效应进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