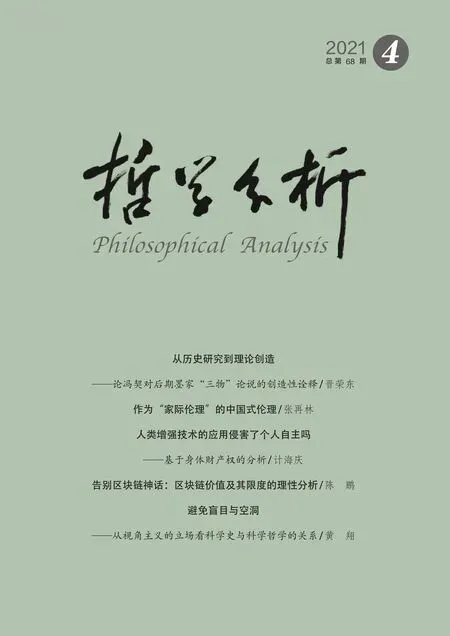还原的观念a
——胡塞尔的诸还原概念及其共同的“方法论”意义
[德]迪特·洛玛/文 张浩军/译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试着阐明胡塞尔的诸还原概念,并确立如下这一观点:他的所有还原概念都遵循一个特定的方法论模型。为此,我将表明,胡塞尔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还原概念,即《观念I》中的先验还原和《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的原初还原(Primordialreduktion)a“Primordial”这个词在汉语现象学中一般被译为“原真的”(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375 页),但这个词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其实是“eigen”(本己的)的同义词,与“fremd”(异己的、陌生的)相对,本身没有“本真”(Eigentlichkeit)或“真理”(Wahrheit)的含义。与“Primordial”相关的两个词分别是“Primordialreduktion”和“Primordialsphäre”,前者也被叫作“第二次悬置”,而后者则是指经过第二次悬置之后剩余下来的纯粹本己自我的领域,这个领域不包含任何陌生(他人)之物,完全是由自我所构造的一个纯粹“属我”的世界。胡塞尔是想首先通过本己之物与陌生之物的区分,为他人之构造找到一个绝对的、原初的、唯我论的起点。考虑到这个词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的主要用法,译者建议将其译为“原初的”(其实译为“本己的”最好,但这与其字面意思不符)。相应地,“Primordialreduktion”译为“原初的还原”,而“Primordialsphäre”译为“原初的领域”。洛玛在本文第五小节也谈到了原初的还原和原初的领域,他把后者也叫作“原初的自然”。洛玛说:“原初还原的剩余物是一个可经验世界的层次,我能‘完全独自’构造这个世界,而不需要牵涉他人的意义构造成就。‘原初的自然’,即我只能凭借我的感性、我的身体和我的经验构造的这个自然……”罗志达主张将“Primordialreduktion”译为“源初还原”,参见罗志达:《源初还原、自身批判与他异化——对胡塞尔源初还原的一项新考察》,载《哲学动态》2021 年第3 期。——译者,而且也进一步给出了一种还原的方法,这一方法在时间上先于先验还原概念的首次提出。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在胡塞尔晚期著作中,至少有三种其他的方法与还原具有同等地位。
第一个方法问题是还原的目的问题。通常人们会说,在胡塞尔那里,所有还原都服务于对某些观点的合法性审查(Rechtsprüfung)。在现象学的方法语境中,可以把合法性审查理解为这样一个问题:此时此地,我有什么直观的权利来知觉一张桌子、一棵树或一个人?b毋宁说,我们是从康德那里知道“合法性审查”这一概念的。在康德那里,所谓的合法性审查是指将特定的一般原则回溯到知性范畴上。为什么我有理由相信,我在那里知觉到的是一棵树而非一座房子?有人可能会说:事情很简单,我看见那里矗立的是一棵树,而不是一座房子。但是,从对合法性要求的完全肯定以及对合法性源泉(“看”)的暗示来看,直观的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成。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更确切地说,在最小的单个直观行为中,即指向直观的被给予性及其意义元素(Sinnelement)交织的直观行为中——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棵树,而非一座房子?c在此,我想说,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教授以及由他和安东尼奥·阿奎尔(Antonio Aguirre)教授[后来与洪尼(H.Hüni)教授]一同主持了多年的“现象学论坛”是我本人现象学训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源泉。每当我回想起这个论坛自由的、具有实验性质的,却又严格按照现象学方法开展的工作时,就不免对之充满感恩和学术的赞赏。因此,这涉及一种“权利”/“合法性”(Recht),一种设定通过在它之中被设定之物的直观被给予性而获得了这种权利/合法性。如果我们在对事态的范畴直观或其他范畴形式的意义上与胡塞尔一道扩展了直观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拓宽研究的方向。但这并不限于这种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直观的权利/合法性。
事实表明,胡塞尔也考虑到了对设定之权利/合法性的证明,而这些设定原则上只能在直观中得到部分证明。这里涉及对认识论经典难题的合法性证明,即涉及例如“(可能变化的)规定性之持存的基底”、一种普遍的因果性的表象这样的意义元素,此外,也涉及时空的无限性、近代以来对于可经验的现实性之数学结构的假设、逻辑原理的有效性、对世界而言的其他主体的设定,等等。所有这些意义元素都不能在感性中被证实,或者只有很小一部分能被证实,尽管如此,它们依旧属于我们的认识活动和思维活动。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通过向直观的回溯把现象学的“合法性证明”(Rechtsausweisung)概念与康德的“合法性审查”(Rechtsprüfung)概念区分开来。在康德那里,合法性审查意味着将在认识活动中所使用的概念回溯到纯粹先天的知性概念上去。康德的合法性审查概念是以quid juris(权利问题)和quid facti(事实问题)的法律问题之对置为指导的。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对一个特定的诉讼案件进行司法审判的法律根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问的是:现有的法规究竟是否实际上适用于当前的案件(例如,需要澄清,当前的这一行为是否实际上只是盗窃行为)?康德只考察了第一个问题,因为他把纯粹知性概念看作最高的、先天的合法性原则(Rechtsgrundsätz),而这些合法性原则必须被包含在每一种具体的、引申出来的法规中。对康德而言,quid facti(事实问题)是一个经验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直观的被给予性,但它们无法通过最高法律原则的演绎得到澄清。
有人可能会以如下方式表明康德的合法性审查与胡塞尔的合法性审查概念之间的区别:虽然康德强调,直观和概念是认识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在他看来,每一概念中必然包含了构造对象的先天知性概念,所以他只审查了认识要求(Erkenntnisprätention)的合法性。与此相反,胡塞尔主要研究了同样能够赋予合法性的直观方面,并且首先考察了特定意向性种类的充实方式之本质特征。概念也在直观中有其起源,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也在直观中有其合法性源泉。然而,胡塞尔从一开始就没有分别对最终的基本概念问题进行研究。他在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中首次指明,构造对象的概念之功能(类型)也必须回溯到直观和经验上来,而且能够在其中得到证明。
在一个直观地被给予的领域中,对知觉、认识和表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有一些方法论的问题需要指明。胡塞尔试图借助各种还原方法来解决合法性审查的一个核心问题。我的主要论题是:每一种还原都是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应当回溯到经验领域中去,其合法性有待证明的设定并不(或者尚未)包含在这一方法之中。a这里的表述必须更准确一些:其合法性有待审查的设定完全是在名义上,或者可以说,仅仅根据其名称,可以允许被包含在所寻求的经验领域中,但这一设定不应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经验领域中,它并不正常发挥作用,虽然其要求(Anpruch)得到了主张,但其有效性并未得到承认。这一详细说明尤其适用于借助先验还原对现实性设定的合法性进行证明的情况。在这一详细规定中,虽然设定的有效性要求作为一种要求的确得到了认可,但这种有效性本身并未正常发挥作用,而只是被用作寻找直观的合法性证明的指导线索。因此,对一种还原的本质论证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只有在一个如此“被还原的”经验基础上,对设定之合法性问题的证明才能在避免循环论证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就可能出现一种构造理论的petitio principii(循环论证)b逻辑学术语,是指在论证中,通过诉诸以稍微不同形式表述的、与待证命题意思近乎相同的命题去证明待证明命题的真实性,也译作“乞题”。感谢北京大学陈波教授为此术语的翻译所提供的建议。——译者。
因此,一切还原的共同特征都是一种方法论特征。在所有情况下,胡塞尔都是为了在一个直观的经验领域之基础上澄清对特殊设定之合法性及其合法性界限所进行的研究。在阐述的过程中,也必须澄清,为什么胡塞尔的还原如此与众不同,因为还原的类型取决于它所涉及的设定。
人们可以按照这个观点列举出一系列设定,进而阐发出隶属于这些设定、专门针对这些设定的各种还原,并对这些还原进行说明。在其中,也有一些还原迄今为止尚未被理解为“还原”。如果我们的论题能够得到证成,那么还原就被证明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这一方法在胡塞尔的整个现象学生涯中,从《逻辑研究》到《经验与判断》,始终在一种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得到了应用。胡塞尔至少考察了以下几种设定:
(1)把感性的被给予物从内容上立义为“某个特定的东西”,例如一棵树的合法性。与此相关的还原是“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这种还原可以在第五《逻辑研究》(第一版)中找到。
(2)把某物设定为“现实的”合法性。与此相关的还原是《观念》中的先验还原。
(3)逻辑与数学的观念性,尤其是逻辑原理。在这里,证明的方法是将判断回溯到个体对象或具体对象的经验上。《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第二部分对此有所论述。
(4)对其他主体性的设定。与此相关的还原是《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的原初的还原。
(5)自然科学的观念化假设。与此相关的证明方法是《危机》中向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回溯。
(6)判断的基本“逻辑”范畴,例如谓词“是”“和”“不”,等等。证明方法是《经验与判断》中将逻辑范畴回溯到前述谓经验上去。
上述六种还原中,有三种研究方法(3、5、6)胡塞尔本人并未称作“还原”,而是称作“回退”(Rückgang),有时也称作“回溯”(Rückführung)。对此需要指明的是,这三种研究方法与其他三种还原具有相同的方法论意义,这三种还原也可以被清楚地列举出来。为此,指明拉丁语的reducere 本身就有“回溯”(rückführen)的意思,还并不足够。当然,也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胡塞尔并未把这三种研究方法称作还原。
上述六种还原的方法论的共同特征,可以用一个一般证明理论的公理来描述:如果你想证明一个论断,那么你在证明的过程中既不能明显地也不能隐含地使用这个论断,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现在就清楚了,在合法性证明的问题框架中,构造理论不是证明,而是一种操作方法,这种操作方法必须回溯到与之相关的直观的被给予性方式上去。对于构造分析而言,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相应的公理来表述:如果你想澄清一个对象原初的直观构造,那么,即将被审查的设定就不应(作为“有效的”或“起作用的”设定)被包含在直观的经验领域中,因为你是把直观的经验领域作为这种构造分析的基础。还原是为了避免论证的“循环”或构造分析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写道:“一门科学所追问的是它不能用作预先被给予的基础的东西。”aHua II,S.33.
当然,现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胡塞尔也没有把这种支持其还原理论的统一的论证作为这样的论证明确提出来?或许胡塞尔没有这样做的一个理由在于:避免循环对于他这样的专业数学家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此根本不值一提。另外一个理由或许在于:他本身对这个论证也并不清楚。虽然在核心点上,他的实际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也能够列举出这些理由,他本人的自身认识还远远不够成熟。
然而,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我的这种诠释的“代价”:尽管胡塞尔本人一再把他的本质方法称作“本质还原”(eidetische Reduktion)b参见Hua IX,S.284f.,S.321ff.。,但从我的诠释来看,这种本质还原从其他那些还原的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还原。因为,为了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审查一种设定的合法性,本质还原并未对经验领域进行任何抽象的纯化。虽然本质还原在这里所进行的诠释中依然是现象学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但它并非狭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还原。此外,有待澄清的是,为什么胡塞尔并未把还原的三个变体(3、4、5)也叫作还原。
但是,付出总有回报。我的诠释的优点在于,它是先验还原和其他还原方法的一个朴素且明智的动因(Motivation)。悬置的动因始终是一个备受讨论的谜题,如果人们恰恰为了扬弃自然态度,而又在自然态度中询问扬弃的动机(Motiv),那么这一谜题似乎无从解答。
一、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
胡塞尔的第一个还原概念鲜为人知,因为它首先是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提出的,而与之相关的绝大多数段落则在1913 年的第二版中被删除了。a关于这个论题,也可参见我的论文“Zu den Motiven und der Vorgeschichte der transzendentalen Reduktion in den‘Logischen Untersuchungen’”,in NN.Beiträge der Konferenz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hänomenologischen Forschung,Freiburg September 2000,Hrsg.von A.Haardt und T.Eden,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Sonderheft(In Vorbereitung)。有一些段落阐述了“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但它们甚至也被那些(毋宁说犹疑不决的)对先验还原的暗示一字不差地“覆盖”(überschrieben)了。b例如,在第一版中,胡塞尔要求“依照其实项组成部分对体验进行描述分析”,但在第二版中,他却说,现象学应当“从一开始,并且在所有接下来的步骤中,都不准做出任何有关实在的、此在的断言”(Hua XIX/1,S.27f.)。显然,胡塞尔放弃了“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删除和“覆盖”这些与还原相关的段落表明,向实项组成部分还原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被宣布为无效。然而,有趣的是,恰恰在第二版中胡塞尔一再把这种向实项组成部分的回溯称作还原。c例如,胡塞尔把这种回溯称作“向实项的体验内在性的还原”(Hua XIX,S.413,脚注*,第二版)。在《第五研究》中我们还能发现这样的文字:“[自我]向能够以纯粹现象学的方式把握的内容的还原”(Hua XIX/1,S.368:12—14,第二版),“向纯粹现象学之被给予物的还原”(Hua XIX,S.368,注释*,第二版),“向现象学之物的还原”(S.369:26—28,第二版)。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覆盖”有时也是与对先验还原的暗示一同发生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两种方法事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之处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也不是以完全不可辨识的方式进行的:在《逻辑研究》第二版中依然可以找到这样的还原!d参见Hua XIX,S.413,注释*,这一注释提醒我们注意第二版中“向实项的体验内在性的还原”。Hua XIX,S.368 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在文中第二版部分,胡塞尔的思想转向,即“现象的、经验的自我向其能够以纯粹现象学的方式把握的内容的还原”被补充了进来,在这里,Hua XIX,S.411 脚注*意义上的“现象学内容”应当被理解为实项的体验之组成部分。
向实项组成部分回溯的方法首先在“第五研究”中得到了详尽阐述。意向行为的本质组成要素有三个(在《逻辑研究》中的名称分别是):(1)行为的质料,它从内容上规定被意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以及这个对象是以何种方式被意指的;(2)设定的质性(现实的、可能的、可疑的,等等);(3)充盈。
在《逻辑研究》中,构造对象的基本模式是对实项的组成部分进行意向性的立义。可以说,在感官中通过感觉被给予我的东西被解释成了对象的表象。当然,这只是对立义过程的一个简单且初步的描述。
胡塞尔抓住了立义过程的一系列特征——立义有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同一个实项的组成部分既可以被立义为这个对象,也可以被立义为那个对象。他用著名的蜡像馆玩偶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活动的玩偶时而看上去像一个玩偶,时而又像一个冲我示意的活人。立义的第二种主要属性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同的实项组成部分被解释为同一个东西,或者说同一个对象。我们可以用对物体的知觉来说明第二种可能性,因为我们在不同视角下——也就是说,在完全不同的实项组成部分中——所把握到的始终是同一个物体,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将这个物体知觉为这个物体,也能够将它识别为这个物体。
实项的组成部分对于合理地规定意向性立义之内容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它们对于胡塞尔称作立义模式(Auffassungsmodus)的立义类型(die Art der Auffassung)也很关键。如果实项的组成部分不允许直观的立义,那么它就只可能是一个图像—指示的(bildlich-signitive)立义,即作为被意指事物之图像的立义,而非作为这个事物本身的立义。
此外,设定的质性也间接依赖于实项的组成部分,因为设定之合法性“实际上”建立在直观的立义之可能性基础上。然而,最终,实项的组成部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们能够使一个立义之内容的规定性成为一种合法的或不合法的规定性,或者,完全一般地来说:我是否可以将某物知觉为一棵桦树还是一个人,这取决于那些将这个对象给予我的感性之被给予性。因此,从《逻辑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实项的组成部分是起关键作用的经验基础,因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对立义之内容进行规定的合法性,即质料的合法性、设定的质性之合法性,以及一种特定的立义模式之合法性才能得到证明。对于意向性设定而言,实项的组成部分是“赋予合法性的经验基础”。
因此,我们看到,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已经倾向于将现象学称作“依其实项组成部分对体验进行的一种描述分析”aHua XIX,S.28.。他在意识之实项组成部分的基础上遵循了对“立义为某物”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观念。然而,立义包含质料、质性和充盈三个要素。对立义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方案首先与质料有关,即这个“被立义为某物的东西”,当然也与行为的设定质性有关。意向行为的充盈或多或少建立在实项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因此在《逻辑研究》中处在赋予合法性的经验领域这一侧。
然而,从《逻辑研究》的观点来看,对一个行为之质料和质性的合法性研究限于并且仅限于一个行为。对所有设定之视域交织的洞见首先是在《观念I》中形成的。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静态的观点尚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仅仅依照一个单一的行为来考察意义设定(Sinnsetzungen)和存在要求(Seinsansprüche)这样的设定质性。《观念I》提出了这样一种研究之不可分割性(Nichtpartikularisierbarkeit)的洞见,因为,视域意向性表明,存在设定“实际上”是以视域意向的方式与所有其他的现实性设定联结在一起的。
对质料和设定质性之批判的合法性审查能够用胡塞尔从洛克那里借用来的“红色球”的例子得到最好的说明。a参见Hua XIX,S.82,197ff.,359ff.。看到红色球,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台球。这样,胡塞尔对意向立义之合法性审查(“批判”)计划的本质做法很快就得到了说明。当我们看见一个红色球时,这也意味着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均匀地着了红色的球。因此,知觉的意义也包含“均匀地”着色的意义元素。
感性以直观充实的方式赋予我们的东西恰恰不是着色的均匀性。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球在某个位置上由于光照的缘故是完全明亮的。“红”这种颜色或许在反光的地方就不再能被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光线被遮蔽的地方。在那里,垫子上的球因其自身的投影而显得昏暗。如果我们现在以如此狭隘的方式将实项的组成部分称作对象设定(质料)之合法性的“字面标准”(buchstäbliches Kriterium)的话,那么依照这一标准,对象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
这一点也能依照一个实在物体的基本情况得到说明。如果我们把一个物体设定为“现实的”,那么这一意义设定就不仅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这个物体“正好现在”(gerade jetzt)被给予了,而且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之前就已经”(schon zuvor)被给予了,并且“还将再次”(gleich noch)被给予,或者也许能够被给予。这两个首要的意义元素尚且能够用实项组成部分的标准来证明,不过,对于所谓的“之前就已经”而言,我们必须引入滞留理论。但是,物体之“还将再次”被给予,这个与现实性设定共同被意指的东西,还不能用现在在意识中呈现的内容来证明其合法性。这一问题提法引出的是著名的认识论问题,即为(可能变化的)诸规定性设定一个持存之基底的合法性问题。
但由于我们既不想把均匀着色的意义元素,也不想把这个红色球的现实性的意义元素纳入单纯不合理的虚构领域,所以,显然,我们除了“弱化”我们的标准之外,别无他法。但这绝不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倒退,而是一种与我们通过知觉实际所为之事的合乎意义的相互适应(Angleichung)。在评判一个知觉设定要素之合法性的适度的、同时在事实上也恰当的标准的意义上,《观念I》的分析强调,设定的“理性动机”取决于本质上属于一个确定的设定之充实类型。这种充实方式(明见性方式)在实在物体那里始终是一个新的视角性的直观,这一直观同时也受制于确定的但有规则的反常现象,例如光照的改变。
当然“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也表明了一些问题。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做一个简要说明。第一个问题是通达实项材料的困难。乍一看,这根本不是最严重的困难,因为它们始终在意识中实项地当下存在着。因此,实项材料是可通达的,然而始终只能以一种“作为这个”或“作为那个”而被立义的对象的方式被通达,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很艰难地“凭它自己的权利”将实项的组成部分变成对象。正如我们在红色球的那个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始终已经把“材料”解释为(影子、反光……)。人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能将它们看作未被立义的材料,而应该始终将它们看作已被解释的东西。胡塞尔写道:“我看到的不是颜色感觉,而是有颜色的东西。我听到的不是声音感觉,而是歌者所唱的歌。”aHua XIX,S.387.
不过,人们应当明白的是,这里所描述的针对“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的反对意见——其中所说,实项的组成部分本身是不可通达的,也就是说,不能成为主题——并不是基于实际被给予的东西而使意向设定之“批判”的观念变得不可能。正如我们在红色球的例子中已经清楚看到的那样,为了使意向设定在直观中返回其真正的基础上,有一些有用的线索。它显示的往往是,我们作了一些设定,这些设定并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经验论意义上的印象上,而是需要精致的分析方法,并具有适当的充实方式。我们的一大部分设定建立在本质上比感性直观更脆弱的根据上面,但它们是被奠基的。这就是红色球的例子要将我们引向的洞见。在《观念I》中,实在的物性是康德意义上的观念,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追寻这一观念,却始终无法获得完全的充实。
进一步的思考涉及对实项组成部分之经验基础所作的专门限制。通常,这样一种根本的限制是可以实行的,其结果,或者说,还原的剩余物,是所有感觉场中实项组成部分的一条河流。人们可以说,在理想情况下,这条河流中根本不存在一种有意义的立义之痕迹。各种各样的感觉在我之中“哗哗流淌”(rauschen),我却并未从中解释(立义)任何对象。
只有当人们在这个体验的组成部分之基础上展开对意向立义之批判,也就是说,只有当我想凭借自己的合法性审查我的作为树的立义、作为桌子的立义、作为一样红的球的立义,等等,问题才首次显现出来。例如,我可能有轻微的牙疼,而我却研究这样的问题:呈现给我的这种感受性是否也允许红色球的设定?当我——正如它需要严格地还原到实项的组成部分那样——已经排除了对象的所有表象,即所有质料时,我将从何“知道”,哪些实项的组成部分属于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就是“这个红色的球”——之描述,而哪些则不是?人们可以通过确定如下两个事实使这种思考具体化:(1)“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就是一种如此彻底的还原;(2)我不再知道,我可以期待看到什么。也就是说,我也没有任何根据来决定牙疼是否属于实项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对于球来说有或者没有一种描述的(表征的)功能。
因此,对胡塞尔的第一种还原的疑虑并不在于“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是无法实行的,而在于:如果我已经实行了这种还原,那么我就不能再这么做了。我之所以实行这一还原的原因和目的在于:对立义的合法性进行批判。a用我在第五小节引入的概念来说,人们可以说,“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虽然是“可能的”,但不是“有效的”。
因此,接下来的一步可能是,人们并不会像在“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中那样穷尽(verarmen)经验的基础。这意味着,人们寻找一个经验领域;意味着“刚好”适合实行这种对立义和设定质性之合法性的批判(或者,意味着人们在寻找一种用于被充实的被给予性的适当标准),但是,被寻找的合法给予的经验领域“尚不”能明确地或隐含地包含这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合法性首先需要检验。基于这两点考虑,人们必须说,在实项组成部分这里的这个唯一的开端太过彻底,也就是说,在排除了质料之后,对内容的对象设定之合法性的比较分析就不再可能了。可以说,一种对实项组成部分的专门限定把质料与质性放在了括号中。但是,对质料加括号从所谓的根据来说可能是无意义的。这个唯一的东西,即我能够在这样一种对证明合法的经验基础之追寻中加入括号的东西,就是设定的质性。但是,对经验领域的这种限定性的穷尽(Verarmung)正就是提出先验还原的《观念I》所建议的东西。b当然,在这里不应该说,在其内容中,也就是说,依照其质料,凭借其权利,检验一种“立义为……”(Auffassung als)可能是无意义的。人们必须只考虑,也就是说,尤其是只接受这些已经被呈现出来的困难。我们也始终已经把表面上“偏离”了对象意义的实项组成部分立义“为某物”,即有一个质料的某物。
二、《观念I》中的先验还原
在《观念I》中,对意向性立义之合法性审查的想法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提升,也就是说,提升到了现实性设定之合法性的问题高度。现实性设定是论题的行为特征之未被变样的原样式。同时,在自身理解中也产生了一种突破。胡塞尔认识到,他在这里真正做的,以及他在《逻辑研究》中已经做了的事情是:在一个确定的经验基础上,对现实性设定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界限进行检验。但他因此也注意到,他把客观性的根本之谜变成了主题,也就是说,通过何种方式以及凭借哪些权利,某物被设定为某个现实的东西。一方面,这个现实的东西始终为我而存在,另一方面,它同样也可为他人所通达。他也注意到,他已经提出了关于客观性的可能性与权利的条件之先验问题。基于此,他把悬置称为先验还原。这么做的根据在于,他借助这种方法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尽管也是在康德意义上的——先验问题。同时,胡塞尔也意识到,被寻求的、有权给予的(rechtgebend)经验基础不能仅仅只是对未被解释的、未被立义的实项材料之理论建构。在这种合法性审查中,质料和实项组成部分与意向性的三个构成要素(质料、质性和充盈)彼此不可分离。因此,只有一种对设定质性的“排除”仍然是剩余的。但设定质性以及“现实的”原样式和所有其变样恰恰是先验哲学的核心问题。经验领域,也就是在悬置之后仍然剩余的东西,还原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剩余物”,应该首先适于规定设定质性的合法性。
关于先验还原的意义,我已经着墨很多。接下来我将着重澄清先验还原的功能。“加括号”并不等于否定,毋宁说,它是对有效性要求的一种主题化。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并且有权将某物设定“为现实的”这个问题在注意的中心被提了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对有效性要求的加括号意味着一种“失效”(Außer-Funktion-Setzen)、一种排除。如果人们停留在加括号这个比喻这里,那么它首先意味着,括号里的部分没有发挥正常的功能。在一个句子的连贯意义中,一个被加了括号的语词在这个句子中不具有任何语法功能。因此,经验领域,作为先验还原的剩余物,不包含现实性、可能性、可疑性等的任何被接受的设定,毋宁说,它“只依照名称”包含这个设定,即只被视为一个要求。
现在自然地产生的一个问题涉及还原的普遍性:为什么还原必须是普遍的?这样一种想法显而易见,即这并不一定是无条件的。如果先验还原的思想已经在《逻辑研究》第一版的尝试中形成了,即为了能够判断意向性设定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而把一个行为的组成部分“还原”为实项的组成部分,那么乍看上去,在一个单个行为和独特的对象那里实行先验还原似乎也是有意义的。
基于如下一系列理由,这样一种个别的还原是不可能的:意向对象有伴随性的视域意向。这些伴随性的意向最好通过实行直观的可能性得到解释:我知觉到了一座房子,并且知道,如果我愿意,我也能够绕着这座房子走一圈,我能进到它里面,我能直观到它的背面,如此等等。我始终能够再次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具体细节中知觉这座房子。我知道,在该物体这里并且借助这个物体,我的身体有哪些运动的可能性。在每一瞬间,我都能向前走、转身、掉头。由于我自己运动或实行直观,所以在对象那里可直观到的一切都进一步指向了其他直观行为。因此,房子是与地面、楼梯、窗户、花园、芳香的花、冰冷的墙等这些东西一起被意指的,而这些东西全都属于这座房子。而且,街道也是同时被意指的,它从别处通向这座房子,而我也可以走到街上去。人们可以继续任意地进行这样的描述,即描述世界所有事物的普遍视域。
每一个表面上单一的对象都以这种方式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在根本上关联在一起,好像根植于世界之中似的。但是,这种根本上的关联并不只涉及对象的意义,而且也涉及设定的质性:这座“现实的”房子指向“现实的”街道,这条“现实的”街道又指向近旁存在的“现实的”城市,这座“现实的”城市复又指向“现实的”世界整体。每一单个对象与作为整体的世界之现实性设定的这种根本的、好像骨节一样的分环勾连和缠绕关系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所有现实性设定的这种交织的一种明显后果是:一种限定在单个对象上的、可以说“单个地实施的”设定质性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人们要么普遍地进行还原,要么完全失败。
或许可以在《观念I》中发现另一个重要的洞见:人们不能在全部范围内将有些设定回溯到感性上去,这不仅适用于高阶表象,而且也适用于例如一个实在物体的日常表象。虽然“现实性”设定对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来说尤为根本,但是它也建立在这样的表象上:一个物体总能够被他人或被我自己变成直观的。因此,这种对更进一步的经验,也就是对未来(我们并不能直观地具有)的预先把握(Vorgriff),在每一个尚且如此单纯的对象设定中被一同包含在其中。但是,这一预先把握也可能是“或多或少”合法的,例如,它可以表现为一个视域意向,这个意向完全可以在我的肉体运动的框架内得到充实:“我能”(ich kann)“总是”绕着这座房子走一圈,“我能”“总是”看到一棵树,等等。这种“我能”在我迄今为止的经验中和我的身体的能自身运动(Sich-bewegen-Können)中被引发。就此而言,它是被奠基的(被引发的)预期,这一预期建立在我的预先就有的经验和对象上。它并不涉及空乏的、单纯逻辑的可能性之表述,这些可能性不是在经验中被引发的,就像我明早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或许可以飞,或者可以“阅读”另一个人的思想。a关于胡塞尔的与空乏的可能性相对的、在经验中被引发的可能性概念,参见EU,§21,d 和§77。
三、原初的还原
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引入了一种新的还原,即所谓“原初的还原”(Primordialreduktion)。在这里我想跳过对这种还原的特殊问题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在它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意义时,我才会回过头来对之作深入探讨。我想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还原的方法论意义上,以便表明,它应该像迄今为止被描述的那些还原一样得到严格的说明。如果我们试图审查设定其他主体性的合法性,而这种审查又应该在一个直观地被给予的经验领域上进行,那么,对“其他主体性”的设定就既不能明显地也不能隐含地包含在这个作为基础的经验领域中。这就是原初的还原的意义。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人的”意义既不能明显地也不能隐含地包含在我的审查所由之出发的经验领域。
原初的还原是一种“主题性的”(thematisch)还原,胡塞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么认为的,而这首先意味着与先验还原之“普遍性”的某种对立——原初的还原并不是说,以相同的方式对经验领域中的所有元素进行还原(以满足其有效性要求),而是说,在我们的世界表象中有针对性地追踪这些“陌生心理的”元素,并暂时忽略其有效性和意义,即对它们进行“还原”。所有那些以任意方式隐藏在其他主体之成就中的设定都将因为这一意义元素通过抽象被完全穷尽(verarmt)。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审查,如此获得的经验领域是否被妥善地构成了,从而成为世界经验的一个独立层次。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审查,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在这个被还原的经验领域中构造某个像“他人”一样的东西。
我不打算详细考察这种构造分析的具体细节和开放性问题,在这里,我只打算强调还原的类似的方法论特征。原初的还原是要构造出一个作为合法性审查之基础的经验领域。这个经验领域不涉及其合法性应当得到审查的元素。然而,在原初的还原中,不可能进行普遍的还原,而且那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所有对象就都被无差别地排除了,而不论它们是被我还是被他人所构造的。因此,原初的还原必须单独进行,也就是说,要依主题的不同而进行。
四、三种进一步的还原:向个体对象之明见性的还原;向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还原;向前述谓经验的还原
在胡塞尔的著作中,至少存在三种系统的关联(抑或更多),在这些关联中,一种可比较的方法措施像迄今所描述的那些还原一样得到了实施。这三种系统的关联包括:1.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第二部分中,对“逻辑与数学中的观念性的批判”;2.在《经验与判断》中将述谓判断的“逻辑”范畴回溯到前述谓的经验之上;3.在《危机》中,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观念化批判。然而,这三种分析都属于一种系统的关联。现在我将简要对其进行描述。
(对于1 和2 而言),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第二部分中,胡塞尔提出了对“逻辑与数学中的观念性进行批判”的计划。这首先涉及对逻辑原理之合法根据的研究,例如,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等等。显然,逻辑原理超越了能够由我们的感性直观所奠基的领域。因为胡塞尔也不是在感性领域中着手寻找赋予合法性的元素,而是回溯到对知觉之个体对象的同类经验上。其主题明确体现在下列表述中:为了表明其合法性,“逻辑需要一门经验理论”aFTL,S.219.,而且是一门个别具体对象的经验理论。
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对形式科学中的“观念性的批判”——这一批判首先涉及逻辑原理——同样也必须回溯到一个本身不具有任何观念性的经验基础上,因为,否则构造分析就会陷入循环。为此,胡塞尔建议回溯到个别具体对象的经验上去,这些个别的具体对象通常既不能包含这样的观念化,也不能包含述谓的意义积淀。此外,这种回溯也能被看作向低层次的明见性形式的回溯[在一种reducere(还原)的意义上]。然而,这一“批判”的方案首先在《经验与判断》中得到了全面实施。
逻辑原理显然是一些基于观念化的表述,也就是说,它们建基于一种(在实际的行动和认识中不可孤立的认识过程之)被设想的孤立性上。矛盾律是说,对于所有可设想的判断来说,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为真。因此,矛盾律是一种观念化的产物,因为它针对所有可设想的判断作出了一个论断。但事实上,我始终只能将矛盾律适用于有限数量的判断。对于那些无限的“剩余物”来说,我只能通过观念化的“预先把握”(Vorgriff)来统摄他们。但是,这种观念化的预先把握又是以什么东西为基础的呢?它也有一种合法性吗?它甚至也可能具有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合法性吗?胡塞尔将会通过其对逻辑之观念化的批评来澄清这些问题。在这里“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一种设定之合法性及其界限的审查。
虽然从经验基础(Erfahrungsboden)出发来澄清这样一种合法性通常是可能的,但这一经验基础本身不能包含任何意义元素,因为这些意义元素的合法性还是成问题的。胡塞尔对这一经验领域首次进行规定的尝试是在个别具体对象及其认识领域中发生的,我们是在与这些对象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的。因此,胡塞尔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所设想的方案已经涉及他后来在《经验与判断》中称作前述谓经验的东西。前述谓经验领域,不仅是述谓判断的逻辑范畴的起源,而且也是观念化设定的动机起源。
现在我们就可以——也就是说,在我们已经称作平行研究和方法论的加括号之背景上——把这种向个别对象之被给予性的回溯理解为还原了。这种回溯是一种对我们所熟悉的日常世界的第一个经验领域的限制。这个日常世界不仅包括对象,而且也包括我们所具有的关于个别对象和对象种类的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而非我们在与实在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知觉所获得的前述谓的知识,从方法论上被排除了。于是,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常知识应当被排除?虽然我们只能推测,但容易理解的是,胡塞尔意识到,观念化设定已经渗入(“涌入”)了“以科学的方式所构成的”文化中,而他正努力避免这种趋向。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不加审查地接受观念之物或“逻辑思想”的做法本就应当接受批判。
或许就这里所讨论的向个体对象之明见性的回溯而言,我们也可以提及“主题性的还原”。所谓主题性的还原是指有目的地并且“以个别的方式”排除这样一些元素的做法——这些元素可能已经包含了这些观念化的东西或与之类似的东西,并且使那些与之无关的东西获得了有效性。然而,这种向作为合法性根据的个别具体对象的回溯并未以这种方式得到实施,因为对于每一种观念性(或者说,每一种逻辑原理)来说,我们都必须实行一种专门针对它的主题化还原的特有的变更。为此,毋宁说,向个别对象之经验的回溯与一种对所有意义元素——这些意义元素归功于我们在进行判断时的一种述谓的意义创建——的“普遍”还原相对应。我们可以说,主题性还原的目的是对所有述谓判断及其成果进行一种普遍的还原。以这种方式确立的合法性根据是一个经验领域,因为我们有对象,即使我们并不作出任何与这些对象有关的述谓判断。
(对于3 而言),但是,这里有一个疑虑:就个体对象而言,我们总还是会怀疑,它们是否可能悄悄地在其对象意义中,也可以说“在其自身中”,包含了观念化,从而将那些“颠覆性的”逻辑意义带入到经验根据之中?在将这种“对观念化的批判”进一步延伸到《危机》中时,胡塞尔探究了这种猜测。《危机》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科学的观念化。这种批判也需要一种回溯,一种reducere(还原),但这次是回溯到前科学的生活世界。
然而,这种“还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向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回溯将我们的注意力——因此,可以将它与同样“主题性的”原初的还原进行比较——转向了在自然科学中历史地—实际地发生的观念化及其始终与人和“首次发现”(erstmalige Entdeckungen)有关的显现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对这些观念性的“原创建”(Urstiftungen)的历史描述和向“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回溯,对观念性进行“批判”的方案才能得到完全实施。通过将生活世界从近代自然科学的所有观念化元素中抽离,它重又变成了一个脱离了这些观念性的生活世界。
五、还原的观念
在这一小节里我将尝试刻画还原方法的本质特征。此外,我们也必须搞清楚“还原是可能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更确切地说,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还原的剩余物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它必须是一个“经验领域”,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直观的、被妥善地构建的,而且相对独立于其他经验领域(自为地可经验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种还原是否也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个被揭示的经验领域是否能够让我们如愿以偿?即,是否能够在直观的被给予性中为被批判的设定提供合法性证明?
在此,我将首先考察还原这种说法的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如此重要,本来早就应该得到阐明了:一方面,还原是指向一个有意识地通过特定的方法纯化了的经验领域的“回退”(Rückgang),另一方面,还原是指将需要被审查的设定向这个经验领域中的直观的被给予性的具体的“回溯”(Zurückführung)。
当然,我们也可以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即胡塞尔的还原或许也与还原论有某种联系。然而,这里存在一种根本的意义差别。还原论的一个心理学的—感觉论的变种有可能是把一个对象与感觉与料(Sinnesdaten)的复合等同了起来。这些感觉与料对于一个主体来说就展现为对象。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说:对象是感觉与料的复合——现在不能再这么说了!人类意识是神经元的一种复杂的联通状态——现在也不能再这么说了!相反,胡塞尔的还原观念是从这样一个洞见开始的,即我们的每一个表象都与复杂的综合功能有关,为了能将某个东西知觉为一个对象,我们必须“始终已经”实行了这些功能。也可以说,还原的观念基于这样一个洞见,即从构造上来说,意识与对象有关;从对象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总已经根据综合的功能而呈现为一个“多”了。因此,如果我们将被思考的对象与作为基础的经验领域的预先规定(Vorgabe)相比较的话,意识已经添加了这些功能。
康德首次提出必须要把在我们的主观综合中已经“构造”出来的对象回溯到综合的主动性上去。综合的主动性完成并且表明了这种构成活动。康德对经验论的生产性的接受(produktive Aufnahme),其标志不在于接受了作为被给予的、容易被把握的质料的感性材料,而在于他有目的地指明了综合的、统一的和联结的行为。当然,人们也可以就此批评康德,他把合法性证明的方向完全片面地放在了对于综合来说必然会被使用的概念及其在人类理性装置中的起源上。众所周知,胡塞尔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康德的影响,他和他的合法性证明走向了直观的被给予性。
毋宁说,胡塞尔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经验论的遗产,在我看来,他的“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这一有问题的尝试应归功于这样一个洞见:将所有表象内容都回溯到——例如由休谟所提出的印象——上去的这一朴素的经验主义方案,对于现象学来说是不足够的。人们必须始终将其回溯到意识的综合成就上去,首先回溯到意向性立义的成就上去,但也必须认真地注意综合成就的较低(例如在内时间意识中)或较高(例如在范畴直观中)形式,及其各自在不同的、直观地进行给予的经验领域中的充实方式。如果只把单纯的感性作为合法地进行给予的经验根据,我们走不远。
现象学的动机,即推动还原的同时在其中表达自身的动机是这样一个洞见:我们思维的所有对象都展现了复杂的综合成就。如果我们想审查单个具体设定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必须始终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再次返回综合的成就,以便能够在感性、动机、经验那里考察原材料(Ausgangsmaterial),这些原材料是设定的基础,并且能够为其合法性奠基。在这个意义上,还原是一种“去—综合的”(de-synthetisch)方法。尽管如此,我们在反思的和抽象的工作中所能获得的这种原材料并非已经无条件地是一种“原材料”(Rohmaterial)。在我们的这种综合成就尚未实行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已经通过直观给出了这一原材料。这个问题在通过“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对对象立义之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计划中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当我们打算将“阴影”或“高光”作为主题时,我们始终已经(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立义。可以说,这一洞见拒斥了经验论的那种诱人的单纯思想,也就是说,为了审查诸如树、房子、他人、权利、上帝等的合法性,人们只需要朝向通过感官而被给予的感觉材料就可以了。相反,适当的、合法的基础只有通过分析的、反思的和还原的(去—综合的)工作才能获得。此外,人们不能过于狭窄地理解合法的经验要素的范围——人们必须求教于预期,因为正是预期,通过预先被给予的经验,具有了一种合法的动机。
在对还原意义的反思中,得到清楚表明的是:如果想使用现象学的合法性证明的方法,那么人们就必须遵循确定的“受经验主义启发的”原则。它们完全是认识论的朴素性原则。因此,人们也可以将其表述为一条一般原则:尽可能准确地规定一种设定的要求与实际被给予的充实之间的区别。几乎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区别,有时,充实的部分是一种简直可怕的贫乏,正如在日常因果性中的情况那样,这种因果性不再是一种在我的经验中被注意到的事物的“习惯”——与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普遍的、精确的因果性的观点相对。有时,充实的部分也极具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充实综合加以扩展,例如在进一步的人格的行为举止中对主体设定的证实。
如果我们也具有实项的被给予性并且能够将其作为主题,如果这些实项的被给予性也不存在于意向立义之中,那么“向实项组成部分的还原”就是可能的。因此,这一经验领域不能“自为地”被给予。然而,对于尝试一种对不同立义的“差异分析”来说,这一经验领域也不是毫无助益的。例如,这种差异分析的出发点在于:当人们更改立义时,它保持为“同一个”实项的组成部分。
原初还原的剩余物是一个可经验世界的层次,我能“完全独自”构造这个世界,而不需要牵涉他人的意义构造成就。“原初的自然”,即我只能凭借我的感性、我的身体和我的经验构造的这个自然,看来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可能是:在对象之构造这里,语言(这里的语言完全是主体间的)和语言概念的必然的参与。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和《经验与判断》向个别的、具体的对象以及对这些对象的前述谓经验的还原,同样作为还原,看上去是可实行的。但是取得成功,即确保没有任何隐含的意义成分已经包含了观念化——《危机》的努力表明了这一点——是何等困难 啊!
一个进一步的、同样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涉及通过还原所达到的经验领域的效能(Leistungsfähigkeit)。如果需要被考察的设定实际上能够在这个经验领域中被回溯到其合法的根据上,那么我就把一个还原称为“有效的”。这在所有还原那里都是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在合法地进行给予的经验那里允许放宽了的标准,那么人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标准塑造得“更软”(weicher)。a文本Nr.14,Hua XV,S.196—214 给出了这一策略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胡塞尔试图在日常被体验到的世代链条(Generationenkette)之经验基础上为时间(空间)的无限性设定找到一个具有经验基础的动机:我们从本质上洞见到,每一个人都必定有一个母亲,“如此等等”!胡塞尔在这里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对于时间性来说,我们有世代。”(Hua XV,S.206.)——至少对于过去时间的无限性来说,因为对于世代向未来的延伸,胡塞尔自己甚至也是持怀疑态度的(vgl.Hua XV,S.210—214)。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批判”计划,即规定我们的认识要求的合法性及其界限的批判计划。就此而言,现象学通过还原方法理所应当地提出了要成为一门先验哲学的要求,而胡塞尔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洞见到这个名称是恰当的。为此,这种奠基的方法就是向一个经验领域的回溯。设定的权利/合法性就是审查,而设定尚不包含在经验领域中。只有在构造分析中,在这样一个经验基础上,人们才不会在合法性证明中犯循环论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