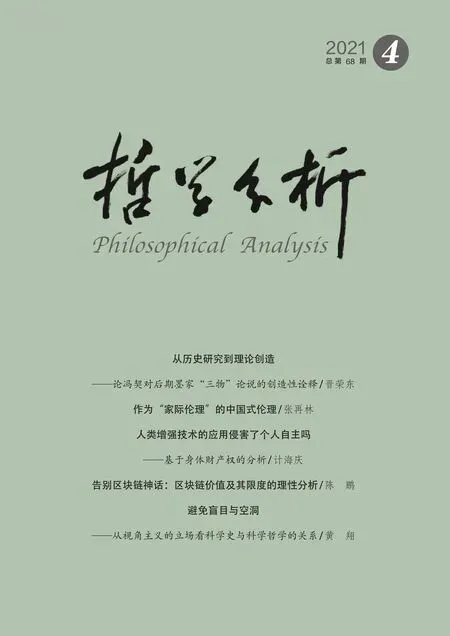布兰顿思想中的黑格尔资源:考察与评估
孙 宁
一、引言
罗蒂(Richard Rorty)在为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56)所写的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如果说塞拉斯的哲学方案是“试图将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那么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哲学方案是“试图将分析哲学从康德阶段推进到黑格尔阶段”aRichard Rorty,“Introduction,” in Wilfrid Sellars,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p.8.。这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论断,但罗蒂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展开。如果说罗蒂作出的判断在当时(1997)还是一种敏锐的洞察,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成熟的契机和丰富的素材来全面评估布兰顿思想中的黑格尔资源。布兰顿在《使之清晰》(1994)中所展现的黑格尔式倾向在《先哲往事》(2002)中获得了来自哲学史的依托。而2007 年的洛克讲座(《言行之际》)可以说是黑格尔思想在分析实用主义语境中的实质性运用,布兰顿在该讲座中明确指出,他所探讨的“由语用中介的语义关系”本质上就是黑格尔的“观念论”aRobert 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00.。近年,布兰顿出版了自己花了近三十年、几经易稿才完成的对《精神现象学》解读的成果——《信任的精神》(2019)一书。这一文本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黑格尔在布兰顿思想发展中的位置,还为观念论语汇和分析语汇的创造性融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范型。
本文的任务有三个:首先,分析布兰顿将分析哲学从康德阶段推进到黑格尔阶段的理论动机和具体方案;其次,梳理黑格尔对布兰顿的两个主要启示,即从理性主义推进到表达主义,以及作为“宽大回忆”的历史理性洞见;最后,讨论布兰顿如何将黑格尔的资源有机地整合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总结性地评估布兰顿对黑格尔的借鉴。
二、康德的失误与洞见
在匹兹堡学派中,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和布兰顿都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概念实在论”。他们都试图阐明,实在并不处在概念的封闭界限之外,世界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概念进程的塑造中了。但两者对概念实在论的理解又存在明显分歧。麦克道尔将自己的构想视为康德式先验路线的延续,他认为概念实在论只有在先验契约(stipulation)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即概念必须在一种推论性直观中本质地与对象相遇。而在布兰顿看来,真正有效的概念实在论不是先验地规定概念和实在的关系,而是要通过一条结合了逻辑主义(共时性分析)和历史主义(历时性分析)的推论主义路线来构造这幅能够将实在纳入概念运作的图景。因此,不同于麦克道尔,布兰顿的概念实在论并不是从深化康德的先验论洞见,而是从批判康德的概念观入手的。
布兰顿在《使之清晰》的结论部分指出了康德式概念观中的三组二元对立:首先是形式与质料的对立,其次是共相与殊相的对立,最后是自发性与接受性产物的对立。在第一组对立中,作为形式的概念与提供内容的质料对立;在第二组对立中,概念性的共相和非概念性的殊相对立;在第三组对立中,概念秩序与因果秩序对立。概而言之,在康德那里,“概念的功能是作为认识论的中介。它们站在知性的心灵和为知性提供内容或质料的世界之间,这个世界由可以被一般概念把握的殊相构成,它因果性地强加于心灵之上,让心灵以某种方式服从于那些因果冲击”a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618.。
布兰顿认为,如果我们将这种二元论概念观作为解读康德的前提,那么麦克道尔试图通过先验契约实现的概念实在论构想显然是无法成立的。不过,概念实在论虽然无法以这种短程的方式实现,但可以以一种长程的方式实现。为此就需要建立一种推论主义的概念观。这种概念观主要由三个理论部件构成:实质推论(material inference)、替换(substitution)和回指(anaphora)。通过这三个理论部件,布兰顿分别将康德那里的三个非概念性极点整合进概念领域,即通过实质推论整合内容,通过替换整合殊相,通过回指整合因果秩序。在布兰顿给出的“推论—替换—回指”(ISA)这条三层推论语义学路径中,每一层次分别对应于句子(sentence)、次语句表达(subsentential expression)和以单称词项的指代使用为范型的不可重复殊型(unrepeatable tokening)。以这个逐层细化的结构(推论的细节要求我们关注替换,而替换的细节又要求我们关注回指)为基础,布兰顿得到了他的概念实在论:“这种被推论性地阐明的概念观许可了这样一幅思维和世界的图景:思维所涉及的东西也被概念性地阐明,它和思维是对等的,在好的情况下,甚至是同一的。事实就是真断言。”bIbid.,p.622.
但布兰顿也看到,尽管我们需要通过推论主义概念观来克服康德式的二元论概念观,但推论主义概念观的关键结论却已经被康德先行洞见到了。我在《匹兹堡学派研究》中指出了“康德—塞拉斯论题”(Kantian-Sellars thesis)在布兰顿思想中的关键位置。c参见孙宁:《匹兹堡学派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18 年版,第145—147 页。概而言之,布兰顿认为塞拉斯第一次澄清并推进了康德提出的开创性洞见,即强调“命题性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propositional)。布兰顿认为,康德的这一洞见包含两个重要信息:第一,阐明人在首要意义上不是观念的思维生物,而是判断的话语生物,由此纠正了自笛卡尔以来的对命题的遗忘;第二,用规范的约束性(Verbindlichkeit,bindingness)来探讨判断的有效性(Gültigkeit,validity),由此将笛卡尔式的“思维之我”推进到“负责之我”,并让认识论问题最终落脚于义务论语境。
强调命题性的首要性的直接后果是在元语言层面确立了一种规范性语汇,并通过规范态度最终建立规范身份。在布兰顿看来,这正是康德赋予“启蒙”的真正涵义。他指出:“在康德看来,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无规范领域——并不存在无法应用概念的领域。我们最好这样来理解康德的根本性革命:他用一种规范性的元语言来同时界定单纯发生的和人所做的。”a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p.625.进一步,康德将事实和规范的区分理解为“规则”(regularity)和“责任”(responsibility)的区分:前者是概念所应用的领域,后者是应用概念者的领域,前者是服从隐含的法则,后者则是清晰地认识并应用法则。布兰顿指出:“这里的区分不是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的区分,而是可以有明确的规范态度和不能有明确的规范态度之间的区分。”bIbid.,p.624.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在康德的帮助下阐明一种概念实在论构想,关键的切入点并不是像麦克道尔那样抓住康德的感受性和自发性,而是考察规则的“隐含”运作(实在)是如何进展到规范的“清晰”运用(概念)的。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实在论首先必须是一种规范实在论。
可以看到,布兰顿对康德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后者的概念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关于规范性的深刻洞见。布兰顿试图通过推论主义概念观的三层结构来修正康德式的概念观,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一种规范实在论的可能性。黑格尔正是在这个理论节点进入了布兰顿的视野。布兰顿在研读黑格尔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可以通过黑格尔提供的两个启示来实现对康德的修正,即从理性主义推进到表达主义,以及作为“宽大回忆”的历史理性洞见。它们分别对应于《使之清晰》所包含的一显一隐两条线索:显性的线索是从“隐含”到“清晰”的推进过程,隐性的线索则是从“清晰”到“隐含”的回溯过程。
三、黑格尔的第一个启示:从理性主义到表达主义
布兰顿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重要启示是,从“隐含”到“清晰”的推进实际上是用一个规则去“解释”(Deutung)另一个规则的过程。隐含的规则在这种层级性的解释递进中逐步转化为清晰的规范,实践性的knowing-how 也由此转化为智识性的knowing-that。布兰顿将这种能力称为“表达能力”(expressive capacity),并将自己的理论称为解释清晰如何产生于隐含的“表达理论”。cIbid.,p.77.他试图阐明,正因为这个表达维度的存在,语言实践的参与者不仅是主动应用概念的理性存在,还是自觉阐明理由的逻辑性存在。布兰顿认为这种表达能力是对启蒙式理性的实质性推进。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判断是意识的形式”这个“康德式论断”上再加上另一个断言,即“逻辑是自我意识的表达工具”。也就是说,“判断被理解为承认某种得到推论性阐明的承诺的实践态度。为了让判断的语义和语用基础变得清晰(让其具有可供判断的形式),逻辑语汇提供了所需的表达资源。借助逻辑语汇的工具,我们能够谈论推论的规范,计分态度的结构(正是在这种结构之内,一个举动才能被赋予承诺或接受一个承诺的意义),以及话语实践的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a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p.643.。
布兰顿看到,这个从理性主义到表达主义的推进步骤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明确展开了。首先来看黑格尔的工作前提。黑格尔并不像康德那样明确区分知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在黑格尔那里,理性隐含在知性中,而理性的实现就是知性的阐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区分“自在”(an sich)的人和“自为”(fürsich)的人明确揭示了这一点,他指出,“诚然,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而有教养的理性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是的那个东西。这才是理性的现实。”b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3 页。这个历史性的连续视角是从隐含到清晰的理论方案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
然后再来看黑格尔的方法。布兰顿将黑格尔的方法界定为“逻辑表达主义”(logical expressivism)。这一方法包含了两层内涵。首先,黑格尔将概念或范畴理解为“思想规定”(Denkbestimmung)。思想规定,作为一种规定(bestimmt),其本身不断发展的,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形成判断,而是在一个辩证历程中帮助思想从隐含走向清晰。不同于康德,黑格尔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方法去反省判断的形式,通过展现概念内部的空间和张力促成命题的辩证运动。这种独特的运用方式被黑格尔称为“思辩命题”(der spekulativeSatz)。根据这种表达主义的概念观,康德式概念观的主要问题是对概念运作的平面化理解,经验心理学的视角让他没有看到我们的表达资源和表达能力是可以不断充实和丰富的。c夏钊提醒我注意,是否可以用思辨命题来代表黑格尔的概念观是值得存疑的。比如,杜辛认为,思辨命题只是基于主谓命题的“同一命题”,它只是思辨的一个面向,并且只能代表黑格尔的某种不成熟的理论尝试,不能完全反映黑格尔对于辩证理性的全部思考。参见Klaus Düsing,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Bonn:Bouvier,1995。
布兰顿在2005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黑格尔实际区分了两类概念:经验概念和逻辑概念。经验概念就是日常语言中所使用的概念,逻辑概念则包括“逻辑的哲学概念和思辨哲学的论断,而这些概念和论断的展开就是《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主题。”aRobert Brandom,“Sketch of a Program for a Critical Reading of Hegel:Comparing Empirical and Logical Concepts”,in Karl Ameriks &Jürgen Stolzenberg(eds.),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German Idealism 3,Berlin:de Gruyter,2005,p.134.布兰顿指出,尽管经验概念和逻辑概念的内容都是在历史中不断展开的,但它们在黑格尔那里扮演了不同的“表达角色”(expressive role):“对黑格尔而言,逻辑概念扮演了这样一种明确的表达角色,它使日常的非逻辑概念的使用和内容的一般特征变得清晰。逻辑概念是一种元概念。”bIbid.,p.134.他还在另一篇回应文章中指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试图从最具体的概念出发(“感性确定性”);而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则试图从最抽象的概念出发(“有”)。这两条不同方向的路径是殊途同归的,它们最终要获得“关于事物如何运作”的知识。布兰顿指出,在黑格尔的语境中,这种知识是可以得到清晰阐明的,它既是《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知识”,又是《逻辑学》中的“绝对理念”。cRobert Brandom,“Replies”,in Bernd Prien &David Schweikard(eds.),Robert Brandom:Analytic Pragmatist,Frankfurt:Ontos Verlag,2008,pp.180—181.当然,《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这两条路线能在何种意义上整合起来,这在黑格尔研究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逻辑表达主义的第二层内涵更为关键,即通过清晰的逻辑语汇重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作为黑格尔在英美学界复兴的一个主要标志,泰勒(Charles Taylor)的《黑格尔》(1975)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布兰顿。泰勒从现代的理论语境出发提炼了黑格尔的两个主题——“表达的统一性”和“激进的自主性”,并将黑格尔理论方案界定为这两个主题的合题。泰勒在这个合题中语境中探讨了黑格尔的“表达主义理论”(expressivist theory):“一个主体之最充分、最令人信服的表达是当他既明确了他的意图又实现了他的意图的时候。”他指出,这种表达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因为“它不仅是生命的圆满,而是意义的明晰”。并且,这种表达主义还对人是理性动物的传统观点作了新的解释:“人通过表达他的所是并因此澄清他的所是以及在这种表达中承认自身而逐渐了解了自身”。d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6—17.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版,第23—25 页。为行文的统一,将原译的“表现”和“表现主义”一律改为“表达”和“表达主义”。和泰勒一样,布兰顿探讨的逻辑表达主义并不只是一种解释如何遵守规则的理论,同时还是一种表达意图的理论。这就意味着这种逻辑表达主义不仅超出了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语境,也超出了分析哲学中的言语行为主义转向,而进展到一种社会实践理论。
《使之清晰》的一个关键区分是规范态度(normative attitude)和规范身份(normative status):规范身份直接解释了承诺和资格是什么,而规范态度则解释了怎样才算是认为某人具有这种规范身份。《使之清晰》的主要思路是通过规范态度来理解规范身份。规范态度和规范身份是个体话语实践者层面上的区分,以此为模式,我们可以在话语共同体层面上作出类似的区分:隐含在共同体实践中的计分规范,以及将某个解释者将原始意向性归属给一个共同体。布兰顿指出,这两个维度不是内在(内在于共同体实践)与外在(外在于共同体的“俯瞰”视角)的区分,而是隐含与清晰的区分。在个体话语实践者上,我们可以通过逻辑表达主义方案从隐含走向清晰,在话语共同体层面上,我们同样也可以从隐含的记分行为走向对话语计分态度的清晰归派,最终实现一种扬弃了语汇的相互外在性的“解释平衡”(interpretive equilibrium)。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处在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和自我意识阶段的心灵并不能把握这几个阶段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些逻辑关联是“现象学家”在反思中把握的,现象学家的反思将相互外在的阶段整合为精神发展的完整历程。对此,布兰顿在《使之清晰》的一个重要脚注中指出,“在《精神现象学》中,现象的态度(phenomenal attitudes)最后发展到与一路考察它们的现象学观点(phenomenological view)相一致。黑格尔令人警醒地将这种清晰的解释平衡界定为‘绝对知识’”a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p.716,n.35.。在《使之清晰》的语境中,在现象学家的反思中被把握的“绝对知识”被重构为“我们”(We)语汇中的“解释平衡”。布兰顿指出:“相互采纳清晰话语姿态的共同体成员表现了完全而清晰的解释平衡,这种解释平衡就是社会性的自我意识。这样的共同体不仅就是‘我们’,它的成员还可以在最完整的意义上说‘我们’。”b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p.643.在这样一种“我们”的语汇中,“内在于共同体并构成共同体的那种计分与将计分实践归属给共同体的解释者本人的计分相一致。外部计分变成了内部计分。将话语实践归属给他人就变成了一种说‘我们’的形式。这就是将他人承认为我们”cIbid.,p.644.《精神现象学》中对应的表述是:“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2 页。。
布兰顿指出,为了实现这幅伦理图景,我们必须对自我和他人有超越传统理性主义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仅使之清晰,还在使之清晰的同时使我们自己清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远不止是理性的表达性存在,我们还是逻辑的、自我表达的存在”dIbid.,p.650.。另一方面,说“我们”就是认为他人不仅是“理性的语言生物”,还是“逻辑的生物”,即“认为他们能够相互采纳——并且至少能够潜在地对我们采纳——我们对他们采纳的态度”。a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p.643.布兰顿试图阐明,我们不仅是理性的语言生物,还是逻辑的表达生物,我们不仅依据理性而言行,还尝试通过逻辑的语汇清晰地表达言行的理由,并通过这种表达不断反思理性在言行中的位置。在这样一种自我反思中,我们不断丰富自己的表达资源,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而这就是理性生物的自我教化过程。
四、黑格尔的第二个启示:历史理性与“宽大回忆”
在康德那里,先验哲学的任务非常明确:先验哲学不考察对象,只考察让对象得以可能的先天认识方式。黑格尔对此的批评是:对认识的批判不能先于认识本身的历史,对判断的研究只能在对对象的判断中进行。根据布兰顿的解读,黑格尔兑现这一批评的主要方案是在社会语境下理解规范的约束性。在社会语境下,约束原则上不能是对单一个体的约束,而必须是一种相互归派的社会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身份。布兰顿在《哲学中的理性》(2009)中指出:“黑格尔的主要革新在于指出,为了追随康德的根本洞见,即阐明心灵、意义和理性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我们必须认识到权威和责任这样的规范身份最终是社会身份。”bRobert Brandom,Reason in Philosophy:Animating Idea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66.不同于“逻辑表达主义”这一相对独特的解读,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这一解读与当代视角的关联更为紧密,我们可以将它放在从科耶夫的存在主义解读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再到晚近对黑格尔的社会性解读这条大的线索之中。cCf.Alexandre Kojève &Raymond Queneau,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New York:Basic Books,1969;Axel Honneth,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Cambridge,MA:MIT,1996;Terry Pinkard,Hegel’s Phenomenology:The Sociality of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Robert Pippin,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Rational Agency as Ethical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Dean Moyar,Hegel’s Con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布兰顿对这一理论议程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精细的分析语汇刻画了建立和运用规范的社会进程。
布兰顿在《先哲往事》中区分了五种理性模式:逻辑理性(logical rationality)、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翻译理性(translational rationality)、推论理性(referential rationality)和历史理性(historical rationality)。d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具体而言:逻辑理性将理性的效力理解为能够区分逻辑上好的和逻辑上坏的论证。工具理性从实践推论出发,探讨欲望、偏好和信念为行动提供理由的方式。翻译理性是戴维森提倡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说他人的某个信念是理性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将此信念整合进自己的语汇,并与之展开对话。在翻译理性看来,逻辑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主要问题在于错误地认为我们可以在首先把握信念内容的前提下再来考察它们是否理性,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考察信念之间的理性关系。而推论理性(也就是布兰顿提出的理性模式)则认为,翻译理性在用自身语汇解释他人信念时并没有考察自身语言实践的结构,因而并没有真正走出唯我论的理论模式,从“我”真正进展到“我们”。推论理性的基本思路和具体策略在《使之清晰》中得到了完整的阐明。
在黑格尔的帮助下,布兰顿又提出了第五种理性模式:历史理性。当然,《使之清晰》中已经包含了历史理性的提示,但这一理性模式在《先哲往事》中才得到明确界定,并在《实用主义的诸视角》(2011)中呈现完整形态。布兰顿认为,前康德的理性主义者——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为典型——已经展现了推论主义的倾向,而正是这种倾向将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区分开来。这种理性推论主义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推论整体主义”(inferential holism),即认为只有概念之间推论关系才能决定某个概念的概念内容;其次是“理性功能主义”(rational functionalism),即认为表征的意义在于它在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a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p.29.而康德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在这条理性推论主义路线的内部提炼出一个规范性视角。我们在使用概念A 之后或者势必要使用概念B,或者势必不能使用概念C,又或者还可以使用概念D,这说明概念的使用必须包含了规范维度,而这个规范维度就是决定推论步骤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种规范层面上的意向性必然是一种规范语汇。布兰顿指出,经验论者只关心如何证成表征信念,并不关心表征的意向性,而康德的洞见恰恰在于说明,表征的意义并不是来自前者,而是来自后者,也就是说,基于规范意向性的表征必然涉及作出承诺、对被表征物行使权威、对被表征物负责等规范身份。
和康德一样,黑格尔也认识到了判断中的规范维度。但和康德不同,黑格尔认为所有先验构成(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都是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alization)。因此,规范意向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由它在之前所有判断中的使用情况所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规范身份的获得一定是一项社会性成就。布兰顿指出,黑格尔试图用一种“社会功能主义”(social functionalism)来补充康德的“规范理性主义”(normative rationalism)。bIbid.,p.31.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康德的思路是成文法(statutory law),那么黑格尔的思路就是习惯法(common law)。cIbid.,p.13.他还建议我们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理解为奎因对卡尔纳普的批评。奎因试图用“单层解释”代替卡尔纳普的“双层解释”,即不是先规定意义,然后再应用于语言的使用,而是将语言的使用同时理解为意义的建立和应用过程。同样,黑格尔也试图用“单层解释”代替康德的“双层解释”,即不是先在先验活动中建立规范,然后再应用于经验,而是说,经验同时是规范的建立和应用。布兰顿指出,这种由使用决定概念内容的“实用主义功能主义”(pragmatist functionalism)是理解黑格尔的“概念观念论”(conceptual idealism)的关键。a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p.53.
根据这种单层解释,我们不能先验地给定规范,而必须通过回溯一个传统或给出一个谱系来探讨规范的建立过程。布兰顿认为黑格尔探讨的“经验”(Erfahrung)明确揭示了建立规范的历时性进程。他在《信任的精神》中指出,“黑格尔将确定概念内容的过程称为‘经验’。如此确定的内容阐明了恰当应用那些概念的规范。因此,经验过程既是在将明确概念内容应用于判断和意向性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明确概念内容的过程。回溯地看,确定的过程就是发现的过程。”bRobert Brandom,A Spirit of Trust: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7.布兰顿认为,为了理解规范的概念结构,我们必须对表达和建立规范的社会实践史作渐进的理性重构,用观念论的语汇来说,理性必须在对自身的反观中获得自身的体系化历史。因此,如果说康德阐明了一种推论主义的意识观,那么黑格尔则进一步阐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自我意识观,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在康德已经给出的两个维度——推论维度和规范维度——之外又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历史维度。
《信任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个历史维度展开的,它的主要阐释工作是在黑格尔的语境中重构建立和应用规范的历史进程。布兰顿在马奎特大学大学所作的“阿奎纳讲座”(2019)中将黑格尔的历史理性称为“回忆理性”(recollective rationality)。cRobert Brandom,Heroism and Magnanimity:The Post-Modern Form of Self-Conscious Agency,Milwaukee: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2019,p.20.这个讲座集中了《信任的精神》的核心解读和关键结论。因为他注意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提出了“回忆”(Erinnerung,recollection),即被概念把握的历史(die begriffene Geschichte)。黑格尔写道:“目标、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为精神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加以回忆的道路,即回忆它们自身是怎样的和怎样完成它们的王国的组织的。”d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275 页。自我意识是如何“回忆”起自身的体系化历史的?黑格尔给出的提示是:“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a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122 页。接下来,黑格尔用主人和奴隶的“斗争”来描述两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他试图阐明,自我意识总是想实现两个相互对立的目标:既否认任何外在于它的东西,又必须通过他人的承认(Anerkennung,recognition)来实现自身。
自我意识的体系化历史必须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是我们理解这一点的基本文本。布兰顿的主要思路是在社会推论语境下改写主奴辩证法,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解读为“明确的交互权威中心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商过程”b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p.55.。他在《哲学中的理性》中给出了具体的改写方案:“只有当他人认为他负有责任时,某人才负有责任;只有当他人承认他的权威时,某人才行使权威。某人通过负责或行使权威来请求他人的承认。在这样做的同时,某人必须认识到,他人能够认为他负有责任或承认他的权威。为了获得这样的身份,某人必须被他人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他人负责。但也只有当承认他人的权威时,他人才能行使这种权威。”cRobert Brandom,Reason in Philosophy,p.70.布兰顿指出,这种“交互权威和责任”是黑格尔对康德的主要革新,即“为了坚持康德的洞见(心灵、意义和理性的本质特征是规范性),我们必须在社会性状态的基础上理解权威和责任这样的规范性状态。康德用理性活动来综合规范性的个体自我或作为统觉统一体的主体,黑格尔拓展了这一思路,用承认的实践来综合规范性的个体自我和他们组成的共同体”dIbid.,p.66.。根据这样的改写,超主体的“精神”(Geist)就变成了“在承认的过程中综合得到的社会实体”e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p.49.。
但布兰顿逐渐意识到,“主奴辩证法”中对“斗争”的强调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们对黑格尔的认识。为了克服这一点,他在《信任的精神》中着重解读了黑格尔在探讨道德时用到的两个“寓言”。这两个寓言给我们的启示合在一起呈现了黑格尔的完整洞见。
黑格尔的第一个寓言是英雄和仆人:“谚语说,‘侍仆眼中无英雄’;但这并不是因为侍仆所服侍的那个人不是英雄,而是因为服侍英雄的那个人只是侍仆,当英雄同他的侍仆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作为一位英雄而是作为一个要吃饭、要喝水、要穿衣服的人,总而言之,英雄在他的侍仆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乃是他的私人需求和私人表象的个别性。同样,在判断意识看来,没有任何行为它不能从中找出个人的个别性方面以与行为的普遍性方面相对立,不能以道德的侍仆身份来看待行为者。”a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172 页。布兰顿指出,黑格尔的精神包含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两个维度,对应于规范语汇中的语汇,前者是规范态度,后者是规范身份。布兰顿认为,前现代传统强调“规范身份依赖于规范态度”(status-dependence of normative attitudes),而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传统则强调“规范态度依赖于规范身份”(attitude-dependence of normative statuses)。英雄和仆人的寓言让我们认识到,“规范态度依赖于规范身份”的启蒙方案是可质疑的,不仅如此,处在这一方案下的理性行动者的“英雄主义”(heroism)最终会遭遇悲剧的命运。不同于这两个方案,黑格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推进到“精神的第三个时代”。在黑格尔式的伦理生活中,规范态度和规范身份是相互依赖的,一方面,规范身份是由规范态度建立的,而另一方面,规范身份又为评估规范态度的正确性提供了标准。
黑格尔的第二个寓言是恶的意识和“硬心肠”的道德判断意识。恶的意识向道德判断意识“坦白招认”:“我就是这个样子”,但后者却“没有在回答中作出这同样的招认”,而是 “维护它自己而抛弃它与对方的连续性”,“竟而摆出‘坚贞不屈’的品格那样的桀骜倔强和决不迁就别人而矜持自负的缄默寡言以对抗别人的坦白认错”。b同上书,第173 页。但道德判断意识最终选择宽恕恶的意识,通过这种宽恕,两种意识最终达成和解。布兰顿在这个寓言中找到了可以被转译为基本语义态度(semantic attitudes)的基本语汇:忏悔(Geständnis,confession)、宽恕(Verzeihung,forgiveness)和信任(Vertrauen,trus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理性的回忆过程被布兰顿称为“宽大回忆”(magnanimous recollection),黑格尔的逻辑表达主义也最终落脚于信任的精神。在黑格尔那里,信任被用于描述不同于启蒙的“纯粹识见”的另一种“识见”:“当我信任一个人时,我所信任的这个人对他自己的确信或确定性,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确信或确定性;我从它身上认识到我的为我存在,我认识到,他承认我的为我存在并且我的为我存在就是他的目的和本质但是信任就是信仰,因为信仰的意识是把自己直接关联着它的对象的,因而也就直观到:它与它的对象是合而为一的,它就在它的对象之中。”c同上书,第87—88 页。黑格尔的最终结构是“我就是出现于知道自己是纯粹知识的那些自我之间的上帝”,布兰顿则更强调这一结构在宗教共同体中的运用,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就是既承认被信任者作出宽恕的权威,又唤起他们这样做的责任”dRobert Brandom,A Spirit of Trust,p.621.。
布兰顿指出,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寓言给我们的启示——规范态度和规范身份的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忏悔、宽恕和信任来重构建立和应用规范的历史——结合起来,就不仅能用“新的认知和理论形式”来理解自我意识,还能用“新的宽大的实践形式”来理解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者。aRobert Brandom,A Spirit of Trust,p.31.他在《信任的精神》中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重维度的“语义学”,他把这种语义学称为“实用主义语义学”(pragmatist semantics)。b《信任的精神》原来的副标题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个实用主义语义学解读”,后在出版时改为“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个解读”,但该书的导论部分仍以前者为题。布兰顿指出,这是一种“带有教化意图的语义学”,也就是说,“概念内容在我们的推论活动中对我们作出规范性的约束,理解这些概念内容的性质就是教育和促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在精神的规范空间中,以后现代的信任形式生活、行动和存在的宽大的人。黑格尔的实用主义、社会—历史语义学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理想的建立规范的回忆和承认实践中承诺了什么,即隐含在我们言行中的对实践性宽大的承诺”cRobert Brandom,A Spirit of Trust,p.32.。
五、总结性评估
在《实用主义的诸视角》中,布兰顿试图通过一条“语言实用主义”(linguistic pragmatism)的整体性思路来同时把握逻辑表达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个维度。他指出,关联语义和语用有两条主要思路:第一条思路是方法论实用主义,即将意义、外延、内容或其他语义解释与语言表达联系起来,其目的在于制定规范的使用规则,从而使表达清晰。第二条思路是语义实用主义,即解释表达的使用者参与了何种实践,他们如何受规则控制,又是如何协商意义的。布兰顿指出,这两条思路的区分实质是观察语汇与理论语汇的区分,它们是语言实用主义的两个面相:“方法论实用主义者试图通过与表达相关的内容(语义)去解释使用表达的实践(实用主义);而语义实用主义则试图通过使用表达的实践去解释与表达相关的内容。”dRobert 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and Contempo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62—63.我们可以通过以上两部分的讨论看到,黑格尔为这一整体构想的两个维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们还可以看到,布兰顿在对黑格尔作出了实质性的借鉴时并没有将黑格尔的理论资源作为可供对勘的理论样本,而是将它们作为自身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我们要就布兰顿对黑格尔的借鉴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估。
首先是方法论层面的借鉴。一方面,布兰顿在借鉴黑格尔时明确采纳了后者的整体主义路径。他在《阐明理由》(2000)中明确区分了从下到上(bottom-up)和从上到下(top-down)的语义解释。前者的代表是“形式语义学”,它的任务是“从下到上地解释如何将语义相关的某个东西——假定它们已经被分配给了简单的表达式——系统地分配给复杂的表达式”,而后者则“从概念的使用开始,一个人就概念所做的,是将它们运用于判断和行动”。布兰顿指出,这两种语义解释路径实际就是语义原子主义和语义整体主义,“形式语义学传统一直是坚定的原子主义式的:将语义解释者分配给一个要素(比如专名)可独立于将语义解释者分配给任何其他要素(比如谓词或其他专名)而被理解”,而“推论主义语义学是坚定的整体论的”。aRobert Brandom,Articulating Reaso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15.从大的视角来看,布兰顿的思路接续了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的整体主义转向。他不但认为黑格尔的方法是整体论的典型代表,还认为肇始于奎因和塞拉斯的语义整体论思路是从黑格尔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核心线索。b布兰顿:《在理由空间之内:推论主义、规范实用主义和元语言表达主义》,孙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49 页。
但另一方面,布兰顿在采纳整体主义路径的同时又明确拒绝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倾向。泰勒区分了黑格尔的本体论辩证法(ontological dialectics)和历史辩证法(historical dialectics)。他指出,“本体论的辩证法从一个得到认识的目的或标准开始。其最初的任务在于表明,当下的客体将依据对于一个目的的认识而被理解”,而历史辩证法而不然,因为“在历史全部展开之前,我们按假定并不认识展开在我们面前的目的”。基于此,泰勒建议我们区分出两种方法:“严格的辩证法”和“解释性的或解释学的辩证法”。cCharles Taylor,Hegel,p.218.泰勒:《黑格尔》,第332—333 页。我们姑且不论泰勒的这一区分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是否成立,至少就布兰顿的而言,他所探讨的逻辑表达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应该都是在“解释性的或解释学的辩证法”的视角下展开的。出于一种黑格尔式的确信,布兰顿认为能够使之清晰的东西一定会终将得到阐明,并且这个结论一定处于理论历程的终点而非起点。但不同于黑格尔,布兰顿并不认为这个在“我们”语汇中实现的“解释平衡”是让全体具有意义的“绝对知识”。
其次是本体论层面的借鉴。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布兰顿提炼了黑格尔思想中的逻辑表达主义,但他并不关心后者的逻辑本体论或泛逻辑主义(pan-logicism),即将逻辑范畴视为实在的有机构成,将逻辑运作视为实在本身的动态展开。黑格尔研究中的一个争论是,他的形而上学是绝对精神学说还是逻辑学。我们看到,布兰顿既没有涉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也拒绝对后者的逻辑学作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解。他试图用黑格尔的逻辑观来克服康德对形式和内容作出的二分,但是又主动规避了黑格尔的本体论维度。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布兰顿本人所指出的,他并没有忽视黑格尔的本体论维度,只不过他的思想处在克里普克提出的“模态革命”之后,即他只能在语义的层面上探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aBernd Prien &David Schweikard(eds.),Robert Brandom:Analytic Pragmatist,p.179.其次,在布兰顿看来,整合了本体论维度之后的黑格尔体系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不同于黑格尔,布兰顿并不认为存在“一组最终的逻辑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是“本体论寂静主义者”,他并不认为有任何一种语汇享有其他语汇所没有的特权。bIbid.,p.182.
但是,正如雷丁(Paul Redding)所指出的,在早期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更接近从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的路径,而不是罗素和摩尔的路径,而这一路径正是麦克道尔和布兰顿的思路。要而言之,黑格尔“既不是像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所做的那样从关于‘存在’的假设中推出逻辑范畴,也不是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篇’中所做的那样从关于可知对象的断言的逻辑结构中推出‘存在’的结构。相反,‘存在’的结构在我们对特殊‘存在物’的谈论中展现自身,这里的‘逻辑结构’包含了我们的谈论所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中介了存在物之间的推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在“逻辑或语义的层面上工作的”。cPaul Redding,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32.而黑格尔的经典解读者考夫曼也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范畴的分析代替了思辨形而上学。他赋予形而上学以新的意义和内容,这些意义和内容在一些20 世纪最好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保留”dWalter Kaufmann,Hegel:Reinterpretation,Texts,and Commentary,Garden City:Doubleday,1965,p.196.。
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会看到布兰顿所作的工作并不是拒斥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是试图将黑格尔的“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ie)和语义层面的形而上学工作剥离开来。事实上,德语和英语学界的一些晚近研究试图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探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和布兰顿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亲缘性。eCf.Klaus Düsing,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Bonn:Bouvier,1995;Anton F.Koch,Die Evolution des logischen Raumes,Tübingen:Mohr Siebeck,2014;James Kreines,Reason in the World:Hegel’s Metaphysics and Its Philosophical Appea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Robert Pippin,Hegel’s Realm of Shadows:Logic as Metaphysics in The Science of Logi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语义层面的形而上学工作是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这条思路并没有因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纲领而被取消。奎因和克里普克等人的理论方案表明,我们仍然有理由站在语义层面上谈论“何物存在”的问题。现在,这条思路在布兰顿的推论语义学和逻辑表达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由于黑格尔逻辑的极端特殊性,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兼容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等待布兰顿和他的两个学生赫洛比(Ulf Hlobil)和卡普兰(Dan Kaplan)合写的《后果逻辑》(Logics of Consequences)出版后才能作出评估。
概而观之,无论是在方法论层面还是在本体论层面,布兰顿都对黑格尔作了契合分析语境的剪裁。在这种剪裁中,不存在任何“还原”黑格尔的诉求,也没有将黑格尔的思想再次体系化的冲动,更多的是在黑格尔的帮助下阐明自己的理论。布兰顿指出,我们可以“在不作出体系化断言的情况下理解黑格尔的承诺或洞见,并由此看到这些承诺或洞见事实上既不要求也不导致这种体系化”aKarl Ameriks &Jürgen Stolzenberg(eds.),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German Idealism 3,p.133.。
匹兹堡学派对黑格尔的解读和借鉴虽然已经逐渐进入了众多哲学家的视野,但这些思想的汇流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消化和沉淀,因而仍是一个尚待展开的思想史事件。比如,专治黑格尔法哲学的科维纲(Jean-François Kervégan)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匹兹堡学派的哲学家“抓住了黑格尔学说(诚然以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此方式对欧洲传统的哲学的史学家而言很成问题),甚至专注了黑格尔学说中表面看来最为可疑的东西,即他的观念论,目的是尝试着在分析的大陆本身之中使一些新的后维特根斯坦问题,后奎因问题,或新实用主义问题涌现出来”。科维纲还指出,这些企图试图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区分出“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代价是人们质疑这种做法使黑格尔的思想的一致性遭受一种任意的暴力”。b科维纲:《现实与理性: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年版,第4—5 页。无论如何,从他自身的理论语境出发,布兰顿认为自己抓住了康德和黑格尔思想中的一些“活的东西”,而在不同理论语境中的其他解读者看来,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不成立的,甚至是一种误读。但这些理论的互动不仅展现了德国观念论的生命力,也呈现了分析哲学的诸种面向,更让我们看到了融合这两个哲学传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