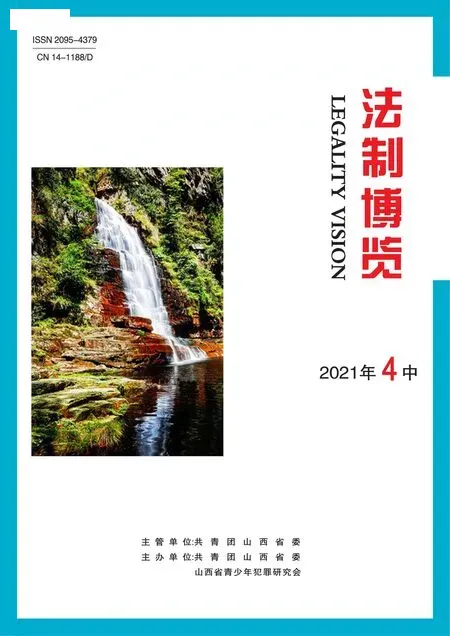吸收犯的吸收关系
乔 菊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吸收犯是我国刑法罪数形态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关于吸收犯,我国刑法没有具体规定,也缺少相关司法解释的说明,只存在于理论研究方面,但是在学术界关于吸收犯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认识。通过研究刑法专著以及相关的论文,发现目前关于吸收犯的吸收关系的认定有较大的争议,存在不同的观点,这样使得吸收关系的内容非常地混杂。本文从通过比较不同学说、了解不同学说之间的差别,从而得出吸收关系成立与否是指不同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伴随关系或者交叉关系。
一、不同学说的争议
吸收犯的研究内容复杂且标准不一,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吸收关系的认定有着很大的关系。关于吸收关系的认定,学术界有以下几种学说:
(一)社会观念或法条条文说
这种学说认为,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吸收关系,应该以社会的一般观念或者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进行判断。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来判断,主要是说根据犯罪性质,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观念,一罪是他罪的必要方法或必然结果。例如盗窃枪支后行为人自己私藏,私藏是盗窃枪支的必然后果,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吸收关系。根据法条的内容来判断,是指依据法律规定,一罪能否被其他罪包含或数个罪被其中一个罪所吸收。顾肖荣教授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不同罪之间要成立吸收犯,必须要依据一般观念和法律条文的内容”[1]来进行判断。
(二)犯罪构成依附说
主张这一学说的学者认为不同的犯罪构成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是吸收关系,但是对于依附关系又有不同的看法。黄京平老师认为“行为人实施的数个不同的危害行为,只有其犯罪构成之间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使得其中一个行为丧失独立性,才能构成吸收关系,被依附的犯罪行为成为定罪处罚的依据。”[2]陈兴良教授认为“任何行为之间的吸收均为吸收犯的吸收关系,并且在强调一行为拥有独立性的同时,强调另一行为没有独立性”。[3]
(三)连续实施说
该学说认为实施的其中数行为和其他的行为连续实施才能构成吸收犯。此时,“实施的其中数行为因为连续实施而失去独立性。”[4]
(四)紧密联系说
此学说认为,不同的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构成吸收关系,是由于行为人在实施这一系列行为时,这些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行为之间存在的联系构成吸收犯的吸收关系,其中一行为是其他行为的必然手段和必要结果。张明楷教授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为一行为是他行为的必经阶段和当然结果。”[5]
(五)相互包含说
持此种观点学者对于何为“包含”的认识又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包含应为一行为包含其他行为,其他行为不再单独定罪。[6]有的学者认为相互包含是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包含,即“一个要件吸收其他的要件,其他要件不法性、有责性均被该行为所吸收”。[7]
(六)主观判断说
这一学说认为,判断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是不是成立吸收犯,“应该从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来进行判断,若存在包含关系则为吸收犯,否则就不成立吸收犯。”[8]
二、本文分析
第一种观点承认了不同犯罪行为之间的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是值得肯定的,表明了吸收关系的客观构成,依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来判断,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没有明确的标准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产生不公正的现象。犯罪行为有四个构成要件,在依据法律条文进行判断的时候,满足哪几个要件就成立吸收关系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在处理不当时,还会导致吸收犯与牵连犯的界限不清,也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观点在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了判断,但是,成立吸收犯的前提是具有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此时成立吸收关系需要其中的行为丧失独立性,这本身就否认了犯罪行为的独立性,这样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这一说法主要考虑的情形是同一犯罪的重度行为吸收轻度行为,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形,轻度行为就不存在了,也就不符合吸收犯的成立前提,即存在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所以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为的连续性是吸收关系成立的条件,但是如果以连续性作为吸收关系成立与否的标准,会导致吸收犯与连续犯之间产生混淆。由于连续性使得其中的数行为失去独立性,也就不存在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了。
第四种观点坚持要成立吸收犯的犯罪行为必须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虽然这一学说指出了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联系才有可能构成吸收犯,但是这样界定必定会导致不能正确区分吸收关系和连续关系,从而导致吸收犯和牵连犯之间界限不清。
第五种观点认为要成立吸收犯,必然是一个行为包含另一行为或者是一个构成要件包含另一个构成要件。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当行为或者是构成要件被其他行为或构成要件包含之后,这个行为或者构成要件就不存在了,在评价时就只评价另一行为或要件,这样又与成立吸收犯的前提相冲突,不存在数个独立的行为,而只有一个行为。
第六种观点认同了由于原因与结果、手段与后果的关系存在,导致吸收关系的成立。但是这一学说是从主观方面对吸收关系进行把握。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进行判断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会使我们陷入主观主义,不利于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的观点都是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对吸收关系进行了阐释,并不全面,因此在研究时,应该吸收其中的正确的部分,并加以补充、改正,才能更好地对吸收关系进行论述。
笔者认为,吸收关系是否成立,要看吸收关系能否在成立吸收犯的情形中得到充分的论证,最终以裁判的一罪论处。“吸收关系成立与否是指不同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伴随关系或者交叉关系。”[9]伴随关系是指不同的危害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情况是有规律的,相伴随发生的。所谓交叉关系是指不同的危害行为发生时存在某些共同的危害行为要素。这些共同的要素不是由于法条竞合而产生的,而是行为在发生时就已经存在。伴随关系或交叉关系的判断,需要对不同的危害行为的要素进行比较,通过对比,发现不同的危害行为之间存在的交叉要素或者一种危害行为所伴随的相应的危害要素,从而可以判断不同危害行为是否存在吸收关系,进而为成立吸收犯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白某故意杀人、强奸案”中,白某对被害人胡某进行强奸时,因胡某正处于经期及白某的生理原因未能得逞。通常在强奸行为成立时,伴随着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这是有规律的一种伴随关系,强奸行为中必然包含着强制猥亵的行为要素,所以在判断白某的行为时,虽然白某强奸未遂,但是该行为必然存在强制猥亵胡某的行为,此时通过吸收关系的理论,强制猥亵行为不再单独评价,仅以强奸罪未遂定罪。
三、结语
吸收犯是刑法罪数论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的刑法学界对于它的研究并没有非常深入,所以在罪数论这一部分还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地带。吸收关系作为吸收犯的组成部分,对于吸收犯如何界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比较不同的危害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交叉关系或伴随关系,进而确定不同危害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吸收关系。这对于我们认知吸收犯的理论有深刻的意义,对于深入研究刑法罪数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