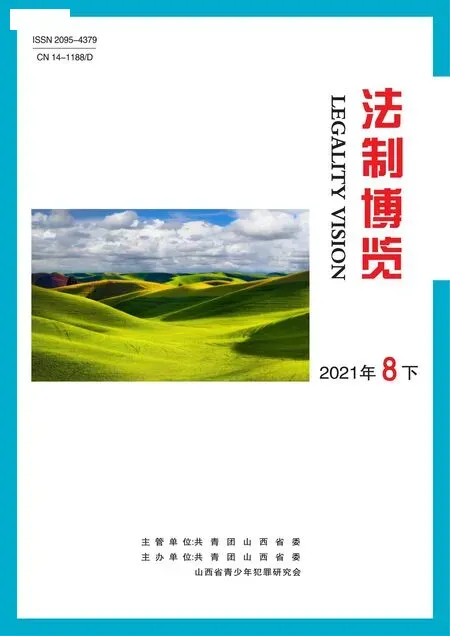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解释论
张丰荣
(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 716000)
一、通过比较法对国外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分析
悬赏广告的存在由来已久,不管是国内国外,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悬赏广告的事件发生。有关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民法学者都有研究,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对悬赏广告的法律定性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单方法律行为说,二是合同说。通过对不同国家悬赏广告性质的比较分析,更利于在《民法典》出台后对我国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解释。
(一)《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第九节第六百五十七条对悬赏广告做了专门规定,通过“有约束力的约定”对悬赏广告作了解释。具体规定:“通过公开地通告,对于完成了某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悬赏的人,负有向完成此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在完成该行为时,并未考虑到悬赏广告的,亦同。”《德国民法典》对悬赏广告的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民法更多对完成特定行为人的利益保护,这也是单方法律行为的体现,悬赏人只要做出了相应的悬赏广告,就受其约束,行为人只要完成了特定行为,实现了悬赏广告的要求,不管事先是否知情悬赏广告的存在,都拥有了报酬请求权可以向悬赏人请求支付报酬。
(二)《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对悬赏广告规定在第二章契约之下,在第一目契约的成立中第五百二十九条悬赏广告,第五百三十条悬赏广告的撤回,第五百三十一条悬赏报酬的受领权人,第五百三十二条优等悬赏广告这几条相关法律条文对悬赏广告进行详尽规定。其中第五百二十九条对悬赏广告的规定为:“以广告声明对实施一定行为人给予一定报酬者,对完成该行为者,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同时,第五百三十条也规定了悬赏广告在一般情形下,都可以撤回。可见,《日本民法典》对悬赏广告的态度是“契约理论”,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出发,悬赏人有向行为人要求其完成悬赏广告内容的权利,同时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行为人有完成悬赏广告内容的义务,同时也有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权利;此外,悬赏广告可以撤销,这表明了悬赏广告的成立与否在于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了意思一致,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符合了契约理论的要求。
《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是关于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不同定性的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认定悬赏广告采用的是“单方法律行为说”;《日本民法典》对悬赏广告采用的是“合同说”。这两部法典对我国的《民法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有关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经废止,但是之前的立法思路和司法解释,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认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行为人在拾捡遗失物或者完成了悬赏广告的规定内容后,能够向权利人领取必要的支出费用和获得悬赏人承诺的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悬赏广告强调的是,悬赏人悬赏寻找丢失的物品,在获得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的内容后,就有向行为人履行奖励报酬的义务,从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方面同时对悬赏人进行了规定,有权利就有义务,与此相对的就是,行为人履行了自己寻找丢失的遗弃物的义务就有获得相应的奖励报酬的权利,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合同行为,双方当事人基于悬赏广告要求的内容事项,达成一致的合意后履行权利和承担义务,促使合同的成立与实现。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解释(二)对悬赏广告的规定是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悬赏广告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除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是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相关规定。由此可以看到,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对悬赏广告做了适用上的明确阐述,即悬赏人以公开方式申明,与特定的商业广告类似,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了要约,同时实施特定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完成了悬赏人要约的承诺之后,便具有了向悬赏人请求报酬的权利。这也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同的合意之后,有要约有承诺[1],并且悬赏广告有合同法定无效的情形除外,可以看到悬赏广告具备了合同成立的全部要求条件,且将悬赏广告规定在了合同法及合同法的相关适用条款中,可以看出最高法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对悬赏广告更多倾向于合同。
(三)《民法典》的规定
自2021年1月1日起,已施行的《民法典》从编排体例上和内容规定上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具有了更明确清晰的认识,在编排体例上,悬赏广告位于《民法典》合同编中的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下的第四百九十九条,这是立法者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明确,即悬赏广告的订立、生效都满足合同的要求规定,在合同编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因此,可以认为悬赏广告应该采取的是契约理论,其成立、效力、权利义务的履行以及违约责任都应当按照合同编的规定来进行,这是在体系上对悬赏广告进行的归类;其次在内容规定上,《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此项规定表达了“以公开方式声明”不局限于狭义上的“广告”,也就是说,采用口头、书面或者电子形式等方式都能够使悬赏广告成立,这与第四百六十九条合同订立的形式一样,《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同时,“完成特定行为”认定为要约的具体内容,“完成该行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即报酬请求权,与合同一方当事人一样,在完成约定的合同义务后,就享有请求对方进行对待给付的权利。因此,综上所述,《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九条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对悬赏广告作出了更加合理的法律定性,即悬赏广告属于一种合同形式,归属于合同编。[2]
若悬赏广告按照单方法律行为来定性,行为人根据悬赏广告的要求去履行义务,并没有完全按照悬赏广告的内容要求去实施,只完成一部分,或者履行效果并没有达到悬赏人心里的预期效果,此时悬赏人也要受到单方允诺之债的规制,并且还不能够将悬赏广告撤销,因为单方法律行为,如遗嘱的订立一样,有一方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并不需要得到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只要悬赏人发布了悬赏广告就受到悬赏广告的规制,没有可撤销的余地;这样就会不合理地增加了悬赏人的负担,对其提出了过高的义务和要求。而如果将悬赏广告定性成为合同,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合同的有效成立与实现,需要双方当事人都努力地完成自己的权利义务要求,否则,另一方当事人就能够提出抗辩,或者撤销合同。
三、悬赏广告的案例分析
我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了有关悬赏广告最新案例,笔者通过对近期的司法裁判文书观察比较,对悬赏广告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是如何定性适用的,进一步地分析。
四川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发布的刘某、广安市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本案通过二审判决对该案进行了定论。此项案例可以对悬赏广告一直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路径的思考,即发现悬赏广告之前就完成悬赏广告的特定行为,再去申报悬赏广告的奖励要求,当事人的诉请能否得到实现,悬赏广告是否能够有效成立。
案件事实:2020年1月22日,刘某、徐某夫妻二人作为房屋购买方与甲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姐姐刘某发现甲公司全民经纪人广告牌上载明“任何个人推荐客户至给公司并实际促成认购签约可获得4000~7000元/套推荐奖励”,当即询问甲公司的销售顾问,其销售顾问解释说,在签订合同前,按照甲公司内部流程规定,应该先备案,才会有介绍费,由于该份合同签订前,没有先备案,所以就没有介绍费。2020年5月29日,刘某夫妻二人再次到甲公司售楼部与其销售主管祝经理当面沟通,以相同理由拒绝支付介绍费。一审法院首先对该悬赏广告的性质进行认定,甲公司对外发布的全民经纪人奖励广告,内容“任何个人推荐客户至公司并实际促成认购签约可获得4000~7000元/套推荐奖励”具体明确,应当认定为要约,该要约应在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时合同才成立;该悬赏广告中取得报酬的前提是行为人完成中介行为,在甲公司的悬赏广告中应该体现为行为人向其推荐购房者,并实际促成其与购房者认购签约。刘某陈述到甲公司处为其胞弟购买房屋,在交纳订金并实际认购签约成功后,才发现全民经纪人悬赏广告,此时要约才到达受要约人,刘某的行为应当认定是为其胞弟购房做陪同并参谋或建议等行为,不能认定为其已接受了甲公司的要约推荐其胞弟作为购房者,并实际促成签约成功的中介行为。刘某在其胞弟认购签约成功而无中介行为的情况下,向甲公司主张推荐奖励,不符合受要约人先接受要约人的要约,后作出承诺合同才能成立的规定,故刘某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在二审法院中,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甲公司是否应当向刘某支付案涉全民经纪人奖励。本案中,刘某在其弟刘某夫妇到访甲公司之后,发现了案涉广告,进而向甲公司工作人员报备,拟完成该广告中的特定行为。但刘某未在其弟刘某夫妇初次到访甲公司之前完成报备,且刘某夫妇已经不满足广告中对新客户的认定标准,即使签订了正式的购房合同,亦不能认定刘某按照要约的内容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对甲公司的有效承诺,故刘某要求甲公司支付报酬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通过上述案例,房地产公司销售房屋对中介的悬赏广告,法院在裁判过程中,首先是对此类悬赏广告的法律特征认定,即向社会不特定人的要约;其次对行为人刘某完成特定行为后是否构成有效承诺进行判断,最后是否达成有效的合同。
四、关于我国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思考和建议
目前很多专家学者将悬赏广告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主要考虑对完成悬赏广告另一方当事人的保护,尤其是没有达到合同成立一方当事人的适格要求,比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在实践中,很少有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地完成悬赏广告所要求的内容,因为悬赏广告一般因特定事项,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了较高的注意、识别和执行能力的要求。在对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权利保护这一块,在完成特定的悬赏广告的内容后,可以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代其接受悬赏广告的奖励,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对奖励进行保管,以便奖励更好地安排与使用。最后,《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以及第一百四十五条已经做了具体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地从事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从法律层面上就对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做了应有的保护规定,所以不存在悬赏广告作为合同就不能很好地对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保障。
将悬赏广告解释为合同行为更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和对双方当事人权益的同等保障;不能够将义务和责任全都加到悬赏人的身上,应该对行为人也有一定的要求,即合同另一方当事人需要负有对等的义务;悬赏广告中的一方当事人向不特定当事人发出的要约行为,另一方当事人看到悬赏广告时,形成合意,积极地以自己的行为去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事项,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此时,双方受到合同的约束,对合同的实现均负有责任和义务。
五、结语
悬赏广告已经在普通百姓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法律制度层面对悬赏广告有着清晰准确的认定是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百姓对法律规范化的呼吁,民法从生活而来,也要到生活中去。对以往法律立法精神的理解,国内外民法的比较分析,再结合当下司法实践的具体做法和《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对悬赏广告具有合同属性法律性质的认定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