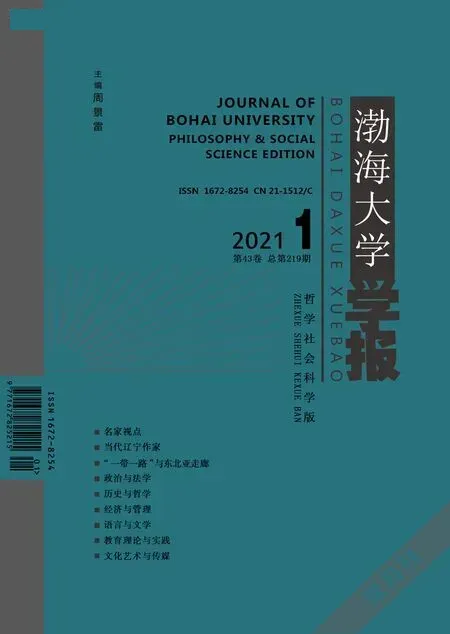王小波作品对知青文学的承载与溢出
——以《黄金时代》为例
张淑坤 刘广远(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 121013)
王小波生前曾多次表示,《黄金时代》是其最满意的作品。这篇小说自作者构思创作到1994年正式发表经历了十余年,这期间耐住了启蒙热浪、思想争鸣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繁荣,抵住了先锋性、商品化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化浮躁,作者对小说创作所追求的至精至诚的精神可见一斑。“他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1]正是这种先锋性,导致《黄金时代》在作者过世后才逐渐被接受。人们从艺术角度品评其创作风格时会关注他的知青身份,但又从不固守知青文学范畴,更多时候感慨于王小波独特的思考方式。本文以《黄金时代》为例,跨越时间与思想的束缚,在无名时期思考共名时代,用整体的视角考察王小波作品与知青文学的游离状态。
一、岁月的“留声机”
“知青”是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定称呼,是指在1968年至1978年间,有一定文化基础,从城市出来到农村或边疆参与劳动、支援建设的一群年轻人。王小波便是知青队伍中的一员,知青经历对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及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地久天长》《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一批受欢迎的作品都是站在知青这片土壤上进行的描摹与思考,《黄金时代》更是这一母题下的经典之作。
“我希望读者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味儿,只是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来读。让老插们把它作为一件经历过的事一样。”[2]王小波就是以这样简单、纯粹的词语来回顾历史,回望自己的青春。提及历史必然要有人的身影,人作为历史的承载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到历史事件当中。当“上山下乡”的号召发出后,无数的城市青年奔赴了乡村。王小波被派往云南山村参加劳动,并在那里体验、经历了自己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时光。《黄金时代》这篇小说虽说存有虚构成分,但是取材的时代背景是真实的,个人的经历也是具有现实基础的。王小波作为巨大的、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部件,由这部件的运转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机器”的存在与运转。作品又塑造了个性人物来剖开世界的一角,打破纸片上撰写的千篇一面,让历史事件立体而理性的存在,也让后人对那些承载历史的却也鲜活的富有自我的人物充满想象。“历史并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对历史多元的、丰富的阐释和解读,会产生更强大的文化力量和丰盈的思想资源”[3]。
韦洛克这样揭示文学本质:“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从生活中选择出来的东西。”[4]小说作为展现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在现实和虚构之间寻求文字所能承载的最大价值。《黄金时代》的故事中,知青们下乡插队,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参加劳动。这些内容被用作叙述背景与环境,既丰满了故事内容,又是对现实的场景描摹。“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剥落,而且都有倒钩。”[5]对残破医疗器械的描写推动了情节发展,引出下文与陈清扬的相遇,也满足了文本对当时贫穷、落后条件的构建。反之,文学作品的创作源于作者的曾有经历或者现有认知,一个小小的医疗器械其实是在映射当时的生活状况。另外,在作品的精神世界中,王小波虽然无意营造压抑、苦闷的氛围,喜欢用戏谑的语言与离经叛道的情节凸显文章张力,但是在故事大背景下,青年们被安排到边远的山村进行体力劳动,陌生的地缘、落后的生活条件,配合“破鞋”“军代表”等一类带有约束隐喻的词语,还是为文章的情感基调添加了一笔沉郁的色彩。当今文坛普遍认为,知青文学涵盖两类文学作品:一种是书写知青经历的作品,另一种是具有知青身份的人所创作的作品。王小波写《黄金时代》,既符合知青身份,又书写知青经历,那么这个作品必然担负着书写历史、承载知青文学的现实功用。
二、开放的私人“精神家园”
知青文学中传达的往往是压抑的苦闷、迷茫的刺痛和批判的反思。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了知青文学先声,向人们展示了时代下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卢新华的《伤痕》拉开知青文学繁荣的大幕,反思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经历及家庭悲剧。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繁盛的大背景下,众多知青题材的作品争相而出,释放长久压抑的情绪。即便是后知青时代的来临,在韩少功、王安忆、李洱等新的一批知青作家汇入对知青题材进行扩展的情况下,知青文学作品的氛围也难逃缺失与压抑。不过,王小波虽同处在这片土地,无法剥离时代赋予的氛围,但却没有陷入迷茫与沉闷,而是抬头放眼,着迷于在知青这片土地上寻找自我。
(一)“自由”打破禁忌
王小波作为第一批自由撰稿人,“自由”似乎可以成为这位作家的主题词,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放弃大学教师这个有稳定收入、有社会地位的工作的做法足以引常人惊叹。但评判自由行为不能仅停留在认识的表面,对其精神自由的解析才是根源认识。戴建华在文学评论《智者戏虐》中将王小波定义为“自由人”形象,孟繁华认为王小波是独特的“自由知识分子”,秦晖乐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释王小波形象,而王小波的爱人李银河作为最了解王小波的人,评价“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他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6]。从这些评论中足以让人感受出王小波身上的自由气息,并能作为依据,解释其特立独行的行为。
萨特的朴素自由理论说:“一个人是自由的,他总可以选择自己要干的事情。”[7]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朴实的向往,不过在实现过程中难免会遇有各种牵绊,使人意愿中的自由受到束缚。而王小波的自由思想中最为突出、最为热烈的表现就是打破禁忌并保有自我。生活中的王小波敢于突破常规,选择不被父亲看好的文学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放弃稳定的大学教师的工作。文学创作中,他更是将自由意愿进行到底,率先在主流文学领域使用私密化语言构建大众场景,打破传统的、含蓄的性写作与性接受模式。《黄金时代》中充斥着性爱场景描写、性动机分析,语言表达上直接、粗犷;描写性器官、性行为甚至是阉牛的场景时,暴露的用语倾向打破常规。对于习惯于传统语境的读者来说,扯掉观念中的“遮羞布”像经历一次“观念革命”。无视羞耻禁忌的表现形式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是对人们艺术接受能力的颠覆式的试探,是王小波不安守的内心世界的流露,仅凭此革新式的文学表现形式,他的思想世界就足以“惊艳”众人。
王二作为王小波的精神化身,承载着作者的意识。费尔巴哈说:“意志是不自由的,但它希望是自由的。”[8]由此我们推演,现世的作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追求自由时难免受困,那么意志中对理想自由的设想顺其自然的赋予了承载者王二。文本中虽从未标榜出王二的自由身份,但是无论行动还是思想,王二的自由程度都超越了现实。故事为王二设定了一次身体上的逃离,以人物疗养为借口进行了一次叙事空间的重构。在后山这个世外桃源中,王二体验了身为人的活着和寂寞、创造和探索。关于后山的片段描写充满了细致的人生体验,自由而畅快。自由思想对世俗观念发起的冲击,在文本中表现最直接的是婚恋关系,也可以说是无视当今社会现有的爱恋观。无论是二十年前的云南山村还是二十年后的饭店,王二与陈清扬都表现出自我意识,即便是要经历观念上的束缚与道德上的批判,也没有放弃各自心中对世界的理解、对自我的坚持。正如文中王二所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我们在干的事算不上罪孽。我们有伟大友谊,一起逃亡,一起出斗争差,过了二十年又见面,她当然要分开两腿让我趴进来。所以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更主要的是,她对这罪孽一无所知。”[5](51)这就是王小波思想中自由哲学的一角,坚持保有对于世界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甚至不惜抵抗世界,打破现有的禁忌,保留最真、最纯的个人精神世界。
(二)对小说的艺术追求
王小波书写知青文学,不是常规理解下的内心宣泄,也并不局限于历史事件的回放,可能仅是在人生经历中提取素材来进行小说创作。王小波多次表达过自己的人生意愿是“写小说”,他对写作有着偏执的热爱,即便他的父亲不让他学文科,想让他“学一种外行人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9]。但是几经辗转,王小波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每个天才的精神世界都是丰富的,他的眼里充满了对小说的热爱,只要小说能让他维持生活,他便愿意将天赋兑现,化为无尽的精神食粮匀予众生。
“简约的艺术在我眼中就成了一种必需。他要求,始终直入心脏。”[10]米兰·昆德拉给出了对于小说的艺术追求,简约且直达内心。对于小说艺术,王小波在对昆德拉的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又怀有个人理解——“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要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11]他们心中的艺术都是抽象的概念,却能感觉出强烈的自我意愿,让人开心可能就是王小波施展才能的动力。回到文本中,《黄金时代》所诉的背景环境是陌生、压抑的,但是在王小波荒诞的言语下竟显得轻松有趣。“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说,这样写缺少细节。后来我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地点是我在山上偷盖的草房......”[5](23)这是文本中描写王二写交代材料的场景及内容,一个人被冠以“破鞋”名号并写材料,这本应是极其愤懑的事情,不过在王小波独特的语言表述下,愤恨自动破解,虽然没有故意设定引人发笑的桥段,但是读者在私密的、暴露的语言刺激下,进行隐私窥探后所产生的惊诧与满足完全取代了应有的沉闷。在开心的尺度把握上见仁见智,未必能达成统一风格,但这样的语言模式贯穿全篇,确实能将隐含的沉郁基调一扫而光。
如果说创作力是小说的生命力,那么王小波的作品无疑具有非常广博的覆盖范围与强大生存能力。从初期作品《绿毛水怪》中神思奇事到《红拂夜奔》中的古代想象,再到《黑铁时代》的魔幻现实,王小波向人们展现了其无穷的创作力,他构造的精神世界是富有追求、有宣泄口的。文本中,从想要找陈清扬治病到想要和陈清扬“敦敦”伟大友谊,再到躲避山上隐居,无不体现出王二主观寻找、主观选择的意愿,面对生活种种境遇他从来不是被动承受,总是积极主动的思考来寻求结果,即便是世俗之中走投无路,他还在山上打造出了“世外桃源”。回到王小波作品的艺术特色上,具有自我主导生活的能力并有宣泄出口的文字表达,总会让读者大呼痛快。当然,除了纯粹的艺术创作给他带来的个人慰藉,他的创作还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正如他在《用一生来学习艺术》中所说到的,“比起科学,艺术更能让人幸福”[12]。
(三)践行自我人生
关于王小波的研究有这样一种现象,当研究者以王小波为研究主体时,很少局限于知青文学,甚至有时会直接跨过。那么什么样的魅力能超越直接的、典型的知青经历呢?我们觉得可以总结为一个智者的思考与表达。
“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13]王小波对于思考极为迷恋,并能从中获得人生乐趣。也正是因此,他的作品才会在蕴含哲思的同时又不乏天马行空的创作。王小波对于思考的追求,在杂文中表现较为直接也更为丰富。也正是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他杂文的成就远高于小说。与杂文的直接表达不同,王小波的思维在小说中的表现是狡黠的、富有逻辑的,看似荒谬却又着实,“要证明我们无辜,只要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之人”[5](6)。思考代替叙事话语,像一个原本赶路的人暂停下来思考前进的路线,又比如“问题不在于‘破鞋’好不好,而在于她根本不是‘破鞋’。就如一只猫不是一只狗一样。假如一只猫被人叫成一只狗它也会感到很不自在。”[5](4)在被分析“是不是‘破鞋’的问题时”,本该严肃的思考却混杂风趣的比喻,这种属于王小波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独特表述方式,既向人展现了思考又留有一丝玩味。这样怪僻的思考与表达似乎成了王小波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读者阅读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观感。
“我觉得人活着必须有尊严。尊严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 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这就是我说的尊严。”[14]在回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这样回答关于尊严的问题。“尊严”可以被认为是王小波人生的终极追求,其中包含着自我价值与他人认可两种精神维度,是在有限空间中探讨无限自我的践行,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怀有浪漫主义的精神追求。王小波的自我价值在选择的权利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中,他跳出传统观念,选择文学。作品中,他敢于表露喜欢,并去追求“革命时期”的爱情;敢于挑战代表权力阶层的军代表,这种理想主义与挑战精神就是王小波的思想质地。另外,在故事中,求证清白、演绎“破鞋”、敦“伟大的友谊”、写交代材料等情节的刻画,无非就是王二和陈清扬求真、求理、求认可的过程。这些精神上的寻求与王小波的价值观中的“尊严”相吻合,只不过小说中的尊严是集体的,是所有身处凡世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们共同的寻找。
综上所述,时代赋予的共性是众人必然承载的,王小波身为一名知青,与每一个知青一样,经历又容纳,把时代的印记深深地融入骨血之中;与每一个知青作家一样,观察又反馈,将历史的片段转换成文学艺术记载流传。时遇所致的个性又是个人魅力所在,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善思、奇趣、特立独行,精神上的丰沛让他创作出不局限于时代的作品,思维上的超越让他的作品构建出共性和个性共存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