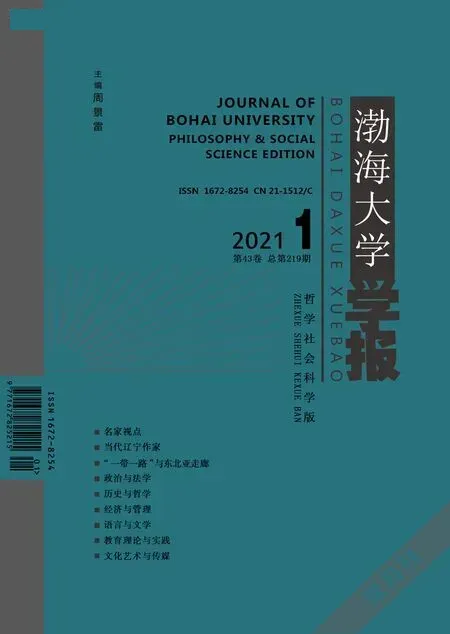童真时代的抒写与自我情感的表露
——对话儿童诗人王立春
林 喦 王立春(.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锦州 03;.辽宁文学院,辽宁 沈阳 003)
“童心”“童真”和“童趣”,这是我们对儿童文学最初的理解。而儿童诗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儿童的视角将纷繁的世界与丰富的内心情感展现于众的,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拓展诗歌的叙事张力,使得诗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诗人王立春一直坚守着儿童诗歌的创作,如果把儿童诗分为以童趣见长和以抒情见长两类,那么,儿童诗人王立春的诗作是游走在两者之间的。王立春身上萦绕着独特的诗歌气质,她有意或无意地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体现着一种童年的审美之光。她的诗歌作品总是将读者带入一条美好童真而又情感丰沛的诗路之中,诗人时而游走于记忆的世界之中,通过幻化的各种“生灵”与读者相通;时而又回归现实的场域,如老者一般抒发内心的情感或寄托期冀。在王立春的诗歌世界里,无论是诗歌的意象还是诗歌的语言;或是时空的表达,都浸润着童年的印痕。“老菜园子”“白云”“风”“雪”“星星”,一个个具有童真的意象,以孩子的视角营造着曼妙的乡土世界。带有东北色彩的土窗,其影子印在炕上变为格子纸,以菜园草木为笔,蓝天、白云为伴,可谓童真童趣一览无余。孩子眼里连绵的雪山、整齐的菜地、清冽的垄沟、脚下的菜香……这一切都为我们展现着独具特色的北方之美。这种儿童视角下的意象群给我们以特殊的诗美体验,诗人用这种儿童独特的感知思维方式进行着艺术表达。
王立春先后出版了《骑扁马的扁人》《乡下老鼠》《写给老菜园子的信》《贪吃的月光》《跟在李白身后》《梦的门》等儿童诗集,诗篇近400首,这些诗歌丰富了儿童文学,也为儿童诗歌增添了一道璀璨之光。王立春的每首诗歌都是有灵魂的,她并不是简单地将童趣、童事建构于诗歌之中,而是在每首诗歌中都呈现出一种灵魂的纯真,诗人诉说着一切,抒发着内在的情感。王立春的儿童诗是具有个性魅力的,更是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的。在儿童诗歌创作中,她的诗歌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与分量。
林 喦:我们大家都熟悉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就已见端倪,当时“儿童本位”的思想以及五四期间提出的一系列儿童问题更加促进了作家对儿童的关注。冰心、茅盾等作家除了创作成人读者所接受的文学作品外,同时他们也都肩负起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专职的儿童文学作家纷纷涌现并进行大量创作,儿童诗歌创作也在其列。面对当今“儿童文学热”的现象,您是如何看待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或者说结合您的创作来阐释下儿童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王立春:我认为儿童文学就是适合孩子各个年龄段阅读的文学作品。因为孩子的年龄段不同,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不同,内容和形式都不同。儿童文学所涵盖的年龄段应该在3 岁到18岁之间,包括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和青春文学,每个年龄段需要的文学作品都不尽相同。儿童文学是渐次成长和不断转变的文学。离开儿童的年龄来谈儿童文学是不准确的,是泛泛的。越小的孩子需要的越要有趣好玩,越趋向于儿童性,越大的孩子越要有故事性、抒情性,再大一些的更需要哲理性、思想性,也就是说越要具备文学性或者诗性。儿童性和诗性流淌在童年成长的两端,随着儿童的成长渐弱渐强。儿童本位这个提法应该更多地倾注在小学中年级阶段,比如2—4年级,也就是童年时代,这是更多作家的作品指向。作品对位越准确,作品的温度和质感才越强,也就越被读者所认可。比如,图画书就是给尚不识字的幼儿的,插画书就是给小学低年级孩子的,而文字书写就是给高年级以上的孩子的。因为读者的兴趣点不同,我们作家的写作定位也要有所不同。
在题材上,儿童文学也包括了文学的所有样式:儿童小说、儿童诗歌、儿童散文、儿童戏剧,且比成人文学又多了专属的两项:童话和幼儿文学。这些丰富的题材使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自成体系。这个世界有分工、有层次、有递进、有承接、有高度。
当然定义儿童文学还有更多的范畴。比如从广义来讲,它有诗性和童趣的高度统一;从狭义来讲,它有浅语性、故事性、教育性、知识性等等特质。
林 喦:作家怎样完成自己的儿童文学书写?
王立春:写作者把自己的文学观转化为儿童所能接受的文字,需要有一种深入浅出的文学表达能力,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文学观、艺术观、教育观用浅显易懂的叙述渗透到孩子成长的每个年龄段,用孩子看得懂并感到有兴趣的语言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向儿童本位倾斜的一种技能或技巧。
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应该是作家对世界深刻观照和对儿童世界精细探索的综合体验和表达。他应该是把深刻的思想或生活的哲理隐藏在浅白简练有趣的文字之下,孩子能够感兴趣地、畅快地通过文字的通道抵达作家的世界。那种浅白是儿童乐此不疲的,而那些审美的探底是作家想要真正给孩子的。或许多年之后,孩子还能够想起小时候阅读的作品来,也才能忽然体悟作品中蕴藏的美,得到一种审美的回味,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部好作品的品相。一个好作家,他也一定会为这种既浅显又深刻、既有乐趣又有寓意的探索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当我们长大,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小时候阅读安徒生和王尔德童话的体验,而那种回味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作品的感悟是那么的不同。一百个人有一百种不同。多年之后,当我们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起皇帝的新装,想起那个快乐王子,还依然为它蕴含在童话故事中那种印记,涌起心疼、快乐、悲伤等诸多的情绪。再如,日本作家佐野洋子《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小时候看就是一个关于猫的热闹和奇妙的经历,而成为有经历的大人后,再读就是一种对爱与死的无限感慨和深度体察,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才是真正伟大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如果儿童文学有外延,那就是作品既是给儿童读的,又是给成人读的。安徒生、王尔德、佐野洋子及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就具有这样的审美价值。尽管安徒生在他的晚年一再地说,他的作品不是写给孩子的,但作品一旦脱离了作家,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已由不得作者。全世界的孩子都像饥饿的人遇见面包一样扑上来,不是孩子的也是孩子的了。
我在创作儿童诗的时候,时时把这种“外延”意识贯穿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努力追求着伟大作家的足迹,争取让自己的作品在具有儿童性、趣味性的同时,也一定具有文学性,让儿童和成人都能从不同的层面感受。那浮在上面的给孩子,那沉在底下的给成人或有一天长大的孩子。
我前期的作品是对童年的诗叙述。在《骑扁马的扁人》中有集中体现。我在诗中用了更多的孩子能接受的语言体系、童话语境,有故事,有情节,有节奏,有动感,还把幽默风趣好玩的语言加以夸张和放大,同时又把忧伤、疼痛,对生活的深刻体悟放进诗中。孩子不一定都能感觉到,但喜欢读就够了。当孩子有一天感觉到突然降临的情感的美,哪怕某一个审美瞬间让孩子记得,我也觉得写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品。
林 喦:诗歌是体现一个时代的,更是体现一个诗人的灵魂的。面对目前的文学创作场域,大家对诗歌的认知似乎缺少了应有的耐心与感悟的本领。但文学与时代总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话题,诗歌更是一种个人对时代的情感迸射,那么,你在创作儿童诗歌时又是如何表现时代以及抒发个人情感的?
王立春:诗人的思想应该超越时代,因为他看得见过去、现在和未来。诗歌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触角和探测器。如果把文学创作比做一场熔炼的话,那么情感应该是火焰,时代的各个场景应该是火焰熔炼的对象。被情感燃烧过的时代意象,会生出崭新的文学形象。
情感是向内的,而时代是向外的。情感越向内,它的热度越高、熔点越高,冶炼出的时代意象越个性、越有特色;而时代的意象越高远、越深长,由情感熔炼出来的文学形象,就越丰富越蕴藉。
白居易有“情根”一说,意思是说感情是生成诗歌的根。当我用诗歌回望童年,就是用纯真而热烈的情感把成长阶段的我呼唤出来。亲身经历的童年生活在感情的炙热熔炼之下生成了诗歌形象,那已不是原来的我,也不是原来的时代原件了。那是我独一无二的感受,也是我的时代、我的地域赋予我诗歌的最好的赋予。
我的童年成长在“文革”时期,成分为地主的母亲被分配到乡下,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是笼罩在一片阴影里的。妈妈是大地主,我是小地主。我写过一首诗,叫《小地主》,我说我是藏在农民庄稼地里的一棵隐着细叶子的地主草,当同学从远处把我呼做“小地主”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声声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身上。这种体验现在想起来还心悸。这是成长中回避不了的伤痛,当我把它写入作品中的时候,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一次次地心被揪疼。有了这种情感,写出来的作品不管好坏,我都觉得那是我内心中感情和时代最深刻的交融,无可替代,弥足珍贵。包括我写的《粗布衣裳》。爸爸给我买回几尺粗布来做过年的衣裳,丑丑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但爸爸说结实。衣裳穿了四季还新鲜如初,我终于明白,“为了不让窘迫的日子/露出肘弯/为了不让我的童年/摞满补丁/爸爸才买了这件/穿不破的粗布衣裳”。我记得有一次在家庭聚会时我兴奋地把这首诗读给爸爸听,读到一半我就哽住了,读不下去,妹妹只好接过去帮我读完。起初是向爸爸炫耀一种写出这首诗的得意,但读下去才发现,我那不知积攒了多久的委屈像堰塞湖一样泄了流……我爸爸当时一声没吭,作为一个父亲,他又是怎样的愧疚和心酸呢?我现在想起来还为自己那时的做法感到难过。
以上我说的是我诗歌中的过去时代。过去的很多诗我是以自我本位创作的。
说到现在,我试图更多的以孩子视角、儿童的本位去写作。我有一首诗叫《作业家》。孩子一天到晚做作业,“学玉米那样做算术/一直算到长出了胡子/一直算到头发灰白/还要像稗子/明知道结不出什么/但也要认真地又种又长/……我每天都在春种秋收/我的一天就是四季”。这种体验是我对我自己孩子没完没了的作业一种痛斥,也是当代所有孩子的成长之痛。当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这个世界又完全是儿童所能够呈现出来的样子。以儿童的本位体验儿童的情感,它应该是一种作家的责任心,代替儿童发出声音,向应试教育发起挑战,是一种呐喊和呼救。
当然,诗人更多的是望向未来,写出那些永恒的存在。我觉得这应该是诗人的未来观。他的人性观、宇宙观、自然观都应该在诗中体现,是面向未来的书写。我觉得在某种角度,孩子是预言家,他是定义这个世界的人。孩子用自己的目光和心灵解密世界,它区别于科学和实用主义的解释。当孩子来定义和体悟这个世界时,科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写了一首《鞋子的自白》。孩子的鞋子,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奔跑跳跃,抱着孩子胖乎乎的小脚丫,摇头晃脑四处跑,他不像大鞋子,挂着名牌,规规矩矩,而是翻着跟头踢小石子,上树荡秋千,拉着沙子满地跑,他会和路旁的小蜘蛛说话,嘴唇豁豁了也不哭,牙齿掉了也不喊疼,最后写“小孩的鞋子能让脚长大/大人的鞋子却让脚变老”。再比如说写到《星星钉子》,“为了使黑暗不至于/掉下来/砸到大地/星星钉子左一颗右一颗/钉满了天空”。还有一首《花儿一岁》:“……全世界的花儿都开了/全世界的花儿都一岁了/美丽的花儿啊/一岁/就是一辈子啊。”
这种对物事的定义,应该是儿童诗特有的品质。掌握了这样一种定义方式,或许对儿童诗的认知就会达到另一个高度。儿童诗是儿童对美的一刹那的凝视,是对世界永恒的观照。
林 喦:您在《看上去根深叶茂》中说道:“在这之前,我写过朦胧诗,是很‘朦胧’的那种,朦胧得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在写什么……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虽然浪费了许多时间,绕了许多弯路,终于在十年后再下笔时,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表达的艺术方式:写儿童诗。”可以看出,您之前有过写朦胧诗的经历,朦胧诗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诗歌热潮,朦胧诗影响了一代人,这种影响自然有时间的广度与深度。对您来说,十年沉积,跃然勃发,这里是否有朦胧诗对您的影响?那么,朦胧诗成为一个诗歌流派毋庸置疑,您觉得儿童诗具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意义呢?
王立春: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的,那个时候中国新诗已行进到朦胧诗时代。朦胧诗的诗人在那个时代是最多的,朦胧诗派以绝对优势占据着诗坛。那个时候,我在辽宁文学院上学,被分到了诗歌组。看大家都在写朦胧诗,我就学着一起写,写爱情诗。爱情诗和朦胧诗是双胞胎。故意把一个特别明白的情感,写得特别不明白,要有跳跃性,要有朦胧感,让大家尽量地看不懂看不透,仿佛只有这样才具备一种好诗的样子。写来写去,我觉得快把自己拽掉了。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获得了很好的诗感。这种创作体验,使我学会了深刻的思考,学会了语言的凝练,学会了跳跃的艺术,学会了偶然性到必然性的建构技巧。我的诗心得以丰盈,为以后创作儿童诗磨炼了一定的诗艺。
后来我停滞了写作十年。当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我学会了跟孩子伊伊呀呀的说话,我整天看着我的孩子像神一样的神情和发音,她做着神的事,说着神的话,我被她弄傻了,傻到许多次都如雷击电掣。我诗歌的潮水开始涌动,我预感一切将要开始。我执念很强地决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写。从朦胧诗跳脱开,我逐字逐句挑选那些浅白简练的文字,写自己用心血酝酿出的诗意。我在给一本杂志写的儿童诗创作谈中写道:我仿佛从厚重的茧壳里爬出来,飞成了轻盈的蝴蝶。说实话,这种转变的过程是痛苦的。毛虫能成为蝴蝶需要蜕变,而蜕变是疼痛,是牺牲。当我牺牲掉我诗歌中浓郁的叙述,回到素朴的童稚语境,我确实有些不甘心。但当一个柔软真实质感的自己在通透的诗歌中走出来,我的惊喜也随之而来了。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的体验。我与生俱来的性格里的痴傻、笨拙、愚钝、执拗,还有明朗、自在、清彻、透明都跑回到了诗里;每一个灵感上生出的小小嫩芽都恰如其分地镶嵌到了诗里。我觉得儿童诗于我,是一种随性赋形的崭新的艺术创造,从这里能抵达一种极致的快乐。这是我一直寻找的诗歌理想,我十年的寻找和等待是值得的。
再说说儿童诗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我觉得儿童诗本来就是新诗的一种,它区别于朦胧诗之后的那些诗歌流派,像一股清流独自流淌,流淌成自己的小溪、自己的江河,奔流向海。五四以来那些重要的、著名的诗人,他们的诗中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可以让儿童喜欢的,这些诗的文学品质是很高的。比如胡适、朱自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艾青等人的诗作。更重要的,诗人们显示了他们的童心,显示了孩子可以欣赏的趣味。这些诗虽然没有标出儿童诗,但却是很优秀的儿童诗。这一部分儿童诗应该在文学史上有它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后80年代初,儿童诗人们开始以群体的姿态出现了。比如柯岩、任溶溶、鲁兵、金波、圣野等等,他们的诗歌在中国儿童诗坛呈现出自己的艺术品相,各自独领风骚。儿童诗人群体发力的时候,它彻底摆脱了其他诗歌派别的束缚,浩荡而汪洋了。
林 喦:在您的儿童诗集里面,大部分诗歌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乡土气息,童年的回忆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之一。您在《我的斯卡布罗集市》中提到,11 岁的时候,您从辽西乡下搬到了城里,可以说乡村童年的生活给了您创作的灵感。有小说家曾经说过,小说的创作就是回忆,是对生活的回忆,是人生阅历的采撷。当然,这种回忆需要我们文学加工,通过想象的翅膀而使其跃然纸上。其实,成人作家将其童年回忆通过儿童视角来进行诗歌创作,面临的难题就是成人与小读者之间的沟通。一般成人写儿童总会以成人的主观情感进行表达,尽管一些作品直接写儿童及其生活,但总会有成人的影子,特别是对儿童内心的挖掘,成人与儿童的内心世界是不一致的。有些儿童诗是以儿童外在行为作为书写的主体,对于诗中的情感性则显得光芒暗淡。因此,诗人以儿童的感觉、儿童的情感为出发点,成为儿童诗能否被合理化规约的标准之一,我想对这一点您是认同的。那么,在进行儿童诗创作的时候,您是如何对这样一个难题进行处理的?也就是说,诗人记忆里的童年与儿童世界里的童年如何在诗歌中达到融通的?
王立春:很多成人作家也在为儿童写作,但却觉得他的叙述方式、他的儿童观,怎么也抵达不到儿童的内心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没有和儿童互换位置,如果能够完成和儿童的位置互换,或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比如当你化成一个儿童,你看世界就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展开了仰望的视角。顽皮和任性将主宰你的世界。你可能是奔跑着、倒立着、仰躺着、斜着、歪着、笑着、哭着来观望那个庞大的世界,你会每天都要问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不懂所以创造,因为没有所以想象。这样才是完全的、完整的儿童世界。会和我们模拟的、想象的儿童世界不一样。
这种互换,应该是作家主动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或诗人的过程。
最好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就像别林斯基说的那样:“儿童文学作家不是造就的,而是生就的。”顾城的诗天生就带着强烈的童话倾向,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孩子。回望我们的儿童诗人队伍,作品最受小读者欢迎的作家,一定是天生性格里就住着一个孩子的作家。另外,母性作家也带有对儿童天然的亲近感,比如像冰心的作品,傅天琳母亲视角的诗歌,都一样也为孩子喜欢。
当然,还有一种抵达儿童世界的方法,就是我们试着去找到和儿童心灵相通的一条桥梁。找到自己的心灵和儿童的心灵交接在一起的一个点,让我们的感觉顺利地抵达儿童的世界,把我们的善与美传导给那些纯良的心灵。
我觉得自己骨子里应该具备了一些好的儿童特质。我的好多作品就是用这样两种方式和读者进行交流的。互换的时候我的作品是儿童本位的,心灵相通的时候我是自我本位的。我试图把自己和儿童的世界做了一个搭建,才会有一种自己和他们完全一体的相融。我的一首诗《一条小河遇见另一条小河》似乎表达了我的这种感觉:一条小河和另一条小河/在桥下见面了/他们绕着圈/打量对方/用水话互致问候/哗哗击掌/再交换彼此的小鱼/然后勾着脖子/一起/向远方跑去。
所有的童年都是一致的,童年是一种生命的共性。作家的童年和孩子童年放在一个等高线上,就能把这两个童年变成一个童年。我们的笔只有伸到童年的深处,孩子才能和你感同身受。
林 喦:您的儿童诗除了那种童真纯净之美之外,爱是贯穿其中的。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著名作家冰心,冰心的文学作品中充满着爱,爱自然、爱母亲、爱孩子。在您的诗歌中,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样的内容。您通过独特的语言及意象、意境的营造,给予读者爱的洗涤。我想您的作品不仅是童趣的书写,更是深层次地抒发了自我的情感,表达着人间之爱。因而,您的作品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便成为自然的事情了。那么,作家冰心也好,其他的儿童作家也罢,他们是否对您有所影响,是谁成为您走上儿童诗写作道路的推动者?
王立春:一路阅读,一路创作。阅读是另一种创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先后遇到了泰戈尔、傅天琳、史蒂文森和特朗斯特朗姆等具有特殊气质的诗人。泰戈尔对印度风情丰富浓郁的描述给我强烈的震撼,而傅天琳的诗歌形象生动,充满了灵动意境。史蒂文森的风趣幽默,他对儿童的认同、全方位的儿童视角对我的触动很大。而特朗斯特朗姆的诗性是一种深沉的、多元的、丰盛的,一个诗人内在修成会在他那里得到映照。
至于那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国传统诗歌,陶潜、李白、苏东坡、杨万里、袁枚的诗歌,那种不求形似而求神似,那种追求简朴和晓畅,那种在广袤空间和时间里诗人的谦卑,那种在对生命宇宙中不断延续的直接领悟,以及对人之外和人之内的生命形式都以同样关切的领悟,都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分。
林 喦:纵观诗歌,我们可以看出,您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儿童诗歌创作现状,您的儿童诗歌除了具有表现多种题材的可能性,我觉得您在努力追求诗歌的独特的自我表达方式。或者说,您在努力寻找、建立属于自己的儿童诗风格,或者说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方向。在此,您能否谈谈对自己诗歌作品的文学史定位,以及未来的创作风格问题。
王立春:对自己诗歌史的定位,我觉得还是应该由读者和批评家来定位吧。我说不清楚,也没有办法定位。
一个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他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声音。如果他独具个性,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就应该在所执着追求的艺术领域,留下自己的痕迹。
对自己未来风格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可以说说。自从创作童诗以来,我写了一定数量的作品,两次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部分作品在质量上也得到了专家和小读者的认可。但是,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狭窄的通道,我不知道怎样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目前,我写的不多,但是我总能隐约感到有更宽阔的领域等着我。于是,我要做一种改变,改变自己的写法。除了写一些儿童长篇小说、儿童幻想小说,还出了一些散文集。但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朝向儿童诗的,在别的艺术技艺里我打磨的始终是儿童诗。我知道我从没离开过儿童诗,它以最强劲的半径吸附着我。一切都为更好的它做准备。最近,我暂停了一切创作,开始向低幼文学的领域走。有人说,不写幼儿文学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于是我把自己的笔触伸进了幼儿文学,试着用轻浅到泥土里的语言打磨自己的童诗感觉。我用自己惯用的快乐幽默的艺术表现,来进行童话诗创作。我写了一个系列的童话诗,把东北的风俗和民俗,情绪和情调都融到了里面。这是我之前一直想表达而未能表达的。我的性情里带着丰盈的满族调性,我所受的那些民谣童谣的熏陶,或许有更深广的挖掘空间。这是我更自在的精神领地,是我的独一无二。
我不会忘记向自己内心的探寻,越向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越大的格局。童诗叙事是向孩童及自我的更深的探索。我觉得这是一个儿童诗诗人的职责,是对一个读者、对自己负责的创作姿态。我应该尽到我的社会责任,担当起自己的担当。
林 喦:好一个担当起自己的担当,谢谢王老师,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