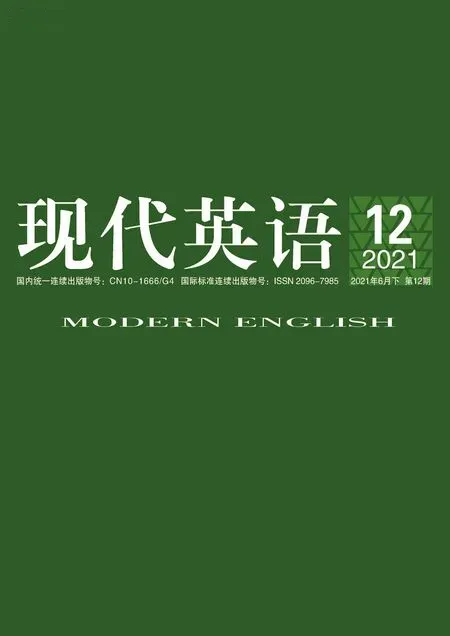基于苏珊·巴斯内特“种子移植”«诗经·采薇»第六章三译本分析
孙瑶 范晓彬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一、引言
诗歌能够反映深层文化,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体现了特定文化的本质。诗歌翻译是翻译界的难点之一,中西诗歌语言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翻译工作困难。著名的英国诗人雪莱认为:“把诗人的作品由一种语言移入另一种语言,就像把紫罗兰投到坩埚中以验明其色彩和香味必须由种子再次抽芽,否则不会开花——这都是巴别塔的诅咒惹的祸。”这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诗歌是不可译的。苏珊·巴斯内特认为“虽然诗不能从一种语言移入另一种语言,但它可以移植在新的土壤播种,长出新的植物。译者的任务必然是决定并找到那颗种子并进行移植”,这恰恰反映出诗歌的可译性。
«诗经»英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对其的英译研究相对薄弱。其相关研究虽对译界有相当大的贡献,但研究角度较窄,缺乏深入系统且多角度的研究。从“种子移植”进行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论文立足于苏珊·巴斯内特“种子移植”对«诗经·采薇»第六章许渊冲、杨宪益、Ezra Pound三译本进行分析,探讨诗歌翻译方法。
二、种子移植理论
苏珊·巴斯内特是国际知名翻译理论学者、比较文学家和诗人,她在翻译专著中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论”,提出翻译不只是语言活动,更值得关注的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文化,其实应该意识到文本自身就是文化。在著名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姆斯的理论指导下,巴斯内特提出“有机诗体”翻译法,即结合“内容为主”和“异域形式”翻译法,换而言之,就是译者以原文的语义材料为主,让文本塑造自身;译者所翻译的原文形式在目的语中不存在,译者自行其是,采用一种新的翻译形式。就是均衡地运用不同方法来取得整体效果。
研究“种子移植”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必然要先清楚“种子”到底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移植”。其实巴斯内特并没有明确指出“种子”究竟有何内涵。何庆机觉得种子“并非一个固定的可以界定的普遍的东西”。陈丕觉得“种子”主要表达一种“功能”或者“作用”。种种解释都表明诗歌翻译是要在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进行文化转移。诗歌就是一颗文学的种子,可以从源语文化土壤移植到目的语文化土壤,就像植物一样。那么译者要做的就是呵护种子,译者需要仔细了解种子的特性,考察周围的环境,从而进行移植培育,让诗歌的种子在目的语文化中开花结果。因此,她认为“译诗不是复制原文,而是在把握好诗歌内涵的基础上创造相似的文本”。巴斯内特认为“要翻译好诗歌,首先要智读原文,即用一种细致的解读过程充分考虑文本内及文本外各种特征”。诗歌翻译究其根本就是“拆散”和“重组”,将原始语言材料拆分,在目的语中进行语言符号的重新组合,这样的诗歌翻译才让原作生命得到延续。
三、«诗经»与«小雅·采薇»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311篇诗歌,反映周初至周晚期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其内容上分«风»«雅»«颂»。«雅»又分«小雅»«大雅»。«小雅·采薇»是其中一首四言诗,是戍族返乡诗,唱出戍边将士的艰辛和思归之情。全诗六章,每章八句。前五章着重写戍边生活的艰苦和强烈的思乡情绪以及久久未归家的原因。末章以抒情结束全诗,感人至深。下文从«采薇»最为有名的第六章对许渊冲、杨宪益、Ezra Pound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四、种子移植理论下三译本分析
中文诗以四言形式展现且极具韵律,叠字反复出现,渲染了气氛,使诗歌读来朗朗上口。
«小雅·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饥载渴。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许渊译本: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发展,特别是MOOC、网络课程如火如荼地建设,优质的网络课程资源大量涌现,网络课程为成人继续教育引入微课的混合教学模式提供了充分的优质的微课视频教学资源,这样促进了混合教学模式的多样化。笔者以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17会计1班为例。
When I left here,Willow shed tear.
I ca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Long, long the way, Hard, hard the day.
Hunger and thirst,Press me the worst.
My grief O'er flows,Who knows?Who knows?
许渊冲教授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互译工作,是全世界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他认为“这八行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集中最美丽的诗句”。“原诗富有意美,音美,形美”。整体来看,许译本读来韵律感强,每行四个音节,双行押韵,符合中文四言诗韵律,且 here,tear,now,bough, way, day, thirst, worst, flow, know 压尾韵,韵律为AABBCC。这正是巴斯内特移植形式特点。第三句long,long和hard,hard体现中文叠字之音韵感,long与hard的重复更加突出了道路的漫长且艰辛。内容上将“杨柳依依”译为“Willow shed tear”,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从“种子移植”角度看,许教授是进行了“种子”确认,对原文进行深入研读,了解其背景内涵。表面杨柳随风轻拂给人愉悦柔美之感,实际上纵观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文章诗词以及此篇诗歌背景,“杨柳”这一意象表惜别之情。将士出征杨柳都落泪,是内容上的移植创造,考虑了文本内外的各种特征。第二句中“雨雪霏霏”译为“bends the bough”, “bough”就指柳枝,虽中文并未提及,但英文此处进行了意象的增加,更体现了今昔对比,突出伤感情绪。许译本也完全体现了其诗歌翻译的“三美论”。
杨宪益译本:
When we left home,The willow were softly swaying.
Our road is a long one,And we thirsty and hungry.
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sorrow,But who knows our misery?
杨宪益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的翻译风格秉承忠实通顺,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异化与归化结合,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杨译本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句式与原文贴近,没有过多地进行再创造,句子长短错落有致,但音韵方面没有将中文朗朗上口的韵律移植到英文中,使得英文译文读起来缺少了原诗的韵味和节奏感。但是此译本相比较而言在内容和形式上最贴近原文。值得一提的是,杨译本将中文诗歌中的“我”译为“we”,相应地使用“our”这一复数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在主语上进行了深入解读,本诗并未指个人,而是借用“我”来指所有戍边将士,因此该译法是一种新的移植,更加突出了所有戍边将士对于战争的厌恶之感。
Ezra Pond译本:
Willows were green when we set out,
It's blowin'an'snowin'as we go.
Down this road, muddy and slow,
Hungry and thirsty and blue a doubt
(no one feels half of what we know.)
Pound是美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美国诗坛领袖。他是在理雅各之后第一个把«诗经»译成自由体诗的人。他认为译诗是诗歌创造性的问题。因此他的译本更接近于自由式翻译,有散文的风格,抛开中文原诗的格式进行了再创造。他将每两个短句译为一个句子,用“when”“as”两个时间状语进行时间上的补充。翻译“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时增加了“muddy and slow”,是对原文的文化内涵和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在译文中进行移植。虽然Pound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但也体现了中西方诗歌英译的差异,庞学专家肯纳在其专著«庞德时代»中曾说,Pound的译本与中国读者所知的«诗经»和汉学家所关注的«诗经»不尽相同,因为这是一部英语诗集。因此,Pound的译本是“种子移植”理论中对目标语文化的敏锐捕捉。他是从中国诗歌汲取营养,通过诗歌翻译为美国诗歌注入新鲜血液,符合巴斯内特“种子移植”包含的基本条件:“益智”与“怡情”。
五、结语
巴斯内特“种子移植”理论为诗歌翻译提供理论基础,她虽未给此理论下过明确定义,但通过她对于诗歌翻译的研究,证明了诗歌可译性。译者进行诗歌翻译时最重要的是深入了解“种子”内涵,在形式、内容、文化上进行移植再创造,让其在译入语土壤中结出果实。
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三位都是翻译大家并精通诗歌翻译,每个译作都有优点和独到之处,并考虑了译入语的文化因素,但译作也并非完美无瑕。总的来看,种子移植理论在诗歌翻译中很难对内容、形式及韵律同时进行指导,这也是种子移植理论在诗歌翻译方面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许译本在韵律和内容上移植较为成功并传达了深层内涵,值得译者学习借鉴。因此,只有译者深入透彻地了解源语言与译入语之后,才能将诗歌翻译提升到更高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