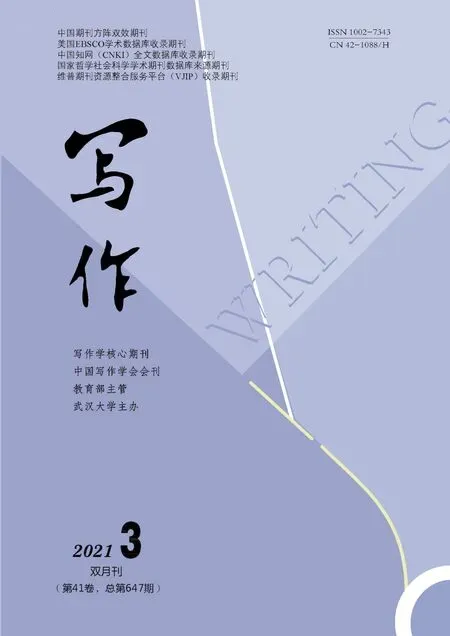港新女性的出走与知识:西西与张曦娜的小说创作探究
谢征达
引言
西西与张曦娜,从出生时代来看,她们分别出生于不同年代。然而,80年代却是她们在各自文学场域中发光发热,获得许多奖项的荣耀时期。更重要的是,该年代她们生产出一系列关注女性,同时也重视在地发展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以两位作家在80年代出版或创作的小说为例,分析她们写作中的女性形象。范铭如在分析台湾女性作家时,便将80年代后视为一个过渡的创作期,是许多台湾女性作家在90年代后成为重要作家的必经阶段。虽然西西的创作早于80年代,但是西西在80年代才算巩固其文坛地位,黄继持更戏言虽然在《周报》已读了西西的文章多时,但直至后期读者才有机会“见上几次”西西。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在香港葛洪量教育学院毕业,曾任教职,为香港《素叶文学》同人。1983年,她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荣获《联合报》小说奖推荐奖,此后便获奖无数。她著作极丰,包括诗集、散文、长短篇小说等30部。2005年获《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1年成为香港书展年度文学作家。西西是香港的文坛常青树。身为一位女性作家,其书写内容并不倾向女性主义内涵,文字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的女性作家痕迹,如罗孚所言的“无巴黎香水气”。西西写下不少关注女性的作品:《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描写一个恋爱中的女人的挣扎,《母鱼》描写了一位年轻女子未婚先孕的焦虑,《感冒》书写陷于婚姻与自由困境的女性,《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以婴儿的成长与老妇的衰老作结构性的对比。此外,《母亲与湿火柴》《候鸟》《哀悼乳房》《飞毡》等作品都是女性题材作品。黄继持曾提到,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感冒》《母鱼》《母亲与湿火柴》等小说都是关怀女性境况的系列作品①黄继持:“……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这引起更多读者注意而西西后来却以为《左耳之作》的篇章。其实这篇既可与《感冒》、《母亲与湿火柴》及往后的《母鱼》等,看成探讨女性境况的系列……”。黄继持:《西西连载小说:忆读再读》,《八方》文艺丛刊1990年第12辑,第69页。。然而,西西关怀女性的写作与强烈的女性主义书写姿态不同,如陈丽芬所云:“西西是我们当代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而她很少涉及女性主义课题,甚至没有叫人注意到她的性别。然而,她作品中的颠覆性甚至为我们当中一些最前卫的女性主义者所不及。”②陈丽芬:《天真本色:从西西〈哀悼乳房〉看一种女性文体》,陈炳良编:《中国现代文学与自我:第四届现当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1994年版,第137页。
张曦娜,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3岁时举家南迁新加坡。曾任新加坡人民协会《民众报》记者与编辑,现供职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记者。1979—1980年获得日本兵库县政府奖学金,赴日本神户芦屋艺术学院进修杂志编辑课程,并到《朝日新闻》等媒体及出版社实习。《掠过的风》获1973年新马港短篇小说比赛第三名,80年代对于张曦娜而言更是丰收的时期。1984年,小说《变调》获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1985年《都市阴霾》获第二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1986年《乌节灯火》获全国短篇小说创作第二名,1987年《入世纪》获金狮奖小说第二名,同年出版《掠过的风》与《变调》。1989年,《镜花》获金狮奖小说第二名。2000年,张曦娜获得区域性认同的“东南亚文学奖”。其中,《变调》和《入世纪》是本论文重点分析的文本,主要从现代女性的形象入手,观察女性面对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时的两难困境。
在21世纪后女性才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的《旅行书写与性别》(Travel writing and Gender)一文从历时的角度,叙述女性在旅游写作所面对到的许多障碍。在西方,冒险(adventure)论述多数掌控在能够在公共空间自由游走的男性手中。因此,欧洲骑士征伐传奇或是海上探险故事都是男性来叙述。女性一直都是欲望的客体,或是作为最后的终点,而不是一位活跃的旅人。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女性自我选择的权力,她们拥有移动的自主选择在男性霸权世界中成了女性能否全然得到自由的重要关键。因此,在“游走”成为可能之前,“出走”是女性突破男权社会约束的重要一步。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著名的剧作《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1879)是激发此一意识的重要文本。女主角娜拉最后走向自我选择的觉醒道路,影响了全球的女性写作。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题目“娜拉走后怎样”同样引人注目。在被视为女性意识保守的东方世界中,鲁迅提出了女性出走之后“何去何从”的疑问,探讨女性在做出了出走的决定之后,社会是不是能保障女性能寻找自己安稳的未来。然而,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女主角最后的死亡却仍告诉我们,男性作家对于女性出路依旧是悲观的。时间推至20世纪70、80年代,无疑是香港与新加坡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大放异彩的时间段。除了两个城市开放的条件之外,无论在经济、教育或是社会地位各方面,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有大幅提升。然而,女性的行动力仍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西西与张曦娜两位女性作家,如何在小说中呈现港新两地的处境;女性的自我选择与思考,以及她们“出走”的渴望与实践。以下主要从两个面向对这两位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第一个部分主要探讨女性的选择意识与权利,并同时思考在“出走”的举动间,女性遭逢到的困难与限制。第二个部分则是探究两位作家如何借小说为女性在文化与教育层面上发声,在“捍卫”知识之中,带出女性角色想要选择的自由。
一、未知的出走
西西的小说与女性人物的出走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西西表示,笔名“西西”意味着“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玩着跳飞机的游戏,展示的是一个活泼自由的女性形象①西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序,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2页。。身为一位作家,西西经常旅游。从1970至1990年的20年间,她先后游历欧洲、土耳其、埃及、希腊、中国台湾及大陆等地;这些游走的经验“融铸成为她艺术生命的养素”②何福仁编:《西西传略》,《西西卷》,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36页。。西西重视女性的生活状态,曾写过一篇散文《第二性》,议论女性地位的变化,她提到女性地位在妇女运动之后才稍微改善,强调现今“女性的地位,卑贱依然,尤其是在贫穷、落后、偏僻的农村”③西西:《第二性》,《耳目书》,台北:洪范书店1991年版,第27页。。西西关心着女性的社会位置,因此,她的小说不乏关怀女性在生活中的自由度与选择的能力。她的女性小说并不突显女性主义中的激昂与明显的抵抗,其笔下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作者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然而,西西笔下的女性并不一定总拥有主动权力,如《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的“我”,因为自己的职业,在爱情上处于被动位置,失去自我追求爱情的力量④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130页。。另一篇小说《东城故事》中,女主角更因为自身的困境,申述着“如果我有权利选择,我愿生长在马赛,我愿生活在18世纪,我愿意做男孩子,我甚至愿意从来就不曾有我”⑤西西:《东城故事》,《象是笨蛋》,台北:洪范书店1991年版,第154页。。然而,从女性书写的角度而言,西西在《感冒》中,女主角在爱情悲剧中找回自主权,不再依附于男性,最终选择出走,使女性在选择的主动性方面有所突破,以一个鲜有的成功摆脱男权传统的案例,展示女性对自己的人生有选择的可能。
面对着自己不喜欢的爱情与人生,女主角的“感冒”犹如一种绝症,“是永远也不会痊愈的了。”⑥西西:《感冒》,《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131、135、152、155页。这一场严重的“感冒”不是一种生理的病,而是一种心理病,是对于自己生活缺少了自由及选择的无助。道德上的束缚使她无法“康复”,家人与不喜欢的对象对她百般呵护,也让女主角找不到合理借口推辞,导致“病情”加重,最后变成了“我只知道,我的感冒,其实是无药可治的”⑦西西:《感冒》,《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131、135、152、155页。。女主角对于自己的人生,就像对自己的“病”一样束手无策。她自己的婚事,忙碌的都是周围亲友:
他们,所有的这些人,我的父母,我的父母的朋友,我的未婚夫的父母,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他们会允许我这么轻易地说一句:我不要结婚了,就由得我不要结婚了么?我已经被困在一个笼子里了,我如今是插翅难飞了。⑧西西:《感冒》,《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131、135、152、155页。
如受困中的小鸟,女主角无法安心自在地选择想过的生活。就算在披上婚纱那天,“感冒”的病症并不会因为大喜之日而消退,反而更加明显⑨西西:《感冒》,《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131、135、152、155页。。“病”是一种拒绝心理的展现。故事的结尾是整篇故事的关键,女主角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为了别人而活,选择了出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女主角获得自由之后,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
啊,我记起来了,前面是一座球场,我听到一片扩散的欢呼声,人们正在看足球呢,人们那么兴高采烈。我何不也去看一场足球呢,我有的是时间。让我就这样子,挽着我的一个行李袋,去看一场足球吧。(可曾瞧见阵雨打湿了树叶与草么,要做草与叶,或是作阵雨,随你的意。)啊啊,让我就这样子,挽着我的一个胖胖的旅行袋,先去看一场足球再说。①西西:《感冒》,《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169页。
逃离不喜欢的婚姻、家庭与生活,让女主角有了自己的时间,也可以为自己作出选择。她决定先看一场足球比赛。足球被视为一种以男性为主的运动,女主角出走之后选择去看足球赛,这一举动除了展示女性获取自主行为的胜利之外,同时也打破了女性活动在性别上的桎梏。足球作为女性的束缚,在另一篇小说《碗》里更加明显。该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母亲,虽然是一位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但封建思想的传统仍然存在着她的内心;她对自己7岁大的女儿踢足球一事甚感忧虑,并且要“想想办法”阻止女儿踢足球②西西:《碗》,《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37页。。女性能否参与足球活动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权力转移的象征,一种打破足球作为男性为主的一项运动,打破女性不应该在足球场上粗野、脏乱地满场跑动的意识形态。《碗》中的母亲担心女儿选择了其他人无法认同的“男性活动”,是一种对女儿的思想束缚。《感冒》的女主角观看足球赛,象征了女性在时空上的完全自由。这种自由也标示着社会对于女性的开放程度,在80年代,此结局的铺排已是一种前卫式的突破。然而,《感冒》是西西小说中女性成功出走的少数例子。这小说也与作者有着莫大关系。虽然身为女性,西西对足球的知识与热情完全不输给男性。西西自小就随兼任甲组足球队教练及裁判员的父亲上足球场,对于足球肯定不陌生③何福仁编:《西西传略》,《西西卷》,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35页。。西西对足球相当热衷,她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她几乎看完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每场赛事,而且每天写足球专栏④何福仁:《从头说起:和西西谈足球及其他》,《八方文艺丛刊》1990年第12期。。在西西眼里,足球比赛犹如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狂欢节庆:
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就像文论家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举行期间,雅和俗接通了,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可以打成一片。球场替代了广场,而球赛成为大家的焦点,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各有自己拥护的对象,有的相同,有的敌对,无论贫富、国籍、都融入这种亲密的世界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⑤何福仁:《从头说起:和西西谈足球及其他》,《八方文艺丛刊》1990年第12期。
与西西的小说对照之下,张曦娜小说中的女性也有独立思维,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兼具理性与知性,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爱好自由。虽然外表坚强,但内心脆弱。身为一名女性记者,张曦娜对于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非常留意。她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大姑速写》,收入了她与23位女性的访谈感想,明显看出张曦娜对于女性议题的关注⑥这23位女性访谈者分别是刘蕙霞、伍玉玲、李宝丝、关山美、吴丽娟、黄世钟、郑英良、朱亮亮、韩少芙、庄淑昭、刘培芳、吴明珠、张齐娥、曾秀娘、邓柳仙、周淑春、焦贵玉、廖静芬、林丽华、周蕴仪、王尤红、彭秀梅、向云。张曦娜:《大姑速写》,新加坡:点线出版1992年版。。小说中的人物在面对困境时,往往因为亲情或道德而显得犹豫不决,以致有欲走还留的现象产生。在她的小说中,作为女性代表的叙述者面对着巨大的家庭伦理压力。
小说《入世记》当中的“我”(陈子娟)是名记者。“我”因为无法遏止少女鄞碧乐悲剧的发生而内心自责。“我”的哥哥子文对鄞碧乐始乱终弃。然而,他在社会上颇为风光,除了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奖”之外,还是一位“热心社区服务工作”的杰出青年。虽然子娟知道自己的哥哥做了错事,但却因为道德与亲情的束缚,并没有将事实公诸于世,最终选择逃避。《入世记》中,除了对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审视,及对上层精英分子的批评之外,道德、家庭伦理与公义的纠葛也是小说欲探讨的议题。《感冒》中的女主角选择离开束缚,《入世记》中的女主角最后也选择独自一人开车远离窘境。⑦张曦娜:《入世纪》,《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版,第45页。然而,两篇小说的不同在于后者中的女主角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自由,相反地,女主角的离开其实是一种自我逃避。
小说中的“我”在S报担任新闻记者数年,虽然工作上并没获得什么满足感,但是却因为自己的华校生身份,担心辞职后无法找到另一份工作,因而寸步难行。①张曦娜:《入世纪》,《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版,第11-12页。“我”失去的是走出自我局限的勇气。“我”自觉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期待自己能成为“小知识分子”。小说中被害人鄞碧乐的姐姐鄞碧仪在“我”家时,拿了一篇叫着《社会的良心》的短文,似乎是要提醒“我”应对社会败类作出严惩。但是,在社会与亲情的责任对立时,“我”选择了后者。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的出走,似乎带有着过多的牵绊,以致在面对苦难时总会遇到道德上的阻碍。她虽然对鄞碧乐的死有着绝对的同情,但是却被亲情所束缚,无法将哥哥的“罪行”公诸于世。甚至到了最后,“我”决定维持现状,选择自我逃避,“决定持续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女性书写的细腻与纠结,现代女性仍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做出决定时面对着周围的众多价值观所形成的压力。
二、回返与捍卫
如前文所提及,女性的出走可以是一种自由选择,如《感冒》;或是一种道德逼迫,如《入世纪》。在西西的小说中,从女性视角展开知识论述,并发挥到极致的是长篇小说《飞毡》。虽然西西在创作中也有以知识论述作为写作的重心,例如《哀悼乳房》。然而,《哀悼乳房》一书中的知识论述已有学者作出论述,特别是徐霞的《文学·女性·知识:西西〈哀悼乳房〉及其创作系谱研究》,当中对西西小说理的医学知识与女性书写都有深入解析。此外,本文认为西西的《飞毡》的知识论运用比起《哀悼乳房》更为极致。后者关心的是女性议题,是集中在女性的身体认知与生活状态的思考层面。该着在“知识与文学”一章中对西西的“知识论述”做出了详细的解说,徐霞认为“西西作品中的知识论述是在文学环境下,由作者、读者构成的特殊情境,所以肯定和百科全书中的知识论述不同”。②徐霞对“知识论述”的说法一词源自《飞毡》扉页中的一句话“深刻而博大的知识论述”,并借用该词指称“西西书中出现的科学及文化知识等内容”。徐霞:《文学·女性·知识:西西《哀悼乳房》及其创作谱系研究》,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版,第102-103页。然而,《飞毡》的知识运用更加庞杂,范围也更广。
对于“知识”的论述,福柯在《知识的考掘》中认为兼有“connaissance”及“savoir”的意思。王德威在翻译时做出的注解是,“connaisance”意指一种专门知识的集合,或一种特别学科——如生物学或经济学等。“savoir”通常泛指一般的知识,或是各专门知识的总合,但此处福柯该字用来指一种“‘隐含的、基层的’意义而非‘整体’的意义。”③福柯对于二字的说明是“我用connaissance来表示主题和客体的关系,以及统御此关系的形式规则。Savoir则意味某一特别时代中,赋予各种各样事物形态一专门及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的特定条件。”王德威:《知识的考掘》,台北:麦田1999年版,第89页。这两种知识在本文的讨论中是不断交替出现的。以西西的例子为例,在《飞毡》中,对于昆虫的科学知识,与在白发阿娥中对年老女性特性的书写,一者为专门知识,另一则是基础的,但本文中并不会将西西的知识书写作出区分,而是以知识作为整体进行观察与分析。知识的文学性是值得去挖掘的。从前述讨论中可以得知,“知识论述”的涉及面超越了知识本身,而是将作者与文学环境集合思考后去理解这种知识论述给文学带来探讨文化形式的方法。
我们可从陈燕遐细述西西《飞毡》中不同的知识元素了解到小说中的知识浓密度:
故事情结中间加插各种各样的知识,有化学、昆虫学、植物学、天文学、心理学、考古学、炼金术、飞行原理,以至乐器介绍、木材知识、文物拓印技巧等各种软硬科学知识:当然更少不了地水南音、儿童民谣等民间艺术,以及拜七夕、打小人等市民生活,也有街市、大排档等城市景观,十足一张百纳被,又像一部详实的地方志,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①陈燕遐:《书写香港:王安忆、施叔青、西西的香港故事》,《现代中文文学学报》1999年第2卷第2期。
西西在创作中纳入了大量的知识,让文本减少了女性书写中的感性,而衍化成一种“知识库”式的故事书写。知识的铺述在小说中不仅有自然科学,还有历史、音乐、文化、民间信仰等。然而,西西以知识建构内容的手法也引来许多异议。马森在《掉书袋的寓言小说:评西西〈飞毡〉》一文中便对西西小说中的大量知识书写颇有微词,除了将之视为一种“累赘”,也认为此举扰乱了故事发展的节奏。此外,他还质疑西西的读者对象并非香港人,因为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没有一个可以代表香港的特质”。小说中大量的知识也只显示了作者的“‘抄书’的功力和对学问的认真”,更认为这么做的模式并非难事,“有一本百科全书就可以办到”,因此奉劝西西“委实应该适可而止”②马森也举例指出《飞毡》中“毡”一字使用的策略性质:“《飞毡》在台湾叫‘飞毯’,这是普通话的用语,香港人管‘毯’叫‘毡’,是故在书前费了作者好一番旁微博引的唇舌来向台湾的读者解说这个特别的用语。”马森:《掉书袋的寓言小说——评西西〈飞毡〉》,《联合文学》1996年8月第12卷第10期,第169页。。但是,我认为这种类似“百纳被”式的知识体制的书写显示的是女性作者的细致,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刻意的叙述距离。以《飞毡》这部小说而言,其主要目的是展现香港的不同面向,虽然《飞毡》中以女主角叶重生的女性话语为故事发展的主线,女性书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故事的历史叙述当中,主导的声音仍旧为男性。小说中女性虽然掌握了知识,但却没有真正远离男性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意识形态。
《飞毡》成为一个综合不同元素的扎实小说,包括了历史生活化的书写,女性状态的刻画与彰显,加上各个面向的大量知识内容,与其说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书写,不如把它看成一种从不同视角建立的香港论述。小说中女性与知识的议题也值得探究,书写的是当时香港女性的教育议题。香港在80年代之后,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除了生育率开始降低之外,香港也在1978年开始向儿童免费提供九年的教育,女性受教育也已经逐渐成为普遍现象③Grace C.L Mak,“Women and Education”,Sussane Y.P.Choi and Fanny M.Cheung eds.)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2,p.23.。小说人物花艳颜在战后获得了教育机会,其表妹李丽莲也念了龙文中学,小说中刻画女性的受教育的情况,与当时香港女性接受教育的情况相符。此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如花艳颜、程锦绣、李丽莲在小说中都从事教职。另一方面,教职的强调是因为西西毕业自教育学院,在教育岗位之外,她也关心整个80年代香港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女性的教育议题可说是小说中女性与知识主题的一种延伸④张丰慈:《摩登长廊里的传奇:论西西的香港都市书写》,“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4页。。在西西的小说世界中,女性在面对缺乏教育与知识时,总是困难重重。以另一篇短篇小说《煎锅》为例,女主角在中文中学就读,因为自己不谙英文,而无法帮助父亲解决工作难题⑤西西:《煎锅》,《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台北:洪范出版1986年版,第46页。。然而,就读英校的弟弟却能帮父亲的忙,而且还教父亲读英文。这里思考的问题不单是男尊女卑的议题,更牵扯到女性接受到的教育与知识的议题,也表现出女性所面对的知识局限与阻碍。
西西在文学中以庞杂内容注入文本,以小说传达对于香港与女性教育的重视。而张曦娜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经常有捍卫新加坡华语及华文文化形象的作用。她从语言与教育入手,探讨的也是女性与知识的议题。8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日渐西化,对华人母语文化产生冲击,教育成了当时新加坡华语小说重要的书写主题。小说中的女性面对的是新加坡华语弱势的难题,导致了女主角纷纷捍卫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与前述西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讨论相似,女性在思考切身的问题之外,也对于公共领域的议题有所重视,张曦娜关心的是语言与教育体制的问题。作为女性华校生或是以华文传统为主的故事主角们,中华文化的知识在新加坡不断流失,让她们感觉不安,面对着新加坡的西化大势,她们作出的是捍卫母语与文化的姿态。
华文教师的形象在新华女性小说中经常出现,如黄华德《当红灯亮起时》里的中学老师蓝玉、《淌泪点圣诞》里的大学助教艾蒂、尤今《框子》里的家庭教师江月娥、陈华淑《追云月》里的中学教师李翠花等等。然而,张曦娜的女性人物在面对着知识教育与母语文化等议题时立场坚定,留守与捍卫的姿态明确。特别是在《变调》与《任牧之》中,张曦娜从女性的视角关注教师处境与教育改革的走向,试图阻止母语文化的失势,以及文化传统的流失。张曦娜本身也对南洋大学的历史发展有所重视,例如她撰写过两篇文章《歪曲史实的传记:〈林语堂传〉之〈南洋大学校长〉及《南洋大学创办过程之内情》,对南洋大学历史的关注不言而喻①张曦娜:《〈林语堂传〉之〈南洋大学校长〉》,《客答问》,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94年版,第230-246页。相关细节,请参阅张曦娜:《南洋大学创办过程之内情》,《客答问》,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94年版,第248-274页。。
张曦娜的作品中更不时出现南洋大学的相关的人物,《变调》的叙述者馨蕊便是一位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她后来当上全职教师,教授作为第二语文的华文。教书并没有给她带来满足感,反而却“却越教越没信心,学生的程度似乎一年不如一年”②张曦娜:《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版,第86、91、101、104页。。女主角面对的是一个日渐西化的社会,华语及华族文化的式微,令她感到无奈。语言的问题涉及到的是现实层面的“含金量”问题,对学生而言,他们深知英语才是主流,而且升学机会及成绩是否优异的主因都在英文,所以才会说“老师,读华文有什么用?将来我们毕业了,还不是没有用,只不过在巴刹和Hawker Centre才用得上”③“巴刹”一词指的是“菜市场”,而“Hawker Centre”指的是熟食中心。。馨蕊的学生这里意在强调华语是局限在中低阶层民众的语言,在正式的场合却不适用,也清楚意识到新加坡在教育制度上及社会上都以英语为优先,华文能力再强,工作的选择仍旧会很缺乏。在这种大氛围底下,女主角在事业上虽然郁闷,但是坚持“论才干、论能力,我们并不输人,为什么却总是处处显得我们不如人?”④张曦娜:《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版,第86、91、101、104页。依旧强调华文文化的重要而坚持岗位。然而,华文文化的捍卫立场也影响到了女主角到情感问题。馨蕊与同为华校生的男朋友毅民,两人在思想上日渐疏远。馨蕊坚持传统华族文化,强调母族文化的重要性,可是男友毅民为了在社会上取得成就而走向歧途,除了帮日本客户找女人外,还打算骗取馨蕊父亲黑市夫人的钱财⑤张曦娜:《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版,第86、91、101、104页。。很明确的,重视传统华族文化与价值观的馨蕊,在面对变得唯利是图的男友时,最后的选择便是离开。虽然在情感上是一个无奈的抉择,但是馨蕊却“反而逐渐明晰而冷静”,加强了自己坚持理想的信念,继续为华族文化而努力⑥张曦娜:《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版,第86、91、101、104页。。
在另一篇小说《任牧之》中,女主角研菲是一位心理医生,与《变调》不同,她对华族文化与华文教育都没有直接的接触与兴趣。她从病人任牧之的悲剧中,感受到捍卫华语与文化的迫切,然而,她却无法改变事实的发展状况。小说的开始是身为前华校中学副校长任牧之的跳楼自杀。任牧之因为华文教育逐渐式微而自责,最后轻生的举动也不受到任何人的关注,报纸上也只有“豆腐干大小篇幅”的报道,不造成任何社会回响⑦张曦娜:《任牧之》,《镜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研菲虽然与事件毫无关系,但是此事却像梦魇般缠绕着她,不断记起任牧之生前最后一次见她时所说的话:“这个城市真是越来越热了”“日子越来越难过呵”。任牧之的死是社会压迫造成的,在继续挖掘更多关于任牧之的事情后,研菲从他遗留下的手稿了解到语言、教育及文化的密切关系,以下是手稿的内容:
有些事我实在想不通,凭什么靠着殖民势力撑起来的语言,会在这样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城市里横行?真是想不通呵,从前,我们反殖民统治,抗议统治者歧视民族教育,我们罢课、示威,我们以热情、傻劲维护华人文化,我们争取母语教育义无反顾,有人牺牲了个人利益,仍然勇往直前,现在我们把自己努力挣取来的东西轻易丢弃了,他妈的,丢弃了……。①张曦娜:《任牧之》,《镜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24页。
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故事中不时出现,任牧之的手稿更让人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的绝望而导致轻生,语言的议题与整个社会、政治,甚至是城市的发展史不可分割。华校生因为新加坡语言政策的改变,原本拥有的学位如同废纸,社会的不认同令他们的生活处境非常艰巨。华族语文地位低落导致传统华族价值观以及华文的学习价值也变得低落,华校生原本掌握的华文知识,反而变成了他们在生活上的负担。研菲逐渐从一位旁观者变成一位同情者,到最后成为华语及华族文化的捍卫者。研菲开始对华校生的悲剧原由感兴趣,逐渐理解新加坡语言改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骤然间面对生命中如此叫人措手不及的改变,他们惶恐、心忧、精神上饱受煎熬。许多人在三几个月内白了头发,恶梦由此开始,头疼、失眠、心悸……日子过得凄凄惶惶。”②张曦娜:《任牧之》,《镜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24页。小说中有一幕相当值得玩味,那是从收音机里传来的一段蔡琴忧伤的歌声:“你只看见我表面的美丽,可曾看见我复杂的心情……你只看见我表面的事情,从来不曾走进我的内心……”③张曦娜:《任牧之》,《镜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24页。纵使研菲是位心理医生,华校生的困境使她向华文文化没落的发生趋近。从一位知识女性的视角出发,知识带给女性觉醒的力量,但是却也带出了现代女性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在以华人为主的香港与新加坡社会,女性在面对现代价值观与生活的转变之时,仍有一些保守的意识,此一现象反映在两位作家的小说中。无论是西西或张曦娜的小说里都对女性的自觉意识作出思考。然而,女性独立自主的推动力源自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为了家庭所作的牺牲,或是女性在职场所面对的不公平现象,其背后的缘由以及对女性的影响在两地的华语小说中都有明确的呈现。小说中各种80年代的女性议题反映出当时女性所面对到的挑战,展现了当时女性作家对文学与生活前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