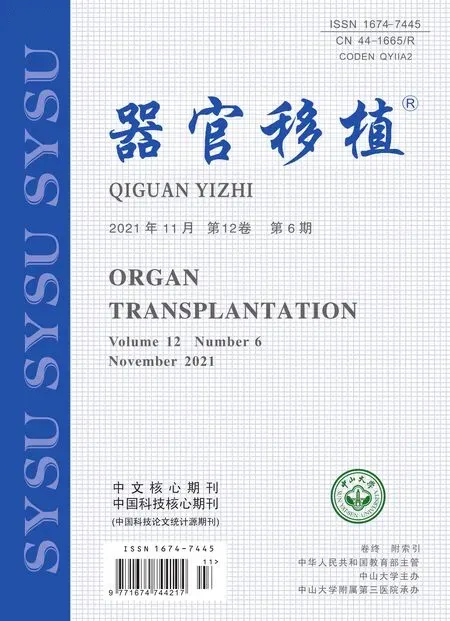枯否细胞极化状态在肝移植免疫耐受中的作用
刘涛 李金政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方法[1],目前尚无较好的方法帮助肝移植受者建立术后免疫耐受。肝脏由一种独特的实质细胞和免疫细胞组成,其功能包括免疫调节和促进抗原特异性耐受。在移植器官中肝脏的耐受性是最强的,但诱导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的具体机制尚未明晰。
作为肝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枯否(Kupffer)细胞发挥了重要作用。Kupffer细胞是肝脏常驻巨噬细胞,在肝内免疫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主要生理功能之一为免疫调节。肝移植术后细胞微环境发生改变,Kupffer细胞被激活并发生极化。本文就Kupffer细胞极化状态与肝移植免疫耐受的关系、Kupffer细胞极化机制进行综述。
1 Kupffer细胞极化状态与肝移植免疫耐受
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成熟,肝移植手术成功率逐渐提高。但是在缺乏免疫抑制治疗的情况下,人类同种异体肝移植术后受者普遍会产生排斥反应[2]。免疫耐受的建立与Kupffer细胞激活的免疫反应密切相关。Kupffer细胞是肝脏组织驻留型巨噬细胞,起源于胎儿肝中卵黄囊的红髓祖细胞。其特点是通过自我更新而非外源细胞补充的方式维持细胞群体稳定[3]。Kupffer细胞具有高度可塑性[4],在不同微环境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表型与功能,即M1型Kupffer细胞和M2型Kupffer细胞。二者具有特征性的差异基因表达,M1型Kupffer细胞具有促炎功能,M2型Kupffer细胞具有免疫调节功能。肝移植术后,由于肝脏代谢紊乱、缺氧等因素刺激,Kupffer细胞受诱导发生极化。不同极化状态下的Kupffer细胞通过分泌免疫调节因子或促炎因子等方式影响免疫耐受的形成。
M1型Kupffer细胞代表炎症巨噬细胞,具有表达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CD74等的特性。其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等因子引发局部炎症,同时促进细胞因子间相互作用放大炎症反应,最终导致肝移植手术失败。M1型极化状态下的Kupffer细胞是缺血-再灌注过程的主要参与者,能够通过招募其他免疫细胞加重缺血-再灌注导致的肝细胞损伤[5]。此外,相较于树突状细胞,静息状态下的Kupffer细胞表达较低水平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 Ⅱ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使其难以诱发免疫反应,决定了肝脏独特的致耐受性[6]。在Kupffer细胞发生M1型极化后,MHC Ⅱ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表达上调,抗原提呈能力提升,从而在免疫反应中发挥正向增强作用,导致急性排斥反应加重。
M2型Kupffer细胞通过分泌抗炎因子抑制炎症反应,具有负性调节排斥反应的功能。IL-10是其分泌的重要抗炎因子。小鼠Kupffer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相互作用后可以产生更多的IL-10。IL-10通过下调MHC Ⅱ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参与免疫耐受的建立[7],这是诱导受体对肝细胞抗原耐受的关键。此外M2型Kupffer细胞可以清除活化的CD8+T细胞,同时通过多种机制调控调节性T细胞。无论是否发生极化,Kupffer细胞均位于肝窦内,因此很容易与T细胞等相互作用[8]。移植物内细胞毒性T细胞的凋亡和清除可能是免疫耐受建立的机制基础。有实验表明,在建立大鼠肝移植免疫耐受的过程中,CD8+T细胞的消除可能比调节性T细胞的升高更重要[9]。凋亡细胞的清除不完全会使凋亡细胞积聚并导致“二次坏死”,释放大量促炎因子,从而加重急性排斥反应。促进吞噬细胞及时清除凋亡细胞或诱导T细胞无能是建立免疫耐受的基础[10]。
2 Kupffer细胞极化机制
Kupffer细胞可以被多种因素刺激,向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极化(图1),进而影响免疫耐受的结局。可以明确的是,Kupffer细胞发生M2型极化对诱导肝移植免疫耐受的形成至关重要。

图1 Kupffer细胞的极化机制Figure 1 The polarization mechanism of Kupffer cell
2.1 肿瘤坏死因子-α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是M1型Kupffer细胞产生的多效性促炎因子,对宿主防御和炎症反应起核心作用[11]。但近年研究发现,TNF-α还可以通过与2型TNF受体结合促进调节性T细胞的成熟,发挥免疫抑制作用[12]。通过对TNF信号通路的有效干预,可以抑制Kupffer细胞的M1型极化同时促进M2型极化[13]。在不同机制作用下,TNF-α诱使Kupffer细胞进入不同极化状态,这也表明了Kupffer细胞极化并非单一调控模式。
2.2 核因子 -κB
核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家族是一个异源二聚体转录因子家族,在多种细胞反应特别是在免疫细胞反应中,其具有广泛的基因诱导作用。在哺乳动物中,转录因子NF-κB家族包括RelA(p65)、RelB、 c-Rel、 前 体 蛋 白 NF-κB1(P105) 和 NF-κB2(P100),后两者分别被加工成p50和p52[14]。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糖原合酶激酶3β(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β,GSK3β)/NF-κB(p65)信号通路受到抑制的同时,Kupffer细胞的M1型极化也受到抑制,相反,上调p65的活性则可以诱导M1型Kupffer细胞增多[15]。有报道称p50的激活对巨噬细胞发生M2型极化是必不可少的[11]。NF-κB家族不同成员在巨噬细胞和Kupffer细胞中具有不同的诱导效应,这可能与NF-κB的激活通路不同有关。NF-κB家族可能有诱导Kupffer细胞发生M2型极化的作用,但目前的研究集中在p65上,该家族其他因子作用的具体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2.3 白细胞介素
IL家族具有数量庞大的成员,在免疫细胞的成熟、活化、增殖等一系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IL-4主要由B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自然杀伤T细胞产生,是M2型极化的经典诱导物[3]。既往实验发现,IL-4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诱导M2型极化,比如激活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6/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含Jumonji结构域蛋白3(Jumonji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3,JMJD3)通路,诱导Kupffer细胞发生M2型极化[16]。IL-4和IL-13的协同可以起到抗炎和组织修复作用[17]。这说明IL-13在诱导M2型极化方面可能和IL-4具有相似的功能。外源性IL-25可以使M2型Kupffer细胞数量增加,但该效应有赖于IL-13的支持,进一步证明了IL-13具有诱导M2型极化的功能[18]。IL-10是M2型极化的主要刺激因子,也是M2型Kupffer细胞分泌的重要免疫抑制因子。IL-10可以下调MHC Ⅱ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并上调抑炎因子的表达来诱导免疫耐受[7]。M2型Kupffer细胞可以导致M1型Kupffer细胞发生凋亡,其机制可能是IL-10诱导抑炎因子的基因转录触发了M1型 Kupffer细胞的凋亡[19]。
2.4 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信号通路
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Akt信号通路能够调控各种细胞功能,因而受到广泛关注。PI3K/Akt通路能调控巨噬细胞存活、迁移和增殖,该通路还可以协调Kupffer细胞对多种代谢和炎症信号做出反应[20]。PI3K/Akt信号可被Toll样受体4和其他病原体识别受体激活,调节产生细胞因子的信号[11],进而调控IL等的产生来影响Kupffer细胞极化。最新实验研究表明,钙离子依赖的PI3K/Akt/STAT3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诱导Kupffer细胞发生M2型极化,增强吞噬与免疫调节能力。钙拮抗剂1,2-双(2-氨基苯氧基)-乙烷-N,N,N’,N’-四乙酸(BAPTA)的应用会导致M2型极化标志物的表达显著下调[10]。此外,多种因子可以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产生极化效应。例如,IL-33可以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的激活增强M2型极化,进而调节肝脏的免疫反应[21]。
2.5 α-酮戊二酸
α-酮戊二酸(α-ketoglutaric acid,α-KG)是三羧酸循环的重要中间产物,其既可以通过三羧酸循环代谢产生,也可以通过谷氨酰胺分解产生。体外实验发现,谷氨酰胺分解产生的α-KG可以促进Kupffer细胞激活并抑制M1型极化,同时还能抑制NF-κB活性和上调IL-10的表达,促进M2型极化[22]。M2型极化状态下的巨噬细胞,包括Kupffer细胞,具有更多的线粒体和更高的耗氧率。M2型极化状态下,线粒体产生一系列变化,有氧氧化成为其主要代谢通路[23]。三羧酸循环的正常进行是有氧氧化完整闭环形成的重要条件,而α-KG是三羧酸循环的重要中间产物,其参与有氧氧化过程是其介导M2型极化的重要机制。缺氧诱导因子-1α的稳定性是巨噬细胞M1型极化的关键,α-KG可以破坏缺氧诱导因子-1α的稳定性,并通过表观遗传调控增强M2型极化相关基因的表达[24],对巨噬细胞的M2型极化起重要作用,这可能是α-KG诱导Kupffer细胞发生M2型极化的潜在作用机制。
2.6 衣康酸
衣康酸是巨噬细胞对脂多糖和干扰素-γ的刺激作出反应而合成的重要代谢中间产物,由柠檬酸衍生的三羧酸循环中间体顺式乌头酸脱羧形成,其进一步反应产物衣康酸酯可在小鼠原代巨噬细胞中积累[25]。在转录和代谢水平上,衣康酸可以通过抑制琥珀酸脱氢酶介导的琥珀酸氧化来调节巨噬细胞代谢,从而阻止巨噬细胞发生M2型极化[26]。肝移植术后,细胞微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细胞代谢进行重塑,可能导致严重的糖耐量不耐受、代谢控制不良和生长不良,术后机体的营养代谢能力与预后密切相关[27]。对免疫代谢领域的深入研究还有助于利用存在代谢问题的供肝,扩大供肝来源[28]。免疫代谢逐渐成为肝移植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衣康酸在Kupffer细胞极化中的作用机制还未有深入研究,其在巨噬细胞中的极化作用可能在Kupffer细胞中同样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究。
3 小 结
在建立肝移植免疫耐受的过程中,Kupffer细胞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各类刺激可以诱导Kupffer细胞向不同方向极化,而多种刺激之间又可以协调合作,构建一个复杂的驱动网络来诱导极化。Kupffer细胞可进入M1型和M2型两种极化状态,发挥破坏免疫耐受或促进免疫耐受的双重作用。已经明确的是,M2型极化状态下的Kupffer细胞对肝移植免疫耐受的建立起着促进作用。抑制M1型极化和促使M2型极化相结合的治疗手段可以进一步提高肝移植术后建立免疫耐受的成功率。根据施加的刺激和由此产生的转录变化,M2型巨噬细胞可以进一步细分为M2a型、M2b型、M2c型和M2d型,它们有着更加细致的分工[11]。对M2型巨噬细胞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探究Kupffer细胞发生M2型极化的内在机制,为建立肝移植免疫耐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