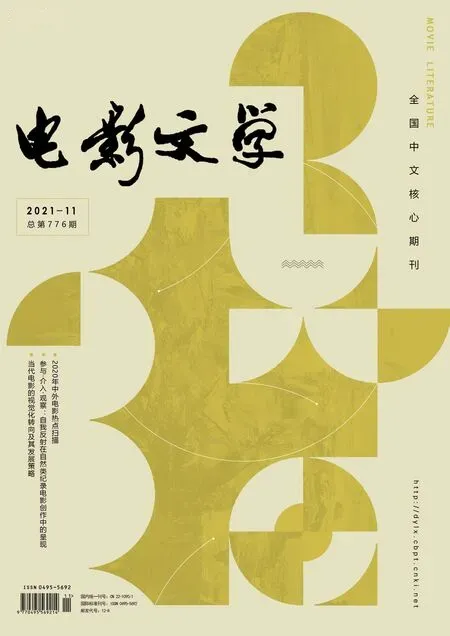论城市影像叙事中的“人城互文”关系
杨怡静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城市文化从本质上讲涉及的是“城”与“人”的相互关系,正如“城即人,只有在发现了‘人’的地方,才会有‘城’的饱满充盈”。基于此,我们在观照影视剧文本中“城”与“人”的互文关系时,将围绕这两者间存在的文化同构关系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基于“城”对于“人”的塑形意义,分析影视剧文本中城市意象如何达成典型人物形象的意义建构与传达;另一方面,基于“人”对于“城”的阐释意义,探析影视剧文本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如何实现对于一座城市意蕴精神的展示与代言。
一、“城”与“人”的互文
每当人们想起一座城市,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印象通常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景观。“建筑是最先被人看到的城市肌体,它们充当着城市的皮肤,所以最容易被人捕捉形成印象,成为人们感受城市形象最直观、最真切的部分。”然而,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异质特征,除了显著地体现于城市建筑景观这一外在的标志性符码之外,还更为重要而集中地存在于城市的隐性文化特质中,即生活于这座城市中的“人物”身上。尽管自然环境、建筑景观等物质形态是构成城市意象的重要主体,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中“人”的生活状态、行为方式、情感表达与精神旨归则是城市意象中更为核心的文化要素。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意象”不仅包含了各种城市物质景观所组成的视觉感官印象,更加指涉了各种风俗人情与精神风貌所反映出的城市文化底蕴,以及城市文化意蕴孕育下城市人的情感方式、精神诉求、生活体验与生命轨迹。
城市影像叙事中,“城市中所呈现的物质景观无疑是城市人劳作的痕迹、智慧的结晶,城市中所蕴含的文化气韵更是城市人心灵的赋予……城市人的性格会因为城市意蕴的滋养而造就,城市人的精神也会因为城市文化的影响而生成。正是源于这样一种相互生成、相互诠释的‘人城’互文关系,才使得城市叙事的意蕴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而多元”。“城”与“人”在无形中建构起了一个丰富、立体且具有复调魅力的文化体系,这自然也成为影视剧文本创作极为宝贵的文化底本。
二、城市意象对人物形象的传达
城市影像叙事中,城市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环境背景和潜在的文化基因,无疑会对影视剧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便是指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了这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与行为逻辑,进而最终导致其命运的走向。人物的性格养成可能源自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社会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有着较为复杂而深刻的生成原因。在这其中,城市意象无论作为人物微观的居住环境,抑或作为中观的生存环境,甚至作为宏观的社会文化大环境,无疑都对人物性格的养成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可谓人物性格养成的地缘文化依据。
“地缘文化,是某一特定区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性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体系,是一种历史意蕴与现实生活的交融积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生活于城市中的人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这座城市特定环境所赋予的某种特殊气质,正如人们通常认为北京人开朗豁达、天津人幽默风趣、上海人精致细腻、东北人豪爽奔放、陕西人憨厚朴质、四川人热情泼辣等,都是基于地缘文化特质对于不同地域人物性格的精要提炼。虽然这样的提炼远不足以囊括每一个人物个体身上的多元性格维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于不同城市中的人们,自然会在言行举止、行为方式、脾气秉性、思维意识、审美趣味、价值判断等方面体现出这座城市所赋予的特殊文化印记,这一点也成为影视剧城市叙事中塑造人物形象、设定人物性格时需要重点参照的一项重要依据。
电视剧《永远有多远》中,主人公白大省所居住的驸马胡同四合院“严整刻板而又充满人际依存与人情慰贴”,它代表了老北京人骨子里的一种安稳、平和而又充满人情味儿的情感特质。在电视剧文本中,四合院中青砖蓝瓦围绕起的房间是白大省的家,既作为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又富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是白大省能够敞开心扉的心灵港湾。每当遭遇挫折与伤痛,她总会在四合院的“家”中重拾起对于生活的豁达、真诚与宽容。电影《长恨歌》中的“弄堂”是全片最为核心的城市意象,成为人物的情感依托与精神写照,不仅是主人公王琦瑶生活成长的日常环境空间,更加是一个赋予了人物性格与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在作家王安忆的笔下,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电影文本中,王琦瑶性格细腻、心思缜密,向往繁华害怕冷清,渴望成功忧心失意,这种瞻前顾后、忧虑重重的性格无疑脱胎于弄堂人家的女子所特有的“小儿女情态”。电视剧《大生活》中的成都老街庭院是温情而闲适的,正是这样的环境滋润了主人公柳东温润豁达的品性。虽然他既没有心怀高远的理想目标,也没有壮志凌云的精神气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常常身处生活坎坷之中的底层小市民,却时刻心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即便生活并不宽裕却时时不忘帮衬比自己更弱小不幸的人们。在剧中,“人”与“城”的性格特征是互文相通的,人物因为这座城市的润泽而乐观善良,这座城市也因为人物的行为而充满温和柔美的情感蕴藉。可见,无论是《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还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或是《大生活》中的柳东,在上述作品中,四合院、胡同、弄堂、庭院等城市意象作为日常生活的典型环境空间,或多或少都为人物特定性格的养成注入了某种潜在的文化影响,而这一点正是人物心性塑造的重要维度。
三、人物形象对城市文化的代言
人是城市的主体,一方面人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思想情感等要素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地域环境的影响而逐渐养成;另一方面,城市的地域文化、时代风貌、气韵精神也因生活于城市中的人而彰显。在影视剧城市叙事中,人物形象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便是如此——城市作为人物成长的土壤,是形成人物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人物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生活习惯、精神风貌、价值趣味等要素亦是城市文化的表现载体,人物形象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为城市文化的一种重要代言。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胡同深处灰灰的四合院意象已被放大为人物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文化形成了主人公张大民性格中“贫”这一特征。表面上看来,“贫”是老北京文化传统赋予北京人性格中的一种爱开玩笑、爱耍嘴皮子的调侃“痞性”;但从内里上看,“贫”这种妙趣横生的话语方式,不仅是人物特有的语言习惯,更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修辞,表征着老北京平民的人生智慧与生存哲学。该剧导演沈好放曾这样阐释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贫嘴”这一特质:“当‘市民’式狭小而又可爱善良的心胸被‘逼’得不‘贫’不行了,这种贫就开始向‘有戏’的方向转化,就会让人清楚地觉察到这种‘贫’里深藏着的那一层层难以言喻的‘尴尬’。而这一线伤感与心酸,能引发含泪微笑的‘尴尬’,则是真正‘有戏’。只有这样,北京人特有的‘贫’才可能突破他的局限,使整部作品既通俗又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的确,主人公张大民身上所具有的“贫嘴”这一性格特征虽然有时也带有一丝京都小民苦中作乐的心酸意味,但在更多时候,“贫嘴”这一逗乐式的话语方式,集中表现出的是人物身上时刻洋溢着的积极、豁达与乐观秉性。也唯有这种生发于世事艰难中充盈着乐观与智慧的“贫”才不是肤浅的欢声笑语,而是一种源于生命韧性而生长出的乐天气质,一种无论处于怎样的困境中都始终保有的感恩生活点滴幸福的品质与能力。
如果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这一人物形象真切地反映出了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大气与平和,所代表的是一种蕴含着乐观豁达的京味生活智慧;那么《情满四合院》中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则生动地表现了老北京人镌刻在心性里的善良与正义,所彰显的是一种蕴含着大仁大爱的京味人生哲学。在四合院这样一种“家庭—街坊”的生活情境中,主人公傻柱用实际行动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诠释得淋漓尽致。傻柱称自己是“胡同串子”,有着老北京胡同人能说会侃的特质,但他总是“刀子嘴、豆腐心”“话糙理不糙”,看似唠叨的言语背后包裹着一颗嫉恶如仇、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心。四合院里但凡有个矛盾摩擦、风波恩怨,傻柱总是第一个勇于仗义执言的人;四合院里若是出现坑蒙拐骗、狡猾奸邪、损人利己的宵小行为,傻柱更是第一个敢于打抱不平的人。事实上,傻柱并非真“傻”,他只是以最为朴素、纯粹而直率的行为方式,以超越个体“小家”的博爱情怀,呵护着四合院这个“大家”。傻柱体现出了胡同四合院文化中老北京人骨子里的精神共性——那是镌刻在岁月里的情深义重,融化入血脉里的爱憎分明,以及蕴藏于生活里的相濡以沫。
城市意象可以赋予人物以内在的生命灵魂,而人物亦可给予城市文化以独特的精神气韵。《好雨时节》《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等影视剧作品均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彰显出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城市文化精神。其中,《好雨时节》得名于杜甫的名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成都的跨国爱情,女主人公吴月即便遭遇生活的坎坷与不幸,依旧保持朴质善良、豁达开朗的乐观心境,诠释出成都人“乐容天下、浮沉自安”的人文精神。《温州一家人》讲述了温州人周万顺一家离乡背井、闯荡世界、勇于拼搏、辛苦创业的人生故事。故事中,主人公周万顺一家四口的人物性格虽各不相同,人生轨迹也情况各异,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共同诠释出了敢为人先、积极创新的“温州精神”。《鸡毛飞上天》讲述了以陈江河、骆玉珠夫妇为代表的义乌企业家踏实探索、勇于创新、诚信经营的创业故事。他们在充满跌宕起伏的商业生涯中,始终不忘“鸡毛换糖”的初心与本质,并与时俱进地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内核,将其与现代商业理念相匹配契合,彰显了现代义乌商人的商业智慧与价值情怀。在这一系列的影视剧作品中,典型人物早已超越其形象本身,成为城市文化精神的一种代言与隐喻,是这座城市最具魅力的文化印记。
结 语
人既是城市文化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作为一种城市的人格化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文化心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与城市文化息息相关。“不同城市人的个性、文化心理、行为特征、精神风貌、教养和趣味等,体现了城市文化的丰富性和不同的品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影视剧城市叙事中应当积极把握“人”与“城”之间的深层互文关系,以提升作品的叙事内涵与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