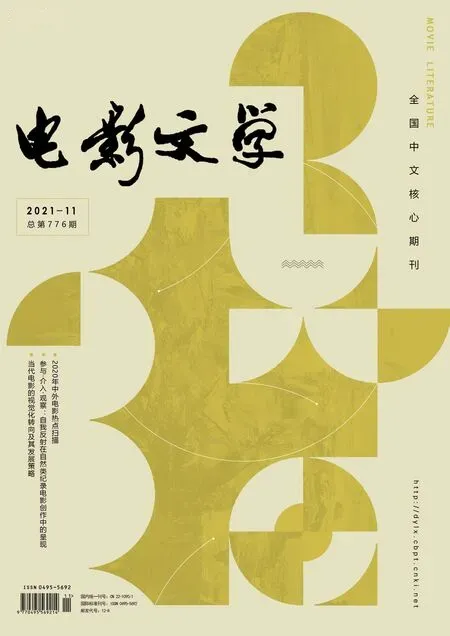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十七年”电影中的爱情叙事研究
秦凤华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爱情叙事在电影故事中可谓铺天盖地,举目皆是。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曾做过一个测验,随机抽样调查100部好莱坞电影,其中95部涉及异性浪漫情节。中国早期剧作理论家侯曜在回答“什么一类的影戏,最能得看客的欢迎”时,也说:“恋爱的故事是很能引起看客的兴趣的。近代的戏剧几乎以恋爱为唯一的要素。”侯曜还解释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因为恋爱是人的天性,所以拿恋爱的材料做影戏,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就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来看,在民国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影片中,爱情叙事普遍多见。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电影《劳工之爱情》(1922)和拉开20世纪80年代新序幕的影片《庐山恋》(1980),都是名副其实的爱情片。然而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中,也有一个历史时段的爱情叙事不那么多,不那么明显。这个时段就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究其根源,爱情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以革命和建设为动作核心的集体主义背道而驰。因此,总的来说,“十七年”时期爱情叙事并不流行。主要体现为两点:(1)爱情题材影片所占比重较小。只有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的1957、1958和1959三年之间,爱情片的出产量相对多一些。(2)对爱情的描绘极其节制。一方面,对谈情说爱场景的处理十分含蓄、隐晦。拥抱、接吻之类大尺度镜头在“十七年”银幕上几乎绝迹(部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有亲脸的镜头,如《草原上的人们》《山间铃响马帮来》);另一方面,淡化了爱情情节的浓度。爱情很少独立成章,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穿插在革命和建设的情节内容里,充当辅助成分。少数较为纯粹的爱情片,则立足于国家婚恋政策和主流婚恋观的宣传。以上种种情形,使得“十七年”电影中爱情描写的存在方式、艺术特征、价值诉求等,都呈现出异于其他时期的“别样”面貌。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十七年”电影中的爱情叙事划分为两大类别:爱情片中的爱情叙事和非爱情片中的爱情元素运用。前一类又可细分为三种情况:爱情与革命的双线叙事、爱情与建设的双线叙事、婚恋政策和婚恋观的宣传。基于以上类别的划分,本文从剧作分析入手,立足于爱情叙写与主流话语表述的关联,对“十七年”电影中爱情叙事的独特性做一番探讨。
一、爱情与革命的双线叙事
按照剧作常规,必须给人物的戏剧性需求设置障碍,才能产生戏剧冲突。在爱情叙事中,获取爱情无疑是主人公最重要的戏剧性需求。如何给他们的这一需求设置障碍,就成为剧作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说:“写爱情故事时,我们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什么东西会阻止他们?”他认为:“从希腊戏剧家米南德开始,所有的作家都用‘姑娘的父母’来回答上述问题。……莎士比亚在《罗密欧和朱丽叶》中把这一常规扩展为双方的父母。”在创作界,为了创新突破,电影编剧们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纵观中外当代爱情电影,爱情障碍千变万化:婚外恋(如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三角恋(如日本电影《生死恋》)、门第之别(如中国电影《桃花泣血记》)、种族差异(如美国电影《猜猜谁来吃晚餐》),甚至死亡(如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
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情形又如何?我们发现,适应主流话语的表述需求,在“十七年”的革命型爱情片中,获取爱情的障碍通常被设置为来自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或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而清除障碍的主导力量则被设定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由此,爱情元素被有效地糅合进革命叙事的框架内,形成爱情与革命的双线结构。
《新儿女英雄传》(1951)中,杨小梅本与牛大水两情相悦,却在母亲的安排下嫁给了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二流子青年张金龙。杨小梅起初之所以不能和牛大水走到一起,是因为牛大水太穷。牛大水穷的根源是什么?地主的剥削。影片开场第一场戏便通过牛大水与杨小梅的谈话对此进行了交代。所以,爱情的障碍物可被归结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后来,杨小梅在张家受到虐待,婚姻难以为继,杨小梅的人生陷入困境。恰在此时,革命的暗流涌进村庄,杨小梅被引上革命的道路。牛大水也参加了革命。当这一对有情人双双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意味着曾经横在他们面前的障碍物终将被清除,他们的爱情不仅拥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还获得了道德层面的合法性(革命者与革命者的结合,无疑是合乎道德的)。
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拍摄的《柳堡的故事》(1957),罕见地描写了一位现役军人与一名农村姑娘的爱情故事。爱情元素同样被糅合进革命叙事程序里。创作者设置了两个爱情障碍物。其一是二妹子被恶霸刘胡子看中。李进和他的部队深入虎穴救出二妹子,既是促使二人感情加深的重要事件,又附带宣扬了打倒恶霸地主的革命主题。此外,横在二妹子和李进面前的还有第二个障碍物:二妹子的身份。二妹子是群众,李进是革命军人,按照当时的军纪,他们是不能谈恋爱的。爱情变成现实必须等待二妹子身份上的升级。所以二妹子获救后,并不能马上和李进谈恋爱。只有当李进再回来(此时的他也当上连长),她已加入革命队伍并入了党,他们才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到一起。二妹子身份的变化,既是影片中这对恋人走向结合的前提,又确证了“十七年”银幕上普遍宣扬的“革命夫妻”的理念。
以上两部影片例证阐释的是革命战争型爱情片中爱情的困境模式及拯救爱情的机制。在古代题材爱情片中,情况有所不同。阻挡相爱男女顺利结合的障碍依然是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等强权势力的压迫。清除障碍的力量则由集体革命置换为个体抗争。
这些影片大都根据地方民间传说或传统戏曲改编,代表作品如《阿诗玛》《蔓萝花》《刘三姐》《彩凤双飞》《陈三两》《画中人》《借亲配》《乔老爷上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由于不存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主人公要赢得爱情,只能通过个人的反抗和斗争。无论是《阿诗玛》中的阿黑和阿诗玛,还是《刘三姐》中的阿牛和刘三姐,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中依赖的主要是非组织性的个人力量。虽然有的主人公获得了乡民的鼓励或帮助,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自我努力,而非像革命型爱情片一样,推翻恶势力的主导力量来自组织。此外,与革命拯救爱情的必胜结局不同,个人抗争的结果有喜有悲。在《蔓萝花》《刘三姐》《陈三两》《彩凤双飞》《借亲配》《画中人》等影片中,恶人或恶势力被打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在《阿诗玛》《红楼二尤》《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片中,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主人公要么一方身亡,如(《阿诗玛》《红楼二尤》),要么双双毙命(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无论结局如何,这些电影的主题意图都是一致的,一方面,歌颂了少数民族地区或封建时代的青年男女们大胆反抗强权的精神;另一方面,强烈抨击了旧社会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而这其实是“十七年”革命话语的另一个侧面。
二、爱情与建设的双线叙事
在被主流话语所规范的“十七年”银幕世界里,与“革命”并列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建设”。将爱情元素附丽在以生产建设活动为动作指向的情节线索中,便成为该时期爱情叙事的另外一大类别。
在农村题材影片中,爱情情节被穿插在人物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里。如,《牧人之子》(1957)讲述的是复员军人德力格尔带领蒙古村民修河,并在修河的过程中收获爱情的故事。《布谷鸟又叫了》(1958)的主人公是一群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和姑娘,爱情的悲喜剧在火热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展开。《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中,一边是年轻人修渠,一边是几对年轻人的爱情纠葛。在城市题材影片中,爱情情节则与主人公们所从事的城市职业活动相关联,这些活动包括工厂的机械装配(《幸福》)、科学研究(《悬崖》)、图纸设计(《青春的脚步》)和从医活动(《护士日记》《生活的浪花》)等。如《护士日记》(1957)和《生活的浪花》(1958)的主人公都是医务工作者,影片将他们的情感故事与他们在医务事业中的曲折历程并置在一起。
饶有趣味的是《五朵金花》(1959)。表面上看,影片着重叙述的是男主人公阿鹏对心爱姑娘“金花”的寻找,并没有明显的劳动生产线索。然而,细看五位金花姑娘的身份:积肥模范金花、牧畜场金花、拖拉机手金花、炼铁厂金花、人民公社副社长金花。原来,每一朵“金花”都将自己投身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活动中。创作者巧妙地将爱情叙事与劳动生产糅为一体。
在建设型爱情片中,创作者往往按照“生产决定爱情”的思路来设置人物特征和情节走向。具体表现为:
(一)以人物在劳动中的态度为标准划分正反面人物形象
凡是热情参加劳动和建设的,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对待爱情的观念也是正确的;凡是在劳动或工作中不热情或者不怎么热情的,都是“坏人”,爱情观也有问题。如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高占武、孔淑贞、茂林和小翠是影片人物主角中的正面人物,他们不但在修渠工作中克己奉公、尽职尽责,而且在对待爱情上也能做到坦诚相待、舍己利人。相反,反面人物李克明,不仅在劳动中懒懒散散、斤斤计较,在恋爱中也是见异思迁、无情无义。再比如,《护士日记》里,女主人公简素华和工区主任高昌平被刻画成正面人物,他们都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他们崇尚的是在工作中携手并进的爱情。而简素华的男朋友沈浩如,自私自利,脑子里只想着个人的得失。他对简素华的追求,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我占有欲的利己行为。
(二)爱情的成败取决于人物在生产建设中的态度
收获爱情的一定是积极分子,落后分子注定要失去爱情。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1)在一些表现三角恋或者是多角恋的影片中,故事的结局表现为积极分子与积极分子的幸福结合,落后分子虽然一心追求心上人但终不成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无私奉献、一心修渠的好青年高占武、孔淑贞、曹茂林、小翠都最终收获了爱情。而在劳动中消极怠工、感情上背信弃义的李克明一无所获。(2)本来相恋的双方因对工作的不同态度而造成感情的隔阂,再加上第三方的插足,两人的感情陷入危机,但持错误工作态度或有错误工作行为的一方幡然醒悟并改掉了自己的缺点、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爱情随之重获新生。如《青春的脚步》中,同在建筑设计院工作的肖平和女友林美兰由于工作上的分歧而造成了感情上的危机。美兰爱慕虚荣,在设计工作中追求华而不实的效果,而肖平在设计工作中实事求是,并对美兰的设计提出了批评,美兰由此移情别恋,爱上了道德败坏的彭柯。但最终彭柯原形毕露,遭到众人唾弃。美兰则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她和肖平的关系也由此获得了修复的可能性。(3)某青年由于对某种普通职业抱有成见,不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爱情生活随之受到影响。《寻爱记》中,零售公司的售票员李勇和百货公司的收款员赵惠同是先进工作者,两人在感情上自然相互吸引,一见倾心。而他们的同事马美娜、张士禄都瞧不起自身所从事的售货员的职业,二人在感情上也陷入了危机。总之,不能一腔热血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便不配拥有幸福甜蜜的爱情。
三、婚恋政策和婚恋观的宣传
“十七年”也拍摄了部分与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拉开一定距离的爱情片,这类影片的主要目的是对新中国的婚恋政策和婚恋观进行宣传。广义上说,所有的“十七年”爱情片都暗含着新中国的婚恋观,如,无论是革命题材爱情片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爱情片,都张扬集体主义事业中的情投意合,而非个人主义的两情相悦。这是当时很重要的婚恋观。此处将要讨论的,是一批比较纯粹的以宣扬婚恋政策和婚恋观为题旨的影片。
新中国成立之前,主导年轻人婚恋选择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1950年,国家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倡导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电影界随之做出反应,以一个个银幕故事对婚姻法的理念进行形象化的演绎。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儿女亲事》(1950)、长江影业公司出品的《两家春》(1951)、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妈妈要我出嫁》(1956),其主题意图都是宣扬婚姻自由、批判包办婚姻。
宣扬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新中国婚恋政策和婚恋观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张扬婚恋选择中的以人为本和道德至上,也是该时期主流意识大力提倡的。此内涵也在电影中得到了表达。
影片《如此多情》(1956)改编自小说《爱的是人,不是职位》。该片的主题内涵正是原小说篇名所概括的,选择爱人应该看人,而不是看职位。故事按“反例法”的思路展开,一位姑娘依仗自己漂亮的长相,一心高攀职位高的男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荒唐事之后,最终美梦破灭。影片所宣扬的“爱人,而不是爱职位”的爱情观,可谓新中国主流话语背景下的一种爱情路标。
《谁是被抛弃的人》(1958)是“十七年”时期另一部别有趣味的爱情电影。在城市做公务员的于树德爱上了别的女子,于是回乡与原配夫人杨玉梅离婚。影片的重心不在于发掘夫妻地位拉开差距后引起的感情问题,而在于对负心汉进行道德谴责。所以影片设计了战争年代杨玉梅不顾个人安危搭救于树德性命的情节,以表明于树德的移情别恋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此外,影片还把他与情人的恋爱设置为他施予对方的感情欺骗。按照主流话语下的价值导向要求,结尾处,于树德竹篮打水一场空:与妻子离婚后,又遭到情人的抛弃,最后还被撤了职。影片借此完成了负心汉罪有应得的主题表达。通过这类影片,我们可以窥探到,新中国主流意识将道德作为爱情活动中的重要砝码,否定个人幸福名义下的爱情追求,张扬以道德自律为基础的婚恋关系。
四、非爱情片中的爱情元素运用
以上三方面是“十七年”爱情片中爱情叙事的情况。一般来说,爱情片在内容上必然演绎一段或几段爱情的发展过程。在此界定下,“十七年”电影中的爱情片的确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许多影片虽称不上爱情片,却有意运用了爱情元素——要么设计一对正在恋爱的情侣形象,要么让男女主人公产生暧昧的感情。使得爱情如同岩石缝中的小花,在主流话语叙述的板块间见机生长,起到点缀的作用。
普遍的情侣形象的设计,造成“未婚夫”“未婚妻”角色在“十七年”银幕上广泛出现。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新中国电影并没有‘让异性走开’,大部分电影仍然遵循自然界和艺术界的一般法则——男女角色配对出现”。如工业题材影片《伟大的起点》(1954)和农业题材影片《农家乐》(1950)、《葡萄熟了的时候》(1952)、《丰收》(1953)等影片中,都有一对正在搞对象的青年男女。
而在让男女主人公产生暧昧感情的剧作程式里,“十七年”的创作者们对爱情进行了严格掌控,将爱情的展示降低最低程度。《渡江侦察记》(1954)、《战火中的青春》(1959)、《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三部影片对爱情的描写仅止于含蓄地表现男女主角互生好感,并没有展开实质性的恋爱场景。《渡江侦察记》中关涉爱情最核心的一场戏是,刘四姐采摘野花放在李连长桌上;《野火春风斗古城》中至关重要的爱情细节体现为,银环拨灯时听杨母说杨晓冬有了对象时紧张得烧了手。而在《战火中的青春》里,由于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近距离并肩战斗时一直女扮男装,所以爱情呈现在主体情节部分是缺席的。颇有意味的是,这几部影片都以男女主人公充满暧昧色彩的告别收尾。《渡江侦察记》与《战火中的青春》相似,男主人公随队伍出发奔赴新的战场,女主人公前来送别。他们道别的话,其实就是爱情的表白,只不过这种表白极其间接、含蓄。《野火春风斗古城》突破惯例,将二人的告别仪式从众人在场的空间抽离,由男女主人公在一个私密的场合单独完成。然而,对白被消减了,只剩下男主人的一句“好了,走了,这儿的工作都交给你了”。安排在女主人公身上的,则只有回应男主人公的一个点头。可见,在这些影片中,爱情的表达被弱化到一个很低的限度,几乎是点到即止,需要观众去感受、领会。
从观影的角度考察,非爱情片中的爱情元素主要功能是提升影片的趣味性。当一些影片的主导情节本身缺乏对观众的吸引力时,增加爱情成分常常就成为编导们的法宝。《伟大的起点》的故事围绕主人公改进炼钢炉的线索展开。内容的枯燥显而易见。为了增强可看性,编剧为男主人公设置了一位未婚妻,并将二人的婚约定在炉子改建成功之后。《丰收》《农家乐》《葡萄熟了的时候》专注于打井、种棉花、卖葡萄等农业生产活动,引不起观众的观影兴趣。于是,创作者在影片中都设置了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让他们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路上并肩战斗。战争题材的影片由于涉及生死,相较于工农业影片,制造戏剧性要容易得多。不过,增加爱情元素,往硝烟与铁骨的世界倾倒些柔情蜜意,对增加影片的趣味性而言也是有利无害。《渡江侦察记》以李连长带领队员完成渡江侦察任务为动作核心。敌我斗争带来的悬念感和紧张感,已能充分调动观众观看的积极性,然而编剧还是设置了“刘四姐”这样一位游击队长。其实,游击队长的角色由一位年轻女性来承担,多少显得牵强。但观众不会介意这种“失真”,反而饶有兴味。尽管全片没有直接的爱情描写,只通过刘四姐采摘野花放在李连长的桌上及影片结束处意味深长的告别来暗示两个人的情意绵绵,对那个时代的观众来说,已经是爱情的盛宴。同样,《野火春风斗古城》和《战火中的青春》重点展示的是战争情节,爱情元素的加入无疑增加了影片的趣味点。
在非爱情片中,爱情如同一种作料、一种调味品。在军事、工业和农业等主体情节中加入爱情作料,显示了“十七年”创作者提升影片趣味性的自觉,但我们发现,单纯依靠爱情作料,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丰富一部影片的戏剧性。或者说,爱情作料最多能锦上添花,但前提是先要有“锦”。《渡江侦察记》中跌宕起伏的侦察情节就是“锦”,李连长和刘四姐的爱情是添上去的“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有地下党员对敌斗争的“锦”,银环和杨晓东的爱情是“花”。而在《伟大的起点》《丰收》《农家乐》《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影片中,由于情节本身陷入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即便添上爱情的“花”,故事还是显得乏味。这一点,是不少“十七年”影片的软肋。
结 语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主体是以娱乐性为导向的商业电影。进入新中国,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影作为一种普及性强、宣传效果好的艺术形式,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作为诞生于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生政权,党需要借助文艺塑造形象、树立权威。正如无身份介绍,突兀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树立权威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便是利用媒体舆论和文学艺术为该执政党撰述一个合法、合理而又崇高的历史;就是在撰述这合法、合理而又崇高的历史的过程中,新中国电影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并且颇为成功的角色。”另一方面,通过大银幕书写新的时代精神,号召民众为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变得极为迫切。在这种情形下,电影的娱乐性被放逐到边缘地带,宣传和教化功能成为主导。为此,新中国打破民国时期的私营电影网络,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电影管理、生产、发行和放映体系,将电影业整合进一个高度行政化的垂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影片的创作都应将主流话语的传达作为题旨。爱情片也不例外。从而,“十七年”的爱情片要么是纯粹的婚恋政策或婚恋观的宣传,要么是将爱情内容与革命或工农业建设内容结合在一起。也是为了适应主流话语的表述需求,有的作品原剧本中本来有爱情戏,拍成影片时却将爱情线索删掉了,最典型的莫过于《红色娘子军》;还有的作品,改编自小说,原小说中的某段爱情叙述原本是重头戏,搬上银幕后这段爱情不见踪影,《青春之歌》便是一例。
总的来说,“十七年”的爱情叙事由于必须镶嵌在主流话语表达的机制里而显示出教条化的缺点,一些作品难免在故事模式上相互雷同,在主题表达上牵强附会,致使今天的观众看起来了然无趣。但也有一些作品能将时代主题恰到好处地糅合在动人的爱情情节之中,代表作如《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柳堡的故事》。这些电影既是带着明显“十七年”烙印的红色经典,又是百年爱情电影长廊中的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个别影片跳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常规,对爱情展开了别具一格的叙述。谢铁骊执导的《早春二月》(1963)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当年,这部影片被当作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草”受到批判。经过岁月的淘洗,而今它已变成许多观影者竞相收藏的“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