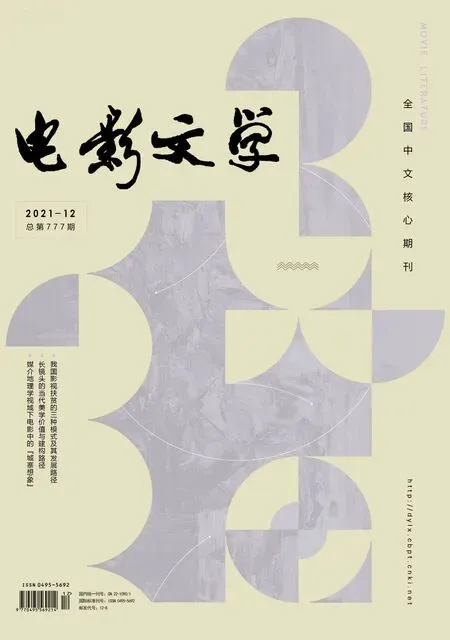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夺冠》的女性意识审视
孙 理(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海南 海口 570100)
性别理论认为,电影作为文化产品之一,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输出的有关观念,势必为男权中心话语所笼罩,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身份是被这种话语规范的。长久以来,女性从各类文化产品中接收到的大多是相对传统与保守的性别意识,如女性高度依赖于男性,即使成功也离不开对男性力量的借助等。这对现实女性的自我认同有着深远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所幸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国产电影开始体现出女性意识,并塑造出完整的、建立了自我价值的女性形象,开拓了中国电影的表现视野。由陈可辛执导的,展现中国女排精神的《夺冠》正是如此,在电影中,女性获得了可贵的主体地位和抗争力量。
一、女性作为自属者
所谓自属者,即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与精神有一种清晰的自属意识,换言之,就是明确自己并不是男性的附属品,无论在私域或公域中,都不应为男性所任意操控主宰。
在《夺冠》中,主人公郎平前后一共有三个身份,分别是中国女排队员、美国女排主教练、中国女排主教练,而这三个身份全是郎平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没有任何一个是依附男性而存在的。电影中多方位地表现了郎平的勤奋,如长期自己加练深蹲,以达到单次深蹲一百公斤的目标,又如在练球之余她还加入了当时的学英语热潮,报班读书等,对于自己在国家队期间要争取的位置和退役之后的去向,对于自己如何参与社会生活,实现人生追求,郎平始终有清楚的计划,并独立自主地完成。
她的自属意识使得,第一,她脱离了男权话语为女性规定的行为与气质期待。在性别建构主义理论中,“男女有别”并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更多是在一定社会文化中后天形成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习俗对两性的个性特征,责任意识和行为方式等都进行了规定。“社会制度坚持把男人和女人的所作所为‘规定’出不同范畴,产生对两性行为的不同期望和评价,并使这两个范畴相互排斥。一个人要么是男性气质,要么是女性气质,呈现出坚强与温柔、进取与依赖等二元对立。”坚强、进取,以及理性、主动、敢作敢为、职业化等,都成为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但是在排球运动中,郎平的潜能被充分释放了出来,她成为一个敢打敢拼,坚强果敢的“铁榔头”,有所作为,积极进取,最终成为排球界的精英与权威。《夺冠》中,在女排发展专家研讨会召开时,男性的记者、体育官员和体育学教授等在圆形会议桌边对郎平形成包围之势,然而郎平侃侃而谈,表现出这些男性所不具备的过硬专业能力、国际化管理方式和刚柔并济的领导艺术,毫不留情地反驳他们过时僵化的理念。尽管男性依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上风,但是女性已经参与进了话语权力分配中。
第二,郎平也没有屈从于男权话语为女性规定的母职与妻职。长期以来,家族伦理纲常压迫着女性,父权、夫权和族权共同以所谓妻性和母性来对女性进行支配,包括将母职进行崇高化和神圣化等,其本质都是要求女性抛弃个人利益与发展空间来为男性服务,以至于波伏娃甚至认为繁衍与哺育后代有碍于女性解放。在《夺冠》中,郎平的丈夫并没有出场,电影也没有安排任何角色与郎平发生感情,而女儿白浪也只有与母亲电话联系一场戏。郎平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但是她并不会因为承担母职而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女儿也对此表示理解,为自己的母亲备感自豪。郎平没有成为一个男性价值体系下,始终陪伴在女儿身边的母亲,她依然自由地选择职业与生活,母亲身份没有成为她独立人格与个性的枷锁。
还应注意到的是,《夺冠》中的郎平及其他女排队员并非是早年国产电影中“无性”化了的女性。早期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是以无性别状态呈现的“铁姑娘”式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革命者或女劳动者,是一种让人看不见两性差异的“空洞的能指”,这使得电影的女性表达其实是被消声了的。然而在《夺冠》中,女性的话语性别身份得到保留,女性并非男性的假面。如陈可辛特意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女排姑娘们集体去理发店烫卷发,光明正大地追求时髦的“红装”,又如她们给陪打教练陈忠和织毛衣等。在自属者的充分自信下,女性不必通过“男女都一样”,或让自己比男性更男性化来获取社会的认可。
二、女性作为强者
女性意识还包括了女性对自己价值、力量和优势的全面认识与充分肯定,摆脱自己在男权话语下的弱者定位。电影中将女性塑造为强者,能够有力地瓦解过往艺术作品中,女性在创造力上被压抑,在形象上被剥削,或被男性“凝视”的意识形态。如张艺谋的《红高粱》,西奥多·梅尔菲的《隐藏人物》都塑造了女性的强者形象。
在《夺冠》中,女性分别以集体和个人两种形式,完成了对男性的战胜和超越。在集体上,女排队员们的较量对象一般也为女性,但是电影中特意安排了一场大年三十晚上中国女排与江苏男排的友谊赛。从竞技能力上来说,男性无疑比女性更有优势,如女排中身高最高的郎平也只有一米八四,而男排队员们则不乏一米九以上者,更遑论力气、体能上的优越。因此江苏男排一开始仅仅将这视为一场表演赛,并没有打算“真打”,而身在男排队中的陈忠和也为女排们担心。然而在女排姑娘们的拼搏之下,尤其是在郎平“铁榔头”的威力发挥出来之后,男排们看到了女排坚韧的精神,终于开始认真对待。在这次对决中,女排成为精神上的胜者。
而在个体上凸显女性力量的则显然是郎平。在电影中,她与原为陪打教练,后来一度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陈忠和形成了一组对比。在年轻时,郎平就以自己在国家队时的拼劲震撼了陈忠和,而在各自走上教练的岗位后,郎平更是显现出了诸多优势,以至于陈忠和主动放弃了主教练职位的竞聘,以给郎平“让贤”。在两人见面时,陈忠和直接表示:“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坦承女性强于自己。郎平也表示自己就是“一意孤行”,“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等,从未对自己的能力和计划游移不定。
在此,女性不是“他者”,而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男性成为女性的陪衬,让女性在体魄、智力上大放异彩。并且难能可贵的是,女性的强大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因此两性最终走向的不是尖锐对立而是和解。
此外,《夺冠》还表现了主人公成为主教练后所带领的冯坤、赵蕊蕊、王一梅和徐云丽、魏秋月、朱婷两代女排队员,她们同样是作为强者出现的,并且在表现这些新一辈女性时,陈可辛有着另一种深入与贴近。如农村出身的朱婷,曾经尝试过皮划艇运动却因为腿太长而失败,终于在排球中完成了自我实现,彻底摆脱了原来困窘的生活环境;又如80后的老队员与90后新队员之间也曾有过矛盾,但最终在郎平的问卷中理解了彼此;从沙排转行到室内的张常宁一度难以克服转球时间过长的习惯,曾经在紧张下打破玻璃,但终于因为郎平的一句“宝贝儿,给你五秒钟把‘沙子’转完”而释怀。她们也曾哭泣,但依然以勤快的训练来解决问题,并且结下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又使得她们迸发出更可观的力量。在男性中心意识的引导下,人们不仅已经默许男性对女性居高临下,女性之间往往也相互鄙弃和敌对。就像凯特·米利特指出的那样:“妇女身上存在的少数人地位的特征:群体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对自己和对同伴的鄙视。”而在《夺冠》中,这种同性排斥与压制被女性战胜了,尤其是她们在赛前一起睡在漳州训练中心,彼此提供情感支撑的情景,令人动容。女性在这里的面貌更为多样,引发着观众对当代女性生存与职业状态的问询与思索。
三、女性作为“受害者”
张晓玲在《性别意识与参政决策》中指出,女性在拥有自属意识和对自身力量的觉悟之外,还应有一种受害者意识。这里的“受害者”并非狭义上的具体某事件的受害者,而是广义上社会资源分配,权力话语不公平状况,或者某种意识形态下的弱势一方。女性意识就包括了这种对自己与其他女性同胞被损害的体认。
在《夺冠》中,陈可辛委婉地表示了集体主义与金牌体制对女性的伤害(尽管男性也可以是集体主义与金牌体制的受害者,但在电影中力推变革的是女性)。如陈忠和初到训练基地,领队在为他介绍老女排的一号时说她:“出了名的要球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磨没了。”队员们为了练接球而手上被扎了毛刺,鲜血淋漓,而教练袁伟民也只是厉声说:“不许哭!”在郎平多年以后将车停在残疾人车位时,她更已是一个“有60岁的心脏和80岁的骨骼,脖子以下没有一块是好的”残障人士。而在身体的损伤之外,她们还承受着精神伤害。如当郎平带领美国女排战胜中国队后,中国观众却指责她是“卖国贼”,尽管她也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为国争光。
这种对女性是受害者的认识也并非一种自怜自伤的消极心态,反之,它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女性在意识到自己被对待的方式还有待提高后,是本着为自己也为他人负责的心态,采取纠偏行动而非一味抱怨,在女性的行动中,她们强大的内在自我与人生掌控力得到彰显。在《夺冠》中,郎平就在自己打破男性话语权威后,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保护与关照。在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后,郎平就声称:“排球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希望我的队员将来不仅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一个优秀的人。”对原本金牌至上的理念进行了反驳。对于自己手下队员陈鹿放弃排球考大学的选择,郎平给予了充分尊重。她甚至会主动提前结束训练,对女孩儿们说:“去谈恋爱吧。”当有队员表示:“我们事业心都比较重,拿不到冠军不谈恋爱。”郎平便开玩笑说:“你们这是球筐吧,真能装。”排球成为女性的享受而非负担,给女性带来的更多是发展而非戕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受害者”身份转变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女性成为中国发展的深度参与者。女性生命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萌发,是与变革意识紧密相连的。《夺冠》的明线是郎平的个人成长史,而暗线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今的巨大变迁史。陈可辛用几组时代感极强的镜头,以及郎平关于民众对女排胜利渴望下降的自述表示,在郎平完成外部世界的探索和内心的自我审视,终于走向成熟时,中国也充满生气地走到了彻底告别“东亚病夫”称号,因为全方位的进步而无须依赖女排来提振民心的阶段。女性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提醒着观众,社会转型与女性意识,现代意识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影像承载着文化,而文化本身则早已被打上了鲜明的男权烙印,这使得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女性往往只是“被讲述者”,她们是男性想象出来,供男性凝视的对象,与其说是真实的女性,不如说是一个个空洞的符号。而陈可辛则在《夺冠》中让女性拥有自属意识、自强意识和对自己被损害的认知,动摇着“男强女弱”的性别意识,让观众看到女性的光芒。这无疑对于电影人继续在体育乃至其他题材电影上继续改变女性形象,树立两性平等价值观,有着一种先导与示范作用。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