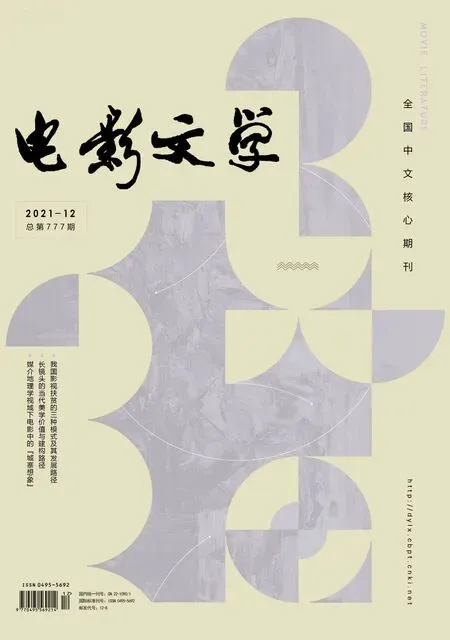新世纪初中国电影中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与时代书写
赵 浩 闫科旭
(1.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2.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重庆 400000)
进入千禧年之后,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蒸蒸日上。党和政府在关注国家整体发展、建设的同时,注重协调好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统筹城乡均衡发展,并将“三农问题”作为当前全党工作的中心。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视之下,电影作为记录时代真实性的影像媒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创作导向聚焦于“三农问题”。“‘寓教于乐’的最佳载体,电影无疑必须在令人惊奇的光影叙事中,承载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观众精神文化的历史重负。”因此,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对“三农问题”高度关注,将农村女性形象的变迁作为“三农问题”的缩影与表达途径,通过塑造丰富多元的农村女性形象来反映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的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内涵承担着远远大于她自身的现实责任与文化使命。农村剧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农村社会与历史文化观念的变迁,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中的农村女性形象作为现实镜像传达的载体,可以窥见我国社会的发展动态与农村女性的命运走向,并以农村女性在生存、情感、成长等层面呈现出来的“弱势”特质为横断面,展现农村女性在现代化语境中遭遇的不公待遇与生活窘境。
一、农村女童形象
“农村女童”一词作为属概念,其涵盖农村留守女童、辍学女童、被性侵女童等种概念,作为种概念的农村女童形象皆在新世纪初期电影中得到呈现。影片《上学路上》讲述了在我国西部地区辍学女童王燕想方设法筹集24.8元学杂费重返校园的故事,该片集中反映了农村男童与女童、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与发展机会不平等的现状。“我国农村女性……在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占60%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8年。”男童与女童在教育上的不公平待遇不仅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结果,而且还是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风俗习惯,贫困状况、缺乏妇女身份认同等多种因素在教育上的共同体现。如影片中的王燕妈妈对男童、女童区别对待,让儿子继续上学,却让女儿辍学,并在当地早婚风俗的影响下,为王燕介绍相亲对象。此外,男童与女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当前发展阶段必然面临的问题。“男女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是教育公平的难点,即使在发达国家,妇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仍然没有保证,在发展中国家,男女受教育不均等的状况就更为严重。”影片《上学路上》所反映的问题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的普遍问题,也是我国在发展阶段现存且正在发生的教育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国在实现总体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的同时,也要注重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努力协调整体与局部发展的均衡,从而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影片《如果树知道》讲述了遭遇性侵的留守女童小莲在老师的援助下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故事,该片从留守女童与被性侵女童两个维度折射出农村女童的生理、心理、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农村留守女童一方面是城镇化进程的产物。“预计2020年之前,流动迁移人口(包括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及新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每年增长600万~700万人。”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是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农村年轻人在面对农村贫困与城市“吸引”的情况下,选择了进城务工,即这些年轻父母在照顾孩子与生活之间,优先选择了生活,因此造成农村众多留守儿童的存在。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女童是由于农村女童的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困扰,部分父母进城务工时选择带男童进城接受教育,女童则留在农村由老人照顾。正如影片中的小莲弟弟就跟随城里务工的父母生活,而小莲却跟随年迈的奶奶在农村相依为命。“由于男女性别差异和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农村女童在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大多低于男童,加之留守家庭结构不完整、功能不完善、力量不足,留守女童渐渐地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留守女童的数量激增,这些农村女童多跟随老人一起生活。然而这些老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背景较贫困、对信息接收较为闭塞,并且在他们现有的认知中,只要保证孙辈最基本的衣食温饱即可,从而忽略了对儿童心理、生理、安全等多方面的教育。也就是说,这些农村留守女童的生活得不到有效监管,因此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成为各种恶劣事件的受害人。“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378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其中受害者为农村地区儿童的有112起,占比29.63%。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问题案件中受害人超过606人,女童遭遇性侵害人数为538人,占比为90.43%。”但由于此种案件的特殊性,在传统“贞洁观”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关乎女童声誉、家庭名声的事件,这些农村父母多选择沉默,放弃诉讼,导致性侵女童未被发现的案件也不在少数。正如影片中的小莲,在“性”知识匮乏与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被性侵之后产生的恐惧与蒙羞的心理,以及家人为了小莲的名声,一再选择隐忍,导致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最后小莲在老师的帮助下,公安机关才得以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农村女童问题关系到社会基础教育问题与基础安全问题,“女童问题既是儿童问题,更是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女童是处于女性生命周期初始阶段的特殊群体,女童的权利是妇女权利的重要内容,女童的生存发展状况是妇女地位状况的重要表征。”因此,新世纪初期电影中对农村女童问题的关注,即对新一代农村女性的生存与成长、命运走向等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被拐卖的农村女性形象
中国电影对于买卖妇女犯罪行为的揭露,早在“十七年”电影中便初见端倪。“十七年”电影中塑造了诸如《白毛女》中的喜儿、《祝福》中的祥林嫂、《武训传》中的小桃等被男人“物化”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们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自由地进行出卖和转让。“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启动,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开始浮出水面,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一度猖狂,甚至出现职业化、集团化的倾向。”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2018年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分别为9150起、7121起、6668起、5397起,而实际被拐卖妇女儿童人数远远不止这些。新世纪初期的中国电影继续聚焦于被拐卖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创作出诸如电影《盲山》中的白雪梅、《喊山》中的红霞、《嫁给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等被拐卖的农村女性形象。
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塑造被拐的农村女性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物化的私有物品
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塑造的被拐女性是贫困社会下的牺牲品,她们沦为宗族繁衍的生殖工具,作为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被出售,并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沦落为男人的私有物品,成功被男人所物化。“男女在社会权利和经济地位的失衡却导致‘物化’在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男性可以成功物化女性,将其作为个人物品进行自由买卖,但在这个以男性意识形态为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女性却难以物化男性。”在这一男女双方共同参与交易的活动中,主动权操控在男人手中,双方的交易地位不对等,当且仅有男人对女性进行买卖时,这场交易活动才可有效完成,并达到交易目的。因为这些被拐的农村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才能被物化,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可见,这种“物化”是单向的,是不可逆的,是男人对女性的“物化”。如影片中白雪梅被人贩子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黄德贵,白雪梅为了40元车费与小卖部的老板进行身体交易。山菊被人贩子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钟老汉,被人贩子拐卖的红霞也是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物品。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女性被出售、被交易,而男人则扮演着物化女性的买方。在这种境遇下,这些农村女性不仅成为男人的附属物品,而且逐渐丧失话语权,甚至被剥夺了自由生育与婚姻自主的权利,主动让位于男人并沉溺于男人构建的二元对立世界之中。
(二)封闭的道德空间
被拐女性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在电影影像的表达中,还是现实生活的境遇下,她们多生活在封闭的道德空间之内,并且不能逾越身体和世俗的红线。“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局限在家庭成员和亲属之间,族长或长辈所代表的父权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无处不在,并成为一种凝视的眼光和规范妇女言行的道德话语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当权力把身体和情感纳入一种体系化的规训体制中,这种社会空间就成为一个道德空间。”因此,这些被拐妇女在失去人身自由与剥夺话语权之后,牢牢束缚于由男人构建的农村道德空间之内,男人所构建的道德空间只是针对女性的生存空间而言,对男人的生存空间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他们依旧是道德空间、生存空间的主导者,维护着自我男权社会与男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这些被束缚的农村女性却把这种道德空间当成既定的规范与行为准则,她们依附、顺从,维护男人构建的道德空间秩序。如《盲山》中的白雪梅与乡村教师黄德诚相遇,白雪梅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但是黄德诚面对表弟对表嫂的“错爱”、表弟对表哥的愧疚、自责、两个家族之间潜在的矛盾等传统的道德秩序,最终未履行将白雪梅带离山村的承诺,而是默认了山村陈旧的伦理与道德秩序,将白雪梅抛弃在大山之中,自己从农村出逃。这也暗示着男人永远掌握着主动权,他们可以冲破道德空间的网络,选择逃离、出走,挣脱道德的束缚,将所有的指责谩骂留给女性——像白雪梅一样的女人。同为被拐妇女的陈姐在男权中心的威慑之下,逐渐认同并且屈从于男权社会的生存规则,尤其是陈姐有了孩子之后,逃离的愿望逐渐消失,成为男权游戏规则的守护人,并劝说白雪梅留在山区。“而对不愿意接受规训的人,谩骂和否定首当其冲,甚至没有人愿意去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她们的存在破坏了空间中的某种道德持续,对权力形成一种挑战。”福柯认为规训是现代社会权力的核心,发生作用的对象是身体,被拐妇女白雪梅、红霞长期遭受暴力、虐待与侮辱,男人对她们进行肉体与精神的控制,这些男人通过暴力完成对被拐女性的身体控制与身体惩罚,将她们幽禁在男权主义的道德空间之内。
(三)被看的欲望表达
电影叙事是根据男人意志进行的叙事,因此,在电影的叙事中男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正如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者劳拉·穆尔维所说:“电影的凝视是男性的,电影以男性欲念建立叙事,导致女性的缺席。”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对被拐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凸显了“看”与“被看”的欲望表达。在《盲山》《嫁给大山的女人》《喊山》等电影中所塑造的被拐农村女性形象,电影导演将她们置于男人“看”的视域之中,尤其是电影中某些大尺度镜头的呈现,如白雪梅被黄德贵父母按在床上,由黄德贵完成对白雪梅的暴力强奸行为,导演在这一叙事过程中,对女性身体的“看”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犯罪现场中当事人对女性身体的“看”,这种“看”是在银幕幻觉当中,角色彼此之间的看;二是影院里的观众对女性身体进行“看”的二次重构,需要将自身从银幕中剥离出来,从而获得视觉快感。劳拉·穆尔维认为:“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看的快感不平衡地分布在两性之间,形成男性=主动和女性=被动的两极化模式。决定性的男性凝视(gaze)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到女性人物身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地位不对等是与生俱来的,正如女性身份与性别均以男性身份与性别为参照系而得以确立,“看”与“被看”也是以男人视域为中心形成的不对等凝视,使男人的窥淫癖与性欲望得到满足。男女双方也正是通过看与被看、凝视与被凝视的方式,将这些被拐的农村女性继续放置在男人的视域中心,归属于男人构建的社会秩序之内。
三、女性农民工形象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逐渐觉醒,为了实现家庭与个人的发展,农村女性从原住地流动至城镇务工,流动比例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较上年增长0.6%;其中女性比例34.8%,较上年提高0.4%,女性农民工总量持续增长。”中国电影对于女性农民工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初露端倪,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过剩而沿海及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一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助力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时期电影中塑造了诸如《黄山的姑娘》中的保姆龚玲玲,《公寓》中的保姆秀娥、小琴、玉芬和惠芳,《给咖啡加点糖》中的补鞋妹林霞等女性农民工形象。“这一时期的电影对于改革开放带给农民工的机遇与挑战做了较为客观的反映,真实地再现了改革思潮下的农民工主体对乡下封建婚姻的逃离、对繁华都市的向往以及打工过程中所受到的猜忌与不信任。”而在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塑造的女性农民工形象相对前一时期的女性农民工形象而言,更能反映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女性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与弱势形象,在现代性语境中女性农民工的种种焦虑与失意。
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对于女性农民工形象的塑造,一方面,体现了新世纪农村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意识的独立,开始改变依靠男人实现救赎的历史地位,她们不再局限于农村狭小的生存空间,试图逃离男人中心主义的生存困境,她们积极实现自救。例如影片《碗儿》《安居》中塑造了碗儿、珊妹吃苦耐劳、积极奋进的女性农民工形象;影片《所有梦想都开花》《女模特的风波》中塑造了林芳、春杏积极向上、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农民工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农民工受到现实困境与心理困境等因素的影响,遭遇性别歧视、职业隔离等不公平待遇,并且缺乏一定的生存技能,她们在面对城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时,随波逐流,从而在城市沉沦,迷失自我。“当她们面对‘我是谁’‘我是怎样的’的问题时,社会生活经验重建的考验、‘显著性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影响让女性农民工难免陷入身份的焦虑。”在这一背景下,女性农民工从农村出走之后,在缺乏生存技能与生活保障时,只能凭借自己年轻的资本与肉体姿色将自己标注为可交易的物品。“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东西都被贴上了可交易标签,长期作为男权文化下的凯觎者的女性很容易被标的为欲望投射的对象,成为被消费和玩弄的对象。”这里的“物化”不再是前文所说的男人对女性操纵下的物化,而是农村女性在城市生活的激流之中自我贴上“物化”的标签,虽然在这一交易活动中,男人依旧扮演买方角色,但是和男人强迫女性“物化”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一个是暴力操控原则,一个则是自愿原则。如电影《租期》中在欲望都市中出卖自己身体的农村女孩莉莉;《泥鳅也是鱼》中的男泥鳅说服女泥鳅“晚上一起睡觉做个伴”,从而两人组成“临时夫妻”关系;《苹果》中在酒店做服务员的刘苹果,被老板性侵怀孕,并以此为筹码和老板进行金钱交易;《工地中的女人》中来自四川的打工妹玉兰,是包工头杜昆包养的众多情妇之一。这些影片中所塑造的女性农民工将身体作为代价与男人进行交易,从而成为她们扎根城里、赖以生存的筹码。
新世纪初期电影塑造的女性农民工形象初具女性意识形态,如:不甘驻留农村,不屈从于男人构建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相当清晰的反抗意识,一种决不甘居‘第二性’的姿态;但它又无疑是一种谬误与臣服的选择:它不仅仍潜伏在地接受了男性文化的范本,内在化了一种文化、社会等级逻辑,而且它必然再度成就了对女性生存现实的无视或遮蔽。”影片中的农村女性并未意识到逃离农村之后,在城市里却闯入更坚不可摧的男权社会。如影片《不许抢劫》中杨树根的老婆梅花跟城里人离开了贫困的农村;《上车,走吧!》中的打工女小辫子离开了农民工高明,坐上了有钱人的轿车。杨树根与高明代表女性逃离的农村空间,城里有钱人则代表更坚固的男权话语中心,牢不可破的男权统治秩序。同时,以上影片所塑造的女性农民工形象折射出当前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境遇,传达出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迷茫与无奈,无所适从与格格不入的生存危机,这些女性农民工的出走之路也反映了鲁迅笔下娜拉的出走之路,不是堕落,就是回家。
四、农村老年女性形象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年轻人口大量流入城镇,空巢家庭将成为我国农村老年女性主要的生活模式。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口中,共有空巢家庭1495.79万户,占农村家庭总户数的7.68%,合计老年人口约为2179.39万人,占农村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的32.69%。”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对农村老年女性形象的塑造,集中反映出当前我国存在的“空巢老人”现象以及农村老年女性的养老与赡养等问题。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人口女性化,将成为未来社会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农村女性的养老和赡养问题也随之而来。农村老年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存在,其他年龄阶段的农村女性较老年女性相比尚且有反抗与逃离的意识,而农村老年女性只能固守在土地之上,没有反叛的勇气与出走的能力,在生活上完全依附子女。由于子女多外出务工,因此,这些农村老年女性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产生一系列农村老年女性的赡养问题。
电影《喜丧》中子女对林郭氏的赡养问题,采取了子女共同承担、轮流到各家暂住的方法。林郭氏的养老问题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成员的活动往往围绕着女性老年人展开,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家庭内部各种矛盾的中心”。在商讨被赡养人和赡养方式的过程中,无人征求林郭氏的意见,林郭氏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听之任之。全权由男人(儿子)来决定,女人(儿媳妇)也试图参与其中,争夺话语权之时,却被男人拒之于外,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产生。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与社会结构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其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在身份、关系和观念层面发挥社会建构作用。”影片《喜丧》中的林郭氏便在老年女性身份、母子、婆媳家庭关系之间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的共同作用下,成为悲剧人物,最后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在《黄土地的守望》中空巢老人林奶奶的两个儿子在城里打工,林奶奶不仅得不到两个儿子的赡养,还要因为大儿子在城里误伤别人的事情奔走操劳。影片中空巢老人林奶奶的生存困境是众多农村老年女性生存现状的缩影,主要受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快了农村年轻人口流动的速度。“由于流动而产生的空间上的隔离,在客观上也削弱了子女所能提供生活照料的质量和频率。”造成了农村老年女性独居留守、“养儿防老”赡养难等问题,影片对农村老年女性的养老与赡养问题的关注,也折射出当前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政之本存乎于农’。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的首要之举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其生活水平和质量。”因此,解决农村老年女性乃至一切农村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本方法,就要采取发展农村经济、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优化农村环境等举措。
结 语
通过梳理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农村女性形象的类型,深入解读塑造农村女性形象的社会化意义。“中国妇女生活的社会化使她们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在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中证实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二是在男女角色的冲突中证明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这个时期电影中所塑造的农村女性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新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展现,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农村女性形象的变迁过程可以看作整个中国女性的发展缩影,以小见大,从点到面剖析了中国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生存现状,引人深思。归根结底,男女在生理结构上的差异是导致她们不平等地位的关键因素,也就是性别因素导致她们不能享受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女性要实现自我发展,挣脱男人设置的牢笼,必须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对自身社会性别的认同,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去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机会平等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身份的认同是以女性自身为主体,是自发的,而不是由男人和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