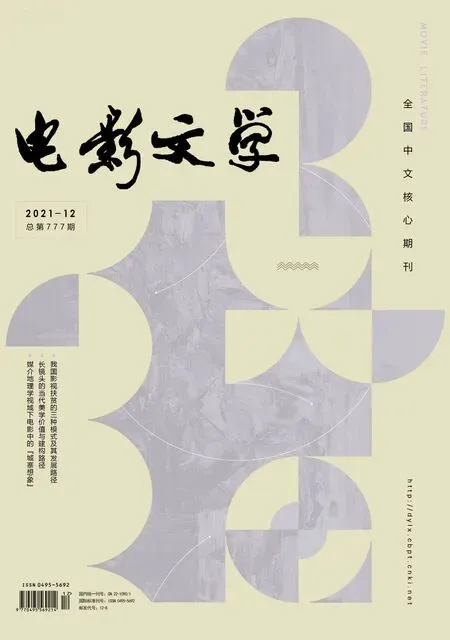仪式传播下韩国电影中的想象共同体构建
张冠文 刘 然(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信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不仅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还参与了人类文明的建设历程。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它通过视听符号传递价值,在一次次“集体朝拜”式的召唤中,凝聚每个观影个体对于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在世界电影蓬勃发展的浪潮下,近年来韩国电影格外引人关注。2020年上半年,洪尚秀凭《逃走的女人》获得了柏林影展最佳导演奖,随后韩国电影《寄生虫》更是一举拿下同年奥斯卡的四项大奖。在获得国际电影界普遍认可的同时,韩国电影的本土发展同样表现优异,从2001年开始韩国本土电影票房常年超过同期引进的国外影片票房,本土影视文化的独立性得以维护。回顾韩国影史,从1999年的《生死谍变》起,现实话题成为韩国影片的重要议题,朝韩关系、财阀干政、反抗侵略等现实主义的话题跃然银幕之上,小人物的视角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形成了仪式感、认同感、互动感三维一体以民族情感为核心的传播仪式,维护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一、基于平民视角与民族记忆的认同感构建
(一)平民视角的认同感构建分析
“传播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召集的前提在于让个体在完成精神自我的构建的同时达成社会自我的认同。传播仪式的首要条件是建立受众对于影片内容的认同,而认同感的建立首先体现为身份认同。近年来韩国电影将镜头聚焦于韩国底层民众,通过对底层人物生活经历的刻画拉近影片与观众的内心距离,电影在视听上的情景再现功能,辅以平民视角让观众产生最真实的触动感。在这一过程中,观影者被暂时性地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代入影片的角色情感,一起经历着银幕中的虚构事件,使得影片的意识共享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在光影仪式中完成了意识的合流,仪式下的情绪和思想受到电影情节的牵引和主导。偏重于现实主义题材的韩国电影剧情背后是大部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缩影,“在展现社会世情变化和反映国民心理期盼的同时,将韩国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与当今现代社会的价值文化体系勾连起来”。
平民视角是刺入事件内核的利刃,隐藏在平民视角这一刀锋下的则是影片蕴含的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文情怀,普通人的举动在电影镜头的聚焦下被放大,在特殊的仪式场域中被赋予特殊意义,引发观众对于行动背后价值观的考量。2016年大热的电影《釜山行》描述了韩国中产阶级在丧尸世界中的遭遇和抉择,与美式恐怖片《古墓丽影》和《寂静之地》相比其视觉效果虽然逊色不少,但作为韩国首部超千万人次观影的影片,它的成功在于没有将镜头对准人与丧尸的对抗,落入爆米花电影的窠臼,而是在绝境中注入人性的考量,爱和人性的探讨是艺术的永恒命题,这种触及人心的接近性加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影片最后,原本自私的父亲牺牲自己保护女儿和孕妇的画面成为公认的催泪一幕,人文主义精神构筑起了角色与观众内心的桥梁。
(二)基于民族记忆的认同感构建分析
历史是民族的根源,是民族的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在民众差异化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连接的作用,在媒介内容碎片化的当代,历史是共性的源泉,是想象共同体的根基。电影将历史重新演绎并传播给受众,对于生长于斯的民众而言,这种情景再现相当于是文化的二次传播,强化了民众的既有文化倾向。电影是民族历史的讲述者,将民族精神代代传承。电影《南汉山城》取材于“丙子胡乱”的历史,创作者没有纠结于主战还是主和,而是以旁观者的目光客观记录历史局势,并对朝鲜民族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各种应激反应客观剖析,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反思历史。
电影是民族精神的唤醒者。从电影《观相》中呈现的首阳大君政变,到影片《南山的部长们》讲述的1979年朴正熙遇刺事件,古今历史的描述不仅在于再现历史事件,更在于让观众与历史人物产生精神共鸣,感受观相师对待朝廷的赤胆忠心,感受南山部长为生民立命的反抗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支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支柱。电影以艺术性与媒介性重塑了民众心目中的历史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维护并建构着公众的想象共同体。
电影不仅再现历史,还构建着现实,达成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延伸。哈德罗·伊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传播具有时间空间偏向性,这一思想对于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影响深远。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观影途径逐渐丰富,影院观影、电视观影以及移动设备观影等多种观影方式的普及,延伸了影视传播的空间偏向,扩大了影视传播的范围;另一方面影片中历史内容的表达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这是维持民族统一的必要存在。电影不仅是讲述者与唤醒者,本身也在谱写着历史。韩国电影《熔炉》通过讲述儿童被性侵引起韩国社会的强烈反响,推动了被称为“熔炉法案”的《性侵害防止修正案》的推出。该电影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影片内容本身,其传播的时间属性得以扩展,在韩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由“表”及“里”的仪式感构建
(一)表层的仪式:观影环境的仪式感构建
从影视传播的情境来看,观影环境分为公开情境和私人情境,在此环境中电影通过表层的仪式对观众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
公开情境主要指电影院或电影节上的集体观影过程。在近似传统的仪式场域中,观众处在封闭的空间以及幽暗的环境里,银幕上的光影和音效是唯一的信息源,能够保证观众的视觉与听觉被锁定在银幕上。“黑屋效应”完成了从个体自我向社会自我的转变,观众的个性被暂时性地抹去。这种银幕“布道”的前提,需要电影本身的气氛渲染,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场景体验的需求。影院观众的集聚让个体有了社群心理层面的归属感,更进一步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观众自身的消费认同以及注意力被俘获,加之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无法及时交流意见,造成了其互动性与主动性的缺失,从这一层面上看是影片观点的单向传播,构成了集体仪式。此外,每年颁发一次的青龙奖、大钟奖以及百想艺术大赏电影奖作为国家层面的意义赋予,影片获奖象征着国家对于影片的价值认同,从而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神圣意义。“当下所有以庆典、节日为出发点而举办的仪式,本来就是为了制造奇观,将一个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现代神话楔入人们的心灵,使之在精神上、意识上对国家、社会和当下的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共鸣。”电影节起到了议程设置的效果,为观众选择了代表社会思潮和民族精神的作品。结合近年来韩国的票房成绩来看,人口仅五千余万的韩国民众,2019年观影人次达到2.24亿,而2019年中国年观影人次为17.27亿,数据对比之下体现出韩国拥有相对较成熟的电影市场、旺盛的观影需求,而韩国电影作为纽带紧密地联结了观众的想法。
私人情境主要指单独观影的过程,这一过程注重于构建拟仪式场域的主观态度和体验。通过分析单独观影的条件可以发现,个体基于兴趣爱好等因素做出选择性接触,在观影过程中同样需要付出视觉听觉的注意力为代价,通过观影完成心灵投射,并通过这种方式寻求精神上的归属感。在人类学家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仪式理论中,仪式“隔离阶段”参与者的思维进入影片剧情,暂时性地脱离了本身的社会身份与情绪,身份得以转化和重构,仪式参与者的社会心理也得以成长。传播仪式观中的传播是交流与共享,这不仅包括电影创作者与观众通过影片实现的思想交流,还包括这场光影仪式的参与者之间进行的观念共享。仪式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造成的交流阻碍,形成特殊的交融关系,为意义的交流和观念的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
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的目的是建构并维系一种有序的、充满文化意义的、能够容纳人类多样性行为的文化世界,本质上是一种以象征符号为中介、共享彼此经验的社会活动,建构社会现实与共同意识,从而实现社会整合,这也暗含了想象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充满象征符号的文化世界中的核心地位。
(二)内在的仪式:影片内容的仪式感构建
影片内容构建仪式感主要体现在影片内容呈现上。观影过程中,观众的情感与剧中人物实现了同频共振,跟随着剧中人物的心路历程参与进了影片的仪式化场景中。戈夫曼认为,个体的自我表征是在情境中被建构起来的,情境中的互动仪式推动了群体互动与群体团结,使得个人依附群体价值。在影视传播的语境下,这种情景体现为影片中的仪式化场景,个体将情感代入至剧情中,电影中对仪式性镜头的泼墨调动了观众的原始情感,使得仪式参与者的意识在电影铺垫的氛围中净化、升华。这种内容呈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对象征物的强调增加了仪式感。国家与民族对于个体而言是大而抽象的概念,在表达的过程中需要将概念转变为具象化的符号,对于国家想象而言,标志性的符号就是能够唤醒民众关于国家记忆的象征物。在电影《国家代表》中国家运动员佩戴国旗站在赛场,镜头的特写也给到了台下挥舞着韩国国旗的市民,在充斥着国家元素的氛围中影片迎来了高潮;同样地,在电影《隐秘而伟大》中,通过一首《临津江》将南北民众联系在一起,歌名“临津江”是处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上的一条江,歌曲抒发了对国家分裂的苦痛,以及对南北早日统一的深切向往。
差异性表达强化了归属感。仪式是塑造族群信仰和价值、维护族群共同情感的重要手段。电影《柏林》讲述一个朝鲜特工为救妻子投韩的故事,影片通过对朝韩双方人物的差异性刻画展现两国在政治意见上的矛盾。影片中充斥着政治斗争和暗杀的朝鲜形象,衬托出一个富有人情味与人文关怀的韩国形象。仪式能“在差异中强化自我认识。通过媒介的集体性参与,那种‘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性经验便不断地生产出来,成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的重现,为国家通过媒介强化认同提供了一个合理途径”。
从剧中人到集体的情感转化。在电影《特工》中,男主作为韩国派往朝鲜的特工结识了一位朝鲜朋友,双方意识形态相左,时代的悲剧下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影片末尾二人时隔多年再一次偶然相遇、无言相望,此时二人代表的不仅是人物本身,更指代了双方背后的朝韩两国在冷战的背景下被迫分裂。电影结尾主角两人站在体育场的两边,中间是喧嚣的媒体,媒体就像是由意识形态拉下的铁幕,两国在世界舞台上相隔而望,同根而生却无法统一。
三、虚拟的参与、实在的旁观——互动感构建
(一)作为虚拟事件参与者的互动感构建
韩国电影的信息接收与观影后的二次意义共享共同构建着传播的互动感。
信息接收阶段指的是观众的实际观影过程,由于电影视角的接近性与观影注意力的集中,观众的情感代入使得他们成为影片中虚拟事件的参与者,这种参与在于观众由临场感形成的虚拟事件的情感经历。声效画面营造的临场感可以模拟出无限接近于现实的象征性空间,影片对于角色的设置、视听语言的呈现以及饱含深意的象征符号承载了引起观影者共鸣的作用。信息接收阶段的互动实际上指的是影视创作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影视创作基于民众的文化背景,其作品也强化了民众的固有观念,同时加深观众的自我认识。电影《鸣梁海战》中面对日本的入侵,朝鲜民众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奋起反击,最终击溃强敌。影片对朝鲜民族英雄的英勇事迹重新演绎,激发了观众的民族热情,光影带来了最直观的情绪冲击。电影“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电影《国际市场》讲述了一个朝鲜战争时期的逃亡者的一生。影片中的朝鲜战争以及战后寻亲等经历是韩国民众普遍的民族创伤,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见循环过程:创作者为了作品的传播,尽力维护并凸显民众的共同想法,民众观影收获了创作者以及其他观众对观念的认可,自身的观念得以强化,创作者在后续创作中也会根据之前观众对于某观念的看法对接下来的作品阐述的思想进行完善,如此循环,达成对社会合意的不断巩固,想象的共同体得以维护。
传播仪式观的内核是分享、参与、理解,二次意义共享过程指的就是在仪式参与者结束了眼前的浮光掠影后,将影片内容或者影片思想分享给别人。这种共享一方面能够传递关于影片本身的信息,另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大范围内的意义的确认,观影群体之间的相互肯定能够更大程度上扩大影片思想观念的传达,同时也完成了从理论上的思想统一到现实中的意见统一的关键性跨越。电影《出租车司机》中以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视角带领观众进入1980年的光州,重温光州民主化运动——男主本是首尔的一名普通出租车司机,受外国记者的高价雇佣驱车来到光州,从一开始对学生行为的不理解,到后来挺身而出拯救抗击军事独裁统治的平民,影片描述了人物从事件旁观者到事件参与者的心态转变,也带领观众完成了精神的蜕变。
(二)作为旁观者的互动感构建
以上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了观众作为仪式参与者参与了影片的虚拟事件,而在银幕前,观众是作为这场视听盛宴的旁观者而存在的,这些旁观者的互动感建立于他们的共同观影体验。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曾指出,在群体团结下个体情感会得以升华,互动下的个体会形成特有的归属感和情感能量,进一步维护群体的思想统一。互动仪式的核心在于高度的情感联结,“简而言之。构成互动仪式的四个基本要素是身体在场、对外设限、共同焦点和情感共享”。观众之间共鸣的产生需要相互交流与意见趋同,这就要求电影的价值倾向与观众之间有足够的共通意义空间,社会互动才得以顺利进行,由此才能够使仪式参与者产生超越影片、立足现实并意蕴深远的意识联结进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电影为互动仪式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以优质内容形成集聚效应,在银幕面前暂时消弭了观众之间的意见差异,在情境的催化下顺利地进行意义的共享。在光影仪式中,观众是为了感知与沉浸而聚集,完成了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控到情境控制的他控的让渡,“在一场类似于精神催眠的‘自娱设定’中,心甘情愿地参与到电视所邀约的心灵狂欢盛宴之中”。本质上观众的观影行为形成了意见的螺旋,在群体认同的情况下不断强化价值观念,笃信影片传达的思想。随着流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观影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欢迎,在此过程中,即使身体跳脱了“黑屋效应”的环境,但电影本身依旧可以通过模拟象征性空间制造临场感。尤其近年来弹幕文化盛行,边看电影边发弹幕成为许多年轻人新的观影习惯,参与者们突破时空限制,在虚拟聚集的行为中,以随心所欲的信息互动来营造出仪式互动感。
结 语
自1999年韩国政府颁布《电影振兴法》以来,韩国电影通过认同感、仪式感以及互动感的多维构建,以仪式传播的方式在文化博弈中保卫了本民族文化,维护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仪式本身对于每个民族而言都至关重要,电影作为仪式传播的重要载体,有能力也有责任构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新世纪以来韩国电影对于想象共同体的构建效果显著,在传播仪式观的视域下,电影不仅是向观众传递影片内容,更是为文化建设与传承提供一条新思路。近年的发展中,我国电影市场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更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承担起构建想象共同体的重任,博采众长,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