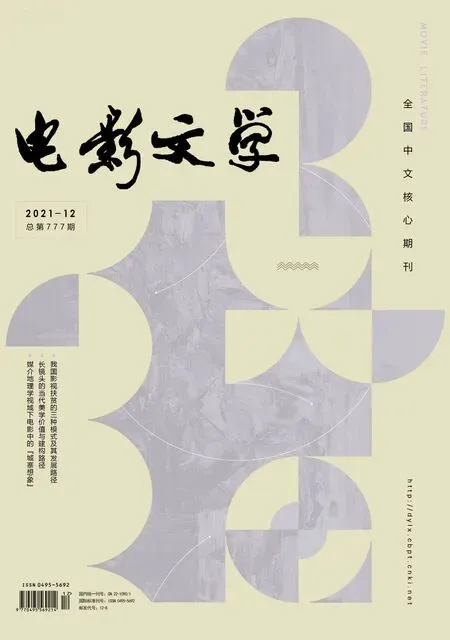媒介地理学视域下电影中的“城寨想象”
尤 达(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从地理角度观之,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百年历史中香港俨然成为英国的一块海外“飞地”,属于英国殖民地但不与本土毗连;而曾经位于香港九龙,面积约2.67万平方米的九龙寨城则成为英属香港时期的一块中国“飞地”。这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几经变迁,成为难民庇护地、三不管地区、记忆怀旧地等。由于身份复杂化、文化多样性、空间奇观化等,城寨颇具传奇色彩,也成为香港电影中反复书写的地方。然而,在1994年4月城寨拆除完成后,这种书写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许多香港导演不约而同地在电影中不惜工本重建城寨,海外导演也同样钟情城寨。这些电影中的“城寨想象”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多重的语境,从中既描绘出香港过去的图景,又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身份重构,更在全球化语境下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媒介地理学,“以人、媒介、社会、地理四者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从媒介生成,使用等基本关系出发,通过媒介呈现地理以及审视其中的人地关系,最终达到突破媒介与地理限制的目的”。立足该视域观察,发现电影中的“城寨想象”,是电影媒介对九龙寨城这座背负特殊历史身份、“所指”隐隐面向香港当下心态,且飘浮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寨,发起的种种“想象的地理”。
一、“城寨想象”中的空间建构:从边缘看中心的多元想象
“空间”指向了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两者“处于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之中,媒介空间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空间,同时又以—种‘想象’的能动性建构着社会空间”。关于“城寨想象”的空间建构便是媒介空间的形成过程。从社会空间审视,九龙寨城如同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城市“后台”,即“被统一的空间实践所排除或隐匿的部分”。这些“散落在统一空间之外的异质生活环境,正可以成为观察城市的对立地点,成为城市之镜”。换言之,从社会空间研究城寨文化可以反观整个香港,其媒介空间的建构也如同一面“城市之镜”,可以折射出媒介中的“香港想象”。福柯所言的“异托邦”指的是“由散布、并存于现实社会中的对立地点构成的镜像”。以此出发,从这“边缘”可以建构出通往“中心”的多元想象路径,这些想象依托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构筑起城寨这一异质空间。
(一)“地方志”史传想象:时代发展下的原型再现
“异托邦”的“地方志”所记录的是“各式‘异质’的人在一个‘异质’的场所的生存景观”。具体到城寨,香港电影中暴力的帮会、贪腐的警察、漂泊的难民构成了这个异质空间内的“生存景观”,海外电影则更多是“赛博朋克”风格下末世的科学家、复制人、机器人或者游戏玩家等。“不同的‘记述者/口传者’对于相关场景的‘复述’会有所差异,但包蕴在差异‘复述’之中的只属于该地方的基本元素却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无论是真实或者再造的城寨,空间的基本构成不会改变。然而,“香港社会的官民结构基本由帮会成员与警察组成,正是这种特定的现实,决定了香港警匪片的盛兴。”于是,在这个异质空间中,有一些出名的“外来者”警察与“居在者”枭雄构成的“生存景观”被不断提及,且“不同的记述者”复述差异较大。这一组组人物原型的再现,构成了时代发展下“异托邦”风格独特的“地方志”史传想象。
吕良伟主演的《跛豪》、刘德华主演的《五亿探长雷洛传》、刘青云和吴镇宇主演的《O记三合会档案》以及刘德华和甄子丹主演的《追龙》都在讲述香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原型人物的故事:“外来者”总华探长吕乐和“居在者”枭雄吴锡豪。这四部影片中,《跛豪》为吴锡豪传记电影,全片气势磅礴地再现了一段黑帮血泪史,在那横跨10年岁月的沉淀间,从城寨一隅触碰着整个香港的时代脉搏。紧随其后出现的《五亿探长雷洛传》,以吕乐为人物原型,既刻画了人物的奋斗历程,也描述了其颠簸半生的情感,总体观之,戏说的成分多了些。全片淋漓尽致地渲染出城寨的旧时气氛,令观众不由自主地沉浸入“城寨想象”。《O记三合会档案》于1999年上映,片子以“阿豪”和“阿乐”指代的两位原型人物,却更像是城寨内两个青年的奋斗发家史,与原型人物间关联度略低。不过该片在开始部分用相当长的篇幅回顾了城寨的真实历史。《追龙》于香港回归20年之际上映,影片不再执着于个人传记,而是聚焦香港人与英国人的对抗,深化反抗殖民压迫的主题。
“在‘地方志’形态中,所有的个体都将以自主参与的方式成为其‘同质化记忆’的一部分,群体性的生存样态是个体生存的唯一凭据,而个体对集体记忆的传承也即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有力证明。”从这个层面论及,上述四部影片无论是传记或者戏说,抑或是兼而有之,都成为九龙寨城这个媒介空间“地方志”史传想象中极为精彩的一部分。
(二)外来者的书写想象:罪恶化与妖魔化
对于“外来者”“异托邦”的开放性和排斥性共存。一方面,“‘外来者’总是会携带其所固有的‘生存模型’来观察和参与到‘异托邦’的空间之中”;另一方面,“外来者”“很难彻底放弃其原有的‘生存模型’而完全融入‘异在’的生存形态之中”。因此,“外来者”进入城寨的行为一般是暂时的,“并可能生成诸多的摩擦、不适应甚至矛盾”,最终任何改变现状的尝试都将失败。具体而言,这些“城寨”中的“外来者”大多为办案的警察、讨回公道的复仇者、揭开真相的解密人等。
从1983年的《A计划》到1993年的《重案组》,成龙饰演的警察两度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城寨。在这种媒介空间设定中,城寨时而是警察与海盗勾结的藏污纳垢之地,时而是绑匪藏身的庇护之所。“罪恶化”想象下,警察这种“外来者”很容易被城寨“‘拒绝’来自‘外来者’的任何试图改变此种‘异在’形态的全部诉求”,于是影片往往以某一起犯罪被扑灭为结局,而非改变城寨这个异质空间的形态。同样的影片还有《三不管》《低压槽:欲望之城》等。海外电影中,《银翼杀手》《环太平洋》均是“外来者”以警察的身份进入末世的城寨,此时不再为了消灭罪恶,而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前者需要知道“复制人”的下落,后者则要得到“怪兽脑袋”。换言之,此类末世电影中城寨已经不是最大的危机发生地,而成为未来人类生活的日常居所。
2013年,黄秋生饰演的叶问在影片《叶问:终极一战》中孤身闯入城寨,为友复仇,伸张正义。2019年,唐文龙饰演的叶问在《叶问之九龙城寨》中再闯城寨,为己复仇,自证清白。香港武侠功夫片中,侠客如同警匪片中警察,大多扮演着正义的角色,而城寨依然是罪恶的符号。两部电影不约而同地将城寨寨主作为邪恶之源,进而让主人公如游戏闯关般发起挑战,直至最终胜利。如此“‘外来者’以自身生存形态去影响和改变‘异托邦’的尝试”,得到了假想般的胜利。然而,武侠功夫片“所表现的那种草莽精神,和当代社会法制精神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事实上,此类影片在香港电影中已不多见,但这种囿于成见的罪恶想象却在西方电影中一再上演,如尚格云顿主演的《血点》、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蝙蝠侠:侠影之谜》等。
2006年李心洁主演的《鬼域》和2015年张家辉主演的《陀地驱魔人》两部恐怖片展开灵异想象,将异质空间“妖魔化”。九龙城寨的空间构造有着狭隘、破败、压抑、肮脏等特点,且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这些与“恐怖片中的古堡、废弃而幽闭的老屋”等不谋而合。《鬼域》以此营造出一个被遗忘与遗弃的空间,一个充斥着怨念的世界。主人公是一个解密者,身处“鬼域”后发现,其实自己是一切的制造者。即便如此,作为“外来者”,主人公“改变‘异托邦’的尝试总是会以失败而告终”。《陀地驱魔人》则通过主人公驱魔寻找事情真相,然后如警匪片、武侠片般将魔王生前设定在城寨,以此凸显邪恶。这两部电影中,城寨的空间设计局部还原度较高。
(三)居在者的书写想象:逃离情结与异样历史
“居在者”站在“刺激‘中心’自身的反思,其对‘中心’及‘外来者’而言,既是某种幻象,也是对其缺失的有效的补偿。”空间层面论及,“异托邦”与“中心”互为镜像,这使得来自“中心”的“外来者”与身处“边缘”的“居在者”,两者的书写想象也互为镜像。“城寨”中的“居在者”,往往是帮会成员、社会底层。“想象的目的绝不在于使‘异托邦’成为新的‘中心’,而恰恰在于以‘镜子’的方式‘映射’出‘中心’所自有的‘缺失’。”
事实上,早期黑帮电影《白粉双雄》《城寨出来者》和《省港旗兵》都通过帮会男性成员的视角看待着城寨。这些“居在者”“天然地拥有某种能够直接感知‘异托邦’特性的优势”,但无一不想“逃离”。换言之,这些影片对“城寨”的认同带有一种悲剧性的色彩,于是逃离异质空间成为主旋律。以《城寨出来者》为例,探讨的话题是从城寨出来的人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与最终结局,最终的答案是:有且只有宿命性的悲剧。此外,《懵仔多情》中的脱衣舞女天娇、《三不管》中的妓院老鸨阿玲和女儿、《三更之饺子》中的堕胎少女,都诠释着女性社会底层的“逃离”想象。如此,在警匪片中“异托邦”与“中心”的互为镜像体现为“居在者”帮会分子的“逃离”想象与“外来者”警察的“罪恶化”想象。从边缘看中心,城寨成为香港这座大都市的“城市之镜”。
另一方面,以原型人物创作的黑帮电影,如《跛豪》《三支旗》《毒。诫》等并无“逃离”想象,而是通过描绘异质空间内崛起衰落的奇特“居在者”,从另一个视角展现香港的异样历史。有意思的是,这种“异托邦”想象并非想“成为新的‘中心’”,但是由于“香港回归之前一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没有政党,由社会各行各业自发组建的帮派(有的沦为黑帮)也就大行其道,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或多或少带有帮派色彩,而维系香港社会秩序的主要是警察”,这便导致城寨枭雄成为风云人物,传记电影凭借媒介的影响力,使得“边地”历史的地位超过“主流”历史。时至今日,普通人记忆中的香港史往往会与这些电影发生联系。
二、“城寨想象”中的时间建构:从过去到未来的多重符号
“时间”代表着“媒介地理系统的变化与流动”,具体指媒介想象的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城寨业已消失,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城寨想象”的时间建构呈现两极化,即与过去和未来产生关联。“电影中的城市时间坐标总体上是扁平的,‘过去’与‘未来’同样被附着在空间符号之上,共同指向一种‘现在’的消费与狂欢。”于是对城寨过去的经验和体认,以及对城寨未来的符号化处理,“都被转化成碎片化、模式化、感官化的‘空间感’”。“城寨想象”正是以书写不同的时代背景完成这样的“媒介地理”的生产。
(一)存在于记忆中的过去
齐格蒙特·鲍曼指出:“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人们越来越希望回到过去,由此进入了一个怀旧的时代。”城寨拆除前后,电影中的“城寨想象”密集地出现,甚至城寨拆除后对于过去的回望依然愈演愈烈,本质原因在于怀旧。正如詹姆逊论述怀旧电影,以电影《体温》为例:“小镇背景有关键的策略作用:它使电影用不着可能令我们联想到当前世界、消费社会的大多数符号和参照。”
第一,孤城时代。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九龙寨城归满清管辖,直至20世纪40年代这里成为清朝军队的驻地。对于这段历史,香港电影中表现较少。1983年的《A计划》第一次表现“孤城时代”的城寨,成龙饰演的警察穿梭于城寨办案,因为复杂的地形产生一堆笑料。在这里城寨不光提供了时代背景,更因空间造型为影片增色不少。2009年的《十月围城》也出现了清兵把守的城寨,满清是革命的对立面,城寨归属为邪恶的象征。由于当时真实的城寨已然拆除,该片也并未去搭景再现,只是将之作为故事背景一闪而过。
第二,围城时代。抗战期间,日本人拆除了城寨的围墙。胜利后,露宿者开始在九龙寨城聚居,一堵无形的墙被建起,城寨与香港隔墙对望。有意思的是,反映这一时期的电影渲染的是一种温馨记忆。1973年翻拍的《七十二家房客》,影片的故事背景定义为广州市西关太平街的一幢破旧大院。实际上,该片是在邵氏的片场搭棚和旺角西洋菜街实景拍摄的,其中棚内搭设的房屋,造型参考的九龙寨城。《七十二家房客》站在20世纪70年代回望40年代的街坊情谊;2004年的《功夫》则互文了这种邻里温情,那旧日里小市民百态在“猪笼城寨”缓缓流淌。所谓“猪笼城寨”无非是粤语发音中“九”如同“狗”,以此解构演绎而来。这些影片都能透过温暖弥散的光线,滋滋作响的油香,狭窄弄堂的穿梭,面目模糊的人影,让观众回到过去,这便构成了对都市化香港的一种批判视角。当时代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唯有从媒介空间中去探寻美好的往昔。当然,对媒介本身,“这种‘回归’的本质是追求娱乐性,所有和谐悠闲的生活并非历史的本貌”。
第三,罪城时代。1948年城寨内的难民成功抵抗英国政府进入整顿,这里成为“三不管”地区。此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沦为帮会活跃地带,成为非法行为的“温床”。以《跛豪》为代表的一批带有传记色彩的电影,回望的便是这一时期的城寨。在这里,“城寨想象”的时间建构采用的是“回忆的模仿”,即“回忆不可能真正被仿造,而是可以对不同的回忆过程进行文学演示,以此产生一种模巧错觉”。这是一种对“过去”的仿真重构,通过模仿真实人物的回忆而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例如,《跛豪》从1990年11月赤柱监狱里的跛豪开始一段往昔回忆;《五亿探长雷洛传》让功成名就的雷洛在烟雾缭绕中回眸昨日;《O记三合会档案》从老年阿豪为警察讲述三合会和城寨历史梦回当年;《毒。诫》从1987年戒毒成功的陈华开启回忆;《追龙》则以画外音的形式开始,讲述人物自己的故事。此外,讲述同一时代的两部叶问电影中,《叶问:终极一战》采用儿子的回忆,讲述父亲叶问的传奇故事;《叶问之九龙城寨》则未设置叙述者,以一段倒叙开始故事。
第四,清城时代。1974年廉政公署进入城寨清理之后,九龙寨城不同于之前的混乱,但“城寨想象”的时间建构并未因为情况好转而停止“罪恶化”想象,而是开始根据真实案件进行改编。《省港旗兵》根据吴建东洗劫珠宝行案改编而成,《白粉双雄》灵感来自真实犯罪新闻,两作均聚焦70年代末的城寨;美国电影《血点》根据空手道宗师杜克·法兰的经历改编,表现了80年代初期的城寨;《重案组》则根据香港富商王德辉绑架案改编,描绘90年代的城寨。
(二)存在于拟仿中的未来
波德里亚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符号特征以“拟仿”为主,“和所谓真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它是自身最纯粹的拟仿物”。“拟仿”带来的是“超真实”。“它不再是造假问题,不再是复制问题,也不再是模仿问题,而是以真实的符号替代真实本身的问题;这是通过重复操作制止每一个真实过程的行动。”波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就是“拟仿”先行的文化,“既然超真实是一种以模型取代真实的新的现实秩序,那么模型就成了真实的决定因素,现实反而成为拟像的模仿”。根据该理论,以1994年城寨拆除完成为时间界点,此后的“城寨想象”中符号化的未来,是依据“模型”建构起由大量拟像组成的“超真实”世界,并以此引发现实中的效仿。
第一,浮城意象。1987年,我国政府与香港政府达成清拆寨城的协议,并于原址兴建公园。此后,城寨的“拟像”却始终浮现于电影媒介的想象之中。香港电影中,2005年开始的两部《黑社会》将帮派内部、帮派之间的斗争或博弈一一展现给观众,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社会之龙城岁月》。由于城寨已经拆除,全片未出现九龙寨城景观,但依然在用片名呼应着曾经的城寨。更重要的是,片中的城寨意味着曾经的道义正在帮会成员心目中消失。“以往的道德、理想在金钱的影响下不断退缩,那个英雄的时代已经逝去,接踵而来的是对金钱的崇拜。”正如片中的台词,“时代不同了,谈的都是生意”,这种“浮城意象”无疑充满着对过去的缅怀,它通过对城寨这个符号的传递折射着当下社会人的浮躁。除此之外,九龙寨城在海外电影中成为“赛博朋克”风格的代名词。“赛博朋克”(Cyberpunk)是“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朋克”(Punk)的结合词,指的是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的结合。早在城寨拆除前,1982年的《银翼杀手》便将城寨“拟像”化,以此构建未来的洛杉矶,此后更是成为此类电影的标准。“赛博朋克”电影将想象引申到未来,急切需要现实的“拟像”来缝合“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如此才能将超前想象与现实境遇相结合。九龙寨城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符号,城寨内不见阳光的黑夜、单一的冷色调、下着雨的街道、高楼下衰败的小巷,以及底层人的挣扎、痛苦、叛逆和反抗,与“赛博朋克”风格天然契合。
第二,危城意象。21世纪之后,随着内地发展态势的大好,香港经济转入低迷,一种“危城意象”随之诞生。反映到电影中,“香港被塑造成一个随时崩塌、烧毁、炸毁、成为空城、危机四伏的都市”。这无疑“展现的正是难以言表的香港文化身份”,而城寨作为曾经“罪恶化”想象的象征,无疑成为“危城意象”中一个典型符号。2006年的《鬼域》带有一种后现代的末世风情,城寨作为剧中人物大脑中勾画出的一座“危城”,最终在万物崩毁中重归虚无,然后再一次填充那些被遗忘的人和物,永不停息。2008年的《三不管》,则把叙事的背景放在了2046年,城寨的混乱让身处其中的人想要逃离。2015年的《陀地驱魔人》淡化了时间概念,但依然指向了未来,片中让九龙城寨彻底崩塌,以此反映对未来的焦虑。“危城意象”,“以寓言的形式展现了香港人想要追寻新出路,改变现有状况的迫切愿望,探讨了人的去留问题,呼唤秩序的重建。”必须看到,这种意象在当下的香港电影中颇为常见,但也必然随着内地与香港对话的持续推进而减少,香港的未来绝不是一座“危城”。
三、“城寨想象”中的地方建构:从凝固到流动的文化距离
“地方”是一个颇具情感的概念,“当人将意义投注于局部空间,然后以某种方式(如命名)附加其上,空间就成了地方”。换言之,其与自我认同、集体认同相关联,可被视为“认同的中介和归属感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表明“地方”原为是一个凝固的概念,本土性与排他性是其特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方”的概念,边界在不断打开。因此,考察“城寨想象”中的地方建构,无疑要从导演的认同,即他们与城寨本身文化的远近入手,按照从凝固到流动的发展脉络,描绘他们的想象路径。
(一)寨内导演个体寻根的文化认同
寨内导演,主要指两位有过城寨生活经历的香港导演:吴宇森和杜琪峰。从作品总体观之,他们的共性在于对城寨有着一种文化认同,即在一个地方生活所形成的对此地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自我存在的形成依赖于内生的、剥离了流动性与距离体验的地方,其中自我的地方体验式文化身份与认同形成的关键环节”。然而,两人一者偏向浪漫主义,一者更多的是现实主义,代表不同时期香港黑帮电影的人物银幕形象变迁。
吴宇森五岁来港,在城寨只是暂居,更多是在石硖尾贫民区长大,然而从他本人对儿时生活回忆看,记忆中的血腥与暴力与城寨文化如出一辙。“街上总有黑道的人拉年轻人入伙,你不去就揍你,我印象里流血是家常便饭,一出巷子口就遭到埋伏。”于是他的作品中将这种文化泛化为暴力的情绪符号,以代表作品《喋血街头》为例,开场一幕,年轻人之间的打架斗殴,血腥复仇成为家常便饭。另外,这种城寨文化又被衍变成一种浪漫主义。“当时我一些邻居小伙伴儿同样有正义感,只是做的方式不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人都是两面性的,后来我的很多作品中都会出现侠盗,我喜欢拍两个性格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成为朋友的双雄片”。因此在电影里他将帮派人物进行银幕英雄化转换,《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便是从城寨泛化出文化之根的。
杜琪峰与吴宇森不同,他在城寨长大,17岁才离开,耳濡目染之下对这里浓浓的世态人情和江湖道义有着深深的情结。首先,他的作品偏向于现实主义。不同于吴宇森“义字当头”的浪漫主义黑帮片,对杜琪峰而言,帮派不是美化的热血传说,而是隔壁的邻居和路上的死尸,是暴力压制下的沉默与秩序,是不明原因的仇杀或结盟。于是,他深受城寨文化影响,塑造出一个黑帮、警察、杀手共存的世界,且各方遵循着既定的程序和仪式,然后于其中人物走向必然的悲惨宿命。其次,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道:“我曾经住在九龙寨城……那里大多是屋邨,虽然人蛇混杂,但是充满浓浓的人情和江湖道义。”于是他的影片有一种对城寨深深的依恋,那是对过去江湖道义的依恋。即便城寨拆除,这一风格依然在杜琪峰的影片中延续。正如《黑社会之龙城岁月》中仅存的誓死捍卫帮规的肥雪,尽管在其他人物眼里这已经是一个神经质人物。
(二)香港导演集体记忆的文化召唤
九龙寨城对其他香港导演同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城寨是20世纪香港社会底层生活的一个缩影。于是他们在影片中发出文化召唤,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
萧荣、蓝乃才和麦当雄是最早发出这种召唤的导演,《白粉双雄》《城寨出来者》和《省港骑兵》用九龙寨城透射社会问题,“表现一群在港求生的小人物,无奈受尽黑社会迫害,而社会亦失去公义,他们愤而个人执法、以暴制暴,奋力挣扎反抗”。潘文杰的《跛豪》、刘国昌的《五亿探长雷洛传》等呼应的是吴宇森开启的黑帮片英雄时代。黑帮电影之外,王家卫、张之亮、黄靖华等导演也在城寨中寻找着什么。王家卫要找的是城市的疏离与人的漂泊和无根,《阿飞正传》对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投去惊鸿一瞥。折射的却是90年代港人疲惫不堪的灵魂;张之亮想要找到底层人们生活中的温情,《笼民》近乎白描般书写方寸之地的人情味;黄靖华用故事里的逃离表达着留恋,《懵仔多情》发起城寨拆除后的第一次港式回望。
随着城寨的拆除,集体记忆被再度强势激活,当观众无法目睹现实中的城寨,唯有依靠想象去还原地理。于是文化召唤显得更为有理有据,电影类型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黑帮电影,如霍耀良的《O记三合会档案》、王晶的《追龙》发出深深的怀旧召唤;又有武侠功夫片,如邱礼涛的《叶问:终极一战》、付利伟的《叶问之九龙城寨》,讲述过去的武侠神话;还有彭氏兄弟的《鬼域》、张家辉《陀地驱魔人》这样的恐怖题材,以及邱礼涛的科幻电影《三不管》等。
这其中,“城寨情结”最为深厚的导演是王晶,他是《五亿探长雷洛传》的监制、《O记三合会档案》的编剧、《追龙》的导演。特别是2017年的《追龙》,他为了真实再现,花费数千万元和两个月时间实景搭建了一座九龙寨城:大到商铺招牌,小到一张报纸,每个道具都经过认真的挑选,做旧。逼仄的巷子、摆放随意的茶水摊、灯光昏暗的赌博及吸毒场所,将特有的生活场景精细呈现出来。更有意思的是,影片中以城寨内不时出现的飞机呼应叙事节奏,这既是生活场景的再现,也是故事中人物命运的隐喻。
(三)异域导演东方奇观的文化图腾
异域导演主要来自日本和美国,按照文化距离的远近幻化出不同的关于东方奇观的图腾。
日本在文化上与我国有着同根同源性,加之历史原因,始终在关注城寨。九龙寨城被拆除后,甚至还在神奈川县原样仿制,连里面的涂鸦都是一样,据说材料都是直接从九龙寨城买下空运来的。因此,早在1977年野田幸男的《骷髅13:九龙之首》便第一次展开“城寨想象”。其后,这种想象大多在动画电影中被描绘。1995年押井守在《攻壳机动队》制作前,带领团队到香港采风,目的就是一睹九龙寨城风貌。2005年森田修平的《捉迷藏》、2013年木村尚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香港九龙财宝杀人事件》等则借用了城寨的概念。总体观之,日本电影中的“城寨现象”是在东方思维下展开的,即站在东方的“地方”概念下,几近真实地去还原。例如,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中未来都市的一部分,完全是真实的九龙寨城:破旧密集的筒子楼,鳞次栉比的汉字招牌,遍地污水的狭窄通路,甚至“乌云压顶”般轰鸣着低掠过房顶的巨大飞机也被再现出来。
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的“赛博朋克”电影是西方导演在想象“城寨”,不可避免地站在西方的“地方”概念下,将城寨转化为一个异质性存在的“他者”。1988年纽维特·阿诺导演的《血点》,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概念的西方化读解:城寨有着难以描画的、只属于香港的独特风情。雷德利·斯科特、克里斯托弗·诺兰、吉尔莫·德尔·托罗、斯皮尔伯格的“赛博朋克”电影,则将这种独特风情指向未来,在对城寨的罪恶性、混乱性进行充分征用的同时,城寨本身的地域性、日常性未被保留。换言之,这些都是西方思维与城寨元素的简单嫁接,以未来的名义将西方价值观嵌入神秘的东方,其间城寨“地方”的概念如同其本身一样消失殆尽。也许曼努尔·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全球性对地方性的取代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
四、“城寨想象”中的景观建构:从真实到虚构的变化演进
“景观”,即“媒介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媒介本身既从属于景观社会……又反映和呈现景观,并不断地塑造和建构景观社会。”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景观如何在媒介中呈现出来,置于电影维度思考,便涉及出品公司的选择。具体而言,“城寨想象”中的景观建构,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借代诠释、真实取景和灵感再造。
一是借代诠释,即并非拍摄真实的九龙寨城,而是以城寨的空间造型为蓝本却借景拍摄讲述其间的故事。如前所述,最早出现于邵氏公司于1973年翻拍的《七十二家房客》中。该片如此做的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地域相同却文化迥异,香港人看待城寨人的心态有些复杂,非常希望展开电影想象;其二,城寨自身既有视觉特色,又具文化内涵,也适合展开电影想象,但贴着“生人勿入”的标签,让电影实拍并不现实。所以,邵氏此举在将城寨作为“能指”,“所指”指向20世纪40年代社会小市民的众生相。此后,大量电影中出现这种借代诠释,如美亚电影等出品的《岁月神偷》,故事背景设定的是临近的九龙深水埗永利街;Black Canyon Productions出品的《新难兄难弟》则讲述春风街的故事,两者的房屋造型都有着城寨的身影。有意思的是,这种借代诠释在此后的香港电影中,九龙寨城不再作为“能指”,而是成为“所指”。特别是1994年城寨拆除后,这种现象因城寨的消失而大量涌现。例如2004年华谊兄弟出品的《功夫》,再造了一座“猪笼城寨”,2006年寰宇娱乐的《鬼域》、甲上娱乐的《三更之饺子》等影片中所出现的景观,“所指”也为九龙寨城。
二是真实取景,主要为警匪片,此时的“所指”与“能指”合一。九龙寨城的存在为警匪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因此,第一次走进城寨取景拍摄的影片,是1978年恒发电影的警匪片《白粉双雄》。该片客观地描述出城寨内下层市民的生活全貌。1982年,邵氏出品的《城寨出来者》更是被誉为“不能重拍的经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全景、最直观、最彻底展现九龙寨城生活景观的影片。由于该片的实景拍摄占比较高,已经具有史料价值。此后,1984年宝禾影业的《省港旗兵》、1988年美国Cannon International的《血点》、1990年影之杰的《阿飞正传》等一系列影片均在城寨内实景拍摄。1993年嘉峰出品的《重案组》成为最后一部留下城寨影像的电影,其史料价值已经远远超过电影本身。
三是灵感再造,指的是以城寨为蓝本想象化地模拟出场景,此时的“所指”与“能指”断裂。这指向的是“赛博朋克”电影,美国华纳兄弟非常喜欢从九龙寨城中获得灵感,以此完成此类影片。最早的是1982年的《银翼杀手》,其后是2005年的《蝙蝠侠:侠影之谜》、2013年的《环太平洋》、2018年的《头号玩家》等,都将城寨作为构建未来高科技控制下“赛博朋克”城市的灵感来源。香港电影中蕴含“危城意象”的几部影片也在以城寨为想象蓝本,拟仿着未来。
“城寨”想象中的景观建构,是通过电影媒介完成想象中的城寨地理与或借用、或真实、或再造的场景相交会。无论这种景观建构与真正的城寨相差几何,但至少电影通过其技术手段,完成了媒介对城寨的描述和解释。毫无疑问,“在用于表现和建构地理的媒介样式中,电影是一种相对完美的手段”。
结语:“城寨想象”中的尺度建构
“城寨想象”中的尺度建构为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四个维度的想象提供了标尺。从以上四个维度的研究发现,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围绕“城寨”所发起的“想象的地理”,其背后潜藏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且与香港城市的变革密切相关,更是指向了全球化。这便涉及“联系媒介与地理最重要的两个尺度”:本土性联系着地方,全球性关联着世界。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本土性在无差别的景观和压缩时空的传播中面临重重危机,体现地方个性和特色的内容逐渐被淡化,全球化对本土性的消解成为不争的事实。”真实的城寨消失之后,关于城寨的本土化想象正在淡去。当《功夫》以“猪笼城寨”代替曾经的九龙寨城,当《十面围城》无暇顾及城寨的真实外貌,观众唯有从《追龙》中隐约回忆起城寨的一草一木,可是这些回忆透出“虚假的历史”。事实上,1994年之后唯有杜琪峰的影片中虽不见城寨但饱含情结,余下更多地或者走向“危城意象”,或者填塞“外来者”的“罪恶化”“妖魔化”想象。换言之,一方面,城寨的消失使得媒介的想象唯有向着“浮城”靠拢;另一方面,“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跨越地理边界生产了一种‘无地方感’的社群,以及一种异化的感受和再现方式”,势必消失的“危城”阴影当下正笼罩城寨。于是,“城寨想象”必然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地域的跨越和边界的消失”而转型。关键是这种转型中文化的拥有者并不具备话语权,当城寨与“赛博朋克”相关联,由此引申出的“全球化”想象让人啼笑皆非。格洛利亚·安扎杜莱和凯利·莫拉加将由国际接触的加速和增多而导致的文化称为“混血”文化。从这一角度论及,不能为“城寨想象”所产生的“混血”文化一味叫好,毕竟这里的想象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已经将城寨重建完成,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城寨“全球化”想象该是从日本发起呢?
因此,从“城寨想象”中的尺度建构角度看,在本土化难以维系的当下,与其一味走入历史,不如着眼未来。一方面,仅就香港电影本身论,“赛博朋克”风格早已出现。受到漫威风靡世界的影响,1993年杜琪峰导演的《东方三侠》便有着浓厚的“赛博朋克”混搭“蒸汽朋克”的味道。在中国科幻电影崛起的今天,融合内地和香港电影人的力量,发展有着城寨元素的“赛博朋克”电影,不失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城寨想象”全球化发展体系更为重要。这里漂泊者的人生故事没有说完,多元化的景观可以呈现,在城市急遽变迁中,提取城寨的新内涵,可以在历史和未来、本土和全球间构建起通道。九一一事件中消失的“世贸中心”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至今熠熠生辉,这无疑为电影中的“城寨想象”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