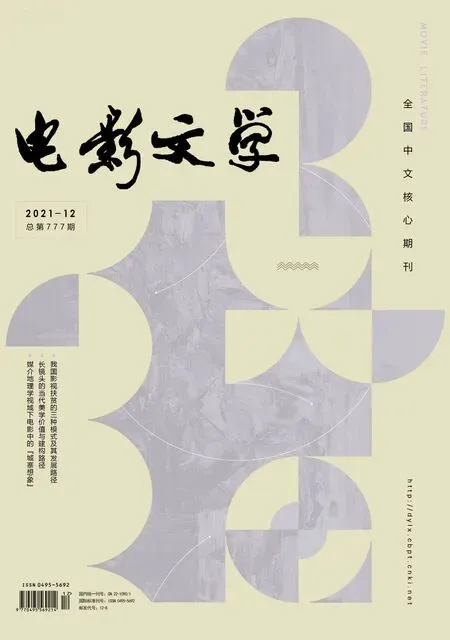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贵州空间建构
毛 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对贵州的关注与书写明显增多,特别是随着毕赣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饶晓志的《无名之辈》,陆庆屹的《四个春天》等名作的出现更让“贵州电影”跃入了中国电影视域的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贵州影像呈现银幕,中国电影中的贵州区域空间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呈现出独特的区域空间样貌。这一空间样貌至少包含三个维度:地域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
一、地域空间
(一)喀斯特山地空间
贵州多山,92.5%的土地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贵州北有大娄山,东北部有武陵山,中有苗岭,西有乌蒙山,高山峡谷,群山绵延,气势磅礴。在有关贵州的电影作品中,也几乎无山不贵州,喀斯特山地是贵州典型的影像空间特征。加之贵州地处低纬度亚热带季风气候,林木繁盛、四季苍翠、生机盎然,截然迥异于“西部电影”中黄土高原、大漠孤烟、沉郁厚重的西部影像空间及其特质,
形成了中国电影影像空间的独特一隅。《我的长征》《遵义会议》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湍急赤水、险要娄山等成为推动影像叙事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话语表述的重要场域。《阿娜依》《云上太阳》《鸟巢》《滚拉拉的枪》等原生态电影中的缭绕群山、参天古木、自然村落又呈现出贵州幽深古朴、与世无争、宁静祥和的一面,是电影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民族群体心理、行为习惯生成的重要空间环境。如果说山林是贵州山地地表风貌,那么山洞则是贵州山地地下风貌。一方面由于贵州喀斯特地质特征,贵州的山形成了很多自然溶洞,《马红军》《云下的日子》中的山洞是电影叙事的重要场景空间,隐现出偏远、阴森、恐怖的影像氛围;另一方面依据生产、生活需要,贵州人依山开凿修建了许多洞居、涵洞、隧道等,且由于贵州多雨潮湿的气候影响,贵州电影中呈现的山洞总是湿漉漉的,幽静的滴水声和幽暗中刺眼的灯光幻化出一种神秘、空灵的影像氛围。
正是这种独特的山洞空间营造了毕赣《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独特的影像气质和叙事风格,可以说贵州的山、洞地域环境成就了毕赣,成就了毕赣电影。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贵州总体呈现为一种奇特、神秘而富有诗意的异域风光。
(二)农村乡土空间
乡土景观与乡土气息是有关贵州电影的又一重要地域形象。在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全面深化的新世纪,贵州电影中仍比较少见现代化的都市影像,即使如《扬起你的笑脸》《炫舞天鹅》等现代叙事电影,在影片开头部分高楼林立的城市场景空间之后,镜头立即转进周边城中村似的民宅一隅,似乎有意躲避对贵州的都市书写。《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故事发生地是黔东南州府凯里,但影片中丝毫看不到现代城市的街景,弥漫整部影片的是神秘的山洞、乡土的山野,泥泞的山路,裸露红砖水泥的民宅,其中《路边野餐》中的人物洋洋一心想逃离乡土荡麦去往城市凯里,但她不知道凯里和荡麦一样同是野人时常出没的乡野。乡土空间成为贵州电影的主要叙事空间,无论是《滚拉拉的枪》《鸟巢》《开水要烫,姑娘要壮》《行歌坐月》《阿娜依》《云上太阳》等原生态艺术电影,还是《马红军》《苗山花》《少年邓恩铭》《文朝荣》《水凤凰》等主旋律电影,抑或是《剑河》《卧槽马》《嗨起,打他个鬼子》《追凶者也》《我和我的家乡》等商业类型电影均为乡土化书写。在这些电影中,贵州乡土空间呈现为两种符号建构倾向:一是在《阿娜依》等原生态电影中,古朴别致的民居、郁郁葱葱的乡林、高低蜿蜒的小路、层层叠叠的梯田,美如人间仙境,宛如世外桃源,贵州被建构为令现代人向往的异托邦世界;二是在《云下的日子》《青红》《我11》《闯入者》中,贵州在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并置中,又被指认为贵州人出走、外乡人逃离的失落地。两极分化空间建构的都是贵州被观看、被消费的他者化角色,以迎合现代观众对贵州的刻板印象与现实想象。
(三)少数民族聚居空间
少数民族聚居是影像贵州中的另一抹地域色彩。贵州省虽不是民族自治省,但全省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56个民族成分,17个世居少数民族,创造了“一山不同族,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民族文化奇观,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成为新世纪贵州题材电影独特的地域空间景观。《滚拉拉的枪》《鸟巢》《阿娜依》《云上太阳》等电影中的苗、侗木质吊脚民居依山傍水,鳞次栉比,掩映在绿色的山林中,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特别是侗族的鼓楼、风雨桥、歌坪是贵州标志性民族建筑,与《水墨青春》等电影中的屯堡石质民居相得益彰;《滚拉拉的枪》《阿娜依》《云上太阳》《侗族大歌》《阿欧桑》《我们的桑嘎》《行歌坐月》《好花红》等电影中的芦笙舞、木鼓舞、锦鸡舞、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布依民歌等可谓五彩纷呈,其中《滚拉拉的枪》中的酒歌、情歌、劳动歌、送客歌、指路歌可谓苗歌汇集本;《云上太阳》《滚拉拉的枪》《苗乡情》等电影中的驱邪仪式、丧葬仪式、成人仪式、洗寨仪式等呈现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朴素信仰与生活哲学。除此之外,还有贵州题材电影中的少数民族服饰、语言、节庆等也是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空间的重要景观。但这些电影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也存在表面化、浅层化问题,民俗罗列超越影像叙事,景观呈现多于文化反思,故事建构沦为了民俗奇观表达的工具性载体,电影深入文化肌理关照民族文化当代价值不够,正如有研究批评贵州籍导演欧丑丑的原生态电影:“大规模、大场面、高密度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展示制造出新的视觉狂欢,并且呈现出日常生活景观仪式化、景观仪式日常生活化的特点。”
二、精神空间
(一)朴素的生态理念空间
新世纪中国电影中呈现的贵州是生态贵州、绿色贵州,乡土贵州。贵州人秉承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哲学,在他们的理念中,自然和人一样是生命体,自然和人相互依存。他们深知人依赖自然而生存,人取之于自然,必感恩自然、崇敬自然、回馈自然。在贵州一些少数民族中,仍保有对自然的图腾崇拜。如原生态电影《云上太阳》中,丹寨苗人信奉锦鸡图腾,世代谨记“山是祖先的身体,田是背,泥是肉,田里的水是祖先的血、是祖先的汗、是祖先的泪”,破坏自然就是亵渎先祖、亵渎神灵。《滚拉拉的枪》中,树是岜沙苗族人的重要图腾,人出生要种一棵树谓之生命树;成人礼要举行专门仪式祭祀树神;人死后用生命树做棺材,并在平整的坟墓上种上一棵新树,人的一生与树紧密相连,取之于自然,必育之于自然。滚拉拉为了挣钱买成人礼的猎枪,打算砍柴用独轮车推去集市卖,被寨老制止。寨老告诉滚拉拉,村里的规矩是柴不能用车推,只能用肩挑,砍的柴够用就行,不能太贪,一树一木都是神灵。在《鸟巢》中,岜沙少年贾响马将鸟视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给幼鸟找食、喂食。尽管响马急着去北京找父亲,但听说一只雕受伤,仍急忙赶去先救雕,并在寨老的帮助下,和小伙伴们一起为雕捣药敷伤。当他在北京看到正在修筑中的奥运场馆鸟巢和无处可栖的鸟儿,他告诉记者,等回家后要比着北京的鸟巢,在自己村寨的林子里,盖一个真正给鸟住的鸟巢。在《阿娜依》《阿欧桑》《行歌坐月》等作品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贵州人的这种生态理念是朴实而执着的,甚至带有某种原始信仰的宗教意味。
(二)积极的生命信仰空间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中,贵州人积极、乐观、豁达的生命观让人温暖而感动。根据贵州晴隆真实矿难事故改编的《幸存日》中,老井王退休日,为了给徒弟们挣点“福利”,他接受了矿长的贿赂答应帮忙越界打通新的采煤层,不料发生了渗水事故,老井王凭借其几十年经验带领徒弟撤退到煤矿地势较高的“三平巷”,等待救援。但矿长隐瞒事故不报,加之暴雨天气和矿井次生瓦斯事故,救援雪上加霜,救援时间渐超生命极限,甚至有专家提出封井的建议。但老井王和徒弟们始终坚信能获救,老井王谎报时间以减轻徒弟们的死亡恐惧,大家相互宽慰、相互打气,以睡觉减少能量消耗,饿了吃软煤充饥,硬是撑到第25天救援人员抵达。这种积极的生命信仰不是在极端条件下被激发,而是存在于贵州人的性格与日常中。陆庆屹家庭题材纪录片《四个春天》中,姐姐远嫁他乡,虽离婚单身,但乐观向上,爱唱歌,爱玩笑;二伯即使生病住院,仍能引吭高歌;陆父陆母爱唱爱跳,特别是陆母做饭唱歌、走路唱歌、劳作唱歌,唱着唱着就不由自主地舞起来。贵州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就像贵州人善唱歌跳舞一样与生俱来。即使姐姐患病去世,陆父陆母也能及时从悲痛中走出,将悲痛化为陪伴,老两口不超过两天就去一次坟前陪姐姐说话,甚至在坟边开垦了一片菜地。影片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一次陆父陆母在姐姐坟边劳作,突然下起了小雨,陆父给陆母撑伞,陆母随即轻轻唱跳起来,不时回过头来对着姐姐的坟说:“你是最爱唱歌跳舞的。”似乎活着与死亡、“此岸”与“彼岸”只是隔了一堵墙。《滚拉拉的枪》中,岜沙苗族人认为,死亡是祖先姜央的想念和召唤,人死后将去往祖先居住的“彼岸”世界,在那里可以与去世的父母、亲人和朋友相聚,生命的消逝就是从一个寨子进入另一个寨子。有学者对贵州民间信仰文化进行研究指出:“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各民族民间信仰文化的发展阶段不同,但许多的民族民间信仰文化还是‘思考’了这个‘彼岸’的。不过这个‘彼岸’不是远处的‘彼岸’,更不是天堂的‘彼岸’,而是就在隔壁的‘彼岸’。”贵州人积极、豁达的生命观是长期与自然相处、与自然对话而涵养出的神圣生命信仰。
(三)通灵的心理域空间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意识代表超我是压制无意识本能冲动的,无意识要获得满足必须冲破前意识和意识的监视,所以无意识一般会选择在意识与前意识处于松懈状态的梦中出现,且要伪装得足够好,否则会惊醒意识而打破梦境。也许由于贵州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云雾缭绕的群山、鬼斧神工的溶洞、幽深潮湿的隧道、原生态的民俗、穿越历史的神灵崇拜,通幽古今的音乐,容易使自然与人、过去与现在,时间与空间、梦境与意识发生叠合、交融、穿越,使贵州人具有一种神奇的通灵感。被贴上“电影作者”和“作者电影”标签的贵州籍导演毕赣及其作品最重要的作者特性就是电影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现实与回忆、真实与梦幻、主观与客观无过渡、无提示性自由跳切。如《路边野餐》中,陈升乘坐火车去往镇远的火车驶入隧道,陈升走出隧道就进入了梦幻的“荡麦之旅”;《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罗宏武推着小货车走进涵洞就进入了潜意识的回忆,坐在即将拆除的电影院中,戴上3D眼镜电影就直接跳接进罗宏武的梦境,幻境如现实影像一样真实。“毕赣对隐秘和神秘有着异乎寻常的趣味,这显然与他的成长经验有关。……凯里苗侗少数民族常年不断的仪式庆典和深厚的民间信仰,易于使生命体与其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原始关系,和对自然万物的泛灵论感知,由此将超自然性引入人的信仰与审美中。”电影迷样的诗意表达和登峰造极的时空建构“是毕赣导演自己的内在感受,或者说是凯里的地方特质。”在贵州完成拍摄的《寻枪》中,民警马山在妹妹婚礼上喝醉丢失了随身携带的手枪,从他发现枪不见的那一刻起,潜意识的幻觉甚至错觉不断出现,幻觉使马山生活错乱。人物独特的心理反应与他穿梭其中的贵州青岩古镇潮湿的天气、氤氲的群山、清幽的石板路、古拙的石筑民居等独特地理环境非常契合,无意识、前意识与意识之间可无障碍穿越,往返。
三、社会空间
(一)红色革命圣地空间
贵州是波澜装阔的中国革命之重要场域,是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必经之地,在此召开了扭转中国革命形势从而挽救革命前途的遵义会议,取得了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斗、战役的伟大胜利,其中“四度赤水”被毛泽东誉为其戎马一生的最“得意之笔”,这些重大革命历史成为中国电影特别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重要素材。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对贵州的书写基本延续20世纪贵州电影国家话语表述策略,以中国革命、红军长征中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出的民族英雄为叙事对象,塑造了贵州“革命圣地”“英雄故里”的形象。《少年邓恩铭》讲述贵州荔波少年邓恩铭目睹和经历当地地方军阀勾结日伪欺压百姓、凌辱乡邻从而选择离开家乡并投身革命洪流的故事,邓恩铭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我的长征》《遵义会议》《勃沙特的长征》等均以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历史事件改编创作,其中《我的长征》《勃沙特的长征》分别设置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外国牧师的叙事视点回忆红军经过贵州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见证红军长征之艰难,攻克艰险之勇猛、之牺牲,以多视点表述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之认同与赞颂。这些电影基本是国家意志层面的精良制作,贵州的高山险岭、激流飞雨见证了中国红军不平凡的历史,贵州成为党和国家正统形象的代表,是国家话语的表述中介,是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被言说、被建构的客体。
(二)友好的人际关系空间
贵州受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影响,现代化进程总体滞后,对中国传统人情伦理承继相对较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封闭,对外接触交流较慢、较迟,很多民族地区仍保持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朴实的社会交往价值理念,邻里和睦,对外友善。《鸟巢》中,贾响马要去北京找父亲,小伙伴们积极帮助贾响马挖野菜赚路费;贾响马偶遇从江米酒节发现可以提供竹筒酒杯挣路费,几乎全村寨青壮年男性都来帮贾响马砍竹子做竹筒酒杯;临行前,寨老还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族寨秉承一个人的事,就是全村人的事的理念;《滚拉拉的枪》中,滚拉拉决定瞒着奶奶去找父亲,无论是离开还是归来时在寨子里的小卖部买胶鞋、买梳子,店主对价格的宽容呈现出传统社会浓厚的邻里乡情;滚拉拉寻父途中帮助一户苗族农家收割稻谷以换取食宿,但大伯一家待他如贵客,摆上丰盛的酒菜,献上真挚的酒歌,待滚拉拉告别时,大伯一家人相送,并唱起深情的送别歌:“流水本无情,一去不回头,哥莫学流水,把我来忘记。不论你是贫或富,我们年年在这里,盼你来相聚。”在苗家人的心里,来即是客,哪怕是从未谋面的外乡人甚至外国人。《云上太阳》中,法国女画家波琳来到丹寨苗乡采风,因病晕倒在禾田里,被麻鸟背回家中请来苗医问诊,当苗医告诉他女孩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让其等女孩醒后赶紧让女孩回家,但麻鸟说:“我们苗家是迎客不赶客的。”一家人细心照料着波琳,即使被波琳误会中伤,仍以诚相待。波琳再次晕倒,苗医表示只有用苗家图腾锦鸡鸟才能治愈,虽然族寨长老们对此意见不一,但最终以投石来决定时所有人却无一例外投了赞同票。波琳最后一次晕倒,苗医要求赶紧送医院治疗,几个苗族汉子二话不说抬着波琳跋山涉水赶了一天的路到达医院,而为了给波琳治病,麻鸟一家毅然变卖所有“物产”,寨子里其他人家也把家里的鸡、鹅、肉等值钱物品送到麻鸟家凑医疗费。如果说波琳最终能治愈且再次回到苗族村寨是因为丹寨美丽的苗乡风景,那更应该说是苗族人淳朴、善良、友好的民风感动了她、浸染了她,甚至同化了她。
(三)急遽的社会变革空间
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新世纪以来,贵州正以后发赶超的势头加快融入现代化发展潮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将打破原有社会平衡,带来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等的急遽变革,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突然被推入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潮流,传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个体面临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焦虑。正如纪录片《岜沙汉子》所揭示的:“一年一度的芦笙节舞蹈变成了有求必应的表演节目;镰刀剃头的成人礼也成了展示岜沙人绝技的固定程序;岜沙汉子的枪多了一个新用途,那就是欢迎游客的礼炮……”《开水要烫,姑娘要壮》中,乡长要求村长按照城里人的审美标准挑选村里的苗舞队:“只要姑娘不要婆娘,因为城里人喜欢苗条的姑娘,要高挑的姑娘,你千万不要找屁股大的姑娘,矮得像西瓜的更不行,你跳得再好别人也不喜欢。”而主人公小片为了能参加苗舞,整日节食减肥,甚至学起城里人的方法裹胸瘦身。如何应对现代文明的激荡,如何平衡现代与传统、发展与传承,电影中的贵州人呈现更多的是一种迷惘、失落、无奈和不适。《滚拉拉的枪》中,贾古旺决定瞒着父母去广东打工赚钱,但又对本民族生活念念不舍:“我要去广东打工了,看不见我的生命树也看不见我喜欢的姑娘了,我也不能唱苗歌了,到了广东都是唱流行歌曲的,苗歌谁听得懂?”因为现代文明的规制,岜沙苗人可以持枪但不能打猎了,曾经让老虎闻风丧胆的吴拉吉变成了喂牛老人;其子吴巴拉则去贷款种芦柑,却因失败欠款而整日躲避在山林不敢回去;老韦的儿子因不想学习、传承苗族快要失传的“指路歌”,选择了离家出走。《我们的桑嘎》中,固守传统的老歌师萨依兰拒绝进民俗村唱侗歌,被村长认为不近人情,不知好歹;在上海打工挣钱的黄月娇应村小学校长的邀请回乡当代课老师教侗歌,不仅被父母斥责,还被丈夫胁迫离婚;其弟弟黄正宇不学侗歌而喜好周杰伦的流行歌曲,虽然最后同意向潘依兰奶奶萨依兰学习侗歌,也是因为女友潘依兰的分手威胁和经济劝诱,因为侗歌在广东可以赚大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撞使身处其中的贵州人开始对本族文化产生怀疑甚至疏离,文化身份认同面临极大挑战。
结 语
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曾言:“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乎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电影对贵州地域空间、精神空间及社会空间的三维描画是基于真实贵州空间的艺术性建构。这些电影反映贵州现实,但也超越现实,是艺术家对真实贵州时空的选择性截取和想象性重构。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商品,遵循艺术规律也服从市场逻辑。新世纪是中国电影大刀阔斧改革以推动产业化发展的历史阶段,电影的市场价值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位置。于是,贵州的差异化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被频繁呈现于新世纪银幕,优美的自然风光,奇特的民俗文化,原始的民族心理,急遽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城市社会创造了一个可供观瞻、窥视的乌托邦世界。无论是贵州籍导演毕赣、陆庆屹、欧丑丑、吴娜,还是外族籍导演宁敬武、韩万峰、王小帅、曹保平等,贵州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风貌被有意无意地放逐和消隐了。创作“贵州三部曲”的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就毫不掩饰地指出:“实际上,贵州有很多地方更加原始、惊人、更好。……索性就保留你的落后,千万别发展,多年以后你看到这种原始,反而是宝藏。”显然,贵州空间在现代性对照中被书写成了乡土主义倾向的异域奇观,这不是本质性真实的贵州。真实的贵州还需要对贵州的景、人、文进行深度、立体的关照与阐释,富有魅力的贵州空间还期待发展中的中国电影继续开掘与深耕,以将贵州电影打造成最富文化反思性和真实灵动感的区域电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