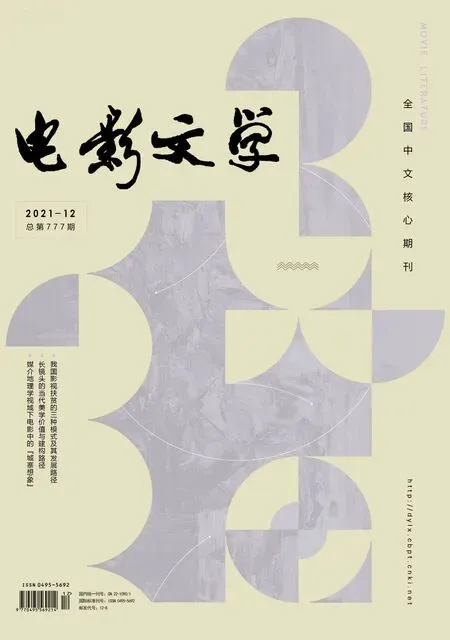论张艺谋的晚近创作
郑 敏(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一、色彩的诗学:由多彩的绚烂走向黑白的沉静
作为中国重要的导演之一,张艺谋导演在中国电影创作的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作为电影摄影出身的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几乎可以用颜色来进行分析和理解。从现有的作品来看,他的作品几乎都包含着鲜明的颜色对比手法,这一手法不仅为他的电影创作打下了特殊的艺术印记,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彼时电影创作的潮流。
色彩之于电影文本主要有两种作用,首先对电影而言,影像的基本内容不可控制,因为它只能取材于现实世界,即使在视觉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影像语言依旧难以摆脱真实这一要求。而对于创作者而言,能试图改变的也就不是这一基本的语言内容,而是附加在影像之外的非现实因素,比如配乐、镜头效果以及表现对象等方面。而影像表现中所使用的颜色就是一个重要方面。除内容外,颜色对于电影文本的表达还在于为有限的影像赋予更深刻的隐喻意义。
从张艺谋早期作品来看,鲜明且突出的色彩是表现环境和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诸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自不待言,晚一些的《一个都不能少》更是如此。从色彩运用的创作方法看,2010年上映的《山楂树之恋》应当是张艺谋电影创作在色彩使用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部电影中色彩的使用主要通过明与暗间的对比来强调外部环境的阴郁与主人公即将面临的苦难,镜头在表现主人公形象时多用淡蓝色或白色的纯洁色调,加上山楂树本身的白色花朵,更加能够表现出主人公的爱情底色。这部电影主要创作的就是一种纯洁的恋爱故事,从故事情节的客观概括出发,这段感情并不完全是一种美好的悲剧,但是影像通过色彩的重新加工,成功回避了大多数源自日常生活的驳杂成分,最终在观众眼前留下了纯净、不带有世俗浸染的感情氛围。
从这点看,张艺谋浓烈的色彩风格在此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虽然他之后的作品也有众多色彩明艳的例子,但《山楂树之恋》之后,他的电影呈现出了更多含蓄内敛的抒情风格。他晚近的力作《影》与《一秒钟》都是这种类型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灰暗的色调与光线并没有使影片产生晦涩与压抑的情感体验,相反,不同颜色的运用所得到的叙事效果为正常的影像叙述提供了全新的感情内涵。
以电影《影》为例,从叙事的内容和策略上看,这部电影文本并没有给人带来难以磨灭的印象。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失去自我身份的主人公以暴力形式重新赋予自我意义的过程。按照当下流行的商业电影叙事逻辑,这部电影只是在叙事策略之外同时实现了复调的人物塑造,并不能真正在叙事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成绩。但是这部电影对色彩的探索,却使得这部商业电影获得了更重要的艺术地位。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一明一暗,虽然外貌相似,但是所背负的仇恨与坚持的立场却毫无关联。从身体上看,一个重伤羸弱一个强健英武,而这种身体的区别毫无意外地同时体现了两个人物的性格特质,前者深居简出,性格阴鸷;后者则感情细腻,忠厚果敢。人物塑造法已基本决定两者的结局。但这部反复以复仇作为叙事线索的电影文本,其实暗藏着对自我存在的发现与确认。这种确认放置在由黑白两色构成的影像中则构建出了完全不同的情感氛围。黑白两色为这种情感的外放寻求了一种沉静的氛围,强调人物黑与白的同时也侧面说明了黑与白在人性中的混织。
颜色在电影文本中的作用有限,它通过加工影像的内在风格来营造处于某一特定环境中的人物特性,并借以营造带有感情的叙事氛围。但是颜色的意义非常重要。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这种重要超出了一般电影在组织影像时色彩发挥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色彩超越了对内容的影响转而成为结构上的某种要素。举例来说,在《一秒钟》这部电影中,黑白的色调并不算多,但是整部影片中最重要的戏剧冲突即主人公看到女儿的影像后被捕就是在相对色调单一的环境下交代的。在这一部分中,整体的客观环境是夜晚,周遭光线比较昏暗,加之在电影院这一昏暗的环境中,影像的基本色调几乎是黑色的,而银幕上偶尔投射出的电影光线又为这一环境赋予了简单的光亮,而放映电影本身又是黑白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影像色调基本同样由黑白构成。这种黑白与混沌又在叙事方面与主人公之间的和解、全片的高潮实现重合,事实上构成了这部电影的叙事高潮。
二、文化与个体:由历史的语境走向个体的挣扎
鲜明的色彩运用除了在内容与叙述结构上具有重要作用外,也往往会与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中国特质联系在一起。张艺谋的大多作品都可用一种明确的民族性特色来概括。他早期电影创作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新世纪之后的《山楂树之恋》都与中国式审美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他的电影中找到属于中国民族历史的审美特性,它在张艺谋的创作中虽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延续下来,但是从这种承续的内里来理解,张艺谋创作中的中国民族传统间或呈现出一种非本土的眼光。
就如《影》,这部电影毋庸置疑是中国古典社会题材,影片的大部分元素与表现手法都属于典型的中国故事,但从叙事文本的核心来看,这部电影似乎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性作品。很多接受者都把电影中最富有阐释空间的“伞”与“刀”理解为女性的阴柔与男性的刚猛,并进一步将之理解为以伞为盾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这种理解符合导演的创作意图。以伞为盾所表现出的女性视角确实是很重要的文本特色,但是在这部电影中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不仅只有这一个,或者,创作者所努力表达出来的不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下某一个人物的生活,而是在这个历史洪流的小支流上,一组人物群像的命运。我们可以发现电影的核心矛盾是作为“影武士”的小人物与实际掌握权威的权臣之间的身份之争。但是电影为这典型的现代性迷思提供了一种非常古典的解决过程,首先阻碍两者身份发现的直接阻力是古典政治权威的争夺,这种争夺不仅对主要矛盾的双方产生影响,在电影文本中围绕这一核心矛盾还有很多衍生问题亟待解决。如都督重伤无法继续完成军事野心与将军之间的矛盾;又比如与皇权间的权力斗争问题;甚至是公主对自己生活自由的争取等,都可以构成电影叙事过程中的重要矛盾。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一结论,除了在文本叙事中可以明确发现这些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叙事的高潮部分——两国的决战时刻,以上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这意味着电影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是在传统的历史语境下发现和解决专属于中国民族的古典命题,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更具现代意义的多元问题。这些问题围绕着某一个人的生存提出,并且围绕这个人物的具体生存体验逐步地进行解答,因此作为电影当中的人物群像,每一个人都在影像构成的社会形态中寻求自我的慰藉和意义。从这一点上看这部电影所关注的就不仅是某个人的身份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各自解决自我问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电影中的传统特性就逐渐被剥离了,转而对人以及人的现代性境遇进行了反思。
文化的逐渐退场与个人生活的逐渐出现在张艺谋的电影创作过程中不是一日之功,但是他晚近的两部作品却可以集中体现出他作品中的这种转变。如果说《影》中的个体书写还存在于较为含混的语境中的话,那《一秒钟》则完全挣脱了群像的书写方式,仅仅就某个个体的生存进行了书写。主人公的个体生命意识实际上也是随着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人性的反思得以确立的。
三、表现到再现:由浪漫的意象走向现实的审视
张艺谋镜头中的艺术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乡村构成的,或者说对于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的作者和导演来说,中国乡村一直是他们创作的重要经验来源。对这一类导演来说,文学与电影文本创作密不可分。当时很多小说家都以最终能被改编成电影来衡量自己小说的价值,相对应的,电影导演对电影文本的选择也慎之又慎。在这一时期小说和电影之间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联系。这一时期,文学界普遍以重构当前的乡土社会为主要的书写对象,其中以寻根文学为代表。但这种乡土书写不仅在于重现中国的乡村特性,而是在面对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时本民族所应当做出的思考层面着力。
照此逻辑,张艺谋早期作品几乎代表性地展现了当时文学界对中国乡村以及民族性的探寻。如代表作《红高粱》,就是典范的文学文本改编的电影作品,回顾其文本基础,可以发现莫言笔下的《红高粱家族》本就是融合了一种现代性的符号化书写,其中对中国乡村的描摹充满了魔幻的意象。而在电影当中,张艺谋成功地将这种意象通过影像化的语言表达了出来。比如影片最后,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阳光照向山关,随着主人公的远走,镜头慢慢延伸,最终在一片红高粱前留下一个长镜头。这个别有意味的长镜头将红高粱这一意象强调出来。这种情况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乡土性与民族性通过影像语言构成了充满阐释空间的意象,并一道构成了张艺谋电影创作的主要风格。
但从《一秒钟》来看,除电影影像并未使用色彩强烈、对比鲜明的手法之外,电影文本所描绘的中国乡村相比之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在乡村这一场域所代表的意义上,《红高粱》等其他作品中的乡村社会就如前文所说因为文学创作风潮、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内在意蕴。而反观《一秒钟》这部电影当中的乡村社会,乡土更类似于一个故事发生的平台和处所,它的故事开展有着明显的环境要求,而乡土社会本身有没有对主人公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电影中的乡土环境并没有直接对主人公的个体生活产生影响,真正产生影响的应当是存在于这一乡土社会中的人。换言之,真正促使主人公在这一文本中产生改变的不是乡土而是“社会”。
对于这部电影当中的乡土环境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而言,主人公并没有对这一空间环境产生过多的留恋。按照身份来说,他是一个外来者,为了追踪自己女儿所在的电影片段辗转多地。这一辗转的过程当然不会使他发生个体生活的改变,文本中他胁迫放映员反复播放电影,或许是舐犊情深,但是也恰恰说明了他与当地生活所保持的距离。而导演为这个人物安排的转变则是以他与女主人公相遇开始的。从内容上看,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将这部电影归类到父女亲情等家庭类的电影类型作品中,并且主人公在文本中的主要人生意义就在于对女儿的思念。但是从电影结尾的处理上看,主人公最珍视的女儿照片已经遗失于沙漠中,那么此时主人公的生存意义已经遭到了否定,但是他重新寻找到的就是在寻找女儿的路上所结识的另一个孤儿,按照这种情感逻辑的变化上来看,主人公所追寻的人生意义从个体的亲情走向了更博爱的人性的感情。在这一过程中,与此前的创作不同的是,作者为这一人性感受的获得提供了很多来自乡土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方面自然不同于早先创作时对民族性的表达,甚至在文本中并没有过多地对此进行批判和渲染,人性的问题在这里被沉淀下来不仅进行着反思,更多的是一种观察的角度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