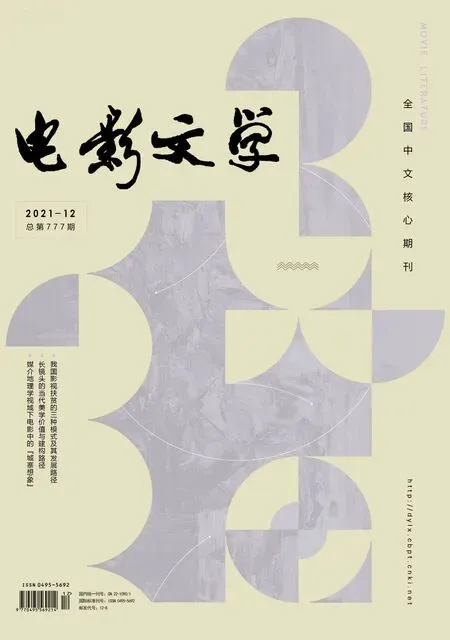陈凯歌、何平、李睿珺电影中的西部风景
荀羽琨(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西部广袤的沙漠瀚海、黄土高原,以及在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中所孕育的生命形态和民族性格,都给当代电影创作带来了新奇刚健的美学风格。“中国电影地域风貌和人文空间的两大资源,一个是西北黄土高原、河套地区;一个是江南水乡、小桥古镇;从早期发端以来的电影家就一直在这两个空间里不断开发视觉资源和电影素材。”西部辽阔荒远的地理景观,不但成为中国电影地域风貌形成的核心要素,而且这种经过审美情感艺术处理后的西部影像,不再是一种自然风景的单纯呈现,它成为不同创作者主观趣味和文化意旨的视觉代言。西部从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在影像叙事中被成功转化成承载了地缘情感和文化内涵的“有意味的风景”。
一、黄土地的寓言:温暖的愚昧
对西部自然景观的表现,是第五代导演电影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对于这批经历过工农兵思潮洗礼的导演们而言,他们对乡土中国的呈现已经发生了新的情感位移,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视野中阴晦了无生气的荒村意象,也不同于革命影片中对“解放区天空”明朗乐观的想象,西部广袤贫瘠的土地既是禁锢生命的牢笼,也是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根系所在,这种温情启蒙主义所呈现的西部,总是充满了一种被情感和理性所撕裂的痛楚和无奈。不管是陈凯歌影片中黄土地的沉重压抑,还是吴天明《人生》中乡村的温馨和谐,它们在影片中的意义,就在于寓言式地呈现了乡土中国“温暖的愚昧”,它既孕育了生命和希望,也吞噬了理想和青春。
黄土地和黄河作为西部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在影片《黄土地》中多次大面积长时段的静态呈现,这种带有颠覆性的影像构图,来自第五代导演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独特的认知和反思。“以养育了中华民族、产生过灿烂民族文化的陕北高原为基本的造型素材,通过人与土地这种自氏族社会以来就存在的古老而又永恒的关系的展示,或许可以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这种相当清晰的文化反思立场,使陈凯歌打破了景观作为造型功能的传统界限,使土地和黄河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视觉符号和寓言,把景观从电影的审美元素升格为一种主题性元素。
《黄土地》中对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表现,象征性地表达了贫瘠停滞的土地上生命的挣扎与渴望。在该影片的文学剧本《深谷回声》中,编剧张子良对陕北自然景色的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想象,在剧本开始顾青出现的场景中,作者描绘了由“蓝天白云”“梢林葱郁”“野花”“红叶”“小鸟”等意象构成的山谷画面,随后顾青和翠巧一家人在洋芋地里劳动时,翠巧爹光着膀子舞镢的动作,翠巧优美的身体曲线,构成了一幅动人的丰收图。这两幅充满田园风光的画面,都意在突出人与乡土之间的和谐。与剧本把故事的发生选择在景色旖旎的秋天不同,电影的拍摄则选择了北方最为萧瑟的冬季,顾青出场时的黄土高原没有一丝的生机与绿色,更没有红花绿叶的诗意点缀,裸露出褐色的刀砍斧凿般的陡崖和山谷,黄土的广博和贫瘠共存于此。剧本中洋芋地里劳动的欢快场景在电影中被置换成犁地,对土地被犁开镜头的特写,还有犁地时顾青和翠巧爹错位的对话,顾青对翠巧爹洒饭祭天善意的嘲笑,翠巧爹则把这种嘲笑认为是年轻后生对土地价值的无知,这个场景突出的是顾青所代表的现代话语和翠巧爹象征的乡土话语系统之间的隔膜和分裂,也暗示了翠巧最后的悲剧结局。虽然顾青对解放区美好生活的讲述像犁耙一样犁开了这块古老而僵化的土地,唤起了翠巧、憨憨和翠巧爹心中对新生活微弱的向往和憧憬,但是这种遥远的理想世界最终还是无法战胜贫穷世界的生存法则,翠巧还是以买卖婚姻的方式被嫁了出去。影片中翠巧送别顾青的片段,顾青向上走到黄土地的高处,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翠巧则带着对顾青的期待往回走,她渺小的身影在山谷中时隐时现,最终完全消失在黄土地的深处,回到这片黄土地给她安排的无法撼动的悲剧命运。
其次,是电影对人与黄河关系的表现,与黄土地的封闭凝固不同,黄河则连接着外面的世界,代表着流动和变化。如果说翠巧爹和黄土地的形象共同构成了乡土文化的视觉符号,那么翠巧和黄河的关系则代表了这块古老的黄土地所孕育的新生和希望。影片中黄河的形象始终和翠巧到河边挑水的画面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在翠巧看到别的女孩的婚礼之后,满怀心事在黄昏时来到在黄河边挑水,面对平静的河水用歌声诉说着自己的苦楚和忧伤。第二次是在翠巧听到顾青对解放区生活的讲述,唤起了一个少女对理想和爱情朦胧的期待,翠巧挑着水,背后是宽阔而欢快的河面,河面上激起的层层涟漪正是翠巧此刻心情的写照。第三次是翠巧准备乘船过河,这时的水流是湍急汹涌的,翠巧的小船在夜晚的河面上显得孤独而渺小,黄河以浑浊的河水养育了这片干涸的土地和它的子民,但当觉醒了的翠巧带着她的理想投身于黄河,黄河却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往回走,则消融于土地,往外走,则葬身于黄河,这让人无疑想起鲁迅所说“觉醒了无路可走”的绝望,这就是乡土中国生命艰难的挣扎和渴望。与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愚昧落后的否定和批判相比,经历过和工农结合的第五代导演,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多了一些温情和留恋,在影片中呈现为养育和禁锢缠绕在一起的土地和黄河意象,对乡土的道德情感使他们无法把愚昧从温情中剥离出来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批判,这是第五代导演独特的精神烙印和电影美学,也是他们在中国电影形象谱系中建构的关于中国图景的文化寓言。
二、大漠峡谷:荒野中的传奇与壮美
西部不但有黄土地和黄河孕育的乡土文化,也有大漠峡谷所生成的游牧文化和英雄主义,与《黄土地》所展现的土地的超稳定形态及其“庄稼人的规矩”对人性的压抑不同,何平的《双旗镇刀客》《日光峡谷》《天地英雄》,则在大漠峡谷的荒野景观中演绎了生命的传奇,展现了人在战胜自然与自我过程中的力量感和崇高感。
何平在文化寓言式的西部叙事之外,深入到对西部人精神世界传奇性的探究与表现,远离社会和人群的沙漠峡谷成为演绎传奇性的最佳舞台。何平对西部传奇性的想象与建构,首先是通过荒漠、戈壁、沙丘、古城、驿站等具有奇观效应的自然景观来呈现,这些原始质朴的西部风景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巨大的造型和想象空间。同时大漠黄沙、古城颓墙往往又因人迹罕至而充满了神秘色彩。《双旗镇刀客》的故事发生在河西走廊中部,沙漠中一个孤立而封闭的小镇里;《日光峡谷》的拍摄地点选在了海拔三千米以上古代驿道上一处残败的兵驿改成的客栈中;《天地英雄》是在丝路古道上一处残破的哨所,这些历史久远的荒原意象在何平的电影中,并不是作为贫瘠落后的视觉表征,而是凸显了西部的辽阔和生命的坚韧,“像诗一样地展示西域的神奇与壮美”。这里不但有能唤起人“震惊体验”的荒野奇观,同时也是一个有别于文明社会的荒蛮之地,历史上曾作为流放之地的西部,生活着刀客、侠士、罪犯等各种游走在社会制度边缘的人物,被自然和历史造就的西部世界里,暴力和正义、善良和欺诈,软弱和勇敢,这些充满矛盾而又富有人性张力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演绎了一个个生命的传奇故事。西部景观在何平电影中的功能,不是为了实现“概念的超越”,而是负载和传达一种生命的坚韧和壮美,表现了绝处逢生的生命奇迹和西部民族英雄精神。
何平电影中人与风景之间的关系被重新调整,人是主体和中心,风景只是人物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最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并最能灵活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和内心体验”。同时由于大多数西部电影对西部人木讷沉默的性格设定,所以借助更多的风景镜头来实现对人物心理的表达,就成为影片一种必要的表现手段。《双旗镇刀客》中其貌不扬的孩哥,却有着超群的刀法,在生死关头战胜内心的恐惧,迸发出生命最大的潜能,杀死心狠手辣的“一刀仙”。这个人物的魅力,就在于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传奇色彩和人性张力,导演塑造这个人物并不是简单把他当作一个刀法高超的侠客,所以影片给孩哥的刀法并未提供过多的展示机会,甚至他的刀法都采用了“大道至简”的原则,没有刀光剑影的打来杀去,而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一刀毙命。这种设计一方面增加了人物的传奇性,另一方面影片可以腾挪出大量的画面去展示这个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内心世界,从而避免了武侠电影人物塑造的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倾向。杨争光在谈到剧本创作的立意和性质时说:“我没写过武侠电影,我更愿意称它为西部传奇。”具体到孩哥这个人物就是他的刀法奇、性格奇,但是他的性格同他的刀法一样深藏不露,怎样展示这个人物之“奇”而又让观众不觉得突兀,风景在这里就发挥了重要的表意作用。电影一开始就采用慢镜头展示了孩哥身穿羊皮袄,孤身一人策马扬鞭奔腾在浩瀚的沙漠中,随后镜头一直追随孩哥的身影,辽阔的天地之间,一人一马,飞驰的马蹄,漫天的黄沙,孩哥与骏马的影像融为一体,这样一幅充满写意的画面塑造出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在双旗镇受到嘲笑和冷落的孩哥,在大漠中放马的时候释放出自己英姿勃发的少年气息,响亮的马鞭,畅快的欢呼,这个画面既呼应了影片开头孩哥出场时的英雄形象,又为后面孩哥在劈肉时展现自己惊人的力量和刀法做了铺垫。在孩哥杀了“一刀仙”的兄弟,去找沙里飞帮忙的这段故事中,影片通过大漠古堡的景观把孩哥和好妹俊朗秀美的少年气息推向高潮。夕阳下雄浑的烽火台,参差不齐的古城墙,无边的荒漠戈壁,金色的沙丘,身穿红衣的好妹,辽阔的天地之间孩哥策马而来,自然的壮美和人物的情感融为一体,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孩哥展现出他的勇敢和道义,也终于赢得了纯美的爱情。从整部影片的角色设定来说,处在双旗镇日常生活的孩哥稚气笨拙,但是一进入大漠这个辽阔的空间,孩哥则展现出自身英雄阳刚的一面,这个人物的传奇性就来自外与内、怯懦和英雄、内敛和张扬之间的人性魅力。
三、家园:西部风景的“去魅”
新生代导演李睿珺的出现,打破了第五代导演对西部风景“文化赋值”式的叙事模式,他的“土地三部曲”(《老驴头》2010、《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把对西部的表现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以一种在地性的经验对西部进行“去魅”,剥离了附加在风景之上的文化寓言和传奇性想象,通过对西部人日常生活的展现,还原了西部作为家园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真实处境。
李睿珺对西部家园意象的建构,是通过一系列以村庄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化的风景呈现出来的,简陋质朴的村庄、杂乱的院落,低矮的祖坟、静谧的池塘、丰茂的草原,这些既不辽阔也不壮美的乡村风景,使西部底层民众的生存风景浮出了影像叙事的历史地表。李睿珺电影中有两个重要的风景意象,一个是坟地,一个是土地,通过这两个连接着生与死的意象,撕开了我们这个时代尖锐的伤痛。《老驴头》中讲述了七十多岁的老驴头为了保护被沙漠所掩埋父母的坟地,独自一人去治理沙漠,影片中大量的情节都是在治沙的场景中展现的。黎明之际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的街道,路边低矮破旧的土墙,公鸡嘹亮的打鸣,路上的羊群,村里人亲切的问候,在这个温馨而充满烟火气的背景中,缓缓骑驴走来的老驴头,孤身一人走向沙漠中的坟场。通往坟场的是一条笔直的看不到头的小路,湛蓝的天空,被白雪覆盖的辽阔的戈壁,远处模糊的山影,这幅宁静悠远的画面构成了与村庄的烟火气相对的彼岸世界,一头连着生的家园,另一头是死后的栖息之地。坟地在一大片沙丘的脚下,周围是稀疏的枯草,老驴头无奈的背影和叹息,使得坟地呈现出一种凄凉落寞的气息。紧接着电影采用大远景镜头呈现了沙丘的全景,黄色的沙丘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老驴头站在沙丘的顶部,虚化为一个看不清面目的黑点,正如无数个被裹挟进时代洪流的底层民众,他们渺小的痛苦和希冀,正在被时代无情地漠视和遗忘。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把坟地上升为整部影片的核心意象,在一种更为极端和酷烈的语境中表达了时代洪流对个体生命的碾压。电影讲述了给人做了一辈子棺材的老马,在自己老的时候却因为当地要实行火葬,无法实现“入土为安,驾鹤西去”的愿望而备受煎熬。老马对土葬的执念得不到子女的理解,更无法得到这个时代的尊重和认同,最后只能以让孙子活埋自己的方式“藏了起来”,影片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残酷和荒诞。与现实本身的残忍相比,老马给自己找到的安身之处,是绿荫环绕的漕子湖边,茂密的芦苇荡,湖里浮游的鸭子,金色的阳光笼罩下的大树和田野,树下孩子们单纯的快乐,在这个平静而充满理想色彩的地方,老马找到了身体和灵魂的归宿。李睿珺对漕子湖风景的表现是充满诗意的,其中寄托了他对过去田园牧歌式乡土生活的怀念和悲悼,对人与自然,个体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李睿珺电影的另一个意象是土地,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李睿珺电影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同于陈凯歌电影对黄土地温情启蒙主义的批判,李睿珺电影中的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和死后的安身之所,《黄土地》描写了翠巧挣脱土地的艰难,《老驴头》则颇为讽刺地表现了农民捍卫土地的失败。电影中与土地相关的画面,都是在冬天萧瑟荒凉的田地里,几个势单力薄的老人挡在拖拉机前面,虽然两次都赶走了张永福,但是资本强大的势力还是在老驴头生病住院期间霸占了他的两亩地,在村委会通知签订转包协议的广播中,老驴头落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李睿珺以写实的方式呈现了土地的荒凉,它既不博大也不肥沃,只剩下贫瘠和荒芜,也不再和劳作的画面联系在一起,被时代所遗弃的土地已无法再承载养育的内涵,这不但是西部农村的现实,也是乡土中国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写照。现实的土地是荒芜的,母亲般的土地只能存在于过去的记忆里。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讲述了两个裕固族少年阿迪克尔和巴特尔,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寻找父母亲在草原上的家。影片从两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工业化进程中草原的消逝和精神的荒芜。爷爷在镇上的家在一片荒漠戈壁之中,水位下降连井也打不出水,兄弟两人在爷爷去世之后骑着骆驼回父母在草原的家,途中的河流已经干涸,过去的村庄变成了废墟。他们穿越千里沿着水源找到的,却是一片碎石满地灰尘弥漫的淘金场,兄弟俩在淘金的工人之中找到父亲的背影,他们对草原和家的憧憬在这一刻变得迷茫和失落,巴特尔沿着一条灰白的路走上去,记忆中的草原却变成了烟囱林立的工厂,高耸的烟囱突兀地竖立在荒原之上,画面的上方是一个逐渐落下的夕阳,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朝着工厂所在的地方走过去,父亲的脚步匆忙而急促,路的尽头是什么,谁也无从得知。水草丰茂的草原和温暖的家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巴特尔的老骆驼在途中生病死去,在死前它凭着记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也带着兄弟两人找到了他们过去在草原上的家,影片以超现实的手法呈现了绿色的草原、白色的帐篷、宽厚的母亲、调皮的小骆驼,这样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是我们每个人和这个时代都无法回去的记忆,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心灵的伤痛。因为城市化的强势逼近,电影对消失的乡土家园无奈的回望和挽留,内在地契合了观众的怀旧审美心理,而这正是李睿珺电影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