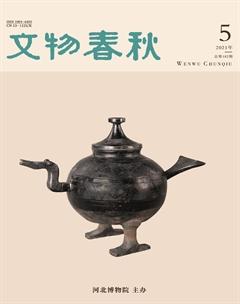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变化与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
雒有仓 黄端胜
【关键词】金文族徽;西周;商周族群;文化认同
【摘要】通常认为,西周金文族徽是商代晚期族氏名号的沿袭,事实上,西周金文族徽还存在许多变化:一是族徽地域分布中心转移,二是族徽铜器数量由增转减,三是族徽种类减少,四是人名、地名、官名性族徽增加,五是族徽功能与性质有所变化。正确认识西周金文族徽的这些变化,对于深入认识当时周人铜器上出现殷商文化标记的族徽与日名,大量殷遗族氏分散迁移各地与周人族群融合,以及西周中晚期殷遗族徽、日名显著减少与周文化的认同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文族徽与商周族群认同研究”(批准号:17BZS038)研究成果
西周时期,金文族徽作为殷遗族氏和商文化的重要标记,在各阶段的青铜器上长期存在,其间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深刻体现着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与融合。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侧重于对殷遗的迁移、管理及身份地位等进行讨论[1—4],少见对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变化与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的研讨[5—8],本文不揣谫陋,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
從族徽铜器出土情况来看,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殷商大族的族徽铜器出土地点较分散。如前述冉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河南洛阳,陕西长安、宝鸡、凤翔,山东临朐,湖北荆州等地;戈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陕西泾阳、长安,河南洛阳,湖北随州等地;子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河南鹿邑、洛阳,山西曲沃,山东滕州等地;举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山东费县、长清,陕西长安、扶风,北京房山等地。各地墓葬多见族徽铜器单独出现,或族徽铜器在该墓地出土铜器中占据多数,说明西周时期的殷商大族成员多被分散迁移至不同地域。另一种情况是殷遗中小族氏的族徽铜器出土地点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地区。如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的商代晚期墓M17、M129、M213出土铭“史”铜器3件,而同墓地的西周早期墓M11、M13、M18、M21、M30、M34、M38、M40、M41、M45、M110、M120、M121共出铭“史”铜器60件[10]:208—333,说明史族不仅是从商代晚期延续至西周早期的族氏,而且一直居住在滕州前掌大附近未曾迁移。
从金文族徽的类型看,一些商代晚期常见的族徽形式在西周时期依然存在。以族徽“子”为例:
(1)“子”单独出现或与父祖日名联缀,见于商代铜器有子鼎(集成1042)、子觚(集成6525)、子爵(集成7316)、子卣(集成4732)以及子父丁鼎、子父戊簋、子父庚爵、子祖己卣、子祖癸觚、子祖辛爵(集成1596、3186、8584、4894、7085、8343)等,见于西周铜器有子鼎、子簋、子爵、子觯、子壶(新收549、1852,集成7320、6021,近出645)以及子父乙鼎、子父辛爵、子父丙觯、子父乙盉、子祖辛盉、子祖丁觯(集成1534、8593、6248、9340、9337,铭图10396)等。
二、西周金文族徽的变化
西周初年,伴随着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首先,关中地区的丰镐取代了安阳殷墟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关东地区的不少殷遗贵族因受周人统治者怀柔安抚,迁居岐周或宗周任职为官,服务于周王室。其次,周公东征之后营建洛邑,将参与“三监之乱”和怀有对抗意图的殷顽民迁居成周,并驻守八师加以集中监管。再次,武庚叛乱平定后,周王室通过大规模分封构建地方统治体系,将大量殷遗族氏分散迁移至齐、鲁、晋、宋、燕等地,成为各诸侯国统治土著居民的重要依靠力量,并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周人与殷遗、土著“三结合”的族群结构,促进了不同血缘群体之间的政治融合。以上三方面政治环境的改变,不仅使得殷遗族氏长期居住一地的血缘聚居状态有所改观,而且促进了商周族群之间的融合,使西周金文族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族徽地域分布中心的转移。从族徽铜器的出土地点看,商代晚期的金文族徽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地域分布以今河南省为主,山东省也有较多分布,而西周早期的金文族徽则以成周、宗周、岐周三点一线为中心,地域分布主要见于成周所在地今河南洛阳地区,关中丰镐遗址所在地今陕西长安县,周原遗址所在地今陕西岐山、扶风县乃至凤翔、宝鸡一带(详见拙稿《西周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与商周族群的政治认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待刊稿)。这种情况应是当时政治中心自东向西转移,殷遗族氏大量西迁的结果。从近年考古发掘材料来看,西北地区的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发现有腰坑和殉狗的殷遗民墓葬以及“薛侯”等甲骨刻辞[13,14],而南方的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则出土19种徽识类青铜器[15]242,这些情况说明,西周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实际上不限于王畿附近地区,在王畿之外的四土之地也有广泛分布,地域范围比商代晚期进一步扩大。
(二)族徽铜器数量的变化。商代晚期族徽铜器十分常见,据我们统计,在已著录的有铭铜器中,现存商代晚期族徽铜器约有5300余件,而西周的族徽铜器共有3300余件。这种情况说明,西周时期的殷遗族氏铜器数量少于商代晚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然而,如果分阶段观察,就会发现有不同情况存在。据严志斌统计,殷墟三、四期共有族徽铜器1660例[16],这个数据即使加上不能分期断代的1200余件族徽铜器,共计2860余器,仍略少于《铭图》《铭续》《铭三》三书著录的西周早期族徽铜器数量2950件。可见,与殷墟三、四期相比,西周早期的族徽铜器仍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西周早期的殷遗族氏分散迁移,不断促使族徽传播地域扩大、使用人群增多有关。然而,自西周中期以降,族徽铜器数量明显减少,见于《铭图》《铭续》《铭三》著录的西周中期族徽铜器仅285例,西周晚期族徽铜器的数量更少,仅存105例。可见,西周中晚期的族徽铜器数量急剧减少,渐趋消亡。这种情况当然并非是由于殷遗民灭亡,而是殷遗族氏因受周文化影响抛弃族徽不用,认同于周文化并融入周人族群的反映。
(三)族徽种类的变化。西周早期的金文族徽种类与商代晚期相比,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减,但总体上变化不明显,所见共1089种,约与商代晚期的族徽种类数量相当。然而自西周中期开始,许多殷遗族氏纷纷弃族徽不用,金文族徽种类明显减少,所见仅110余种。到西周晚期,金文族徽已不常见,所见仅20多种。金文族徽种类的以上变化,是周文化后来居上的反映,也是殷遗民抛弃族徽不用而融入周人族群的体现。
(五)族徽功能与性质的变化。殷商时期,金文族徽除常见于青铜器外,也常见于甲骨文作人名、地名、族名[17],学界称之为“三位一体”。这是因为族徽所代表的族氏不仅是一个血缘团体,而且由于长期居住一地,族氏名实际上已成为地域性血缘团体的代名词,故有“胙土命氏”的政治含义。西周时期,由于商王朝统治秩序被推翻,殷遗族氏的地位普遍下降,族徽已不再具有“胙土命氏”的政治功能,而主要作为殷商族群表示同族血缘关系的符号而存在,从而与不用族徽的周人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别。因此,从性质上看,商代的金文族徽所代表的大多为血缘与地域相結合的政治集团,具有表示血缘关系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含义。而西周时期,由于殷遗族氏大多被分散迁移各地,隶属于封地诸侯等各级贵族,并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18]原则纳入了周人建立的宗法秩序,因而其金文族徽多属单纯表示血缘关系的父系家族名号,没有“胙土命氏”的实质内涵,从而成为殷遗民表示血缘关系的文化符号。显然,这种文化符号在西周时期的存在乃至消亡,实际上体现着殷遗民逐渐融合于周人族群并认同于周文化的一种历史过程。
三、商周族群的融合与文化认同
西周时期,殷遗族氏与周文化的融合认同,较明显地体现在金文族徽与日名使用等方面。关中西部的先周遗存及周初墓葬少见腰坑、殉人、殉牲,“绝少见到日名、族徽铜器”[19],说明周人原本不使用族徽与日名,而现存周人铜器铭文表明,“族徽文字是殷人的专利,周人则弃而不用”[20]。因此,通过对族徽与日名的考察,可以认识商周族群在西周时期相互融合与文化认同的情况。
西周早期,姬姓周人贵族使用族徽与日名较典型的例证,是近年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两件西周早期铜器[15]220,114:一件是M27出土的伯生盉(铭图14705),盖、器同铭:“伯生作彝。曾”;另一件是M111出土的曾侯鼎(铭图续121),盖、器同铭:“曾侯作父乙宝尊彝”。前者“曾”位于铭尾,应为族徽,后者“父乙”之称为日名。按曾姬壶、曾子原簠、曾侯舆残钟铭文中“曾”为姬姓,新见楚王鼎(随仲嬭加鼎)和新出随仲芈加编钟以及同名匕、缶的铭文表明“曾”即“随”,为汉东地区的姬姓诸侯封国[24]。另M111同出犺簋铭文有“南公”的记载,“南公应是南公适,曾国应是南宫适的封国,其族姓为姬姓”[25]。可见,前述伯生盉上的族徽“曾”和曾侯鼎上的日名“乙”,应是西周早期曾国姬姓贵族对于殷商文化初步认同与融合的表现。进一步来看,叶家山曾国墓地先后出土有19种族徽,说明当时有大量的殷遗民随迁。而M1出土3件铜鼎铭“师作父癸”“师作父乙”,这类“师”之称谓“除象师雍父这样称父号者外,大体上可视为殷代以来的旧族”[26],即为殷遗“以官为氏”的族徽,说明随迁的殷遗民中有成周八师的成员。而姬姓曾公室贵族之所以使用族徽与日名,应是受随迁殷遗和商文化影响的结果。从该墓地年代稍晚的M2、M28、M65出土的多件曾侯器上均无日名,亦不见将“曾”置于铭尾的族徽用法来看,姬姓曾公室对日名和族徽的使用仅限于最初受封的一段时期内,而这种暂时性的使用最终被姬姓周人贵族排斥和拒绝。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商周文化此消彼长,周文化后来居上,占据主导地位有关。
与周人贵族个别、零星地使用族徽和日名不同,西周早期的殷遗贵族多见使用族徽与日名。例如:
臣高鼎(铭图2020):“乙未,王赏臣高贝十朋,用作文父丁宝尊彝。子。”
从西周墓葬铜器来看,在礼制层面也有商周族群相互融合认同的明显反映。例如西周早期的殷遗墓葬以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为代表,出土有盘、盉等器,已开西周盘盉固定配置的先河,但铜器的形制大多具有浓厚的商代遗风,礼器组合既有爵、觚、觯、尊等酒器48件,也有鼎、簋、鬲、甗等食器29件,铭文多见族徽与日名,既有浓厚的商文化特征,又有明显的西周因素,发掘者从出土铜器所见酒器、食器所占比重出发,认为这种情况应属“重酒重食的组合”[28],即为偏重于商礼重酒而又有周礼重食并存的体现。山东滕州前掌大M11、M18、M21、M38、M120[10]551—562及M308、M309、M312[29],北京房山琉璃河M50、M53[30],湖北安居羊子山M1、M4[31],以及陕西泾阳高家堡M4、M1[32],长安张家坡61M106[33]、67M87[34],宝鸡竹园沟M7、M8[35]等墓葬,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但在同时代的其他墓葬中往往又有食器比重超过了酒器的现象,这应当是重食的周代礼制在商周文化融合过程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反映。从西周中期的墓葬来看,在一些有腰坑和殉犬的墓葬中,随葬的铜器往往有族徽与日名,有些墓葬还出土数量相等的青铜酒器与食器,如1978年陕西扶风齐家村M19出土食器5件(鼎2簋2甗1)、酒器5件(爵2觯1尊1卣1)[36],1975年扶风庄白村墓葬出土食器6件(鼎3簋2甗1)、酒器6件(壶3爵2觯1)[37],可见当时的殷遗后裔仍遵行商代礼制,但同时已经接受了周代礼制。西周晚期,在能夠确定为殷遗后裔的墓葬中,有些铜器不见族徽,但出土有铜酒器,铜器组合以食器为主,如河南洛阳白马寺M21出土食器3件(鼎1簋2)、酒器2件(壶2)[38],铜器组合中的食器数量超过了酒器;有些墓葬不见腰坑,出土铜器仅有食器,酒器多为仿铜陶器或明器,如1992年陕西长安马王村M92出土青铜食器4件(鼎2簋2)和仿铜食器陶甗1件,酒器则为仿铜陶器5件(爵2觯2尊1)[39],器物组合具有明显的重食特点。这些墓葬的规格都不是很高,墓主人都属于中下层贵族,说明在西周晚期的殷遗中下层后裔中,代表商文化的饮酒器已经退出了礼制范畴,而代表周礼的食器的比例大幅提升,表明周文化最终得到了殷遗后裔族群的广泛认同。
————————
[1]李宏,孙英民.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J].史学月刊,1999(6).
[2]杜正胜.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四分.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
[3]宫长为,徐义华.殷遗与殷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张礼艳.沣西地区殷遗民的社会地位及其变迁[J].考古与文物,2013(2).
[5]钱唯真.商周金文中族氏徽号的因袭与变化研究[D].台中:东海大学,2007.
[6]张懋镕.试论商周之际字词的演变: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一[G]//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27—244.
[7]张懋镕.商周之际女性地位的变迁: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二[G]//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45—269.
[8]张懋镕.金文所见商周之际诸兄地位的变迁: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三[G]//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70—274.
[9]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元年[M]//阮元校刻本影印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2134—2135.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1]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6—211.
[12]雒有仓.商周家族墓地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J].考古,2013(8).
[13]李政.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发现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铸铜、制陶作坊等重要遗迹[N].中国文物报,2017-12-05(2).
[14]马强.周王朝西北边疆的新发现: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J].大众考古,2020(2).
[15]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6]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2—83.
[17]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7:67—91.
[1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十一年[M]//阮元校刻本影印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1735.
[19]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证明[G]//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論集: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23—250.
[20]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J].考古,1995(9).
[21]司马迁.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
[2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9,71,81,35.
[23]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8—130.
[24]张懋镕.李学勤与“曾国之谜”[J].江汉考古,2020(2).
[25]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5).
[26]白川静.西周史略[M].袁林,译.徐喜辰,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79.
[27]张懋镕.试论商周之际字词的演变: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一[G]//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西部考古: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05.
[29]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G]//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岱考古: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27—375.
[3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苏天钧.北京考古集成:1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0,23.
[31]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J].文物,2011(11).
[3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5—31,69—106.
[33]赵永福.1961—62年沣西发掘简报[J].考古,1984(9).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J].考古学报,1980(4).
[3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J].文物,1979(11).
[38]张剑,蔡运章.洛阳白马寺三座西周晚期墓[J].文物,1998(10).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J].考古,1994(11).
〔责任编辑:成彩虹〕
————————
①据王长丰统计,商周金文族徽共有2168种,见氏著《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9—636页。这一统计数据包括同族徽的不同字形,实际上现存商周金文族徽共约1900多种。
②冉族铜器数量根据《铭图》《铭续》《铭三》著录统计,下文戈、举、子族铜器统计依据相同,不一一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