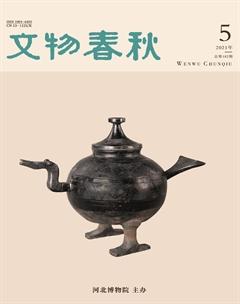论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中的媵婚关系
金方廷
【关键词】曾侯乍季汤嬭媵鼎;一器媵二女;异姓媵;媵婚制度;春秋时期
曾侯乍季汤嬭媵鼎是一件春秋时期的曾国媵器,2002年出土于湖北枣阳郭家庙,出土时损坏严重,残留铭文(图一)“曾侯作季……汤嬭(芈)媵……其永用……”[1]11。此器收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下文简称“铭图”),称曾侯鼎,编号为40224。著录者最初将这件器物视作曾、楚联姻的证据,认为是“曾侯为某位嫁到了曾国的芈姓楚国女子作的鼎”[1]13。之后黄锦前在《读近刊曾器散记》一文中将“季汤嬭”连读,增补该器铭文为“曾侯作季汤嬭媵〔鼎〕,其永用〔之〕”,认为这个称名反映的是“名/字+姓”的女子称谓方式,又列举近出随仲嬭加鼎和河南淅川徐家岭出土鄬子孟升嬭鼎等例,证明这是一种金文中鲜见的女子称谓方式,认为这篇媵器铭文反映了“楚女出嫁,曾女为媵”的婚姻关系[2]。
在曾攀增补前,该铭文所反映的作器人与被嫁女性的关系颇为难解,而在“季”字之后补上曾国族姓“姬”字组成“季姬”,不仅合乎常见媵器铭文的辞例规则,作器人“曾侯”与被嫁女“季姬”也有了明确的亲属关系,且与以往观察到的媵器制作惯例相符。曾国为姬姓诸侯国,增补铭文中的“季姬”即为曾国的女子;“嬭”为楚姓,铭文中另一位女子“汤嬭”从其族姓看应为楚女,这样一来,此器铭文所记录的应是“一器媵二女”的情形。而姬姓曾国国君为一位嬭姓(即楚姓“芈”)女子制作媵器,使这件器物成了罕见的“异姓媵”的重要例证。下面将曾侯乍季汤嬭媵鼎作为记载春秋时期“异姓媵”的重要材料,结合其他相关案例,系统分析这篇铭文所记载的婚姻关系,并就春秋时期的异姓媵现象进行讨论。
一、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所见婚姻关系
通常,媵器铭文的释读难点在于通过作器人和出嫁女的身份来解释铭文背后的婚姻关系。增补过的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中出现了两位女性:“季姬”是姬姓曾国之女,是作器人“曾侯”排行为“季”的女儿;另一位则是作为“异姓”出现的“汤嬭”。这种为自家女与异姓媵女共同作器的情况在金文中还有数例,详见表一。
这些铭文在记录女性称名的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共性。陈昭容认为这类铭文“嫡先媵后,次序分明”[3]215,刘丽则总结称“一器媵二女器类的铭文格式,大体是前一个为自家女,后一个为异姓女”[6]。单从女性称名方式来看,当一篇媵嫁器铭中出现两位不同姓的女性时,她们在称名形式上的差别反映了她们同作器人的亲疏关系。其中仅有一名女性的称名里带有排行,其称名格式为“排行+族姓”,这位女性通常来自作器人的家族[7];另一位“异姓女”则在称名中同时携有族氏,如表一所见“邛嬭”“秦嬴”和“番妀”都是典型的“族氏+族姓”的称名格式,用来准确指称其出身。如曾侯乍季汤嬭媵鼎和曾侯簠的作器人“曾侯”分别称呼本族女性为“季姬”和“叔姬霝/叔姬”,上鄀公簠的作器人“上鄀公”称本族女性为“叔嬭”;称呼异姓女子时则带上了族氏,即“汤嬭”“邛嬭”“番妀”等。樊君鬲的铭文则比较特殊,仅用了单字族姓“嬭”标识出了异姓媵女。
前文提到,异姓媵女的称名中往往携有族氏,比较常见的是携带父亲宗族的族氏,如表一中出现的“秦嬴”和“番妀”。秦嬴为秦氏嬴姓自不必赘述,而通过周王为妻子番妀所作王作番妀鬲(铭图2870),可知“番妀”为周王妻子的父国(氏)父姓,故番氏为妀姓[6]——这两位女性的称名均属于典型的“父氏+族姓”的形式。但曾侯簠和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中出现的“邛嬭”和“汤嬭”是出身楚国的嬭姓女子,她们的称名显然没有采用“父氏+族姓”的形式。
关于传世品曾侯簠铭文中的女性称名,学界多有讨论,其中罗运环认为铭文中的“邛嬭”当为楚国再嫁之女,称名携带的族氏“邛”为前次婚姻的夫家族氏[8],笔者以为这一看法值得重视。曾侯簠铭文中明确记录了制作这件媵器的婚姻场合是“叔姬霝乍黄邦”,作器人为“曾侯”,缔结婚姻关系的双方是姬姓曾国和嬴姓黄国,出嫁的女性“叔姬霝”是曾国之女,“邛嬭”在这场婚姻中充当着异姓媵女的角色。在媵器銘文中,女子称名除“父氏+族姓”的形式外,另有“夫氏+族姓”的形式,如楚王媵邛仲嬭南龢钟(铭图15247),铭文作“唯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邛仲嬭南龢钟,其眉寿无疆,子孙永保用之”,邛仲嬭即楚国嬭姓女子嫁于邛国者[6]。
目前学界多认为“邛当即江黄之江”,江、黄是周代南方相邻的两个嬴姓诸侯国,江在今河南省正阳县东南、息县西南一带[9],故而“邛嬭”可能是一位出身嬭姓楚国、嫁入嬴姓邛国的女性。按此理解,曾侯簠铭文所记录的便是曾国与黄国联姻,楚国以再嫁女陪媵。而作为陪媵的异姓女,邛嬭仍保留着前一次婚姻的夫家族氏,这也是为何会在曾侯簠铭文中同时出现曾、黄、邛三个国名。
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在格式上与曾侯簠尤为接近。按此逻辑推测,“汤嬭”应是位来自楚国曾嫁入“汤”的女性。
“汤”从“昜”得声,在此应当读为“唐”。2001年湖北郧县出土一批春秋时期唐国的铜器,铭文中的“唐”写作从“牛”从“昜”的字形[10];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新见的唐侯制随夫人诸器铭文中的“唐”字则从“土”(图二)。黄旭初、黄凤春曾指出,“唐”字古文从“昜”,与从“昜”得声的字相通[10]。故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中的“汤”亦从“昜”得声。宋国支族子姓荡氏的“荡泽”在《左传》中亦称之为“子山”,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称为“唐山”。“子山”之“子”强调的是其子姓,“唐山”之“唐”则代表的是其族氏“荡”。通常男性所在族氏不会随意更改,《左传》中作为宋国支族族氏的“荡”与《史记》中的“唐”当为同一古字的不同转写,而这个字应该就是一个从“昜”的字。从“水”的“汤”虽不是“唐”在古文献中常见的写法,但古文献中“荡”“唐”相通的例子证明了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中的“汤”可读作“唐”。
根据上文,我们确认“汤”即毗邻曾国、同为“汉阳诸姬”的唐国[11]。《国语·郑语》云:“应、蔡、随、唐,皆姬姓也。”[12]461《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了楚国“克州、蓼,服随、唐”,可知直到春秋晚期曾(随)国和唐国仍存在,并且已经成为楚国的附庸。因而汤嬭的“汤”在这里是作为这位女性过去的夫家族氏出现的,这个称名指示的便是一位出身楚国、嫁入唐国的女性。
春秋文献中亦不乏以再嫁女陪媵的记载,《国语·晋语》所载“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12]333,就是以晋怀公之妻怀嬴作为媵女再嫁晋文公,并且仍以她上一次婚姻的配偶晋怀公的称号来称呼她,可知这种称名习惯并不限于金文辞例。相比史籍中关于再嫁女陪媵的记载,本文讨论的曾国媵器记载的以异姓再嫁女陪媵的媵婚关系则更为特殊。
二、春秋时期的异姓媵问题
自同一国纳娶多女在春秋时期是诸侯婚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13,14],且以“侄娣从”为代表的同姓陪媵为主。如《左传》所载:纪国先后娶鲁伯姬、叔姬,“冬十月,伯姬归于纪”[15]21,“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15]52;卫庄公“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15]30;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15]239;鲁庄公娶齐哀姜、叔姜,“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15]263;晋文公同娶秦五女,“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15]410;鲁孟孙穆伯娶莒戴己、声己,“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则为襄仲聘焉”[15]562;杞桓公娶两位鲁叔姬,“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15]587;鲁臧氏宣叔娶铸妊、铸妊侄,“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纥,长于公宫”[151082;齐侯娶颜懿姬、鬷声姬,“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151048;鲁襄公娶胡敬归(媿)、齐归(媿),“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15]1185;卫太叔疾娶宋子朝之女及女娣,“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15]1665。
在当时的婚姻家庭关系中,以侄娣为媵的优先性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李玄伯先生所说,侄娣为媵的婚姻关系非但“婚约是连带的”,“生子亦系连带的”[16]。考之《诗·召南》疏:“妾之贵者,夫人侄娣也”,也说明夫人之侄娣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庶妾[17]。按照“媵不书”“媵,浅事也,不志”的规则,绝大多数情况下,媵女被史书提及的原因是嫡夫人无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鲁国敬归之子卒,季武子欲“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鲁穆叔规劝道:“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15]1185“适”通于“嫡”,从“非适嗣,何必娣之子”一语可知,春秋时在嫡夫人无子的情况下,侄娣之子往往被立为继嗣者。这一记载意味着,或许在一些婚姻中可以一次遣嫁多位媵女,但在继嗣次序上唯有与嫡子母系同宗的侄娣之子适合作为嫡子的“替补”。从血缘角度看,选择侄娣的后代可以确保婚姻的后嗣仍是最初缔结婚约的两个家族的后代,这也是一种在应对难以预料的生育问题时试图人为维持“两姓之好”的手段。
相比之下,异姓陪媵则是比较罕见的陪媵形态,其与同姓侄娣陪媵存在着本质区别。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异姓媵”案例是春秋时期宋国迎娶鲁共姬时卫、晋、齐三国来媵,这是典型的多国遣女陪媵他国且陪媵中有异姓媵的案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对此事分别记录、评述如下:
(1)《春秋》成公八年经:卫人来媵。
《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15]840。
《公羊传》: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18]402。
《榖梁传》: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尽其事也[19]336—337。
(2)《春秋》成公九年经:晋人来媵。
《左传》:晋人来媵,礼也[15]844。
《公羊传》: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18]404。
《榖梁传》: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19]339。
(3)《春秋》成公十年经:齐人来媵。
《公羊传》: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三国来媵,非礼也,曷为皆以录伯姬之辞言之?妇人以众多为侈也[18]407。
这场牵扯四国的复杂的婚姻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样是遣女陪媵鲁女,卫国意在巩固同盟关系,晋国意欲缓和与鲁之间因归还汶阳之田所造成的不快,齐国则试图弥补汶阳事件造成的齐、鲁矛盾[20]。值得注意的是,卫、晋、齐三国陪媵鲁女,卫、晋同鲁国均为源于周室的姬姓国,齐国则属异姓国,对比前引《春秋》三传的评述,与鲁同姓的卫、晋陪媵,《左传》均称“礼也”,且特别说明“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对于齐媵女则仅记“齐人来媵”,不言是否合乎礼制,且《公羊传》还提出“三国来媵,非礼也”,说明至少在《春秋》所遵循的礼制框架中,异姓媵可能并不合乎礼制。
从这个材料出发,再来观察那些记载异姓媵事件的青铜媵器铭文,不难发现异姓媵通常发生在较为复杂的历史政治语境之中。除了前文所述的两件记录有异姓媵事例的曾国媵器,鄦子妆簠铭文也记录了两位不同姓氏的女性。鄦(许)为姜姓,“孟姜”当为作器人鄦子妆的大女儿,“秦嬴”则是这场婚礼中的“诸侯女来媵者”[21]。这些异姓媵女的出身国通常都是这场多方婚姻关系中的“大国”,如曾侯簠和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中的异姓媵女均出身楚国,鄦子妆簠铭中的异姓媵女来自秦国。同样,在宋国迎娶鲁共姬而卫、晋、齐三国来媵的案例中,作为异姓媵出现的齐国也是这场婚姻关系中与鲁国地缘最为相近、受其影响最大的“大国”。
在周人所建的南方诸侯国中,曾国地位颇为显赫,正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22]:曾国初封时,周室期望其与蔡、应等一众“汉阳诸姬”共同“涉政淮夷”,曾国因而成为周人经略南方的前沿重地;到昭王南巡时,曾国又受赐甬钺,并获准“用政南方”①。与这种地缘政治地位相对应,曾国在以姬姓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婚姻网络中也占据着核心位置,如曾国与周边的嫚姓邓国和嬴姓江国、黄国等均多有通婚。黄尚明曾指出,曾国缔结的“本土化”婚姻关系始于西周中后期,目的是为了结成政治同盟以对抗日益强大的楚国,与此同时曾国也时常和楚国联姻[23]。这与姬姓鲁国在山东地区的情况非常类似——鲁国一方面积极与东方诸国缔结婚姻,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近邻强国齐国的影响,并与之联姻[23]。从这一点来看,本文探讨的曾侯乍季汤嬭媵鼎及曾侯簠的铭文很可能展现了以曾国为核心的区域性通婚关系的另一面,即曾国在与黄国这样的“土著”邦国联姻时,也很难完全拒绝来自楚国的影响,而楚国派遣媵女以异姓媵的方式陪嫁,本质上是用异姓媵这种周人婚姻制度中的变例来控制和干涉毗邻的姬姓诸侯国。迫于周边大国势力的影响,曾、鲁等姬姓诸侯国不得不容许楚、齐遣异姓媵女参与到自己的联姻活动当中,从而打破了沿袭自西周的通婚旧制,楚、齐等非姬姓国家借由婚姻关系开始干预周人建立起来的以姬姓为核心的婚姻政治网络。
正所谓“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无论是在周王畿地区,还是周人出于经略东方、南方的目的建立的诸侯国之间,都可以观察到以姬姓宗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区域性通婚网络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政治网络。从这个背景出发可以看到,自同一宗族选取陪嫁媵女在春秋时期颇为常见,在缺少嫡子或嫡子早夭的情况下,以嫡妻同宗女性的子嗣替代嫡子,能确保继嗣者是联姻的双方宗族的直系后代[24,25]。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婚姻关系常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纠缠在一起,这使得媵嫁作为“礼之轻者”反而成为了政治的延伸[19]115。“异姓媵”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非姬姓大国绝非偶然,这些新兴大国参与进以姬姓为核心的周人通婚网络,在本质上改变了以姬姓宗族为主体的周人婚姻政治关系。
三、结语
根据常见的媵器铭文辞例对曾侯乍季汤嬭媵鼎铭文进行增补,发现这件器物不仅是“一器媵二女”,其铭文记载的媵婚关系还是罕见的“异姓媵”。铭文中的异姓媵女“汤嬭”应为二次出嫁的楚女,称名中作为族氏出现的“汤”为位于江淮一带的姬姓唐国。该鼎是曾侯为女季姬及楚国再嫁媵女汤嬭所做的媵鼎。
春秋时期常见诸侯嫁女以多人陪媵的史事,然而文献中所见的媵婚常以同姓陪媵,其中又以同宗姐妹陪媵的“侄娣往之”的形式最为普遍。考虑到以侄娣陪媵的制度通常与宗族继嗣者的选择有直接关系,罕见的异姓媵记载很可能只是媵婚制度中的变例,且通常孕育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数例异姓媵,可以看到以异姓身份陪媵的女性通常出身于非姬姓大国,如秦国、楚国、齐国等。这种情况表明,以异姓陪媵很可能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缔结婚姻关系时寻求利益平衡的一种手段,尤其当周室逐渐衰微时,势弱的姬姓诸侯国不得不面对邻近异姓大国所施加的影响,异姓媵就成了这类异姓大国参与乃至干涉以姬姓为核心的婚姻政治网络的一种比较特别的形式。
————————
[1]方勤,吴宏堂.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2]黄锦前.读近刊曾器散记[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8年:总捌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65—76.
[3]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分与角色研究之二[G]//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二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193—278.
[4]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8:535—536.
[5]曾攀.浅析“曾侯作季汤嬭媵鼎”铭文[J].江汉考古,2019(6).
[6]刘丽“.一器媵二女”现象补说[G]//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199—204.
[7]李峰.西周宗族社会下的“称名区别原则”[N].文汇报,2016-02-19(W14).
[8]罗运环.古文字资料中所见楚国同各诸侯国的关系[C]//罗运环.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13—432.
[9]肖启荣,黄锦前.“邛”“江”考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1).
[10]黄旭初,黄凤春.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J].江汉考古,2003(1).
[1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36.
[14]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26—27.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6]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257—258.
[17]黄以周.礼书通故[M].北京:中华书局,2007:274—275.
[18]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9]柯劭忞.春秋榖梁传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0]曹晓伟.春秋时期媵婚研究[J].理论学刊,2014(4).
[21]吴闿生.吉金文录[M].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8:245.
[23]黄尚明.从青铜器铭文看曾国贵族的婚姻关系[J].江汉考古,2017(4).
[24]JULIAN PITT-RIVERS. The Kith and Kins[C]// JACK GOODY. The Character of Kin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25]MALVIN P THATCHER. Marriages of the Ruling Elit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C]// RUBIE S WATSON,PATRICIA B EBREY.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責任编辑:陈宁〕
————————
①“用政……”的辞例还见于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的“用政蛮方”和焂戒鼎铭文中的“用政于六师”,这种表达同禹鼎铭文中“政于井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系年》篇中的“政东方诸侯”类似,即“统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