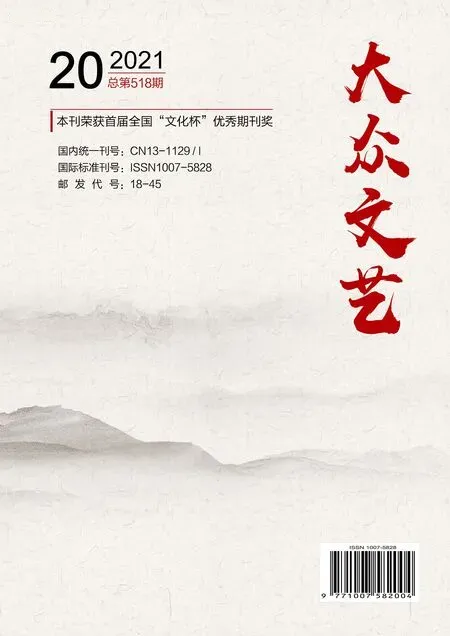京剧《贵妃醉酒》中的场景及人物狂欢艺术解读
吴婧茜
(天津传媒学院,天津 301925)
《贵妃醉酒》是梅派京剧创始人梅兰芳先生受1913年上海发起的“戏剧界革命”的影响,打破“青衣”的传统表演规则,在老戏《醉杨妃》的基础上修改排演的一部戏剧艺术作品。这出戏剧一经上演,便艳惊四座,在国内外的戏剧舞台上,皆获高度赞誉。《贵妃醉酒》也因此成了众学者纷纷研究的对象。
《贵妃醉酒》主要讲述了宠妃杨玉环在遭遇唐玄宗失约百花亭后,郁闷饮酒,醉后忘形的故事。整体情节看似简单,但剧中人物却为观众演绎了一场冲破常规,打破身份约束的后宫狂欢。这种狂欢情节的设计与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不谋而合。巴赫金理论中“狂欢”二字的核心在于人们在狂欢活动中能够短暂地实现精神的自由、情绪的宣泄和角色的置换。本文结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场景的设定、人物的设计两方面入手,对《贵妃醉酒》中体现的“狂欢化”艺术进行解读。
一、场景的狂欢艺术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至文艺复兴时期风靡欧洲的“狂欢节”庆典活动的基础上分析概括出的一套诗学理论。而举办狂欢节的广场在全民的狂欢活动中不但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性元素,也是人们释放情绪,追逐平等自由的重要空间。巴赫金在“狂欢化”理论中特意提出了“广场元素”的概念,他指出“狂欢广场”“是情节上和现实中都可能出现的场所”,而这个场所又必须是可以容纳各类人,具有一定空间开放度的,能够让人们在此相聚,产生交际的地方,比如街道、公园、酒馆等。
《贵妃醉酒》中发生情节的两大场景都具有“狂欢广场”的特质。第一个场景是杨玉环从寝宫移驾百花亭的一段路程。这段移驾的过程被学者们称之为“游园”。而“游”字,揭示了这一情节的发生地并非单一场景,而是一段具有转换性及延展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不论是贵妃仪仗经过的宫道还是主仆众人驻足游览的玉石桥都因具有开放性及公众性的特点,而与巴赫金提出的“广场元素”定义相吻合。尤其是在玉石桥这一场景中,贵妃斜倚栏杆,悠然自得地同众人一起欣赏鸳鸯戏水、锦鲤欢游、大雁并飞的一幕,更是突出了场景中的元素设置对作品狂欢化氛围的衬托作用。在这段具有“广场”特质的开放性空间中,贵妃与众人不仅产生了言语上的互动,更是达到了情绪上的愉悦同步。在这里,封建社会主仆之间的身份隔阂,在欢快的游园气氛中逐渐消失,达到了众人同乐、和谐共融的“狂欢化”状态。
第二个狂欢场景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百花亭。众人备齐酒宴,只等唐玄宗圣驾到此,却得到“驾转西宫”的消息。在这个固定的场景空间中,杨玉环在众人的轮番进酒下,上演了借酒消怨,醉后行为上放飞自我的全过程。尤其是贵妃微醺后的下腰饮酒,换装后踉踉跄跄上演的一出“拈花”,更是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贵妃醉后的媚态以及贵妃“忘我”的狂欢。在百花亭中,杨玉环打破了身份和礼教的约束,短暂性地获得了情绪上的宣泄及天性的解放。在这里,所有人都破除了身份上的隔阂。高力士与裴力士身为仆从诓驾贵妃,贵妃醉后也可以短暂性失态调戏众人。可见,百花亭正是巴赫金诗学理论中所谓的“狂欢”场景。
所以,不论是一段路程还是一个固定的场景,“广场元素”的存在都是为了给人物创造一个可以暂时脱离现实世界规矩教条,实现狂欢的空间。场景元素的巧妙设定,不仅增强了戏剧的欣赏价值,渲染了“狂欢”氛围,也加深了观众对主角情感的理解。
二、人物的狂欢化设定
巴赫金在他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中指出,人物角色的设计也可以带有狂欢化的色彩,而往往以“狂欢化”的形式塑造出来的人物都是复杂的矛盾体。因此,狂欢化人物的内在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且呈现的形式非常极端。关于人物的设定,巴赫金还提出了“加冕”和“脱冕”的概念。“加冕”即在狂欢节活动中,众人让乔装打扮好的小丑拥有国王的待遇;而“脱冕”则指在狂欢节活动结束后,小丑被卸去国王身份,又回归原本的自己,被众人嘲笑。这样迅速且充满颠覆性的身份转换,完美展现了巴赫金认知中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即“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在强烈的变化刺激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隐藏的潜意识也得到了释放。在京剧《贵妃醉酒》中,人物的“狂欢化”也是通过角色“加冕”和“脱冕”的过程展现出来的。
(一)贵妃的“脱冕”
《贵妃醉酒》中,主要角色杨玉环的人物设定便极具狂欢化色彩。杨玉环是后宫中深得皇帝喜爱的贵妃,地位尊贵,风光无限。剧情中,杨玉环应唐玄宗之邀,满心欢喜地赴约百花亭,不想却遭遇皇帝失信“驾转西宫”。这样的变化,使杨玉环瞬间从“后宫粉黛三千众,三千宠爱一身专”的宠妃变成了众人眼中的“弃妃”;由众人高捧的贵妃瞬间变成了众人心中的笑柄。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身份降级,是角色的“脱冕”。这次“脱冕”从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贵妃的身份固然尊贵,却也始终是皇帝的附属品,只能被迫忍受这种随时可能被夺走的“不完整爱情”。于是,贵妃心中抑郁,在百花亭中借酒消愁。在整个饮酒过程中,杨玉环是一步步逐渐“脱冕”最终达到解放天性的状态的。和最开始以扇、袖遮面,小口酌饮的端庄行为比起来,接下来的大杯痛饮、衔杯下腰饮酒,久醉不归,摘下高力士的帽子引逗不还、学男人走路等情节的发生,使杨玉环由一位身份高贵、举止端庄的贵妃逐渐变成了一位醉后放浪形骸,可以和侍仆肆意嬉笑打闹的女子。这些贵妃醉后的“反常态”行为,颠覆了封建社会定义下贵妃的身份和权威,正如巴赫金所说,是“狂欢化”人物“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嘲弄、戏耍、歪曲与戏仿”,也是贵妃对封建礼教不满的宣泄及对封建男权制度下不平等男女关系的反抗。而角色形象前后的极大反差,则是贵妃成功“脱冕”后的狂欢艺术表现。在“诓驾”这段戏中,杨玉环被高裴二人联合诓骗的剧情设计,使原本在下人眼中需要“小心侍奉”的贵妃突变成了被下人联合起来欺骗的对象,这是角色的“脱冕”,也是封建社会中主仆本对立关系的体现。
《贵妃醉酒》剧情中杨玉环几次经历“脱冕”导致的颠覆性形象转变,使人物更为丰满,也更真实化。这种颠覆性的“脱冕”,意味着原本角色身份的暂时“死亡”以及新身份的短暂“诞生”。杨玉环借助醉后的新身份实现了贵妃身份的解脱,达到解放天性的状态,同时也表现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对逃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平等自由的向往。
(二)高力士与裴力士的“加冕”
《贵妃醉酒》中,除了杨贵妃这个主要角色之外,两名随行的侍仆高力士与裴力士也是推动剧情的重要人物。剧中的高裴二人,都是善于察言观色又慧心妙舌,懂得分寸又行事谨慎圆滑的人。从贵妃一出场,高力士与裴力士便极尽所能地小心侍奉,这是身为后宫下位者需履行的日常职责。在后宫,上位者掌握绝对的权力,坐享荣华。而地位卑微的仆从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并时刻保持清醒谨慎。这是权力拥有者与被役使者之间对立关系的体现。但随着杨玉环的逐渐“脱冕”,高力士与裴力士便获得了“加冕”。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主仆有别,身为贵妃的杨玉环醉酒之后,面对侍仆高力士与裴力士,下腰饮酒的做法是有失身份、不合礼法的。但是在这场饮酒狂欢当中,却真实地发生了。这种打破主仆关系的情节设计,是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打破正常秩序,颠覆正常逻辑的行为体现。除此之外,高力士与裴力士在百花亭中合谋上演的一出“诓驾”,也是二人“加冕”的体现。一直求生欲极强,小心侍奉着贵妃的高裴二人,在贵妃醉酒之后,竟大胆诓骗贵妃,瞬间由小心侍主的仆从变成了贵妃权威的挑战者。这种打破常规的行为,类似于巴赫金理论中小丑被“加冕”后拥有的与原身份不相符的短暂性特权。但每一次角色的“加冕”或“脱冕”都是相伴而生的且“加冕”的有效期并不长久。所以,在高裴二人对贵妃实施“诓驾”之后,便遭受了来自贵妃的泄愤。随着贵妃的重新“加冕”,回归高位,高力士与裴力士也“脱冕”回归了侍仆的身份。双方身份的归位及高裴二人在剧中“加冕——脱冕”的过程,体现了狂欢世界的戏剧性。
(三)“隐形”人物——唐玄宗的“脱冕”
在《贵妃醉酒》中,还存在一个隐形的线索人物。称其为“隐形的线索人物”,是因为在整场演出中,这个人物既没有登场,也没有任何台词。但他的那些以旁人转述的方式呈现出的举动却主导了整个故事的发生及后续情节的戏剧性转变。这个人物就是皇帝唐玄宗。古代社会以“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衡量君子、绅士的标准。而皇帝作为古代封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更应言出必行。但《贵妃醉酒》中塑造的皇帝唐玄宗,却没有做到诚信待人。剧情中,唐玄宗不守约定的任性做法是有失君王体面的。这次失约使众人眼中一言九鼎的皇帝变成了失信之人。而在杨玉环的心中,唐玄宗也由一位深情专一、自己深爱的男子变成了一位薄凉绝情、自己怨恨的男子,这是角色的“脱冕”。对于唐玄宗的失约,众人也许皆怀怨气,却无人敢做出直面的指责和对抗,这是众人对于封建君主权威的低头。在这部戏中,唐玄宗这一人物及他的“脱冕”都是隐形的,却牵连着所有人的悲喜,间接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主所拥有的最高统治地位及权力,也反映了等级制度之下,人们生活的压抑与艰难。
三、结语
综上所述,梅兰芳先生改编的京剧《贵妃醉酒》中对于狂欢化场景的设置,不仅给戏中人物提供了平等对话,破除身份禁锢,消除等级隔阂的空间,也为观众在舞台上营造了一个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所提道的“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的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而戏中人物的“加冕”和“脱冕”则是人物狂欢化的体现。这种身份的短暂转变不但可以使剧情变得起伏跌宕,同时也加强了人物形象的饱满度。所以,京剧《贵妃醉酒》中贵妃上演的酒后狂欢,不仅揭示了封建男权社会下,身为后宫女人心中的痛苦,也表现了贵妃对打破身份禁锢,实现男女平等的追求,是封建社会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