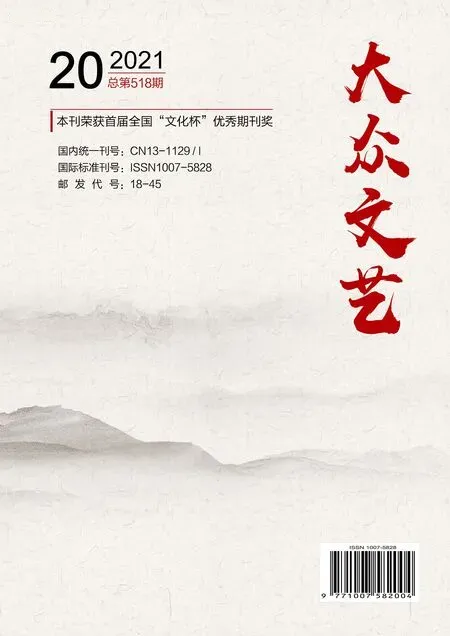《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边缘群体的救赎
党文利
(南昌大学,江西南昌 330031)
对于如何处理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矛盾,实现边缘群体的救赎这一问题,魏斯伯格曾通过对犹太人的研究,将边缘人的生存方式划分为四类:平衡、同化、回归、超越。
一、平衡
平衡意味着遵从,而非解决边缘性问题,即当边缘群体身处主流世界,一味地屈从,抛却内心的焦灼与个体的反思。此时的边缘群体属性未变,但是话语权却进一步丧失,最终成为绝对的边缘人。克莱文杰对约塞连因恐惧而逃避战争的行为嗤之以鼻,大加指责,俨然成为“第二十二条军规”忠实的捍卫者;哈弗迈耶疯狂地迷恋着飞行,甚至在前期作战时从不采取规避动作,而是要亲眼看着“炸弹落地开花,喷射出橘黄色的火焰”,似乎在满足一种变态的快感。这个荒诞的非理性世界一方面使飞行员感受到直接的压迫,另一方面又让其处在一种“温水煮青蛙”似的状态之中,渐趋盲目沉沦,似乎被压迫的理所当然,而反抗自然不具有任何意义。此时,边缘群体选择以平衡的方式向主流群体妥协,其自我意识也在渐趋瓦解,直至沦为主流群体的附庸。
然而,相对于主流群体,边缘群体在力量方面势必处于弱势,甚至当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时,就会出现被迫的服从。罗曼•先钦《叶尔特舍夫一家》中叶尔特舍夫一家人在被逼无奈之下从城市搬往乡村,开始他们的边缘人生活,起初叶尔特舍夫和妻子瓦莲京娜极度不适应乡村的生活,并且对乡民们的陋习与粗俗嗤之以鼻,可日子总的过下去。为了生活,为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一家人也开始了售卖兑水酒精的勾当,在现实的困境中挣扎求生,精神也渐趋迷失。相对于哈弗迈耶无意识的服从,叶尔特舍夫一家的屈从起初是为了生存,也即他们是在意识到自我的不良境遇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但是,以上结果均显示出,一旦边缘群体妥协沉沦,无论是自我意识丧失还是被逼无奈,其结局均为在困境渐趋迷失自我。
二、同化
所谓同化,即为主流群体接纳吸收,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面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地位权力的高低,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势必存在极大的冲突。此时,边缘群体渴望发声,其反抗之音必定损害主流群体的利益。而主流群体在压制其反抗未果时,便会想方设法以利益诱之,将其纳入自我的阵营。当约塞连行事过于乖张,甚至威胁到卡思特之流的地位荣誉乃至生命安全时,科恩中校同意让其回国,不过要其答应一个卑鄙的交易——“喜欢我们,加入我们中来,做我们的伙伴。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回国以后,都要替我们说好话,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项卑鄙交易的目的就是让约塞连为主流群体所同化,与他们同流合污,成为这个荒诞世界的维护者,从而继续迫害像约塞连一样的飞行员。约塞连最终放弃这个罪恶的交易,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回国的理由是已经完成了五十次以上的飞行任务,而不是官方报告中伪报的原因--为救卡思特上校而被纳粹刺客所伤。这种对同化的拒绝与反抗或许会使边缘群体面临绝处逢生的境遇,也即“柳暗花明又一春”,就像拒绝了罪恶交易的约塞连获得精神的救赎一般;但是,也有边缘群体秉持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愚勇,带着自以为决绝的勇气进行无谓的反抗,最终丧失存在的意义。
同时也有边缘人主动融入主流群体中,希望掌握话语权,成为具有自身价值的“备受尊敬的边缘人”,进而为边缘群体发声。桑拉德•希斯内罗斯的《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埃斯佩朗莎意图通过写作的方式“走出限制女性个体的空间”,获得边缘话语权,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这种积极地融入并非对原始族裔的抛弃,而是对作为边缘群体的墨西哥族裔的真正救赎。埃斯佩朗莎的积极融入与约塞连的反抗不同,她是通过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进行微妙的抗议,但是二者殊途同归,其目的与归属都在于话语权的获得。然而,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调和性,这就使得群体之间的融入并非易事。如在现实的文学创作中,许多拉美女性作家希图通过写作的方式融入主流作家行列,但是,文本的虚构性与现实的残酷性让这种融入及其结果似乎流为空想。
三、回归
所谓回归,即边缘群体在试图融入主流群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遭受灭顶似的打击,最终不堪重负,选择重新回归本群体。约塞连起初因为一时的软弱答应了科恩中校和卡思卡特上校提出的“卑鄙交易”,事后意识到官方报告的虚伪性与交易的欺骗性,最终选择了放弃,以“开小差”的方式逃往瑞典;后期作战,炮火重重,甚至连痴迷于飞行投弹的哈弗迈耶也开始做出狂野的规避动作来,甚至在听说约塞连可以回国时,请求如果被允许带一个人回去一定要考虑他,这种对战争态度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被主流群体真正接纳的不切实际性。边缘群体选择回归,同样会继续面临渐趋丧失话语权的困境,甚至不为边缘群体所接纳,彻底沦为帕克所说的“边缘人”。如移民在接受异族文化时有着强烈的不适感,但又抛弃了己族文化,在两种文化中无法寻找到自我真正的归属,沦为两种社会与两种文化的边缘人。
同时,边缘人回归也存在着意识到作为边缘人享受的待遇优于跻身于主流群体的境遇,无论这种优待是精神上的满足还是物质上的给予。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主人公匹普不满自身地位的低下,努力跻身上流社会,享受作为主流群体的话语权,但在此过程中,经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最终回归本性,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当切尔诺贝利遭受核辐射侵蚀时,部分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听从官方的要求撤离,而是选择留在故土,其留下的原因并非眷恋故土,反而是因灾难而受到政府的救济故而不愿离开。对于追求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抑或物质上的优遇的选择,我们不做道德上的批判,仅从边缘群体生存方式而言,是否应该选择回归,回归后该如何自处的问题亟待大众的思考。
四、超越
超越意味着选择第三条道路来克服两种文化、两个群体的对立与冲突,这种超越一方面针对个人,另一方面面向集体。奥尔预先演习过多次飞机跌落时的状态,学会了海上谋生的手段,甚至其准备的逃生工具明晃晃地放在飞行员面前都未曾惹人怀疑,最终成功逃往瑞典,他已不再是皮亚诺萨岛甚至整个美国荒诞氛围笼罩下的边缘人物,从而在个人层面上摆脱了两个群体对立对自我的束缚。约塞连的逃离在文本中留下空白,但是其从头到尾的抗争行为对飞行员和军官都产生了影响,如随军牧师由最初对约塞连的疯狂感到震惊到认识到他并不是一个怪人,并为之提供帮助,直至为约塞连可以回国而激动不已,甚至感染到自己,提出要与卡思特们抗争到底。由此可见,卡思特上校与科恩中校提出的卑鄙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边缘群体的和解。同样,约塞连的抗争行为对于两个群体产生的这种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超越。这种基于个人与集体的超越使得横跨在两种文化上的对立与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也使个人甚至群体得以处于矛盾暂时消解的和平阶段。
这种超越也意味着两个群体的妥协,但是横跨在群体间的障碍并未得到有效的消除,反而在这种妥协中愈演愈烈,最终演化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莫里哀的《伪君子》作为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妥协的产物,得以在剧院上演,但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的消除,资产阶级作为古典王权时期的边缘性存在必将随着时代的演进与封建王权进行此消彼长的斗争。也即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矛盾根深蒂固,表面消解的冲突中实则蕴藏着更大的矛盾,唯有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才能使群体对立短暂消除,进而形成符合社会潮流的又一新的群体间的对立。
因此,当边缘群体面临为主流群体所排斥的状况时,其可以选择的出路不尽相同。首先,边缘群体在数量上或许与主流群体旗鼓相当甚至更为庞大,但是话语权力的拥有使得二者无法达到势均力敌,此时,边缘群体便面临着无意识的屈服与迫于生计妥协的状况。其次,一旦固有的矛盾激化,二者发生激烈的对抗冲突甚至威胁到话语权的归属问题时,双方将面临是否接纳和主动融入的选择。然后,当边缘群体主动融入寻求自我和群体的救赎抑或放弃自我的意识与主流群体同流合污,继而发现自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或者意识到作为边缘群体能够享受的待遇更甚之时,便会选择回归的道路。最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性质与力量随之发生变化,二者或许能够通过第三条路超越两个群体间的文化对立与冲突,实现社会的变革,进而形成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的群体间面对话语权的争夺,周而复始。然而,这种超越并非停留在同一层面上的无限循环,而是秉持着否定之否定的理论逻辑,螺旋式上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