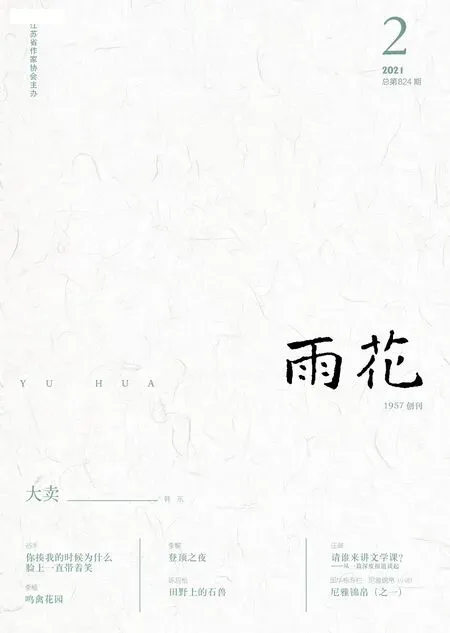游目骋怀
儿子·老子·母亲
一
徐悲鸿、蒋碧薇之子徐伯阳曾因一次不当作证,深陷舆论风暴中心。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可知事情过程约略是:
2007年底,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北京饭店、首都博物馆展出作品,其中一幅由海外藏家提供的站立女人体油画作品,标为徐悲鸿创作油画《裸女·蒋碧薇女士》,分外吸睛。该画背面有时年八十岁的徐伯阳亲笔题字:“此幅油画《裸女》确系先父徐悲鸿之真迹,为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物。徐伯阳,2007年9月29日。”并缀留鲜红名章。随后,此画正面、背面照片,以及徐伯阳与画作的合影,均在媒介广泛传播,此画被推许为“徐悲鸿油画人体写生作品的一个重要代表”。细心者不难发现,徐伯阳所言《裸女》,在宣传时,已换上新名《裸女·蒋碧薇女士》。
经过大规模缜密的造势铺垫,此幅被认定为徐悲鸿创作的高94 厘米、宽56 厘米的油画作品,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2010 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隆重登场,以人民币七千二百八十万元的价格成交。
名家作品拍出天价;收藏者如愿以偿地猎获中意之物;艺术品受到尊重,亡故的艺术家声誉得以弘扬,存世的艺术家后人与有荣焉;拍卖公司亦因征得高端拍品并成功拍售,彰显公司声名,同时收取丰厚佣金——这真是多方共赢、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孰料,喜事未能画上圆满句号,却乐极生悲。时隔近十五个月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十名学生联名举报,这幅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注意!画作又易名了。但由于缺乏资料,无法确定此番画名变换究竟系拍卖方所为,抑或是举报者笔误),实为他们同学中的某位在1983年5月的一堂人体油画课上的习作,习作模特是江苏农村来北京工作的女孩L,完全不可能是徐悲鸿前夫人蒋碧薇。他们还公布了五幅与《人体·蒋碧薇女士》场景、人物特征相同的课堂习作作为佐证。
证据确凿,瞬时引爆舆论场。海外藏家是如何获得此画并让徐伯阳签字作证的?拍卖公司是眼力太差,还是另蓄盘算?至于“错认”母亲的徐伯阳,更成为舆论“箭垛”。画中模特是个江苏农村进京谋生的女孩,蒋碧薇当年虽也是从苏南小镇走出来的,但那女孩不是这女孩……“衣服脱了,就认不得妈了吗?”网民如此嘲讽。刻薄,却可以理解。
二
五代·汉·王仁裕的《玉堂闲话》中,记载了一件奇葩之事:
长安完盛之时,有个面容似是二十岁左右的道士,自言年龄已达三百余岁,称得益于长期服食丹砂,所以不显苍老。京都人都很羡慕这个“活神仙”,争相登门请教长寿之道,购买其配制的仙丹,一时门庭若市。有天,数位朝廷官员前来拜访道士,聚饮正欢,门人进来禀告道士:“您的孩子从老家来了,想见您。”道士闻言大怒,叱骂其子不已。同席客人听后,忍不住说情:“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眉不悦片刻,顾及说情者颜面,方吩咐门人:“叫他进来。”于是,见一位满头白发、弯腰曲背的衰弱老叟,进来拜见道士;礼毕,便被道士责令去里屋。然后,道士缓缓地对客人们说:“我这个儿子太愚昧了,让他服食丹砂,他不肯服食,结果……你们都看到了,尚不及百岁,竟苍老如此。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所以,一直让他住在乡下老家。”坐客听后,对道士愈加信服,奉之若神。后来,有人私下查问知晓这个道士根底的人,方得悉那位佝偻老叟,竟是此道士的老子。
王仁裕笔下的这个妖道,只为了糊弄世人骗取金钱,竟然指父为子,与父串演双簧。现在,徐伯阳竟于显见不是徐悲鸿创作的油画背面贸然签字,证明此画确系其父真作,演成如此低劣之“乱认父亲”笑剧。
“无情最是黄金物,变尽天下儿女心。”——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生发的人生感喟,真成了声贯今古的不朽名叹。
进退有度
邓散木,上海人。乳名菊初,号钝铁,学名邓铁。
提及这位现代篆刻家、书法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书画署款,所钤印文,或居所、书斋、作品集题名,喜用的那些词语,个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俱可归入时下所谓的“重口味”序列。
如:邓散木作画、题字的落款,喜署“粪翁”“海上逐臭之夫”。据云,“粪翁”来自《荀子·强国篇》:“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意为厅堂上面尚未打扫,那么郊外的野草就顾不上清除。言下之意,似欲清除一下世间杂草与污秽。沪上报纸当年介绍邓氏展览,常用“登粪厕”“看粪展”“尝粪一勺”讥之,其嗤之以鼻,作诗自我剖白:“非敢求惊人,聊以托孤愤。”
如:邓散木生平只拜服清末民初的常熟篆刻家赵古泥,刻印宗袭其法,尝自镌一方明志章——“赵门走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称“牛马走”;邹容要做“革命军中马前卒”,姿态俱谦卑,但有度,邓散木却一步就迈到了台口。
如:三长两短,作为一个表述悲情事件的成语,本指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特指人的死亡。邓散木偏选此成语来概括自己艺术水平的高低,云:篆刻、作诗、书法为“三长”;“两短”是填词、绘画。其书斋名就叫“三长两短斋”;印谱集就题名为“三长两短斋印存”。
如:邓散木将居所称作“厕简楼”,特制一块铜牌挂在门前。厕简,为古人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记得李后主那则逸事吗?这位佞佛的国主,为了表示对僧人尊重,亲自削制厕简,甚至不惜在自己脸上拂拭,以防厕简削得不够光滑,触伤僧人体肤。细心如此,体恤人如此,也难怪他能填出那般深情款款的词来。只是,以此种情怀执政,又适处五代十国那风疾雨骤的乱世,其人生孕出悲剧,也是必然。据云邓氏曾将厕简解释为马桶豁帚,两者虽同为旧时之人排便后用来去除污秽的用具,但厕简是用作刮清体肤污秽的,马桶豁帚则是用来清洗厕具污秽的,将二者混谈,显见有误。至于邓氏将个人居室称作置放马桶豁帚的处所,欲体现的仍是清扫天下污浊之意,与自号“粪翁”堪谓一志相承,只是出语未免过于奇葩。
邓散木最骇人之举,当推其创办并主编《市场公报》时,竟出版一期“哀挽号”——哀悼自己仙逝。朋友和读者读后,或登其宅,或往报社,分送花圈、赙金或挽诗。孰料一周后,该报又推出“复活号”,云邓氏复活……
和一些书画家往来,印象中,彼辈颇热衷通过展现在世俗生活中的特立独行,来显示与众不同。而桀骜不驯,甚至悖逆人情,则是基本套数。这种被世人称为“炒作”的行为,在此类艺人眼中,有时竟比以德润身、技臻至善更显重要。自然,其中文化修养高者,亦不屑为此。
在艺苑,邓散木能吟诗、会填词、可作文,亦算有文化之人。可他偏难脱匠气,不仅依旧玩此陈年戏法,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津津有味去玩,委实令人齿冷。
某寺院请邓散木书写“大雄宝殿”匾额,寺僧求其落款署己号“钝铁”,其不允,照例以“粪翁”二字署之,佛头着粪,固执如此!当然,邓散木终非一狂到底者。据陈巨来记述,抗战胜利后,上海四明公所求画家孔小瑜绘一幅蒋介石着长衫、坐石上小像,请邓散木题字。他题了仿伊墨卿体隶书四字:“后来其苏”。此语出自《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意为:“王啊!你来了,我们便可以兴盛了。”而四字后的署款,则是“散木敬题”。如此看来,邓氏也是能伸能屈、进退有度者。还记得耿直的闻一多在稠人广众间那铿锵怒斥吗?“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才是血,由理想引导的言行,较之以攫名夺利为目的之炒作,终究要沉雄、浑厚得多。
“佯狂难免假成真”,设如邓氏为蒋像题字之举没遭曝光,庶几世人真目其为“艺苑祢衡”。二战时,保卢斯兵败斯大林格勒,率残部投降苏军,开历史上德国元帅向敌手投降之先河。消息传至柏林,希特勒讥之:“只差最后一步,没有跨进永垂不朽的门槛。”邓散木妻张建权口述《邓散木传》传世,全书叙述邓氏一生经历甚详,言其清高孤傲之举无数,却只字未及其给蒋像题字署款事。大约,张建权认为只要自己绝口不言“这一步”,邓散木就可以跨进永垂不朽的门槛了。
字迹与个性
一
清代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识之高下存焉矣。”这种认为透过书法,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养、才华和志趣,观察一个人的笔迹,可以了解其性格和人品的观点,在东西方都存在。
写出《人间喜剧》纷繁浩轶长卷的巴尔扎克,曾自诩善分析笔迹。他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研究时间,常向朋友矜夸,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笔迹,准确无误地说出此人的性格特征。一天,朋友某女士交给巴尔扎克一份一个男孩的手迹样品,声明与其非亲非故,他尽可对她讲实话。巴尔扎克仔细研究了这份笔迹样品,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提供手迹样品的女士:“跟你讲实话吧,这个孩子既粗心,又懒惰,必须严加管教。否则,就会给祖先丢脸。”“这真是怪事了,”女士微微一笑,“这笔迹是从你小时候的作业本里弄来的呀。”
以此作主干敷衍而成的版本略异的故事,不仅收入了江苏版小升初阅读资料,还见于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显然,这是讽刺巴尔扎克以及“书如其人”理论具有主观、片面谬误的生动材料。
二
涉略西人著作,确可发现运用字迹推测个性的事例。
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与其妻子合著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在这部厚重自传里,弗氏夫妻述说了1953年至1954年以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身份“游学”剑桥大学时的一些琐事。而弗里德曼因为弱冠之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与一名从德国来美进修的研究生威廉·克罗默法塔特交往密切,接受了他的“笔迹包含了一个人个性的可靠信息”的理论,从此成了一名业余笔迹学家。所以,他特辟出专节,津津有味地讲述了其在剑桥通过看笔迹推测作者个性的数则成功故事。
有一天,弗里德曼去拜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鲍尔,鲍尔刚收到凯恩斯得意门生理查德·卡恩的一封信,读后很不高兴,便把信递给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展笺一顾,瞬即被卡恩字迹行间离散并大幅度向下倾斜的特有书写风格吸引,而对信中内容失去了阅读兴趣。他径直对鲍尔道明了自己通过字迹对卡恩产生的印象:“肯定是个特别悲观的人。”但他没有记载鲍尔有何反应。碰巧,弗里德曼隔日与卡恩相约共进午餐,其间讨论了凯恩斯和卡恩分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财务主管时制定政策的差异。卡恩坦言:“最大的不同就是,凯恩斯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而我是个冥顽不化的悲观主义者。”弗里德曼说他对谈话的内容再次失去兴趣,急向卡恩展示了严重向上斜的字行样本,并问道:“凯恩斯的笔迹是像这样的吗?”卡恩表示未曾留意,但承诺待弗里德曼去其房间参加酒会时,会提供一些样本。后来,卡恩果然遵诺向弗里德曼出示了凯恩斯的笔记本,凯恩斯的“书法”竟完全如弗里德曼所料。
弗里德曼对笔迹有研究的消息迅速传开,参加聚饮的许多素未谋面的学者都拿着自己的手迹,来请眼前的“笔迹大师”推测个性。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竟也递来一份书写样本,让他分析。弗里德曼看后断言:“这显然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所以,对我来说可不好分析。但是,我会说这是由一个有着相当的艺术天赋,但没有智力天赋的人写的。”弗里德曼此处所言之“外国人”,是指非英美人士。结果,他又测对了!原来,“字主”是凯恩斯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
在这里,有必要八卦一下弗里德曼为什么说莉迪娅缺乏智力天赋。英国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积三十年之功,撰竣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凯恩斯传》,不仅赢获“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的美誉,还被英国女王封为勋爵。在这本传记中,斯基德尔斯基花费大量笔墨,对莉迪娅的出身、经历、性格和“布鲁斯贝利成员”排斥莉迪娅的言行,做了细致的记录。
莉迪娅于1891年10月21日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从小在帝国芭蕾舞蹈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进入马利英斯基大剧院,成为专业舞蹈演员。20世纪初叶,性格独立并富有冒险精神的莉迪娅长期漂泊欧美,在各大剧院演出。她曾经和享有“舞蹈之神”美誉的芭蕾舞男演员尼金斯基同台献艺;毕加索为她画过像。据说,她有过包括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在内的数位情人。1921年岁杪,当出身知识贵族之家,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大学一路接受上流阶层教育,因写出20世纪最有影响著作之一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而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文化名流的凯恩斯,与比自己小八岁的莉迪娅热恋时,后者已是剧团一位经营主管之妻了。而凯恩斯除了几次短暂而不成功的恋爱,对女人几乎毫无经验,更何况是像莉迪娅这样已经有了极不寻常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女人。
爱情是盲目的。凯恩斯迅速坠入情网的“失态”之举,引起了他所在的当时英国最有势力的上流文化圈子——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成员的集体震惊。这个精英圈子的成员包括写《到灯塔去》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的画家姐姐范奈莎·贝尔,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印度之行》的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写《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提出著名论断“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当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代言人克莱夫·贝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亲密得超过了一般概念的朋友,有些成员之间还存在着自由而散漫的爱情关系。他们个个自视甚高、桀骜不驯,随着一些成员功成名遂,成为那个时代文化时尚的仲裁者,所提倡的道德价值观也在四处传播。可想而知,当凯恩斯决定把莉迪娅这个完全局外的人物带进群体之后,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成员自然从心底排斥这个外来物种,而指责对方无知,则是这群知识精英百试不爽的撒手锏。
斯特拉奇说,莉迪娅是个可怜虫,一点特点都没有。克莱夫·贝尔常嘲笑说,莉迪娅的“精神家园”是沃尔沃斯百货商店。才女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莉迪娅不可救药的一点,是“没有头脑”;在给朋友的信中,她刻薄地写道:“莉迪娅有松鼠那样的灵魂,你不能想象她的举止:她能坐在那里,用两个爪子给鼻子两侧擦拭磨光达一个小时。但这个可怜虫陷在布鲁斯贝利里面,除了必须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她还能做什么呢?我向你保证,她坐下来读《李尔王》的那副样子真是凄惨。”
弗里德曼、琼·罗宾逊尽管不置身“布鲁斯贝利成员”之列,但从弗里德曼在炫耀自己推测成绩时,沾沾自喜道:“那绝对是我在剑桥一年中最大的胜利!”可见,出于学术势利,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琼·罗宾逊,或者那天在卡恩房间参加酒会的其他剑桥学者,在对莉迪娅智力水准判定这一点上,和“布鲁斯贝利成员”的观点均高度趋同。
由于阅读有限,我没能看到彼得·鲍尔、理查德·卡恩和琼·罗宾逊这些当事人对弗里德曼通过字迹推测作者个性场面的描绘或能力的记录。此处,引用的只是弗里德曼的自述孤证。但是,在弗里德曼写这段回忆文字之际,彼得·鲍尔依然活跃在经济学领域,并和弗氏仍有往来。由此看来,弗里德曼留下的这段栩栩如生的文字,绝不像有些回忆录的高寿作者那样,是待到同时代的当事人都离世之后,才在那里精心编织一个个无中生有,却极利于文饰自身形象的神话或鬼话。
三
中国人宝重书法,言及书道,也嗜发形而上学之论,且喜以作者在世俗生活中的功过道德,来阐释、论证、评定其书法艺术风格及成就。前引刘熙载观点,属较为系统之总论。另一些书论,与刘熙载同调,因出语更为具体,容易取来与其所论述的法书参照验证,则殊让人感觉不近情理。
蔡京、秦桧、严嵩这几位传统历史教科书中铁板钉钉的“反面人物”,俱以擅书扬名于当世,但出于政绩或品行原因,在书法史上,他们被简单地忽略、屏蔽了。其中,严嵩留存于世间的字尤多,像山东曲阜的“圣府”额题、天津蓟州区“独乐寺”寺匾、京城酱菜店“六必居”店招等,上面的字写得真是方严浑阔,正气凛然,令人入目铭心,根本颠覆了通过一个人的书法,可以透视出其品德的观点。只是因为“奸名”身随,这些没有落款的严嵩书法匾额,悬挂点也长期不以文字标明作者,无疑影响了严嵩书家之名在后世的传播。
赵孟頫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巨擘。《元史·赵孟頫传》曰:“(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由于元灭宋后,赵孟頫作为赵宋后裔,仍出仕元官,便有后人据此否定赵孟頫人品,进而连带贬损其书法艺术风格及成就。明人项穆在《书法雅言》第十三篇《心相》中,曾皮里阳秋地说:“若夫赵孟頫之书,温润娴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项穆竟从赵孟頫的“妍媚纤柔”书风中,敏锐地发现了他缺乏临难不苟的节操,搜寻到了他最终背宋仕元的根由。明末清初的傅山,在书论中更径言:“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诸如此类的说法,似有理,终不耐推敲,却流播甚广,竟积淀为民族文化审美意识之一部分。
如果舍弃通过书法去发现作者品行的企图,降低通过书法来了解作者个性的期待,仅围绕书法谈艺术,结论无疑更加科学。近代著名作家、学者、书法家顾随的一则论书轶事,便让我对他钦佩不已。顾随四十岁开始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启功言其“平生服膺惟在沈尹默先生,心摩手追,升堂入室,偶临唐碑魏志,亦不失秋明指腕之法”。此处所言“秋明”,即沈尹默的号。虽然对沈尹默钦服如此,他对沈尹默书法成绩的评价仍很客观:“默师作字,按笔多于提笔,故行书上接千古,独步一时。而不善作草。旧尝于兼士先生处见其草书,不及行书远甚,则少用提笔之故也。”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赠给老师顾随一册,顾随看了封面上的书名题字,写信告诉周汝昌:“(这五个字虽是)默老结构之法,然而不精不熟,勉强之迹宛然在目,绝非老师亲笔也。”他猜测书名题字可能出自沈尹默弟子、儿子,或是沈夫人储保权。其实,这题名是周汝昌集顾随的字而成。而顾随和巴尔扎克相同,居然没有认出自己的字,闹了一个小笑话。顾随曾自负地说:“拙书比益有进步,此道只让得默老一人。若其他以书法擅名当世者,与苦水作弟子亦须回炉改造一番,方可商量耳。”所言“苦水”,指其自己,此言既自诩个人书法成绩独步当代,洵乎超逾时人之上,却也坦言“天外有天”,而沈尹默就是那高出自己的“天外天”。
结合顾随平素对个人书法水准与沈尹默书法水准差距的清晰认识,可见其对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书名题字的评价,与巴尔扎克发表对“小男孩”手迹样品评判意见时那种超然物外或矫揉造作的口吻迥然有别,确是就字论字,是态度极其真诚且富有学术水准的良心之论——虽不免令人发嗤,却绝不缺乏艺术鉴赏的精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