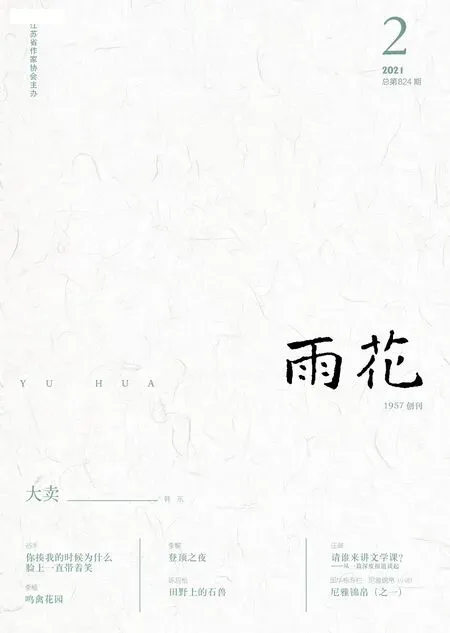我的喀普斯朗河
1
我想了想,还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姬甄来的时候,总不能让她看到我这样。扫完地,我把桌子挪了挪位置。桌子是上任工友留下的,三合板压制,绿色的,掉了不少漆。桌上的废铜烂铁被我收进一只纸箱,都是些零碎的钟表零件。平日里下了工,我就喜欢鼓捣这玩意儿。墙上挂满闹钟。用大伙儿的话说:你除了爱修表,就没别的爱好了?我说,还真没。
夜深人静时,我就喜欢挑着台灯,手里攥着细螺丝刀,看眼前被拆开的表在发条的作用下,“嘎达嘎达”地走动。当然,墙上的那些钟也“嘎达嘎达”地走动着。很多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确认它们走动的声音是否一致,还有些时候,我会让自己沉浸在这种声音里,仿佛时间是一种能听得见触得着的东西。
姬甄来时,我收拾得差不多了。肖伟所剩的几件棉衣被我叠得整整齐齐,妥善地装在黑色塑料袋里。姬甄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我说:“进来啊。”她方进来。我环视屋内,顺手抄了个塑料凳给她。她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后,坐了下来。
我说:“你也别太难过了,事情不想发生也发生了,日子还得过。”她没说话,不知咋的,一行眼泪从眼睛里滚出来。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以前没遇上过这种情况,说实话,虽说肖伟都结了婚,我却还没恋爱过,更不懂得如何安慰女生。我摸了摸裤兜,掏出几张揉得有些皱的纸巾,犹豫再三,还是递了过去。姬甄没接我的纸巾,她兀自站了起来,用衣袖抹了抹眼泪,抱起桌上肖伟的衣服就往外走。我说:“你桌子上的东西不拿了?”她没理我。
我以前和肖伟同住,自打他和姬甄恋爱后,就搬出去了。一晃好些年过去,谁承想,今天会成这个样子。时间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所有美好的事物。
来铁热克镇时,是1997 的夏天,我们才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火车从陕北穿过,进入宁夏,进入甘肃,再进入新疆,车窗外是云烟雾绕的秦岭,是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是地窑与苹果园相间的小农人家,是漫无天际的向日葵地。看到戈壁的时候,姬甄从欢悦转向忧愁。我把车窗推高,风呼呼地灌进来。姬甄说:“旱成这样,我们吃啥?”肖伟笑道:“来之前我已经了解过,新疆野兔多,而且繁殖能力超强。”彼时,我和姬甄总会很有默契地相视一笑,意思是,我们三个中间,肖伟永远是那个最理智、最乐观的人。
风一阵阵灌进来。火车驶进一片辽阔的草原后,每隔一段距离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站岗的哨兵。我们三个把头探出窗,向哨兵们挥手作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挥洒和浪费我们的青春。
到达火电厂后,姬甄被安排到化工科,肖伟被安排到宣传科,我则去了燃运科。都说化工科的姑娘长得不好,姬甄偏偏是个例外,用大伙的话说,三百六十度无死角。鼻子高挺,眸子深邃,肤如凝脂,我能想到的形容词就是这些。初到火电厂,不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去喀普斯朗河捕鱼,或者驱车到雪山下兜风,那是天山南麓的山脉,山脚下木屋的门前就是一条蓝色丝带般的河流。别说,有几次我们真遇上了野兔,只是怎么追也没追上。在草地上,不只有野兔,还有旱獭。我最爱和姬甄在草地上寻找旱獭,那种胖乎乎的小动物,憨态可掬,常常逗得姬甄忍俊不禁。那时候,姬甄爱同我单独出去玩,只是我比较木讷,出去的次数多了,也没什么实质性的表示。渐渐地,她就不大愿意出来了,总是用三个字回绝:没意思。是啊,每次都是去河边,或者去山上,去久了,确实没啥意思。
再后来,姬甄就同肖伟恋爱了。我后知后觉,发现时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有些话本想说出来的,藏久了,却发现已经错失良机。他们恋爱后,肖伟买了一辆力帆摩托车,姬甄坐在肖伟身后,双手环住他。两人去戈壁滩玩,车子拉动油门,“突突突”地从桥上疾驰而过。我刚好在桥底下钓鱼,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做电灯泡了。那以后,我有意同他们疏远,准确地说,也不算疏远,算是不去打扰吧。之后,肖伟和姬甄结婚,婚后我同他们联络得更少,就像普通同事。据说两年前,姬甄怀过一个孩子,不知什么原因,没能保住。祸不单行,半年前,肖伟也没了。
2
我还是决定送送姬甄,火电厂效益不好,前几年排污量超标,听说被上面盯上了,今年来查过许多次,搞得厂子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些人给裁掉了,还有些等着辞职,我居住的那排厂房以前热热闹闹,这会儿见不到几个人住。上世纪80年代修的厂区宿舍,如今年久失修,看上去斑斑驳驳,破破烂烂。
把姬甄送出大院,我说:“改天吧,改天我们去看看肖伟。”她转过身注视着我,阳光明晃晃的,有些刺眼。她虚着眼睛,刘海荡到额前。她用手捋了捋,没说话,转身离开了。
我想沿街走一会儿,立冬后,铁热克镇街上人更少,人们宁愿窝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出来溜达。到桥头时,我看到刘老汉正在补鞋,嘴里碎碎念念的,不知道在骂些什么。我前些天交给他一双鞋,还没见补好。我问:“刘叔,我的鞋补好没?”刘叔抬头看看我,慢吞吞地说:“那双褐黄色的皮鞋啊?”我说:“嗯。”顺势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烟来,递了一支给他。他接过烟,在地上的竹筐里翻找我的鞋。我蹲下来抽烟,鞋已经补好了。难得天气这么好,我就抄过他身旁的小板凳坐坐,晒晒太阳。
我问:“刘叔,你到这多少年了?”他没正眼看我,边补鞋,边瞅着对面的面馆说:“二十多年了。”他弯下腰捡一块碎皮,碎皮在他手里就是宝贝,只要上了补鞋机,“咯噔咯噔”地随着他踩动的脚旋转三百六十度,就成了一块大小均匀的材料。刘老汉抄起身边的剪子,按住皮子的边缘剪下,再像刚才一样补上去。
对面面馆的门帘掀开了,出来一对男女,是老鹰子,跟在她身后的男人看不清脸。瞧那模样,不像是本地人,四十来岁,剪一短寸,胸口挂着金链,膀大腰圆。我心想,也不知道啥时候勾搭上的。刘老汉脸色不太好,没说话,能看出有些气鼓鼓的。我不知道他为啥不高兴,拿起鞋决定回去。起身,走到厂区宿舍大院门口,看见老鹰子和那男的在街边吃小吃。这两人还没吃饱吗?我心想。我没跟她打招呼,她这人嘴巴厉害,在火电厂出了名,什么事到了她嘴里,黑的能说成白的,小的能说成大的,传播力特强。她在身后叫我:“小夏,你没去找姬甄?”我回过身,她脸上挂着笑。“前几天我可看见她来你这了啊,你们俩最近走得蛮近。”我不太高兴,没理她。她又笑道:“还不理姐姐啊,看把你嘚瑟的。我听说,肖伟死后他家得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姬甄好像一分没捞着,真是可怜。”我没给她好脸色,回了她一句:“管好自己的事吧。”回到屋里,我打开姬甄落在桌子上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纸钱、香烛,她是想让我同她去烧纸。
天气转凉后,燃运车间比原先忙。大伙没日没夜地加班,工资却不如从前。有时候累了,我就坐在运输皮带边睡觉,盯着皮带上黑魆魆的煤炭发呆,心里郁闷,好好的,肖伟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天,我下了早班,在澡堂冲了个澡,决定去找姬甄。她的车间闹哄哄的,工友们说她已经回去了。我想趁下午不上班,和她去看看肖伟。
到姬甄家,她的屋子门锁着。我正打算走,她从屋里出来了,一股热气随之往外冒。她才洗过澡,我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该不该进屋。我说:“东西我都带来了,你要是得空的话我们去看看肖伟。”她揉着头发说:“进来吧。”我进了屋,在沙发上坐下。姬甄给我倒水,揉着头发进了里屋,让我等她。
3
风有些大,呼呼地吹着。好在有太阳,天空湛蓝。我蹲在地上烧纸,手里握着一根棍子,一边挑松黏在一起的纸钱,一边用围巾掩住嘴巴。我把肖伟的棉衣也烧了,烟气熏人,直往眼睛嘴巴里钻。
姬甄站在坟前,一身黑色羽绒服,头发吹得凌乱。她一边捋着刘海,一边向肖伟敬香。我说:“他爸妈没想过带他回去?”姬甄说:“年纪大了,家里穷,加上孩子多,所以……”
我明白姬甄的意思,没继续问。肖伟出事的那天,燃运车间紧急集合,领导召开工作部署会议,再次强调安全生产,生命大于一切。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一个宣传科的人,跑到冷却塔去干啥?有人说是去网鱼,也有人说是失足。总之,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断了气。好不容易联系上他在内地的亲人,等他们赶来的时候,尸体都火化了。厂领导也没推诿,赔了十四万。只是这钱,姬甄一分没要,全给了肖伟父母。肖伟父母开明,知道她俩结了婚,没小孩,以后要去要回,那是她自己的事,和肖家没半点关系。
我点燃一支烟,插在肖伟坟前。起身,自个又点燃一支抽起来。烧完纸,姬甄在肖伟坟前磕了几个头,她像是要和肖伟说点话,我怕她尴尬,独自朝路边的树丛里走去。
其实读书那会儿,我就挺喜欢姬甄,现在也喜欢,只是我性格内敛,做事瞻前顾后,从没把心里话说出来。可转念一想,这会儿要是和她好,又算是哪门子的事?对得起肖伟吗?就算对得起肖伟,我心里也有过不去的坎,父母能理解我娶一个丧夫之妇吗?
秋风萧瑟,路上到处是散落的杨树叶子。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姬甄和我都静默着,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快到镇子时,我想问她一句话来着,话到嘴边,觉得还是不太合适说,至少时间上不太合适。厂子这几年效益不好,肖伟去世后,人们常在底下窃窃私语,说厂子坚持不了多久了,原来的厂长也换了,去了别的地方,新来的厂长不抓生产,天天钻头觅缝讨好上级,大家都在为各自的未来筹划着。要是厂子真倒闭了,我们能去哪呢,还回不回内地?回的话,姬甄会走吗?肖伟现在算是彻底睡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了。
走到桥头,刘老汉老远就朝我招手。姬甄见状,说她先回家。我朝刘老汉走去。我说:“刘叔啥事?”刘老汉说:“你是不是会修表?”我说:“会点,咋啦?”他说:“上次补鞋那钱我不收了,换你帮我修一只表行不?”他年纪大,人也实诚,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我说:“行,不过钱我还是要给你的。”他说:“那你先忙,改天我去找你。”我说:“行。”
我那屋比往常潮湿,我把棉被拿出来,挂在门口的铁丝上晾晒,紫外线强,兴许能杀死部分细菌。屋子里太乱,哪怕收拾过,还是感觉乱糟糟的。我又打扫了一遍,把屋里没用的玩意儿全扔了。快到饭点,我准备去食堂吃饭,走到院子大门,姬甄来了。她说:“上我那吃饭去。”我环视四周,人来人往的。我说:“算了吧,食堂吃方便。”她说:“随你吧。”说着,旋即转身。我说:“好吧,那我还是去你那吃。”
进屋,一股暖流迎来。我说:“你这到底比我那暖和。”她说:“我这有暖气,你那没几个人住,厂子都不愿意供暖了。”“是啊。”我一边说着,一边坐了下来。姬甄炒了几个菜:西红柿炒蛋、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还有回锅肉。我说:“过年回武汉不?”
她夹着菜,沉默了一会儿说,回不回都一样,哪都是家,哪都不是家。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早知道不该问的。我认识姬甄比认识肖伟早。那会儿我们在武汉读大专,同班,五六十个人,但我从没主动找她说过话,三年里我们说的话不超过十句。选工作地点时,学校把我们三个分到一起。肖伟比我开朗,认识没几天,就和姬甄熟络起来。
那时候,姬甄应该是有所察觉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她没搞懂我的心,我也没搞懂我自己,明明心里念着,偏偏要躲避。男女之间的事情,一个眼神就能感知得到。有时候我偷偷瞄她,她发现了,转过脸装作啥也不知道,若我仔细看,准会发现她有些脸红。很多时候,我觉得她对我应该是有些好感的,只是隔在我们中间的那层纸,始终没有被我捅破。
4
“你呢?你要回家不?”姬甄问我。我说:“回吧,去年就没回,我爸妈挺想我的。”姬甄“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良久,她说:“阿楠,我想问你个事情。”我说:“什么事?”她说:“算了吧,没什么。”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她说:“真没什么。”我说:“说吧,有话就说。”她看了看我,问道:“我这人是不是很差劲?”我说:“哪方面?”她哽咽了下:“哪方面都有。”我说:“你挺好的,不存在差劲,谁敢说你差劲?”她说:“没谁。”
吃完饭,姬甄说不知道咋回事,最近这片断水了。我说:“那今天的水从哪来的?”她说:“去水房挑的。”水房那段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长长一排宿舍,现在没人住,水房在宿舍的底端,夏天里有人洗衣服,冬天里冒着热气。热气一释放,四处弥漫,白茫茫的,人置身其中,仿佛进了云层,啥也看不见。
我说:“怪不得喊我吃饭,敢情是要我干活啊。”她说:“我可没说请你挑水,你愿意挑就挑,不挑拉倒。”我说:“你还生气了?”她没说话,收拾碗筷。我说:“饭都吃了,哪敢不挑?”
我在前,她在后,沿着荒废的水泥路朝前走,这条路走的人少,两边杂草丛生,枯败萎靡,脚从草里过,能沾出好些草屑。快进那片乳白色的雾气时,我让她别进去,就在原地等我。她站在外面,抬头注视着挂在屋檐下的冰凌。我摇着扁担,“嘎吱嘎吱”地走进雾气中。水房里暖和,水管不结冰,不会堵塞,随意一拧,水就来了。接好水,我又和姬甄朝着她家的方向走。她要替换我,我说我一个人能行。“以后每周一三五,我给你挑水吧。”我说。她说:“行。”我说:“你也不说句客气话?”她说:“你还想让我咋客气?”
从姬甄那回来,到桥头时,老汉还在补鞋。我说:“刘叔,你那块坏了的表带在身上吗?”他说:“就是手上这块。”说着,从手腕上摘了下来。他说快忙完了,让我抽烟等他。我抽着烟,他问我是不是和姬甄好上了。我说哪的话。他说:“那姑娘挺好的,言语不多,待人平和。”我吐了口烟圈,说还没到那一步。他笑道:“听你这话,还是有朝那步发展的念想的嘛。”他这么说,我才觉着,姬甄似乎真没从我心里走出去过。我说,现在在一起,不知道合适不。他说,咋会不合适?我说,不晓得。他说,你是嫌弃人家结过婚?我没说话,又吸了一口烟。他补充道,这年头,但凡恋爱的哪个没睡在一起,结婚和不结婚的区别也就是一张纸而已,走一道法律程序罢了。我心想,话虽这么说,可红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像是写进历史一样,涂也涂不掉。这么想着,我都感觉自己老封建。老汉又说:“不过回头想想,你这样纠结也正常。”
刘老汉补完鞋,说先这样吧。我说:“你不修表了?”他说:“改天吧,改天去你那。”说着,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他一边用一张废弃的三轮车篷布把工具盖住,一边自言自语,年轻时候喜欢就趁早,不要挑三拣四,像我这把年纪了,就晓得啥叫孤独了。
天气越发的冷,铁热克街上行人寥寥,偶见两三个行人,俱是匆匆忙忙的。每周一三五,我都按时给姬甄挑水。有天她从茶几上递给我几只鞋垫,说从街上买的,也不知道合不合我的鞋码。我说,四十,应该合。挑完水,我照常回宿舍,没在她那久留。长期挑水,哪会不被人看见,久了,背地里议论的声音就有了。走在街上,老感觉有人嗑着瓜子讨论自己。姬甄倒好,像没事人似的。
老汉拿表到我那儿修的那天,修完表,我从床底下翻出一副象棋,两人有一招没一招地下着。他说:“踏马。”我说:“拱卒。”他说:“飞相。”我说:“出炮。”他说:“给你说个事。”我说:“啥事?”他说:“前几天我看见老鹰子去找姬甄了,带着一个男的。”我有些诧异,问是哪个男的。他说:“北厂那边的,那人以前我见过。”我踏了个马。他说:“吃!”一颗炮踩在我的马上。我说:“那人干啥的?”他说:“做生意,开个录像店,人外表看着老实,实际不咋样,脾气暴,还好那口。”我说:“好哪口?”他说:“就喜欢街边站着的那些女的,他之前的老婆跑了,不知道为啥跑的。”我说:“将军。”他说:“我划士。老鹰子爱给人做媒,我劝你还是了解下,免得后悔莫及。还有,你这屋子,冷清清的,黑暗暗的,要我说得改善改善,人家姬甄来你这也好有个坐处。”刘老汉的话像一块石头,一下子砸进我心里,荡起一圈浪。关于老鹰子,大伙对她的印象不怎么好,她人也不坏,就是嘴巴大,什么风到她嘴里准能吹出大浪来。
可能是说了交心话,刘老汉到我那儿下棋勤了起来。我们聊棋,也聊生活琐事。有天夜里,我从外面带了两个小菜,抄了四瓶二锅头,两人喝得尽兴。烧酒下肚,刘老汉就啥话都向我倾吐,原来他身上一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告诉我。我说:“你怕老鹰子,难道不怕我?”他结结巴巴,说:“怕啥?你也是,有,有秘密的人。”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我确实有秘密,我把自己暗恋姬甄的事情告诉了老汉。老汉说:“你这算个屁的秘密!”他说他喝多了,喝多后,人看什么都不是东西。他趴在桌子上,有些动情,伤心得抽泣了起来。他说:“我那也不算是秘密,如今回头来看,真不算什么秘密了。”他想明白了,说本来打算警告老鹰子的跟班的,现在想想,没那个必要。“有什么必要呢?”他反问我。我说:“刘,刘叔,确实没,没那个必要……”
我们俩喝高了,他趴在桌子上睡觉,我躺在床上动不了。钟表“嘎达嘎达”地走着,我们俩都沉浸在各自被麻醉的世界里。刘老汉醒来时,说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唯独时间,过了就真的回不去了。我搭不上话,困得要命。说完,我听见他起身移动凳子的声音。门开了,有风灌进来。门又关了。
5
姬甄给我买了一双大头皮鞋,我有些错愕,不知道怎么谢她,问多少钱。她不高兴:“谈钱就别来我这了,你帮我挑水,给你买双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拗不过她,我换下脚上的旧鞋,穿上新的,还别说,大小适宜,挺舒坦。
我们沿着废弃的水泥路走,姬甄照常跟在我身后。水房外的雾气比之前浓重,四处弥漫。地上的水汽结了厚厚一层冰,我差点摔了一跤。姬甄要继续走,我让她别动。我说,你就在那等我。进了水房,吓我一跳。老鹰子也来挑水,跟着她的,是那个戴金链子的板寸男人。两人正抱着,见我进去,老鹰子一下子挣脱开来。我挺不好意思的。老鹰子说:“你也来接水?你们那没断水吧。”我知道她话里有话。我说:“帮姬甄挑水。”老鹰子脸上不高兴,说水满了。那男的去提水,挎起扁担,两人就出去了。
从水房出来,姬甄站在外面,双手戴着手套,不停搓着,嘴里呵着气。我说:“冷吧?”她说:“还好。”老鹰子和那男的走远了,身影消失在前方拐角处。我说:“跟着老鹰子那男的是谁?”姬甄看看我,说:“我怎么知道?”我说:“我还以为你晓得呢。”她说:“你这人奇怪了,我咋会晓得?看样子是她相好吧。”我说:“你咋晓得是她相好?”她说:“一天上上下下的,是个猪都能认出来。”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猪喽?”她说:“我可没说。”我说:“那就对了。”她说:“你比猪还笨。”敢说我比猪还笨,我心里不服,质问她:“照你的意思那我们俩天天上上下下,也是相好了?”她朝我背上打了一拳。“去,赶紧挑你的水吧。”她把话题绕开,“你猜老鹰子来找我干吗?”我说:“猜不到。”她说:“借钱,还说给我介绍个对象。”我眼睛一亮,心想,老鹰子果然干不出好事。我问她老鹰子要给她介绍谁。她定睛看着我:“你很关心这事?”我不知道怎么回,说:“问问不行啊?”我停住脚步,换只肩膀。我说:“怕你遇到不好的。”她似乎有些认真,笃定地站在我面前:“啥叫不好的?”我说:“比如脾气大的,会家暴的。”她说:“你呢?你脾气大不大?”我支支吾吾,说不知道……
姬甄留我吃饭,我没吃。这个中午,我把围脖裹得紧紧的,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走,在三岔路口找了家酒馆。这家酒馆是铁热克的老招牌,只需十五块钱,就能坐在楼上喝一整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边喝啤酒边吃榨菜,越喝越冷,越冷越想喝。
窗外行人匆忙,各类运煤车碾压着坑洼的路面“哐哐当当”地驶过,有人推着手推车在路边叫卖,远处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这座小镇因煤炭兴起,如今也因煤炭渐渐衰落。电视里放着各种迎新春的广告和综艺节目,外面零星的炮竹声随之应和,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突然有些想家,不知道要不要回去。对于姬甄,我到底该如何选择?想到过年期间,人们各自回到热闹的家中,团团圆圆,红红火火,举杯庆贺,促膝畅谈,一起吃着饺子、汤圆。而她呢,会不会一个人冷锅冷灶?
从酒馆出来,夜已经黑透了。街上几个小孩嬉闹,把擦炮丢在路边的冰块上,炸起冰花。还有小孩把擦炮丢进钢管里,“砰”的一声,炸得像放大炮似的。看着他们窜来窜去,我没有半点喜悦感,反而心生厌恶。
我径直朝着宿舍大院走去,院子里蹲着一个人,瞧不清脸,我想绕开。那人抬起头,说:“兄弟回来了。”我停住脚步,看清是老鹰子的跟班。他站起身来,从兜里摸出一盒烟,掏出一支递给我。我接过。他摸出手机,打火。我说:“我自己来。”他说:“兄弟,我向你打听个事。”我说:“你讲。”他说:“这几天有没有见刘老汉?”我说:“见的,怎么了?”他说:“你要是再见到他,帮我给他传句话。”我说:“什么话?”他说:“他老了,论文论武都敌不过我,他过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多年前屁大点的事情,希望他看得开点。而我的事,他也少管点。”
我说:“你能说清楚点不?”他说:“这事说不清楚,说清楚了就不是事了,这样吧,你就按我原话转告他。”
整个晚上,刘老汉都没有来我那里。也不知道刘老汉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我硬是没见着他。每次留意桥头,都不见他摆摊的身影。
6
人们把电影院围得水泄不通,我让姬甄把身份证给我,她站在门口的石阶旁等我。挤了好半天,才挤到售票窗口。那人说:“要几张啊?”我说:“两张。”从售票员手里接过票,我又不断朝人群外面挤。
那段时间,春节的气息越发浓重起来,久不开业的电影院每隔两天就放映一部电影,武侠的、爱情的、枪战的,都有。姬甄想看黎明和张曼玉演的《甜蜜蜜》,可在家用VCD 看过后,电影院就从来没有排过片。这天晚上放的是刘德华、张家辉主演的《赌神1999》,片子才上映没多久,看过的人也来买票看,不断给身边人剧透。我没心思听,心想,期待感全让这些人给毁灭了。
跟着人流挤进剧场,偌大的电影院里没有丝毫喜庆感,电影光怪陆离,场景转换特别快,看到刘德华和朱茵接吻那段,很多人在下面起哄,抽烟的抽烟,吹口哨的吹口哨,哪有点工人的样?简直就是地痞流氓和街边小混混,从开片到剧终,剧场里充斥着各种嘈杂的争论声和缭绕不断的烟味。
姬甄捂住嘴,走出电影院就趴在路边的垃圾桶旁吐。我说:“味道太重,下次选个人少的时间来。”她没说话。我们沿着回去的路走。快到她家时,她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我,说老鹰子前几天又来找她了。我说:“她又来干什么?”她说:“就是上次要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说想约我见个面。”我说:“那你答应没?”她说:“我还没想好。”我没说话。我们继续沿着马路走。她说:“我思来想去,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听说那人挺老实,应该能包容下我。”我不知道她指的包容是什么,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后,我反而不太自在,不知出于何故,脸瞬间就红了,还有些微热。我从兜里摸出一支烟,静静地抽着。夜风有些大,扬起姬甄风衣的下摆,很快到她家门口了。她说:“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没有回宿舍,沿着马路继续走了会儿,抽了不少烟,想找个人说说话,不知道该找谁。几天没见刘老汉了,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我决定到他的住处看看,放电影这么大的事,全镇有一半人来看,竟然没见到他的身影。
他家住在桥头不远处的工人街,我一直朝那走,拐了好几个胡同。那地方我以前去过,是去拿补好的鞋。院门没锁,一推就推开了,里屋亮着灯,有些昏黄。我敲门,他开门后一脸诧异。我说:“大晚上到你这,不算打扰吧?”他说:“快进来。”
我们俩喝茶。我说:“这几天你跑哪去了?”他说:“办点事。”我说:“啥事?”他说:“你真要听?”我说:“前几天老鹰子的跟班找我,让我传话给你。”他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刘老汉抬起杯子,抿了一口茶。我说:“老刘,刘叔,我问你句真话,他是不是和你有啥过节?”老刘双手握住杯子,一脸郑重:“过节谈不上,我是无意中知道他和我同村,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会那么小?我出来几十年了,以为逃避了过去,逃避了村庄,却不想在这里遇到旧人。我以为他知道我的事,起初我去找过他,警告他,后面发现没这个必要,因为他对我的事不感兴趣。这几天,我每天跑到河边静坐,渐渐明白了许多东西。”
刘老汉讲到这里,我大概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这事刘老汉之前和我讲过,他十八岁那年,娶了隔壁村的一个女子,洞房花烛夜圆房未成,尔后半年时间,他竟然没有经历过一次鱼水之欢。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刘老汉成了几个村上下出名的性无能,在当时,这是极大的耻辱。村子的封闭,使他的新闻像炸弹一样炸开,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周边没有任何人家愿意再把姑娘嫁给他。刘老汉陷入孤独和迷茫之中,一气之下,带着行李远走他乡。
我说:“你在河边发现了什么?”他说:“你想知道的话,我明天带你去看看。另外,这人不靠谱,他让你传话,是因为他想打老鹰子的主意,老鹰子的苦头在后面呢。”
7
这个昏黄的上午,我和刘老汉来到喀普斯朗河边。水流潺潺,河流两边结起厚厚的冰层,唯独河中央能见水流。好在不算枯燥,我们各自带了鱼竿。老汉说,他几十年来一直以为自己在战胜孤独,却从未发现,其实他一直没有真正地处在孤独中。我说,那是因为你身边还有我们这些人。他说,不是。我对他的话表示迷惑。他说:“你玩过打水漂没?”我说:“小时候常玩,可这儿没有薄片的石头。”他说:“你用鹅卵石砸中间的水试试。”
他从河边捡来一堆鹅卵石,一股脑丢在我面前的冰床上。他说:“你丢一个试试。”我说:“这样会吓跑鱼。”他说:“我们本来也不是来钓鱼的。”我捡起石头,朝河中间砸去,“咕咚”一声,溅起点点水花,接着河流归复平静。我说:“丢了。”他笑笑:“你得继续丢啊。”我继续丢。他说:“你把自己想成砸在河里的这些不起眼的石头,你就不会再纠结姬甄的事情了。”
我始终没有明白他的话,可能他上了年纪,看东西比我深比我透。回到小镇,我们随意吃了点东西。他先回家,我在街上买了点墙纸,决定把宿舍糊一糊。到宿舍后,我把屋子重新装点了下,整个屋子看起来比以前敞亮许多,屋里从来没有这样温馨过,想想还差点什么,还差一只新的台灯和一台新的VCD……
我打开VCD,选了几首舒缓的音乐。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很快进入了梦乡。我被带到一座繁华的都市,那里或许是贵阳,或许是成都,又或许是武汉,总之不是铁热克镇。我站在天桥上,眼下车辆川流不息,行人摩肩接踵,各自奔忙,唯独红绿灯在固定的时间节点上绿了又红,红了又绿。我转身冲下天桥,朝着路边暂时停靠的公交车跑去,不知是多少路,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开去哪里。就这样,我跟着人群往前挤。车门关闭的时候,我眼前一亮,前面用手扶着车杆的姑娘,侧脸与姬甄极其相似,可她始终没有转过身来。我想喊她,但又不敢确认。公交车驶过好几站,在一处站牌前停靠,那姑娘下了车,我紧跟其后。人群蜂拥而至,我不小心被马路牙子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一跤。待转过神来,那姑娘已经消失在人群中。我十分恼火,环顾四周,全是高楼与陌生人,怎么也看不到她了,不晓得该朝哪个方向找,我顿时心急如焚,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此时,我的手正平放在胸口前,感觉心跳剧烈,“扑通扑通”。幸好是一个梦,我暗自庆幸,回心一想,我庆幸什么呢?我又在焦急什么呢?
新年的跫音越来越近,坐在屋里修表,时不时能听见外面传来的炮竹声。刘老汉找到我,说老鹰子出事了。我满是狐疑。他说,被那男的骗了,这会儿钱被裹走了,坐在家里哭哭啼啼,当时那男的就警告我,说他不抖我的事,我也别坏他的局,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身边那些老头又有几个在那方面是能行的,男人嘛,到头来都要走到这一步,只不过我比他们提前而已。
我没心思听他的感慨。收起桌子上的表,我说:“去看看。”
老鹰子蹲在门口哭。老汉和街坊们不断安慰她。
我从老鹰子家出来,决定去找姬甄。老鹰子眼光不行,给姬甄介绍的对象应该也不靠谱。到了姬甄家,门锁着。我又去她们车间,问了几个人,都说没见到她。我心想,她是不是和那个相亲对象见面去了?我穿过小镇,朝北面一直走,依然没有找到她。她会不会是去河边了呢?跑到喀普斯朗河边,只见白茫茫的河床,没有半个人影。
回到宿舍大院,才看见姬甄站在夕阳底下,她没有我屋的钥匙,估计等了许久。我有些来气,三步并作一步走上前,我说:“你跑哪去了?”她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去找你,没找到,到哪都没找着。”她说:“你找我?你找我干啥?”我说:“我担心你。”她笑道:“我有啥好担心的?”我说:“我以为你去见相亲对象去了。”她说:“你咋知道?”我说:“你真去了?”她笑道:“你猜。”然后她一本正经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票来:“我去买票了,打算回武汉过年,也许……”
“也许什么?”我问。她说:“也许,也许明年春天我就不来了。”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抱住了她。我有些难受,说不出原因的难受。她像只兔子,在我怀里一动不动。我说:“不要回了,你要是不嫌弃,我把这屋子修整下,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她没有说话,我没有看她。寒风里,我的下巴蹭在她的额头上。我的手捧着她的脸,有一股冰冷的眼泪划过指尖。那一刻,我想好了,就在这里,就在这间又暗又破的房子里,度过这个不一样的春节。
鞭炮声此起彼伏,大年初一早上,外面天寒地冻,窗子上结了一层雾水。姬甄伸出纤细的手,在上面画了一个太阳,还画了一座山,山下是一处农家别院。我说:“你画的啥?”她说:“村庄啊。”我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