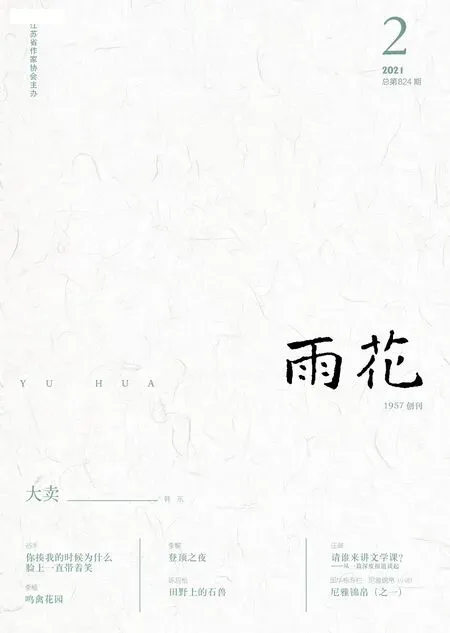尼雅锦帛(之一)
序章
我是往来于长安到康居的一个粟特商人,我有一个十多人组成的商队,我们的货物由驼队和马队运送。我把西边遥远国家生产的东西,像玻璃杯、香料、皮货、宝石、药材、布匹、葡萄酒和各种新鲜玩意儿运到长安,也把根据客户需要在长安采购的东西,运到康居和更西边的地方去。我们这些粟特商人,是这条大道上最受欢迎的人!
现在,我的驼队停留在精绝国的驿站里休整,他们正在把带来的葡萄酒木桶卸下来。康居葡萄酒很受这里的人欢迎。一听说我的商队到达了,这个小小的城邦国都沸腾了,很多男人拿着皮袋子,到驿站排队买葡萄酒。他们这里的男人女人都喜欢喝酒。这注定是一个开怀畅饮的夜晚,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喝醉了,夜空中飘荡着葡萄酒的香气和烤肉的香味儿,还有一种醉醺醺、暖洋洋的气息。
驿站的店主是个什么都懂的老头,长着一个红鼻子,他喝醉了喜欢谝闲传。我问他,你们精绝国是怎么在这沙漠边上建起来的?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爷爷的爷爷告诉我,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打仗。我们是山地人,和那些骑着马席卷过来的人打仗。他们是住在山脚下的绿洲和荒野里的人,荒野里有戈壁有沙漠,还有野兽,沙漠狼和野狗群,他们猎捕那些野兽。他们骑马,背上插着战旗,旗子上是一匹高高扬起前蹄正在奔跑的马,他们是马的一族,他们的行动就像是一阵风,因为有马的助力。马的一族一直沿着这整条巨大山脉下的谷地行走,他们是从更远的山谷平原走来的。他们骑着马,他们的马很漂亮,有的马跑起来身上会出汗,那汗的颜色是血的颜色,所以叫汗血马。”
我问:“那你们呢?”
老头摸了一下红鼻子,举起木碗喝了一口葡萄酒,用有力的牙齿撕扯着羊腿肉:
“我们?我们是鹰的一族,生活在雪山上。我们是从雪山的那一头翻越过来的,沿着雪线走,哪里的盘羊、岩羊、山羊多,我们就跟着它们走。我们说鹰能听懂的语言,把文字写在羊皮上,卷起来,就是我们的书籍,然后拿着它给一代代的孩子们讲故事。马的一族嘛,他们的文字写在木板上,这很奇怪,不过也不稀奇,他们种树,所以他们把字写在木条上。细细的木板子上,那些像虫子一样的字一看就头晕,歪歪扭扭地蠕动。直到有人能在我们两个部族之间,把这两种文字——鹰能懂的语言和马能认识的字互相翻译起来,我们才明白彼此的意思。”
我问:“过去你们都住在山上?那你们怎么来到平原了呢?”
“我们生活在雪莲花盛开的冰川上和高高的雪峰下面。我们不能住得再高了,再高的地方是鹰居住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干扰神圣的鹰的巢穴。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天天都能看到鹰在天空中飞翔。鹰是我们部族崇敬的动物,它们飞得高、看得远,我爷爷的爷爷他们那辈人的皮制盾牌上、额头上,都有一只鹰的烙印。我们部族在雪山上生活,都住在石头屋子里,在山的缝隙里放牧山羊,但那些羊经常摔下悬崖,它们的尸体被老鹰重新抓着飞入天空,被带到更高的巢穴里面去了。我们祖先的生活很艰难,山上食物短缺,部族的人口也不多。部族按照雪山连绵起伏的区域划分了范围,我们部族就在这接连起伏的山坳里、半山间生活,云彩经常缭绕在人们的腰间。大家驯化了那些山羊,它们有时候下山会带回绵羊,然后它们在山上交配生崽子。可山上依然食物短缺,特别是碰到雪灾的时候。大雪会不停地下,好多天都不停,人们把柴火烧光了,把存粮和干肉都吃光了,把骨头煮烂把骨髓都吸食完了,大家瞪着发红的眼睛互相看着,没有吃的了,然后,鹰的一族就像是天空中鹰的爪子一样,从半山和半空中俯冲下山了。”
红鼻子老头说到这里,感到自己控制不住酒意,舌头也大了,他说:“我会把我爷爷的爷爷从火中召唤出来,让他给你们接着讲吧。”说罢,他又喝了一大口葡萄酒,走到院子里的篝火边喷了几口,火苗子“腾”地升起来了。
果然,在火焰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白胡子老头,在火焰中闪烁着,开口说话了:
我们是鹰的一族,我们来到了绿
洲,要去抢粮食。
听到我们下山了,有时他们有防备,马的一族吹响了牛角号,就呼啸着冲过来。马的一族,他们的武器是长刀和短刀、盾牌和铁鞭。我们鹰的一族的武器是弓箭、单刀、投石器和匕首。马的一族靠的是马匹奔跑的速度,靠的是席卷而来的气势冲击我们的阵型。我们靠的是猛虎下山的勇气,靠的是雨点般射出的箭。马的一族的盾牌上,烙着一匹高高扬起前蹄的马,我们射出的箭,一下就被那匹扬起前蹄的马用嘴衔着,可我们的刀立刻削断了马的前腿,马的一族掉下马来,手里拿着长刀。他们的长刀是绑在木杆子上的,挥舞起来都带着风。近身搏斗的时候,我们只有像一阵旋风那样快,才能杀死他们。
每一次打仗,战斗的情形都很惨烈。马的一族马匹奔腾,人在马上,他们就像是一阵黄色的狂风那样从绿洲边缘的杨树和柳树林里冲出来,猛地扑向我们。我们就像是一股黑风暴那样,“呀呀”叫着从岩石和山坳里冲出来,和他们迎面相撞。我们更加敏捷野蛮,就像是雪豹和狼、熊和老虎一样下山了。我们每一次总能从他们的村寨里抢到绵羊和女人,然后就赶紧撤退,就像是鹰一样,一把抓到一只羊羔子就会飞到天空中,回到鹰巢里。
我们就是这样的。这样做能保存实力,我们人少,要见好就收。不然,马的一族就会占着人多势众,切断我们上山的路,用马匹的阵列和绑在木杆子上的长刀砍掉我们的脑袋。他们会在后面追我们,一直追到马匹无力上山为止,到没有上山的路为止。我们鹰的一族在石头的后面向他们射出箭雨。
我们鹰的一族,也有很多被他们杀死的。我们一些勇士的脑袋被砍掉了,可是身子还能跑,那样他们就不追了。没了脑袋的鹰的一族的男人,会跟着我们一起回到山上,还能再活好几天。虽然他们没有眼睛了,没有耳朵了,可他们的四肢还在,还有感觉,还能和我们一起走路,一起坐下休息。
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我们有脑袋的人就要小心翼翼了,我们知道这些没有脑袋的鹰的一族的男人们心里是很悲伤的。他们不能再吃饭了,他们只是和我们一起回到了山上,他们沉默着走路,身影和雪的反光形成了闪烁的光芒。然后,他们会一个个地向着更高的雪山上走去。我们都从石头屋子里出来,怀着悲伤的心情,看着这些没有头的鹰的一族的男人,一个个消失在雪山上的雪原中。
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天空中响起了鹰的啸叫,只见一只只大鹰从雪山之巅,从雪山上更高的地方飞起来,就像是一个神圣的鹰的家族在天空中聚会。它们盘旋着,巨大的翅膀带来了阴影,掠过了山间,让那些惊恐的山羊纷纷跳崖,让我们缩了缩脖子。
那些大鹰看着这些无头的勇士沿着山道缓慢地行走着,就像是一队自己给自己送葬的队列。我们惊呆了,
我们看到那些大鹰俯冲下去,一只只分别叼起了一个个无头的勇士,再飞入天空,逐渐隐入半山上的云雾中。就这样,无头的勇士们被大鹰叼着,去了更高的雪山。
这时,鹰的一族的族长,我们的大首领,他身披雪豹皮衣,他的脑袋上有着一只死去的大鹰尖爪做成的头顶装饰,就好像一只鹰蹲在他的脑袋上,或者是一只鹰护佑在他的身后,张开着翅膀。鹰头在他的脑袋上,鹰的眼睛是他用黑曜石做成的。
他说:“那些大鹰让我们的无头勇士回到了雪山之巅,它们雪葬了他们,他们将变成雪人,成为永生的不朽不坏的人。”
我们都恍然大悟了,我们的勇气倍增,嗷嗷叫着。我们看着那一只只大鹰在为我们的无头勇士举行着葬仪,发出了响彻山谷的啸叫声。
那个飘摇的白胡子老头的影子不见了。红鼻子店主又朝篝火喷了一口葡萄酒,火焰中再次显现了那个白胡子老头的脸,他继续讲:
所以我们和鹰是共生的两个族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鹰的一族。
马的一族和鹰的一族的战争经常发生,山地人和平原人经常打仗。都有死人的时候,最惨的时候,是各自死一半的男人。我们也会休战,因为没法再打下去了,打下去就没有男人了。没有男人,女人的肚子就鼓不起来了,就不能再生娃了。这个时候就休战了。也许会休几个季节,也许会休好几年,等到再有人力和物力的时候,我们再打。
其实,鹰的一族的日子要苦得多,我们是住在山上的,我们打猎,我们放牧山羊。马的一族在平原和绿洲生活,他们种植谷物,饲养马匹、牛和绵羊。他们继续和我们鹰的一族打仗,有时候我们打赢了,我们杀死马的一族的男人,那些男人被我们的箭射中了,被我们的匕首刺中了,被我们的短刀砍伤了,他们的血流尽了,结果会怎么样?
后来我们知道了,那些血流尽的马的一族的男人士兵,依然能够在战场上站起来。他们的血流尽了之后,全身变得苍白,可目光依然是坚定的,只是没有了力气,拿不动兵器了,这时,他们会一个跟着一个走,就像是我们的无头勇士在雪山上行走那样,他们也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向着与大雪山相反的方向走,走啊走,一直走出了活着的人们的视线,走出了绿洲的边界,走向了荒野上的戈壁滩,戈壁滩上还有很多风滚草、骆驼刺、芨芨草、红柳丛,走啊走,这些苍白的、死去的、血流尽的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一直向着荒野走,穿越了戈壁滩,走到了沙漠里。无尽的黄沙早就滚动着前进,向着马的一族居住的绿洲进发。沙漠和我们都想打败马的一族,占领他们的村寨和绿洲。
这些苍白的、血流尽的战士们来到了沙漠的边缘,在那里站立着,观察着,然后各自开始在沙漠中挖沙坑,
把自己埋进去。他们在沙子下面会聚集水汽和湿气,会汲取夜晚凝结的露水,他们埋进去的地方,会长出一丛丛红柳,阻挡沙漠向绿洲进发。
鹰的一族的无头勇士,成为了永生的雪人,在雪山之巅长眠。马的一族的流尽鲜血的战士,在沙漠深处成为地面蓬勃生长的红柳的根。
这样的传说在我们两个部族之间就这么流传开来了。
你们会问,除了打仗,难道就不会有和平吗?难道我们一定要把对方的头砍下来,让对方的血流尽吗?我们中间也有人这么问。
契机出现了,那就是,鹰的一族有人会跑到马的一族那里去,马的一族的人也有上山投奔鹰的一族的。男人女人都有。
我们劫掠了马的一族的女人和粮食,这些女人会在某一天带走鹰的一族的男人,下山回归马的一族。总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鹰的一族和马的一族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鹰的一族的女人们生出来的孩子,典型的鹰钩鼻不见了,变得像马的一族的男人们那样的平脸膛。马的一族的女人们生出来的男孩,有时候却长着鹰的一族的男人典型的鹰钩鼻子。两个部族的血液混合了起来,打仗的动力减弱了。
后来,鹰的一族的人口在减少,因为马的一族在山脚下绿洲上的地盘在扩大,他们养的马匹越来越多,对抗我们鹰的一族的办法也更加有效。他们的牛皮盾牌能够阻挡我们的箭雨,他们的牛皮鼓声能震荡我们的耳膜,让观战并给我们鼓劲的大鹰从空中纷纷掉下来,让我们在战斗中丧失了勇气。马的一族的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绿洲在持续扩大。
可浇灌绿洲的河水是从山上下来的,这条河我们给它起名叫尼雅河。我们鹰的一族经过仔细盘算,对马的一族发起了一次有力的战斗,就是在春天冰雪开始融化的时候,用巨大的石头阻断尼雅河的河道,挖出一条河沟,让尼雅河拐弯。随着夏季来临,尼雅河的冰川融水迅速增加,结果河道改道了,尼雅河的河水不再流向马的一族的平原绿洲了。
水源被阻断,这等于是断了马的一族的生命线。我们都准备好迎接一场最终的大战。我们猜想,尼雅河改道之后,马的一族种植的谷物、喂养的马匹、冒烟的村寨和平日的饮水都将陷入困顿。马的一族肯定大为恐慌、暴跳如雷,对我们发起总攻击。
结果,他们派出一支讲和的队伍,上山和我们谈判,还带来了很多绵羊、谷物和毛毯作为礼物,想和我们结束对峙,成为公开通婚的亲家。
我们的族长收下了他们带来的礼物,让鹰的一族的人辩论了三天。最后,大部分人认为,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和我们打仗,还送来了绵羊和谷物,是有诚意的。而我们的女人现在也生出了更多长着马面的男人,两边的亲戚越来越多了。这仗实际上也很难再继续打下去了,我们可以和他们讲和。于是,族长派出了十二个人组
成的队伍,带去了我们的礼物:盘羊、山羊、雪莲,雪豹和黑熊的皮。
过了好多天,这些男人才在我们的翘首以盼中回来,本来我们以为他们都被杀害了。现在,十二个男人都带回来一个马的一族的女人。休战的信息更加明确了。族长下令,把尼雅河的河道重新疏通开来。
尼雅河的河水欢快地冲向了平原上的绿洲。鹰的一族和马的一族就这么握手言和,互相通婚,互相融合。很多年以后,山上的鹰的一族的人就逐渐走下山来,和马的一族生活在一起,建立起绿洲上的村庄,一个个村庄连起来成了更大的村寨。后来,大家建起一座城市。城市就坐落在尼雅河的河边上,有城墙、有官署、有商铺和食铺,还有可供来往客商打尖住店的驿站。精绝国的主人叫国王,他掌管一切事务。
篝火的火苗逐渐黯淡,那张火焰中飘摇的白胡子老头的面庞不见了。我还想让红鼻子店主继续召唤他爷爷的爷爷,可他的酒喝完了,他问我要酒喝。
我让伙计再去给他取一皮袋子葡萄酒,我还想听他讲尼雅的故事。等到他又喝上了我给他的葡萄酒,就兴奋起来,下面是他的讲述:
“精绝国城门前的大路上,像你这样的粟特人从西往东走,还有从东向西走的汉地僧人、商人,有很多人在这条大道上来来往往。精绝国通行多种语言,佉卢文、汉文、吐火罗文都有的。那么,你一定关心鹰的一族和马的一族的那些死去的人,那些鹰族无头勇士雪人,还有马族流尽鲜血的战士,他们的灵魂和躯体如何安放,会不会回到精绝国来。他们还真的回来了。”
红鼻子老头讲到了这里,很得意地喝了一大口葡萄酒,他下巴上的胡子沾了不少葡萄酒的汁液,故意放慢了讲述的语调:
“有一天,在一个明亮的月夜,在雪山之巅的无头雪人纷纷走下了山峦,而在沙漠深处红柳丛下的勇士们,后来变成了褐色的干尸,他们也从沙漠深处走出来,向精绝国进发。就这样,无头冰雪人和褐色干尸人,从两个方向走过来,他们都想进入精绝国,看看这座生机勃勃的城邦之国,那是他们的后人建立的,他们要参与进来,要和活着的人一起生活。可是,在夜晚皎洁的月光下,精绝国的人忽然看到了这两群奇怪的人,一群是雪白的冰雪无头人,一群是有头但全身呈现黑褐色的干尸人,在城门外缓慢地、怪异地走过来,要进入城内,大家都很害怕,大声嚷嚷着不让他们进来。精绝国的城门设计得很巧妙,能够自动开关。一旦他们冲过来,城门就关闭了,一旦他们离开,城门又打开了,如此反复多次。
“那个夜晚,精绝国的国民都站在城墙上观看这一奇景,白色冰雪无头人和褐色有头的干尸人后来站到了一起,互相牵着手,要进入精绝国。他们可以用肢体语言交流,表达着要进入精绝国的决心。后来,太阳出来了,站在城墙上的人看到,那些白色冰雪无头人和褐色有头的干尸人,在太阳跃升的一刹那,开始汽化,一眨眼就变成了白色的烟和褐色的烟,逐渐飘散着,转眼就都不见了,彻底消失了。精绝国那遇到危险在夜晚自动关上的城门,又打开了。可城外已经是空空如也,只有一条大道向东西两边无限地延伸开去。”
红鼻子老头讲完了,也彻底喝醉了。他们把他抬到驿站的房间里。我也困了,明天一早我的商队还要出发,前往那万里之外的光芒四射的长安城。
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我手里握着一枚蚕茧,在暗黑的时间中沉睡。
我又梦见了前往精绝国的道路。那条路很长,很远,只有你上路了,你才知道它是多么遥远,遥远得我就是把脑袋想破了,都不能想象出个眉目来。我还特别怕腥膻味,没有到达之前,我听说精绝国的人喜欢吃山羊和绵羊肉,夏天也穿皮袍子,带着老远就能闻到的腥膻味,真是烦死人了。
本女子,我,细眉公主,虽然眉毛很细,可我从小就是男孩性格,喜欢习武练棒,我的几个哥哥都打不过我,这才是他们决定把我远嫁精绝国的原因,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都希望我走得远远的。
我们从洛阳出发,沿着黄河走,走着走着,就到达长安了。长安那时还比较繁华,但已经比不上洛阳的雍容华丽了。
这一路有驰道,有大道和小道,走得比较快。可是从长安往西的道路,越往前走路边的树木就越少。经过长安、凉州,经过甘州、肃州,我们一路都在宽阔大地的绿色走廊中行进,遥遥地望去,谷地两边是两列逶迤连绵的山峦,它也在行走一般,似乎在陪伴着我前行。再往前走,就是边关的关口,我看到,无尽的戈壁滩和黄沙梁上,生长着一排稀疏的白杨树,就像是一道大地的眉毛,等待着日出。
太阳出来了,我们就会继续前进。我随行的两个婢女,一个叫绿袖,一个叫红袄,都是鲁女,她们都曾在山东临淄养蚕种桑,现在一路上被道路的颠簸弄得昏昏欲睡。可是我,还在好奇地透过窗户往外看,端详着那广袤的陌生天地。
我的身上悄悄带着一些蚕卵。一路上,我坐在两轮马车上,四匹驽马拉车,疾速奔跑在大道上。十二名汉兵和从精绝国派来的迎接我的卫兵并驾齐驱。精绝国卫兵也有十二名,他们都是腰挂利刃的卫兵。他们中间还有一位使臣,他叫苏笈多,是一位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精绝国人,戴着缠头的巾帽,穿着腰间束扎的袍子,就是他带着这十二名卫兵,不远八千里路,前来汉地,为精绝国的王子求亲,选一位汉家王侯的女子远嫁精绝国。他们选来选去,就选上了我。
他这是第二次来汉地了。第一次来的时候,苏笈多带来了精绝国国王安归迦王的木简信函,信中并没有说精绝国王想结亲的事情,只是请求大汉朝赐给精绝国蚕种和缫丝技术,还有织锦用的提花机器。信中说,精绝国的人都喜欢丝绸,很多年以来,都是依靠粟特商人和汉地的商人来往买卖。精绝国也曾尝试种桑养蚕,可这些年,桑树种了不少,但养的蚕都活不了,即使养的蚕结了茧,缫丝技术又不行,眼下碰到灾害,桑树死了不少,蚕种也都没有了。而养蚕种桑是汉地自古就有的一门技艺,盼望大汉能选派秀女和巧匠,帮助精绝国养蚕种桑,传授缫丝技艺和织锦术。
大汉朝廷对精绝国安归迦王的第一封信的请求没有答应,告诉苏笈多说,养蚕种桑,是大汉独有的技艺,到了西域蛮荒之地自然会水土不服。精绝国本就是放牧和种植谷物为业的,不必考虑自己养蚕种桑。
于是,苏笈多就无功而返了。可精绝国的安归迦王锲而不舍,他可是脸皮够厚,他不怕被拒绝。过了一年,安归迦王又派这个皮肤黑黝黝的使臣苏笈多来了。
苏笈多带来了精绝国安归迦王的第二封信。这一次,在信中,安归迦王不再提请求大汉赐给蚕种、帮助精绝国养蚕种桑的事,他这一次是为他的儿子、精绝国王子阿钵吉耶求婚,希望能让阿钵吉耶娶到一位汉家王公的贵族女子。
大汉朝廷接到了这封信,几经商议,就把鲁王的小女儿,也就是我,选送精绝国,嫁给精绝国安归迦王的大儿子阿钵吉耶。因我长着两道细眉毛,皇帝赐我为“细眉公主”。我父亲觉得我平时脾气大,长得不好看,颧骨太高,眉毛太长太细,鼻子太大,像个西域人,是几个孩子中最顽皮的,把我远远嫁掉才好。
这把我气坏了!好吧,既然你们嫌弃我,不待见我,那我就跑得远远的,还要多带些自酿的桃花、杏花、樱桃香水,我才不怕那些腥膻男人呢。
汉臣告诉苏笈多,汉地养蚕种桑缫丝织锦的技术,不会传给精绝国的,谁泄露砍谁的头!细眉公主远嫁精绝国的一路上,各个关卡都要严加检查,一旦发现随行人员包括我,将蚕种夹带、匿藏,就要严加惩罚,取消这次结亲。哎呀,这等于是彻底断了精绝国安归迦王的念想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真的想结亲,只是想要大汉的蚕种和缫丝术、提花机而已。
在我打点行装的时候,苏笈多从驿站前来敝府,看看我准备得怎么样了。他看看旁边没有人,就对我小声说:
“我们安归迦王让我给公主转达他的口信。他说,精绝国面对大雪山,背靠戈壁滩,生活条件很艰苦,怕公主嫁过去以后生活不方便,特别是没有漂亮衣服穿。你带的丝绸衣裳,过几年旧了,就不好看了,就得穿他们的皮衣皮裤和棉袄了,臃肿不说,还特别难看,你到时候不要难过。”
我这次准备带几木箱绫罗绸缎,与两个婢女绿袖和红袄共赴精绝国。昨天,朝廷派人来,专门检查了我带的东西,不许我带太多丝绸锦帛。为了表达皇家恩典,赏赐给我的未来夫君阿钵吉耶一款织锦,织锦是方形的,上面的瑞兽和吉祥纹样之间,还缀有几个大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
苏笈多这么一说,我就很焦虑:“那怎么办?本公主别的不怕,不吃羊肉我可以吃水果蔬菜,可没漂亮的丝绸衣服穿,那可不行啊!我可不喜欢穿羊皮做成的衣服,棉麻的倒还可以,但容易起皱,还容易变色,容易脏。这可是我没想到的。”
苏笈多趁机说:“我们安归迦王让我带话,假如公主能想办法带来蚕种,然后在精绝国养蚕缫丝,自己给自己做漂亮衣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恍然大悟,同时点了点头,一边指着苏笈多说:“哈哈,就你们国王聪明是不是?让我带蚕种,我怎么带?藏到哪里?那可是要杀头的。朝廷都说了这个事情了,你都忘记你上一次灰溜溜回去,是什么原因了吗?”
苏笈多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嘿嘿笑着,说:“公主啊,我可以帮您想个主意,比方说,把蚕种藏在你身上,那无论是过城门过关卡,还是最后过边关,他们搜别处可以,搜身就不好搜了,我估计边关哨卡的人不敢搜身啊,因为您是汉家细眉公主啊。想想吧,为了您能穿上漂亮衣服,拼一下,也是值得的!”
他的话都说到点子上了。女人最怕的就是没有漂亮衣服,女人最担心的,就是永远少一件衣服。我想来想去,想了一个晚上,手里握着几枚蚕茧和几页毛纸上的蚕卵,在我自己的身上比划,藏在哪里好呢?
我就从脚开始想,藏到鞋子里?不行,一不小心给踩瘪了。藏在小腿绑腿里?不行,女人没有这样的绑腿。藏在衬裙里?哎呀,不好,温度变化会把蚕宝宝提前孵化出来,怎么办怎么办?要急死本公主了。藏在腰间?不行,腰带很紧,也是容易检查的地方。万一过关卡的时候,边关守将一声大喝:“宽腰带!”我一哆嗦,解开外腰带,“扑嗒”一下子掉下来几个蚕茧和蚕卵片,那我就被抓现行了,就地装进囚车把我押回大汉,那可就丢大丑了。藏在束胸里贴近胸口?哎呀,我的脸一红,也不行呢,胸口感觉很灵敏,藏几个蚕卵叶片,乳房皮肤就起会小疙瘩,感觉不舒服。
继续往上想。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咦?我就把蚕种藏到我的发髻里好了。对了,就藏在高高的发髻里。城门口检查站和驰道上的检查站,以及阳关的边关检查站,他们的注意力应该都在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上,像那些绸缎布匹和木箱子,而不会注意我的发髻。
我就把一些蚕种藏在了我的发髻里,又用金簪扎紧,而且,我的发髻还有丝帽罩着,以免被路上的风沙弄脏。
果然,启程后的这一路,在城门关检查站、驰道检查站的检查中,我们都顺利过关了。他们的检查很细致,他们似乎接到了命令,按照通关令附件上的记载,对我们的携带物一件件进行核对。
每次检查的时候,苏笈多都冲我挤眼睛,他知道我带着蚕种,可是藏在哪里,我连他也没有讲,所以他是既担心又怀有一种猜谜的快乐。
去精绝国的路途充满了艰辛,我们走得时快时慢。到达阳关的时候,我看到边关关口戒备森严,士兵的兵器闪耀着寒光,高大的城墙连接着城垛,就是一只鸟也别想飞过去。
在过关之前,我和苏笈多商量,要不要在这里的客栈停留一晚。苏笈多说,最好不要,过了这最后一关,抓紧时间赶路才好。
我们立即前往关卡。在阳关关口,守将带着铠甲鲜亮的士兵,戒备森严,根据来往的客商手里拿的度牒文书和货物清单,对往来客商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这里有一个小市场,什么都可以交易,我看到来来往往的商人们长得各色各样,最远有来自大食、康居的人。
我们过关的时候,关卡的士兵检查得非常仔细。苏笈多他们那些男人很快就过关了,可我和红袄、绿袖却被拦下来,带到一个房间里,守将说是要严加盘查,还要搜身。
我一下子紧张了,难道他们得到了什么密报,在这里要搜身?我十分生气,大声嚷嚷着,我是汉家细眉公主,看你们怎么对待我!
守将的态度变得温和,他知道我是去精绝国结亲的远行人,前路迢迢,未来的命运不可预知,要去精绝国那个鸟都飞不到的地方去。但职责在身,必须对我们详加检查。守将还带来了三名穿便服的女人,说是边关将士的女眷,让她们对我们进行搜身检查。
我想,坏了,她们是女人,就可以对我们三个人搜身呀,会不会是守将得到密报了,认为我们带着蚕种?
我做出一副很坦荡的样子。红袄和绿袖两个婢女并不知道我带了蚕种,藏在我的发髻中。三个边关将士的女眷的脸蛋红扑扑的,她们面带微笑,开始搜我们的身。其中一个搜我的身。我坐下来,有点紧张,我发现她搜得很细心。她那两只手在我的身上,从下到上,慢慢地搜着摸着,让我脱了靴子,她在里面仔细掏,让我脱了袜子,她仔细地摸和捏。又窸窸窣窣地摸着我的衬裤裙,腰带也解下来了,还让我解开了束胸。
我有些恼怒,我的脸气红了。解开束胸的时候,我自己不仅没有解放的感觉,反而呼吸困难,她的目光盯着我:“公主,您呼吸很急促,别着急,就要结束检查了。”说着,要给我解开头巾,看看发髻里面有没有东西。
我假装生气地挡开她的手,说:“你的手脏,我自己来!我要先把束胸穿戴好吧!”
她略显尴尬地让开,我恼怒地把束胸系紧,然后自己动手解开发巾。我的发巾是白色丝绸做的,我在空中抖了一下,那发巾就像是一只白鸽子一样在空中飞动,我的手一收,它就又回到了我的手心里,然后,我解开了发髻,让长长的头发飘散开来,里面什么都没有。给我搜身的女人的表情似乎有点失望,她疑惑地把我的白色发巾拿起来,抖搂了一下,什么都没有搜到。
我就像是变魔术那样,挽起长发束起发髻、扎上金簪的时候,又把蚕种藏进去了。接着,我把发巾扎好,穿好了衣服,和红袄、绿袖一起走出了屋子。
苏笈多的表情松弛下来了。我们顺利地过了阳关。
过了阳关,西去之路无故人!我就义无反顾了。后面的路即使再遥远再艰难,可我的心里是轻松的。护卫我们的十二名汉军完成了任务,留在阳关边关了。我们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沿着一条古道前行。
路上,苏笈多问我,蚕种到底还在不在我身上,我笑而不答。其实,我的笑容已经让他知道答案了。
我像是被放飞的鸟儿一样,感到无比自由。我们沿着一座巨大山脉的山脚往西南方向走。那座大山就像是一扇屏风,护佑着我们。我们走得时快时慢。沿途不断有水源补给,有一处地名叫野马大泉,因野马群常来一眼大泉喝水而得名。自大山上延伸出来的山谷中,总是有欢快的河水,冲向这条大道上北面的戈壁和沙漠。沙漠那边时常刮来风暴,我们就会停留在山脚下的一片树林里躲避。
我们再度出发,穿过红柳沟,来到一条大道上。走几个时辰,就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商队,骆驼队、马队、驴队都有,和我们交叉而过。坐在马车里,我能听到苏笈多用汉语、粟特语以及我不知道的语言和他们说话。他们都是奔走在这条大道上的商人,带着玻璃制品和香料、布匹,去汉地换买漆器和丝绸。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丝绸。
走了好多天,我们终于抵达了精绝国。远远地我看到了一座城,可城墙上没有看到一个人。我在马车里心跳得厉害,就快要见到我的夫君阿钵吉耶了。但他并没有出来迎接我。
我的两个婢女红袄和绿袖也从路上的不适和疲惫中苏醒,变得兴奋起来了。
等我们靠近精绝国城门的时候,那座城门自动打开了。我们的车子在马队的护佑下,快速进入城内。
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细说了。那一幕幕至今都像是一朵朵云、一场场雨那样清晰可见。精绝国的国王安归迦王服饰华丽,穿着很长的袍子,戴着漂亮的高帽子,他接见了我,我奉上了带来的蚕种。他的眼睛亮了。他激动地端着一个盘子,接过我藏在发巾里的蚕种,那蚕种小小的,几乎看不见。我指给他看,他就像是见到了稀世珍宝。“太棒了,这蚕种,就是我们精绝国的希望所在。我们的桑树有很多,可活蚕没有了,也没有人会养蚕,你来了,带给了精绝国这稀世珍宝。辛苦了!”
苏笈多已经向他报告了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和带来蚕种的困难。他赏赐了我们很多礼物,我也带给他和王后很多礼物,成匹的丝绸、锦帛、棉布以及铜镜、香袋等。王后很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筹备阿钵吉耶王子和我的婚事。按照他们的规矩和我的要求,在出嫁之前,阿钵吉耶是不能看到我的脸的。我的脸盖在红盖头的下面,精绝国的王室为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直到掀开了盖头的那一瞬,我才看到了我的夫君的脸,啊,他真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呢,而且,阿钵吉耶身上并没有什么腥膻的味道。
他看到了我的脸,用汉语说:“啊,果然是细细的眉毛,细眉公主,你的脸真白、真明媚,比月亮还好看。”
我有点羞涩地笑了,其实,我的羞涩是假装的。他很快就知道我会弯弓射箭,我会奔跑如飞,我和一般的女子不一样。
那天,精绝国陷入到了狂欢之中。精绝国国王的小小宫殿其实就是几间大的厅堂,装饰得十分简朴。他们的饮食都摆放在很长的雕花木桌上,很大的木盘子里装满了我感到很新奇的水果:巨大的石榴、成串的葡萄,还有西瓜和金黄的甜瓜。一只烤熟的骆驼被放在最大的毯子上,包括国王,每个男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小刀,去割肉吃。皮酒囊里装着葡萄酒,酒是暗红色的,随便喝,他们载歌载舞,人人都会跳舞唱歌,很快人人都喝醉了。
我发现精绝国很小很小,小到了就像是洛阳的几个里坊那么大。他们的人口只有几千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小国家有寺庙、有官署、有民居。精绝国的人信奉佛教,他们有一座位居城北的佛寺,里面有一座高高的佛塔。后来,我在精绝国的每户人家都看到了佛龛,家家户户都供着佛像。
我的夫君、阿钵吉耶王子喜欢打猎,善用弓箭。他发现我也会射箭,就更高兴了。
我用带来的那面朝廷赏赐的红、黄、蓝、绿、白五色锦,给他做了锦护臂。这面锦护臂有袋子系在胳膊上,锦帛的花纹非常美丽,有凤凰、鸾鸟、麒麟和白虎的图案,这都是瑞兽,还有祥云和瑞草装饰在边上。在这些吉祥的花纹图样之间,还有一行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做这件锦护臂需要裁剪,我从中间剪下,正面只留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几个字,“诛南羌”三字被我缝在背面了。
这款织锦是成匹织就的。做这面锦护臂,我只用了大半幅。阿钵吉耶喜欢射箭,他力大无比,负责训练精绝国的五百胜兵。他还养了几只大鹰,鹰要停在他的胳膊上,爪子很尖利,虽然给大鹰修剪了利爪,可他的胳膊还是需要保护。
阿钵吉耶非常喜欢我给他做的这件锦护臂。他问我锦护臂上这几个汉字的意思,我告诉他:
“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这五颗大星,它们要是出现在东方的天穹中,就有利于中原之国大汉的战争胜利。”
阿钵吉耶很高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戴着锦护臂。白天带鹰的时候,换上的是皮护臂。
我们结婚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将蚕种孵化出活蚕的工作中去,这是我来精绝国要做的一件大事。春天来了,我要将蚕种唤醒。精绝国很早就种有桑树,分布在城北的河边上。有桑树就好办了,蚕卵孵化出来,蚕宝宝就有桑叶可以吃了。
阿钵吉耶有时候陪着我一起做这个事。他感叹说,蚕实在是太神奇了,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循环的。成虫咬破蚕茧,化身为飞蛾,蛾再产卵,如此反复再生,实在太神奇了
我说,是呢,蚕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蚕卵孵化之后,幼虫一开始像是小蚂蚁一样,小小的,黑黑的,还要蜕四次皮,每次都不吃桑叶,这个过程叫作“四眠”。然后,我看着蚕种孵化,蚂蚁般的黑幼虫是一龄虫,蜕皮之后,变成二龄虫,脑袋大身子小,身子也变白了。到了第四次蜕皮之后,白白胖胖的蚕虫,有一拃长,接着,大蚕吐丝结茧。
我在精绝国养蚕成功了。我们在精绝国养的蚕越来越多,在尼雅河边的桑园里,绿油油的桑树叶上到处爬满蚕虫。它们在桑叶上游走,吃桑叶的声音沙沙响。它们结茧,它们咬破茧子出来飞翔——这里的人不喜欢杀生。
我让精绝国的人给汉地送去礼物,在汉地悄悄购买缫丝机和提花机,我要用来教精绝女子抽丝缫丝、织锦织帛。他们在汉地把提花机化整为零,偷偷运回来。只有这种提花机织锦,才可以织出经纬十分复杂漂亮的锦帛。织出了漂亮的锦帛,我的漂亮衣服,精绝国女子的漂亮衣服就多了起来。
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我和阿钵吉耶生了三个孩子。我们把孩子养育大了。他们有的去了汉地,有的去了康居。最小的儿子留在身边。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精绝国的安归迦国王病重,身体每况愈下,中风之后,不会说话了,躺在床上。这些年,他更喜欢阿钵吉耶的弟弟莫伽多,曾一度打算让阿钵吉耶的弟弟莫伽多继承精绝国王位。这几个月,在阿钵吉耶的身边和他弟弟莫伽多的身边各聚集了一批人,都在等待国王去世的那一天。
又过了一些天,安归迦国王已经说不出话,他无法确定谁来继承精绝国的王位。
老国王安归迦王死了之后,葬礼刚刚举行的那天,天气发生了变化。从遥远的沙漠刮过来了一场黑风暴,席卷了整座精绝国的城池。
就是在这场黑风暴中,精绝国发生了一场变故,统领胜兵的将军鸠伐耶不再支持我的夫君阿钵吉耶,他转而支持小王子莫伽多,胜兵三百人在鸠伐耶的带领下,包围了阿钵吉耶和他的一百多人,一番血战,阿钵吉耶的人寡不敌众,大部分被杀死了。
阿钵吉耶来到我的屋子,他浑身都是血,他说,莫伽多他们就要杀进来了,我要来保护你!
我那个时候正在织着一面锦,我让阿钵吉耶不要悲伤,要沉住气,看看他们能怎么样。我说,我就在这里,织最后一面锦,然后和你一起去面对他们。
阿钵吉耶说:“外面是莫伽多和鸠伐耶领着的几百胜兵,我要去出去了,我要和莫伽多会会面,我要当面问他,他想当国王,我就让他当,我可以死,但要放过你,让你回大汉去,你本来就是从那里来的。我去当面告诉他!”
他说完就冲出去了。我停下来,我的织机发出了呜咽声。
他这一出去,就没有再回来,我只听到了黑风暴击打着屋顶、窗户和墙壁的声音,天空黑沉沉的,到处都是沙子席卷着,空气弥漫着杀气和沙尘,外面兵器撞击着,屋内的我扶着提花机,我咳嗽着,等待着阿钵吉耶归来。
他没有再回来。
天色忽然亮了,我看到门缝下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就像是来告知我一样,有一股血流了进来。那血会说话,它告诉我一出悲剧的结果,那就是,阿钵吉耶死了。
我走了出去,我看到了莫伽多和鸠伐耶站在一起,我的夫君阿钵吉耶躺在地上,胸口中箭,流出了汩汩的鲜血。流进屋子的鲜血是阿钵吉耶的,他的弟弟莫伽多杀了他。
他们向我围了过来,我说:“别过来!”
我迅速退到了屋子里,把门关上,我知道横竖都是一个死,我要陪伴我的夫君阿钵吉耶一起去了。我取出了迷药,那药能让我封闭呼吸,就像是死了一样,我喝了下去。我即刻昏迷了。在昏迷之前,我没有忘记把蚕卵盘在我的发髻里,把一枚白色的蚕茧紧紧抓在我的手心里。
他们后来安葬了阿钵吉耶和我。我们躺在一具雕花的胡杨木棺材里。我给阿钵吉耶剪裁缝制的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还在他的胳膊上。他们给我裹了一件我织就的锦帛,在云纹和飞鹤的图案之间,有“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这几个字。
我就这样躺在阿钵吉耶的边上,沉沉地睡去。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发髻里藏有蚕卵,等待着孵化,在我的手心里,有一枚蚕茧,也许还会破茧而出,到那个时候,我将和蚕蛾一起,再度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