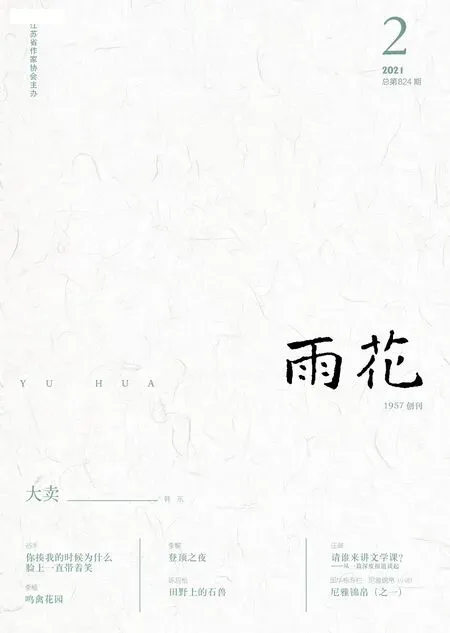鸣禽花园
1
“在另一个空间,你不一定认识我,我也不一定会遇见你。”俞红扔下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搬到乡下去住了。这话她不是没说过,五六年前,我们领着女儿在玄武公园的湖边散步的时候,她就是这么说的。我敢肯定自己的记忆没有问题,当时听到这句话,我还不以为意,只是想起更多年前我们初识的那个云雾萦绕的早晨。
那年刚放暑假,我们乘坐同一辆大巴回家,座位正好连着。我主动搭话,她倒也大方,只是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如我所料,她果然也是个大学生,只是专业相当冷门。我笑问她怎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她冷不丁地看我一眼说:“宇宙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更是我的宿命。”我又笑了,接着又觉得她的回答挺高妙的,令我有些自惭形秽,也有种没法聊下去的感觉。她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善聊天,这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更加有力的印证。
我不再吱声,趁车子颠簸的时机蹭她一下。有一次车子拐弯的幅度大了点,她的身体趔向车窗,我则故意不加控制地倒向她这边,还装出伸手去把持前排座位的样子,其实根本没用力。她扭头瞥了我一眼,有些不悦,这时我已经正襟危坐了。
后来我问俞红:“当时真的不高兴了吗?”她不置可否。
她家并不远,出城往西一个半小时车程就到了,而我还要继续向西,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但我也跟在她后边下了车。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就此别过,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
她回头看我,面无表情。我指着一块写着云湾村的路牌问她:“你家就在这里?云湾村,名字听上去不错。”她没回应,继续往前走。我上前夺她手里显得沉甸甸的包裹,她闪开了。她站在那里,回头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子才开口说:“你快回家吧。”
我看了看远处云雾缭绕的青山,以及山脚下散落着的青砖白墙的院落,只好掉头离去。
真正踏入云湾村,要等到第二年暑假。那时我们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甚至跟其他所有恋爱中的大学生一样,我们也去过两回小旅馆。
俞红家在村落最后边开始爬坡上山的位置,孤悬于村落之外,在山脚下,没有院墙。三间瓦屋前是一片偌大的空地,长满荒草,只有一小块狭长的地方被开垦出来,种植一些黄瓜、豆角之类的蔬菜。紧邻菜地西边有一个小池塘,山上的泉水流下来,在这里汇聚后再流向下游,在村口汇聚成一个更大的池塘。由于池塘底部是裸露的山岩、碎石,即便有一些淤泥,也能得以沉淀,所以池塘清洌无比。池塘里也几乎没有水生植物,一些小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看得分明。
我有些兴奋,绕着池塘跑了好几圈,像一条久别水域的鱼,恨不得一猛子扎进水里。俞红站在房子东侧上山的路口朝我招手,我没看见,她只好喊我的名字,我这才朝她跑过去。
小道路口有一颗枯死的老树,叶片全无,干枯的树干和枝杈戳向空中,和周围的绿色形成鲜明对比。我跑到俞红跟前,她看了我一眼,拉起我的手说:“走,跟我上山。”
山里安静极了,湿冷的气流在密林间浮动,树影婆娑,泄露着天上的光影。我有些害怕,担心突然窜出一只野兽,或者一条巨蟒。四处张望,终于在路边发现一截一米来长的断竹,我捡起来,紧紧攥在手里。万一有什么事,我可以用它保护俞红,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们沿山腰的羊肠小道向上走,走了个把小时,就没有路了。俞红抓住一些能够顺手抓住的树干、灌木枝条,开始向无路可走的陡坡上攀爬。见她毫无怯意和决绝前行的样子,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上去。
又爬了半个多小时,我已经气喘吁吁。眼前终于豁然开朗,一片红褐色的平坦巨岩出现在我们面前,岩面开阔得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它和这一带所有山体的岩石都不一样,其他岩石都是花岗岩,这片巨岩却含有赤铁矿成分。要不是俞红提醒,我还真没注意到它和周围山体的区别。
“也许它们,”我向周围划拉一圈说,“也许它们都是这种岩石,只是被林木遮盖住了吧。”
“如果是你说的那样,”俞红也向周围划拉一圈说,“它们也会像这片巨岩一样寸草不生。”
我这才注意到,巨岩之上果然一片荒芜,没有树木和青草,也没有鸟兽经过的痕迹,只有一些被风化的红褐色碎石安静地躺在日光里,使这一片地方怎么看都与周围的群山格格不入,恰如俞红家东侧枯死的老树与周围的绿色植物格格不入一样。
俞红来到巨岩中央,指着一块凸起半米高的岩石说:“嘎咱(那一带方言对爸爸的称呼)就是在这儿捡到我的。”
2
其实我早有觉察,俞红已经不止一次地萌生去意。
我们是在毕业后第三年领结婚证的,可是婚后第二年,她就提出想要回到云湾村居住的想法。
“那我呢?”我问俞红。
“你还留在城里呀,继续你的工作和生活。”
“你什么意思?”
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感情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从相识、恋爱,到结婚买房子,从来都是我积极主动的,尽管这使我看上去有些一厢情愿,但俞红也从未有过不满和怨怼。对俞红的想法,我当然没法同意,工作才刚刚起步,美好生活的画卷才刚刚展开,除非你觉得我们没法生活在一起了,可是缘由呢?俞红说没有缘由,也不是没法生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呢?俞红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接踵而至的妊娠反应,暂时打消了俞红回去的念头。她产下一个跟她一般模样的女儿,一个朋友还帮我们的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小疼。李小疼也就成了女儿的学名。接着就是哺乳、喂养婴儿这些事情。半年产假,哺乳期的俞红没再提过离开的事。
平心而论,俞红对我和女儿没什么不好,家里拾掇得井井有条,我和小疼的衣食住行,也让她打理得有条不紊,从来不需要我操心。她能让我每个早晨都衣着整洁地出门上班,让李小疼还在幼儿园大班就过了钢琴十级,三百首唐诗倒背如流。老师对孩子喜欢得不得了,其他家长也很羡慕,纷纷向俞红取经,结果当然都是自讨没趣,俞红根本懒得传经送宝。俞红大学读的是天文专业,本来我还担心这个专业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也得跨专业。我先她两年毕业,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便对她说:“你最好考研,甚至再读博士,你这个专业想找一份对口的工作太难了。”俞红说:“不需要,要不是嘎咱逼着我上学,我连学校门都不用进的。”结果她不但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还迅速成为天文学领域的佼佼者,业务论文经常在国际性的学术期刊和论坛上发表。
让我费解的是,俞红做这一切的时候,总给人一种缺乏热情的感觉。她似乎没有爱与被爱的感知力,没有享受天伦之乐的心理系统。她像个机器人,行使着生活赋予她的每一个角色所应完成的动作。尽管这些动作堪称完美,但总令人莫名地不安。
对这样一个妻子,我根本没有批判的资格。有一次我和小疼开玩笑说:“妈妈就像一个超级智能机器人,她都把你调教成一个小天才了。”这话不但没有引起俞红自豪的反应,反倒令她怔住了,似乎有所警觉。她忘了手里的煎蛋锅,直到发出一股焦煳味,我冲进厨房提醒,她才回过神来。我默默看了她一会儿,她没回应,只是铲掉焦煳的锅底,洗刷干净,重新为女儿和我煎了一锅鸡蛋饼。
是李小疼上幼儿园后的一场大病,再次阻止了俞红回到云湾村的念头。当时我有些气愤,对着已经回到乡下住了一个月还没回来的俞红咆哮:“小疼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这个家都离不开你。”说完我的眼睛潮湿了。电话那头的俞红沉默许久,撂下一句“我马上回来”,就挂了电话。
小疼得的是脑膜炎,我吓坏了,除了自责,也把更多的怨气撒到俞红身上。她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或者委屈。医生要求住院治疗,要进行数次腰椎穿刺并使用大剂量的青霉素,我有点六神无主,却也只好接受医生的方案。俞红却不同意,只让医生开一些又便宜又常规的消炎药和退烧药,说我们吃这些就可以了,不用住院。负责收治的医生有些不快,用圆珠笔点击着桌面,不大情愿地说:“是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俞红并不理会,只抢过医生开具的药单塞到我手上,自己抱起孩子就回家了。
一星期后小疼的烧退了,病状全消,就像只是患了一场小小的感冒。我不放心,又带她去医院化验了一番,症状果然消失了,脊髓液指标正常。不过我还是惊魂未定。你俞红凭什么这么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呢?通常情况下,要几万块钱才能治好的病,你凭什么就只给孩子拿几十块钱的普通药?
“你就知道钱,这是钱的事儿吗?”俞红淡淡地说。
从那以后,俞红再也没有提过要离开的事。直到今年小疼进入全市最好的外国语学校读书,俞红撂下开头那句话,终于还是回云湾村定居了。
她甚至都不给我谈一谈的机会,也没给小疼哭闹纠缠的机会。
3
这个家就要散了。我感到事态严重。第二天一早,我让小疼换好衣服,笨手笨脚地给她编了两条羊角辫。小疼到镜子前看了看,说没有妈妈编得好。我把她叫到面前,双手搭在她的肩上问:“你爱妈妈吗?”小疼点点头。
下楼的时候,小疼抬头问我:“那你呢?”
我没吱声。
我们来到云湾村,俞红却不在家。院门敞开着,几个工人正在院子里忙碌。一位我见过两次的远房表哥正在指挥工人干活。
为了能够回到云湾村安居,俞红曾经把一笔钱交给这位表哥,让他带人把老房子推倒,重新盖起一幢二层小楼。院墙也垒了起来,西墙把池塘圈进来,老树则在东墙的外边,南墙一直延伸到那片荒草地外围的树林边。她买来除草剂,让我背上喷雾器,把那些荒草全部喷了一遍,第二年开春再喷一遍,一年喷好几次。我说,你是想种什么吗?如果要种东西,最好不要大量使用除草剂,这会影响作物生长。她说你不用管,让地秃在那儿就好了。
对那片荒地,她似乎另有打算。
我曾劝俞红,嘎咱年事已高,我们把他接到城里住,给他养老送终,你又何必折腾呢?这话说过的第二年,也就是大前年,嘎咱便去世了。他是老死的,无疾而终。嘎咱是个哑巴,一生未娶,穷困潦倒,捡到襁褓中的俞红那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村里有人劝他放弃俞红,说你个穷哑巴,拿什么养大孩子呢?也有人家要抱养俞红,哑巴没同意,他认为这孩子是上天送给他的,谁也别想抢走。
哑巴姓俞,女儿来自那片人迹罕至的红色巨岩,哑巴便给她起名叫红红。
因为是被哑巴嘎咱养大的,所以俞红也懂手语。大学几年,俞红就是靠一套流畅的手语,在聋哑学校兼职养活自己的。俞红曾经跟我说,要不是自己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她宁愿去聋哑学校当教师。她喜欢带聋哑儿。“那是一个无声却神秘的世界,他们的语言和想象力比你们人类精彩多了。”俞红说。我揶揄俞红:“搞得你们都是外星人似的。”俞红的身体一紧,过了良久才缓缓说道:“其实我就是外星人。”当时我刚刚在手机上订了三张《星际穿越》的电影票,便抱起小疼说:“走喽,咱们跟外星人妈妈一起去看看她的家乡。”小疼在我怀里笑嘻嘻地朝身后的俞红招手:“快点快点,外星人妈妈。”我回头看了一眼,俞红怔在那里,面色分明有几分不易觉察的凝重,眼圈里有一层模糊的水雾。
表哥说俞红去附近的村庄了,具体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给表哥递了根烟,问他这是要盖什么,表哥有点诧异。他的表情显然是明白了这样一件事实:俞红并未跟我说过要在这里做什么。他很快恢复了平静,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对着那片打过多遍除草剂,如今野草依然茂盛的荒地划拉一下手臂说,红红要在这个地方盖上鸡舍……见我立马僵硬起来的表情,表哥不说话了,过了许久才又说,红红这孩子,打小孤僻惯了,你说这,好好的天文学家不当,偏要回来养鸡。
我强忍着愤怒。我想让工人们停手,把他们统统赶出去。这时俞红坐着一辆柴油三轮车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辆,两辆车上装满了鼓囊囊的蛇皮袋。见到我和小疼,俞红并不诧异,也毫无惊喜。她揽着女儿的肩膀,招呼表哥和工人帮忙卸车。一个工人肩头的口袋绳松了,金黄的玉米倾泻出来,洒落一地。
小疼已经完全懂事了,但毕竟还是个孩子,即便肚里有话,也未必愿意表达,或者还不知道如何表达。她抬头看看俞红,又看看我,便掰掉俞红搭在她肩上的手,掉头走向屋里。我把手里的烟蒂狠狠摔到地上,追了过去。
我把小疼揽在臂弯里,一起坐在沙发上,轻轻拍着她。小疼脑袋枕在我肩上,怔怔地看着窗外。“爸爸,妈妈真的要离开我们了吗?”小疼问了一句。我的眼泪忽然涌出,小疼也早已泪流满面,终于忍不住钻进我怀里,“哇”的一声哭出来。
4
俞红带小疼爬上那片红色巨岩,来到凸起的岩石旁说,外公就是在这里捡到我的。小疼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讶。她仰头看着俞红问:“他们为什么把你丢在这里,难道不担心被野兽吃掉吗?”俞红微微一笑:“没有他们,外公说过,妈妈是上天送到这儿来的。”
“你是被遗弃的,现在你也要遗弃我和爸爸了。”小疼说着又哭了。
“不是这样的,”俞红坐到岩石上说,“妈妈是外星人,你真正的外公外婆,也是外星人。”俞红说着解开小疼的辫子,要给她重新编织,但被拒绝了。小疼披散着头发,用衣袖抹了把眼泪,定睛看着俞红,似乎在等一个确切的答案。
俞红看着远方的天空,沉吟良久才说:“我是外星人的孩子,你也是,你有一半外星人的血统。”
“我不信!”小疼大喊起来。
“你必须相信。”俞红抚摸了一下女儿的脑袋,继续说她编织的故事,“我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外婆,她是个罪犯,要被流放到别的星球。几个警察驾驶飞船,押解一批犯人离开他们的母星。可是离开没多久,飞船就失事了,应该是发生了暴动。犯人和警察火并,死了好多人,有犯人,也有警察。慌乱中,你的外公,他是个警察,他差一点打死外婆,可是外婆没参与暴动,只有他们俩成了幸存者。飞船的导航系统、定位系统和通讯系统都被摧毁了,外公外婆在宇宙里迷了路。太空里一片黑暗,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飞船正滑向哪里。他们关闭了飞船上的大部分功能,只保留两个人的维生系统,但就是这样,飞船上的能源还是在一点点消耗。患难与共中,他们有了爱情,互相鼓励着要活下去。但不幸的事情总是伴随左右,这一点你要记住,将来你的生活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没有关系。对外公外婆来说,我的出现成了他们的不幸,最大的不幸。外婆怀孕了,那就是我,你的妈妈,诞生于漆黑冰冷而又荒芜的外太空。”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跟孩子瞎掰什么呢!”我想制止俞红。
俞红幽幽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爱怜。“你最好也听听,我早该告诉你的,但一直没有机会。”俞红说着又转脸看着女儿,继续她荒诞的故事。
“外公惊喜之余,更多的是忧虑。飞船上的能源眼看将耗尽,我的出生,将会加速一家三口的灭亡。在这期间,外公已经修好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他们这才知道已经来到太阳系的火星位置。外公清楚,飞船残留的一点能源,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返回母星了,甚至不可能到达最近的一个能够补充能源的联邦星球。通过探测系统,外公侦测到了地球。外公发现飞船上的能量仅够一个人维系着生命来到地球了,否则就是船毁人亡。外公悄悄把自己反锁进休眠舱,关闭了休眠舱的能源供应。就是那么一点点能源,他也不能用,而是要留给外婆。绝望中的外公忘了计算我的出生也会消耗飞船的能量,所以外婆根本不可能活着降落在地球。
飞船滑进地球大气层燃烧起来之前,外婆已经奄奄一息了。她使尽余力,启动自动导航系统和传动装置,把我送到了这块岩石上。外公死了,外婆死了,飞船也死了,他们就埋在这片红色巨岩下。”
“所以呢,你是想回来,一点点挖开巨岩,找到飞船和外公外婆的尸体吗?”小疼显然有些信了。
“对,你妈妈本事可大了,她只要念句咒语就能山崩地裂。”我嘲笑说。
俞红吻了一下小疼的额头,微微笑着说:“巨岩就是他们的坟墓,飞船则是墓室,妈妈没必要再去惊扰他们。妈妈的使命是制造足够的能源,重新启动飞船,把他们送回自己的故乡。”
“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我们外星人有记忆遗传基因,所以外公外婆的所有记忆,都在我脑子里呢。可惜你有一半地球人的基因,这个基因在你身上便退化了,否则你也能拥有妈妈的所有记忆。你能来到我的脑海里,看到宇宙的样子,看到外婆家美好的景象。那里真的很美。”
5
由于第二天我要上班,小疼要上学,晚饭后,我们决定回城里。对俞红的话,小疼将信将疑,但被我三言两语就瓦解了。当着俞红的面,我几乎怨毒地对小疼说,外星人都是冷血动物,你妈妈也是,她要走就让她走,咱们父女,在这个星球上照样相依为命。从情感上讲,小疼更倾向跟我在一起,所以她连晚饭也吃不下去了,一直躲在屋里嘤嘤抽泣,最后还是俞红把她劝出房门的。俞红对她说:“妈妈会经常回去看你们的。”小疼才勉强停止哭泣。
小疼问:“那你会带我和爸爸一起离开吗?”
俞红沉吟了半晌说:“我们外星人的生理结构,能快速调整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可是你已经退化了,爸爸更不行,所以你们都去不了。”
“你说外公外婆是凭着爱的信念才生存下来的,对吗?”小疼不死心地问。
“是的。”
“可是你根本不爱我,也不爱爸爸。”
“不,妈妈爱你们,永远爱你们,可是我们不是非要生活在一起。在另一个空间,你们同样存在,在那里我们仍然生活在一起,甚至要比这里长久。”
我生气地把俞红拉到旁边,小声怒斥她:“你有完没完啊,有意思吗你?”其实这时候我挺担心俞红忽然变回原型,轻而易举地把我干掉。她也许不会消灭小疼,那毕竟是她的女儿,但未必不会干掉我,比如伸出螳螂般的利爪,在我胸口捅出一个大窟窿,或者吐出绿色的黏液,把我溶解掉。我不敢想象俞红的原形是个什么样子,《阿凡达》里那种样子也就罢了,可如果是《异形》里那种丑恶残忍的生物,我该多么不幸啊。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天哪,我居然和一个青面獠牙、利爪如锯、腥液黏身的外星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一起散步、吃饭,一起睡觉,睡在同一张床上。她倒是不惧怕黄酒,我身边也没有一条如花似玉的青蛇。
想到这些我不禁呵呵笑了。
由于走神,好几次车子差点儿撞到高速公路的护栏上。小疼吓得不敢吱声,双手捂紧眼睛。车子稳定后,我腾出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使她安定下来,她也很快就睡着了。直到车子停进车库,小疼仍然睡着,我抱起她。小疼的手臂蛇一样缠着我的脖子,进屋把她放到床上后,仍然紧紧箍着,无法松开。我要掰开小疼的手臂,她突然嘤咛一声:妈妈不要走。我的眼眶一下子湿了。我躺下来,搂紧她娇小温热的身躯。看着她白皙俊俏的脸蛋,我忍不住亲吻她的额头。一个好好的小家庭,说散就散了,今后只有我跟小疼生活在一起了。想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浑身筛糠似的颤抖。小疼突然睁开双眼,两只眼球发出幽亮的绿光,如星光下黑豹的双眼。
6
俞红返航的计划是这样的:她通过搜索外星人父母遗传下来的记忆,已经确定了太空船的位置,就在那块红色巨岩下。飞船性能良好,只是能源已经耗尽,无法起航罢了。而她要做的,就是收集鸡粪,她说这是目前地球上便于开发利用的最佳燃料。也就是说,只要积攒足够多的鸡粪,她就能顺利起航,把父母送回太空深处的老家了。
我有点杞人忧天,不知道飞船如何脱离那块红色巨岩的禁锢,难道它能像潜水艇浮出水面那样轻而易举地浮出岩石吗?
俞红在院东墙对过的坡地上竖起了二十个巨型金属罐,圆形的,汞银色外身,每个都有十几米高,直径大概有五米。金属罐底部是密封的半球体,顶部也是半球体,只是多了个舱口。俞红和鸡舍工人通过焊接在罐体外的悬梯爬到顶部,打开舱口盖,才能把清理出来的鸡粪倒进罐子里,再关上舱口。每天如此。
对俞红的行为,云湾村的居民们本来就不解,再看到那二十个竖立在不同坡度、高低不一的冰冷罐体,不禁慌张起来。一些传言在村民中间散播,有好有不好。有的说俞红这孩子懂感恩,是回来给她的哑巴嘎咱守孝呢。也有的说她就是个怪胎,从小就跟人不一样,既然在城里安了家,就不该回来。还有的说俞红根本不是回来养鸡的,而是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要不然她怎么会放弃体面的天文学家工作,回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呢?因为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语言也不通,即便有人想打听点什么,也没那么容易。插句题外话,从认识俞红到现在,我确实没学会半句她家乡的方言,太难懂了,简直像外星语。
大家的顾虑和隐约的恐惧很快就让俞红打破了。她聘请的五个养鸡工人来自云湾村五个最穷的家庭,现在他们都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自然不会说俞红的闲话。俞红还让工人们把所有的鸡蛋分到各家各户,分文不收。大家伙高兴坏了,有的干脆把吃不完的鸡蛋拿到镇上、县城里卖,换回一些食盐、酱油、洗衣粉等生活必需品。
到了第三年,俞红的鸡舍已经扩大到云湾村的好几个地方,占地数百亩。这当然不是俞红一人之力。是村长找到了俞红,说你干脆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吧,咱把村里人都叫来给你养鸡,在外打工的,愿意回来的就回来,还有邻近村落的闲人,总之咱不缺人手,就是穷怕了。于是云湾村有了自己的养殖业,宰杀作坊,包装间,运输队。鸡蛋、活鸡和生鲜鸡肉被一批批地运往外地,甚至连鸡毛也能换成钱。俞红没提别的条件,只要求人们必须把所有的鸡粪收集起来,装进那些巨型金属罐里,否则她就停止供应保证鸡群不患瘟病和令肉质鲜美的养殖技术。村民们对俞红充满感激和敬畏,也就不在乎她收集鸡粪这一令人无法容忍的怪癖了。而为了这些,俞红也忙碌起来,整天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俞红的鸡粪罐也远不止二十个了,而是连成了一片,高高低低地占满一片山坡。俞红常常坐到二楼的阳台上,隔着玻璃窗看着那一片金属罐发呆。月光下,银白色的金属罐反射着幽幽冷光,显得陌生而神秘,像一片外星人的墓地。到了早晨或白天,阳光照耀金属罐群,那一片山坡便熠熠生辉,同样陌生、神秘如外部星球上的一个场景。
按照俞红自认为是外星人的说法,这片金属罐无疑成了他们在地球上的一个能源基地,一片地球上的花园式基地。我开玩笑地问俞红:“这么说来,我们的地球也成了你们的联邦喽?”俞红正儿八经地回答:“我们的技术还不能探测到地球,不过对于那些能够探测到并且有利用价值的星球,我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征服。”我不屑地“切”了一声,挑衅似的摸了摸俞红的脸蛋说:“我的外星人老婆,你还是想一想怎么把这么多的鸡粪罐运上你的飞船吧。”小疼也跟着起哄,抱着俞红的腰说:“外星人妈妈,你要是能让其中一只鸡粪罐平地飞起来,我就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对我,俞红不置可否地一笑,似乎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但小疼得到了答案。
7
俞红说是经常回来看女儿,其实大多还是我带小疼去云湾村看她。路途虽然不远,但她与我和小疼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有种远到天边的感觉。
每次到那里,都不觉得俞红有丝毫的惊喜。养鸡场里有伙房,有负责做饭的阿姨,她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俞红不再像从前那样过问我和女儿的三餐。好在做饭的阿姨每次看到小疼来,都会特意张罗一些花样翻新的菜品,专门送到我们一家三口的餐桌上。通过阿姨的眼神,我觉得村民们似乎知道了一些什么,似乎又一无所知。阿姨的眼神充满对我和小疼的怜悯,尤其是小疼,那么乖巧聪明的一个可人儿,却形同已经失去了妈妈。有一次我去伙房,听到正在切菜的阿姨自言自语说:唉,可怜的孩子。也不知道她眼里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指我,小疼,还是俞红,我想多半是小疼。
俞红也不再过问孩子的穿着冷暖、学习情况,好像她决定回云湾村后,我跟孩子的生死就跟她没有关系了。难道她当真以为,我跟小疼在她的世界里获得了永生?俞红的解释则是,小疼已经长大了,她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你说的简直是屁话,”我暴跳如雷,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从头到脚,你看看你现在还有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还有没有一点妈妈的样子。”俞红并不生气,拉小疼来到东墙根儿那棵枯死的老树下,指着高高树杈间的一只鸟窝对小疼说,每年这个时候,是雏鸟学会飞翔的季节,你仔细观察一下。
我拽着俞红,再次爬上那片红色巨岩。我找人了解过了,它和周围的山体没什么区别,都有赤铁矿成分,只是它的赤铁成分含量更高,所以不能生长植物罢了。我也找医学专家看了你的体检报告,和正常人无异,你不是外星人,你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地球人。
“我们有迅速转化基因,以便适应新生存环境的能力。”
“算了吧,那你怎么没变成一条狗?”
俞红没吱声,她并不在意这种根本无法聊下去的尴尬。我被激怒了,把她摁到那块凸起的岩石上,褪下她的裤子。这一回我专心探测她的身体,和别的女人并无二样。这越发激起我的好奇和疑惑,于是奋力挺进。她的反应和别的女人也没什么区别。凸起的岩石在无知无觉中下沉,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我们陷进一个深深的圆形岩洞,一束光打进来,打在我们扭动的身体上。
那天回城的路上,小疼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她的观察结果。那是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鸟,鸟妈妈用带有硬刺的木枝筑巢,巢里铺上羽毛、柳絮、干草等柔软的物质。当雏鸟长大后,鸟妈妈便将那些柔软的部分全部撤去,留下带刺的树枝。鸟妈妈把雏鸟拱出鸟窝,迫使它们离开鸟巢。雏鸟挣扎着,很害怕的样子,但终究还是被拱了出来。下坠之时,雏鸟拼命扇动翅膀,一下子就学会了飞翔。
小疼还沉浸在观察的兴奋和想象中,对我说:“鸟的样子真奇怪,难道也是来自妈妈母星上的物种?”
我抚摸着小疼的脑袋,又想起俞红眼里不止一次闪过的水雾,终于明白那是她知道自己终将离开我们的不忍和不舍。
我对小疼说:“妈妈不是外星人,她只是太孤单了,我们要多陪陪她。”
8
那次以后,我和俞红开始异常迷恋那个岩洞。圆形洞口透进来圆形的光柱,有时是阳光,有时是月光或者星光。洞底岩石平滑,如一张天然的圆形石床。我们无处躲藏,任凭洞口的光线笼罩。我们在这光线里起伏、纠缠,喘息声或喊叫声顺着洞壁飘向洞口,很大一部分被反弹回来。有时我会觉得难堪,便返回洞口,砍一些树枝将它遮住,结果又被俞红搬开了。她躺在我身下,热切地搂紧我,说就让它敞开着,让光照进来。
有一次结束,我揽着俞红的肩膀问她,准备怎么处理那些鸡粪罐。我是心里有谱,觉得她应该不会再离开我们了,才敢这样问她的。俞红仍然没说会不会返回自己的星球,只说她打算把那些鸡粪罐浓缩成丸剂般大小的胶囊,投进她父母的飞船的能源舱里,这样飞船就能启动了。她带我从岩洞进入飞船,在里面参观了一番,最后进入一间密室。密室中间悬浮着一只篮球大小的物体,俞红说这个就是飞船的能源舱。见我仍然面露疑惑,俞红继续解释说,能源舱只是一种特殊构造的设备,真正的能源,是来自球心位置一粒芝麻般大小的黑洞。
“是的,飞船全部的能源,就来自那粒芝麻般大小的黑洞。”俞红强调说。我问俞红:“别说是那些鸡粪罐,就是这一片山林,都能装进那粒芝麻大的黑洞里,是这样吗?”
“是的。”俞红的回答不容置疑。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惊醒,由于门窗关着,听不清楚。我见俞红不在床上,想她可能已经起床去工作了,便穿衣下床。开门来到二楼的阳台上,我看见一个村民正从山间的小道上跑下来,一边跑一边惊恐地喊叫着,巨岩崩塌了,巨岩崩塌了……
我惊恐至极,第一反应是俞红在不在。我满屋子找俞红,没见到她,又跑到院子里,边边角角找了个遍,仍然没有俞红的影子。我冲回房间,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疼,一边给她穿外套一边几乎带着哭腔说:妈妈返航了,妈妈返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