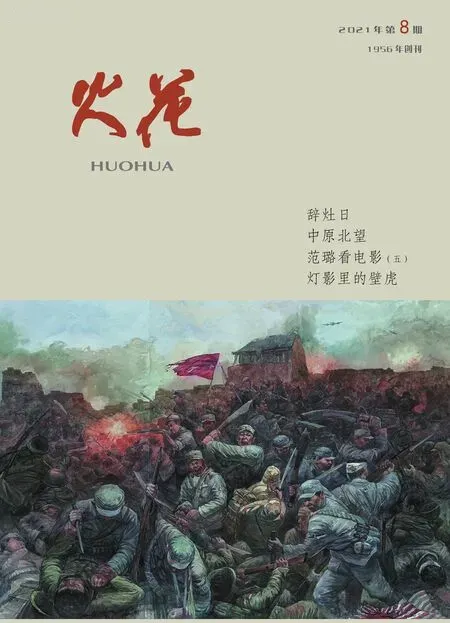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二)
鲁顺民 陈克海
第二章 走出去的人们
一、“没念个年级”
赵家洼人口外流,最先一批是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兴县、保德的老移民回到故乡。毕竟人不亲土还亲,回到故乡,乡里乡亲还有个照应。
是啊,改革初年,民间活力焕发,到处是希望的田野,田野充满希望,故乡那边有许多机会与可能。当年祖辈携儿带女,一路奔波来到赵家洼,原因只有一个:这地方饿不着人。改革开放,温饱无虞,农民还有其他“想法”。
马忠贤老人回忆说,自从改革开放分工地,村里就没拉脱(注:中断)个往外走人。早先迁来的人陆陆续续迁回保德、兴县的就有十几户,下来,还有上内蒙古的。
上内蒙,进后套,本是山西人持续三百年的移民路线,老人嘴里现在还可以随口说出内蒙古许多地名来,中瓜地(准格尔旗)、东胜(鄂尔多斯市)、临河(巴彦淖尔市)、陕坝(杭锦后旗)、三道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前旗(乌拉特前旗)、中旗(乌拉特中旗)、后旗(乌拉特后旗)、吕祖庙(包头市东河区)等等诸般,这些祖先用脚踩出来的地理空间,深深嵌入在民间记忆里。而留在赵家洼百姓嘴里的这些地方,也跟赵家洼、宋木沟、赵二坡、中寨、阳坪这些地方一样,“二姑舅啊二姥爷,三亲六眷漫绥远”,也是一村一舍的保德人、河曲人、宁武人、兴县人,都是外来移民。人行千里,口音不改。
他们迁徙,他们离开,就像他们到来一样,可以视作一种生活常态。其实,还不止赵家洼,在岢岚县,在晋西北其他地方大致相类。
就山西省而言,太行、太岳山区,广有河南、河北、山东移民,吕梁山区则广布陕北老乡,他们或避兵燹,或躲荒旱,举家迁徙来晋。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门心思安居乐业,太行山、吕梁山深度贫困地区,几代人掘土而居,墙不挂皮,地不漫砖,坑洼不平,生活质量相当之差,那情形就是随时准备拔腿就走,准备下一次迁徙的架势。
诚然,就赵家洼村而言,以上两种类型,返乡离开,走西口出走,人口流失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走的也是可数的几户,村落还基本上维持着“地分下去”之后的乡村生活、生产秩序,被生产队约束的生产力因改革开放再度释放,有种粮大户,有养羊大户,即便有外出打工者,也是可数的几个年轻人,“家里的地不能丢”。
但这正常吗?
难说。
相对同时期出现席卷中国乡村的农民工进城“民工潮”,赵家洼村青壮劳力仍然从事传统农业和牧业的情形就显得迟钝多了。
多方了解,陈福庆找到第一批离开村落进城的赵家洼人。
第一批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方便孩子就学。
在生产队“最红火”的时候,赵家洼有小学,不仅是小赵家洼,大赵家洼、骆驼场都有过教学点。尽管教学质量差强人意,但总还极大地方便了村落子弟,孩子们念小学,大家几乎没有放在心上,至于孩子大了上初中、上高中,生活能够自理,那就更不用家长太过操心了。总之,读书还是个事?
真还是个事。
关于赵家洼小学,陈福庆在家访老贾贾高枝的时候,听到一个令他哭笑不得的细节。
老贾两儿两女,陈福庆问他女儿:读书读在几年级?
老贾女儿不好意思:没念个年级!
这回答逗笑陈福庆,但他也听出来,老贾的女儿是没念过几天书。
为什么呢?老贾说:“女子没念过几天书,没文化,就是受苦,打工。那会儿光景(注:日子)都过不起,能念得起书?就没念年级。二小子倒是念了两天,就在阳坪乡初中。有文化不一样,现在在城里搞装潢。那个时候地多,娃娃们也早早地帮着放牛,喂猪。就是去念书,娃娃们那么小,一天要走四五里地。村里老师也不行,都是民办教师,几个年级混在一起上,文化没学下,就是个害,还不如早些回来帮衬家里。”
老贾说:“娃娃不念书,也怨我,当年和人下棋,不让人家悔棋,两个人吵了一架,人家老婆是小学老师,代教,结果把咱娃娃敲打得不行。下个棋,就把人惹下了,气撒到娃娃身上,这还是老师?能教育成个啥?我和你老汉下棋争吵两句,你就把我的娃娃另眼相看。要这,能学成个啥?回哇(注:回家吧)。”
一步悔棋,误了终身。究竟还是重男轻女,四个孩子“苦重”,偶然随时光临,偶然就成了必然。但当年的乡村教学质量实在是难圈难点,已经很难适应今天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期许了。
第一批因子女就学进城的,有一个赵亮香。
赵亮香夫妻2008年离开村进城,为的就是孩子上学。当年,夫妻俩都是二十郎当岁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现在已经年近半百,儿娶女嫁,当了爷爷奶奶。
赵亮香,就是首开小赵家洼的赵福义、赵玉娃兄弟俩一族的。赵亮香为赵玉娃的孙子。赵福义、赵玉娃两兄弟从静乐来到岢岚县,“立起”小赵家洼村,才有后来陆陆续续从保德县、河曲县、宁武县逃荒过来的赵家洼人。
但赵亮香的父亲却是保德人。赵亮香父亲本来姓崔,是保德县的大家族,祖居保德县的崔家历史上出过进士,出过举人。当年,日军进犯保德县,烧城池,毁渡口,作恶多端。赵亮香祖父早逝,祖母带着两儿一女辗转逃难,一双小脚带着三个孩子,到了赵家洼,实在是走不动了。
此时的东家赵家兄弟,实际上也是肯下苦的庄户人家,可惜子孙不旺。前脚赵福义抱养养子顶门,后脚赵玉娃接纳从保德逃难来的崔家母子,长子仍姓崔,次子给赵家顶门立户。这就是赵亮香的父亲赵凤梧。那时候,赵凤梧才五岁。
老赵家待赵凤梧不薄,悉心培养,耕读传家的保德崔家子弟也争气,1958年到供销社做了“公家人”,1971年县里的重点工程东风水库上马,赵凤梧在工地上当民兵连长,水库建成,再回供销社,担任阳坪乡供销社主任。退休之后,老赵赵凤梧在村里种了10年地,几年前去世。
赵凤梧4个子女,长子赵忠义在县法院上班,次子即赵亮香,三子赵忠平,还有一个闺女。
不愧是赵家洼开辟鸿蒙之家,赵凤梧自己供职供销社,是赵家洼过去仅有的“公家人”,子女对孩子们的教育也特别上心。赵凤梧的妹妹早年嫁到城里,两个外甥都是研究生,现在在内蒙古东胜教书。
赵亮香49岁,“没念出书来”,但他跟妻子都是勤快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29岁,女儿23岁。当时两个孩子在城里念书,“花销大”。
为什么把两个孩子都打发到城里租房念书?那时候,村里的小学已经撤并,读书需要到阳坪乡政府所在地。而从赵家洼到阳坪乡,十几里地对山里的孩子来说倒不算什么,但需要顺沟走到宋木沟,再过岚漪河,河对岸是赵二坡村,再顺公路向西走几里地才能到阳坪乡政府。
冬天结了冰还好说,孩子踏冰过河倒无危险,怕的是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岚漪河里长流水,开春冰消雪融,浪林翻滚,秋天雨季,山洪汇入,更像几十条巨蛛蛔蜒,吼声震天,洪峰过处,水流相撞,能激起一片黄色的雾霰。直到前些年,河上才铺设几道涵管,修了一座简易桥梁,但秋水时至,简易桥梁两边的引道会瞬间被席卷而去。
何况十多年前还没有桥,就是一架简易桥梁,时有时无,时好时坏,村人到乡政府到县城颇不方便。梁津一断,两岸就隔成两个世界,到阳坪乡读书,如何放心得下?
两口子商议,反正在阳坪读书是个不方便,到城里读书也是个不方便,与其在乡里担惊受怕,莫若让两个孩子到城里经见世面。于是在闺女9岁那一年,也就是2002年,他们把两个孩子都送到城里读书。儿子比闺女大6岁,给两个孩子赁了一间房住下,兄妹俩互相照应,每月房租50元整。两口子不忙的时候到城里照料一下,这就是他们搬家之始。
两个孩子一走,留下更多的“花费”需要两口子撑起来。两口子年过而立,正年富力强,种着40亩地,下苦耕耘,但一年所获,刨去各种“害债”(注:成本),“贵贱”攒不下个钱。孩子们一开学,夫妻俩就犯愁肠,向亲戚们“抓借”。
两口子光靠种地,连日子都“护不住”,务农之余,开始喂猪,一口气喂了三四头猪,到年根一算账,就是把粮食让猪吃了,再变成猪肉出售,还是个没有长余;然后又喂牛,喂牛没有技术,他们不知道牛也跟其它牲畜一样,长到一定周期,就是个费料,光投入,没产出,再一算账,又没有长余,还赔了。
庄户人家,种地不敢丢。万物土中生,土里有黄金。家有千万,长嘴的不算。赵家洼虽有养殖传统,但个体经营不懂成本控制,没有养殖技术,养猪不赚钱,养牛赔了些,还是老传统,养羊保险一些。当时,县里提倡养羊,一段时期,县政府把养殖绒山羊当作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突破口,搔绒可卖钱,肉品可交易,大力提倡,大力号召,要把岢岚县建成“骑在羊背上的”县份。那时候还没有退耕还林政策,赵香亮夫妇俩投资一万元,买回35只大母羊,当年就孳生下32只小羊羔,最后发展成140多只一群羊。
其时,村里加上他们家,一共9群羊,纵是赵家洼草坡大,林子密,一旦超过相应承载力,效益就大打折扣。赵亮香两口子仗着自己的羊品种好,有技术,一年羊绒和肉羊出栏,可以获得2万元纯收入。其他人家则不行,能赚上1万元就算好的了。
赵亮香妻子张改秀对陈福庆说,人哪,不怕有想法,就怕没办法。这也是沾了当年政策的光啊。
2008年,儿子在宁武县的煤矿找了一份开铲车的活,又在宁武找了个对象,开始谈婚论嫁。女方提出,绝不回村里去住。下文虽然没有注明,但明摆着人家是要新房子。村里倒是有老人盖下的房子,可人家不回去有什么办法,只能想着买房。乡政府所在地阳坪村倒是买房方便,但与其在乡里买,还不如干脆在城里买。
几年养羊还真是见效,有一些积蓄,花14万元在县城北道坡找下一个卖主。正房三间,面积不大。当年城里一户人家的宅基地也就这么大,不可能有再大的房子。农历十月办妥买房契税一应事宜,腊月就搬进去准备迎娶儿媳。
赵亮香从2008年算起来,正式离开村庄已经有不短的8年时光。若是从为儿女读书农闲时在城里赁屋居住,已经10多年了。放羊的“营生”放在一边,40亩地退耕的退耕,包租的包租,基本上不再作务。赵亮香在城里打工已经有一段时间,后来跟村里人到陕西省府谷县的焦化厂去打工,每一个月刨去常花销,可以拿回2000多元。
2014年精准扶贫,赵亮香因有就学子弟,因学致贫,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6月,女儿大学毕业,不再有上学花费,脱贫退出。
回想当年,赵亮香妻子张改秀很感慨,她说:我们那几年真是辛苦,人也勤快。秋天儿子开学,学费不凑手,就上山打马茹茹。打上半个月,路边有内蒙的商贩来收。就是靠打马茹茹,可以给儿子弄回一学期的学费,还买了一台缝纫机。
她说:村里评贫困户,我们进入是因为有学生娃娃,退出也没有怨言。但是,像村里那谁谁谁,他能有我们这辛苦?政策好啦,就可以躺在政策身上啦?
陈福庆就笑起来:你们是有志气人。
不知道他是说赵亮香首批带头出迁村庄进城,还是说他们靠勤劳把自己的日子搞得如此从容。
两者皆有。
赵亮香他们从村里搬出来之后,“看样学样”,村里年轻力壮的人家也开始陆陆续续搬进阳坪乡政府所在地,搬进县城,过起另外一种生活。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出迁的速度特别快,前后还没用了十年,村里人家的炊烟就稀了。
二、“一黑夜搬两次家”
一家有一家的不易。
许多村民搬到城里,搬到更远的地方。老刘刘福有扳着指头给陈福庆细数,有搬到神池的,有搬到五寨的,里面都是些曲曲折折沟沟坎坎,不能细说。
陈福庆找到搬到城里的张二縻,首先扑在眼前的,是一段曲折家史。
我老子是保德的。我爷爷是宁武的,这个是后爷爷。
我奶奶是保德康家滩人。爷爷本姓乔,保德东关人,河路汉,成年跑河路,给人扳船。
日本人打到保德,放火把保德城给烧了,爷爷也死了。没办法,我老子8岁上跟上我奶奶,一路逃荒,上的苛岚。
奶奶引了(注:领了)一个我父亲,还有一个叔叔,两个孩子。叔叔死在逃难路上。你看当年有多难。刚到岢岚,先在付家洼寻了个老汉。据说这个老汉也不错,结果老汉给八路军引路,叫日本人给打死了。奶奶又带上父亲跑到赵二坡,在赵二坡又寻了个老汉,结果是这个老汉养活不过,连个吃喝穿戴都供不上,又嫁到小涧道,这才跟上我这个后爷爷。一个小脚女人家,也真是命不好,自己拉扯一个孩子,自己把自己嫁了四次总算安稳下来。
我这个后爷爷也是逃荒下来的,一开始就是在中寨给人放羊。放了好多年羊,才在骆驼场后面小涧道那买下两孔土窑。入巷(农业合作社)以后,才从那老山沟里搬出来。先是对面的黄家岔,再过了二三年才又搬到大赵家洼。大赵家洼起先就赵存仁、赵润存他们那一家,其他户都在更远的沟里头住。在先,那些沟沟岔岔里都住着人,一条沟岔岔里住那么三四户人家。
我这个后爷爷叫张福成,我父亲给我这个后爷爷顶门子,改姓张,叫个张贵才。
我这一代,我大哥出去了,在阳泉矿上。我和两个弟弟都留在村里没出去。两个弟弟,一个六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没婚娶。老三张縻存,吃五保;老四张存先,在外头打工。两个都是贫困户。
村庄由“碎砖烂瓦”“弥砌”而成,其实,在赵家洼和赵家洼周边赵二坡、宋木沟、中寨、阳坪等村落,由“碎砖烂瓦”“弥砌”而成的家族也不在少数。像张二縻、赵亮香家族因战争、因灾荒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祖辈,拖儿带小,历尽坎坷,辗转奔逃,为当地男性收留,重新组合家庭,后辈为人“顶门立户”者甚多,也不是个案。这些行走在苦难而哀愁大地上的妇人,那时候只有一个目的:活下去。
这是村庄里公开的秘密,对这个秘密,村民都非常坦然,所谓“谁家锅底下没有一层黑”?大家谈起来,并没有忽略这些乡村女性祖辈对家族的贡献,而且刻意强调她们对家族繁衍之功,语气里是怀想,是敬重。
陈福庆在整理村民名录的时候,读到张二全的名字时,大家笑说,他叫张二縻!
“縻”何以读成“全”?
说起这老张家祖辈名姓流传,刘福有才给陈福庆数说清楚。
张二縻所说的这个后爷爷,名字叫做张福成,这是花名册上的名字,一直没有叫出去,大家只叫他张拦全喜,你说张拦全喜大家都知道,你若问张福成大家反而得想半天。张二縻的父亲叫张贵才,但大家都叫他张八八。一样,你说张八八大家都知道,叫张贵才大家反而也得想半天。
而张二縻呢,弟兄四个,还有三个姐妹,共7个孩子。老大叫张縻住,下来老二跟下老大叫,就叫张二“縻住”,老三改了,叫“縻存”,老四跟了老三叫,名“存先”。兄弟四人,三个名字里有个“縻”字,就是生下来怕不好养,要把孩子的命给“縻系”牢靠,向老天祈祷给挽留下来。跟村里孩子叫“拴住”“拦住”“拌住”是一个意思,希望孩子能躲过七灾八难,无病无灾活成人罢了。
縻,在乡音里读为去声,乡间老先生讲,这个“縻”字的正确写法应是“入”字下面一个“土”字,但电脑里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字,只能用“全”这个近似字来替代。不独是登记表如此,就是身份证也如此。
登记表也好,身份证也罢,都是错讹百出。不过,这不打紧,乡里乡亲,谁还不知道个谁?名字写错不打紧,“能叫音”(注:知道在称呼他)就行。
这一“縻”不得了,一鼓作气,“縻住”四男三女七个孩子。
陈福庆不禁感慨,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同万物一样,当一个名字跟自己的生命、身体叠加在一起,那种隆重的仪式感、庄重感会伴你终生。而一个人的名字在乡村社会的流传程度、流传方式则与一个人被乡村社会的接纳、认同程度,以及与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高度相关,而且,透过名字流传半径与流传方式,大致可以判断一个村民的生存境况。
老大縻住早年出走乡关,在阳泉矿务局做煤矿工人,剩下三个男丁则全“縻”在村里。老三、老四,一年过六旬,一接近六旬,都是单身。
留下来的张家三兄弟,都在赵家洼务农为生。1980年一分开地,张二縻就开始养羊,接着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生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1980年,张二縻才25岁,正是一身好“苦水”(注:有力气),人口多,地也多,张家父子兄弟一共种有190亩坡梁地,另外还分有20多亩“沟塌地”(注:平地),“紧着个刨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种地之出,养羊之入,不几年老张父子弟兄齐力下苦,老张家在赵家洼算不上最有钱的户,但绝对不差。
问题出在三个孩子都大了,都需要到城里念书。张二縻心思跟赵亮香一样,孩子在阳坪乡读也是个读,进县城读不也是个读?在阳坪乡你得赁房子,进县城不也是个赁房子?
所不同的是,张二縻进城当年,也即2001年就买了自己的房子,地点在县城的向阳街,三间半正房,加起来的居住面积80多平方米,还有一片院子,可以设栏养羊,总共花了5.58万元。
张二縻勤快,肯下苦,养羊早不假,但是2001年,一只羊也就百十块钱,饶是你本事大,5万多块钱放在赵家洼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哪来的钱?
借的。
“不借你不行。硬攒怎么攒得下?娃娃们念书,买种子化肥,雇牛雇人工,都要用钱。”张二縻告诉陈福庆。
东借西借,先贷了款,然后在亲戚中间借了一圈,加上自己平常的积蓄,算是凑够了房款,花些钱稍事收拾就搬了进去。直到2007年,张二縻把羊全部卖掉,才最终还上所有欠款。
花费这么大的气力买房,为甚?是一件“泼烦”事伤透他的心,“捉主意”(注:下决心)借钱买房子。
倒是老张的媳妇快人快语。
娃娃们到城里念书,赁了处房子,一黑夜搬了两回家。
为甚?
开始租的那户是个养猪的,快别提!当时着急火燎搬进去,就想的是有个黑夜睡觉地方。等真睡了,睡不下来,一屋子都是苍蝇,又臭气熏天,这还能念成个书?当天抱上铺盖又去寻第二家。
第二家倒是不吵也不臭,就是黑灯瞎火,半天灶火也烧不燃,为给娃娃们做个饭,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泼烦。要是明儿起来,再不满意,还得搬!
黑夜里就和老汉商量,要不买房吧。那会儿买房是不贵,就这房子,房东要6万。当时别说6万,手头有个6000,也了不得。好不容易有点钱,都拿去买羊了。6000都没有,我们思谋来思谋去,还是要买。姓娃念书是一方面,将来娶媳妇,迟早也是个买。
当时赵家洼在县城里买房的不多,但别的村有人往城里搬了,就是图个上学方便。就这,去信用社贷了3万,又找亲友们凑了3万,总算是住进了自己的院子。
住也主要娃娃们住进来,我和老汉又在村里养了几年羊。不养羊不行,塌下的饥荒谁来帮咱?
进城十多年,也就是个打工,见甚做甚。我这会儿也是给人做做饭,挣两个日常零用。这几天月饼厂人手多,我去给人做饭,一个月给2700元。月饼厂一年也就忙这两个月。这还得是生意好,碰到不好的时候,也就忙个二十来天。
离开村庄,走进城市,日子肯定比在村里方便得多,即便打工也有个去处,但生活压力并不见得就轻多少。60岁那一年,老张得了病,头晕,站不稳,一查,是轻度脑梗。再一査,血压又高,还有冠心病。杂病缠身,不能“动弹”,只能找些轻活来做,闲了就帮着看看孙子,再闲了,上街去和别人下盘棋。颐养天年说不上,但一副进入晚境的样子,“女子们缺不下咱一口吃”。
当初为了孩子读书才搬到城里,最终三个孩子还是出息,究竟比待在村庄里眼界要宽,当初“一夜搬两次家”,终有回报。
老大海龙,34岁,已然成婚,生有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学了装潢手艺,岢岚有“营生”(注:工程),神池、五寨周边县也去,日子过得还好。
老二海燕,31岁,已经出嫁,婆家也是平民人家。
老三海明,30岁,读罢高中,又读技校,现在保德县一家煤矿做合同工,一签6年,后续2年,交罢五险一金,一月可得3000元工资。
所以老张对自己当初“捉主意”进城特别满意。
出来了还是好,我们这个年纪,净毛病,想看个病买点药,都不方便。孩子们一年四季都在外头,甚不得靠自己?村里头想买块豆腐吃,你还得坐半天车,车钱够买十斤豆腐了。
老婆还说再过二年回村里种种菜,我说回去干甚?再过些年真的老了,在村里也种不了地了。别人都往城里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还回去?老了埋都别把我埋回去,要不子孙后代给我点个纸还费半天工夫。你在城里头,一年米面,就是放开肚皮吃,又能吃几个?我的钱净吃了药了。
由乡村出走,老张是一代人,他们的儿子是第二代人,再好的村子也架不住两代人出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经过两次大的人口变动。第一次,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占到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一,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青壮农民离开土地涌入乡镇企业打工,是所谓“离土不离乡”再创业,非农性收入成为一部分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二次,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城镇化步伐加快,青壮农民背井离乡,“民工潮”席卷大江南北,是所谓“离土又离乡”再创业,非农性收入成为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乡村农业生产分工日细,春耕、夏锄、秋收,覆膜、种子、灌溉,这一系列农事操作日益专业化,生产过程不再像传统农业那样,“农民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以弥补资本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而出走乡关闯天下,尽管有像老张“一夜搬两次家”这样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有农民工讨薪难,因户口限制子女就学难等等诸多问题,但非农性劳作的固定或者定额工资、现金收入方式,远比从事农业生产来得多,来得快,来得实惠。
两厢合谋,农民进城,谋生、创业、拓展,逐渐影响到了乡村伦理和乡村思维。2008年,赵亮香的儿子要结婚,不得不买房。给儿子娶媳妇,人家媳妇就不愿意回村里,必须在城里安家。况且,年轻人株守家园,不动到外头打工的心思,谁看得起?
反过头来讲,就像赵家洼九十多年前建村立舍一样,一群为谋生、为生存奔走的苦人儿来到这里,然后安营扎寨,然后繁衍人口,然后,又是新一轮的出走开始。
所谓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所谓故乡,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一段流动着的历史。
今天,你既不可以想象,一个人口不流动的村庄,会不会真的就是梦幻般的世外桃源;也不可以想象,一个人口不流动的村庄,村民的后代会得到稳稳当当的成长、教育、磨炼、创业的机会,可以放心大胆地“至死不离寸地”安放一生。
所以,大儿子海龙结婚的时候,老张“操了个心”,到民政局办证,没有按规定把儿媳妇的户口办回到赵家洼,而是留在她原籍城关镇。现在,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是城镇户口,只有儿子一个人的户口还落在赵家洼。
老张为这个谋划也很满意,所谓“鸡蛋不往一个篮子里放”,万一有什么世事变化,将来也好应付。
三、另一种出走
其实,细推究起来,除了“分开地”回到原籍的老一茬村民,除了投亲靠友“走西口”的那几户,因孩子上学搬迁的远不是赵家洼村人口格局松动、人口流失的开始。
年轻人的出走才是真正的开始。邸建华大概是第一个从赵家洼走出去的年轻人。
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年轻,1965年生人,年过半百,进入人生的深秋季节。但在1988年他离开村庄外出打工时,也不过24岁。
邸姓在岢岚并不多,在赵家洼独此一户。但邸家的后代很出息,大家都津津乐道。说起祖先,邸家跟其他户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沟一岔的穷人家”。
邸建华说:
我们邸家是从宁武迁过来的,据说老家叫个宁化,具体哪个村,记不清了。那地方邸姓是大姓。
爷爷叫个甚,我也不清楚,就知道是从他那一辈搬过来的。为甚搬过来?可能是那会儿穷得过不了,想着搬个地方,能讨口吃的。
起先也不是在赵家洼,先是到了马家河,现在的西豹峪乡。在马家河住了几年,老遭灾,住不成。又搬到梁家会,就是阳蒿塔附近,离城关不远。在梁家会也是种地。当年我爷爷就在岚漪河边搂谷子,看见日本人过兵,人蹲下去了,锄头还立着。日本人还以为他是八路军的探子,就一枪把我爷爷打死了。没办法,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我叔叔,还有两个姑姑,又到赵家洼寻了户人家。我父亲就生养了我一个。
我父亲叫邸满屯,二爹(注:二叔)叫个邸保大,还有两个姑姑。
二爹生有六个孩子,四女两男,我哥邸建忠是老二,上头有一个姐姐,嫁到偏关县。我哥1961年生,念了个忻州农技校,后来工作分配到县公安局,当刑警。老三又是一个女子,先是嫁到偏关县,后又搬到包头。老四邸建平,现在定居在咱县的三井镇。老五是女子,老六也是。一个嫁到南山村,一个嫁到城关。
我们这一家子,除了我,都早早就从赵家洼出来了。
我哥他的娃娃们净念书,两个女儿都出息,大女儿研究生毕业,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207研究所;小女儿在成都念的大学,又到天津念的研究生,南开大学金融系,今年毕业又考上工商银行总行。在赵家洼,子弟们出息,我哥算是拔了头筹。
但是我不行。搞集体化时红火,白天干活,晚上开会,那时候我小,一个人在家不敢待,晚上跟着父亲去开会。5岁上,1969年,母亲去世。10岁上,1974年,父亲又去世。从小父母双亡,可怜的。那时候我家住在骆驼场,10岁的娃娃没法生活,二爹收留,把我接到大赵家洼,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1979年大些了,再回到骆驼场。那时候14岁,回去连饭也不会做。生产队还没解散,地也没分开,就凑合着在队上动弹。
那时候的骆驼场,在整个赵家洼大队是个小队,户少人也少。总共五十来口人,具体有多少户,记不清了,大概十四五户。
从上往下我给你数。
张拴虎家,一户,他老子叫个张好存,我没见过。他们弟兄三四个。
李辛喜家,三个小子李爱渊、李爱德、李爱明,两个女子李爱冰、李爱玉,因为这地方穷,小子们一直娶不了媳妇,又回了保德。
张根存家,一个小子张来虎,这会儿户不知道在哪,反正在阳蒿塔住。
栗二仁家,他要了个老婆也没生养,老婆先是和他吵架跌死了,剩下他一口人,现在也死了。
吕有成家,一个小子叫吕来牛。吕有成他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会挑针,开方子,抓些药,小时候还给我看过病。
再下来是李渊家,就一个闺女,娉(嫁)到(五寨县)三岔那了。
范老虎家,一个小子范来拴,后来搬到宋木沟。
李明举家,他是骆驼场的老住户,就一个小子李阴虎。李阴虎两个儿子一个女子,后来他死了,老婆改嫁,户都搬走了。
再就是我家。
高美珠家,就一个儿,在骆驼场住了多年。
贾高枝家,他是从兴县来的,他老子贾补存先来,还有他兄弟贾近枝,他们这一大家,就有十来口人,单干后,他老子和他兄弟又回兴县了。
李爱渊家,他家后来搬到哪,我也不清楚,反正户不在赵家洼了。
范来拴家,他叫高美珠舅舅,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甚。
霍明则家,一个小子叫霍校堂。霍明则死了,他老婆带着儿子进了城。
康补利家,他父亲叫个康江撬。
又过了两年,才开始单干。1982年正式分地,各忙各的。头一次分了十几亩,后来我出门打工回来,又给重分了一次。我在骆驼场种的有二十多亩地。
出门打工那一年,我24了。为甚?种了几年地,不会种,倒是把种子种下去了,甚也收不回来。1988年,有个亲戚介绍,叫我到北京,给一家铸造厂干活。那时候打工挣不多,一个月就是个八九十块钱。打了五年工,也没存下钱。
1993年,正好我二爹家娃娃们净出外面了,分得些地,没人给他锄刨。他家差劳力,就叫我回来。倒是把怎么种地学会了,就是不挣钱,种了几年地,还是甚也没挣下。
到2005年,村里有人在府谷焦化厂打工,邀我过去。刚去的时候,一个月工资1200元。在那干了四五年,要是正式上下班,最好时候,一个月能挣个2000多。
邸建华真是一个苦命人,少年失怙无依,由二叔收留,但二叔有六个孩子,家庭负担也相当之重,邸建华14岁开始独立生活,独立谋生。
陈福庆望着眼前这个高个子男人,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把自己还收拾得干干净净,心里不由敬重。但是,邸建华早年父母双亡,没念过几天书,身无长技。24岁外出打工,29岁归乡才开始学习务农,到40岁年纪又外出打工,倒是光杆一人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年他外出,并不像许多正常环境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外出打工者那样,心怀壮志,为的是闯一片天地出来,谋划另一种生存。他出走,“不会种地”,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活出个人样子来。
但直到五十出头,并没有走出个样样来,还是一个“没结果”,依然一个人过活。2014年“精准扶贫”开始,邸建华理所当然成为贫困户。
晋北地方,把这种无奈的出走,称为“刮野鬼”。一个人无业无家,如野鬼,像孤魂,居无定所,随风游走。严格地讲,当年来赵家洼落脚的老一辈人,除了躲避战乱而游走至此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曾有过贫苦无依的“刮野鬼”经历?
晋西北地方流传有民歌:
转圈圈旋风漫滩滩水,
什么人留下个刮野鬼。
三九天沙鸡绕天飞,
什么人逼得咱们刮野鬼。
人家红火咱作难,
好比孤雁落沙滩。
一对对白鹅凫水水,
光棍汉到处刮野鬼。
阳婆一落火烧云,
刮野鬼的哥哥还是两腿风。
阳婆一落火烧山,
刮野鬼的哥哥到处串。
大雁回家头朝南,
刮野鬼的哥哥活得好心惨。
跑前山来溜后套,
走遍天下吃不饱。
白天打短走四方,
黑夜里熬油补裤裆。
有老婆的哥哥早睡觉,
没老婆的哥哥满村绕。
前半夜没风前半夜暖,
后半夜冷风心上钻。
没笼头的马儿没桨的船,
刮野鬼的哥哥没收拦。
墙头上跑马掉不过头,
刮野鬼的亲亲难收留。
“刮野鬼”游走四方,其苦如此。难道几辈子人下来,竟然没有多少改变?
马无笼头船无桨,既无技能,又无知识,种地也勉勉强强,邸建华可能只是他那一茬农民的一个特例。
康补利,1968年生,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打工,电话探访当日,他正在一个“小不点烧烤城”给人配菜、打扫卫生。1995年就出去了,先后在呼和浩特、临河、化子县,2012年才落脚在烧烤摊。起初的工资为1000元,2015年至今是2000元多一点。
50岁的张存先,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务工,走包头,绕石拐(包头市石拐区),最后在包头一家民营铁厂务工,有一回,铁水包倾覆,至烧伤为二级残疾。补偿也没拿到多少,只身回到故乡养伤,至今单身。
“刮野鬼”谋生不易,主要不易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上。邸建华如此,康补利如此,张存先更如此。
这仅仅是因为邸建华他们个人素质导致这样的结果?赵家洼人到现在还念叨,不管教学水平如何,村里总算还有过学校,有过弦歌不辍的日子。但是,究其竟,直到今天,中国农村的教育仍然是“升学”教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毫无特色可言。邸建华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是这样,像邸建华那一茬受过初、高中教育最后高考落榜的回乡青年又怎么样呢?
过去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所谓“四大无用”,分别是“锁子铁,断关针,下乡干部中学生”。寒窗十年,最后回来是废锁之铁,断关之针,毫无用处。或者说,传统农耕,操着从汉朝就使用的犁,赶着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使用的牛,你学下一肚子数理化史地政,那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是什么?
近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方兴未艾,国家投入巨大,许多乡村青年受惠多多。设若当年职业教育能够恵及山村农舍,邸建华外出打工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
学科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本质的区别,上世纪二十年代,阎锡山聘请黄炎培先生入晋设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遍地开花,从高职到中职教育体系完备,效果非常明显。阎锡山曾说,学科教育是甚?就是学甚做甚;职业教育是甚?就是做甚学甚。
绕口令般一番话,委实让人深思。
话说远了。
2011年,邸建华再次回乡,是因为要照顾他的叔伯哥哥。当年父母双亡,二叔收留,虽是侄子,却视同己出,这份恩情邸建华始终未敢忘却。哥哥邸建忠出了一场意外,脑子受伤致偏瘫,邸建华把照顾兄长这副担子担了起来。兄长的孩子们都在外头,嫂子还要上班.思来想去,也只有他一个“闲人”。
侄儿侄女也孝顺,虽然不能说是工资,一月给他1000元,全职做起男“保姆”照顾兄长。现在,他住在城里,但村庄的模样还深深刻在记忆里。
那个养育自己又赋予自己太多磨难的村庄啊!
到2015年,骆驼场就剩下3户,贾高枝家,康补利,还有我。多年在外打工,常年不住人,不烧火,不通风,我那土窑窑潮得,去年也塌了。我在城里照顾我哥,一般走不开,不过刁空也能走个一两天。
大赵家洼集体化时有27户,一百二三十口人,还有学校。小赵家洼那时候人最多,有43户,有一百五六十口人。搞精准扶贫时,大赵家洼也就剩下5户,田贵林、田贵存、张二縻、李虎仁、李云虎。
陆陆续续,人都走了。
不说城乡二元分治,不说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壁垒,改革这些年,外出“闯天下”“闯市场”的农民工进城,尽管有不确定性,但在某种程度上,“闯天下”“闯市场”本身就是进城农民和刚性的体制达成的非制度化机制,进而不同程度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农民工外出,不再是简单的“刮野鬼”,为“刨闹一口吃喝”。包括赵家洼在内,中国农村青壮年出走乡关,已经跟先辈四处游走“刮野鬼”有了本质的区别。
四、第四代
不费工夫,就找到马龙飞。
马龙飞在岢岚县振兴路开了一间小饭店,跟妻子两个人经营。两人既下厨,又记账,又是服务员,正经夫妻店。
马龙飞是老支书马忠贤的孙儿,1989年生人,也属蛇,小邸建华整整两轮,又一茬年轻人。小伙子年将而立,脸上还脱不了孩子的稚气,只是个憨笑。
马龙飞,祖父马忠贤,父亲马贵明。马贵明系马忠贤长子,在阳坪乡政府工作。马龙飞兄弟三人,大哥马飞,1983年生人,属猪;二哥马鹏飞,1985年生人,属牛。马龙飞是家里的老小。
说起家里弟兄三个,他呵呵笑:我们弟兄三个,都没待在村里,都“跑”了。大哥念书还行,山西财经大学毕业,现在在内蒙鄂尔多斯跟朋友搞一个旅游公司。二哥和我,都“不爱念书”,在阳坪读到初中——也没有念完就不念了。二哥在县里的搅拌站给人打工,开罐车。我呢——他摊了摊手——就干这个。
“光不溜”兄弟三人,没有一个务过农。尽管读书假期,帮助爹妈在地里干过一些活,能做什么做什么,那也不能算正经下过地。大哥读完书,只身前往内蒙古扑腾自己的事业;二哥2006年结婚,婚后两口子在村里没待多长时间就出去打工;2007年,马龙飞18岁,二哥前脚走,他后脚也跨过岚漪河,直奔城市而去。
十八岁出门远行,外面每一条蜿蜒的柏油马路通向的远方,引领着去任何地方,都有好多好多机会。诱惑与预想是一方面,其实马龙飞“不爱念书”的那些日子,看着每年叽叽喳喳呢呢喃喃的燕子飞起复落下,早就认定,干什么都比一辈子种地强。他拿定主意,说什么也不能回村种地。
小伙子务实,不想种地,顶多算心野,说不上胸怀大志,他想着在外边学门手艺,“做甚营生还不如个种地”?身怀薄技,总能养人。现在的社会又比过去好,怎么也不愁谋口饭吃。
2007年,马龙飞先到太原,直接找了家饭店打工,做服务生,再后来下厨学艺。在太原做一段学徒,后来又跟朋友跑到了长治市,仍然是在饭店学厨,并没有专门进烹饪学校,一两年下来,厨艺精进,可以独立掌厨。
太原半年,长治两年,独立掌厨之后,又到了保德县。保德县扼晋陕通道,交通繁忙,仅供过往司机餐饮就是一大产业,饭店甚多。马龙飞来到保德在饭店里打工,月薪3000元。
马龙飞祖籍保德县,他来保德,并不是因为祖籍在这里。爷爷那一辈人,与故乡亲戚尚有往来,小时候,还见过故乡过来的爷爷那一辈姑舅、两姨亲戚。后来,爷爷老了,故乡的消息也就稀了。到他这一辈,干脆什么也不知道。
马家来赵家洼安家,到他这一辈,是第四代人。
第四代人回故乡,目的与心情跟老一辈人完全是两回事。
说是两回事,心底里究竟还有一种念想在。意外的收获是在保德县的饭店打工,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媳妇当然是保德人,家住保德县东关镇,“也是个不爱念书的”,初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两个人眉对眉,眼对眼,很快就确定关系。
2012年,两个人结伴回乡,在村里办了婚事,转年又回保德继续打工。
婚礼所费,全是这些年外出打工积蓄,彩礼66000元。
回岢岚,是因为孩子出生。两个人商量,回岢岚,一方面有大人可以帮着看孩子,可以安定下来;另一方面,本乡田地,同学也多,遇事有个照料。
2014年,两人带孩子从保德县回到苛岚县。刚回来,其实等于从头再来过,筹划了足足一年,“在家里坐了一年”。2015年,总算是筹了一些钱,在县城振兴路租了一个门面,夫妻店就这样开张了。
回乡定居,开夫妻店经营,开支不小。
门面房房租,一年10000元。
县城房租,50平方米单元楼房,一年4000元。
女儿上幼儿园学费,一年1600元。
女儿兴趣班学舞蹈,一年700元。
这是数得上来的大宗开支,共计16300元。加上日常开支,一年下来,直接生活成本为20000元。说到饭店经营,马龙飞倒也实在,一一数来。
哪里存得下钱?开个饭店,挣不挣吧,就是守着老婆娃娃,一家人能有个照应。
一天流水也寡搭(注:不怎么样),碰上人多,五百六百也有,遇见人少,一天二百三百也是常事。咱这地方,小饭店,也就是炒个家常菜。来的人顶多就是吃碗炒面,喝瓶啤酒。小饭店,人多了也不往这来,来了也坐不下。
刚开始,没生意,还卖过一段时间早点。卖了一段时间,人受不了,早上四点人就得起来,一直忙到晚上十点,还得洗碗收拾,熬不行。卖了一个多月,受不住,快算了哇。现在就是上午九点钟开始准备,歇不下来,一直得忙到晚上十点。
一年流水就是个小十万。刨掉成本,煤电水气房租,还有家里开支,吃喝穿戴,还有行礼支应门户,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能存个万数块,了不得了。我要是出门打工,一个月挣上三四千,老婆娃娃在家里头也得花,一年下来,也就是攒万数块,这还照应不上家里。人家学得好的,做厨子一个月挣七八千上万的也有,精致的菜咱也不会炒。慢慢往下糊吧。去村里做事宴,倒也好办,要有人叫,咱也可以给应付。
结了婚了,出去也出去不成,没个好做的,娃娃也这么大了,就在家里吧。生意好了,多挣两个,没人来,也能够个生活。
改革开放几十年,生活噼里啪啦发生过些什么,远在赵家洼老一茬人的视野和经验之外。80后、90后,在“二进制”信息时代长大的这一茬孩子,尽管“不爱念书”,他们接触到的、感受到的、体会到的现实,他们的父亲、祖爷肯定是不知道的,也肯定与他们的生活并不相干,但显然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另外一个空间,可选择的机会比祖辈更多。
马龙飞这就说起他们那一茬人——大他三四岁、小他三岁的那一茬人,当初同年仿纪一起“耍大”,一起成长,一起结伴跨过岚漪河,再走四五里地到阳平中学读书,男男女女有十几个人。
看着马龙飞年轻的面庞,陈福庆感到,当初这些孩子的笑声,呼朋引伴的呼喊声,同田野里的布谷鸟叫声和在一起,仍然清晰地包裹在早晨漫过岚漪河谷的薄雾里。
马龙飞笑着,说起他们那茬人。
曹进军,跟我一般大,他父亲就是曹六仁大爷。他有时候在北京,有时候在石家庄,学的是电焊。
曹晓军,曹进军的弟弟。他学的做地暖,也是到处跑。
马瑞,是我叔伯弟弟,我二叔的儿子,跟我二叔在府谷打工。还是他先去,现在在一家焦化厂里做车间主任,然后又把我二叔带了过去。
还有杨家叔伯弟兄两个。大的杨云飞,在太原打工,专门给酒店配货,做得还可以;小的杨国栋,跟人学修车,就在岢岚县城里打工。
还有田保云,他父亲是田贵林。他给人开车,司机。
田继云,也跟我差不多,小时候可不容易,他还没断奶,娘就不声不响跑了,姐弟两个都小,由父亲田贵存带大。他现在在宁武、神池一带搞装潢。
马龙飞说话,始终笑着:我们这一茬在村里一起长大的,都不爱念书,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修车的,搞电焊的,给人开车的,搞装潢的,做甚的也有。
谁也谈不上混得好,也谈不上差,都平平常常。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