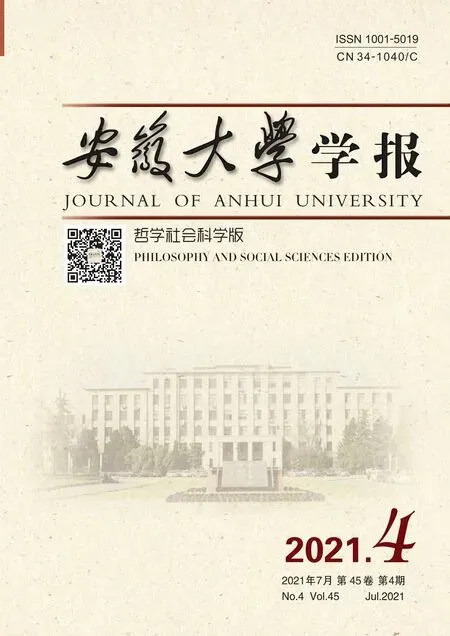地方冲突与国家治理:1935年黄河水灾与苏鲁治水纠纷研究
李发根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泰山之西,“渠脉纵横,湖泽垒垒如贯珠,天然一水利行政区域也,不幸此天然之区域,以人工强为区划,分属于苏鲁两省。于是此区域中之水利,亦遂苏鲁各自为政,不相顾恤。鲁人有邻壑之谋,苏人怀曲防之意”。这一论述点出了苏鲁水利冲突的焦点与缘由。但两省的水利纠纷是长时段形塑的结果。南宋黄河夺淮以降,很长一段时期,并未沿今之故道入淮,而是分成数股,南北分流。明中后期以下,主要受运河漕运影响,黄河才基本上围绕今之废黄河入淮。可以说,明中期以前淮北水灾尚不严重,故而苏鲁水事纠纷较少。明中期后,基于维持运道考量,国家治水实践中将全部黄水逼向徐、邳地区,导致淮北水灾频仍,地区间冲突加剧。鉴于大运河穿苏鲁而过,国家对沿线治理较为重视,两省水事纠纷尚轻,冲突主要集中于苏皖。1855年黄河北徙,经山东入海,此段河身逐渐淤垫,水灾频发。起初因地形等因素,水患多集中于中下段。随着“自强”逻辑的渗透,国家和地方的经世方略开始转向其他地区,鲁西南黄灾日重。进入20世纪以后,至1938年花园口决堤,此段水灾超过了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以及山东中下游段,并时常危及苏北,致使两省冲突日重。故而,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张锡昌(笔名张西超)认为,“因为晚近的水利建设是局部的,没有整个计划的”,导致苏鲁间时常发生冲突。同时期还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苏鲁两省水利纠纷迭起。
1935年7月,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引发一场可能是1855年黄河北徙以降最严重的水灾,“灾情之重,空前未有”。鲁西南近20县被灾,加上其他受灾县份,山东共计40余县受灾。由于大溜南奔,直入运道,经苏鲁交界之微山湖入中运河,运河无法容纳,进而波及苏北10余县。两省围绕水灾治理,发生了纠纷和冲突。此时的山东由“不买国民党账”并“独占”鲁省的韩复榘掌控,江苏则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省份,事关政权合法性构建的导淮工程、维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淮北盐场等主要集中于苏北,进一步而言,南泛黄水进入运河将与淮河合流经长江入海,亦可能危及国民政府政治、经济中心。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与双方看似皆义正词严的陈述中,冲突背后的真相何在?中央政府如何介入、处理纠纷?治理成效怎样?此次纠纷的处理为考察“十年建设”时期国民政府国家治理逻辑、实践与能力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学界对此次水灾早有关注,但就目下所及,主要集中于灾害的影响与救治以及笼统地点出了苏鲁因之而出现的纷争。本文基于大量一手档案材料梳理此次纠纷的缘由,辨析双方陈词中的真实与虚构,并考察中央政府的介入、成效与地方应对,以管窥国民政府国家治理的逻辑和能力。
一、纠纷缘起与事件聚焦
1935年7月11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正在四川着手“经营西南”的蒋介石发去急电:鄄城黄河南岸董庄一带堤坝满溢,水势甚猛,持续暴涨,高度越过新加堤顶,虽经组织民夫拼命抢护,却无甚效果。或许因为此段黄河自民国以来决溢频仍,河防人员与韩没有预想到接下来的水势走向,所以只是将这一信息告知蒋。蒋同样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收到电报两日后才象征性地批复:“各处水势虽猛,仍应尽全力抢护。”但是,韩很快就意识到此次黄河漫溢极有可能酿成巨灾。11日晚些时候,在给蒋的急电中,他甚至将水灾的可能走势与1933年的黄河大水灾相提并论,言及决口“虽经督饬拼命抢护,而堤防一溃,势难遽行堵塞”,并“以省库支绌”,请蒋“迅饬筹拨款项,施放急赈,以活民命”。13日,韩急电蒋续报决口及抢护情形,谈到决口渐次冲刷,口门宽已达200余丈,水向东南泛滥。虽经各县县长督率民夫筑坝束水,但因水势浩大,终归失败。只有传谕各保村庄并饬多备船只、木筏营救灾民。14日,与蒋关系密切、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在给蒋的密电中也报告了类似情形。
短短几日,形势可谓急转直下,15日韩复榘在给蒋介石的急电中除了重申此次黄灾使“连年被灾,民生困苦已达极点”的鲁西南进一步陷入绝境外,强调如果不能迅速堵塞决口,口门愈冲愈大,一旦全河夺运入淮演成改道现象,“目前桑田立成沧海,则前途隐患更有不堪设想”。同时再次申明山东省库入不敷出,恳请中央迅速筹措工款,派员堵筑。由于1933年设立了直隶于国民政府的流域性专业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下文简称“黄委会”),1934年国民政府以全国经济委员会(下文简称“经委会”)为“全国水利总机关”,故而蒋在批复韩的急电中指出:“已转电行政院经委会、黄委会妥速办理矣。”由于黄河决口将直下苏北的信息已见诸报端,因此15日导淮委员会(下文简称“淮委会”)给时为督察冀鲁豫三省黄河防水事宜、黄委会副委员长的孔祥榕等去电,“希迅速抢堵免害及于淮域”。但得到的回复却是:防汛时期防堵照章应由各省河务局负全责,已严饬山东河务局速备料物相机抢堵及保固鄄城境的江苏坝,以防水势再涨时全河南移。同时淮委会亦给经委会去电,请其负责主持设法抢堵决口,以免黄河夺流入运,改道徐淮入海,鲁西南、苏北尽成泽国,导淮工程亦将全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但经委会并无实质举措,不过是要求山东省政府和黄委会“从速督饬设法抢堵负责挽救”,江苏省政府“饬属切实戒备以免灾情扩大”。
前文提及,这一时期黄河为灾主要集中于鲁西南段。但山东每年用于治河的经费极为有限,以1935年言,全省修防经费共30万元,“所有春修、抢险、防汛各费,皆由该款内开支”。正常年份尚难勉强维持,遑论大灾之年。因此,山东也更多寄望于中央政府。尤其是此次决口,直接危及苏北的导淮、淮盐等事关国民政府“大局”的事务。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迟迟未能采取有效举措,水灾愈演愈烈,围绕历史时期苏鲁水事纠纷焦点的微山湖,两省冲突再起。
7月27日,韩复榘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将此次苏鲁纠纷提上台面。电文写道:迭据灾区各县民众报告,洙水、赵王各河先后决口,究其原因,实由苏省境内筑堤修闸迎截黄水,使下游不能宣泄,南阳湖水倒漫所致。查所陈各节,确系实情,倘不急图挽救,灾祸之来势将愈演愈烈。鲁西南民气易动,深恐别生枝节。蒋要求两省“商洽补救”。面对韩的控诉,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迅速做出回应,30日在给蒋的急电中称,“阅之不胜骇异”,实乃“市虎杯蛇,远道传闻失实”。随即陈述“实情”,谈到苏省仅就“微山湖西岸原有堤坝加高培厚,仍保留蔺家坝口门以资宣泄”。此堤与山东南阳湖和鱼台堤一样皆为防水西泛,并非正面抑遏黄流。此外,南泛黄水由于漫溢,水行较缓,“微湖容量并未十分饱满,微湖西堤今犹未发挥屏蔽铜沛作用”。因此鲁省的指控“实离事实太远”,并电请韩复榘派员来苏实地踏勘,则误会不难立解。
随着灾害的扩大,山东方面的抗争依旧延续。8月1日,韩复榘致电行政院:“蔺家坝为运河泄水咽喉,闻江苏省政府有堵筑之议,请迅电制止。”同时期,“山东滕县微湖沿岸居民代表张宗淕”给国民政府去电写道:“今黄河开口,水入微湖往南而下,民等时以泛滥为忧,正在日夜惊惶。讵意苏省人民于鱼台县至张孤山筑堤一道,又由蔺家坝重筑十五里之堤,黄水遂而倒流……泛滥平地,沿湖一带数十万生灵俱陷于有死无生之状态……若将蔺家坝扒开,微湖之水顺流而入淮河,鲁南、苏北世世可无水患。”因此,“请求迅饬苏北筑堤当局于所筑之堤立时破毁,再饬苏鲁行政水利机关将蔺家坝扒开”。济宁等10县“民众代表”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述及江苏筑坝截流致使鲁西南被灾,强调灾民“群情愤慨,咸欲相率南下,誓死堑平苏堤,借谋一线生机。代表等以一息奄奄之灾黎实不堪再供此巨大之牺牲,更恐惹起误会,结果不堪设想”。
两省纠纷很快演变为直接冲突。据江苏方面后来的报告称,8月29日,苏北邳县中运河胜阳山隔堤被鲁人挖掘。“河水出槽,益以风雨侵袭,于是中运东堤在邳县之大榆树,西堤在宿迁之苏家房,及窑弯、沂河南岸,先后漫决,运西与黄墩湖,运东与羽头、骆马诸湖,水连一片。”9月初邳县看守所呈省高等法院的电文,提及因“现县城西南不老河及中运河两岸堤埝溃决”可能出现困境,也从侧面证实此次黄河决口至此才真正波及苏北。9月3日,陈果夫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苏省邳县与鲁峄连界,近以鲁省兵民越境掘堤掳去此间监工及民众多人,报纸迭有登载,已饬地方官吏严束自己,听候和平处理。”随后,蒋在给韩复榘的电文中希望苏鲁“切实合作防堵并解释民间误会,俾免纠纷而速弭巨灾为要”。韩也承认,山东方面确实有掘堤之举,但将原因归咎于“苏省在运河建拦河坝并于坝间河内抛麻袋石料阻水宣泄”,强调“被灾人民迫于自救,聚众扒掘……峄县县长事前未能阻止,并经过严予申饬”。同时说明,现峄邳两县纠纷已“和平了结”。
至此,在官方文本中,苏鲁两省围绕此次黄河决口而产生的纷争,基本情况已经呈现,但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解释却大相径庭。
二、事件真相的复原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文本的生成与时间、空间、权力等相互纠缠。马克思、恩格斯则说得更直接:“生活决定意识。”同一事件解释的差异性,往往是不同主体各自利益需求的呈现。在地区性的水事纠纷中,各方常常自恃“正确”,致使事件真相晦暗不明。此次苏鲁纠纷,如果仅就两方给中央政府的电文及公开陈词来看,皆义正词严。孰是孰非?其中原委一时难以辨别。但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爬发现,苏鲁两省通常是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来解释“事件”。
赵王、洙水二河,受黄河北徙经山东入海影响,“年久失修,淤塞太甚”,像赵王河一段甚至“完全淤成沙滩”。洙水河流经五县,菏泽、嘉祥一带的水均由此宣泄入南阳湖,“河槽平时干涸,雨季则水势汹涌”。虽经1931—1932年浚治,但实际效果并非如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所鼓吹的那样,“有形收获,显然可见。至各地水道纠纷,彻底解决,人民辑睦,相安无事,其无形之益,更不可以数量计”。1933年黄河水灾虽然对南阳湖的波及较轻,可洙水河还是决了口,周边“一片汪洋”。而赵王河更是因经费等问题迟迟未能疏浚。全面抗战时期日本方面的调查表明,赵王河“其间河床断续;而低地无河床,雨季中,则低地尽属水流,殆无堤防也”,洙水河“年年于夏秋泛滥”。就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河虽经政府组织挖修,“终未彻底,未能起到应有的排水作用,是以每逢较大雨水,即造成严重的灾害”。此外,当时的调查表明,晚清运河漕运废弃以后,济宁一带“水利失修,湖河淤垫”,南阳湖相当一部分被“填为耕地”,此处又是鲁西南数十条河流汇聚之处,与独山湖交界处极窄且有高地,排水不畅,因此,在雨季时大水常倒灌沿湖诸河。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央社1935年7月20日济南电,黄河决口时期,山东雨季业已来临,济宁、巨野、郓城等地大雨,皆注入南阳湖,使其无法容纳,形成倒灌,导致赵王河溃决。概言之,赵王、洙水两河决口为灾有着很深的历史和自然等原因。
1935年7月15日,淮委会技士对济宁等处调查后,在致总工程师须恺的密电中写道:“南运连日暴涨,由天雨及汶水下泄所致。”另据济宁县报告:“黄水已侵入该县境,赵王、洙水两河距南阳湖仅四十里,县长建设科长均出巡,雇民夫抢堵两河堤工。”可见,尚在苏北修堤筑坝以前,赵王、洙水两河河堤已岌岌可危,而要知道此时黄河南泛流量还远未达到最大值。其实,早在14日晚,由于黄水猛涨,巨野段洙水河业已溃决,虽“拼命抢护,未能堵御”。同一天夜,天津《益世报》驻徐州记者发回的专电称:南侵黄水“水形较缓,约需一周间方可到达微湖”,就是距离最近的苏北沛县离黄水也还有180里。同样,洙水河沿线县份的水事冲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据《申报》16日从济南发回的专电,黄水入洙水河后,巨野、嘉祥两县“因为守堤、扒堤,利害不同,将起械斗”。这对洙水河决堤显然也会产生影响。据汶上救济水灾委员会所述,至迟在7月19日洙水河已从巨野向北泛滥,汶上“九十两区,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济宁救济水灾委员会给济南红卍字会的电函记载,赵王、洙水两河于7月20日“突告溃决”。而需要指出的是,苏北修筑微山湖西堤等工程,最早开始于19日。当天,江苏省建设厅还强调,“黄水尚未至微湖,因昭阳、南阳两湖之北,尚有一段高地,须漫过此高地,方达苏境”,甚至认为上游如不继续发水,则苏省无虞。《青岛时报》23日刊登了前一天下午自济南的来电,谓此时黄水才“渐向苏鲁间各湖归纳”,“倘水不减,旬日后”才会祸及苏北。综上所述,将赵王、洙水两河决堤归因于苏北筑堤修坝在时间上也是说不通的。
1935年8月8日,刚刚视察过苏鲁水灾情形的山东省国民党党部常委李文斋,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及微山湖宣泄湖水最重要口门的蔺家坝之情形:口门原宽50公尺,“现在江苏因黄水南泄,转在该坝口门加修,故口门现在为二十八公尺……河道中前时干涸,七日早已见水,但仍系湖水,水深不过一公尺,至微山湖黄水进行甚迟,每日仅二里许”。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即便苏省修筑了蔺家坝,并将泄水口门收窄,但此时黄河大溜尚未到达微山湖。此外,7月底前往微山湖一带视察“真相”的山东代表在报告韩复榘时说道,江苏沿微山湖西所筑百里大堤,“对黄水之漫流,关系尚小”。故而,就是来自山东方面的资料也显示,赵王、洙水等河决堤实与苏省无甚关联。总之,将赵王、洙水两河决口归咎于苏北筑堤修闸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说赵王河与洙水河决堤的主要责任并不在江苏,那么,8月底山东方面掘开苏北邳县堤坝的主因则与苏省相关。虽然陈果夫一直强调苏北筑堤不过是约水入海,冀免泛滥扩大,并非正面遏流,甚至对山东也有利,但实际上此举无疑加剧了鲁西水灾。
7月14日,中央社电,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曦与铜山区专员邵汉元等协商,“决议在微湖南岸建筑江苏大堤一道……令铜沛各县,迅征民夫十万人,限两周内筑竣,绕微湖成半圆形,西起鱼台,东达韩庄,计百二十余里,可为苏北屏障,并拟在微湖入运口门,造坚固大闸,迎截黄水改道入苏之势”。7月3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承认确有此工程,但强调“该堤只防黄水南下,并不阻其入海,故鲁省误会,业已消释”。显然,这一解释不过是为了平息舆论及尽可能缓解苏鲁冲突罢了。虽然江苏方面公开强调,仅“就微山湖西岸原有堤坝加高培厚”,但事实并非如此。1935年10月,江苏省建设厅在公开的相关报告中明确记载,从7月19日开始修筑微山湖西堤,大略自鱼台、沛县交界至铜山张谷山止,共88公里,投入工夫约7万人,于8月9日完工。并称此一“新筑微湖西堤”及105.5公里的不牢河南北堤“工程最为伟大”。陈果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去因山东南部山洪暴发,微山湖容纳不下,泛滥成灾,常常祸及徐州东部,故早有沿微山湖筑堤之主张,然而因山东百姓反对,江苏亦无决心,一直迁延下来。但苏省抓住1935年黄河决口这一契机,征工12万人,于12天内沿微山湖筑堤100公里。因此,在面见蒋介石时,陈谈到苏省“受害极轻”,所谓被灾惨重不过是外界“想当然”。此外,据时任铜山县县长王公玙所言,当时的确在“境内微山湖抢筑长堤防堵,至黄水渐见退落”,与民众“额手称庆”。可以说,仅从江苏立场而言,大堤的修筑对抵御此次水灾起到重要作用。以至于抗战胜利后,为追念领导这一工程的邵汉元之“勋绩”,江苏省政府提议“定名该堤为邵公堤”。
此外,在署名“江苏淮扬徐海人民徐钟令等”于10月底致国民政府反对韩复榘有关黄河改道分流方案的电文中,虽然将责任归咎于山东,但也证实了苏北确实有筑堤阻水行为。电文写道:“本年山东黄河疏防决口,灾及鲁苏,鲁西之菏濮等县,苏北之铜沛丰邳各地方均争先恐后筑堤,阻遏南阳、微山诸湖,使已受黄水不致漫溢泛滥,此在两省救死不暇之灾黎暂顾目前,出此下策。其为惨痛,尚何忍言。因鲁既作俑在先,吾苏不得已而效尤,衡情自属可原,理论外无二致。”
时任峄县县长,也是亲历者的刘化庭在后来有关此事的回忆,为我们了解掘堤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据他所言:
邳县政府派人拦河口筑坝拥[壅]水。本来,王母山河口有七八公里之宽度,如不筑坝阻水,山北一带(包括邳县山北六个乡镇)受淹不大。经人力拦河筑坝,阻水下流,山北沿运河的乡村一片汪洋,村落之间,路断人稀,往来均用舟楫,台儿庄镇围墙较高但不没入水者仅有半尺。全镇居民联络五、六区沿运乡镇一齐来县府呼吁。事关两省人民生活大计,我上报省府,但措辞却为责任计,说是“苏鲁两省沿运灾民数十万,群集台儿庄,携带武器,云将往邳县王母山破除非法拦河阻水之堤坝,疏通水势,减少灾害”等语,并一再报称,前往劝说,以免酿成祸端。其时,韩复榘命令我前往破坝疏通水势,并令鲁南指挥部派队相助。鲁南指挥谢书贤只打电话令我“相机进军,莫伤人命”。我坐守台儿庄派副队长携带机枪、迫击炮前往示威。守坝者仅有一个连长带一排队伍,见了我们的兵力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连长自知理屈,言明老百姓疏水破堤,他们决不放枪开火,若水已疏浚,坝已破除,请我们对空开火,表明他们不是不保护堤。
根据刘的回忆,当时苏省确实应负筑堤阻水之责,以至于引发微山湖沿岸被灾的鲁省地区,甚至包括苏北一些受灾民众的抗争。但掘堤并非像当时山东方面及部分权威媒介所言,是被灾人民迫于自救的自发行为,以及事前峄县县长未能阻止。其实山东省政府和峄县县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主导者。
另据韩复榘之子韩子华所言,由于苏北筑堤堵水,又于运河入境处堵截,加剧了山东水灾,陈果夫自知理亏,“先汇寄十万元,作为帮助山东堵口之协款”。但韩复榘“忍无可忍”,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协助灾民强行扒开截堤。
三、国家治理与地方应对
面对纠纷,国民政府适时介入。7月31日,经委会在致行政院函中提到,针对山东、江苏有关赵王、洙水两河决口之争,一面电饬黄委会“迅派负责人员前往实地查勘,并径与苏鲁两省政府洽商统筹兼顾办法,免生意外”,一面分别电两省政府查照办理。并重点强调,“苏鲁两省以上下游所见各异,或致发生误会,亟应召集各方,会同商讨,早定大计,共策进行”。遂定于8月5日召集两省政府主席,淮委会、黄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及相关专家开会商讨。会议达成三项决议:首先是关于黄河决口南流之水应如何分泄利导问题,决议由黄委会和山东省政府负责“将流入南旺湖之水,设法导入东平湖,挽归黄河”;由淮委会和江苏省政府统筹“将流入微山湖之水由湖口闸、蔺家坝导经中运河、六塘河、灌河出海,自微山湖入运水量以中运河所能排泄之最大流量为标准”。其次,董庄决口未堵筑以前,由黄委会和山东省政府迅速派员实地勘察形势,拟定引河位置及挑溜掘淤办法,导引大溜归入正河。最后,黄委会临时动议由山东省政府负责办理堵筑决口事项,并指定孔祥榕督察。决议经行政院通过,“分令苏鲁两省政府遵照”。不难发现,决议把疏导黄河水流及堵筑决口的主要任务划给了山东,江苏仅负责将流入微山湖之黄水经中运河导入大海,且入运流量完全依照苏省所报中运河所能承受量为准。因此,两省从自身立场对决议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代表韩复榘参会的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在会议结束当天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第二项决议即由苏北泄水是救灾之关键,“尤为苏鲁至好防水方策”,江苏方面还应加宽河身、加深河底,特别是要远筑堤坝,使黄水尽量宣泄。山东则并未遵循国民政府决议。8月中下旬前往视察黄河决口泛滥情形的一位黄委会技正在报告中强调,“前曾建议挂柳缓溜及保护江苏坝等项迄未实施”。8月29日即会议结束近一个月后,淮委会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抱怨,山东应办工程“进行之程度若何?迄无所闻。似此敷衍塞责,任其决口扩大而不加以抢堵,任其大溜下注,忍使以邻为壑,殊失通力合作之本旨”。蒋指出:“所有堵口办法应依决议之规定实行,由贵处随时径电鲁豫[苏]两省及经委会、黄委会催促赶办,务期彼此切实合作,以弭巨灾。”8月28日陈果夫给经委会的电文称,黄河暴涨,远超中运河所能排泄水量,苏北“危殆万分”,“倘大溜继涨不息,则漫溢溃决,下游将不堪设想”。经委会给山东省政府的电文中要求,“克日实行疏导黄河决口水流会议决议案内之导引大溜归入正河及挑溜挂淤办法,并另电黄河水利委员会严予督促”。此亦足见国民政府的相关决议在山东未得到执行。
此次会议决议中明显受到偏袒的江苏省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淮委会亦不满足,随即对涉及苏省的部分提出异议,认为通过派遣技术人员调查发现,中运河原本排泄流量有限,淮委会和江苏省政府只能在既定的排泄量标准之下将流入之水由湖口闸、蔺家坝导经中运河、六塘河、灌河出海。“如微山湖之水再因黄流下注,增涨不已,超过中运河泄水量,时苏属淮域各地恐不免遭灾。”所以,请经委会统筹全局,尽先将流入南旺湖之水设法导入东平湖,挽归黄河,借以减少漫入微山湖之水量。当然,最主要的举措是,“将已决各口从速尽力抢堵,引溜归入正河,或急则治标,速辟引河实行挑溜挂淤办法”。即把主要工作推向山东方面。
时至8月下旬,离黄河决口已届两月,相关治河之举并无推进,水灾越发严重。当时受经委会委托前往鲁西南、苏北查勘水灾等情的黄委会委员长李仪祉电告经委会:“黄水南犯形势严重,已电山东韩主席严令鄄城一带限五日内将高粱收讫,掘开鄄城民埝,放水由黄花寺入本河等。”经委会也认为,黄水南犯中运河,流量继长增高,苏北徐属一带泛滥区域扩大,津浦、陇海铁路遭受影响,故李所陈办法“诚为救急之举”。因此,希望行政院电催山东。当天,行政院即电韩按此意见“严限速办”。
这一要求随即受到山东方面的抗争。9月3日,“鄄郓范寿阳等十余县灾民代表桑平伯等”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去电,先是对中央限五日内开掘民埝引黄水入本河一事感到“不胜惊异”,认为此次堵口工程首先应该“接长江苏坝逼水归次河”,即由微山湖下泄。其次是在“江苏坝以下择适当地点,筑若干挑水坝并包裹李升屯东残埝头进行合龙”。再者是“疏浚对岸滩地以利流量”。唯独掘鄄城民埝入本河“实属最下策”。此举将导致“鄄郓范寿阳五县百余万生命、数千万财田尽行漂没”,二百余里官堤“到处可以出险”。万一溃决,则东平、汶上、宁阳等十余县尽成泽国,津浦路亦有横断之危,其东均有陆沉之虞。故而“祈从速收回成命”,拨发巨款修堵决口才是解决两省纠纷的根本之策。
虽未见山东官方的公开态度,但通过相关资料可以推知,中央政府此一决议亦未能在山东执行。9月18日,离掘埝限期已过了近半月,蒋介石在给经委会诸常委和韩复榘的密电中,结合李仪祉的相关建议“均未能行”,还提到“此时牺牲少数尚为值得”,暗示山东方面应该遵从中央要求掘开鄄城民埝引黄水入本河的决议。9月19日,淮委会第19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中记载:“掘开鄄城民埝放南犯之水归入黄河本河,虽经行政院议决限期实行,据闻现尚未遵办。”次年,胡焕庸在有关黄河堵口争执的文章中,还在为李仪祉的建议未能得到“中枢”和山东的采纳而感到遗憾。他甚至认为,中央放弃这一建议是因为“不忍鄄城套地之内,用人为之力,致其淹没”。很明显,这一说法与事实是相悖的。事件的真相乃是国民政府保“大局”的命令被山东置若罔闻。
概言之,国民政府无力整合两省以应对此次水灾。即便1934年7月14日已确立经委会为全国水利总机关,并规定“水利关涉两省以上者,由中央水利总机关统筹办理”,但经委会并无多少经费可供治黄。“南京十年”,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占国民政府每年总支出的67%~85%,这还是来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有一部分军事支出被隐蔽在其他项目中。因此,用于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特别是1935年发生华北事变,已届日本全面侵华前夜,黄河决溢时恰值迫于压力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府要员集体辞职,历时一月左右,国民政府显然也无暇他顾。另外,同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进行改组,更名资源委员会,相较于经委会,蒋更为重视该机构,相关资源也向其倾斜。因此,到1935年,经委会能支配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已经极为稀少。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由于经费微薄,尚需“财源涸渴”的地方协助,这种水利行政的统一不过有名无实。8月17日,经委会委员韩国钧在呈文中写道,1934年度全国水利事业预定400万元,实发只有40%;1935年预定494万余元,“实发不知若何”,而1934年所列治黄工程又移至1935年。当时的治黄工程空有虚名。研究表明,黄委会成立后近两年内只有经常费而无事业费,直到1935年才有了区区36万元事业费,还是在反复呈请后才得以下拨。以至于1936年3月底,在黄河修防会议上,下游几省皆言经费困难,根本无力完成应办工程,请求中央予以协助,但黄委会所能做的也仅是:“除据情转请中央恳力予协办外,务望各河局于困难之中亦各自谋进行。”此外,极为重要的防汛工程经费,只能寄希望于各省自理,即“各省原有修防经费,亦仍由各省照旧负担”。
1935年9月,陈果夫向蒋介石抱怨经委会“散漫”,“所谓统一水利行政,尚不如未统一以前”。这与1935年初来华考察黄河的国联专家所提看法相似,他们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缺乏统一机构,无权使各省通力合作,以执行治河方案。”当时《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对国民政府国家治理,尤其是治水能力做了较为精辟的分析。文章指出,“中国政治机构不完”,影响行政效率,“水利一端,其最著者”。水利行政虽号称统一,然“实际殆与不统一等,或更过之”。水利行政虽划归经委会管辖,但行政系统上与各省无隶属关系,故而地方水利之事仍请示行政院,再转经委会,黄河问题则又由经委会再转黄委会。“层层递转,手续繁复,而洪水泛滥,民在倒悬,何能堪此周折与迁延?”至于此次苏鲁冲突,“行政院无制止纠纷之力,经委会无平亭争议之方,此诚极水政纠纷之弊害”。
苏鲁冲突的导火索是黄河决口,因此,堵口无疑被视为平息纠纷的主要举措。蒋介石给经委会各常委和韩复榘去电要求:“经会与鲁省府协同赶办,无论如何,期于明年三月汛期以前完全办竣以免再酿巨灾,重损国力民力。”但起初韩复榘就以山东“人力、财力不胜艰巨……请由黄委会负责办理”,随后借“省政繁重不能兼顾”,“一再电请中央”交由黄委会接办。堵口工程最急之务即是经费问题,财政部下拨300万元公债,黄委会本希望以7折向中国银行济南、青岛分行等抵押,但最终只能以5折向7家银行押借款150万元。直到1936年3月堵口成功,此次黄河决口引发的两省纠纷才算告一段落。
四、结 语
苏鲁水事纠纷由来已久。在明代运河漕运体系建立以前,淮河水系未致紊乱,明中期后,国家治水实践中将全部黄水逼向徐、邳地区,致使淮北水灾频仍,但地区性冲突主要集中于苏皖两省。由于运河穿鲁苏而过,国家对沿河水道治理较为重视,故而两省水事纠纷并不明显。1855年黄河北徙,受自强逻辑影响,运河漕运体系废弃,中央和地方退出相关治水实践,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鲁西南段黄河决溢频繁,泛水流入微山湖,致使苏鲁水事冲突加剧,且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严重。
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大溜南奔,直入微山湖,危及苏北,甚至有改道之势。江苏积极应对,于微山湖一带修堤筑坝,两省纠纷接踵而至。山东将南阳湖周边的赵王、洙水两河决口及“民众”“自发”挖掘苏北堤坝即归咎于此,江苏则一概否认。通过资料的整合、分析发现,赵王河与洙水河决口有着极深的历史、自然等因素。加之,相关段决口时,或是江苏的筑堤工程还未开展,或是黄水尚未至微山湖,因此,将赵王、洙水两河决口归因于江苏筑堤是没有说服力的。但8月底山东方面的掘堤事件,确实与江苏修堤筑坝,拦截黄水,阻水下泄,引发微山湖周边山东地区被灾有极大关系。此次掘堤也并非如鲁省所言完全是地方民众自发所为,实由政府积极参与甚至主导。
政府的治水举措也是考察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1927—1937年被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建设”时期,国民政府曾视水利建设为“一切建设之基础”。针对黄河决口引发的苏鲁纠纷,国民政府适时介入。但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极为有限,治河所占更是杯水车薪。因此,所谓“统一水利行政”也只是有名无实,相关治水责任更多还是由地方承担。而各省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互相推诿,使得中央相关决策几成一纸空文。民国以降,苏鲁纠纷的主因之一即是黄河治理的“任其自便”,导致时常决口南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成立了全流域性质的治河机构并统一水利行政,但在治河实践中,日常的防堵亦步履维艰,遑论整合资源进行全流域治理。加之受时局影响,水事造成的地区性冲突不仅未见根除之曙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恰如1935年11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方觉慧等委员在提案中所言:“现时黄河河务分隶沿河各省,虽未至以邻为壑,而畛域攸分,各自为政,平时工作迁延观望,向无合作精神,出险之后,诿过卸责,惟有急迫呼吁。中央为统筹水利计……以为可以稍弭灾难矣!孰意堵口之工程甫完,溃决之惊传踵至……年复一年,若无底止。”就此视角而言,“十年建设”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成效与治理能力难孚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