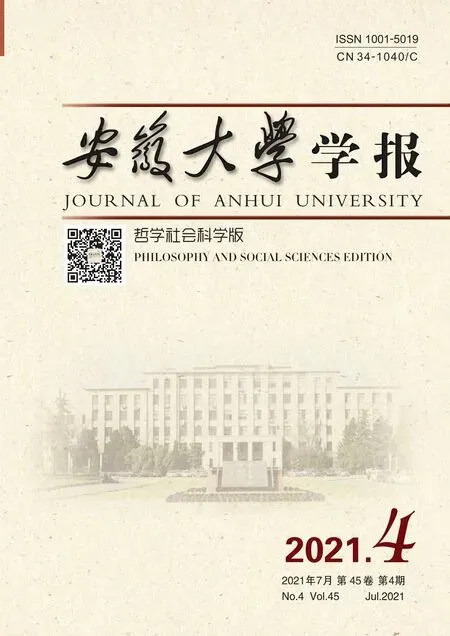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
徐国利
倡导“文史合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诸多史家运用现代文史理论对这一传统作了批判性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是其中贡献最大的史家之一。郭沫若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有超凡的文史天赋,故而比一般史家对文史关系有更精深的识见。他致力于将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相结合,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走出一条独到的文史结合道路。郭沫若文史关系的理论及实践包括史学和文学两个层面。就史学层面而言,他讨论的议题主要涉及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在宗旨和任务、思维形式、手段方法和认识功能等方面的异同。他指出,文学与史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文学有其独到深刻的社会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历史研究中应当重视运用文学性史料。在史学实践上,他注重“引文入史”,在历史认识上运用文艺思维,在研究中使用文学性史料,在表述上使用文学化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使其史学研究和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魅力。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颇有典型性,为中国现代文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对此问题虽有一些探讨,但是缺乏系统的专题性研究,只是研究其他问题时有所涉及,故拙文对此作进一步研究。
一、史学研究和史剧创作异同论的文史关系意蕴
关于文史关系,郭沫若主要阐述了史剧创作与史学研究任务的不同、研究方法与创作手段的差异及两者的辩证关系,既指出两者在思维形式、研究(创作)手段上的区别,又指明两者在宗旨和目的上的一致,即都要求得“历史之真”;文学有独到深刻的社会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史学研究必须重视文学性史料的运用。
郭沫若对文史关系的认识是与其史剧等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相伴生的。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创作历史剧,代表作有3部,即1923年创作的《卓文君》和《王昭君》,1925年创作的《聂嫈》。1936年,出版历史小说集《豕蹄》,“豕蹄”谐音“史题”,即以史事为小说创作题材。40年代上半期,为服务抗日民族民主斗争的需要,他的史剧创作进入高峰期,写出6部名作:1941创作的《棠棣之花》,1942年创作的《屈原》《虎符》《高渐离》和《孔雀胆》,1943年创作的《南冠草》。在历史研究上,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后开始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系统研究中国古史,成果于1929年结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1945年,出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7年出版《历史人物》。这三部史著绝大部分是40年代撰写的史学研究文章。也就是说,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在40年代都达到了高峰。在积极创作史剧时,他还对史剧理论作了大量阐述。有学者统计,郭沫若共发表了52篇史剧理论文章,其中20年代3篇,40年代31篇。这些文章对文学和史学关系有较多论述,这显然与他这一时期丰富的史剧创作和深入的历史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虽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他对文史关系问题进行明确的理论阐发却是在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前期。其基本观点是,史剧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历史研究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本质区别。一方面,历史文学创作必须以科学的历史求真为基础。他谈到历史文学中典型人物及事迹的塑造时说,“关于人物之先天的(生理的,心理的)与后天的(社会的,职业的)各种特征之抽出与综合,自然是典型创造的秘诀。然而这抽出与综合过程总须得遵循着科学的律令”;“我始终是站在科学的现实的立场的。我是利用我的科学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我所描画的一些古人的面貌,我在事前是尽了客观的检点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其真容,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污迹。……但如古人的面貌早是经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而被歪曲成为了恶者,或者本是无赖而被粉饰成为了英雄,那作者为‘求真’的信念所迫,他的笔是要取着反叛的途径的”。也就是说,历史文学中典型人物及事迹虽然需要文学性的塑造(创造),但是必须遵循科学规律,要以历史求真为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又存在根本差异,他说,“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合理”。可见,史剧创作旨在把握“历史的精神”,不应为“历史事实”所束缚。所以,他批评一些史家混淆文学与史学的立场而指责史剧的做法,“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不过,这些论述是在不同文章中谈及的,并不系统。
1943年4月,郭沫若在《戏剧月刊》发表《历史·史剧·现实》,对历史学与史剧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史学家与史剧家的任务不同。他说,“史学家和史剧家的任务毕竟不同,这是科学和艺术之别”,两者的不同是:“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何谓“发掘历史的精神”?他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历史并非绝对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是非”,对此史学家只能纠正。何谓“发展历史的精神”?他说,“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这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任务虽然不同,但都以求得“历史的精神”为目的,当然,探求历史之真的手段各异。二是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他说,“历史的研究是力求其真实而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史剧的创作是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质言之,历史研究旨在具体史事之真的探求与还原,史剧创作则着眼于揭示历史精神之真的完整历史画面和形象的塑造。三是史剧创作以历史研究为前提和依据。他说,“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因此,“创作之前必须有研究,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反过来说,便不必正确”。可见,史剧创作既要以历史研究及历史真实为前提和基础,又不能限于历史事实之真的层面,优秀的史剧必须是对社会历史本质之真即历史精神之真的揭示和反映。这些论述涉及文史关系的深层次理论问题:第一,史学之真与史剧(文学)之真的内涵不同,一是“发掘历史之真”,一是“发展历史之真”,亦即“科学与艺术之别”;第二,实现史学之真与文学之真在方法上的异同;第三,文学如何表达和反映历史之真。从文史关系的角度看,这三个问题涉及史学与文学两大学科的学科性质与任务、认识形式、表述方法这三个学科领域问题,表明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20世纪40年代后期,郭沫若继续拓展和深化文史关系的理论。他仍强调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的区别,说:“我们要知道科学与文学不同,历史家站在记录历史的立场上,是一定要完全真实的记录历史;写历史剧不同,我们可以用一分材料,写成十分的历史剧,只要不背现实,即可增加效果。”但是,论述重点已经转向探讨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辩证关系。
首先,从文艺从属于科学的立场论证科学研究是文艺创作的前提和基础。郭沫若对科学在人类认识中的根本地位和科学精神的本质作了阐述,说,“科学是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的阶段,是人类精神辨别是非、认识真理的最高成就”,因此,今天的一切认识都离开不科学和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便是“祛除主观的成见(私),而以客观的真实(公)为依归的纯正的精神动向。认识客观的真理,更依据真理以处理客观或促成客观的进展,而使之服务于人生,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便是科学的精神”。所以,科学是文艺的前提与基础,文艺创作从属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精神。他进而说,“文艺工作假使是属于研究或批评的范围,那完全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即使是属于创作的范围,我们也可以说只是科学精神的另外一种化装表演而已。文艺创作本质是人生的批判。即便粗浅一点说,任何创作都不能不经过一道研究过程。伟大的剧曲或小说固不用说,就是一首短短的即兴诗,它也是经过认识过程而来的”,所以,“没有研究便没有创作。生活体验也依然是一种研究,文艺工作和科学精神是分不开来的”,“文艺的主观也必然要经过科学的客观才能养成”。把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作为史剧之类的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根本,是其文史关系论的新发展。不过,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唯科学主义,是郭沫若受唯科学主义思潮主宰所致。事实上,文学艺术虽然以对现实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从属于科学,是科学的分支学科。文学艺术与科学之间虽然存在联系,却是两个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学科,二者没有从属关系。
其次,文学艺术对科学研究有渗透和辅助作用,并且比科学的史学有更强的历史反映能力。郭沫若反对将科学等同于纯客观和将艺术等同于纯主观,说:“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态度,它是要经过客观真理之明朗的认识以养成主观定见之坚毅的操守。科学正是在养成主观的能动力量而不是阉割它。”可见,科学不能与纯客观画等号,科学研究同样需要形象思维。1958年,郭沫若与记者谈及抗战时期自己的史剧创作时说:“写历史要根据史料,史料是有限制的,历史家要根据史料加以推理和判断,实际也就是想象。好的科学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如一块切片,科学家就要从这一切片来上下纵横地推测到全体;要从一个牙齿构想出爪哇猿人……当然,他是按照规律来想,而不是胡思乱想。”此言强调了文学艺术思维在历史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文学艺术还能更好地认识历史真实和还原历史之真。他说:“写历史剧原有几种动机,主要的就是在求推广历史的真实,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在过去的人类发展的现实里,寻求历史的资料,加以整理后,再用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那有价值的史实,使我们更能认识古代真正过去的过程。”可见史剧比史学有更强的历史认识功能,即“推广历史的真实”和“更能认识古代真正过去的过程”。他又说:“历史家把事实现实的记录下来,戏剧家就在认识了这历史的真实以后,用象征的比喻的手法,写出更现实的历史剧来。”易言之,历史剧用象征、比喻之类的艺术化手法可以再现“更现实”的历史。关于文学艺术比史学更能反映历史真实和社会现实的看法,是现代史家对传统文史关系理论的重要发展,梁启超、陈寅恪和翦伯赞等都作过不同程度的论述和阐发,相较而言,郭沫若的论述更为深刻。郭沫若等现代史家的论述为现代史学大量运用文艺作品作为史料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二、“引文入史”的史学实践成就
郭沫若不仅重视文学与史学关系的理论探讨,还积极践行文史合一的思想。其史剧创作是“援史入文”,借用历史题材从事文学创作。其历史研究则是“引文入史”,或是以文艺思维从事历史研究,或是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或是用文学语言书写历史。在这三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斐然成就,使其史学研究和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一是将文学艺术思维方式引入历史研究,解决了理性的逻辑思维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郭沫若从理论上阐述了既然科学研究需要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史学作为社会科学更需要有想象力。其《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说,用甲骨文和金文解释殷周社会变革时要善于发挥想象力,“不在这些地方驰骋一下想象,倒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谢保成说,“诗人气质与学者博识还造就出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交织,更使他在古代器物考释领域成为具有开拓之功的一代宗师”,他最初的甲骨文研究,“相当一部分有创见的新说都可以归功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交融。其他专家,虽然也多是从字形入手考释卜辞,但因思维方式不尽同,因而创获亦逊于郭沫若”。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前完全是门外汉,称自己1928年八九月间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初阅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时,只知是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字,“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为此,他又到日本东洋文库借阅王国维的《殷虚书契考释》,很快便能识读甲骨文了,声称面对这些墨黑的东西,“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功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随后他将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研究殷商史,1929年便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时还写出《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成为甲骨文研究专家。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即在于有着超凡的相象力。其金文研究也是如此。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年代断识是一大研究难题。1931年,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提出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方法,说:“然此等于年有征之器物,余以为其图象与铭文当专辑为一书,以为考定古器之标准。盖由原物之器制与花纹,由铭文之体例与字迹,可作为测定未知年者之尺度也。”这里指出花纹、形制在青铜器年代断定中的重要作用。他据此推翻了前人仅据文辞判定毛公鼎为周初器物的观点,考释其当为周宣王和平王时代的器物。要断定青铜器的花纹和形制,就需要有形象思维和艺术眼光。刘悦坦认为,郭沫若所从事的考古学意义的古文字研究,需要有与远古文化相通的原始思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是“互渗律”思维,“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也就是说,在互渗思维中同一主体同一时间可以有几种不同存在状态,从而形成几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互渗、交叉甚至突变,“能够发现那些在逻辑思维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事物和现象中隐藏着的相似性,从而把不同事物和现象联系起来”。郭沫若便具有这种神奇的思维能力,能用超常想象力代替推理和考证,“比一般人更能了解远古文化的奥秘,理解人类远古时代的文化,能想象出古人如何在龟甲兽骨上刻写、占卜,并且用以研究甲骨文背后的原始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使得缺乏学术基础的郭沫若可以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跃成为考古、古代史研究领域内建树卓著的大家”。事实上,形象思维的运用贯穿于郭沫若的整个史学研究,如,他用“移情”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使其历史人物的描绘感人逼真。他晚年谈到武则天研究时曾说,研究历史人物要“依据真实性、必然性”,为此,“总得有充分的史料和仔细的分析才行。仔细的分析不仅单指史料的分析,还要包含心理的分析。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便能够接近或者得到真实性和必然性而有所依据”。此言更明确地指出要以艺术思维研究和解读史料。可以说,人们读郭沫若的史著,能够强烈感受到其中艺术性的想象和文学化的思维。
二是将文学作品当作重要的史料。中国现代诸多史家对此作了积极探索和运用,郭沫若同属开创者之一,其突出特点和成就集中在用《诗经》研究殷周史,并总结以《诗经》治史的原则和方法。《诗经》对西周至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有较全面的描述和记载,可谓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便将它作为基本史料。他说,《易经》是中国由原始共产制变为奴隶制时代的产物,这是在殷周之际完成的;《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代的产物,这是在东周以后完成的,不过,“这两个变革的痕迹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我们现在依据这两部书来参考比验罢”。可见,《诗经》和《尚书》包含着殷周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历史信息。同时,先秦古文献可存疑者相当多,《尚书》便是如此,然而,“《诗经》是我国文献上的一部可靠的古书,这差不多是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的”。因此,郭沫若视其为研究殷周史的主要文献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即是用这两部书为基本史料来作研究的。他考察殷周社会变革时,引用《诗经》研究当时的生产和战争。如,他认为战争支配者发动的战争是产业发展的工具和产业发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然会向外发展和殖民,西周时周王的征战即是这种性质和类型的,《诗经》的不少篇目有生动记载,《诗经·大雅》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和《常武》,“那都是宣王时候向四方征伐的战诗。征服了一个地方便把自己的产业方法去使它同化。当时所谓开疆辟土,其实就是推广自己的农业”。后来,他对如何运用《诗经》研究周代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44年2月,他用《诗经》中的农事诗研究周代社会性质,写出《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他说,自己写《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时,对古代史料还没有充分接触,“感情先跑到前头去了,因此对于这些诗的认识终有未能满意的地方。这些诗,对于西周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启示,如认识不够,则西周的社会制度便可成为悬案。因此我更要费些工夫来,尽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于它们再作一番检点”。他通过对《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工》《噫嘻》《丰年》《载芟》和《良耜》等农事诗的解读,进一步论证了西周奴隶社会说,以反驳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西周封建说。此文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可谓“以诗证史”的姊妹篇。后来,他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识发生一些变化。1951年6月,他与范文澜讨论研究周代社会如何征引《诗经》时说:“《诗经》尽管‘从来无人怀疑’,但问题实在很多。材料的纯粹性有问题,每一诗的时代有问题,每一诗的解释,甚至一句一字的解释都可以有问题。我不是要全部否定《诗经》,而是不同意对《诗经》的全部肯定与随意解释。批判要严密,解释要谨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诗经》乃至一般史料所必备的基本态度。”从最早说《诗经》“差不多是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转为声称“问题实在很多”,表明他对引《诗经》入史有了更严谨的态度。他提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读的基本原则,无疑要比原先的认识要全面和客观。
三是用文学化语言进行历史书写,许多史著文采飞扬,可谓历史散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历程中,郭沫若的史著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对中国革命发展亦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与其史著多具文采密不可分的。有学者说,郭沫若的史文带着鲜明、生动、充满热情的文风,“在他的笔下,历史呈现出生动的、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其著述“充满理性,而又想象丰富,坦率、真挚、热情,体裁多样,文字活泼,且具有形象感,不仅描绘历史,陈述对历史的认识,也描绘史学家自己,这是郭沫若在文风上最值得称道、又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便是历史论说名篇,使用的是类似散文和诗歌的文句,一句或两句为一段,常用比喻说理,生动活泼。如谈到封建时代旧史观使人无法认清中国历史时说:
在封建思想之下训练抟垸了二千多年的我们,我们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视。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内障的明盲。
已经盲了,自然无法挽回。还在近视的程度中,我们应该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及早疗治。
已经在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难道得了眼病,还是要去找寻穷乡僻境的男巫女觋?
已经是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为甚么还锢蔽在封建社会的思想的囚牢?
巫觋已经不是我们再去拜求的时候,就是在近代资本制度下新起的骗钱的医生,我们也应该要联结成一个拒疗同盟。
谈到王国维思想情感与学术方法的冲突时,他写道:“王先生,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不过,王国维对古史研究却有开拓性贡献,“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这种生动而寓情的文笔遍及郭沫若的各类史著,如《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谈到如何处理古代神话传说文献时说,“关于神话传说可惜被保存的完整资料有限,而这有限的残存又为先秦及两汉的史家所凌乱。天上的景致转化到人间,幻想的鬼神变成为圣哲。例如所谓黄帝(即是上帝,皇帝)尧舜其实都是天神,却被新旧史家点化成为了现实的人物”,这方面的史料清理学界至今仍未弄出一个眉目来,“在这一方面,我虽然没有作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但幸而早脱掉了旧日的妄执,没有坠入迷宫”。谈到东周的王室衰落和诸侯兴起时,他这样描述:“周室就这样倒霉了下去,便形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春秋前半)。但那些老牌诸侯也并没有辉煌得多久,又挨一连二地沿走着周室的途径而趋向末路。姑且把鲁国来举例吧。这是西周诸侯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何玉兰论及《十批判书》时说:“纵观郭沫若的一生,诗人气质是其人格气质中的重要元素,在其《十批判书》中也分明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天才诗人的气质与精神。由于诗人气质与好恶情感的渗入,不仅使《十批判书》具有锐利的见解,而且具有鲜活的流畅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文情并茂的特质,创立了一种别样的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范式。”总之,在郭沫若的史著中,严谨的科学研究与优美的文辞表达是并行不悖的,读其史文,若读散文。
三、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的学术贡献和特色
郭沫若在文史关系的理论及史学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既丰富和拓展了文史关系的内涵和范围,又在“引文入史”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与其他现代史家相比,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探索及其史学实践成就有着鲜明的特色。
在文史关系理论上,郭沫若的思想主要包含在有关历史剧和史学研究以及二者关系的论述中。郭沫若通过对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宗旨和任务、研究方法与创作手段上异同的辨析,揭示了何为史学之真、何为文学之真以及文学与史学求真方法的差异,指出科学化的逻辑思维与艺术化的形象思维在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各有其地位和功用。这些问题实际关涉到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史学与文学的认识形式、史学与文学的表述方法三个层面的问题。他还对史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辩证关系作了回答,一方面从科学与文艺的从属关系角度阐明文艺创作必须以科学的历史研究作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对科学的历史研究也有渗透和辅助作用,文艺比史学有更强的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能力,这就为史学研究运用文艺作品作为史料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思想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文史关系理论。在实践上,郭沫若积极践行自己的文史思想,在“引文入史”上取得三方面的成就,即用文学艺术思维进行历史认识和思索,解决了历史研究中逻辑思维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在识读甲骨文和金文等早期文字上有充分的展现;将文学作品作为重要史料,把《诗经》与《尚书》等传世文献和甲骨文及金文相结合用以研究殷周社会史;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历史写作,使其历史著述文采飞扬而影响广泛。郭沫若“引文入史”的成就使其史学研究和作品散发出独特魅力,为传统文史关系理论的现代发展开辟了新路。不过,其文史关系理论也有局限性,在文学艺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上有明显的唯科学主义色彩。他将文学艺术附属于科学,称它为科学的分支学科,这自然导致他对科学性的历史研究与文学性的史剧创作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文史关系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重要议题。中国史学有着文史不分的传统,倡导“良史莫不工文”;同时,随着史学发展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传统史学又出现了文史相分的趋势,唐代史家刘知幾和清代史家章学诚等对此均有丰富的论述。中国现代诸多史家运用现代史学和文学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传统文史关系理论作了发展,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一是对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差异作了现代性阐释,二是探讨了文学思维与史学思维的异同,三是扩大了文史撰述原则与方法异同的研究范围,四是对史家文学才能的内涵作了新解释,五是将文学作品作为重要史料并在历史研究中广泛运用。再者,许多史家因受到良好的文史教育和训练,对文学亦颇有造诣,甚至亦是文学家。故而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撰写史著时也注重文学化的表述,不少史家还创作了许多历史诗作和散文,使文史合一的传统得到多方传承发展。现代史家对传统文史关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史学性质及文史关系的认识,推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其中,陈寅恪、张荫麟、郭沫若和翦伯赞所做的贡献最为突出,且各具特色。陈寅恪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以诗文证史的传统,系统论述了“以诗证史”和“援诗入史”的方法;他还大量运用诗词和小说来研究历史,成就卓著。这使人们认识到古代诗词、小说的史料价值和正确使用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利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范式。张荫麟在学科性质、学科思维和语言形式等方面对史学作了系统阐发,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命题,强调历史研究既要作客观的研究和叙述,又要运用艺术思维和文学表述,倡导弘扬中国古代重视历史审美的优良传统;其《中国史纲》将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为中国现代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树立了典范。其文史关系理论和实践是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唯科学主义的有力反驳。翦伯赞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重在发掘传统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历史要素,在历史研究中大量运用各类文学作品。他发扬文史合一的传统,重视历史著述中语言文字的表述,许多著述文采飞扬、饱含激情,其《中国史纲》成为文史结合的又一经典之作。
与上述三位史家相比,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实践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他主要是通过对史学研究和史剧创作及二者关系的分析来阐明文史关系理论的,这就使他的视角和取径与上述三位史家大相径庭。视角和取径的不同使其所探讨的内容与上述三位史家异多同少。其异多之处,通过与上述三位史家的文史关系理论相比即一目了然,此不复述。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指出了文学比史学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本质和揭示历史精神,由此肯定文学作品独特而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郭沫若对史学与文学思维的异同及关系的阐释虽与张荫麟的论域相同,但是视角和立场相异,郭是从史学与史剧的辩证关系着眼的,张则是从史学的学科属性立论的。其次,在史学实践上,四位史家都重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学作品,但是由于他们均是结合各自史学研究领域进行的,同样各具特色。郭沫若历史研究所使用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经》,他把《诗经》和其他传世古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相结合用以研究殷周社会史,不如其他史家的历史研究运用文学作品的范围广泛。如,陈寅恪结合唐代诗歌、小说和明清诗词研究唐史与明清史,翦伯赞则运用历代文学作品研究中国通史。至于将文学思维运用于历史研究,郭沫若则为其他史家所不及,可以说文学思维贯穿其史学研究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且取得丰硕的成果,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然而,在历史著述的文学性书写方面,他又没有留下翦伯赞和张荫麟《中国史纲》那样的经典史作。
郭沫若之所以能在文史关系理论上富有独到精辟的识见,并在“引文入史”上取得重要成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从小所受良好的传统文史教育对其文史研究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郭沫若说,自己四五岁起就每天读《四书》和《五经》,虽不怎么懂,“但毫无疑问,从小以来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础”;十三四岁时开始读诸子,最先接近《庄子》,“最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的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并直接触发了“五四”时代讴歌泛神论诗歌的创作。他自幼还受到严格的诗歌教育,4岁就跟母亲口诵古诗,为“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发蒙前已暗诵了很多诗。其家塾对子弟还立有“白天是读经,晚来是读诗”的规矩。8岁时,他开始由塾师教读《唐诗正文》和司空图的《诗品》,并喜欢上《诗品》,这影响了他后来“关于诗的见解”;9岁开始学做对句和五七言试帖诗,主要教材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其中,“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对于唐代诗人,他喜欢浪漫主义风格的王维、孟浩然、李白及柳宗元,不喜欢现实主义风格的杜甫和韩愈。早年良好的文史教育特别是诗教为郭沫若成长为文史大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的身份使之对文史关系问题有更精深独到的认识。从“五四”时期投身新诗创作成为著名诗人,到三十年代致力中国古史和古文字研究成为著名史家,再到四十年代创作大量历史剧,郭沫若最终是集史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而且,他还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史学发展的开路先锋,茅盾说:“他的诗集《女神》,在当时激起了多少青年的热情,鼓舞了他们前进的意志,这正是中国新文艺史上一个‘狂飙突进’。同样地,他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一连串的考古的著作,在当时也在繁琐的中国考据学的氛围里投下了一个炸弹,也正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狂飙突进’。”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和极富原创力的研究和创作,使他能将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有机结合,抒发独到精辟的文史之见。相较而言,陈寅恪、张荫麟和翦伯赞三位史家虽然亦富有文学才情,特别是陈寅恪的诗词、翦伯赞的诗歌和历史散文写作都达到很高水平,但他们毕竟称不上文学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有一席之地,与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不可相提并论。最后,有丰富的文史研究与创作成果作为坚实的基础。郭沫若对文史关系的理论探讨是与其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紧密结合的,是源于其坚实的史学研究和丰厚的文学创作。仅就其史学研究和史剧创作高峰期的20世纪20—40年代来看,重要的史学(包括考古学)著述便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殷契粹编》和《石鼓文研究》等,史剧主要有《卓文君》《王昭君》《聂嫈》《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当然,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和史剧创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为中国现代文史关系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开辟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