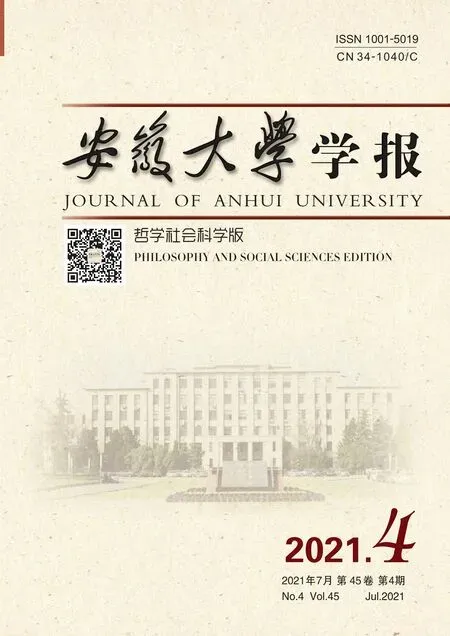“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盛险峰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其在礼乎?在政乎?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左传》云:“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唐孔颖达正义:“政待礼而行,犹人须车以载,礼是政之车舆也。”据《孟子·公孙丑上》:“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汉赵岐注“见其礼而知其政”:“见其制作之礼,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既然礼的制作关乎国家治理效果,那么礼乐崩坏亦可管窥王朝衰微。“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而对于礼与政的关系,北宋欧阳修认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所谓“治出于二”“礼乐为虚名”,其实只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形式上的差异,实际上秦以后帝制时代的国家治理中,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这表明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最为深远、极为深刻。
一、礼与“人情”
礼植根于我国独特的农耕文明,认识其发生及功能,是探讨礼与政关系的前提。礼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认识礼政关系是不能离开儒家视角的。在儒家看来,“人情”与礼的关系,既可以解释礼的发生问题,也可以阐释礼的功能问题。
礼的发生,是礼的基本问题。儒家立足于人,认为礼依人情而生,并围绕“人情”,对礼的发生的认识形成不同阐释框架。
从性情关系上看,礼是“以性制情”的手段,此说可称为性情论(认识论)。这一立论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为儒家基本主张。《周易·乾卦·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注:“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孔颖达正义:“‘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在这一认识下,礼作为“以性制情”的手段,是“久行其正”的保障。性情论源自《周易》,以始为正,故其说之发展则有始终论、复性论。如《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唐代李翱认为“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
从情礼关系上看,有“缘情制礼”之说,此说可以称为情礼论(决定论)。据《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无疑,荀子情礼论是以人性恶立论的,但认为礼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人欲无限性与人获得满足欲——“物”有限性的矛盾,则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因而制礼也是先王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手段。《史记·礼书》:“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人情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的反映,为人的自然禀赋。而“欲”作为“七情”之一,为人情的核心,大体可以涵盖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基本需求。由此可以推断,礼与人情的不同,是学而能,是社会的规则,以学而能的礼去改变“弗学而能”的人情,才能解决人欲与物的矛盾,维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
从心情关系上看,人情是人心的反映,即心情论(反映论)。《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欲恶”作为人心的反映,因人心不可知、不可控,所以礼作为人可见的“欲恶”和不可见的“心”“一以穷之”的手段,由人心而产生,唐代司马贞认为“礼因人心,非从天下”。心情论反映了人心与人情的关系,礼除了对人情的制约,也对人心有建构作用。
以上三论,是以人为核心建构的,对礼产生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心理性进行阐释,从不同维度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礼的发生具有客观性、人文性和心理性的特征,这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逻辑基础和认识起点。而人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属性,使礼又具有自然之理和社会之理的双重性,正如孔颖达等在《礼记正义序》中所云:“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这表明,礼的产生是以人情为基础的,即“礼由人起”,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礼除了具有“践履”之义外,还具有规则之义。
礼以人为核心,人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组成的基本细胞。礼作为家天下政治的工具,其功能体现在人、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
以人的视角来看,礼可以塑造君子人格。荀子认为:“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为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君子既要“得其养”又要“好其别”,“别”是“养”的保证。在立差等秩序的基础上,礼顺乎人情使君子得其养。又据《史记·礼书》:
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因此,礼义下的性情和礼义可以相得益彰,反之,性情下的性情和礼义两失俱损。荀子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唐代杨倞注:“专一于礼义,则礼义情性两得;专一于情性,则礼义情性两丧也。”荀子的情礼论从“别”与“养”关系出发,进而揭示“性情”与“礼义”关系,认为得之于礼义下的情性与礼义可以塑造君子人格。推及性情论和心情论,性情论意在礼可以发人性之善,心情论表明礼可以正人心。所以礼可以从不同层面建构君子人格。
从社会和国家的视角看,礼与人情的关系犹如“器”与“田”的关系,是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工具。在农耕文明里,礼与人情的关系被置入富有农耕文明的语境和意象。《礼记·礼运》:“故圣人作则……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孔颖达疏:“上既有法象为先,故可执礼义为器用,如农夫之执耒耜也。”“用礼义以为器,可耕于人情。人情得礼义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人情得礼义之耕耘,才能在人情的田中生长出秩序的“禾稼”。《礼记·礼运》:“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孔颖达疏:“上‘人’是人民,下‘人’是圣人。奥,主也。田无主则荒废,故用人为主。今以人情为田,用圣人以为田主,则人情不荒废也。”礼作为耕人情之“田”的器,具有工具性: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
以上在治国犹如农艺这一前提下,用“器”与“田”推论礼与人情的关系,以耕、种、耨、获、食、肥之事分别指喻礼、义、学、仁、乐、顺,并以“顺”作为人、家、国和天下等不同层次的共同标准。其中,礼与义,如实与花,“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孔颖达疏:“礼是造物,为实,义以修饰,为礼之华。”这样,礼与义结合才能在人情的田中长出礼乐文明的花果。
以上从礼与人情关系角度探讨了礼的发生及功能。其中,性情论和心情论具有学术思想建构的意义,而荀子的情礼论则具有政治的张力。荀子认为礼建立起来的差等和秩序,目的在于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荀子·礼论》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里所谓“三本”,有“贵始”之义,“所以别贵始。贵始, 得[德]之本也”。可见,礼是奉天地、先祖和君师为“三本”建构起来的,意在解决人与天地、先祖和君师的关系,即对人在自然、血缘、政治、文化中进行定位,因此礼不仅关乎人与自然和社会,也关乎人与政治和文化。具体而言,“三本”对礼的建构作用不一:“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作为人的生存环境,是满足人欲——物的来源,解决人与天地的关系,这是礼产生的动力;而“先祖者,类之本也”,是人这一生命现象的血缘逻辑,这里的“类”是指父系的类,由父系建构血缘关系的差等;至于“君师者,治之本也”,这是政治和文化的逻辑。“天地”“先祖”和“君师”决定礼的内容和形式。“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因而,相对于自然意义上的人情,有所谓“人义”上礼制化的人情与之相对,“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里所言“十义”,是以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为差等建立的秩序。无疑,“十义”作为礼乐文明的象征,是礼制化人情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固化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儒家看来,礼产生于人类自身从自然的获得能力与欲望这一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演进的产物。礼既具有工具意义,也具有目的意义。从工具意义上看,“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见,礼作为“人道之极”,凡人事无所不及。“礼义人情,其政治也。”从目的意义上看,礼的功能超越工具性,成为自然万物的尺度,被认为天经地义。“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故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礼在这样范围天地、涵容家国的普适价值下,建构出的礼制化秩序社会,是以差等秩序为工具和目的的,这为集权专制政治提供了社会和文化的土壤。
二、礼与周公制礼
礼由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则上升为国家制度性的规则,这与制礼是不可分的。从制礼上看,周公之前的制度设计,限于文献不足征,渺不可知。而在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为中国古代“天下为家”演进历史中的重要大事,影响深远。周公制礼推动了礼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国家治理和价值建构等不同层面。
从制度建设上看,周公制礼实际上是礼的国家制度化。礼之所以国家制度化是由于家天下政治的需要。礼的国家制度化,关键在于礼是必须经人制定的并上升为顶层制度设计,而这个“人”又必须具有特殊身份。《礼记·中庸》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郑玄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礼,谓人所服行也。度,国家宫室及车舆也。文,书名也。”从制礼者来看,礼经周公制作则成为国家制度,这实际上是礼与家天下政治的关系决定的。据《礼记·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从“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以设制度”看,礼是维护家天下政治的手段,因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在夏、商“谨于礼”的基础上,通过制礼使礼进一步国家制度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礼对王位继承进行规范,确定王位继承的唯一性原则。周灭商之后,殷鉴不远,周公认为商代九世之乱源于王位继承上的人情之争,家天下政治的需要促使礼进一步制度化,进而服务于国家治理这一政治目的。王国维高度评价周公制礼在制度设计上的创新:“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其中“立子立嫡之制”,确立了西周最高权力继承制度的唯一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周公制礼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礼制度化的基本逻辑。《公羊传》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种继承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立子立嫡制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发展,体现了礼的亲亲尊尊之义,使礼的精神与最高权力的继承制度结合在一起。周公为立一代新制,以身作则,其人格风范和政治实践得到后世的赞誉,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制度。在这一制度基础上而衍生出的宗法制度、丧服制度、分封制度、君臣之制和庙数之制,体现了礼的亲亲尊尊精神。其中,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和“同姓不婚之制”,血缘关系对社会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组织以及地理空间的想象,实际上把异姓(异族)纳入亲亲尊尊之中,体现了大一统思想。第二,礼向礼典化发展,成为国家的基本制度。王国维认为服务政治的需要是礼向礼典化发展的原因,“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周礼·天官·大宰》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据《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再据《礼记正义序》:“洎乎姬旦,负扆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孔颖达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孔子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周公制礼体现了三代时期礼向礼制转变,向国家制度转变,这是家天下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国家治理上看,周公制礼体现了以礼治国的特征。礼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王以礼治天下,后以礼治六宫”。周公为维护家天下政治,通过制礼加强礼的制度化建设,使之适应家天下政治的需要。而以礼治国的目的就是通过礼建构亲亲尊尊的等级秩序,稳定家天下的统治,并以此作为判断家天下政治下国家治乱的标准:“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周公制礼使西周国家治理达到了治出于一,礼不仅遍及人们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也贯穿身心家国,无所不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因此,周公制礼适应家天下政治的需要,推动礼的制度化发展,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国家成为礼乐文明的体现。
周公制礼又在道德、文化和心理等不同层面进行价值建构。在道德层面,以礼治国是以德治国的核心。“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可见,周公制礼是以差等结构彰显道德并实践道德,目的在于维护家天下政治,达到礼乐文明的礼治。礼是基于人自然意义的差等建构起社会意义的差等,所谓自然意义的差等是指男女有别,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意义的差等,体现了亲亲尊尊之义,周公制礼使礼向礼制转变并成为礼治的工具。在文化上,礼治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为诸子百家出现提供了条件,儒家文化本身与家天下政治具有不可分割性,并在帝制时代成为正统思想。儒家与家天下政治相表里,成为家天下政治的工具,在文化和思想上体现了家天下政治的取向。在心理上,礼在家天下政治的驱动下,在道德和文化思想的双重塑造下,必然会反映在社会心理上,正如《礼记·大学》所谓的“正心”和“诚意”,而“正心”和“诚意”从塑造个人心理到塑造社会心理,则成为礼的主要功能。礼在价值建构中所体现的不同层面,符合家天下政治对秩序和稳定的要求,同时为家天下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以为帝制时代王朝政治提供文化支撑。
周公制礼的目的是通过血缘秩序建构地缘秩序维护家天下统治,周公制礼依托于人情,又塑造出新的人情,在这一礼制化人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其本质特征为亲亲尊尊的差等及其政治和观念。周公制礼在“天下为家”时代建构出严密的等级秩序,这一人情社会既体现了国家的发展,也是古代国家政治、文化思想产生的土壤。
三、礼与秦行郡县
秦行郡县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升级,是对战国变法运动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从战国变法实践来看,就不能不考察礼与秦行郡县的关系,二者虽在治理方式上有本质的不同,但维护家天下政治的目的并无二致。秦始皇对于新统一地方采用何种制度治理,是通过廷议的方式广征意见: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政见的不同,实际上是在秦统一后君臣对国家制度设计选择的不同。面对廷议的分歧,秦始皇鉴于分封制的弊端,赞同法家李斯的意见,专制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把郡县制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经历战国变法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后,即使选择分封制也不能认为是完全采取西周的治理方式,而是更类似于西汉初期的分封同姓王,因为经过战国变法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战国变法使国家治理方式升级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种治理模式经过战国各国变法实践,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主要手段和统一的前提,郡县制符合这一要求。因此,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于顺应了战国变法后社会发展的趋势。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目的在于家天下政治的长治久安,“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尽管他采用的终始五德之运与其万世之期尚有抵牾之处,但以郡县制和皇帝制度来维持家天下政治的目的已很明显。此后,郡县制成为帝制时代历代王朝的政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制作政令,施于后王”,在这两点上,秦始皇的目的已经达到。
郡县制和分封制在制度设计和国家治理上有本质的区别:其一,西周分封制度是以“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为核心价值,“亲亲以相及也”,其主旨在于借助血缘关系的地缘化维护周王室的统治,周王室与诸侯国关系较为松散。郡县制则是以其确立的中央与地方的地缘关系维护秦朝统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严整紧密统一。二者存在国体制度设计上取向的不同以及地域空间治理上的差异。其二,分封制度主要依靠礼乐制度建构起来的天下秩序,郡县制度则主要依靠法律并结合礼制建构起来的国家秩序,二者在治术上有根本的区别,天下秩序到国家秩序体现了国家的演进。其三,从大一统角度看,分封制下的大一统与郡县制下的大一统,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分封制下的大一统是象征性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郡县制下的大一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实质性的。不同时代的大一统,体现了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的发展历程,也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必然逻辑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秦行郡县的划时代意义主要在于对帝制时代的制度设计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更进一步说就是为后世的制度设计埋下了集权、专制的基因,这一基因并不会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变化,这就是历代王朝政治遵循并信奉的专制主义。
从战国变法和秦朝制度的选择上看,礼与秦行郡县具有因果关系。下面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从制度设计上看,周与秦朝实行的制度不同实出于礼法之别,而礼与法之别由儒家和法家的不同可窥一斑。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总结儒家和法家之别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据此,礼与法之别主要在于:礼以人论,以人定事,以血缘别亲疏贵贱;法以事论,以事定人,以事功论贵贱赏罚。以礼治国,向为三代历史叙事的主题。西周初期实行的宗法、分封、丧服、同姓不婚等制度,都是以人的角度为出发点设计的制度,其核心价值为亲亲尊尊。这种以人定事,使“亲亲”通过血缘关系弥漫于同姓、异姓以及“夷夏”之间,既达到了维护家天下政治的目的,又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内聚力。但由于社会发展和血缘关系亲疏变化,人与事的结合使历史演进并不是按照亲亲尊尊制度设计的理想逻辑,而是按照事的逻辑对人关系的解构,具有外散性。经过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公制礼建构的礼序社会的坍塌,否定了以人系事的逻辑。至战国时期,各国为富国强兵掀起以事功为核心的变法,确定了以事系人作为改革的基本精神。在这一改革推动下,各国政治一新:一是由事序人。序人逻辑由人到事,因而人的能力和事功成为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魏国“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作尽地力之教”;韩国“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各国兴起的变法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新旧更替。二是以事治地。由齐威王对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赏罚可见一斑:“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各国对地方治理由分封制诸侯对王室的“藩屏”到郡县制守令对中央负责,事功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治理的成效和赏罚标准,中央与地方集权关系逐渐确立。三是因事驭臣。各国君主为加强对臣的控制,采用当时盛行的“法”“术”“势”学说,为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服务。慎到主张“势位”,“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四是依事立法。法家思想为各国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源泉,法家成为各国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加强法制建设成为战国变法的主要内容。以事系人作为战国变法的基本精神,全面刷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由于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是人性恶,因而对于君主而言,也只有通过“尊君抑臣”和“尊君愚民”才能保证君主集权专制,这成为《商君书》和《韩非子》二书的基本精神。这样,在礼、法的人、事区别的基础上,战国时期通过变法运动由礼序社会变为法序社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而礼也成为秦国统一后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手段。“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在治理国家上礼法具有内在的互补性,正如汉代贾谊所言“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与法都是通过建立差等秩序维护家天下政治,所以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与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尊主卑臣”是不可改易的。
其次,从社会结构上看,礼法主张虽有人、事分殊之别,但对社会秩序建构的目的是一致的。《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种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有别的社会里,“礼义”所体现的差等秩序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王国维认为“《丧服》之大纲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正如《礼记·大传》所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这一治理天下的逻辑里,“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成为“人道”不可“变革”的规则。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动,至战国时期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各国变法运动使这一变动得到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确认。而以事为逻辑建构的社会,推动了古代国家的发展,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当然,即使战国以前盛行礼制时期,礼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也有不同的规则和作用,足见家国之别,以及宗统和政统的关系。“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正是家天下政治的需要,推动礼制的变革。秦孝公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商鞅认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此,从社会结构上看,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是基于差等社会的目的性,从维护家天下政治目的而言,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是一致的。在这一目的下,礼制所建构的以人系事必然走向以事系人,战国变法为家天下政治提供了新的治国方案,因此礼与秦行郡县有因果的必然性。
从制度设计、社会结构上看,以人为主的礼序社会和以事为主的法序社会,必然走向人事合一、礼法合流的社会,礼与秦行郡县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秩序是以人为差等建构的。中国古代礼制化的人情社会,是专制基因赖以存在和长期延续的土壤。法序社会是以事建构人的差等,事功成为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战国时期的变法确立了以事为逻辑,必将导致集权,集权必将走向专制。郡县制雏形于春秋时期,是诸侯国对地方治理进行的制度上的探索,这一创新从制度本身推动了分封制瓦解。而推行郡县制的目的,除了提供有别于分封制这一地方治理的方案外,还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功能,这在战国变法中显得尤为突出。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集权与专制相伴而生,在郡县制基础上形成中央集权的同时,管理地方并服务于皇帝的专制机构——中央官僚机构也必然应运而生,“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依托郡县制的“皇帝之号”与“百官之职”,就是所谓“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秦以后帝国时代的政治架构,而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皇帝制度,基本形成了帝制时代政治权力演进的逻辑,这就是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权力专制于皇帝。郡县制设计的基本精神在于集地方权力于中央,而处于枢纽地位的相权则事实上威胁了君主的权力,所以自秦以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一方面不断削弱相权,另一方面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进而使中央和地方职官制度不断创新,其目的在于维护家天下政治。在秦以后的帝国时期,历代王朝为确保家天下政治的稳定和长久,统治者无不对地方和中央官制进行设计和调整。在历史上,无论“秦汉”“隋唐”,还是“宋元”“明清”,“集权”“专制”成为历代王朝家天下政治的基因,甚至出现了家天下政治“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这种极致职官现象。在帝国时代,郡县制与集权式家天下政治是表里关系,历代王朝选择郡县制这一基本制度模式,其里必然是集权式家天下政治,专制基因也必然被携带并左右着制度设计。
由于人与事的关系,从集人到集事是必然的,而集事必然导致集思。从郡县制与大一统关系上分析,专制集权与国家大一统体现为因果关系。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分封制实践的精神所在,它系统化于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之中。《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西周时期大一统体现了周公制礼作乐制度设计的秩序,其秩序的理想状态即天下礼乐文明;秦行郡县后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集权关系上,进而推动专制主义的形成。秦统一过程实际上是郡县制推行的过程,在秦亡以后,从两汉至明清的历朝历代,除了外力引起朝代鼎革外,大多数情况是郡县制下的地方不断出现离心中央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非郡县化,即集权和专制出现问题的“封建化”。当集权专制出现问题,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也在下降,地方上出现了“封建”的权力体系。比如,东汉末期的州牧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演进的基础,唐代方镇(藩镇)也是五代十国历史演进的依据,所以郡县制的制度设计与国家大一统息息相关,二者是因果关系。郡县制保证了国家大一统,郡县制遭到破坏就会出现割据分裂。再加上儒家文化自汉代以降成为正统思想,郡县制作为体现儒家大一统思想的象征,“政治与文化的大一统,成为秦汉后两千余年中国的主潮”,“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强化国家共同体的号召之下,以君主为轴心的统治者为至高权威,决不允许有些微的违忤与怀疑,通过不断放大刑法的残酷性来维护其专制统治”,这又从文化思想上使郡县制度深入人心,从长时段上保证了历朝历代制度选择的惯性和制度依赖。
从国家起源理论上看,“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差等社会孕育并促使集权专制的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国家与旧的氏族组织的不同,“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为公共权力与社会的高度分离,这表明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对于公共权力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对社会的塑造又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制度设计及政治实践,特别是政治道路的选择,决定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而差等社会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仅促使集权专制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了古代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从中国古代人情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遗传了专制基因,并促使专制基因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色。
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体现从天下到国家地域空间关系建构的演进。周公制礼是以血缘关系维系地缘关系,虽有宗法氏族社会的遗风,但已具有成熟国家的特征;而秦行郡县是以地缘关系建构中央集权,体现了集权国家的特色。在差等社会的建构上,二者具有同质性,从权力的集中上看,秦建立帝国政治使差等社会上的政治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特征,这是自周公制礼以来差等社会继续演进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周公制礼塑造的礼制化人情社会,成为王制的社会基础,也是秦行郡县的社会基础;而郡县制塑造的人情社会,发展了周公制礼的人情社会,为中国古代政治遗留了专制基因,这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
以上分析了差等社会与集权专制的关系。差等社会和集权专制分别作为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遗留的社会和政治特征,二者互为因果。在这一关系下,秦以后的帝制时代出现了在思想文化上的特殊现象,即儒家思想得到政治的推动不断发展,这作为帝制时代差等社会和集权专制的反映,成为帝制时代的文化格式。
四、余 论
差等社会和集权专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的特质,也是历代王朝建立的基本国情,它决定了历代王朝建构的政治特色,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道路的类型。
从国情上看,我国独特的农耕文明孕育了特殊的差等社会。所谓独特的农耕文明,是从大禹治水后形成的:一方面大禹治水不仅使地可艺可宅,奠定高山大川,形成了农耕社会的基础,同时也使这种农耕社会体现了自然禀赋的特征;另一方面,大禹也因治水推动了中国古代国家的演进,使中国历史进入家天下历史阶段,这一治水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的图景和国家发展的路径。正如柳诒徵所云:“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教宗,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柳氏所言实则是礼之“三本”的具体化,即农业——“天地,生之本也”,家族——“先祖,类之本也”,士大夫——“君师,治之本也”。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差等社会,在周公制礼的塑造下,必然孕育集权专制基因,这一基因通过郡县制成为帝制时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因而,中国古代国情就是差等社会和专制基因,二者相互作用,与时俱进,不论王制时代还是帝制时代,二者决定并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演进的基础。
从特色上看,中国古代是集权型的国家。差等社会孕育了专制基因,在人情社会的土壤里,专制基因在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这推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演进,并形成了独特发展逻辑和王朝命运:一是王朝性成为家天下政治演进的必然规律。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家天下政治皆体现出了王朝性的特征,这是家天下政治难以克服的历史宿命。二是循环性成为家天下政治的一个特征。在家天下政治演进中,王朝的兴衰、统一与分裂,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规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断循环,影响了中国历史超越性的发展。三是大一统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终极追求。以大一统为目的,只能按照差等社会走集权专制的模式。不论在王制时代还是帝制时代,历代王朝都以大一统作为统治的目标,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四是因袭性成为中国古代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演进的长时段特征。“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要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礼对社会和国家演进的内在制约以及法的因时而变,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从类型上看,建立在差等社会和集权专制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类型和发展道路,被称为东方型。这种类型政治演进的模式,专制基因与差等社会相得益彰,专制基因在差等社会里不断地发展,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成为历朝历代家天下政治的基本特征。这种类型的政治在文化上推崇儒学,崇尚礼制,儒学在百家中凸显出来,成为官方哲学。儒学为集权政治提供了文化上和社会上的强力支撑。这种类型的政治由于儒家文化传播和以礼制为主的制度辐射,对东亚一些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对中国古代国情、特色和类型的探讨表明,礼与政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秦行郡县奠定了帝制中国的政治基础,而礼为这一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礼以人系事的逻辑必然演进为法以事系人的逻辑,最终走向以人系事、以事系人逻辑相结合。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尽管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使秦行郡县在政治上开创了新时代,但礼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进一步说明,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影响既深且远,使中国古代政治带有文明的色彩,并成为推动中国古代政治演进生生不息的源泉。
从中国古代制度设计上看,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影响深远。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但同时也遗留了人序的差等社会;秦行郡县肇启中国古代帝制时代,但也遗留下专制基因,二者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国情、政治特色和类型。而差等社会和专制基因对中国历代王朝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已成为古代中国历史的惯性和长时段的规律。对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进行探讨,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演进的路径,并揭示中华文明演生的内在延续性。
附记:本文遵照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同时也参考了吉林大学文学院马卫东教授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