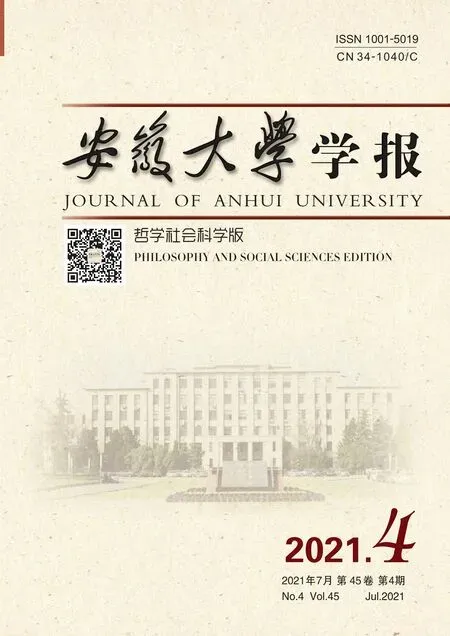“杨刘风采,耸动天下”
——再论西昆体诗人的文学地位和历史贡献
刘 杰
作为宋初“三体”之一,西昆体诗歌曾在北宋真、仁之际的文坛上风行一时,“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然而由于西昆体所追求的繁缛华美风格与后来庆历一代诗人的文学品位相左,故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还常常伴随着“浮薄”“浮靡”之讥。相应地,西昆体的代表作家杨亿、刘筠以及后来的晏殊等“后西昆派”诗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者往往将他们简单地视为西昆体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就笔者所见,只有朱刚在《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中对杨亿等人的文学史地位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后者指出,跳出古文运动的单一视角,“杨亿—晏殊—欧阳修”的发展线索比“柳开—穆修—欧阳修”更能代表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发展进程。不过朱刚先生的关注点在于士大夫文学,故其笔下的文坛领袖更接近于士大夫精神领袖,具体论述也侧重于对杨亿、晏殊仕途经历的分析,对其文学活动关注不多,而杨亿等西昆体诗人登上文坛领袖之位所依靠的不只是显赫的官爵,其影响力也不只表现在政治上。事实上,北宋前期的“文宗”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存在,与前代文坛领袖或有“名”无“位”或有“位”无“名”的情况不同,北宋前期的“文宗”兼具了“宗师”和“盟主”两重身份,名位与声望的结合,让这些士大夫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成为一代士人的精神领袖。不难发现,欧阳修之前的几位“文宗”都是西昆派诗人,作为文坛领袖,他们对于一时文学的影响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推广西昆体。本文便以文坛领袖的身份为切入点,对杨亿、刘筠、晏殊等人的文学史地位和贡献再做一番考察。
一、耸动天下:杨亿作为“文宗”的典范意义
文坛领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自觉”,文人群体中也开始产生对自身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于是一种基于文学成就和话语权力的精神领袖应运而生。文坛领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文学成就之上的精神领袖,即“宗师”型领袖;另一类则相反,其领袖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文学以外的政治权威,笔者称之为“盟主”型领袖。在宋代以前,这两种类型的领袖常常是分庭抗礼的:魏晋南北朝既有曹丕、张华、沈约这样位高权重的“盟主”,也有建安七子、二陆兄弟、大小谢等才华横溢的文学“宗师”;盛唐诗篇辉映千古,但其时文坛的执牛耳者仍是在朝的张说、苏環、张九龄等政治显宦。北宋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将科举和两制馆阁召试制度相结合,逐渐建立起一种以文才为导向的连续性、规范化的选举制度,文章之士可以凭借才华,沿着“进士高科—馆阁—两制—两府”的晋升之路跻身决策高层,成为兼具“宗师”和“盟主”两种身份的一代“文宗”。在北宋初年的两位文坛领袖宋白和王禹偁身上,“宗师”和“盟主”两种身份便已渐趋合一:仕途显达的宋白更偏向于“盟主”型领袖,然其科第名位最初也是凭借文才得来;苦于“无师友论议”的王禹偁属于“宗师”型领袖,但其也曾“三掌制诰,一入翰林”。“宗师”和“盟主”的合一趋势在真宗朝有了更为关键性的发展,杨亿的出现标志着集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宋型“文宗”真正形成。
杨亿是作为“神童”迈入政坛的。在太宗的赏识下,年方十一岁的杨亿得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在大部分人都还困于场屋的年纪,杨亿便已进入馆阁,获得了极高的仕途起点。真宗即位之初他被破格擢为左正言,经过短暂的外任后,咸平四年(1001)杨亿不试而受命为知制诰;五年后复掌内制,声望也随之达到了极点:“故翰林杨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为天下学者所服。”此后除了大中祥符六年的出走阳翟事件,杨亿一直都在朝中担任清流要职,且还曾于天禧三年作为副考官同知贡举,平日里也“喜诲诱后进,赖以成名者甚众”,“当时文士,咸赖其题品”。与王禹偁相比,杨亿的仕途显得格外耀眼,既没有长期贬谪在外的落寞,也没有“三入承明不知举”的遗憾,生前身后都不乏师友论议,是当之无愧的文坛“盟主”。
尤为可贵的是,杨亿并不满足于已有的荣誉和成就,而是从很早就有意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文坛带来新的风尚,景德年间编书之余的西昆酬唱便是这一想法的初步实践。唱和之风在宋初相当盛行,徐铉《翰林酬唱集》、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苏易简《禁林宴会集》以及宋白《广平公唱和集》都是当时朝廷名公之间的唱和诗集。但这些诗集都是将唱和作为馆阁公事之余的应酬消遣,而杨亿则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表明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态度:
余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余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弃,博约诱掖,寘之同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昌和,互相切劘。
杨亿声明他之所以组织这次唱和,并不是出于闲暇无聊,而是因为受诏编书一事恰好将他与志同道合的钱刘等人聚集在一起;而馆阁这一特殊的环境最吸引他们的也不是地清务简,而是其丰富的藏书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前贤,打磨诗艺。对杨亿而言,馆阁编书的经历是一次难得的机缘,他抓住这一机缘,网罗了一批最有声望的馆阁词臣,充分利用眼前的文化资源,用其既定的诗歌风格完成了一次集体写作。《西昆酬唱集》收唱和诗七十题,其中四十二题皆为杨亿所发起,超过半数。此时的杨亿已经是名动天下的辞章圣手,“文字所出,后生莫不爱之”。在其努力下,西昆体在真宗朝后期大行于世,“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要之,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杨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领袖作用: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政治机遇和人脉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了这场唱和活动,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文学影响力使这种新的诗风迅速成为文坛主流——既是“盟主”,又为“宗师”,风头一时无二。
此外,作为“文宗”的杨亿还表现出鲜明的自觉意识,这一点也与前辈迥异。王禹偁自负“他年文苑传,应不漏吾名”(《览照》),对自己的定位也只是《文苑传》之一,是很多文章才子中的一个,而杨亿身上则体现出了一种由“之一”到“唯一”的自觉。杨亿很早就开始对当时文坛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总结。所谓“闻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士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十编”,这部《笔苑时文录》(下文简称《笔苑》)应该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总集,选录对象既有诗,又有文,颇有当代《文选》的意味。宋初官方和私人都热衷于编纂大型图书,其中诗文总集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以及后来晏殊的《集选》等,然《文苑英华》的收录范围是南朝梁末至晚唐五代,《唐文粹》选录唐人古文,《集选》(已佚)是“大略欲续《文选》”,“删次梁陈迄唐”,唯有杨亿编选的这部《笔苑》是当代文人的诗文选集——在同时代的人还在整理前代文章的时候,杨亿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当代的文学成就进行总结,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现实观照意识。《笔苑》全本已失传,原貌亦不可考,不过《长编》所提到的杨亿日常“讽诵”的部分内容被门生黄鉴记录下来,收录于宋庠整理的《杨文公谈苑》一书中,即“雍熙以来文士诗”“钱惟演刘筠警句”“近世释子诗”三则摘句诗评。杨亿所点评的对象身份包括在朝士大夫、乡人、布衣甚至诗僧,世代跨度从“前辈”“当时侪流”再到“后来之著声者”,俨然一部诗坛点将录。又就风格而言,这三则诗评所涉及的诗歌恰好分别对应后人总结的“宋初三体”——“雍熙以来文士诗”大约可对应白体,“钱惟演刘筠警句”自是西昆体无疑,“近世释子诗”则是典型的晚唐体。在这里杨亿表现出了一种“置身事外”的鸟瞰式评论姿态,尽管也表现出了对西昆诗风的特殊偏爱,但他却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而是一个高于所有这些风格流派的存在。这种“置身事外”其实也是一种“唯我独尊”,杨亿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其所扮演的“文宗”角色是一种高于其他所有人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伴随着这种从“之一”到“唯一”的自觉,宋型“文宗”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斯文不坠:真、仁之际“文宗”的代际更替
在宋初的文坛上,杨亿的出现仿佛一颗流星,凝聚了一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但也不幸过早地陨落。杨亿去世不到两年,长年沉迷于修仙练道的真宗也离开了人世,继位的仁宗年仅十三岁,天圣、明道年间(1023—1033)的实际掌权者为章献太后刘氏(但为了与史书叙事保持一致,本文行文中在提到最高统治者时仍称仁宗)。就文学而言,真、仁之际是一个颇为寂寥的时代,杨亿的离去仿佛带走了时人的文学热情,宋祁就曾感慨:“天圣初元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唯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不过宋祁的话也指出了一点,在诗歌低谷的天圣、明道年间,正是刘筠、钱惟演、晏殊等西昆体诗人还在文学阵地上惨淡经营,“文宗”的担子也相继落到了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身上。
杨亿去世后,西昆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刘筠和钱惟演,但后者阿附刘后,热衷权术,又长期在外任职,对文坛的影响有限,故“文宗”的担子便落到了长期供职翰林又多次典掌贡举的刘筠身上。刘筠在真宗朝便以歌诗与杨亿齐名,有“杨刘”之称,文名盖过钱惟演,此时接替杨亿成为文坛领袖也是顺理成章。刘筠于咸平元年(998)进士及第,外任五年后还京,参加了杨亿主持的召试,得任秘阁校理;此后一直在馆阁供职,其间参与了杨亿组织的西昆酬唱活动;大中祥符七年为知制诰,天禧四年前后为翰林学士。杨亿去世后不久,刘筠因对丁谓一党不满而自请出京外任,次年(乾兴元年,1022)便被召回,复任翰林学士,这也标志着刘筠正式登上文坛盟主之位。在担任翰林学士之前,刘筠便曾于大中祥符八年以知制诰权同知贡举,此后又于天圣二年、天圣五年两知贡举,得贤甚多,有“知人”之名。至此刘筠“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名冠一时,是士林公认的“一代文宗”。
刘筠仕途起步较晚(年二十九方中进士),至此时已年近六旬。天圣六年(1028)八月,刘筠离朝,回到其素来喜爱的庐州做地方官,两年后病逝于此;而几乎同时,另一位久负盛名的天才神童晏殊回到了权力中心,接替刘筠成为新一代文坛领袖。作为“神童”,晏殊早年的经历几乎是杨亿的翻版:年少成名,十余岁便得以进入馆阁读书,大约而立之年便跻身两制词臣之列。这一时期的写作训练和声望积累,也使得晏殊在天圣中期接替刘筠成为文坛盟主显得水到渠成。曾巩《类要序》便称:“当真宗之世,天下无事,方辑福应,推功德,修封禅,及后土、山川、老子诸祠,以报礼上下。左右前后之臣,非工儒学、妙于语言,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公于是时为学者宗,天下慕其声名。”天圣八年(1030),晏殊知礼部贡举,拔擢了欧阳修、蔡襄、石介等一大批贤才,更巩固了其文坛盟主的地位。此后晏殊的仕途虽有起落,但自宝元初还朝之后便基本处于稳步升迁状态,庆历三年(1043)拜相后更是位极人臣。从天圣六年(1028)到庆历四年(1044)罢相,晏殊执掌文坛的时间长达十余年,直到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一代士大夫的崛起,其地位方有所撼动。
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刘筠与晏殊的代际关系问题。从年龄上讲,杨亿出生于开宝七年(974),刘筠生于开宝三年(970),二人年纪相近;而晏殊生于淳化二年(991),比二人小了约二十岁,是下一代人。但联系杨亿和晏殊的“神童”身份,三人在政坛和文坛上的代际关系与实际年龄并不一致。如同朱刚所指出的,“神童”出身让他们过早地步入了仕宦生涯的辉煌期,结交的都是比自身年长至少一辈的名公巨卿。例如杨亿在政治上始终倚靠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集团,与比自己年长十余岁的王旦、寇准交好;刘筠虽然年长杨亿四岁,但其于咸平元年(998)二十九岁时方才及第,步入仕途比杨亿晚了十四年,咸平五年参加馆阁召试时,杨亿还是他的主考官,故严格意义上来讲刘筠应是杨亿的门生;晏殊少刘筠二十二岁,但其年十五即获知于真宗,随即得授秘书省正字,进入馆阁的时间(景德二年,1005)仅比刘筠晚了三年。综合这些因素,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三人的代际关系应是杨亿最长,刘筠和晏殊同为后辈,且都得到过杨亿的提携奖掖;二人不仅主盟文坛的时间相近,具体作为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故本文将两人先后执掌文坛的天圣、明道年间合并为同一个时段进行集中讨论。
三、皇权与文柄的博弈:关于真、仁之际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
就文学成就而论,真、仁之际是一个较为平庸的年代,主流创作都笼罩在西昆体的遗风遗泽之下,前有杨亿的雄文博学,后有庆历诸公的大刀阔斧,刘、晏夹在其间,尤显黯淡无光,再加上文献材料的缺失,二公主盟文坛的功绩常常被忽视,乃至于被民间的古文家夺去了风头。其实,回顾北宋文学的发展历程,真、仁之际实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其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不乏暗潮涌动,经过刘筠和晏殊的努力,皇权和文柄之间的关系逐渐从杨亿主盟时代的尖锐冲突转向缓和甚至合作,以“文宗”为中介的“政治—文学”互动结构正式形成。
(一)申戒浮文——来自皇权的压力
杨亿等人先后成为“文宗”自然使得西昆体诗歌在真、仁之际风行一时,同时文章领域也是由所谓的“时文”——即杨亿等人提倡的同样以繁缛靡丽为尚的昆体四六——拔得头筹,“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西昆体的流行始终伴随着最高统治者的排抑:从大中祥符二年的《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到天圣七年的《戒浮文诏》,真、仁两代皇帝都采取了高压手段以扭转这种风气。这便使得作为西昆派代表的“文宗”与皇帝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有学者认为,西昆体本来就是一种逆时而生的文风,其绮艳缛丽的风格与真宗本人所偏爱的“雅正”背道而驰。不过就现有的材料看,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之前,真宗并没有表现出对杨亿及其倡导的西昆体诗歌的不满。学者常引《玉壶清话》所记的这则轶事来说明真宗对西昆体的批评: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 “关榆渐落边鸿过,谁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李维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轩。”孙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锁层楼。”钱惟演云:“置酒军中乐,闻笳塞上情。”都尉王贻永云:“河朔雪深思爱日,并门春暖咏《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上谓综曰:“并门在唐世,皆将相出镇。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题咏述怀宠行之句,多写于佛宫道院,纂集成编,曰《太原事绩》,后不闻其作也。”综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
刘综出镇并州是在景德四年六月,此时昆体诗歌已经流布朝野,备受追捧,真宗便借为刘综送行的机会编选了一份“平淡”的句图以示警告。但细读材料便会发现,真宗只是编选了一份句图而已,所谓“深究诗雅”“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都是笔记作者释文莹的说法;而《玉壶清话》作于元丰年间,上距真宗朝已有七十余年,其所猜测的真宗心理并没有太高的可信度。这则材料本身的叙事也疑点颇多:首先,文莹强调真宗选诗时于杨亿“止选断句”,似有贬抑之意,但实际情况是真宗于每人都是只选一联,从数量上完全看不出对杨亿的偏见。其次,对于当时人来说,能够名列御选句图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当初太宗曾经“御选(杨徽之)集中十联写于屏”,从而引发了时人的艳羡:“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中。”如果真宗真的有心要打压杨亿等人,又何必将其诗歌选入句图还特意叮嘱刘综将句图立于晋祠?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打压方兴未艾的西昆体,不如说是在为这种新诗风的流行推波助澜。再次,所谓“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的说法也站不住脚,真宗所选的八联诗皆近体,大都对仗精工(仅杨亿一联非对句),用典故者也不在少数,晁迥、杨亿、刘筠等人的诗句其实完全可以选入《西昆酬唱集》。所谓的“平淡”,其实是受送别的题材所限,再加上刘综出知的并州乃边关重镇,故众人大多选取了鸿雁、塞垣、营帐、暮角等边塞意象,使得诗歌所呈现的意境偏于凄怆肃穆罢了,与修辞风格的“平淡”不是一回事。故笔者认为,就真宗编选句图一事而言,其在景德年间尚未表现出对杨亿和西昆体诗歌的不满,相反,他还在利用手中的权柄为杨亿等人的文名宣传造势。因此所谓的“雅正”云云,只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一贯表态,与其对杨亿的赏识并不矛盾。杨亿在太宗朝后期就开始为尚为皇子的真宗草拟章奏,真宗继位后不久他便跻身两制,备受器重,直到唱和《宣曲》事发,真宗才表现出对这几位自己一手提拔的词臣的不满,并下诏谴责“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限制相关文集的雕印。史料所限,今人已无法得知杨亿对此诏的直接反应,但直到大中祥符六年前后,杨亿在评点当代诗坛时还不无得意地称“近年,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学者争慕之,得其标格者,蔚为嘉咏”,可见不但没有屈服于诏书的压力,还公然与皇帝唱反调,将真宗所认定的“浮靡”之辞称为“嘉咏”。有意思的是,在皇帝明确表达了对“文宗”不满的情况下,大批的士子仍然选择追随他们心中的文坛领袖杨亿,而对皇帝的不满置若罔闻,直至天圣年间,西昆体仍风行一时。毕竟对于尚未踏入仕途大门的普通士子来说,皇帝遥在云端,“文宗”才是决定其前途命运的恩师座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心生不满也是自然的。杨亿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打击,但后期的真宗开始流露出对他的不信任也是事实,其中天禧三年的科场风波尤为值得关注。此年由钱惟演知贡举,杨亿同知贡举,就主考官的设置而言无疑是偏重西昆体的,但同时真宗又任命属于王钦若一党的陈从易主持“别头试”(即为考官亲属举行的单独考试)。陈从易“颇好古,深摈亿之文章,亿亦陋之”,此次别头试的题目有云:“策问时文之弊,曰:‘或下俚如《皇荂》,或丛脞如《急就》。’”显然,他是在有意引导考生抨击杨亿等人提倡的“时文”。参照王钦若一派的行事风格,这一做法即便不是真宗授意,也起码得到了皇帝的默许。不过此次考试因考校问题引发了下第举人的闹事,为平息众怒,主考官皆被降职,其中陈从易的考校结果尤为不堪,对“时文之弊”的讨论也便不了了之,真宗借助科场削弱“文宗”权威的计划最终落空。
但皇权与文柄的矛盾并没有随着真宗的去世而了结,不久天圣年间便又发生了一次“申戒浮文”事件,使二者的关系更为紧张。天圣六年九月,仁宗任命陈从易和杨大雅为知制诰;次年下诏再次对所谓“浮华”时文进行申戒。陈从易已见于前文,杨大雅亦以好古著称,二人此时皆已年过六旬,忽得进用,显然不是正常的晋升。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久负盛名的刘筠离朝外任,晏殊刚刚返京,尚未站稳脚跟,在这个时候朝廷忽然任命两位“好古”的耆旧为知制诰,其用意颇可玩味:就其“以风天下”的目的而言,仁宗似有意将陈、杨二人扶持为新的“文宗”。不过仁宗的这一计划终究还是落了空,事实证明,陈、杨二人才力并不足为一代“宗师”。他们久不获用,除了“好古”“违世”之外,文才不够突出应该也是重要原因——对比王禹偁亦以好古著称,并不影响他“三掌制诰,一入翰林”。在天禧三年科场事件中,陈从易选拔出的两名“别头试”进士被陈尧咨评为“文理荒缪”,可见其人之才并不足以服众。这一事件从侧面证明了宋型“文宗”集“宗师”与“盟主”于一身的特点,单靠政治上的造势并不能够干预“文宗”的人选。
(二)科场改革——“文宗”的智慧
尽管真、仁两代君主对“文宗”话语权发起的挑战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些举措无疑给刘筠和晏殊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也将西昆体推倒了风口浪尖之上。宋型“文宗”是“宗师”与“盟主”的统一,而政治名位是其“盟主”身份的重要基石,故从本质上来讲,“文宗”对皇权是既独立又依附的关系。皇帝不能凭一己之意志动摇“文宗”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文宗”也不可能与皇权永远对抗下去。杨亿与真宗的针锋相对未免有意气的成分,但到了仁宗朝初期,在皇权持续施压的情况下,如何平衡皇权与文柄的关系成为刘筠和晏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刘筠、晏殊未尝不在寻求转变。除了在西昆体创作方面的贡献,刘筠以天圣二年“以策论升降天下士”知名于世。历来对此事的研究都侧重于影响,很少有人关注刘筠为何要这样做,至多是追溯一下科举重视策论思想的渊源。但有人呼吁重视策论并不意味着作为“文宗”的刘筠就要顺应这一潮流,毕竟没有迹象表明刘筠此前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何况其本人还是西昆派“时文”的缔造者之一。联系“申戒浮文”背景,笔者认为,刘筠之所以突然改弦更辙,重视策论,应当是与真、仁之际针对西昆体的高压气氛有关:他是在有意分散时人对科场诗赋的关注度,以此来为西昆体“降温”。对于刘筠来说,此举不失为一种相当机智的“曲线救国”:既顺应了当朝的风向,又不必对西昆体本身发起冲击——在叶清臣以策得高第的同时,另一位“后西昆派”的代表作家宋祁也金榜题名,其省试《采侯诗》传诵一时,流传下来的断句“色映堋云烂,声迎羽月迟”仍是西昆体所崇尚的华丽风格。宋祁本人后来还怀着感激的口吻回忆“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如此看来刘筠对宋祁的赏识还高于叶清臣。但对当时人而言,叶清臣的案例无疑更有示范意义,天圣五年春闱,仁宗又特意将外任的刘筠“驿召”回来担任主考,几天后又特意下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并将省试逐场淘汰的旧制改为三场考完后通同考校。显然,刘筠的努力得到了仁宗的认可,长期以来皇权与文柄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不久后的天圣八年,晏殊受命知贡举。与杨、刘相比,晏殊和西昆体的关系要远得多,其本人并未参与西昆唱和,对这种文风大约只是欣赏和模仿,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且愈到后期,晏殊愈为重视韩柳的古文,在与女婿富弼的书信中盛称韩柳文章,言语之间还对早年在馆阁时众人“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颇为不满。因此,天圣年间的晏殊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在戒浮文的问题上与皇权对立。天圣八年的贡举所留下的材料不多,但此年登科的欧阳修、石介、尹源、蔡襄等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古文家,从中大约可以窥见晏殊取人的标准,这一批士人的及第无疑给当时的士林确立了新的典范。此外晏殊还积极领导教育复兴,天圣四年的应天府兴学直接促成了北宋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兴学热潮。事实证明,天圣年间的文坛风气确有转向,西昆体“时文”落潮,“学者稍趋于古焉”。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皇帝与“文宗”之间彻底实现了和解,“皇帝—文宗—文坛”的权力互动结构正式形成,“文宗”充当了皇帝与文坛之间的中介,皇权借助“文宗”的影响在文学场域中获得了一部分话语权,而“文宗”也留住了皇权的支持,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四、古文运动:皇权与文柄合作的成功范例
如上文所言,自从天圣后期始,皇帝和“文宗”在重视策论、推行古文方面已达成一致。一方面,“文宗”顺应皇帝的意愿对科举、教育进行改革,通过提高策论的地位而为皇帝不喜的西昆体诗文“降温”;另一方面,皇帝也对“文宗”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支持,天圣年间后没有再发生类似“申戒浮文”的事件。这种合作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继任“文宗”欧阳修领导下的古文运动的成功。
欧阳修为晏殊之后“文宗”的继任者,庆历之后既“以文章擅天下”,又长期担任翰林学士,其间“所荐皆天下名士,无有不在高选者”,一时“世莫敢有抗衡者”。不唯如此,欧阳修还明确向友人表达过对杨、刘的景仰,“杨刘风采,耸动天下”之语便是出自其口,可见其对“文宗”的想象便是以杨亿等人为模板的。表面上看,古文运动的文学追求与西昆体背道而驰,但实际上,欧阳修为推行古文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可以在西昆体前辈那里找到源头。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杨亿曾“闻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士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十编”;而据曾巩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所言,欧阳修也曾编纂过一部名为《文林》的当代文选,“悉时人之文佳者”。联系欧阳修对“杨刘风采”的向往,其编辑《文林》很有可能是出于对杨亿《笔苑》的效仿,都是有意在对当代文学做出总结,并为时人创作提供范例。此外欧阳修在庆历年间进一步将省试流程改为策、论、诗赋三场试,逐场定去留,进一步抬高策论的地位,使其成为进退的关键,这一做法也与天圣年间刘筠、晏殊的科场改革一脉相承。这些实践经验使欧阳修对科场的导向作用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嘉祐初年险怪的“太学体”风行一时,欧阳修所采取的对策也是通过科场进退实现对不正之风的扭转。与刘、晏的“立而不破”相比,欧阳修此次的做法是“破而后立”:将此前盛行的“太学体”一并打倒,改立苏轼等人平实流畅的文风为新的典范——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他对科场积弊早有不满,故借此次主考的机会“痛革之”。此榜一出,立即在士林中引起了强烈震荡:“一旦喧然,初不能遏”;“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依惯例,若有下第举子闹事,朝廷一般都会安排复查试卷,重新定取去留名次,例如上文提及的天禧三年科场风波。但受益于刘、晏苦心经营下形成的皇权与文柄的良性合作关系,这一次“文宗”欧阳修得到了来自皇权的全力支持。仁宗皇帝一反先例,不仅没有安排复查,还在殿试中特赐欧阳修选定的进士全部及第,无一黜落,以示立场。如此一来,闹事风波也不了了之,再加上这一榜进士的确“颇当实材”,反对的声音逐渐消弭,科场风气也随之一变:“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曾未数年,忽然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真、仁两代皇帝的复古心愿也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古文运动的最终成功固然仰赖于欧阳修本人的才学和魄力,但“文宗”的权威和来自皇权的支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皇权与文柄的这种通力合作的关系正是西昆体“文宗”所留下的宝贵遗产。
综上,就北宋文学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言,杨亿、刘筠、晏殊等西昆体代表诗人的贡献绝不仅仅是开创了一种诗风。作为执掌文坛的领袖人物,杨亿兼具“宗师”和“盟主”两重身份,开创了由“文宗”领导文风走向的文学生态。但杨亿的强势也招来了来自皇权的打压,其继任者刘筠和晏殊一方面在文学低谷期坚持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则致力于通过制度改革来缓和皇权与文柄的紧张关系。在两位“文宗”的经营下,二者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后来欧阳修领导下古文运动的成功便从这种合作关系中受惠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