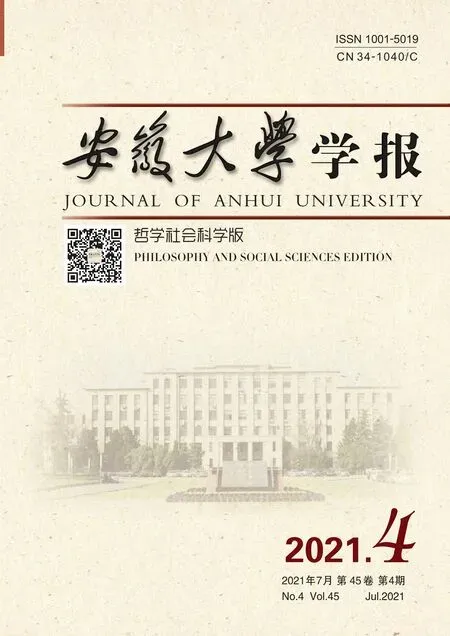从“畏”到“无聊”
——从情调的角度理解海德格尔对生存论视角的修正与补充
张晋一
海德格尔毕生都在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其前期的思考最终凝结为《存在与时间》这部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马迎辉认为:“从这种其本质就是‘去—存在’的存在者出发探讨存在问题构成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工作的最重要的特征。”但在海氏之后的研究中,他修正了《存在与时间》的视角,不再从此在生存论的视角出发探讨存在的意义。在这种转变中,一个引起注意的地方是海氏在1927—1930年间对情调的选取及描述发生了变化。从存在论—生存论的角度来说,不仅情调是此在在世敞开自身的必要条件,而且对“本真的”情调的赢得就是一种现象学还原。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两种现身情态:怕和畏。畏是此在在世展开的本真的现身情态,而怕是畏的非本真变式。在畏中,世界向此在敞开,此在不对任何存在者感到怕,而是对世界的敞开本身感到畏。借由畏的情调的开启,此在才能使自己先行向死存在,才能将自身从日常状态的种种由常人支配的可能性中掇取出来,还原至本真生存的可能性中。在《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一文中,海德格尔表明,此在被“无聊”的情调所调谐(stimmen),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者被还原了,此在被带到“整体中的存在者”(das Seiende im Ganzen,存在者整体)面前,继而由“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脱落导致的虚无以及虚无“无之不化”的运作机制通过畏的情调而获得开启,海德格尔借此描述了“存在论差异”的差异化运动。及至《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1929/30),海德格尔彻底放弃了对“畏”的阐释,而是对无聊展开了三个层次的分析,分析最终表明,在“深度无聊”的基本情调的开启下,具体的存在者和世界都被还原了,一方面此在与“作为自行拒绝着的整体中的存在者”相遇;另一方面此—在领会了在“此”存在之“自由的必然性”。
我们看到,由不同情调引导下的现象学还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海德格尔对不同情调的选取,甚至对于此在的生存论视角的修正,其背后涉及了什么样的考虑?新的还原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扭转了从此在生存论的视角出发对存在一般意义的研究思路?深度无聊的“深度”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学界既有的研究来看,实际上,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从“现身情态”到“基本情调”,这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甚或是被等同使用的,研究者将“畏”与“无聊”进行比较分析时也并未发现或突出其中的差异。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生存论的、通过畏这个现身情态进行的此在分析与后来在“深度无聊”这种基本情调主导下进行的此在分析是有差异的,或对“基本情调”何以成为“基本的”产生疑问,但其未能从学理上给出海氏术语变化的原因。此外,所有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暗示,海德格尔对情调问题的阐述可以带来异常广阔的理论景观,特别是就情调是此在在世展开自身的方式这一点而言,如果此在的这一展开方式发生转变,那么此在与世界、时间性、存在者乃至与存在的关系必将随之发生改变。
本文意图发掘从“畏”到“深度无聊”亦即从存在论上的现身情态到存在状态上(ontisch)的情调这一变化的学理基础和根源,并且试图展示此在与世界、时间性、存在者乃至与存在的关系的变化。这涉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即一般形而上学(存在)与特殊形而上学(最高存在者)的平行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展示出由不同情调所引导的理论景观之间的差异。
一、畏与深度无聊及其差异
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在“预先考察部分”就明确地表述:“哲学的把握活动(Begreifen)基于某种被感动状态(Ergriffenheit),而这种被感动性又在于某种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中。”但在《存在与时间》中“基本情调”这个“术语”只出现了一次,海氏甚至说“对……基本情调的分析”不在基础存在论的计划内。
难道,在基础存在论中真的只有“现身情态”吗?它与“基本情调”不相容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偶然道出”的这样一句话难道是实情吗?《存在与时间》中的“畏”的情调(现身情态)与后来《形而上学是什么?》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无聊”的(基本)情调有差异吗?如果有,这种差异的核心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笔者将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介绍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畏和(深度)无聊的描述并分析海氏于其中的运思思路,第二步是探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一)《存在与时间》中的畏的现身情态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揭示出现身情态/情调、领会与沉沦(此三者由话语分环勾连)共同组成了此在的展开状态,此在处于操心的整体性结构中。操心的结构统一于时间性,此在正是作为时间性而“存在”。此在处在生存活动中,首先,这意味着此在同时在存在状态上(ontisch)和存在论上(ontologisch)存在;其次,此在生存在世界上,即“在—世—之—在”是此在先天的生存结构;最后,只有从此在之生存的整体性上着眼,才能将此在的本真性从此在的生存的诸种可能性中掇取出来。
此在取得本真性的可能性在于,它必须先行到死中去,而向死存在则必须由畏开启出来。由于领会和现身共同构成此在之“此”,此在在面向死亡的终结存在时,一方面必须从此在的良心公开出来的呼声中听取自己本真的可能性存在,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畏的现身情态“能够把持续而又完全的、从此在之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存在中涌现出来的此在本身的威胁保持在敞开状态中”。只有如此,此在才能以“决心”的方式进行自身筹划,在存在论上以本真状态展开自身。畏是此在以本真状态在世的可能性的条件,此在没有畏就谈不上向死存在,此在向本真状态的筹划以及生存论环节的组建都必须依赖于畏这种现身情态。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情调和现身情态指的是一个东西。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在存在论上用现身情态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在存在状态上乃是最熟知和最日常的东西:情调(Stimmung);被调谐状态(Gestimmtsein)。”在对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生存论的分析中,出现了怕和畏两种现身情态。“怕”同“畏”虽然都是存在论上的现身情态,但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状态,前者处在非本真的日常状态中,“怕之所怕”总是指向一个具体的存在者。而畏则开启了此在的本真状态,海氏对畏的界说如下:
畏之所畏为世界之无;而世界之无不等于说:在畏中似乎经验到世内现成事物的某种不在场。……操劳的期备找不到任何东西可由之领会自己,它探入世界之无;而当领会撞上世界,领会却被畏带到在世之为在世面前了……畏之何所畏却已在“此”,那就是此在自身。
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也就是说,在畏的现身情态中,世界显示出全无意蕴的性质,即此在不会在任何一个存在者那里感觉到威胁或阻抗,不确定的、不在任何一个地方的畏向此在袭来。但是,畏之所畏者也不直接就是虚无(Nichts),而是作为上手之物的虚无(Nichts von Zuhandenem)也即作为一般上手事物的可能性的(Möglichkeit von Zuhandenem überhaupt)世界本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之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能通过遍历且加总存在者的方式来揭示,它只能以否定褫夺的、被拒绝的方式“在整体中”呈现。畏的现身情态揭示的是世内事物的无意蕴性(Unbedeutsamkeit),揭示的也就是此在“单纯的”在世(In-der-Welt-sein)这回事;与此同时,畏在存在论上把作为一切上手事物可能性的意蕴整体的世界之为世界揭示出来。
(二)《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的畏与深度无聊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提到了深度无聊与畏。深度无聊是情调的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 der Stimmung),也是此—在的基本发生(Grundgeschehen)。在深度无聊中,某人莫名地感到无聊,“寂然无声的雾弥漫在此在的深渊中,把万物、人以及与之共在的某人本身(einen selbst)共同移入一种漠然状态(Gleichgültigkeit)中”,此—在与“整体中的存在者”(das Seiende im Ganzen)相遇。
而畏成为此—在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在畏中,某人惶惶不安(unheimlich),其间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宁静,万物和我们本身都沉沦于一种漠然状态(Gleichgültigkeit)之中,此在感受到畏的震荡,其中发生着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脱落,虚无伴随着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脱落运动前来照面。
由此看来,畏比深度无聊似乎更加具有深度:
沉降着的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让脱落的指引……亦即对脱落着的整体中的存在者的指引——无就是作为这种指引而在畏中簇拥着此在——乃是无的本质,即:无化。
从“被给予”的现象上看,深度无聊启示有(整体中的存在者/存在者整体),而畏启示无(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脱落与虚无被给予)。而前文已经揭示,“虚无”本身并没有在《存在与时间》中出现,因此,畏开启了存在论—生存论中并没有出现的“虚无”。从“被给予”的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人或物或存在者已经被还原了,接受者是此—在。这个此—在并不特指人,它是人的此在(das Dasein des Menschen),即嵌入到无中的状态(Da-sein heißt: Hineingehaltenheit in das Nichts)。
尽管相对于深度无聊,海氏更加凸显了畏作为一种基本情调对虚无的揭示作用,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事实上,这里有三个超出了《存在与时间》中生存论还原的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对于接受者的此—在而言,在深度无聊和在畏中的“情调氛围”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种对存在者——包括对象存在者、人以及与人共在的“某人”本身——的不加区分的漠然状态的还原在“深度无聊”中已经完成了,这一点暗示了畏的功能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被深度无聊彻底替代的可能性。
其次,虽然整体中的存在者是贯穿每一个具体存在者、支撑每一个具体存在者的存在者,但是当它作为整体中的存在者出现时,其并不具有预先设定好的结构和层次,如海氏的描述,寂然无声的烟雾,将一切都变得不相关起来。因此此—在不能把它当成现成存在者去把握,只能倚赖否定和拒斥的形式,因此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被给予只能是它的脱落被给予。在此,“畏”相比于《存在与时间》中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它不仅仅在生存论中以否定的形式揭示了此在生存的在世之在,而且能够以非对象化的方式,在超出此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指示出一种无区分状态的整体中的存在者,这个整体中的存在者赋予了一个存在者实存的可能性以及构型一个世界的可能性。这里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转变,即海德格尔不仅仅在存在论上讨论现身情态,而且在综括了存在论与存在状态的意义上讨论了基本情调——它直接地指向了此在的基本发生。
最后,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提及的“整体中的存在者”这个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没有出现。而根据方向红的研究,海德格尔对“整体中的存在者”这个概念的发现和使用,对于理解其哲学至关重要。“整体中的存在者”是世界实存的基础,也是此在生存的必要条件。简单来说,“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者”,而“整体中的存在者”贯穿和支撑了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者。整体中的存在者让此在成为一个“之间”(inmitten)的平台,它使得此在能够与存在者建立相关性并进一步实施筹划。只有基于对“整体中的存在者”的理解,“存在论差异”才表现为“不着的运动”,表现为“存在论的差异化”,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现成的存在与存在者“不同”。
(三)《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深度无聊”
在这个文本中,海德格尔完全没有提到畏,但与《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的内容相比,深度无聊则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这一点体现为深度无聊不仅承接了《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的深度无聊的“功能”——作为一种基本发生与整体中的存在者相遇,而且,《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的畏的“角色”现在也彻底由深度无聊所扮演,深度无聊成为此—在在存在论与存在状态上的基本发生。原因在于:当海德格尔发现“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被给予”和“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脱落的被给予”是一回事的时候,他就无须像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那样,对事实上的同一个步骤分别地用“深度无聊”和“畏”这两个基本情调来进行标画。
在深度无聊中,它使某人无聊(Es ist einem langweilig,它对于某人来说是无聊的)。在其中,深度无聊的两种功能,即放空(Leergelassen)和羁绊(Hingehalten)让此—在沉陷于其中,存在者以及此—在本身都不是无聊的原因,这是一种极端的临界经验。整体中的存在者自行拒绝,它以自身拒绝的方式在漠然状态(Indifferenz)中呈现。
正如《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文本所示,此—在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并不直接就是人,而是意味着人之在“此”的发生。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中的此—在,向外震荡到其时间性的时间视域之幅度,并且这恰恰就只能向内震荡到本质行动的当下即是(Augenblick)”。深度无聊正是时间视域对此—在的吸引,使被吸引的此在被逼进入当下即是之中。作为此—在生存之真正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这种生存只有当其处于整体中的存在者之中时才是可能的,而这种“在整体中”本身在吸引的视域中恰恰在整体中拒绝,亦即“在整体中”只能以否定和褫夺的方式被给予。
在这种情况下此—在作为“我”已经被还原了,作为此在的生存论本质的“去—存在”和“向来我属性”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无法为整体中的存在者提供一种生存论结构,剩下的只是此—在的基本发生——此—在,作为在“此”存在。时间之视域在整体中敞开,这个在整体中敞开的幅度,就是世界。同时时间之视域向此—在敞开,逼迫此—在进入“在整体中”生存的本质的当下即是(Augenblick),在其中此在必须要面对此在的存在以及不得不存在的可能性。世界由之一道被还原为世界的源初发生,此在“首先与通常”活动于其中的(周围)世界,坍缩为世界之为世界的展开的可能性。
(四)“畏”与“深度无聊”的差异
在对海氏的文本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基本的分析之后,现在可以讨论“畏”与“深度无聊”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是的话,那么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必须承认,《存在与时间》与《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都力图以一种整全的、通过与存在者进行争辩的方式获取此在的本质,但我们不应被二者意图上的相似性所蒙蔽。鉴于其行文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从“畏”到“深度无聊”的过渡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畏”与“深度无聊”,哪一种情调是更重要的?这取决于我们的关注重点。当关注重点在于“此在作为‘之间’的参与或生存筹划活动”,对“畏”的承认就会对此在更加重要;当关注重点在于“刻画此在和世界的动态关系以及存在论差异的动态过程”时,“深度无聊”则具有存在论—存在状态上更加深刻的意义。因为深度无聊不仅属于此在的生存活动,它同时内在地要求此在停止对存在者的操劳以及对意蕴整体的组建,且无须执着于回到此在的自身性——由此“整体中的存在者”才能在不进行预先规定的情况下自身给予,并进入存在论差异的差异化活动中。
就《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的内容来看,此在在深度无聊的开启下已经进入了对任何具体的存在者都等然视之的状态,存在者和世界不再以有意味的方式向我们“表达”。如果我们承认,整体中的存在者只能以否定和褫夺的方式被给予,那么,在自行拒绝着的整体中的存在者的开启下,一切都索然无味,“畏”如何对深度无聊之“深度”作出“反应”呢?“畏”在“深度无聊”中是无力的,“畏”在此情此景中失去了向我们“说话”的可能性,它只能将一切可能的话语保持在可能性的克制之中,在这一层面,“畏”失去了其在《存在与时间》中那种能将自身性揭示出来的独特权力,也没有为“良知的呼唤”留出空间。《形而上学是什么?》中的“畏”的悖谬性正在于它把还原的成就交付给了“深度无聊”所揭示的要素,同时还将此在限制在了一种“有”但僵硬的状态中。深度无聊之“深度”不就在于,让整体中的存在者在移开的同时簇拥,在拒绝的同时逼迫,并且在世界坍缩的同时逼向此在的必须在“此”吗?因此可以作出结论,无论从形式上(为了便于区分)还是实事上(从还原的结果来看),都应该允许人们将《存在与时间》中的畏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深度无聊视为还原的两个步骤。
因此,如果我们将“畏”的现身情态及其开启的效应限定在《存在与时间》的框架内部,那么可以认为“畏”中所取得的本真性乃是着眼于此在生存论时间性的整体,而作为基本情调的深度无聊所着眼的乃是此在不得不接受其在此存在,也就是其生存的本质可能性的整体。对存在的领会、对本真性的赢得(“畏”的给予)有赖于此在的实际生存,此在的实际生存已经以“有”一个现成的自然、“有”一个作为“一般上手事物的可能性”的世界为前提了,而基础存在论上的现身情态(畏)必须要奠基在此在的被抛性——世界也是在此在的被抛性中才能一道被给予——之上,而使此在的被抛得以可能与使此在在“此”存在得以可能是一回事,接受此在的被抛性就是接受此在在“此”存在,这个“此”同时包含有存在论—存在状态上的双重意蕴。由此,足以证明参与此在基本发生的深度无聊比作为现身情态的畏更具深度,两者之间有质的差异,畏和深度无聊(下文简称“无聊”)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还原方式。
二、情调转换对理论图景的更新
理解了这两种情调的差异后,我们就能以更加动态的眼光看待基础存在论中此在与世界、时间和存在者的关系,并且由此可以发现,由深度无聊所引导的理论景观已经超出了《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视角”。
(一)此在与世界的关系
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世界”的定义有四种,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是后两种定义:
3.世界……被了解为一个实际上的此在作为此在“生活”“在其中
”的东西。世界在这里具有一种前存在论的生存上的含义……4.世界最后还指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生存论上的概念。世界之为世界本身是可以变为某些特殊“世界”的任何一种结构整体,但是它在自身中包含有一般的世界之为世界的先天性。世界这个词作为术语,我们专门在第3项中规定的含义上使用……
尽管生存论视角是在存在论上对此在的生存进行分析,但生存论的视角处理的大多是此在“首先与通常”活动于其中的、存在状态上的(周围)世界(含义3)概念,此在通过畏赢得的本真的整体性可以说是对周围世界在整体上的否定。尽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畏开启了世界之为世界(含义4)的存在论上的先天,但世界之为世界的塌陷和敞开、世界之为世界的发生根本上只能经由无聊情调的开启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因为《存在与时间》只对世界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即上手之物的虚无/不可能性,如此既没有涉及其存在状态上的基础——整体中的存在者,也没有在存在论上对世界的世界化活动进行展示。
回顾“世界”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定义,“我们将这个‘在整体中’的幅度,这个在深度无聊中敞开的幅度,称作世界”,可以发现,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与时间》中存在状态上周围世界的含义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因此仅仅就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概念”。确切地讲,世界之为世界的世界化(运动)震荡在存在论差异的运动中,它当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存在论上的概念,甚至其比《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概念更加形式化了,但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以一种生成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存在论上的“概念”,它成了世界筹划自身的源初运动。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生存的筹划活动必然奠基在世界本身的筹划之上,这也对应了《存在与时间》结尾一连串发问中对“存在论上”优先于“存在状态上”的怀疑。所谓世界的筹划,就是世界闯入存在论差异的运动中,通过让主宰的方式主宰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敞开,这种主宰活动受到筹划的约束,源初的同一性随着世界的敞开实现为具体的存在者。
此—在的实际性与世界的根据(筹划的约束)绝不在于世界,更不在于此在,毋宁说恰恰在于存在之多义性未分裂之前的源初同一性。世界的世界化活动在存在论上根据源初的同一性持续不断地差异化为万事万物,分化为特定的具体的存在者,尽管此在已经生存在一个作为分化结果的世界之中,但这绝不意味着此在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回溯到此在(同时也是世界之为世界)之基本发生。由此可以判断,不仅世界的塌陷与敞开在生存论视角中是无法得到描述的,“存在论差异”的差异化活动在生存论中本质上也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
差异化运动就是不化(nichten),而差异性指的就是存在和整体中的存在者之间的绝对的差异,如果将“时间在整体中敞开的幅度(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系统,那么整体中的存在者则是这个系统实际存在的基础,存在则“位于”该系统的“外部”,存在绝对地超越于、异质于这个“系统”。对于个别存在者而言,它在存在状态上有赖于整体中的存在者的支撑,有赖于世界的实际存在;它在存在论上则以它的规定性为前提,即以存在为前提。
(二)此在与时间的关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区分了时间与时间性,这也就意味着,在生存论的视角下,此在由畏所引导的先行向死,只能取得本真的时间性而非与存在相应和的时态性(Temporalität,时间状态)。
然而在无聊中,海氏并没有刻意地区分(时态性意义上的)时间和时间性。事实上,时间本身可以作为视域给予此在,它同时导向了“此在的存在”与“世界的敞开”:
一切存在者在其“什么”和“如何”中都同时拒绝,我们说:在整体中[拒绝]。现在就是说:在一个原始统一的时间视域中。这个“在整体中”显然只有当存在者被一个、同时又是三维的时间视域所包围时才是可能的……
它使某人无聊。这种此在在其中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在的情调,具有被吸引的特性,这个吸引者无非就是时间视域……时间,向来就是此在自身在整体中存在。这种整体的时间作为一个视域而吸引着。被时间所吸引,此在无法发现存在者,存在者恰恰就在这种吸引着的时间视域中,作为自行拒绝着的东西在整体中宣告出来。
由此,此在无聊中、整体中的存在者的自行拒绝与此在被时间的视域所吸引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在这里看得应该更清楚,即使是在无聊中,海德格尔也正是依循时间线索阐发存在的意义。同时,此在在统一的时间视域本身的吸引下,无须也无法考虑时间的到时是否是本真的,因为任何具体的存在者都已经被还原,整体中的存在者也保持为自身拒绝的状态。对于此在的生存而言,时间性当然是更匹配的术语。因为只有在世的活动(和存在者或人打交道)才能给予此在时间性的节奏,客观的世界时间才能从生存中以约定的形式诞生。如果仅仅是时间自身流动而不给出存在者,那么由于此在失去从存在者方面领会的“节律”,此在是无法识别出时间视域的,或者从生存论上说,时间将无法“伴随”此在的生存,此在无法将其视为“我的”。因此如果说生存论视角下此在能够找到本真的自身,那么在无聊中此在则可以“遭遇”作为时间的时间。
(三)此在与存在者的关系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整体中的存在者”在生存论框架中是没有位置的。生存论是从此在首先与通常存在于其中的日常状态开始的,世内存在者只有上手和现成在手两种状态,共在则完全由常人所支配。世界完全在一种匀质化的平均状态(Durchschnittlichkeit)中展开,完全谈不到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之存在。极端地说,即使是在畏中取得了本真性的此在,在进入了本质性的当下即是后,便不可避免地立刻消散(生存)于周围世界之中,重新回到那个“首先与通常”存在的非—本真的本真状态之中。
然而,在无聊的开启下,此在进入了一种漠然状态(Gleichgültigkeit)或漠然无别(Indifferrenz)的状态,这种状态与流俗理智所处身的平均状态不是一回事。前者有能力揭示存在者的存在,后者只能与现成的存在者打交道。存在者前述谓的敞开具有一种“在整体中”的特点,如果此在不是一开始就被这种“整体”所环抱,它是不可能发现存在者更遑论与存在者打交道的。
无聊中涉及的无差别性实际上关涉的是此在在发生上的根据,是使此在的生存活动得以可能的东西:“此在中的基本发生
,我们通过以下三个环节
来记录:1.约束之对峙;2.补全;3.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第一,如果人们意图运用逻各斯对存在者进行揭示,那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亦即言说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者自身的敞开,每一次存在者给出自身都是带有遮蔽的解蔽,因为每一个存在者都是在其具体实现、其现实化、其存在的“此”中的显示,它在显示的过程中就给予逻各斯约束。第二,对每一个存在者的揭示都默不作声地援引了“整体”,援引了“存在者的存在”与“整体中的存在者”,并没有孤立的被认识把握的存在者,存在者只有首先“在整体中”被补全才能在生存活动中被此在领会。第三,只有满足了上述两点,人们才能用逻各斯揭示存在者的存在。
前文所述的此在与世界、时间、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显示出无聊所开启的基本发生是如何超出了生存论的视角,海氏甚至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结尾处隐晦地批评了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路:
三方面描画的此在之基本发生的原始结构,我们不能通过援引此在结构(Daseinsstrukturen)来装配(zusammenbauen),而是相反,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发生之内在统一,并恰恰由此才会谋得对此在之基本建构(Grundverfassung)的洞察。
如果作为建构者的此在在世界的基本发生中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海德格尔前期构筑的生存论视角乃至《存在与时间》的局限。
三、余论:从生存论视角到生存论与元存在论视角的统一
综上所述,无聊是对生存论还原的再次还原,基础存在论—生存论的视角被还原至综括了存在论—存在状态的更加整全的视角,如此便彻底去除了生存论可能带来的激进化的主体性倾向。
由此,还有一些伴随而来的结论。从无聊这种更加动态的、彻底的无条件性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此在的生存论活动已经被“此在—世界”的之字形解释模式形式地规定了,而无聊开启的等然视之的漠然无别(Indifferenz),恰恰对应于存在自身之同一性所包含的诸复多性的无差异性(Indifferenz)。畏处理的是此在的“死亡现象”,但由于此在的“本质”是生存,死亡悖谬地阻止了此在的生存,因此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死亡是此在“不可能的可能性”,而无聊巧妙地“绕过”了并且处理了死亡问题——在深度无聊中,由于“主体”被还原,此在其实已经进入了拟死亡(Quasi-tod)的状态。生存论中的呼声现象是由此在向本真的自身呼唤,但此在因存有之声(Stimme des Seyns)被调定的(gestimmt)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则完全可以不依赖于此在。由此我们可以联系海氏中后期“克服形而上学”阶段的说法,《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提到的源自莱布尼茨的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无?”不是根本性的提问,因为这个问题仍旧是着眼于存在者。综上所述,“畏”向“无聊”的还原,其实质是对“存在与时间”的又一次重演(Wiederholung)。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海氏对情调的改换源于根本性的视角的偏转,是继《存在与时间》之后的一次思想转向。从畏到无聊,从现身情态到基本情调,从生存论到此在的基本发生,这种转变意味着海氏后来在整体上超越了其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探索。此在相对静态的和形式化的“生存论视角”无法切入存在论差异的差异化运作,而存在者作为整体中的存在者的存在和源初的时间视域,就代表了深度无聊最终所触及的“深度”。
最后,尽管本文根据海德格尔1929—1930年的思路对勘了此在的生存论视角,但这些由于视角的转变带来的突破,绝不意味着《存在与时间》中所处理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对畏的描述,通过畏而进行的还原归根结底隶属于对此在的生存论描述,同时隶属于超越论哲学的谱系。然而这只是第一步,以“在整体中的存在者”为主题的“元存在论”标志着一种与基础存在论不同的探索模式。虽然在元存在论以及我们在此所论证的“无聊”的还原中,海氏确实回返到某种“存在状态上”,但却绝不是返回到《存在与时间》中提及的“现成在手状态上”,而是由此达到一个在发生上更源初的阶段,实现了向存在论—存在状态上的更深维度的敞开。与此同时,海德格尔的目光不仅停留于此,他已然深入到了统一存在论—存在状态的层面,这种统一则是还原的最终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