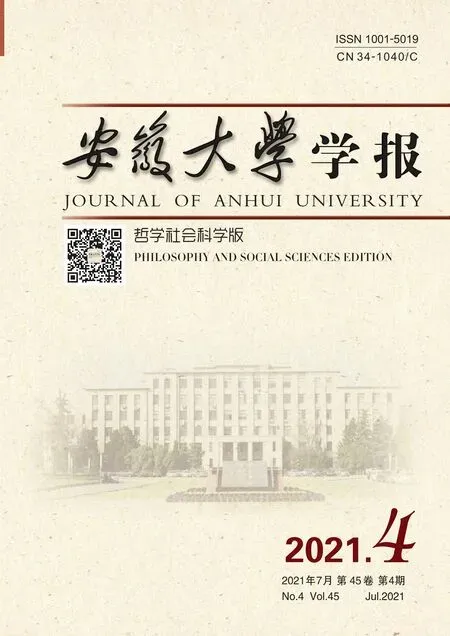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明政教结构的“原型”
——《论语》四科章疏解
赖区平
一、四科的性质:政教与学术的合一
《论语·先进》篇次章有言: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里将孔门十位弟子分为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后世称为四科十哲。
此章在列举四科十哲之前,还记录孔子的一句话:“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不及门之说,有不同解释。郑康成注:“言弟子之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按《孟子·尽心下》说:“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君子即指孔子。刘宝楠《论语正义》援引此言以申郑注,说:“无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门’也。”接着又说:“《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虽宁武子非孔子同时人,然必有从者臣卫之事,误以属之宁武子耳。及陈、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贡如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免。又《檀弓》言‘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游,亦赖群弟子仕进,得以维护之。今未有弟子仕陈、蔡,故致此困厄也。”依此,这章涉及仕进和教学,或政教和学术的关系,体现了政、学之间的对接性;只是“学而优则仕”属于正常的理想状况,这里则有“学已优而仕难进”的现实感叹。事实上,“四科”本身正是指政教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合一,具有政学合一的性质,位列四科的贤哲即是具备政教与学术能力的人才。
虽然《论语》解释史上的两位大家郑康成、朱子都将“不及门”之言与四科十哲合为一章,但也有解释者认为四科十哲当独立为一章。此外,这里还涉及孔子厄于陈蔡之时,十哲是否都在其身边的问题。清初儒者多对十哲皆从陈蔡之说提出异议,例如冉有此时仕于鲁国季氏之家,但这也无妨依类而列出十位代表。孔子授徒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人,十哲之说只是大致列出代表,有些著名弟子没有列出,并不奇怪。实际上,除非完整列出七十高徒,否则无论怎么列都会有人感到遗憾。最重要的是,四科章的重点与其说在于选出具体十哲,不如说更在于四科分类。无论有多少高徒,都可归到四类中,这是可确定的。这里主要关注的也不是具体的十哲问题,而是四科问题。
其实,抛开分章与时间问题,这两部分内容还是有内在关联的,如《论语注疏》邢昺所说:“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进,遂举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进之人。”因夫子不及门、不及仕进(“不试”者)之言,记录者才接着将具有仕进之才德(“学而优”者)的四科十哲记录下来。这就像《论语·子罕》载“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随后就依类记下:“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此二言即使分两章,仍然可见关联。类似地,《先进》篇这两段话的内在关联,不在于十哲是否从孔子于陈蔡,也不在于它们是否应合为一章,而在于它们谈及门人的仕进境遇与仕进能力,关涉政教能力之学习和仕途问题,这也正是这两段话乃至《先进》一篇的主题所在。总之,这里有一个政治与教育、政教与学术的关系问题。
孔子时代的“学”,仍然是奔着仕进从政的目标而来,“学”具有十足的政教意味,乃至孔门弟子学以成才(成人)都以政教能力来分类。即使是文学科的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仕就是在王之天下、君之国、卿大夫之家中从政。子夏为人师,设科开教也以“仕”为目标。孔子教育人,分为四大专业,目的在于培养政教技艺,成就政教人才,使弟子们步入仕途,平治天下国家。
综上,四科具有政教意味,四科分别出几种类型的政教人才或能力,显示出治理阶层(士人、君子)和职官制度的内在结构。同时,对政教系统的学习,对政教能力的掌握,也就意味着相应的学术能力(这点下文论“文学”含义时再作说明)。后世也有认为,言语科指作论立说,近于子学,文学科指诗文创作,近于集学,清儒陈澧、曾国藩更明确说,四科即指义理、辞章、经济、考据这四门学问,其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将四科对应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四科确实有学术知识方面的意义,但与后世四部之学既有关联也有差异,这点应该注意。总之,“四科”作为政教能力和学术能力之合一,体现了政学合一的性质。当然,四科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教人才和能力,政教性是四科的首要性质。
二、从政教到学术:四科的含义及其演变
明确了四科的政教性质,可更好澄清四科的含义及其演变问题,至少,不能仅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来看“德行”,而政事科也不能包揽一切政教之事。
(一)德行二义:孝弟与明德
关于“德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德行科在四科中地位最高,兼备众才。这一点可谓古今解者之共识。《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前三子属文学科,拥有圣人才德的一部分;后三子属德行科,“具体而微”即全具圣人之才德,只是未显著光大而已。《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损益四代礼乐(《论语·卫灵公》),孔子又说仲弓“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可以为君。宋翔凤也说:“德行,修德行仁,作之君者也。”“故颜渊问为邦,雍也可使南面,闵子骞辞费宰,伯牛事少见而孔子惜之,与颜渊同辞,所谓‘具体而微’,‘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者也。”德行指为君者的能力。其二,德行是本,其他三科虽各有所长,但也需有一定的德行。这点在宋以来的理学解释中得到更多强调。如明儒王樵《四书绍闻编》说:“如子贡长于言语,其学岂必不以德行为本?”清儒李颙《四书反身录》说:“孔门以德行为本。”然而,理学家也认同德行科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德行科既是最高的,又是基本的。
“德行”可指最基本的孝弟爱人之德行。《论语·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孝弟是基本的德行,为仁之本。《孝经》说“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郑注:“至德,孝悌也。要道,礼乐也。”《孝经》又说:“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弟被视为先王顺治天下的至德,是德之本和教化的源头。“门内之治恩掩义”,所有的家庭人伦德行终归以仁恩、恩爱为主。这里说的孝弟,就代表人类最基本的家庭人伦德行,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品行。它是仁爱的萌芽,能够孝弟,即有最基本的爱人能力。据《尚书·尧典》,舜最初就是由于孝友深笃而被举荐的,而其后的试舜四事中,首先提到的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也就是使民众都能顺行五伦。这表明,拥有深笃的人伦能力,也就能在政教系统中进行人伦教化。换言之,孝弟、孝友之人伦能力,同时也构成最基本的政教能力。
然而,“德行”非仅指孝弟爱人这样的基本德行,也非指不为官而在野有操行。今天容易从内在化的、个人的道德修养来理解“德”,但德字在先秦尤其是春秋以前具有更厚实的含义。其中,“德”在不少情况下特指统治者、领导者的品性,而非一般民众的秉彝常德,其常见表达即“明德”。姜昆武先生说:“明德者,天子以诚虔之修养得之于天之德。在天曰天德,在人王则曰明德。”《尚书·皋陶谟》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即是“以天子诸侯之制度,章服之荣,以予人主。此全受命于天,以统治此小民者也。则其德亦必求合于天也。……故明德是就人主言者也。此义可以统先秦诸说,不仅《诗》、《书》已也。故明德实源于天德,天德即明德之第一义谛,纯乎其为宗教色彩之熟语成词,固无可非议矣”。姜昆武认为“明德”最初是天子之德,“自周以来……进而至诸侯亦得言明德”,“战国以后,则大夫以下亦得用此一成词”。这种意义上的德,指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谈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对应于四科的前三科,立德在品性、方法和效果上都要优于立功、立言,故其政教地位也最高。立德之德显然不是泛言的个人道德修养,而是一种统领全局、治理天下的领导能力,具体表现为“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即“德作为一种内在品质,最直接的表现是‘怀柔远人’,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有德的领导者有一种吸引、凝聚和安顿远近人民的魅力、感召力。
如果说使人民自相亲睦、孝慈弟友,这是人伦教化之功,那么使民众亲附于上位者,就体现了凝聚民心的明德。且明德不仅指凝聚民众,也指凝聚整个治理阶层,使治理阶层自相亲睦,其具体表现为知人,进贤退不肖,所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就与天的关系而言,元首之明德体现在上通于天,则天、知天、乐知天命、敬天,其征验在于有凤来仪,其极致在于仁及草木,打通与天地万物的关联。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具有明德、至德的人君,其最高统治方式表现为无为而治。“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最高的统治方式,是对天的完美效法,能做到这一点即为至德,其所成就的功业文章也是至高无上的。总之,有德行者能够妥善处理与自身,与官、民、天的关系,安顿天地万物,使之各得其所。
综上,德行包含三义:(1)基础的孝弟德行,体现了最基本的仁爱能力;(2)不言而信、无为而治的高妙德行,其极致即恭己无为的君德与正己而物正的大人,这是一种统筹全局、安顿各部分使之各得其所的统摄领导能力,一种柔远能迩的凝聚力,也即明德;(3)与天或天道、天命相沟通的能力,是知天、则天、法天、通天的圣德—天德。后二者(明德与圣德)通常是关联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德行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基础性德行,孝弟爱人是为仁之本、政教之本,故后三科也都需有德行,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所倡政教有德性的底色;其二为统摄性德行,这是最高的领导能力,是为明德、圣德。德行科之二义,其实正对应于“仁”之二义:孝弟爱人是基础性之仁,总领众德是统摄主宰性之仁。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这正是整体统摄性的仁—德,正如在四科中,德行科统率后三科,这是从有德者自身而言,即自身的德行能统率其他诸能力,从整个政教系统而言,则是领袖之德行统率群臣群贤之德能,而由此,也就进一步统率所有民众,乃至仁及草木,上通天道。
(二)言语与政事
“言语”科包含机智谋略、能言善辩两方面的能力,以机智为主,如宰我、子贡的形象所示。言语、文辞有两个面向:其一为重知的言辩,其二为主情的文饰,后者其实已不是“言”,而是言之“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就文饰而言,只是这文饰附着在言语上面而已,是言语上的文饰。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行之“文”,即具备礼仪文饰的行为举动,这时文饰就附着在行为上面,是行为上的文饰。也因此,言、行本身与言、行之“文”有别,“文”(主情的文饰)本质上属于文学科,而言语科则主要指重知的言辩方面。
如果学校不结合产业,“闭门造车”培养出来的人才肯定不适应生产一线,行业企业不参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课程的设置等,也将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鼓励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内容的设置势在必行。如从职业院校的校级到系部级别,都要设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主要由行业企业的现场专家组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通过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审定。
孟子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孟子·公孙丑上》)言语科指说辞、辞命方面的能力。而从《论语》中可见,宰我善问,如问三年之丧改制问题,又如假设“井有仁焉”来追问如何能行仁而不受愚弄(《论语·雍也》);而子贡也体现了智慧,孔子曾告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语·子路》),子贡还能审时度势地经商致富,“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总的来看,言语科体现在外交使令、礼制改革议论等政教方面的机智言辩,这些事件或场合多需要根据具体时变情势而灵活应对。下面将看到,这与文学科掌文书、通礼仪等程式化、仪式化的活动,形成较鲜明的对比。言语科的善为说辞,有别于文学科在礼仪、文章上的文饰。但不应忽视,言语科的相关事项也多是在仪式性场合下展开的。
当然,“言语”观念在后世也有不同的含义:其一指在内政以及尤其是外交出使场合中机智、善辩的政教能力;其二类似《左传》所说的“立言”,言语科被视为造论立说、子学式的说理;其三,言语科也被对应于辞章之学、集部之学。后二者是从学术知识方面来解释言语科,它们显然对应于上述言语的两个面向:以言语科为子学强调重知的言辩面向,以言语科为集学则侧重主情的文饰面向。
“政事”科包含制定经济政策以及与军事、司法、工事等方面相关的能力,如子路、冉有的形象所示。子路果决勇敢,军事才能了得。孔子还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虽然孔子追求无讼,但也可见子路有很好的司法审判能力。而冉有多“艺”,其志向在于“可使足民”(《论语·先进》),冉有为政三年即可富民;当然,他做季氏家宰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即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取财于民,以增益主家,致使孔子呼吁“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无论如何,冉有治政理财能力了得。
政事科所关涉的种种事项的运作开展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外在强制性和群体性的特征,相应的表现形式有赋税、劳役、刑罚、兵役,因此也体现为对财物或力量(体力)的强力裁断或分配、取与。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治理者所追求的是正义的裁断、裁制,公平的分配,公正的取与。并且,它们都涉及投入体力以及事为,由此也多与“工具、功利、效果”有关,所针对或控制的对象多是一般下层民众,司法、军事则相关于罪犯和士卒。正是群体性、体力性尤其是外在强制性的特征,使得这些能力及人才可统归于“政事”科,而公平、正义也成为与之相关联的主导德性。
就四科来看,政事本指政治或政教领域的一个方面,后世则渐渐将其等同于整个政教领域。这与德行、言语、文学三科的含义变化也是相应的:正由于德行、言语、文学不被视为政教的组成部分,政事一科才独当一面,成为政教的代名词,虽然这并不合乎四科中政事的本来含义。
(三)文学观念的演变:从政教到学术、从经学到辞章之学
“文学”原义并非指经学,更不是后世那种与政教能力相分离的单纯学术能力。实际上,四科人才都是通过学习《诗》《书》礼乐之典章文献而成就自身,故文学科不能独占《诗》《书》礼乐之学或经学之名。与前三科一样,文学科的“文—学”二字应是并列,类似《论语》说的“文—献”。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郑玄注:“献,犹贤也。”文献之“献”指贤才,文学之“学”则有博学于师、学于贤者之义。“文”字则有礼乐典籍之文(礼文)、“文之于礼乐”之文(文饰)诸义,因而也具有博学于文、博闻强识的特性。作为一种政教能力,文学指的是熟悉礼乐仪式、名物典章,可作为礼仪顾问、指导,如公西华“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论语·先进》),或作为礼乐教师,如子夏在西河为君王师,或能够起草、记录和保存相关诏令文书,进行仪式化活动等。文学即指这种礼仪文饰方面的政教能力。
与此相应,“文学”也指称有关这一文饰性政教能力的学识,以及基于此特长而对政教系统的特别认识。文学不仅作为一种政教能力,也作为相应的知识类型或学术能力,二者在文饰性这点上是内在贯通的。事实上,不仅是文学,四科中的每一科都可视为政教与学术能力的统一。例如,言语科指另一种政教能力,即言辩能力,以及有关这一言辩能力及相应政教领域的特定学识。政事科指经济、土木工事、军事刑罚等方面的政教能力,以及有关这一政教能力及相应政教领域的特定学识。类似的,德行科指兼备诸能而统领全局、安顿各方的政教能力,以及有关这一政教能力及整个政教的整体性学识;基础性的孝弟德行则关涉一种使人伦相亲的教化能力,以及与此人伦教化相应的特定政教学识。总之,四科都体现了政教能力与学术能力,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学术能力即指能够掌握关于政教能力及相应政教领域的学识。也因此,能坐而论道即能起而行之。
就学术知识方面来看,四科人选都是经由六艺或经学研习而成才,其中,文学只是经学之一部分。可见,文学本身指称某种学术能力或知识,但却不能直接将其视为整个经学本身。不如说,四科是经学开出的四或五朵花,四科之学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完整的经学或经术,其中,文学科体现了经学或经术的礼文文饰方面,政事科体现了其强制治事方面,言语科体现了其机智言辩方面,德行科则体现了其孝弟人伦的基础性,和统领全局、安顿各方的统摄性这两方面。并且,这里的经学也是政教与学术相统一的。而后世学术,则一方面分成诸多学术类型,经学只占其一,另一方面,经学又逐渐变成一门与政教相分离的单纯学术。正是在这一学术和经学演变的过程中,文学的含义也发生演变。
“文学”观念的演变历程,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略窥端倪。《世说新语》分36门,依照《论语》四科之说,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为其下32门之大纲。这表明四科之说也对人物品评有纲领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文学”一门先列郑玄、服虔这些经师及魏晋善老、庄、易、佛之注家名士,接着再列曹植、左思、潘岳等文人。以此为契机,可考见“文学”观念的含义演变:(1)孔门四科皆擅诗书六艺,其中“文学”科只是特指熟悉先王礼乐典籍,能依礼而行,并有记载、引用、教授、传承先王典籍的能力,概括而言即:文饰、修辞、记忆;(2)孔子以后,儒分为八,诸儒习六艺或有变新,而文学科因其记载、传承六艺之学的作用而渐渐成为明经的代表,乃至独占经学之名(记载、传承,发明章句,保存“礼容”);魏晋以来,也将注解道家、佛家之学者置于“文学”名下,二家也各有其“经”;(3)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文人创作兴盛相应,魏晋之时更加重视“文学”观念的文辞修饰意义,致使“文学”由解释、引述之学变为辞章、创作之学,再次形成新的文学观念(相当于后世集部之学、《文苑列传》所指)。
至此,已有三种“文学”观念:文饰性政教能力(及相应的学术能力,作为经学的一部分)、经学、辞章之学,其中发生了两次含义转变:其一,从作为士大夫的政教能力转变为单纯的学术能力,从政教类型转为单纯的学术/知识类型,但更确切地说,是从政教与学术合一之能力转变为单纯的学术能力,尤其是,从作为经学之一部分转而为整个经学本身,从指涉文饰性政教官员转而为指涉经师;其二,从经学转变为辞章之学,从指涉经师转变为指涉文人。这种转换是耐人寻味的。而抛开其中差异,仍能看到三种文学观念的相似之处:从礼仪的文饰功能到文章的文饰功能——都强调文饰;从礼文以情质为本到文章注重抒写真情——都侧重情实;从熟悉礼文到熟悉记载礼文之文献——都体现对礼文的熟谙;从六艺的章句结构到文章的篇章布局——都关注结构;从士大夫在礼仪场合的赋诗言志到文人墨客的作诗言情——都旨在抒发情志。尤其是,不同的“文学”观念在各自系统中所具有的地位也类似,礼乐典章的记载和存续很重要,但毕竟不如礼乐的运用和实现,与此类似,文章修辞的创作也很重要,但毕竟不如文章所载的内容和义理:可见,“文学”观念虽有多种,但它们在各自系统中都并非占据最主要的地位。这些是文学观念嬗变、几种含义藕断丝连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原因。
总起来看,四科指称四或五种政教能力,并体现相应的学术能力。其中,德行科含二义,包括孝弟爱人之基础性德行(这也是一种人伦教化能力),以及明德领导之统摄性德行。当拥有这几种能力的政教人才在位从政,就居于相应的官制职位上;从政者施行政教,则其政教能力就得以发挥,表现为相应的几种类型的政教权力。
三、四科的结构:严密的两两对应关系
从结构上看,四科之间两两相对,具有一种奇特的整齐对应关系: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由此,四科将人的行为活动分别为“行—事—言—文”四种类型。
首先,关于“德—行”,《周礼·地官·师氏》郑玄注言:“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这是从身心内外来分别德与行。郭店竹简和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分别了“德之行”和“行”,如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这是从德是否在心中成形,来分别恒久的德之行和偶尔一时的善行。当然,四科中的德行科,所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修养,甚至也不是泛泛而言的政教德性,而是领导者的德行,是一种整体统摄性的政教德行。
其次,关于“言—语”,《论语·乡党》也谈及:“食不言,寝不语。”注家多引《毛传》等以解之。此外,先秦不少典籍也谈到语、言。如《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言指直接言说,语指相互论辩,可见二者有一定分别。言语科之人才不仅能考量所说的内容,而且需顾及言说的语气、方式等,这也关涉言说的背景和时机。换言之,不仅要考虑说什么,还要考虑怎么说。
再次,关于“政—事”,《论语·子路》载:“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马融注:“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为大夫,虽不见任用,必当与闻之。”即认为“政大、事小”。郑康成注:“君之教令为政,臣之教令为事也。”朱子注也类似:“政,国政。事,家事。”即认为“政公、事私”。如前所说,四科中的政事与其他三科相对,其内容有特定范围,并非所有政教之事都属政事,这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最后,关于“文—学”,二字并列,近于“文—献”,文有礼文典章、文饰、与质相对之文等含义,学有学于师、学于贤者之义,这点前面已论及,此处不赘。
先秦经典常见前三科合说与后三科合说这两种情形。究其原因,一方面,德行科统摄后三科,故只言后三科;另一方面,文学科所守护的礼乐典章,乃是前三科都要学以致用的,故只言前三科。如《尚书·秦誓》言及三种士臣:旅力既愆之“良士”、射御不违之“勇夫”与“截截善谝言”者。其中,勇夫如子路,自属政事科;善言者如子贡,则属言语科;而“良士”已是老成之人,故勇力不足,而阅历很深,整体权衡统摄能力则更强,大致属德行科。又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论语》说的“仁、知、勇”,大致是前三科合言。而《论语》《礼记》《孟子》等常提及的“君子三道”,例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即“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论语·泰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以及“不言、不笑、不取”(《论语·宪问》)之说,大致都是后三科合言。“三道”都相关于礼文,但各有侧重:言或辞气,体现善辩明智(“时然后言”),指向言语科;“动容貌”则基于脚步动作,显示整个人的身体轮廓与行动,所以跟“取、与”的行动有关,行事取与要合乎正义(“义然后取”),这跟政事科有关;脸上的颜色,则指狭义的礼仪文饰,正颜色体现为端庄恭敬,不苟言笑(“乐然后笑”),这指向文学科。
四科之间也有一定的先后次第。第一科有优先性,地位最高;第二、三科的排序,今本《论语》是先言语后政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是先政事后言语,这种不确定本身是富有意味的,使人想到四部之学中,乙、丙二部(史部、子部)最初排序的不稳定性;文学科位列最后,文学是诸政教技艺的载体和基础,这也应从政教人才或能力的结构上来把握。
四、余论:四科作为政教结构之原型
《论语》四科说在后世有不少影响,例如汉代著名的四科取士之法就源于此,由此也可见四科作为政教人才或能力的基本分类。更重要的是,四科并非心血来潮的随意归类。在早期儒家经典世界中,围绕“四科”形成了一个文明谱系,从政教人才/能力、官制、政制、教育、学术,到心灵、德性、伦理,环环相扣,这些环节具有内在同构性,都呈现出一种四科式的结构分类。例如,关于教育方面,《周礼·天官》载“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礼记·昏义》也说“古者妇人先嫁三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人接受的这四项教育,与男子之四科四教在结构上相同。妇德对应于德行,妇言对应于语言,妇功对应于政事,妇容即礼容、文饰,对应于文学。差别在于,男子四科关涉门外之治、天下国事;妇学则关涉门内之治、家事。这表明,经典世界中先秦时代男子、女子的教育学习,在内容类别、能力培养上有共法,都分四类。又如,关于伦理、德性、心灵方面,思孟五行说的五德“圣—仁义礼智”,对应于作为主宰的“心—四端”,并对应于某种君子五伦,一如《孟子·尽心下》所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有别于常见的民众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君子五伦指的是父子、君臣、朋友(宾客)、师生(贤者)、天人(圣人与天道)这五者,其中不仅包括人伦,而且包括与天的伦理关系或曰天伦;并且,此五伦、五德(以及“心—四端”之心灵结构)也内嵌于一个庞大的四科文明谱系中。而如前所说,后世以“四部”之学为核心的学术分类,其源也实可溯及四科之学。今天重思整个学术分类和知识谱系,古典的四科之学正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点。就政教结构而言,《尚书》中《尧典》(《舜典》)和《皋陶谟》的官制类型和政教人才、政教能力分类,也体现了同样的四科结构,由此,还可揭示一种与《周礼》“六官系统”不同的“五官系统”。古文经学的《周礼》六官以具体官制为标准来划分,相比之下,四科式的五官系统则以政教能力来分类,因而更具有恒定性,其勾勒出一种独特的经学的古典政教结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四科”构成了古典政教结构乃至中国文明的一种原型。四科作为一种奠基性的原型,渗透在以政教为核心的古典中国文明的各个领域。由此,古典儒学/经学展示了一种对文明谱系和世界历史的系统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握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的整全视野,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