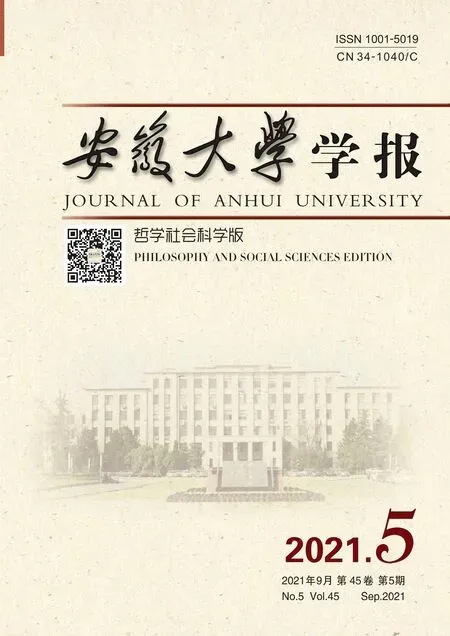“风格”批评的流衍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孙启洲
一、引 言
“意境”与“风格”既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也是现代词学史上相当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一组范畴,前者“是内容形式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中偏于内在意蕴的方面”,后者“则是偏重于外在形态的方面”,“就是艺术作品的因于内而符于外的风貌”。在接受西方审美无功利的美学观和纯文学的理念之后,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借“境界”这一融合中西文学内涵的关键词,将词学由依附经学话语的传统转向建构新型的美学话语,触发了中国现代词学乃至现代美学的机栝。与此同时,晚近以来,西方现代风格理论伴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中国学界,现代学者对“风格”逐渐形成相对明晰的认识,不断尝试将其嵌入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之中,进而影响到现代词学的表述方式,形成了以“风格”为重要范畴的词论话语。现代词学的境界说与风格论,共同构成了词学现代性的双重美学向度。
古典词学传统中,涉及风格论的材料相当丰富,尤其是对于词人和词体风格的讨论,内容繁多。但是古典词学风格论,尚未构成体系性的论述,多为感悟式的触发,吉光片羽之间,虽道着神貌,然多零碎而含混。古典词论中多以风、气、神和味等诸多名目,来表述与风格相关的内涵,而“风格”一词的使用并不如现代时期自觉频繁,况且“‘风格’或style或stil原不是我们旧书里固有的名词,即使有,它的含义也决不会和现在完全一样”。
如果说王国维以“境界”评词,是对词本体最高审美理想的探索,开创了词学批评的现代范式,那么胡适以“风格”论词,则是对词的创作主体的独创性的凸显,为词学批评另辟新的美学话语。学界关于词学意境说的研究成果甚丰,然而对于词学风格论传统却鲜有措意。由此而言,厘清词学批评史中“风格”意涵的古今流衍,比较概念意义变化背后的学术知识观念的转变,述论涵括词人、词派以及词体的时代风格等在内的现代词学风格论的形成过程,将成为学界观照词学批评由古典形态向现代范式转型的又一重要路径,也足以展现现代词学复杂多样的审美诉求,揭示在新旧词学的过渡阶段,词体审美要求的变迁及其批评话语的时代性特征。
二、以“风格”论词的古典传统
以“风格”论词,并非始于现代,早在北宋时期,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中就曾言:“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此处的“风格”指词作为文体的创作规范,具体而言,填词一要合音律,二须含韵外之致。尤至清代,“风格”在词话中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但各家对于“风格”的具体使用及其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
清人词话中所涉“风格”处,多以词人作风为论述对象。大致可分如下几种情况:一是以名家词风形容具体词或词人的风格。如《灵芬馆词话》评罗璔《菩萨蛮》一词:“大有饮水侧帽风格。”《听秋声馆词话》形容张星耀《洗铅词》:“风格颇近玉田生。”二是以时代风格论词或词人风格。如《词苑萃编》引严秋水评彭羡门小词:“啼香怨粉,怯月凄花,不减南唐风格。”《蕙风词话》认为《秋涧乐府》中《鹧鸪天》一词:“清浑超逸,近两宋风格。”三是以流派词风评词人风格。如《芬陀利室词话》赞周稚圭词:“凡此皆有花间风格,下亦不失为小山父子。”这种以名家风格、时代风格和流派风格品评词人风格的方式,虽可见词人间前后传承的关系,但却失之模糊笼统。
与词人风格论相关联的是风格的雅、俗之辩。沈雄《古今词话》中两次出现“风格”,均以“风雅”为旨归。一处引宋实颖评陆次云词:“正学之能采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以拟玉山之风格,其谁曰不可。”另一处引朱彝尊语:“月团词绮而不伤雕绘,艳而不伤醇雅。逼真南宋风格,安得不叹其工。”足见古人将风雅蕴藉视为词体风格应有之特征。这种词学风格论渗透着经学话语的诗教传统,词体的价值评判依附于正统诗论的“风雅”观念,将“雅正”视为词风所应追求的最高准则,这自然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风格”内涵不同。
“风格”与风雅、醇雅相关联,且有高下之别,实已含有风度、格调之意。谢章铤将人品与词品合而论之,他以为:“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自为菲薄,然辛以毕生精力注之,比苏尤为横出。吴子律曰:‘辛之于苏,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殆不可以学而至。’此论或不尽然。苏风格自高,而性情颇欠,辛却缠绵悱恻。且辛之造语俊于苏。”况周颐亦重风格的高低、升降,他在论刘云闲词时说:“窃谓词学自宋迄元,乃至云闲等辈,清研婉润,未坠方雅之遗。亦犹书法自六朝迄唐,至褚登善,徐季海辈,余韵犹存,风格毋容稍降矣。”显然,词的雅正与否,是其评价词人风格高低的重要标尺。在况氏的词学论述中,风格与情辞是可并列而论的两组概念,“风格”更侧重词的整体意蕴、风貌和格调。
况周颐所言“风格”虽含格调高下之意,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词人与词作之间存在的罅隙:
晏同叔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蒋竹山词极秾丽,其人则抱节终身。何文缜少时会饮贵戚家,侍儿惠柔,慕公丰标,解帕为赠,约牡丹时再集。何赋“虞美人”词有“重来约在牡丹时,只恐花枝相妒,故开迟”之句。后为靖康中尽节名臣。国朝彭羡门孙遹《延露词》吐属香艳,多涉闺襜。与夫人伉俪綦笃,生平无姬侍。词固不可概人也。
在况周颐看来,人格、品行与词人词风密切相关,但不能完全以词风定人品。此说恰为我们提供了文学体裁制约创作风格的经典范例。唐五代的文人词,因最初供歌儿舞女演唱,“以助妖娆之态”,形成了清艳婉丽的花间词风。故传统词人多以婉约词体为正,并以此规范填词之法,后人填词多遵此法,即使性情刚烈者,其词亦须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词人风格的形成与其语言表达方式之间亦存直接的关系。况周颐以“重、拙、大”说界定词体风格的特征,填词既要以此为规范,也须以此为审美追求。因此,他反感尖、纤之作,认为“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真意尽漓,反不如国初名家本色语,或尤近于沉着、浓厚也”。由此可知,词中语言刻意雕琢而求尖新,直接导致词的风格流于靡丽浮艳,已失词之真价。但尤须注意的是,况氏所论仍要辩证地看待,词句的“艳”并不意味着格调的低,如其评荣諲咏梅词“‘似个’句艳而质,尤是宋初风格,《花间》之遗”。在况氏而言,浓艳但却自然质朴之词,亦不降其格调。
除此之外,况周颐在谈填词用韵时,有三处言及风格,可知词韵的选择对于词风亦有影响。《蕙风词话》曾说明咏物咏事词的做法:“须先选韵。选韵未审,虽有绝佳之意、恰合之典,欲用而不能。用其不必用、不甚合者以旧韵,乃至涉尖新、近牵强、损风格、其弊与强和人韵者同。”选韵是填词的关键,选韵不当会导致音节与词意失调,词的整体风格无法达到和谐的状态。词作为韵文的一种,韵律是其最为重要的文体特征,决定着词作节奏的缓与急,以及词人情感的表达效果,这些都与词作整体风格的形成密不可分。他回忆自己学习填词时所感虚字叶韵之难:“‘儿’字尤难用之至。(如船儿、叶儿、风儿、云儿云云。)此字天然近俚,用之得,如闺人口吻,即亦何当风格。”此说是词中用韵比较特殊的案例,强调虚字韵的使用与词作整体风格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虚字所具有的表达风格存在差异,或有口语与书面语之别,或有雅俗之分,不同的言说对象应当选择不同的字和词,否则词的风格也难以协调。另有,况氏在分析李蠙洲词时言:“‘饧’‘黠’叶韵虽新,却不坠宋人风格。然如‘饧’韵二句,所争亦止絫黍间矣。其不失之尖纤者,以其尚近质拙也。学词者不可不知。”在他看来,叶韵而求新奇,则极易为病,但如能自然表达,以质拙克服尖纤之弊,自能不失风格。在对语言与风格之间关系的论述中,贯穿着他对词体审美特质的要求。
纵观中国古典词学发展史,虽有以“风格”论词的传统,但“风格”远称不上中国古典词学的核心范畴。在传统词话中,以“风格”论词之处,多指向单个词人风格的描述,虽然也有南唐风格或者花间风格一类以时代和流派命名的风格类型,但皆用以形容词人风格。这与以风格品评人物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因此“风格”多蕴涵人品、格调之意,这也是“文如其人”的理论逻辑的体现,延续古典文章风格论的余绪。既然如此,风格就带有感情色彩,有雅俗之分、高下之别。
据前文引述亦可知,词学家多依其个人词风宗尚,品评其所激赏之词人词作,如朱彝尊赞《月团词》有南宋风格,王国维以五代风格形容冯延巳词风等,其实逆而推之,正是词学家先存有偏好南唐、北宋或南宋词风的潜在标准,故对有此类似词风的词人词作,方能深得其中三昧,由此可见时代风格也有优劣之别。在众多词话中,鲜有“元人风格”“明人风格”或“清人风格”之论,可推想在当时的词学家看来,这三代实难配得上“风格”一词,应是对南宋之后词体中衰的普遍认知所致。
质实而论,以时代风格界定个体词人风格,实在失之笼统而无边际。试想文学风格虽然受特殊时代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或许有趋近的倾向,但毕竟各时代文人自身的个性特征,才是影响其文风的关键要素,因此各家风格以及词学宗尚,存在诸种差异。南宋诸家中既有白石和梦窗的清空与质实之异,也有辛词的豪迈之风等等,不一而足,故以时代风格品评词人风格虽生动形象,但在理论逻辑上实难行得通,这大概是古典词话重感悟式批评的弱点所在。随着现代文论的兴起,理论家展开更为系统、深入的风格学研究,“风格”一词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而以“风格”论词,也成为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理论表述的重要方式。
三、由“意境”过渡至“风格”:现代词学风格论的生成
晚近以来,随着西方美学思想被不断地翻译和介绍,直接触发中国文论由古典形态向现代范式的转型,而作为美学重要论域之一的“风格”,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梁启超所倡导的“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学主张拉开了“诗界革命”的大幕,早在《夏威夷游记》中,他就曾设想:“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氏虽未明言“风格”究竟为何意,但综观其诗论,可知此概念多指诗歌的古典风味和体式。在他看来,“诗界革命”当在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可为“渊懿之风格”,亦可为“宋人风格中最高尚者,俊伟激越,芳馨悱恻”,最终达到“茹今而孕古”的诗境状态,这是他一贯的诗学理念。然而此时,尚未形成具有明确范畴和逻辑体系的风格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风格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逐渐应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俞平伯曾在1921年的《学林》上发表《〈石头记〉的风格与作者底态度》,以“《石头记》是作者底自传”为立足点,探讨文学家的创作态度与小说风格形成之关系。与此同时,学界已开始大量译介西方风格论的著作,龙詹兴、吴寿彭和陈介白先后翻译过叔本华关于风格的论述。1929年赵荫棠编译《风格与表现》一书,译有柏奈特的《风格论》,刘呐鸥翻译弗理契的《艺术风格之社会学的实际》(1930),宗白华曾译过歌德的《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1935)。国内学者如邵子风、傅东华等人也集中关注和发表风格学的文章,直至40年代,徐中玉的《风格与思想》,朱光潜《谈文学》中的《体裁与风格》等,均是文学风格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中国现代学人,引入西方美学中的“风格”范畴,与本土风格论传统相融合,形成现代文学风格论的新传统,而这尤其体现在以新的学术视角对古典文学的文本风格,重新进行系统地研究与阐述,现代词学风格论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真正开始将“风格”作为核心概念论词的,则非胡适莫属,他将词学“境界说”导向了“风格论”的批评话语。
任访秋曾发表《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比较研究王、胡二人词学观的异同,并将此文寄予胡适。在给任氏的回信中,胡适极力澄清其所言之“意境”与王国维的不同之处:
他的“境界”说,也不很清楚。如他的定义,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我所谓“意境”,只是一个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看法)。我称它为“意境”,显然着重在作者个人的看法。你的解释完全错了。我把“意境”与“情感”等并举,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对于某种情感或者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那一点,从那一点观点出发。
如果说王国维从文学本体出发,将“境界”界定为文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是对文学审美共通性规律的理论归纳,是对“一”的追求,那么胡适的“意境”则更侧重作家主体在文学创作时采取的创作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创作样态,这正是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质素,是对“多”的呈现。
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中,胡适的表述更为明确:“意境只是作者对于某种题材的看法。有什么看法,才有什么风格。古人所谓‘诗品’,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大概都是指诗的风格。其实风格都是从意境出来;见解是因,风格是果。”由此,施议对在回溯百年词学发展史时认为,“现代词学境界说,于开拓期尚未见实质性的效应。之后,由于胡适、胡云翼相继推衍,逐步向左倾斜,以至演化为风格论”。原本用以界定文学审美理想的“意境”,则一变而为描述创作主体性的词汇,这就与内符于主体性情而外显于语体形式的 “风格”意涵,产生内在勾连的可能,所以意境被胡适视为风格形成的前提,由此意境与风格都具有主体性的情感因素,各自均有高下之别。
胡适关于词人风格的论述集中于《词选》一书。要实现古典词学话语向现代学术话语的转变,首先需要确立以“风格”论词的理论渊源及其合法性,胡适曾评张先词云:“晁补之说:‘人以为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晁氏所谓‘韵’,我们叫作‘风格’。柳永风格甚低,常有恶劣气味;张先的风格也不高,但恶劣气味较少。”胡适此处直接言明将古代文论中的“韵”转换为现代文论中的“风格”,为他评词提供风格论传统,也实现了知识话语的替换,但其“风格”的内涵,依旧不能脱离“文如其人”的传统惯性。胡适将词的风格与词人人格结合而论,认为在苏轼前,词多抒儿女之情,轻薄不足道,而苏词重开新意境,创立新风格,其悲壮与飘逸之风自胜他人一筹。所以,胡适论词激赞东坡词和稼轩词有真人格,而对柳词和秦观词则颇多讥评之语。
与此同时,“风格”亦是其叙述词史发展的重要依据。在胡适看来:
山谷,少游都还常常给妓人作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稍后起的大词人周美成也能作绝好的小词。但风气已开了,再也关不住了;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的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
胡适从词体风格的演变,简要地勾画出词史从相对统一的类型风格到凸显个性风格的发展进程,就此而言,自觉地以“风格”论词,已然成为胡适词学的重要特征。
胡云翼关于词人风格的阐述,深受胡适词学风格论的影响。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中所言之“境界”亦含有风格意味,如其认为“刘过的词也和辛弃疾一样,有悲壮和飘逸的两种境界,但均不能造其极,所以终究是第二流的词人”。同胡适一样,他也将情感与意境对举,将词分为内外二义,即外在的形式美,包括词的音律和字面,而内容的充实,则包含情感和意境两个因素。他以为“乐府词发展以后,我们只念着词调的铿锵,看着字句的华美;不仅南渡词人那种悲凉感慨的作风失掉了,就是写儿女之情也写不好”,此句中的“慷慨悲凉的作风”便对应着他所言的“意境”,其实已指向风格的内涵。但与胡适不同的是,他不以词作风格的外在表征作为评价词人的唯一标准,而是更看重词所具有的描写性的文体特征。因此当胡适不满于柳词的风格卑下时,胡云翼却另有说辞:
风格不高,实不足为柳词病。古今词人风格之高无如姜夔,然我们读姜词总如雾里看花一样,没有能够十分使我们感兴的。词的第一要义是描写,如果离开了描写而谈风格,真是舍其本而齐其末。
胡云翼虽然延续了胡适以风格论词的批评模式,但是他更坚持以文体属性为评判词作高下的基本准则,然而突出“描写”作为词体的首要特征本就值得商榷,况且借此贬低姜夔清空一类的词风,实在难称公允。
胡适与胡云翼二人变词学“境界”说而为“风格”论,一方面以颇具现代美学意义的“风格”替换古典词学中的“韵”,实现传统词论知识话语的内在转换,逐渐建立新的词学观,并与现代文论相衔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词人风格为线索纂述词史的模式,直接影响着此后词学家的词史书写理路,开启现代词学研究的新范式。
四、现代词学风格论的推演: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
与胡适和胡云翼等人的词论相比,龙榆生的词学风格论,更注重风格作为一种流动形态的呈现,辩证地分析不同时期词人创作的细微变化,并且在词人风格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延伸至词派乃至词的时代风格流变的探讨,标志着现代词学风格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大概是受到当时学界风格学理论兴起的影响,龙氏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一系列有关词人风格研究的文章。《东坡词之风格及其特点》是龙榆生较早探讨词人风格论的代表作。他将词人风格视为主体人格个性的充分表现,重点考察词人所处的思想环境对其填词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龙榆生肯定王鹏运以“清雄”二字概括苏轼词风,但他对于苏词的认识却不拘于此,而是更进一步梳理苏词风格在不同阶段、不同生活境遇中的变化。他将苏轼创作过程分为杭州至密州、自徐州贬黄州以及黄州去后等三个时期。初期杭州时“少年风度,潇洒风流,故其词亦清丽飘逸,不作愁苦之语”;至密州时离群索居,生活稍嫌枯燥,其词中已有凄婉之音,忧生之叹;居徐州时,其词“开拓排宕,所忧者为‘无常’之感”;之后因文祸而迁至黄州,“忧谗畏罪,别具苦衷”,其词亦“无穷伤感,光芒内敛”;离开黄州之后,饱经忧患的苏轼,填词多“即事遣兴,间参哲理,拟之黄州诸作,稍嫌枯淡”。
在龙榆生看来,“词风转变之由,与个人性情,时代环境,咸有莫大关系”,所以他从不以单一某类风格为词人定性,而是通过对词人创作的时间段的纵向分析,强调词人风格在不同年龄段、经历不同生活境遇之后的动态变化。这是一种更为合理的研究词人风格的理路和方法,因而他也并非像胡适那般以词人某种风格来评介词作之优劣。他试图通过对于词人风格流变的研究,展现词人性情的多重样态及其语体表达方式的层迭演变,而不拘拘于粗浅的概括和片面的褒贬。
龙榆生还将这种研究思路推衍至词派风格和词的时代风格流变的分析中。他曾发表《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一文,阐述其对于词派风格流变的认识。他先从情境、修辞和声律三个方面确定苏辛词派的大致风貌,将苏辛词风的先导上推至范仲淹词,再论证苏辛词风的形成过程,即从苏轼到苏门弟子逐渐形成的相近性词风特征,同时也辩证地阐述苏辛词风的差异。最后则是梳理苏辛词派在南宋的发展流变,他总结道:
苏、辛同为横放,而以身世关系,所表情感,亦自殊途。南宋作家,近稼轩者尤众,英雄失志,悲愤情多。其或耿介清超,饶有逸怀浩气者,则步驱苏氏。……放翁悲壮之处,时近稼轩;张孝祥亦出入东坡,又未易严定疆宇。
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他对于苏辛词派中各家风格均有精到的辨析,既总结流派中词人创作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也具体分析单个词学家在不同境遇中所形成的个性风格,使我们足以认清词派风格在各词人词作中的承继与流变。
除此之外,《两宋词风转变论》是龙榆生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时代词风流变的重要文章。他以词人风格或词派风格的转变,贯穿整个宋代词风流变论的研究。此文开篇便批驳词学史上南北宋之争的门户之见,明言“两宋词风之转变,各有其时代关系,‘物穷则变’,阶段显然。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正与上文所言其辩证的词学风格论一以贯之。龙氏不以静态而笼统地概括去简化对于某一时代词风的认知,而是尽力回到词史发展的历史场域中,观察词风流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龙榆生将两宋词风的转变过程分成了六个主要阶段。他从古代历史地理现状以及词人的境况着手,断定北宋初期词受南唐词风影响为多,以文人学士词为盛,词之风格“沉着厚重”,此为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介于词为音乐文学的特质,所以龙榆生亦将宋代音乐与词体演变之关系视作促使词风流变的关键要素,故而在第二阶段着重探讨教坊新曲的兴起与慢词词风形成的内在关联。第三个阶段的划分,则突出苏词对于曲子律的解放。词人一改纤丽柔靡的词风而抒发浩气逸怀,使词体日尊而距原始曲情益远。此后大晟府的建立,引发词风的第四次转向,以清真词为代表的典型词派,向着合于律吕而又浑雅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国势的兴衰与词派的发展,也是他探讨词风转变的立足点。因此,龙榆生在第五阶段中强调南宋国家权势的衰落和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使慷慨悲歌之士抒发英雄抑塞磊落不平之气,苍凉悲壮的词风则成为此一时期词史递变的显著特征。在苏、辛词风解放曲子律的趋向之外,以姜夔和吴文英为代表的宋末词人,精研律吕,填自度腔,使词之风格流于典雅一脉,完成两宋词风流变的最后一个阶段。
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是对词学风格论的全面认识。他在思考词体艺术特征时总结说:
我总觉得词所以“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它的主要关键,仍只在曲调的组成方面。由于作者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又善于掌握各个不同曲调的自然规律,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技法和风格;而这种种不同的技法和风格,却都是存在于词的领域以内的。
龙氏格外强调词调之学,因此对于词乐、词律与词人风格关系的研究更为深入。而这种以辩证的逻辑思路和动态的视角研究词风流变的过程,正是现代词学与古典词学的区别性特征所在。他力图从时代环境、地理因素和词体音律等多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不同阶段词人创作的大致趋向,观一代词风之转变,跳脱出静态地轩轾两宋词风高下的窠臼。这种词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远比一味褒贬的意气之争更具现代学术研究的立场与精神。
龙氏曾在那篇对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具有奠基意义的文章——《研究词学之商榷》中指出:“前辈治学,每多忽略时代环境关系,所下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惝恍,莫知所归。此中国批评学者之通病,补苴罅漏,是后起者之责也。”所以,他极力倡导建立现代词学的批评之学,结合词人的身世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推求词人、词派以及时代风格的转变,考察其中的利弊得失,而非以研究者个人偏好褒贬研究对象。“风格”在龙榆生的词论表述中,逐渐走出从“意境说”向“风格论”的过渡阶段,“风格”已然成为词学批评的核心话语,而且“风格”的意涵摆脱了评鉴人物品性的褒贬色彩,转变为用以描述和形容词人创作阶段性特征的美学概念,走出古典词学风格论笼统含混的状态。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通过重返历史语境,厘清词人以及词体时代风格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促使词学风格批评话语的流播,其风格批评实践,更新了学界的词史观念,也推动着词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五、修辞学视域下的词学风格论:詹安泰论词体风格
岭南词学大家詹安泰对于词体风格的分类和研究,也是现代词学风格论的重要内容。1945年,发表于《龙凤月刊》上的《论诗之风格》是其专门阐述风格论的一篇文章。詹安泰所谓风格:
盖人之禀赋,□有不齐,于人人所共有之通性外,又必有其“自性”(即所谓“个性”);其发为文辞也,于人人所共有之通法外,又必有其“自法”(即所谓“手法”)。“自性”藏于内容之中,而“自法”见于形式之表。
因此,在他看来,风格涵括了才性与体制两部分,创作主体的才性为文本倾注别样的情感层次,并运用自己独特而又纯熟的表达技法将其清晰地传达出来,由此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阶段性表现形态。
在对词体风格的具体辨析过程中,詹安泰则着眼于词的文学性特征即语言修辞,总结词之风格的多样性表现。在他看来,“作风不同,修辞斯异,盖作风就整体言,修辞就个体言;作风就已成之形式言,修辞就运用之技巧言,二者固有密切之关系也”。所以詹安泰在《词学研究》一书中,设专章讨论“词之修辞与作风”的关系,从文学修辞的角度将词体风格分为拙质、雅丽、疏快和险涩四派。他不偏嗜于某种风格,而是辩证地说明各种风格在创作中的优劣之处。拙质之词,使读者明白易懂,其长处在于切挚动人,而短处则在浅陋凡近。雅丽之风恰与拙质相反,追求辞藻的华丽,有巧夺天工之美,但过分斤斤于辞藻,便会造成“非晦昧则变质”的结果。疏快一派,倾向于词风豪放一脉,“以雄健顿宕”为美,开拓了词境,而学此词风未成者,亦流于浅率粗狂之病。险涩词风历来易被词学家所诟病,但詹氏就修辞方式而论,认为“险易见巧,涩易得重”,因而“险涩非词之病,险涩而至汩没真意,乃真大病耳。”
《词学研究》一书原本设置十二章,现仅存七章,其中“论派别”一章为詹安泰词学风格论的重要内容,现虽已不可见,但在其之后所著《宋词研究》中“‘风格、流派及其传承关系’当与‘论派别’一章为近”,故可以此为参考,解读其词学风格论。詹氏在词体风格四分法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将词的风格细分为八类,即真率、疏快、婉约、奇艳、典丽、豪放、骚雅和密丽。詹安泰将词体风格与词人流派相结合而论,于每一种词体风格之下列举代表性词人,并重点分析其词风格的特点和形成的缘由,以及词风承传关系等。
真率的词风以柳永词为代表,其融情入景之词亦含清丽之气,“自然流转,一气贯注,深入细致,具体明朗”是柳词所表现出的显著风格特征。此后,张先、秦观、黄庭坚、杜安世、贺铸以及周邦彦等词人,皆受其词风的影响。苏轼则是疏快一派的开创词人,挥洒自如和才情奔放的个性,造就其以诗入词、疏宕明快的词风特点。疏快之下又细分为高旷、清雄和明丽三种子风格。这种词风的渊源可追溯至韦庄、李煜和范仲淹等词人,而黄庭坚、晁补之、陈与义、朱敦儒和向子諲等承继与发扬了此类词风的特点。婉约派则以秦观和李清照为代表,词风以婉转含蓄见长,描写手法曲折深透,是“远师南唐,近承晏、欧而参以柳永”之后所成,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均沿袭此种词风。张先、贺铸是奇艳词风的代表,笔力精健、采藻艳逸是其突出特征,王观、李之仪和周紫芝等皆为此类风格的名家。
除此之外,周邦彦被划归为典丽派风格的代表词人,此派更重音律的谐和,遣词的典雅和造句的精炼、严密,万俟咏、晁端礼、徐伸和田为均是此派中人。稼轩词承继东坡词而来,却演化成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豪放词风,从文人词变为英雄词,陆游、陈亮、刘过等均为其追随者。清空骚雅和险涩密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类型。前者以姜夔为代表词人,填词讲求空灵的意境、清新的格调,“以健笔写柔情”。史达祖、张炎等人词风与之相近。后者以吴文英词为代表,其词“讲究字面,烹炼句法,极意雕琢,工巧密丽,时时陷于险涩”,尹焕、黄孝迈等皆为此类词风余绪。
古典词话中不乏对于词体风格的界定,但鲜见像詹安泰这般从语言表达与文体关系的角度系统地进行分类研究。他分析每一种风格在修辞技巧和表达效果上的突出特征,并梳理其渊源和形成缘由,说明某一风格在后世所受之评价,及其对于后来词风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不仅总结词人的主要风格,区别各家各派词风的差异,也清楚地意识到每位词人风格自身的多重性。这种从语言修辞探究词体变迁的学术研究路径,一方面,展示不同类型的词人创作的不同取向,以及词体风貌的多样形态,另一方面,也足以钩织出词家在创作上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是厘清词史发展脉络的一种重要方式。詹安泰修辞学视域下的词体风格论,更多的是从文学“自性”的角度探讨风格问题,完全摆脱古典风格论的道德性评价,而成为描述、总结词人创作特征的更具学理性的美学术语,更进一步丰富词学风格论体系的内涵。
六、结 语
“风格”同“意境”一道,成为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中的重要范畴,同时也为现代词学研究所借用,改变了词学话语原有的表述方式,尤其是话语背后词学观的新变,造就了词学研究的新传统,因此从“风格”入手,梳理和分析词学发展史中风格论的流衍,是观照词学现代转型的有效且可行的理论路径。当前学界关于现代词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词学家的个案研究,而从问题域出发,通过厘析词学关键词的方法考察词学古今演变的过程,也是打开词学现代转型研究视野的一种有益尝试。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境界说”为中心建构的词学批评模式,率先敲开词学现代转型的大门。在此之后,胡适和胡云翼将“境界说”暗度陈仓地转化为词人风格论,逐渐摆脱传统词话的模糊与笼统,初步建立以“风格”论词的新传统,实现词学知识话语的现代转换,促使现代词学风格批评的生成,建立起新的词学话语表达方式。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是对词人风格研究的不断推进,而立足于词人风格论基础之上的词派风格研究,及其对于词史演进过程中时代风格演变轨迹的厘析,足可展现词人风格与词体风格的流动性变化,此一阶段标志着“风格”已然成为词学批评中的核心话语。詹安泰坚持文学本位的立场,更强调文学语言与文体风貌之关系,明确提出从修辞学的视角划分词体风格的方法。由此,词学风格论实现从古典时期的模糊与笼统状态,历经过渡期的摸索,转变为更具现代美学内蕴的词论话语,形成以词人风格——词派风格、时代风格——词体风格为架构的相对丰富的风格论体系,开辟出词学阐释的新路径。
综前所述,词学“风格”批评的古今流衍,表征着中国词学批评模式的现代转型。一方面,与古典词学传统相比,“风格”俨然成为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的核心范畴,传统词论中的“风”“韵”等概念逐渐统一在内涵更为明晰的“风格”一词之下,实现理论话语言说方式的现代建构。另一方面,现代词学风格论也趋向弱化甚至剔除原有“风格”意蕴所带有的道德伦理要素,而更具现代美学批评的特征,标志着现代词学观的逐步确立,意味着传统的经学观念开始让位于现代美学观念,成为词学批评的主导话语资源,这也是词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质。再一方面,现代词学家关于词学风格论的阐释更为精细和系统,纠改了古典词学风格批评失之笼统的弊病,极力呈现词人与词派风格的动态变化以及词体风格的复杂样态,并以此观照中国词史的发展脉络,更新了固有的词史叙述方式,也开辟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新范式。更进一步论,具有现代美学意涵的“风格”一词成为词学批评的核心话语,以及现代词学风格论体系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同样折射出中国文论话语或者说文学批评范式的现代性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