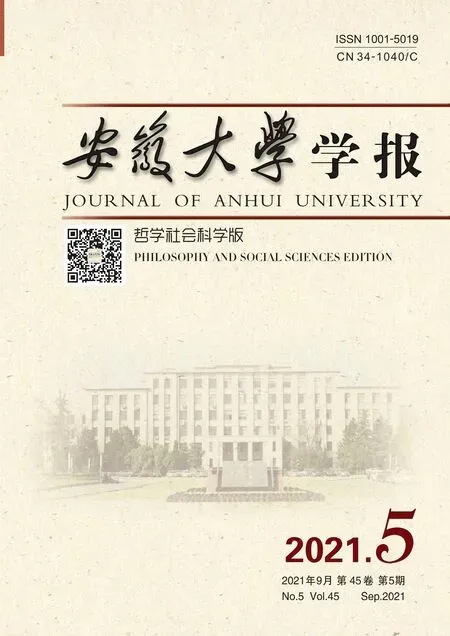新世纪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研究(2010—2020)
刘文祥
一、选题的提出
本文主要对2010—2020年也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乡土中短篇小说展开研究。之所以选择中短篇小说主要是因为本论题是一个研究盲点,人们在考察当下乡土小说的时候,更习惯以长篇小说为样本,长篇小说在反映乡土变迁、发掘时代内蕴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也更能够代表一个作家的风格,成就一个作家的文坛地位,所以人们在理解时代、汲取经验和认识的时候,非常依赖于长篇小说。而且很多长篇乡土小说发表之后都会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各种评论一时间也会席卷而来。但长篇小说也有自己的内在不足,其写作要经历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打磨完成,如刘继明的《人境》写作历时15年之久,但对于现实的考察和认识还停留在2004年农业税取消前后,也即是说,长篇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时候远不如中短篇那样直接和有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单独把2010—2020年这一时段内的中短篇作品拿出来进行讨论并不一定恰切,却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纠正乡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某种滞后性的需要。近年来乡土文学研究越来越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处境中,乡土文学研究中很少出现新的论断,在很多研究者眼中,乡土创作似乎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没有什么较大的变化。这固然是乡土创作领域的无力导致的,更也可能是认识的局限导致的。在对当下乡土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中,很多人都习惯以1990年代为起点进行考察,大量冠以“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研究,其实在作品样本的选择上还都停留在第一个十年中。这样的研究所揭示的未必是真实的文坛生态,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乡土文学认识的滞后,甚至部分人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时至今日,很多人对乡土文学的印象都还停留在对贾平凹、李佩甫、莫言、韩少功、阎连科、刘震云、贺享雍等作家的认识上,对“70后”“80后”等后继作家的乡土创作关注力度还不够。这主要是因为“50后”等经典作家的书写经验尤其是其开创的宏大叙事的书写范式,还主导控制着我们对当下乡土文学的视野和期待。尽管“70后”“80后”等作家在事实上已经是乡土创作的主力,但是由于其创作多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还很难确立属于自身的话语权和经典地位。因为新的作家们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变化了,当下社会无力生产具有统摄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则,这使得他们的经验是断裂的,是不连续的,没有经历过稳定的文化环境,就难以复制出稳定的心理结构,所以新一代乡土作家更擅长或者被迫选择中短篇写作这种方式进行表达,我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而是要积极紧随时代的变化,发掘乡土的创作新变,纠正认识上的不足。
其次,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变化最大的十年,我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乡村肢解、分裂,然后扭曲成为熟悉又陌生的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而且尤其可悲。这一时期的乡土写作相比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显然要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也更需要坚守的勇气,因为那么多急速变换的东西胶合在一起,使得乡土更像一个巨大的混合物,更替、分离而又模糊、混乱,呈现出难以辨识的面目。在这样的时代,乡土书写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当下人们急切想知道的并且还不清楚的地方。但乡土书写中有影响力的作家尤其是“50后”作家,对这一现象的处理似乎并不能够令人满意,他们笔下的苦难、革命和道德叙事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远了,一些作家都已经步入耳顺之年,无论是经验、精力都已经很难支撑其继续创作。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乡土变化更需要被记录、被表述,对转型期乡土社会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只能是相对年轻一代的作家,很多作家也在从不同方面进行着努力,及时厘清他们具体的写作状况显得十分必要。
最后,从新世纪之初,很多人对乡土写作持有一种悲观态度,有关乡土文学消亡的问题便争论不休,那么十多年以后的乡土文学是否沿着当初学者的认识路径发展的呢?作家们书写的乡村衰落到底到了何种程度?诸多的谜团都与之密切相关,显然不对中短篇小说进行详细梳理,仅凭一些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来进行总结是不合理的,因为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对现实的理解内化需要有一个过程。当下乡土社会看似已经变得过时、单调和缺乏解释力,但乡村又未必是外显的那样衰败、空虚和混乱。乡土文学并不总是在衰落,在衰落中也可能孕育着新生,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梳理相关的作品。
考察第二个十年乡土中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概况,其实并不轻松,目前文坛上有100多种创作期刊,每年都会发表各类良莠不齐的中短篇小说,对其做一番系统梳理也确实需要费一番功夫,要想获得最为全面的认知,就必须耐下心来,选择尽可能多的样本进行归纳分析。基于此,本文主要选择了《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十月》《小说月报》《江南》《花城》《钟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上海文学》《长江文艺》《雨花》等三十余家比较主流的创作杂志为样本标的,从中择取与乡土相关的中短篇作品展开分析,力求尽可能地把握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发展态势。
二、2010—2020年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新变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乡土小说从主题和风格上看,并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仍然延续着以往的写作思路和主题前进,这一时期大部分书写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乡村现实问题上。其中非常多的作品都涉及拆迁、征地等,如唐晓玲的《钉子户》、周建新的《分裂的村庄》、潘绍东的《牵牛记》、杨小凡的《家燕》等;反映乡村腐败问题的也比较多,如李延青的《发小们的病》、冯俊科的《老戏台》、向本贵的《扯扯渡》、侯波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等;乡村留守问题的写作也很盛行,如尹文武的《拯救王家坝》、费克的《最后的山羊》、牛海棠的《自己的葬礼》、罗伟章的《声音史》等;还有书写农民进城之痛的作品,如刘庆邦的《回来吧,妹妹》、曹多勇的《迎面相撞》、邵丽的《城外的小秋》等;关注当代乡村情感与伦理变化的作品也很多,如王华的《向日葵》、晓苏的《道德模范刘春水》、贾平凹的《倒流河》、王祥夫的《归来》等。在乡村现实书写之外,还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和领域。书写乡村历史与发展变迁的作品比较丰富,如叶弥的《到客船》、陈集益的《造水库》、何雨生的《乡村照相简史》、胡学文的《〈宋庄史〉拾遗》等等;还有一些作品从怀旧的角度书写乡村,如李云雷的《哈雷彗星》、陈仓的《父亲的棺材树》、陈原的《归乡者》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也比较常见,如杨争光的《驴队来到奉先畤》、谈歌的《扩道》、董立勃的《杀瓜》、朱日亮的《野猪泡,野猪跑》等;描摹乡村世态人情的作品也有一些,如李瑾的《李村故事》、大解的《众神谱》、郭建勋的《面》等;从生态角度切入乡土的,如尹学芸的《两条河》、葛水平的《嗥月》、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炖马靴》、胡学文的《去过康巴诺尔吗》等。从凶杀和迷案角度切入的作品也有,如郑小驴的《我略知她一二》、肖江虹的《我们》、余一鸣的《风雨送春归》、曹寇的《塘村概略》、尹学芸的《破阵子》等。通过对乡土小说发展态势的简单梳理,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乡土中短篇小说和第一个十年也差不多,似乎一切都在变化,但是又似乎没有变化,作家写得似乎还是熟悉的东西,但是细读之后我们又感觉到了某些让我们不安和惊奇的东西。
(一)从“现实坍塌”到“叙事坍塌”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个十年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进城务工和拆迁并居使得无数的乡村成为空心村、留守村,大量的土地被抛荒,乡村的各种资源不断流失,乡村整体处于一种坍塌的处境中。而这直接映衬在了作品中,在阅读近十年的乡土小说过程中,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便是:乡土正在被前所未有的暮气所裹挟,老年人开始成为乡土叙事中无可撼动的主角,或者用作家阿乙的一句话表示最为恰当:回到乡村,扑面而来的竟是“聊斋”般的阴森气息。如刘庆邦的“叔辈故事系列”、赵燕飞的《落棺》、李贤峰的《扁豆花》、格尼的《和羊在一起》、葛水平的《东山草马》、费克的《最后的山羊》、盛可以的《兰溪河桥的一次事件》、陈仓的《父亲的棺材树》、蒋军辉的《风铃》、陈旭红的《亲和酒》、乌宿的《九爷爷的黄昏》、晓苏的《海碗》、王芸的《嘘村古树》、李约热的《龟龄老人邱一声》、温亚军的《崖边的老万》、丁迎新的《一个人的村庄》、毛建军的《第三日》、冬安居的《人偶村》、黄军峰的《立夏》等等,其数量非常多。可以说乡土小说正在被老人叙事所挤满,这样的作品中充斥着萧索和无聊,很多都是没有中心,没有情节,没有对话,这是在乡土小说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呈现为一种“叙事坍塌”的形态。如果以前乡土叙事还有几分热闹的话,那么现在只剩下荒凉、冷漠和栖居其上的幽怨。乡土写作中最具活力的群像是青年人,但是当下大部分作品中,青年人物开始大面积消失或者形象“灰色化”,作为主角的更少。如李约热的《村庄、绍永和我》、刘庆邦的《东风嫁》、刘继明的《边走边唱》、季栋梁的《泼烦》、王祥夫的《牛皮纸袋》、曾剑的《那年的那场雪》、余同友的《科学笔记》等作品中,以往乡土中那些引领时代、改造时代的青年英雄都普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迹于乡土之上的无业游民、刺头、混混,大部分的乡土青年都不事稼穑,强占公共资源,扭曲人伦道德。在乡村空巢化的年代里,有志气的青年都试图在城市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乡村留守青年多是被看作时代的淘汰者、零余者,他们混迹于乡村却又不依附于土地,他们既无力也无心去挑战时代,却又想轻松获得比一般村民更高的成就和认可,这导致了他们的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甚至会采取极端化的方式谋求利益——而这些很容易被理解为道德上的慵懒、不务正业和游手好闲。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乡村讨论最多的是乡土破碎化或者碎片化书写,这点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体现得最明显。碎片化意味着乡土生活日常还能隐约拼接起来,还有整体性可言。但“叙事坍塌”意味着乡土很多时候不再以完整的面目出现,作品展现的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是一部分乡村图景,以往乡土小说中那些丰富性的元素已经大面积丢失,乡村是中空的,是无聊的,完全不再是我们理想中的样式。这既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映,同时更意味着作家信心的丧失和把握现实能力的不足。
(二)从“进城叙事”到“返乡叙事”
在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和一直被视为“罪恶”的城市正越来越被绞合在一起,共处于一个对立、复杂且极具张力的整合体之中,而这又反过来继续构成乡土叙事体系的一部分,并助推乡土叙事在维系自身的同时,对各种变化进行有效洞察。新世纪初文坛上充斥着大量的底层叙事、进城叙事、农民工叙事,评论界对此展开热烈讨论的同时也折射了人们对它的不适应感、抵抗意识和不知所措。在第二个十年中,一些作家仍然耕耘于此,讲述着进城者遭受的种种磨难,如肖江虹的《我们》、修白的《空洞的房子》、陈玺的《一抹烟尘》、季栋梁的《泼烦》、胡学文的《苦水淖》、付秀莹的《春暮》等等,其中一些仍然不乏惨烈。但相比之下,大多数作品中的打工者/离乡者对城市并没有太多的仇恨,叙事也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宣泄基调。这倒不是作家热情的消退,而是因为随着现代化的拓展,乡村在文化上已经丧失了自身边界,城市和乡村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于大流动时代的城乡中国变得更加适应。
如果说以前入“城”是主调,那么现在回“乡”也开始流行起来,特别是近年来“返乡书写”话题多次在网络引起热议,这点在乡土小说中也体现得很明显。邵丽的《城外的小秋》、陈应松的《夜深沉》、陈正林的《户口还乡》等都反映了进城者对于城市的不适应以及回乡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乡土小说中也诞生了大量的还乡叙事,以“回乡”“还乡”命名的作品不在少数,比如陈宏伟的《还乡记》、梁弓的《还乡记》、王咸的《回乡记》、付关军的《回乡记》等等,众多题目类似的作品以及城乡观察视角的切换,印证了作家们对乡土的疏远、隔膜和不以为然。饶有意味的是,很多回乡叙事中充满了算命、算卦等迷信式的叙事,很多时候乡村被纳入主人公/观察者的视线中,往往并不是一种眷恋,而是一种对乡村的好奇。陈仓的《父亲进城》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为上海成功人士的儿子想要带一辈子居住在深山老林的父亲去体验现代文明——这绝非是一种传统乡土小说中的孝道叙事,而是“我”对父亲/乡村的好奇。“我”在带着父亲坐公交、住酒店、坐飞机的过程中,一直不断试图去窥探父亲的身体,甚至试图带父亲进入情色场所,探查他的反应。陈应松的《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则是通过一群城市人对乡村的肆意评判,昭示了乡村遭遇的“知识碾压”。这昭示着农业文明的本体正在消逝,它的最后一丝神秘也为城市观察者觊觎、掠夺。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回乡叙事都显得单调、无聊,充满了流水账式的记录,甚至让我们疑心:乡土叙事似乎变得越来越简单?还是理解一种过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部分作家书写中,重归故乡、整饬乡土开始成为一种潮流,比如严泽的《杨春生做屋记》中老杨回乡盖房,准备在故乡颐养天年;宋红星的《两亩地》中,退休的舅舅回乡学习种田,种植绿色蔬菜;刘汀的《草青青,麦黄黄》讲述了北京的成功白领田晓因为厌倦了都市生活而返乡创业;侯波的《胡不归》中,薛老师退休返乡带领村民调解矛盾,重修祖庙……这些都充分说明,乡村不同于城市的审美、居住、生态等功能也开始显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乡村也必然呈现出更多新的面貌。
(三)从“50后”“60后”“70后”到“80后”作家的创作
对于乡土文学,人们担忧比较多的是未来发展前景问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乡土小说创作主要是哪些人在支撑着?这里我们用评论界比较流行的代际划分进行梳理。目前看,乡土中短篇小说基本上呈现为“50后”“60后”“70后”几代作家三足鼎立的局面,“50后”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应松、刘庆邦、莫言、何顿、谈歌、夏天敏、冯俊科等等;“60后”作家主要有王华、葛水平、晓苏、石舒清、胡学文、尹学芸、季栋梁等等;“70后”代表是肖江虹、陈集益、盛可以、曹寇、旧海棠、李清源、王妹英等等。在乡土小说的评论中,人们一直对“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比较悲观,他们被认为是远离乡土并对乡土写作丧失兴趣的一代。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认识还只停留在马金莲、甫跃辉、颜歌等几个主要作家身上。经过笔者的梳理发现,在2010—2020年这十年间,“80后”的乡土写作也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比如,孙频的《东山宴》《月煞》、郑小驴的《光》《鬼节》、王威廉的《秀琴》、宋小词的《柑橘》《锅底沟流血事件》《血盆经》、陈再见的《微尘》《你不知道往哪边拐》《回县城》、陈崇正的《碧河往事》、甫跃辉的《红马》《鱼王》《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陈美者的《神仙脚》、钟华华的《纵火者》《河边》、王松的《王五归来》、孙一圣的《还乡》、曹永的《捕蛇师》《愤怒的山村》、刘汀的《草青青,麦黄黄》《魏小菊》等等。单纯从数量上看,似乎还可以,但相比于数量众多的乡土中短篇小说,所占的比重其实也并不高,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甫跃辉的《收获日》、宋小词的《锅底沟流血事件》《一把薄刀》、草白的《土壤收集者》、曹永的《捕蛇师》、刘汀的《魏小菊》等作品都显现出一定的功力,特别是马金莲近年来一系列乡土小说如《碎媳妇》《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低处的父子》《一抹晚霞》《绣鸳鸯》《坚硬的月光》等,从平凡之中发现生活的苦痛、人性的美善,显现出了对乡村生活的熟稔。更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来我们发现“90后”作家也开始涉足乡土小说,如李司平的《猪嗷嗷叫》,作品以小见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艺术惊艳。
早在十几年前,贾平凹等作家都曾担忧乡土作家离乡土越来越远,对乡土的疏离造成经验的危机。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目前来看并不紧迫,“50后”和“60后”作家是目前乡土写作的主力,即将接棒的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能够继续承担起乡土文学书写的重任。在“50后”和“60后”作家成为乡村书写主体的时候,他们只能从自身出发了解乡村特别是年轻一代乡村人的变化。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刘庆邦的《东风嫁》与刘汀的《魏小菊》为例进行比较,《东风嫁》中的米东风是农村大龄剩女,却误入夫家囹圄,遭遇家暴,在夫家没收手机之后,一心想逃出乡村;魏小菊也是一个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乡村不安分者”,她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之后发现了世界的宽广,她选择离开家庭到北京闯荡,用父母的拆迁款周游中国,又在世态炎凉中看清了自己的归宿。《东风嫁》显然还是用传统的启蒙、家族视角来看待青年人,对他们的行为还有隐隐的嘲讽;刘汀的《魏小菊》则是秉持开放的观念,对魏小菊那些“出格”的观念给予了接纳。我们为什么一直对当下乡土不满,因为乡村的变化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更是人的观念在变,这也启发我们或许只有青年人才能够把握最新的乡土观念变化,写出最新的乡村思想懵动。未来“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值得我们期待。
(四)从旧乡土风景到新乡土风景
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一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乡村风貌的变化也被作家记录,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农业文明形态下的风景逐渐远离现代人的视野,越来越成为一种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乡土小说区别于城市小说的根本所在是其独有的地方色彩、民俗元素,如果乡村失去了这些,那么乡土能够剩下的就只是区别于城市的命名、场景和曾经的记忆了。我们对于乡村的理解都是牧歌式的,优美的自然环境、整齐的民居村所、其乐融融的伦理关系,在2010—2020年的乡土中短篇小说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乡土小说在这些方面的书写上开始力有不逮,作家心态似乎并不是那么淡定,总是焦急地告诉你乡土正在发生的东西,似乎描写一种风景、讲述一段烟火故事显得过于温顺、人道亦或是抽象,就没有资格理解更深奥的当代乡土社会。诗意的乡村似乎越来越珍贵,向本贵的《竹村诉说》、高巧林的《草屋》、季栋梁的《野菊坪》、邢庆杰的《油菜花开香两岸》、张寒的《看着父亲牵羊过渭河》、王往的《渔歌》等等是为数不多的还在坚持诗意乡土的塑造。构成乡土文学肌理的是日常生活、世态人情、礼仪风俗等,这方面的描写也越来越显得珍贵,郭建勋的《面》、王方晨的《下夕烟》、老藤的《青山在》、季栋梁的《乌乎纪事》、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三题》、向本贵的《五月赛龙舟》、张志明的《乡村鸡事》、蒋浩勇的《大潭湾纪事》、付秀莹的《三月三》、申弓的《那串光灿灿的钥匙》、刘齐的《黄河婚事》等还都能够看到以往乡村的生活样式。还有一些作家作品表现出了对土地的坚守和眷恋,作家陈集益在这方面用力最深,他的《金塘河》《杀死它吧》《驯牛记》都集中描写了乡土耕作生活,体现出对劳动的赞美。温亚军的《麦子》、彤子的《瓜》、铁扬的《笨花村旧事》、凤鸣的《打干井》等等作品也都表现出浓郁的耕作风情。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和资源的投入,乡村风貌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新乡土风景也开始逐渐被描摹出来。越来越多的进城者开始返乡,大量的资本和资源下沉到乡村,乡村新农业形态频频出现。比如田耳的《韩先让的村庄》中写了经过旅游开发后的乡村:“鹭庄云蒸霞蔚,雾霭深锁,那些破烂歪斜的房子色块明晰,与碧绿的稻田形成鲜明反差。”此外还有很多新村居,比如朱辉的《七层宝塔》:“从前村子的格局,路啊,桥啊,大槐树啊,都被抹掉了,房子被垒起来,六层,平的变竖的了,他爬不动。他爬得动他也找不到,村子打乱了,乡亲们各奔东西,几十栋楼,都长得一样,他犯晕。”尹学芸的《贤人庄》中:“这是被人称为一期工程的地方,已经有了一望无际的意思。房屋推倒,果树拔了,栽了一水的银杏和木槿,苗木还小,但整齐划一。”新劳动风貌也开始出现,《草青青,麦黄黄》中的田晓开始了“互联网+农业”的经营:“麦子垂着头,秸秆已经褪去了绿意,几乎全黄了,但仍能感觉到纤维里还含着水分。麦穗要更干爽些,麦芒尖利,麦粒圆鼓鼓的。田晓一边跟网友聊着天,一边掐了一穗麦子,递给苏途,示意他尝尝。苏途从麦穗里剥出一粒麦子,颜色是褐色,但还很饱满,带着一种温润感。”这些新乡土风景昭示我们,乡村的未来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乡村在衰落,却也可能正在新生。
三、2010—2020年乡土中短篇书写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启动,乡村面目正在急剧变化,对变化的执着使得很多作家对现实形成了一种依赖,变化的现实连同对变化的焦虑一同进入了乡土写作中,写作成为一种平行行为,也使得乡土写作存在着很多症候。
(一)峻急的现实与时代反作用力的匮乏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乡土中短篇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美学的崇拜甚至是沉迷,追求此时此地,追求立竿见影,仿佛急切地去抓住时代,前文我们讲到当下乡土小说充满着大量的挽歌式书写,在乡村的衰落之外,大量的作家还写了乡村所面临的利益争夺。乡村在衰落,衰落的乡村更是充满着压抑,很多作品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极端对立,利益冲突让人触目惊心。如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中因为嫉妒邻居的钟永连利用各种手段整得邻居家鸡飞狗跳;严泽的《乾隆通宝》中父亲和儿子因为上访而家破人亡;晓苏的《野猪》中,依靠土地为生的徐乃宝被迫将石作仁一家全部枪杀;陈应松的《滚钩》写的则是善良的捞尸人为社会舆论所扭曲;尹学芸的《青霉素》中刘正坤利用医学知识杀人;王晓燕的《河之殇》中奶奶选择了杀死丈夫……甚至连儿童也参与进来,如杨遥的《闪亮的铁轨》中那个找妈妈的少年“左胳膊上有一个歪歪扭扭的‘恨’字”;戴冰的《杀心》讲述了孙子如何制造炸弹杀死奶奶;姚家明的《真实背景》叙述了12岁少年持刀复仇的故事。乡村也成了丛林社会,书写者也着实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现实的变化上来,似乎没有惨烈的叙事会使得乡村过于平常。乡土有多大的变化,书写就需要有多大的强度,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极致变得不可抗拒。乡村只剩下了城市化加速之下的挫折感、利益受损之后的焦虑感和百无聊赖的寂寞感,似乎只有充分描写乡村挣扎、破裂、求生的时候,作家才能够从根本上深度地、直接地、近乎古怪地展示乡村社会结构的一个或者多个层面。但人们对第二个十年的乡土小说又有着这样的认知:好像乡土小说离我们越来越远。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说当下乡土作家并没有紧跟时代,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看到目前乡土中短篇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便是对乡土现实问题的揭示;说它紧贴时代,很好地表现了现实,似乎也难以服众。为何很多作家眼中的乡土世界是变化的,呈现出来的东西又是那么保守以及不对称?这意味着生活形式转化为艺术形式上遭遇了障碍吗?或者生活形式本身就已经成了问题?
乡土不仅要写人的生存困境,更要关注人的精神困境,这是鲁迅等乡土文学开创者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在2010—2020年的乡土中短篇小说阅读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大部分作品对变化有着非常高的敏感度和识别能力,但是这些对现实的观察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写作资源和能力,也并没有在理解乡土上提供更为深刻的认知。写作是一种对抗时代的方式,只有在对抗中才能够解构对象,但当下时代的力量作用在作家身上,大部分作家却没有形成一种反作用力:表面看作家在努力反映时代、对抗时代,但现实变化远远超出他们意想,写作终究被时代所裹胁。人们对乡土社会气息的感知上有着确定的结构,很多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似乎还是曾经熟悉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有一种本雅明说的感觉:“似乎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由于对现实事件的过分关注,整全的、丰富的乡土似乎便被留在了身后,乡土只是告诉我们正在发生的事件,却没有了交流的愿望甚至是能力。所以乡土书写者善于收集那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熟悉的面孔、执拗的灵魂等诸如此类的让我们熟知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却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亲近。这使得乡土写作各个方面呈现出紧张和焦虑,使得乡土书写衰弱的同时又在加速——而加速却是以一种盲目的状态进行的,外显出来的却是力度与美学的矛盾,付出与接受的不相称。这一时期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衰弱的反作用力,既没有塑造早期现实主义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又丢失了乡土文学传统中的文化反思力度,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二)结构性写作:有限的乡土表达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农民的精神、观念、意识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传播学理论中,一个社会如果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系统,那么就可以被认定为现代社会。从目前农民对于微信、抖音、快手等大众媒介的青睐来看,乡村已经在某些方面变得非常“现代”,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指出,信息社会最大的力量是移情,在参与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移情让人们对异域生活和价值观念产生认同和渴望。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乡村在新媒体的催化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保守、固化,农民在审美、个性和认知上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似乎只是获得了有限的表达,乡土小说无法在整体上揭示出农民的时代精神风貌,也就难以满足人们对于乡土的期待。那么农民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最为真实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目前对于这样的追问所给出的答案,可能不光读者不会满意,甚至连作家可能对自己也不会满意,也难怪会出现像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这样近距离、急切地去触摸乡土心灵、精神的民族志式的著作。
近年来有一些中短篇作品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并不一定是因为艺术上多么精湛,而恰恰是直面了转型时代的种种精神困境。如侯波获得“马烽文学奖”的中篇《胡不归》,叙述了后乡村时代“新乡贤”如何重整乡土及其面临的困境;朱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七层宝塔》则书写了村民变成市民的种种心路历程。另外我们要提到的是郑局廷的《界埂》,其对于乡村各种利益冲突并没有流于表面的村霸问题揭示,更是深入发掘农民如何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的思想变迁。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则是通过父亲做微商的经历来重构了我对父亲和乡村的理解。这些作品都是深度书写转型的作品,乡土社会的转型不仅仅只有冲突,更有精神上的困境,而这些要远比以前更为复杂。所以,对于当代作家而言,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非常足。他们一方面急切地去反映现实,触摸现实,一方面又习惯性地漠视那些乡土中的变化力量。当下乡土书写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乡土书写使现实困境广为人知的时候,也为自身的艺术升华制造了障碍。
当下的乡土写作越来越进入一种结构性写作时代。结构性写作并非传统意义的作家分化以及认知的分化、美学的分化,更是视野的分化,这种写作很容易只看到局部,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眼中、理解中的乡土,用单一观点去理解乡土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丧失了对乡土整体的认识欲望。于乡土小说而言,时代的发展更新了事物,却也让很多作家与乡土甚至是自我的关系变得隔膜甚至陈旧了。我们自以为走得很远,自以为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其实我们仍然处在自我的垂直线上。如大部分“50后”和“60后”作家缺乏对青年生活的了解和认同,他们看到更多的是乡村的凋敝和鳏寡孤独;对于“70后”和“80后”作家而言,他们基本上居住在城市,对乡村的了解有限,回乡主题和葬礼主题就很容易成为写作的焦点。这样的乡土写作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典型环境,却极少有与之相配的典型人物,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但总是让人感觉是残缺的。
(三)美学的虚空与乡土的隔膜
乡土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先锋性,在于其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美学范式。当下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形式试验、方言写作的急剧锐减。乡土小说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充斥各种的形式试验,不断探索可能的审美表现方式也是乡土小说不断发展的动力。1990年代以来还有阎连科、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不断对乡土进行形式创新。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乡土小说中,我们会发现“另类”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比如阿乙的《撬坟记》用一种戏谑化、狂欢化的语言反思了人们对乡村丧葬制度的接纳;叶辛的《大山洞老刘》是形式上比较特殊的一部作品,采用了“微信体”对话的方式展开,讲述了知青们对于老刘的回忆和乡村变化的感触。“90后”作家索耳的《乡村博物馆》也是一部写法上较为独特的作品,不分段的、粘稠式的表达从侧面印证了书写乡村的困惑。而形式本身也具有表达性,在台湾的“后乡土”或者“新乡土”写作中,形式的探索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下作家形式探索兴趣的降低,是对乡土书写信心的不足,还是找不到恰切的表述方式呢?乡土方言写作也面临着危机,呈现着锐减的趋势,宋以柱的《摸灯》、盛可以的《喜盈门》、季栋梁的《野菊坪》等等都是方言写作的代表。乡土小说新形式的锐减也从侧面印证了乡土创作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只不过在陈旧主题上重复着单调的乐章。所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乡土小说中审美也成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担心的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美学色彩蜕变的问题:一方面是对乡村剧变的盲目和峻急的呈现——有时这种粗鲁甚至让我们瞠目结舌;一方面是美学上的虚空,缺乏温情,流水账泛滥,民俗风情的大面积消失,甚至要借助于新闻启发来完成自己的故事,比如凡一平的《上岭村丙申年纪事》直接借用了闻名全国的“佘祥林案”完成故事的讲述。这看似是一种主动选择,又像是一种自发性行为,时代在变化,我们并不必然像以前一样书写乡土,但无论哪一种写作都必须以对乡土的深度关怀为己任,对于人性体察、对于文化的挖掘都需要耐心和升华。百年乡土文学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经验是:书写乡土其实是一种雅典式的信仰,无论乡土如何,都需要作家知识、智慧才能够完成对象化。作家不得不缓慢地、按部就班地、甚至痛苦地前行,与此同时,自身的认识和思维能力也得到丰富和扩展。人们对于乡土都会有着不同的道德姿态,否定乡土与美化乡土都是常见的,最为可怕的是书写乡土的同时又在漠视乡土——对它的命运心有戚戚,对它的美学又不以为然。
或许属于乡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加上大部分的乡土写作者已经远离乡土,极少人会把乡土视为自己同代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调整自己去适应乡土,发掘其美学上新的可能。乡土借助太多激烈的东西来认识真相,作家与现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正是在这种依赖中,作家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却很少被看到,我们似乎越来越进入到一个写作乡土而不是乡土写作的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乡土和乡土写作还是不同的,前者更为宽泛,乡村只要作为背景存在即可,而后者则是文化熏陶的产物,这直接决定了乡土写作是否能产生“在地感”。所谓的“在地感”意味着我们能够把一个人物同他的生存周边联系起来,乡土是他们思考的内容,也是思考的工具,这样的认识中固然存在缺陷,但是却能够给乡土写作带来可行的条件、有用的实践,并产生必要的稀缺性。19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中,人物总是能够和现实社会产生本质关系,人物成为揭开社会之谜的钥匙,社会关系深度嵌入到个人生活和行为中。但是当下的乡土写作中,人物与周边已经脱钩,在相当多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乡土的演变,乡土书写各种内部的、深度的关联已经被取消,也直接影响了美学质效。而乡土美学精神的空乏,更有可能危及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百年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都与乡土相关,比如莫言、贾平凹、汪曾祺等都是以关注乡土变迁为人们称道。真诚的、本然的乡土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破解,它只需要日常生活的还原,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那么乡土文学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