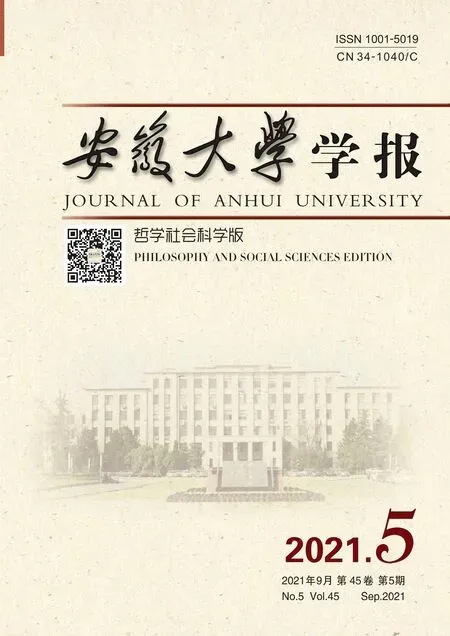《庄子》的语言自觉与其神秘论道之理解
林 凯
《庄子》一书内容广博,要旨则在“论道”:一方面它对终极本源之“道”的存在、形态和功用作出了一定说明,另一方面也对最高存在境界的“得道”状态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何理解这些论道之言,是阅读《庄子》的根本问题。然而,无论通过作者直陈还是寄寓他人言语,《庄子》论道给人的第一感觉却是狂妄虚阔,神秘难解。仅从文字表面看,其所谓“道”是一种化生天地万物但又超越时空、无法定格的超越性主宰(见《庄子·大宗师》论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一段),而其所谓“得道”则是一种齐同万物以至可以乘风御气、水火不侵的类神仙状态(见《庄子·逍遥游》对“姑射神人”的描写)。这样的超验论述,首先就容易引发读者经验上的质疑,容易被斥为“大而无当”“狂而不信”(《庄子·逍遥游》)。若要在讲求理性与实证的当下语境中对庄子论道作出合理的诠解,这样一种读者质疑显然无法绕开。
那么,如何回应这些经验质疑,进而阐发《庄子》论道的“真正”意义?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开拓出多种理解,典型可见两种方案。第一种,将这些神秘描述理解为对某些抽象哲学义理的隐喻说明,从而使文本可以适应大众一般的理性把握方式。这种哲学化理解奠基自郭象,并流行于后世,在当前讲求理性的学术语境下更是受到推崇。第二种则认为《庄子》论道实际是对某种真实经验的直接描述。极端者如某些神仙道信仰者会认为庄子就在描写真实存在的“神仙”,但更多人持温和态度,从道教内丹功夫出发认为它是对静修(或冥契)体验的准确刻画。古代学者成玄英、陆西星在功夫论上作出了经典的阐发,现代学者如杨儒宾、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则努力贯通日常一般经验与非日常的静修经验,以使后者获得可普遍化的理解。从这些探索可见,后世学者试图辩护,《庄子》论道应当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或为一种哲学隐喻的意义,或为一种真实经验的意义。
以上“疏通”方案使庄子的论道之言获得了一定的可理解性,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读者的经验质疑。问题是,这些疏解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庄子自身所期待的理解方式从而真正切中作者之“本意”?后世读者如果完全轻视作者意图,仅仅执着自身特定的理智要求去疏通文本,则未免存在强使庄子论述屈从读者俗常理性的嫌疑。在文本诠释中,尊重作者的表达方式与意图应该是一个优先的原则。如果能经由作者提示的线索指引,找到所谓“作者的方式”,也即作者惯常的表达方式以及相应的作者期待的理解方式,那么这种兼顾作者意图或期待的理解路径就将更具有文本的合法性。以上疏解方案对自身的“理解方式”在文本上的合法性往往缺乏足够反省,这或许在解读其他诸子文本时问题不大,但在《庄子》这里就显得不够完备。因为《庄子》文本有着相当独特的表达特色:除开像其他诸子那样对一般语言使用有所反思,庄子更对自身语言使用有清醒的“作者自觉”。比如庄子清醒地知道自身言说的特色,并对自己为何如此言说作出了解释(见《庄子·寓言》论“三言”),他也知道自身言说可能引发经验质疑,因此积极作出了回应。这些自觉回应强烈地表明:在当时诸子论辩语境中庄子的神秘言说其实处于极大压力之下,他无法完全自说自话,而不得不直面来自读者(或对手)的诸多质疑。因此,庄子对其语言表达作出了一定的设计,并在其语言实践中执行这些设计,同时还对这种设计本身有自觉说明,以为自身辩护。这样的“作者自觉”显然可为读者提供某种阅读指引。集中分析作者对读者经验质疑的自觉回应与处理,我们可能由此领悟作者希望其言说得到怎样的理解,从而获得一种具有较强文本依据的理解方式。
本文要做的工作是:考察庄子对自身语言使用有所自觉的那些文本,探讨庄子是否对读者质疑有所自觉?若有所自觉,他又如何回应这些质疑?进一步,为了处理或化解这些质疑,他宣称或实际采取了怎样的语言策略?这些策略的实际效果又是如何?经过此番分析,我们或能获得作者提供的阅读指引,从而对庄子论道的意义有一番新的理解与定位。
一、对读者质疑的自觉
庄子论道狂妄虚阔,容易招致世人在经验方面的质疑,这一点作者本已自觉。如《逍遥游》开篇讲述大鹏故事后,庄子直接描述了一种最高的得道人格:“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字面而论,此种飞升遨游的身体机能显然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读者阅读至此随即产生疑惑。继续阅读该篇,我们没有看到庄子以直接的方式回应这种隐含的读者疑惑。然而他并非没有自觉,他只是将这种自觉“嵌入”了随后的肩吾寓言之中:
肩吾问于连叔曰: “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庄子·逍遥游》)
该寓言“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姑射神人,实际就在回应庄子一开始主张的得道人格;肩吾听闻此言而有“大而无当”“惊怖”“不近人情”“狂而不信”等经验上的疑惑,几乎就是我们开篇阅读庄子之得道人格时的疑惑。庄子在直陈得道后继续构造这样一个闻道反应的寓言,当是有意回应读者的质疑心理,并对自身言说进行辩护。我们容易由此感受到,作者对其论道所可能引发的读者反应是有充分自觉的。只是按庄子的方式,他并不通过直接论述来表达这种自觉,而是将它“嵌入”寓言之中。
以肩吾寓言为范例,可以认为,那些包含听者在闻道后产生疑惑的寓言实际“嵌入”了作者对这种读者反应的自觉。我们还能在以下寓言中看到这种自觉:《齐物论》中孔子将听到的得道之言斥为“孟浪之言”,瞿鹊子则以之为“妙道之行”(但却被境界更高的长梧子批评为“大早计”);《秋水》中公孙龙听闻庄子言论后“汒焉异之”;《达生》中高人扁子担心束于儒教的孙休在听闻得道之言后“惊而遂至于惑”;以及《庚桑楚》中南荣趎无法理解所听到的奇妙的修道言论,感叹自己闻道只能“达耳”而已。这些描述大致展现出读者对神秘道论“无法理解”的三种反应:第一种是否定,当对方观念与自身立场有所冲突并造成压力时,最容易引发自身的惊恐乃至否定,如肩吾、孔子、公孙龙和孙休;第二种是相对中立的不置可否,保持谦虚,但按常人经验依然无法理解大道,如南荣趎;第三种则是肯定,但它却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肤浅的认可,如瞿鹊子。综合这些细致描绘的闻道后的听者反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子的确自觉到其高妙道言将引发读者经验上的疑惑与误解。
如果说,肩吾寓言将庄子论道之内容的特点定为“狂、大”还只是从读者角度作出的评价,未必不会存在误判,那么,看最后《天下》,作者自评其言“谬悠、荒唐、无端崖”和“瑰玮、参差”,则庄子论道之狂妄虚阔,实际也是当时作者和读者的共识了。可见,庄子自觉地意识到了自身言论的奇特,也意识到其可能引发的读者质疑。
二、作者的解释与辩护
既已自觉到质疑,庄子又将如何理解并回应这些质疑?换言之,在庄子看来,这些质疑究竟怎么产生,性质如何,责任归谁(作者表达的失误抑或读者素质的不足)?在庄子作出的辩护中,责任全部转移到读者一方,也即读者自身的理解局限造成了这种疑惑。如肩吾寓言借助连叔为这种狂大之言所作的辩护: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庄子·逍遥游》)
以耳目之聋盲作比,庄子指出读者的知见也存在“聋盲”,这是造成道言难解的根本原因。读者的习常知见有其特定界域,看不到界域之外;如果固执己见,那么界域之外的可能性只能被直接否定。类似的类比还体现在《大宗师》意而子问道的寓言以及《庚桑楚》南荣趎感叹“达耳”的寓言之中。特别在《大宗师》中,这种知见局限的具体内容还得到了进一步界定: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庄子·大宗师》)
在这个寓言中,意而子的知之聋盲被赋予了更明确的内容,即遮蔽于“仁义”与“是非”,也即束缚于名教与论辩。这种束缚造成的局限,更清楚地体现在《秋水》公孙龙寓言: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汒焉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
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与?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庄子·秋水》)
这个寓言直接谈到“庄子之言”本身的特点和所引起的读者反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自身言说效果的自觉。它也表明,作者所考虑的读者质疑并非面向所有大众,而是有特定针对,即主要针对当时语境中束缚于名教和论辩的诸子——这才是庄子实际要与之竞争的对手。这个或有虚构成分的公孙龙,既明“仁义之行”,又善“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其能兼顾“仁义”与“是非”,实是当时诸子之典型。综合其他质疑庄子论道的人物,如《逍遥游》以为“大而无用”的惠子,《齐物论》以为“孟浪之言”的孔子,他们都未能超出“仁义”与“是非”的束缚。可见庄子所论知之局限具体便是束缚于当时名教与论辩,其代表人物即为当时的儒墨学者,正是儒墨之是非导致了“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秋水》言“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儒墨学者便是这样知有聋盲的“一曲之士”。
从以上寓言所“嵌入”的作者的自觉回应看,道言之难解罪在读者自身的知见局限。但由于庄子并没有在寓言中理性地分析知见何以局限,而只是借助高人的姿态作出类比性的讽刺,其显然并不能真正说服读者(特别是那些好辩的诸子),并不能让读者甘心承认问题就在自身。退一步说,即便这些高姿态的讽刺能让读者泛泛地承认自身必有不足,它们也不能证明庄子对道的表述就是正确的。因为,庄子如何能保证自己没有类似的知见局限?彼之非不能保证此之是,只能保证此之“可能是”。所以,这些寓言给出的解释和回应仅仅表明作者对读者质疑有所自觉,并有意为自身辩护,但其辩护尚未给出充分理由,也没有进一步给出具体的处理或化解。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就像文本中的高人那样仅仅显示姿态,那么它只能加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抗,这对道言意义的顺利传达并没有多少益处。但实际上,庄子并不停留于此,他还有更多积极的处理。
三、化解质疑的语言策略
自觉到读者质疑并对读者素质进行讽刺性批评,这并不能消除读者质疑,也不能真正有效提升或引导读者;相反,它可能造成激烈的对抗。若想化解质疑,使意义得到更好传达,庄子需要在批评之外做更进一步的引导工作。比如对其道言进行某种程度的“顺从”读者理解习惯的说明(顺向),或者采取某种语言策略激发读者对自身局限的反思,并将其引向某种新的理解方式(转向),如此等等。就文本展现看,庄子在这一层次的确作出了自觉的说明以及相应的表达设计,向读者传达了其引导的努力。
(一)“三言”修辞
想要化解质难,最简易的方式也许是一开始就不要让读者产生疑惑。完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暂时缓解读者的质疑情绪则可能实现,比如不要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通过其他方式间接说出——由此容易想到庄子的“寓言”策略。庄子使用了寓言,并且更重要的,他以明确自觉的方式使用寓言。这种自觉表明,作者关心读者反应并有意积极处理相关质难。“寓言”或者说“三言”,乃是庄子处理读者质疑的“明确”自觉的策略: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庄子·寓言》)
这段直陈的议论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作者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三言”理论,而是针对自身文本的语言使用方式进行说明,表明自己有意使用了“三言”方式。如“十九、十七”表明的是寓言和重言在《庄子》文本中实际占据的比例,是作者对自身语言实践特点的自觉归纳。如果作者不做这个归纳,读者自己其实也可以在阅读中归纳出某些作者(不自觉地)使用的语言策略,并可将之称为文本“隐含”的“作者方式”;而现在作者提前自觉归纳,还对自己为何使用这些策略给出解释(比如“非吾罪也,人之罪也”“所以己言也”),那么这种“作者方式”就不是隐含的,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有意选择。可以说,“三言”是作者“公开”的语言策略,它表明作者的特殊用心。
按庄子宣称,他使用“寓言”,根本上是考虑到读者同是异非的习常偏见(“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出于避免与读者之间直接的是非论争,庄子选择寄托他人之口,而不以作者直接议论的方式去言说。从文本实践看,他也的确贯彻了这一设想。这典型体现于《逍遥游》,从作者直谈“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的神人,转变到寄托肩吾寓言去谈“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这种转寄他人的策略,使得读者在心理上能暂时与神秘的论道话语保持距离,不会马上抗拒作者的论述,不会执意要与作者争一胜负。这至少避免了读者与作者的直接争辩,尽管读者依然不能理解这些神秘论述。也即,寓言修辞可以缓解读者的质疑情绪,让作者自身得到暂时的安全。不过,它也仅仅是“缓解”而非“化解”,它并不能真正消除质疑。因为即使不质疑作者本人,读者也会质疑被转寄者。
同样,庄子采取借重先贤时哲的“重言”形式,则要利用当时尊贤的语境,虚构圣贤替自己说话,以使读者保持谦虚自省乃至“已言”,也即中止争辩。这显然也是考虑到当时读者好辩是非的习惯。当然,“重言”的圣贤权威也能一定程度地增加言说的可信度,使其比单纯“寓言”更好地抑止读者质疑;只是,庄子的借重往往以圣贤之口说庄子自己的话,读者容易感知其中怪诞,因而其可信力又大大减弱。应该说,“重言”更重要的作用还是在中止论辩,以让作者安全。而庄子采取“浑圆无际”的“卮言”,目的是为“穷年”(“悠游终生”)、“得其久”(“维持长久”),实际也是为避免与读者发生论争。因为若陷入论争,言说者便难以“悠游”,言说本身也难以“长久”。
综合起来,按庄子自身的解释,其采取“三言”的修辞策略主要出于对当时读者素质(即好辩是非)的考虑,避免自己的言说遭受直接质疑而陷入无休止的论争。在实际的修辞实践上,他的确贯彻了其“三言”主张;而就实际的修辞效果来说,这个语言策略也基本能实现他想要的避开质难的阅读效果。这一自觉表态以及其语言实践上的贯彻,显示出庄子本身就试图以积极的方式来化解读者对其神秘论道的质疑。只是,这一修辞策略的效果是有限的,它并不能真正消除读者的阅读疑惑,也不能使包含在寓言之中的那些论道狂言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尽管不少学者认为“三言”是理解《庄子》的“钥匙”,但庄子在该处的自觉提示尚显粗略,其意义也许不必夸大。可以说,它仅仅是作者处理读者质疑的第一步。而这一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体现作者处理质疑的“明确”的自觉。
(二)情节转变设计
庄子虽然自觉提示了“寓言”修辞,但其提示还相对简单,因为它尚未对寓言运用中更深一层的独特形式作出自觉说明。比如神话的使用,比如抽象概念的拟人化,比如对话情节的巧妙设计,这些都是“寓言”框架之下更深层的修辞,比单纯“寓言”一词更能影响意义表达,是我们探讨庄子修辞时更应注意的层次。尤其是情节设计这一方式,庄子往往在论道寓言中设计一种从“(问者)不理解道(答者)不言说道”到“理解道言说道”的情节转变,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解惑过程。我们或可进一步猜想:某种意义上,寓言的情节转变设计暗示了作者对读者质疑的回应和化解,它是庄子处理读者质疑的更进一步的语言策略。不过这种设计毕竟不像前面“三言”那样得到作者“明确”的自觉说明,这里尝试结合庄子自觉谈到对读者素质转变的期待意图,去看其情节设计中显示的听者(聆道者)的素质转变,以说明这种看似隐含的策略其实已有一定的作者自觉意味,可以看成作者“半自觉”地处理读者质疑的方式。
1.“半自觉”的策略
从庄子某些自觉的直白看,他对理解的渴求是非常强烈的。如在《外物》篇他是如此渴望一位得意忘言的听者:“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在《齐物论》中则通过他人之口感慨:“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在当时诸子之中也许惠施还能一定程度地理解庄子,可惜他去世得早,“自夫子(即惠子——作者按)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可见,庄子并不像某些遁世高人那样高傲地轻视他人的理解,以至孤芳自赏。这些作者直白还显示,庄子渴求理解却也不会轻易顺从世俗错误的理解习惯,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理想听者”,也即一种素质提升的听者(“忘言之人”或者“大圣”)。这里表明了庄子对听者素质转变的“自觉”的期待。
同时,庄子又相对隐蔽地通过其他高人之口,反向强调了对听者的期待:如果听者没有准备好相应的理解素质,也即其知见局限并没有打破,那么最好不要与他谈论关于道的狂言,因为这很可能加重听者的惊恐或迷惑。典型如《达生》中束于儒教的孙休在听闻得道之言后,作者表达了“恐其惊而遂至于惑”的忧虑: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鸟止于鲁郊,鲁君说之,为具太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忧悲眩视,不敢饮食,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今休,款启寡闻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载鼷以车马,乐鴳以钟鼓也,彼又恶能无惊乎哉!”
这里通过扁子之口说出:对于束缚于名教、见识短浅的听者,得道者不应告知超出其理解范围的“高言”,否则将引起其惊恐迷惑。离开后的孙休很可能已陷入迷惑状态;肩吾寓言中肩吾听到类似的“狂言”后的“惊怖其言”,或能间接暗示这一点。《知北游》也继续通过他人之口表达了这种不应该对未具相应素质之听者言道的主张,如在师傅老龙吉去世后,神农感叹:“天知予僻陋慢訑,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老龙吉“藏”其狂言而死的做法,实际隐含对听者素质的一种顾虑。《秋水》公孙龙寓言中,作者最后并没有继续解释神秘的“庄子之言”的内涵,而以一个“邯郸学步”的隐喻对束缚于名辩的公孙龙进行了劝退,显然也暗示了类似的顾虑。
因此,比较正反双向的作者表达,庄子对转变读者素质以使读者获得对其论道的正确理解,有着非常“自觉”的期待。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自觉的期待是否又会贯彻到其文本某种具体的修辞实践之中?庄子对此没有明确宣示。这跟庄子自觉宣称要将其消除争辩的意图通过“三言”修辞表达出来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判定,庄子的某种修辞选择必然受到他对读者素质之自觉期待的影响。但是,如果能找到较多案例说明,某种“隐含”的“作者方式”的确明显表达出一种转变听者素质的意图,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修辞方式就是在贯彻庄子对读者素质的自觉期待。
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比如《秋水》中北海对已经突破自我局限的河伯说:“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涯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通过北海之口,作者明确表达听者素质转变乃是可否言道的关键条件。并且在其后北海与河伯的对话中,我们也看到北海对河伯进行层层破执,直至最后才对道有所论述,这实际就突显了听者素质的重要性。又比如在《人间世》中孔子也只是在颜回“心斋”之后才说出关于得道的信息,而在之前不过以论辩破执的方式对颜回进行示训。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后文还会有具体展开。这就足以说明,在寓言中通过情节转变的设计来彰显听者素质转变的重要意义,应该是一种作者惯用的隐含的表达方式。结合作者对读者素质的明显自觉的期待看,这一隐含的惯用表达应该就是对其期待意图的实际贯彻。也即,庄子虽然没有直接宣称要通过某种语言策略来承载其所直白的对读者素质的期待意图,但他实际已经这么去实践了。这种无明确宣称但实际已在实践的方式可谓之“半自觉”。
通过“半自觉”的转变读者素质的寓言情节设计,庄子给出了对读者质疑的积极处理。他究竟希望读者转变到哪一层次,具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转变?庄子对此尚未有自觉的明示。但其对情节设计的“半自觉”,将会引导我们特别关注其论道寓言中所设计的听者转变,从中或能有所发现。
2.理解之指引
在寓言情节设计中突出听者素质的转变,这样的案例很多,我们可以从促进听者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不同,区分出两类。
第一类,说者以话语的方式对听者进行“直接”引导,破除其思维执见,乃至向其指明修行的方向,帮助听者实现自我提升。前面提到《人间世》“心斋”寓言中孔子对颜回的话语引导便是典型。孔子在说出最后那番得道之言前,他对颜回进行了多番曲折的心理引导,努力使听者心灵发生转变,为聆听大道做好准备。他先是扑灭颜回准备以道德说教进行救世的满腔热情,继而破除颜回更为精明的顺从策略,以至颜回不得不承认“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到了这一步,孔子还不着急说出大道,继续要求颜回修行“心斋”;在虚静修行之后,一切水到渠成,孔子才主动说出最后的得道之言。整个故事通过曲折巧妙的情节设计,显示出听者颜回心理逐步转变的过程;通过最后一步静修的飞跃,听者的理解素质终于准备完毕,论道之言便在这样的情境下说出了。类似的案例还有《秋水》中北海通过层层的大小辨析引导河伯突破视野局限;《知北游》中老子回答孔子问道之前要求“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也是先引导听者进行精神静修和放弃知见。这些故事设计突出的是,在言道之前说者主动对听者的观念障碍进行了清理。
第二类,说者仅仅作出“间接”引导,听者就主动进行静修,获得自我提升。这种听者主要依靠自身进行转变的案例,典型体现于《在宥》的广成子寓言。按寓言的设计,黄帝首先向得道的广成子咨询如何利用大道进行“治天下”,结果遭到广成子的拒绝与讽刺;其后“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黄帝再问则仅仅咨询如何利用大道去“治身”,结果广成子大喜,非常主动地对大道进行了开示。这个寓言描述了前后两次不同的问答情况,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提供了诸多的暗示。前后对比,既有问者所问内容的变化(从“治天下”到“治身”),也有答者所答内容和态度的变化(从拒绝回答到主动回答)。而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关键在问者自身素质的转变,也即黄帝经过退隐静修(“闲居三月”)之后得到了巨大的心理净化(通过所问内容的变化来显示这一成就),为聆听大道作好了真正的准备。类似的案例还有《庚桑楚》中南荣趎向老子问道,在接受老子对其功利之心的批评后,南荣趎也主动进行静修:“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然后老子才逐渐将大道说出。这些故事设计突出的是,经由说者的间接引导,听者主动进行静修,清理自身观念的障碍。
以上两类,无论促进听者素质转变的主要因素在说者还是听者,转变的完成最终都要依赖双方共同的合作。具体就是:静修是实现转变的关键一环,它必须听者亲身践行;但将听者引向静修却是说者的工作,他会根据听者自身不同的特点,或通过详细的辨析进行强力破执,或通过拒绝的姿态进行富有启发的点拨。这些强调听者转变的寓言设计表明,得道者是不轻易说出论道之言的,他要考虑听者的理解准备以及可能的听者反应,尽量采取适当的方式保护未有准备的读者不受迷惑,也保护自身的言说不被质疑或误解。这些考虑也同样适用于庄子本人。
从这些情节设计,我们可以获得对庄子所期待的“理想读者”的基本认识:首先,他有良好的自我反省能力,能意识到自身知见局限并在观念上作出自我突破;其次,他有良好的情绪状态,注重内在精神而不外求功利,虚空宁静,极具包容性。那么,如何才能达成这样的理想状态?按以上寓言提示,超理性的静修是最为关键的锻炼方式,但理性的自我反省和视野突破也不能忽视。《秋水》中北海的层层辨析,《人间世》中孔子的连续辩难,都充分利用了“理性突破”这一主体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过分强调非理性的静修而完全排斥理性的作用,仅仅认为理性是对大道理解的阻碍,那么就错失了庄子对理性之积极作用的发挥。
那么,这一语言策略的效果究竟如何?它真正消除了阅读者的经验质疑吗?进一步地,它促进了读者对其论道之言的理解吗?
就语言策略所要传达的观念内容看,读者的确能够通过情节的转折体察到庄子对读者素质的期待意图,了解庄子希望读者提升到哪个层次以及如何去提升。但是,接收到这一观念暗示与认同这一观念,却是两回事。寓言中的听者通过静修做好了聆道准备,但读者仅仅是阅读到这一点而并没有实际去静修,那么读者自身其实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并不会如寓言中的听者那样理解说者所论之道。最理想的情况是,读者或能认同庄子传达的静修有助理解大道这一观念,自身既未能静修,那就保持谦虚;这样即使不能正面促进对庄子道论的理解,却也能在较大程度上化解读者质疑,使其心存敬畏。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持有不同观念的读者(比如当时崇尚理智的诸子)不会轻易认可这个观念,他们更容易否认难以经验的静修过程。对于此类读者,庄子寓言所提供的另一种“理性突破”的辩说当能起到一定的辩护作用。即使不能在“立”的意义上直接促进读者对道论的理解,它至少能在“破”的意义上推动读者理性地作出自我反省,消除自身执见,这样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读者质疑。
而就语言策略自身的形式来看,寓言情节的发展能带动读者不断调整阅读心理,使得阅读本身成为一种实际的“精神锻炼”。语言修辞的形式所具有的这种功能,或比其传达的内容更值得关注。读者即使接受了静修观念,却未必就能真正去“修炼”;而在寓言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实际地跟随作者描述的节奏,自然地调整心理预设,缓和要与作者争辩的心理,并极容易将自身置入故事之中(如将自身置换成寓言中的问道者,将庄子置换为答道者),顺从作者引导而作出自我反省,拓宽视野,转换视角,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对自我的心理突破——这是阅读中真实发生着的精神的“锻炼”。这个“锻炼”对读者思维固执的破除是有效果的,它与庄子所要传达的破执观念正好相互促进。不过,它也只能止步于此,无法真正进入“静修”,因为“静修”必须施以额外的身心修炼,是阅读锻炼无法替代的。阅读过程中的“锻炼”主要还只是调动读者习常性的经验记忆和理性,使其对习常观念或“破”或“立”;至于想要由此建“立”对某种超常经验(“心斋”“得道”等)的切实理解,单纯依赖阅读是难以达成的。
显然,相较“三言”修辞的避开质疑,这种更为深层的情节设计策略在化解读者质疑方面有着更为实质的效果。它给出了“静修”的指引,也进行了“理性突破”的正面化解,更在修辞形式上提供了相应的阅读“锻炼”。虽然它在“立”的促进上依然尚有不足,但在“破”的消解上颇有成效,至少可能使读者“悬搁”质疑,恢复中立的、谦虚的接受状态。
(三)理性辨析
前面提到,对于庄子道论的实际读者也即当时崇尚理智的诸子而言,庄子寓言所运用的“理性辨析”比起“静修”之论更具有实质性的化解质疑的效用。在作者“半自觉”的情节设计策略中,“理性辨析”是其引导听者转变的常用方式,在《人间世》“心斋”寓言、《秋水》北海寓言、《庚桑楚》南荣趎寓言中反复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理性辨析”实际也是一种“隐含”的化解读者质疑的方式。另一方面,前文“作者的解释与辩护”一节已谈到,肩吾寓言、意而子寓言、公孙龙寓言都“嵌入”了庄子对读者“知见局限”的自觉批评,但由于庄子并没有给出对“知见局限”的理性分析,这些寓言蕴含的批评并不能真正化解读者质疑。将这两方面相互参照,则发现,肩吾寓言所缺少的对“知见局限”的理性分析,却在北海寓言的“理性辨析”中得到了某种展开。也就是说,庄子对读者的“知见局限”有明确自觉(见肩吾寓言),并且,他虽然没有宣称要以某种方式去破除此种局限,却实际使用了某种方式(即理性辨析)去破除(见北海寓言)。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理性辨析”也是庄子自觉地用来破除读者执见、化解读者质疑的语言策略——尽管这种自觉也相对隐蔽。
不过,包含在上述寓言中的理性辨析还是比较有限的。笔者的目标是,将我们的视野扩展到寓言之外那些通过作者直陈方式对知见局限所进行的辨析,比如《齐物论》就有大段这样的直接讨论,它们更为丰富和深刻。对于尽量要避免与读者进行直接论辩(见“三言”)的庄子而言,通过作者自陈方式进行“理性辨析”显然是一种艰难而有意的选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作者为了处理读者质疑作出的自觉选择,应该与其在寓言中使用“理性辨析”是相通的。这样,通过分析《齐物论》中作者直陈的“理性辨析”的语言策略,我们又可更充分地把握庄子对读者质疑的积极处理。毕竟,就处理质疑的力度而言,以直陈方式对读者知见的必然局限进行理性说明,应该比避开质疑的“三言”策略、调整读者心理的情节设计更直接有力——特别是针对本来就偏重理智、好辩是非的诸子而言。
那么,从理性辨析的角度,读者知见的局限即“知”之聋盲究竟体现在哪?庄子所批评的知见局限,究竟是针对知见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无法避免的局限,还是批评特定类型的知见而已?前者关涉在彻底意义上取消知见,后者则只涉及对知见的持续完善。就《齐物论》看,庄子并不想纠缠于当时流行的坚白同异、义利之辩等具体的是非之争;“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齐物论》),他要从整体上反思一般性的是非之争,揭示人类知见本身的根本性局限。
《齐物论》指出,当时诸子普遍处于是非之争中,但这种争论在庄子看来并不会导致“真理越辩越明”,反而遮蔽了大道,即所谓“道隐于小成”。何以如此?究其原因还是在论辩双方不可避免的自我立场局限。按《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一段分析:论辩双方往往以自己的立场为“此”,以他者为“彼”;兼顾双方视角去看,则任一方都既是“彼”又是“此”,故有“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此之分实由“我—非我”视角造成,二者本一体两面,故有“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即彼是相因。进一步,由于论辩主体往往“是”此“非”彼,则既“此”又“彼”的任一方所作出的判断就同时带上了“是”与“非”两种属性,即“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因此,在庄子这里,关于某物的任一判断若从此判断者立场看均属“是”,若从彼判断者立场看均为“非”;彼此立场是同等有限的“一体两面”,没有谁能更为优先,因此基于“彼此”立场作出的“是非”判断也是同等有限的“一体两面”——故而是非相对,是非相因。可见,在根本上,是非分判源自论辩双方难以避免的视野局限性;要超越它,除非超出自我局限,消解“彼此”,“得其环中”(《庄子·齐物论》)。
通过直陈的辨析,庄子指出知见局限的根本成因在论辩主体一开始就必然具有的立场或视野局限,他总是见“此”不见“彼”,无法获得整全视野的认知。这个分析在逻辑上是具有合理性的,在破除读者的理智执见方面颇具力度;而阅读这种论辩,读者确实可以被引向对自身局限的整体反省,从而对自我视野有所突破。当然,这种理性辨析的功能主要还是体现在“破”而非“立”;即使读者原来的知见立场倒塌了,读者更多是恢复中立,并不容易就转变为另一种非知见的立场。因此“道”是否就如庄子描述的这般,这依然是存有疑惑的。没有经历真正的“静修”体验,也许我们根本不能在“立”的意义上去判定庄子的道言。
四、结 语
以上分析旨在表明,对于其神秘论道可能遭受的读者质疑,庄子是一直有所自觉的,他始终考虑到读者接受的一面;这种考虑作为一种“显意识”贯彻到其论道表达中,促使他有意选择了某些特定的表达策略,尽可能积极地对读者质疑作出回应与化解。将作者自觉直白的期待意图与文本中实际的修辞策略相参,我们至少能发现:庄子在论道中自觉地运用了“三言”、寓言情节转变设计以及理性辨析这三种策略来贯彻其避开与读者直接论争、破除读者执见并提升其素质的意图,以求实现对读者质疑的化解。而这些语言策略在一般读者阅读庄子论道之言的过程中,也的确能发挥维持心理距离、刺激其自我反省的实际效果,一定程度地消解读者质疑。当然更难得的是,庄子同时在文本中自觉或半自觉地向读者表露自身对语言表达的思考与著述意图,这又进一步提升了读者自觉的“阅读意识”:首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始终觉察到作者自觉意识的存在,内在地与这种共情又超越的意识对话,养成一种关注作者表达策略及其背后意图的阅读习惯;其次,读者的自我反省将在作者的引导下得到加强,读者便可能获得某种“理性突破”,使自身视野更加开放,从而对即使在日常经验之外的大道也能保持某种中立态度,不会轻易将道论斥为虚妄,以为进一步的“静修”做好准备。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即使质疑能一定程度地消解,(缺乏静修经验的)读者对道论的切实理解也依然很难得到正面的促进。静修是一种身心整体的行动实践,无法仅仅凭借语言和思维达成,这构成了读者理解的鸿沟。在此岸,我们尽可能凭借正常理性将可以言说的言说清楚;而对于彼岸的存在,我们只能保持沉默。我们或许应该承认,在切实经验的意义上庄子的论道始终对一般读者保持着某种“神秘性”。尽管当代流行以哲理隐喻方式对道论内涵进行揭秘,其有助于推动读者的理性突破,但它与庄子希望引向的深一层的静修突破还是有一定距离。杨儒宾等人将道论描述视作真实的静修体验或是一种更接近庄子本意的解读,但如何借助日常经验增进对非日常经验的理解,则始终充满挑战。或许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庄子才又以“作者自觉”的方式开启着某种指示,使读者理解得以处于张力之中,从而有不断精进的可能。
从理解庄子论道这个案例稍做延伸,我们或能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诠解问题有进一步的方法论反思。不同时代语境下的读者由于自身的理解习惯而对古代思想有特定的理解要求,比如站在今日立场我们就容易要求庄子的论道符合实证理性,以此标准去批判或者转换其论道之意义。这种“符合实证理性”的要求对古代文本构成了一种来自读者方面的诠解压力。但文本本身并非没有独立性,它往往内含某种维持自身的抵抗力,具有自身的意图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要求读者优先按照“作者方式”去“同情”地理解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去做适合的理解批判。这便是文本对读者的反向压力。像《庄子》这样有着明显作者自觉的文本,这种反向压力表现得最为强烈,读者万不可忽视。读者和文本双向的压力,在较为理想的诠解活动中应该构成一种对话的态势,在不断的相互提问和回答、观他和反观之中,激发出富于创造的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