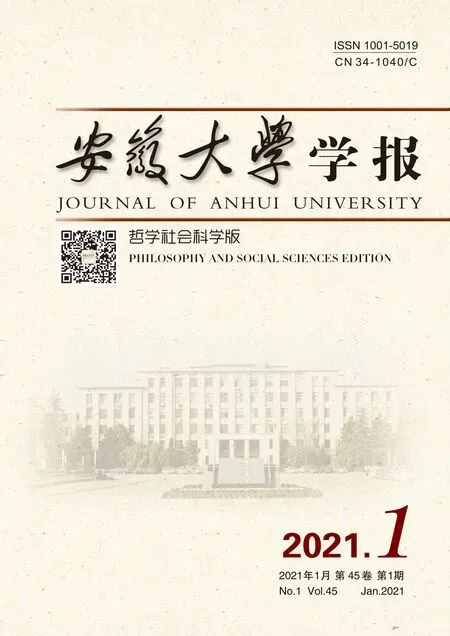“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曾振宇,王 晶
“勇”之为德,其来久矣。《尚书·仲虺之诰》载仲虺向商汤敷陈:“天乃锡王勇智”。《诗经·长发》歌颂成汤之德亦言:“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谏”。可见在商朝“勇”已被视为君主的重要品性并进入政治视野。但“勇”备受推崇,始于春秋时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知死不辟,勇也”,《国语·周语中》云“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在征战频仍的时代,勇德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德性。勇德之论,孔子之前已屡见。至孔子时,勇德被内敛为德性生命的品质,孔子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称为天下“三达德”,知、仁、勇三者融为一身,便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君子。孟子重视道德的内在化,真正的大勇精神是“反求诸己”的不动心之勇——仁勇。作为先秦儒家“殿军”的荀子接踵而起,对孔子、孟子思想既有继承,也有自己独特的发明。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从历史与哲学双重维度,梳理荀子论“勇”的基本内容,掘发“勇”观念的现代性意义。未中肯綮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荀子对勇观念的划分
许慎《说文解字》云:“勇,气也,从力甬声,勇或从戈用,古文勇从心。”“勇”的最初含义是指战争时代的勇猛之力,如“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国语·周语中》);“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国语·齐语》)。战争年代,人们经常处于外部兵乱威胁中,“只有靠最简单的、最率直的类型的勇敢,人们才能够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一切东西”。但当面临的生命威胁减少时,战争时代造就的武力之勇也应相应地消退,勇继而被定义为关于善恶的普遍知识。智慧与勇敢相互交融,战争的勇敢和真正的勇敢开始区别,对“勇”的认识也从着眼于生存困境的突破转为培养一种有价值的美德。如孔子既言“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又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第20章》);孟子既言“好勇斗很,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又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继承了孔孟儒家论“勇”的基本精神,厘清与人的德性无关的勇敢和符合美德的勇敢之间的区别。在荀子看来,与人的德性无关的勇敢是“血气之勇”,“血气之勇”受激情或情绪的支配,缺乏是非、判断之心,行勇中追求利益、荣誉等人爵目标;而符合美德的勇敢则是“仁义之勇”,其以仁义为道德理性,在经验世界中追求道义、立德等天爵目标。通过辨析“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进一步探讨了儒家思想视野中“勇”观念的实质意涵,确证了儒家的勇是以个体生命活动为中心、以道德实践为精神母体的生存智慧。
荀子对“勇”观念进行了考察,他从社会政治领域出发,在立足于社会秩序理论的基础上,将人与生俱来的性情以及在追逐物质资源时所投射出的勇的多种面相概括为四大类:“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荀子曰: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狗彘之勇”勇于争食,无是非、羞耻之心,不避外在强势与死伤,唯利是图而已;“贾盗之勇”着眼于世俗的荣誉期求,勇于争财,无辞让之心,勇胆猛戾,贪利不惮,以追逐货财为最高目标;“小人之勇”具有某种“不顾”特性,面对危险厄难,易受无节制愤怒的驱使,且“小人之勇”建立在虚假判断基础上,产生有见识偏差的勇敢精神,轻死、逞强、暴戾是其主要形式,狂妄、肆无忌惮是此种勇的特点。荀子认为这三种“勇”皆是血气之勇,受外在实存处境的影响,实际上属于勇敢的假象。这种假象一方面表现在勇敢的行为依赖强有力的外在血气或情绪(如愤怒),被其所裹挟,是一种被动的、缺乏自我主宰的莽撞行为。如果仅视勇敢为情绪、情感支配的行事倾向,必然会导致不义、不当的后果,造成“贱礼义而贵勇力”的乱世。由愤怒产生的行动不是勇敢的行为,真正勇敢的行为是由基于个体良知的自我决断所产生的合情合理的行为。另一方面勇敢的假象还体现在勇敢行动追求的目标上。血气之勇是为了外在的利益而藐视危险,“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如此不仅会威胁自身生命安全,甚至会带来“天下之所弃”的灾难性后果。
与此相对,仁义之勇作为道德活动,追求的目标应是高尚的,聚焦于人性美德和伦理行为而非外在利益、荣誉等期求,真勇是使人达到人性的卓越的美德。荀子所论的士、君子等人物所行之勇即是仁义之勇的典范,其追求的是“义以为质”“壹于道”等天爵目标,而非其他荣誉、权力等社会目标,持节守义,不为权力倾轧是其特点。诚如陈来先生所言:“善恶观念是指挥,可是若邪恶观念指挥了人性能力,其结果也不是善的了。”道义追求着眼于善的目的,而非情感、欲望、利益,由此而凝聚的人性能力才是道德行为。
由“士君子之勇”切入荀子勇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可发现:士君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为解决道德困惑提供了一种非机械的抉择过程,他们在道德中执守正确的价值愿景,比任何评价性说教更有说服力,使得万物与人各得其宜,美美与共。士君子的共同愿景是美政,实现公道、行义的社会,即使面临死亡危险亦坦然为之。从这个角度正视“士君子之勇”,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道德,也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是关乎他人与社会的德性,类似于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性公德,以公共政治理性为依归而非旨在提炼仁义为伦理的承诺和形而上的原理。
不过,荀子意识到通过规诫、他律制度统摄“勇”的局限性,社会性道德在其原则基本实现后,已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对人生价值、生活理想、生命意义等等终极关怀的追求。换言之,符合美德的活动是基于对普遍原则的忠诚,它们提供了可预知的结果。但对君子来讲,规诫尽管重要,但它并不适用于人道的昌盛,其对超越于人的现实存在的本质存在较少触及。真正的美德是通过道德修养提撕主体的心灵坚毅,使人生的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美德依赖于品质而非原则或制度体系。荀子在《性恶》篇中又将“勇”一分为三:“上勇”“中勇”“下勇”,其指出“上勇”所论述的个体独立自足的价值和意义才是自我内在的完善,是仁义之勇实质,荀子曰: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荀子·性恶》)
“下勇”的特质是轻身重货,无思虑、是非之心,凡事以必胜为强,即使付出生命也不后悔,“北宫黝之勇”即是此类勇之例子。“中勇”强调在礼法等社会规范的约束下,行正身、正人、正国家之事,其强调的是礼法等外在社会性法则的重要性,而非行为者自觉、自愿地完善主体道德,但“中勇”比受血气、激情驱使的“下勇”高尚,此类勇在秩序边界或是高层次目的规导下行勇,能辨明勇敢的假象。但在荀子看来有文有质的“上勇”才是仁义之勇,“上勇”既有“与民同乐”“与民同苦”的天下情怀担当,又有“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的君子气节和巍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的独立风范,既有勇的外在道德实践又有内在坚毅精神,保持了道德和人格尊严的圆满性与完善性,如荀子本人也是既有“百里之国,足以独立”(《荀子·富国》)的事功抱负,更有“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的坚毅品性和超越俗世的天地境界。“上勇”也即仁义之勇,是道德理性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自觉主宰,是关乎自我的德性,体现个体精神心理的凝聚,它是对人之本质属性或人格圆满性的肯定。
综上所述,追逐物质利益的“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下勇”等是荀子所谓的血气之勇;“中勇”则是在社会秩序归导下行勇,是积极之勇,但不属于荀子所说的仁义之勇;“士君子之勇”“上勇”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勇,“士君子之勇”作为公认的仁义之勇的典范,在社会中充当榜样的作用。“上勇”是仁义之勇的实质,蕴含让个体安身立命、心灵坚毅的精神建构,是对“善本身”的追求。荀子所谓“士君子之勇”“上勇”始终与儒家的道义担当相关涉,都是有国家情怀和伦理责任的大勇,其让人在面对利益、权力等诱惑时,能自觉地、有意识地以理制欲,以伦理道德的行道压制禀受于自然的生理性的血气,这种勇的着眼点不再是战胜困难、临危不惧,而是主体对道义的自信与持守,道义的意义大于生命本身。但是,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上勇”“士君子之勇”的动机是善的?荀子常言“本仁义”(《荀子·劝学》),在荀子看来,“士君子之勇”“上勇”之伦理状态的背后是仁义的精神活力。但此种“仁义”不是工具主义的修正作用,而是世俗主义和超越主义的统一,道义之勇是仁义之勇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勇敢与自我的关系得到了解释:通过“勇”的道德实践方式,将“道义”内敛为德性生命的品质。“仁义之勇”是为仁义的卓越而勇,这种“仁义”不只具有一般的道德伦理色彩,还是高扬道德人格的根源,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异曲同工。由而,“仁义之勇”不只是一种伦理范畴的“勇德”,更是一种根源于心灵的坚毅力量,具有能够塑造独立人格的内在道德动能,激发行为主体去践行道德。总而言之,“仁义之勇”关注的是自身人格境界的提升和突破,此种精神不受现实层面的功过利害、成败荣辱的限制,高扬的是道德主体的绝对价值,肯定了人是其自身的目的。“仁义之勇”使“仁”所蕴含的动力之知与“勇”所蕴藉的行动力量紧密联系,共同为道德实践服务。
二、勇与君子人格的建构
儒家不仅关注具体道德的目的意涵,更关注“我应该成为什么品质的人”,其关注点始终在行为者本身。培养一种完善的道德人格,继而引导人的精神向善是儒家伦理学的目的,这也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引导性功能。这种引导性功能可以促使君子人格的养成。诚如美国汉学家柯雄文先生所言:“古典儒家伦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在阐述伦理概念及其在道德教育中实践的重要性时,集中于君子或模范个人。”君子是德性人格的代表,君子人格的培养离不开实践的修养方法,而“勇”的重要伦理价值即在于实现由知向行的关键性转变。
“不惧”是勇的表现方式,是君子必备的重要品质。勇体现在逆境下的坚定,敢于经受可怕的事物,《荀子·法行》篇记载君子之德的五种表现:
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
君子之德有多种表现,其中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是其中之一。勇的本质特征是克服妨碍人们遵循理性的障碍,使人在面对恐惧、痛苦和人生各种障碍甚至死亡时变得坚强,彰显刚毅的人格特性。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时常能看到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巨大,仓促进入某种困境的无知鲁莽的行为。这些行为表面上是无畏的,实际上并没有呈现出勇敢美德,似勇而非勇。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不畏惧危险困境,有时是出于骄傲自负,或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性知识。虽然勇敢与不惧、大胆密切相关,但显然这样的不惧是反于勇德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过度滥用勇气会导致罪的发生。“勇者不惧”并非源自对刀剑、自然灾害的不惧,而是为追求某种善的理想忘记生死。荀子更是直言“勇而无惮……是天下之所弃也”(《荀子·非十二子》)。胆大妄为之勇是乱世之征,不仅缺乏理性的缓和,更是激情的滥用,即使表现出勇于面对危险的精神,但不是出于德性和普遍善的目的。“勇者不惧”并不是无所畏惧的情绪状态,也不是为危险而冒险,而是强调理智德性对实践的指导。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真勇并不意味着无所畏惧。二程有言:“圣人未尝无惧也,临事而惧”。真正的勇者出于道德行为的美好和高尚,对特定事物或身处某种特定环境时则会表现出一定的畏惧。但“畏惧”不等于怯懦。“怯懦的人是那种事事都怕的沮丧的人”,怯懦是由于信心的不足,惧祸患及我身,在威胁性的东西面前产生退缩、逃避等行为,甚至对不该害怕的事物也怕,是畏惧情态的过度,不是勇敢德性中的畏惧精神。同样“畏惧”亦不等于恐惧。儒家言“君子三畏”,是对合德者的敬之、信之,并不需要人的恐惧。君子作为知天命者,其行为准则是“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郭店楚简·五行》),有德行的君子因敬重天命、闻道而恭才有畏惧精神,非是对恶事恶物的恐惧,如荀子言:“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荀子·不苟》)畏惧的本质是对道德法则的敬畏,而非空虚无实之战栗惧怕,乃是心有主敬地戒谨惧德,修己安人。
二程言“治怒为难,治惧亦难”,“易惧而难胁”是成就儒家君子人格的修养方法。荀子作为经验主义者,以“礼”之厚、大、高、明的位格切入,主张“以礼治惧”,以对礼法的敬畏之心,展现顺吉逆凶的生活方式。《荀子·儒效》和《荀子·大略》两篇记载勇行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荀子·儒效》)
无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长。故塞而避所短,移而从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僻,勇果而无礼,君子之所憎恶也。(《荀子·大略》)
荀子从现实的群体秩序出发,从“木受绳则直”的经验改造出发,强调以礼法节制人的血气之勇、情绪之勇。激情的勇是理性之勇的对立面,它的实现往往与善的目的背道而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节制激情,使人受公共理性主宰。有效的行为预期和可延续的活动方式依赖于对规则和秩序的追求,礼法提供了恰当行为的参照系,是有序的行事规则。礼法使个人言语和行为活动在一定的规范内展开并得到他人如其本然的理解,是培养大众德性的重要教化手段。《荀子·乐论》更直接地彰显了在天下视域中“勇”与礼法关系的现实政治意义:
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
在有意义行为的边界之内,“礼”规定了勇行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其是成就自我道德人格的有效方式,“礼”使态度、意向以及情感表达变得容易。“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荀子·儒效》)。礼法身居高位处,为众人的祸福所系,是普遍的价值规范,当对其心存敬畏,“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荀子·王霸》),对礼法等规范的敬畏符合应然的道德善。
荀子“以礼治惧”不同于儒家孔孟的治惧观。孔子主张“以义治惧”,认为“义”凌驾于其他具体道德之上。孟子则主张“以心治惧”,强调四端、四德之心的仁观能力,为探求真勇精神做内在化的尝试。荀子则是向外诉求礼法的社会维度,通过整体一致的原则,凸显受限制的勇观念的发展过程,实现君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自我期许。在荀子看来,礼法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们为表现本真自我创造了条件。不过荀子也意识到一切“人为之物”都是相对有效的,礼法等规则是在长期实践中建构并可能变更的东西。因此荀子从现实主义出发对伦理生活进行思考,探讨如何将习俗的规则提升到道德生活层面,使之有助于生活的改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礼法被转化为实践,并内化为自发的德性,才是道德行动法则的至高功用,不是所有的道德都只关心规范。外在论是聚焦于作为制约体系的狭隘意义上的道德,但道德的实质内容是聚焦于人之需求的能力,是一种指向人性的方式。
“勇”是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品格,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他者对“勇”予以规导、节制的成物意义,同时又驱动主体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落实,成就个体内在价值,又具有成己意义。公众的道德规则世界与私己的个人理想世界之间并不存在裂隙,但究竟如何从“成物”的社会过程转到“成己”的自我过程?荀子则是通过耻观念来打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行为者自身通过耻辱观提撕自我,实现“知耻而后勇”。荀子曰: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荀子·修身》)
有所畏惧的勇通过自我知耻、知辱表现出来的真正指标就是身体的义理化,即义理贯穿人的血气形躯,使身体的血气功能法则化、理性化,如北海之滨的苏武、凛然正气的文天祥、为汉族殉国的刘宗周等人以耻辱为惧,以仁义为操守,义理之勇沛然莫之能御,这些皆是儒家大勇人物的代表。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将勇与耻辱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年轻人应该表现出羞耻的感情,因为他们常受到激情的左右而做出错误甚至不道德的事情,羞耻感有助于减少他们犯错的机会,只有对耻辱有畏惧,防止辱名加于身,个体的行为才会符合义理之勇的行事法则,倘若“做了坏事而不觉得羞耻,是卑贱的”。耻辱作为一种愧歉的道德情感,具有情感制裁的作用。个体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时,会引起公众舆论的谴责,耻辱是道德行为的枢机,是预防血气之勇造成恶行为的关键。
“耻”促使主体审视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意识状态是否都在道德管辖范围内。孟子论耻辱的重要性时言:“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耻辱作为否定性的道德意识,是良心的呼唤,发挥自我判断的功能,是道德生命的自我检测能力。杨儒宾先生言:“如果儒家的‘成人’要求学者需在文化世界中成就自体,儒者不能不重视一个连带而来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项常见的后果,此即人在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不免庸俗化,不免在群体的价值取向中遗忘自己”。“成人”是一个持续的和无休止的修身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耻辱充当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不安心理,不断呼唤行为者回归“诚”的真实状态,唤醒个体沉沦的本真世界,呈现个体内心真实的自我,此也即“改过”。勇于面对“过”是勇者的行径,如子路“闻过则喜”,知其错,知其过,坦然面对并改过,需是极大的勇气。
“知耻足以起懦”,道德上的羞耻体验给主体带来强烈的驱动力,促使个人存在状态的改进和精神状态的提升,其基调就是勇于改过、超脱旧俗、变化气质,这在宋明儒者那里达到了顶峰,如王阳明的“夫君子之学,求以变化其气质焉尔”,陆象山的“虽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刘宗周的《人谱》更是对“知过”“改过”等儒家修养工夫穷尽其源。伴随着对心灵生活之是非、真妄的省察,吾人私意、私欲萌发,当下即会察觉,由而“痛汗微星,赤光发颊”。“人非尧舜,安能无过”,在人生命实践的成圣、成贤过程中,过与不足会伴随着修养功夫的始终,而“切己自反,改过迁善”便是成圣功夫的重要面向,《人谱》的忏悔活动是回向本根的灵机行动,其通过对现实自我的省察克治,使真实的自我得以从生命本源处涌现。从孔子到刘宗周,我们看到一种扎根于生命本质的“耻”的道德意识,这与西方的“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耻”是出自仁义、性善或良知,是重建自我生活的革命性力量。明人袁了凡《了凡四训·改过之法》亦提出人欲改过,不仅要“发耻心”和“发畏心”,更须“发勇心”,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改过迁善。对君子而言,“耻”是道德动力之知,发挥了从失败的道德实践中吸取教训的作用,而“勇”作为道德能力之知,是主体改过的行动力量,“发勇心”而后勇于行,意味着这种自我革新的道德行动是根源于意志自律的真切的行动,其对君子式道德人格的养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仁者必有勇”(《伦语·宪问》),有仁的君子同时具备勇的德性,勇是实现君子之德的重要德能与动力,是应对道德多样性并解决各类伦理问题的基本手段,它构成了道德关怀的内外向度。又如“勇者不惧”“临事而惧”,其强调勇的一举一动皆有道德法则的贯穿,颇有“率义之谓勇”的意味,其中蕴含一种社会价值。同时有理则的勇作为普遍的价值美德,超脱血气之勇而跃升为社会性的公德,其道德行为本身超出了伦理制度与规范的相对性,与道德人格相联系。再如“知耻近乎勇”(《中庸·第20章》),其强调耻辱之心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蕴含成就个人价值的意味。从这点看,君子被视为人格典范,不是指他在知识、能力上的卓尔不群,或是对规则条理的接受,而是出于君子拥有内在道德的完善性,其体现道德关怀的内在向度和内在价值,而“勇”既是激发人按照道德原则行事的潜在力量,发挥道德驱动力的作用,又为卓越的君子人格提供了伦理完善的可能性。
三、“仁之为守,义之为行”:荀子勇观念的道德形而上学
李泽厚评价荀子“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体系,孟荀各领一翼,如孟子多讲“仁”“义”等内圣之理,而荀子则注重“礼”“法”的外在规范,大议军旅、法行之事,这一点成为荀学区别孔孟的重要特色。就儒家的勇观念而言,荀子与孔孟正统并非是对立和歧义的状态,荀子大体上遵循了孔孟的释勇路线,如孔子言“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孟子有“曾子之守约”的大勇精神(《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亦认为勇有“仁义之勇”和“血气之勇”。“仁义之勇”是儒家勇观念的本质性内容,对仁义之勇的坚守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入德之门。而勇于为非的血气之勇则遭到荀子的严厉批判,他说:“有勇非以持是,则谓之贼。”(《荀子·解蔽》)此旨在强调在主体的价值意识中应用高层次的伦理道德意识统摄低层次的自然生命意识。
荀子意识到以礼法为标识的社会伦理规范只能约束有思辨心和道德心的个人,并不能规约社会上所有的个体,换句话说内在论的哲学人性学的规范更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荀子所说的仁勇精神是有其价值根源的,荀子以人性为内在基础,证明仁是内在于人性的德性。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
荀子认为“欲食”“欲暖”“欲息”等食色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禹桀之所同,这些欲望是人的自然之欲,有其合理与合乎人性的成分在,不可完全理解成“人之性恶”,只有无节制的顺人之性、顺人之情才会产生争夺、乱理等恶的倾向,韦政通先生说:“依荀子之意,产生恶的关键在‘顺是’,照下文‘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的话看,顺是就是依循着自然之性,放纵它而不知节制,于是有恶的产生。”可见,荀子的自然之欲并不等于恶,“失而丧之”才是将人性引向恶的原因。因此,荀子强调人的自然之性具有潜在的善性,也即“伪”的成分,通过后天师法以及礼义制度的规导可以引领人性向善的倾向发展。
在“性”范畴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即认为人性的自然德性和仁有密切联系:
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人禽的区别在于人能“分”“辨”,此说类似孟子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少之又少的东西在孟子那里就是人的内在德性,在荀子则是主体的道德判断、道德自觉。孟子的仁义德性为其所贵,荀子的“义”亦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是人最贵之物。“义”并非只是具体的道德德目,而是先验性的道德原则,是内在于我的,具有普遍性。且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义常并举,仁不离义,义不离仁,如“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杨琼注为:“诚心守于仁爱,则必形见于外”,“守仁爱”已表明仁是内在于道德主体的,是“形于内”“心之所发”,而非简单的外在礼义规范。“‘致诚’就是让内在于人性的仁义‘是其所是’地澄现与彰明。”仁作为客观精神,是人性之内在根据,是一切道德的源出处,义是行礼时“比中而行”的中道精神,只有在先验性的道德本能基础上,才能理解荀子所说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此外,荀子通过“先仁而后礼”来探讨仁义和礼法的关系,认为礼法等规范的文化精神是仁,仁不仅是逻辑在先,更在道德精神层面在先。荀子从现实群体秩序出发,论述“礼”的起源: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欲虽不可也,求可节也”,强调依靠外在力量,也即“外铄”的渐靡作用,如具体的制度、办法来止息争论,节制欲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在国家政治层面,有无礼法是“国之强弱贫富有征”,如齐国强大,南以破楚西以诎秦,曾经叱咤一时,最后却被燕赵联军所破,仍避免不了衰亡国败的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礼义是“道诚之存也”,是实现天下秩序、王道政治的唯一途径。荀子还扩充礼范畴,他认为礼学不仅是人伦体系的制度规范,也适用于一切物,“礼”最终成为一种宇宙秩序。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
“礼”不仅是人类社会统治秩序的法规,亦是协调天时地物的权衡法则,是自然和人文的最高准则,是宇宙之礼。但在荀子看来,外在礼仪与内在情感的相互交融才是礼的最高境界,“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荀子·礼论》),文理兼备、情文俱尽才是文质彬彬,礼之功用与价值了无间隙,才能实现儒家“成乎文饰,终乎悦快”的人文教化目的。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礼存在的正当性之精神基础是什么?如何证实由礼出发的动机是善的?一言以蔽之:在荀子看来,礼法的强制虽能约束“小人以力”,使社会有秩序,但其在“君子以德”的自发道德本性层面的作用却极为有限。对此,儒家的回答是“仁”,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荀子亦有“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的提法,皆是强调“仁”是礼法的伦理支撑,是作为普遍准则的礼背后潜伏的道德精神。从这点看,荀子礼学本质上和孔孟哲学一脉相承,是儒家仁学的分支:
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荀子·大略》)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
仁的文化精神通过礼贯彻,为国以仁为先,礼其表也,仁其本也,礼之践行,乃是仁之构成,仁的伦理精神才是礼义之道。“礼”是秉持正确之精神而行动的形式,“仁”则告诉我们此精神为何,甚至史华兹说:“只有通过礼制途径,人们才能将其内在的把握自我的能力向社会显现出来,并在内部生成更高的、杰出的道德能力——‘仁’。”人是伦理关系的主体,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礼将仁义精神贯彻到人伦中。
荀子的思想体系中有“向高度提”的层面,也即其在道德形而上学视域中看伦理行为,追问的是主体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源。“仁义之勇”作为人类道德行为的伦理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客观规范和秩序的层次,强调意志独立的人生态度和主观战斗精神,具有普适性价值,自有作为其基础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文化精神。那么作为伦理价值的“仁义之勇”,其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何在?“仁之为守”,仁义之勇的道德行动来自仁的内在驱动,因此徐复观所说的“仁没有在荀子的精神中生根,所以由他所强调的礼,完全限定于经验界中,否定了道德向上超越的精神”值得衡评。在荀子看来,“仁”是保证社会秩序规范化、个体行为道德化的精神依托,荀子所谓“上勇”“仁义之勇”都是本体之仁的精神显现,它使个体在履行道德行为时可以超越物质力量对人的束缚,摆脱现实功利追求,在心理镜像中形成某种独立自足的强大力量。“仁义之勇”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实践都是基于“仁”而起。“仁”驱动道德主体不断向善,将个人与社会联结起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以对方为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责任的要求”,从而避免“勇”的血气状态和个人本位立场。“仁”凸显了个体的价值自觉,使“勇”的内涵从无畏无惧的身体性力量拓展到道德性的社会伦理原则,继而发展出影响社会集体的公共效用,这种光辉是本体之“仁”的呈现,“仁”是塑造整全人格和礼法秩序的内在精神依托。
四、结 语
荀子对“血气之勇”和“仁义之勇”的态度,昭示出儒家之“勇”与价值认定密切相关。“不惧”是“仁义之勇”和“血气之勇”的主调,为培育血性人格,克服妨碍人们遵循理性判断的障碍,提供强大的意志动力。但真勇并非是逞血气之勇的鲁莽,而是对所遭遇的人与事有所“畏惧”,“畏惧”的对象不是现世的存在者而是无形的道德精神,是仁义等道德法则。基于伦理美德的真勇是在仁义与礼法范导下,以羞耻之心为“启动装置”,使勇敢行动既符合理性法则又具备坚实的人性基础,在本己的个人道德和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中都体现出生而为人的道德自由与人格尊严。“仁义之勇”属于生存论意义上的“为己之勇”,不仅具有提撕个体自觉遵循外在道德准则的伦理价值,更具有将外在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自我心性品质的作用,其关注的是主体人格的突破与超越。这种勇才具有善的道德品格,是荀子仁义之勇的精神实质。“勇”在道德生活中具有激励个体进修德业的意义,是挺进高层次价值美德的最高实现形式。
儒家的成人之“勇”已经成为塑造国人性格和气质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对这一观念的梳理将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当下时代是麦金太尔所说的“德性之后”的时代,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德性与价值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现代社会的挑战,道德冷漠与道德旁观现象频出,德性处于生活的边缘,“勇”德伦理也同样被人遗忘,如此对“勇”德文化的追寻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