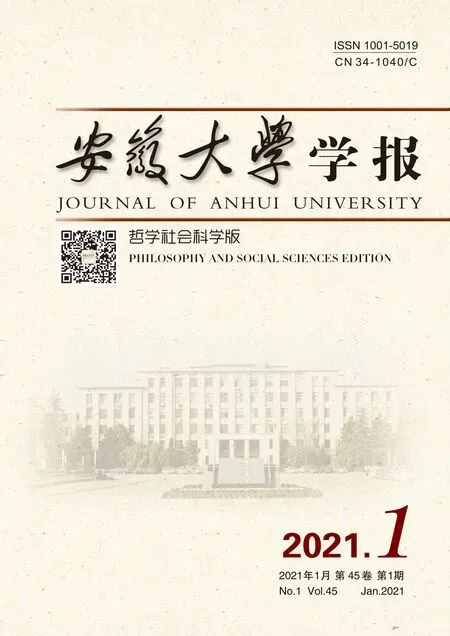李公麟《九歌图》的意涵与批评
许 结
在楚辞图像史上,李公麟绘制的《九歌图》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其后张渥、赵孟頫、仇英、陈洪绶、萧云从等画家的赓续之作,构成了以《九歌》为题材的系列绘卷。据《宋史·文苑六·李公麟》记载,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桐城)人,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历泗州录事参军,以陆佃荐,为中书门下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其“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然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李氏除史臣所称《山庄图》(《龙眠山庄图》),其《五马图》《维摩居士像》《九歌图》亦著称于世,而观其画作,人物、史实、释道、士女、山水、鞍马、走兽、花鸟尽入笔端,人称其“释道”得吴道子旨趣,“山水”得王维正传,“着色山水”追李思训心法,画“马”有过韩干。而综观有关李公麟的评价,亦多聚焦于绘画,此“但以艺传”之故,然上引史传又谓“因画为累”,其中复杂的批评心态,也自然因缘于如《九歌图》的创制。
一、作为“经图”的《九歌》书写
《宋史》传记所载李公麟“因画为累”,可对应《旧唐书·阎立本传》中记述其为主爵郎中侍从唐太宗传呼作画时“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时的情形,特别是立本退诫其子的话:“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技。”所谓“末技”与“为累”,都是史家对书画的轻蔑之词,相较而言,阎立本因高官厚禄,比照的是仕途,要在功业;而李公麟是“风流不减古人”,比照的是名士品质,更多书卷气。由此又牵涉到李公麟所处时代对绘画的态度,以及其绘本取效经典的路径。概括地说,李公麟的《九歌图》是被涂抹了一层经义的典雅色彩,而被视作“经图”来制作的。
李公麟的《九歌图》有文献清晰载记,然因真迹流失,现传者多为同时或继后画师的临摹作品。然返本考源,据陈池瑜研究认为李图有两种:一是根据梁朝萧统的《文选》所辑录屈原《九歌》中的六首诗而绘制 ,共六个场景;二是根据楚辞《九歌》中十一首诗绘制的全本 ,即九位神仙和两个颂诗仪式场面, 共十一个场景。这两件图卷长、短正本,在13世纪末被私人收藏,但长本(十一个场景本)在明代中期失传,到14世纪又有多种摹本传承,其图也成为元明时期表现《九歌》题材的范本。据周殿富编著《九歌图七种古注今译》,又首列李公麟《九歌图》三种,即有景本、无景本与六段本,作品或为《九歌》并《国殇》十图,或有分图者,如《云中君图》分二幅,《山鬼图》分三幅等。 所谓“六段本”,就是摹写《文选》所录《九歌》中六首作品的图绘。清人吴升《大观录》卷十二评此图即李公麟绢本白描六段《九歌图》云:
图只按《文选》所载《东皇太乙》《少司命》《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山鬼》……墨笔作山水、树石、屋宇、舟舆、人骑,俱极纤细。人物间施浅绛色,图之景,各随歌所诠次而描摹之。
这已说明其依《文选》所载而系列图绘的特色。无独有偶,与李公麟交好的苏轼在北宋元祐间“书九歌”,其书法作品正与李氏所绘绢本白描《九歌图》相合,亦即张丑《清河书画舫》所述“槜李项氏藏苏长公行书《九歌》一卷,止录《文选》中所载六章”,并认为“盖宋人无不精熟《文选》者”。这里蕴含了一个信息,即苏“书”与李“画”,都有摹写《文选》的特征,这也说明萧统的《文选》宜为北宋书画取效的重要经典。
考《文选》编纂,一改汉人骚(辞)赋合称的传统,而另辟“骚”为一体,收录《离骚》《九歌》等十三篇作品,其中《九歌》又选录其中六篇,分别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明录“骚”之意云: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对萧氏区分骚与赋,前人质疑甚多,近人高步瀛于《文选序》之“李善注”的义疏中释“骚人之文”谓:“《汉书·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骚即赋也。昭明析而二之,颇为后人所讥。然观此序,则骚赋同体,昭明非不知之。特以当时骚、赋已分,故聊从众耳。”这仅说明当时如阮孝绪《七录》已立“骚”目的时代特征,却未言及萧氏《文选》录文的两大要素:其一,文章的经典性,这是其别“骚”一体而不附于“赋”文的思想基础;其二,文学的藻采特征,这也是其选录《九歌》偏重“二湘”“少司命”与“山鬼”以展现其妙曼形象的原因。唐宋两朝是“选学”昌盛的时期,比较而言,宋代确有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说的熙宁后士人“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的现象,究其源是科举考试之帖括代兴,所谓“此特就一般之士习言也,至积学之士,著书考订,其中涉及《文选》者仍多有”,其中晁补之《续楚辞》、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撰述,已然为骚学经典。由此来看苏“书”与李“图”,其依萧《选》而对《九歌》的钟爱,其摹写正是其经典化的艺术呈现。换言之,李公麟的《九歌图》是以绘笔追奉《选》学经典而展示“骚”学经典,从而开辟《九歌》“图像”化的新方式与新时代。
由《选》学经典上溯,李“图”显然受到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的影响,关键在“依经立义”。张丑《清河书画舫》述历代绘画,认为:“古今画题,递相创始。至我明而大备。两汉不可见矣,晋尚故实,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之类。唐饰新题,如李思训《仙山楼阁》之类。宋图经籍,如李公麟《九歌》、马和之《毛诗》之类。”其谓“宋图经籍”并以李画为例,既说明宋绘重视“经”类典籍的风尚,又揭示了《九歌》为“经”的意图。考述包括《九歌》在内的“楚辞”典籍的为“经”之路,最典型的就是王逸《离骚经章句叙》: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汉人以《诗》为“经”,而王逸又以“骚”拟《诗》,继后至宋代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无不以《离骚》为“经”,《九歌》等皆附“经”以行。由此再看李公麟《九歌图》的创意,一在重视经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假“经”为“画”,以尊其义。对此,宋濂《画原》有段论绘语值得关注:
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世道日降,人心浸不古,人往往溺志于车马士女之华,怡神于花鸟虫鱼之丽,游精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
这是从本原的意义强调“经图”的历史意义,但与张丑的“宋图经籍”之说不同,此将经籍图仅归于汉魏后“有可观者”,值得玩味的是宋濂批评后世“溺志”的“车马士女”又恰恰是如李公麟《九歌图》取象的方式而为“经图”的书写。这也是李图及马和之《诗》图不同于前人“附经而行”的如《易图》等,而以形象化的书写更为绘画界重视的原因。二在因“愍其志”而重视对其忠贞形象的书写。这一点不仅在历代的“屈原像”有所体现,也表现于如《九歌图》的构画间。如李图“东皇太一”绘制的“至德”尊神的形象,“湘夫人”拟于芷兰的嘉淑形象,都印合于王逸所说的“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的经义思想。缘此,贡奎《题〈九歌图〉》云:“忠言去国今已矣,悲愤空复遗骚经……寓情托写岂真见,龙眠落笔无遁形。”其中“龙眠落笔”指李公麟的画,“岂真见”指图绘只是摹形与影写,而“无遁形”无疑是指思想旨趣,这里有《九歌》所写的原始形貌,有屈原作《九歌》的理想与趣味,更重要的是有王逸“依以立义”解读的内涵。正因如此,张丑《清河书画舫》说:“余不佞,未能窥画学之奥,而愿为检法(李公麟)执鞭者,则以《九歌图》卷板实中有风韵沉着,内饶姿态。其间山水、树石、人物、屋宇,形形色色,事事绝伦,非胸襟丘壑汪洋如万顷波,胡能为此擅场之笔。”这表面是对李氏《九歌图》绘形与笔法的推赞,却自有体义蕴含于内。
绘画重在形象,而前贤论此艺又极重“心”与“志”,早在西汉扬雄于《法言·问神》中就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传承其义,元代吴澄《题李伯时〈九歌图〉后》言“世之好者,好李之画而已,非好屈之文也,谁更论原之心”。这其中由“画”入“文”喻“心”,可视之为认知李图的情志与画则。
二、立意为先与行笔精妙
有关李公麟《九歌图》的绘制与传世,郑振铎《楚辞图》、饶宗颐《楚辞书录·图像第四》、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图谱提要》、崔富章《楚辞书录五种续编》等,均有详细载纪。据崔编所载,首录故宫博物院藏甲、乙本(9图)两种,次录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孙承泽旧藏本(11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王橚题跋本(白描9段,有山水树石屋宇等景界)。其中有清高宗弘历题识云:“《九歌》辞采奇丽,意境惝恍,非伯时通神之笔,不能得其仿佛。……《宣和画谱》谓公麟画一立意为先,此正公麟超轶陆(探微)、吴(道玄)处。至其人物秀发,行笔精妙,以虎头(顾恺之)《女史》卷相证,尤信其能入前人之室云。”其中赞美公麟“通神之笔”,并引述《宣和画谱》以强调李图“立意为先”与“行笔精妙”,既是对其绘作的称颂,也是极为中肯而精到的评价。
绘画是造型的艺术,其视觉观感首先在“形”(象),而前人以“立意为先”赞述李公麟的《九歌图》,指的是作者以“意”主“形”,而读(观)者的鉴赏或批评,仍需是以“形”见“意”。我们读《九歌》之图,无论是白描人物,还是有景界烘托,都是以原作的人物形象为主体的展示,而于中观觇“为先”之“意”,又需通过李公麟的“行笔”得其趣味。略述主旨,宜有两端:
一曰“古意”。学界曾有研读文徵明“二湘图”时提出的一句很有意味的话语,即“古意的竞争”,指的是画师力求营构出的“高古形象”。换言之,有关“高古形象”的绘制,既有“古辞”原“象”的描写,还有“古辞”中存“象”的故事,这也是解读李公麟《九歌图》之“古意”的意涵所在。而这一点,还宜回到前引王逸《楚辞章句》的话语,如其《九歌章句叙》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
这段话中隐含了李公麟图绘追摹的双重“古意”,一是“信鬼而好祠”的神话意涵;一是“托之以风谏”的经义意涵。
考察楚人信奉神灵,有天、地、人三大类,如天神有上皇(太乙)、日神(东君)、云神(云君)、司命(大司命 、少司命)、风伯(飞廉)、雨神(蓱号)、日御(羲和)、月御(望舒);地神有山神(山鬼)、水神(如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等;人神有祝融、颛顼、高辛、轩辕、伏羲、女娲以及厉神(殇鬼)等。而这些神灵在《九歌》中又多以丰满的个体形象呈现(《离骚》诸神多排列描述),如“天神”之“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司命”,“地神”之“湘君”“湘夫人”“山鬼”,“人神”之《国殇》中的“殇鬼”等,这也是《楚辞》文本中最为突出的“神像”的聚合。如《云中君图》,李公麟白描图突出“云神”个像,旁衬二侍者于左右,以印合“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形象,而另设景界的《云中君图》,则以主神乘鸾驾居中,以群神烘托,并有龙飞于天际的景象,尤切合于歌辞的“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的描绘。而对白描图的“云中君”,道然题赞曰:
其云扬扬,其水汤汤。变化莫测,四海翱翔。神降其福,人思曷忘。章以鸾乘,驾以龙骧。臣之慕君,地阔天长。
这则题赞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以“变化莫测”状云神之像,突出绘画中神性的特征;其二,所言“章以鸾乘,驾以龙骧”显然不限于白描图,而是结合全景本的构画叙写的;其三,赞语末两句的“臣之慕君,地阔天长”,又变神话意涵而为“心志”表现,从而揭示了李图转向经义意涵的笔法。
“托之以风谏”在《九歌图》中的反映,既是歌辞所述的“心志”,也是“依经立义”思想的深层表达。这种由“神性”向“人性”的变移,在李公麟全景本《九歌图》中《山鬼图》的思考与行笔有极为典型的呈现。该图将地神“山鬼”绘制成“人形、有毛”的精怪形象,与此相关的是朱熹《楚辞集注》对《山鬼》的释解“以上诸篇,皆为人慕神之词,以见臣爱君之意。此篇鬼阴而贱,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鬼喻己,而为鬼媚人之语”,这正从反面以彰显李图的意象。既然剔出“山鬼”的不可“比君”,恰说明《九歌》中多数神灵是可“比君”以寓“志”的。例如《东君图》,李公麟的白描画突出庄肃典雅的容颜,与峨冠博带的服饰,配以龙辀云旗,影写歌辞“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的景象,既寓“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回兮顾怀”的心志,并呈现以“杳冥冥兮以东行”的“东君”之行径与诚德。对这一句的解释,洪兴祖《补注》云:“杳,深也。冥,幽也。日出东方,犹帝出于震也。”这显然也是李图的喻意所在。又如《少司命图》,李氏白描画以发髻束首,以飘带萦身,善雅面像,以拟状歌辞中“荷衣兮蕙带”“临风恍兮浩歌”的形象,“登九天兮抚彗星”的天象,特别是“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的志愿。据《汉书·郊祀志》记载,“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文选》李周翰注“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善”,而李图的绘饰,也是突出其司命职守与“殄邪祛恶,劝祐忠良”(道然赞语)的德行。这其中由“星神”转化为人生志向的书写,也是绘者精心撰意,以摹拟辞章而深入于义理阃奥。
二曰“今意”。一切文艺作品的摹写,都是当代的书写,李公麟《九歌图》的“以意为先”既明古意,亦彰今意。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北宋文士的辞赋与书画多重写意,即文人赋与文人画并兴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李公麟的“楚辞图”如《九歌》的绘制,与同时好友苏轼写意赋如《赤壁赋》,有着共时的特征,而后世大量图写《赤壁》的创作,也正契合于写意赋入图的时代因缘。据史书记载,李公麟当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同为驸马王诜座上客,李绘有《西园雅集图》(现存多种摹本),以人物、鞍马、山水、花鸟取胜,盛邀时誉。如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曾评李画有云:“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其神交万物,正是“以意为先”的另类说法。缘于以意主形,后世评论家才为李公麟留下极为重要的位置,如邓椿《画继》论:“郭若虚谓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以予观之,伯时既出,道子讵容独步耶。”这里虽然包括了李氏白描的线条技法的简澹与游刃自如,或称天下绝艺,但其中神与物交的意境,才是论艺的结穴。明代吴中书画家文徵明《跋李龙眠孝经相》论其画“集众善以为己有,能自立意,不蹈袭前人,而阴法其要”,“众善”难言,“立意”为先,实为要则。
由于先“意”而后“形”,李公麟《九歌图》虽以人物擅扬,如“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山鬼”的姿态,但通过后人的鉴赏,却多能去形达神,由态及意。如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李伯时九歌图》评云:
昔人称其人物似韩滉,潇洒似王维,若论此卷之妙,韩、王避舍矣。他不具论,即湘夫人一像,萧萧数笔,嫣然欲绝,古今有此妙手乎?
此论李氏《湘夫人图》,以为“萧萧数笔,嫣然欲绝”,而视为丹青“妙手”,可谓知言。再看笪重光《跋李龙眠九歌图卷》的评鉴:
李龙眠白描人物,推为画家上乘,此今古定评也。余每览一真迹,如获鸿宝,赏心久之,寝食两忘,不减宋君痴癖。……展玩斯卷,秀润清旷之态……非宋人笔墨,焉能精妙若是,为可珍也。
其论《九歌图》全卷,“宋君痴癖”语用《庄子》外篇《田子方》中的典故:“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此论“一史”之妙,在于无心于画而风神毕现的精神境界。论者用此典评李图趣味,其磅礴之气、萧散之意尽在画中,又溢射图外。
夷考历代画论,称赞李公麟所撰《楚辞图》者甚多,如谓“伯时作画,多不设色,此白描湘君、湘夫人。绾髻作雪松云绕,更细如针芒,佩带飘飘凌云,云气载之而行。真足照映千古”(乐乡记);“李伯时作《九歌图》,余所见非一。此卷(六图绢本)尤精密遒劲”(王穉登题语),评语中的“白描”与“遒劲”,自然属于行笔精妙,是画家自身的艺术造诣与境界,但其绘图能够“照映千古”,却宜旨归李公麟所处时代共有的“骚心”。与李公麟同时代的人如黄伯思,其《跋龙眠九歌图后》评其六图本,就认为“贝阙、珠宫、乘鼋、逐鱼,亦可施于绘素,后人或能补之,当尽灵均之清致”,所言“清致”,正是屈骚之“心”,而绘笔透过物象、事象而呈现的意象,已然为画者之“心”。不妨对照黄伯思《新校楚辞序》批评后世仿效《楚辞》的语象,所谓“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指矣”,可见其对李公麟楚辞“图像”的赞述,更有非常的意义。我们再看《宣和画谱》第七卷载语:“(龙眠)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荻、台舆、皂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小大美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这里并美李图的“笔法”与“立意”,特别是先立意而后缘饰,既是评论《九歌图》等绘作的精到语,也是当时作者与论者的审美共识。
三、骚绘经典:肇造与影响
缘于在当世李公麟的绘画就受到了极高的重视,于是后人承续其说乃至推尊其为“画圣”,代表说法如张丑《清河书画舫》论画云:“夫右丞、检法(李公麟曾任御史检法),画圣也……传闻检法博学精识,出刘贡父上。官京华数年,不一迹权贵之门。佳时胜日,载酒出游,坐石临流,翛然终日。山谷谓其风流文雅,不减古人,而为画所掩。其为当时推许如此。及观检法之画,笔法如春蚕吐丝,云行水流,初看甚平易,细玩则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焉。”并美王维与李公麟为“画圣”,一为山水,一为人物,而李氏之博雅与笔法,尤为其称道。如果我们视《九歌图》为标志看李氏“画圣”说,又当结合另一北宋作家宋祁“《离骚》为词赋祖”的话语,这又开启了元明以后屈原为“骚圣”之论。由此视域,自然可以显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屈原首出“骚语”,而公麟首作“骚图”,其《九歌图》作为骚绘经典,具有初造之功,其泽被后世,影响巨大。
在李公麟之前,鲜有涉及《九歌》的图绘,据田野发现,有学者视徐州汉墓出土的男女两偶画像砖(二女御),以为《九歌》图像,并对应《少司命》中“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的歌辞,以解读其义。但这仍属推测之词,其中有合理性,即楚神在汉代民间的广泛传播,也有不确定性,就是没有考据学的实证。于是标明以《楚辞》作绘,兼括其人物与景观者,李公麟绘《九歌图》当为迄今文献所载存之“楚辞图”的肇开之举。有关李图,姜亮夫认为可确指为真品者有两种:一为绢本;一为纸本。纸本为十一段,公麟自书《九歌》全文,为赵兰坡所藏,仅描神鬼之像,而无景界,是收入宣和内府画作。绢本就是依据《文选》所录《九歌》六神(东皇太一、少司命、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山鬼)的六段本,有山石树木屋宇等景界,并有曹纬书《九歌》全文(今佚)。而作为中国绘画史之发展期的宋元时代,李公麟《九歌图》的出现,正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继此,画家在屈原作品中,偏爱《九歌》中“二湘”“山鬼”等绘画,出现了创作题材的“因袭性”,也形成了一种不可忽略的绘制传统。张澂《画录广遗》记李公麟《离骚九歌图》传于世,而仿本极多,以致张丑说“赝品满天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李图的影响至巨且广。
《九歌图》在李公麟所处的宋代就开始有了影响力,这从两方面表现:一是共时的趣味。据有关楚辞图谱记载,宋代录有书法作品如苏轼“书九歌”“书九辩”、颜乐闲“篆离骚”、米芾“行书离骚经”、吴说“书九歌”,绘画作品如李公麟《九歌图》《湘君湘夫人图》、马和之《九歌图册》以及不知名的《临九歌图》等。二是直接临摹。仅宋人临摹李公麟《九歌图》 者就有多种,如明朱之赤《卧庵藏画目》载《九歌图》《石渠宝笈》卷十六著录的素笺本、《石渠宝笈》卷三十六著录米芾篆书本、卷四十四著录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乾隆御题本、署“李伯时为苏子由作”的故宫博物院藏本、赵雍书赞本(已流出国外)、吴炳篆书本等。然就传世作品来看,继李图后绘《九歌》者当以张渥、赵孟頫(元代)、仇英、陈洪绶(明代)、萧云从(明末清初)为最著名,而萧云从的绘制《楚辞》的画幅数量,可谓集大成。缘于萧氏《补绘离骚全图》为清四库馆臣所辑录,乾隆特别题写八韵以颂赞云:“画史老田野,披怜长卷情。不缘四库辑,那得此人名?六法道由寓,三闾迹以呈。因之为手绘,足见用心精。岁久惜佚阙,西清命补成。共图得百五,若使表幽贞。姓屈性无屈,名平鸣不平。迁云可以汲,披阅凛王明。”这首诗庸常,但其中也透露诸多信息:其一,“老田野”乃民间作画,非宫廷命题,此亦《九歌》系列绘作的境遇;其二,“六法道由寓”内含绘事六法(气韵生动等)与“道”,也不乏经图经义的意蕴;其三,“手绘”“用心精”,亦“心画”思想的传承,是对“楚辞图”形与意的赞述;其四,“惜佚阙”已不单指萧图,而是由此追溯古图佚失的感喟;其五,“表幽贞”诚以“骚图”见“屈志”,复将图志汇入骚史;其六,“迁云可以汲”明确“画”与“史”的意义,彰显“丹青”与“汗青”的同源共采。
由此反观李公麟《九歌图》对后世的作用,比照前述几家影响力较大的“骚图”,择要说明,略有三端值得关注:
一曰“白描法”。虽然传世李图的纸本与绢本有白描图,重简笔勾勒,以人物为主,有景致图,兼取烘染,人景合成,但后世赞美李氏者,无不集中于白描法,即单用墨色线条勾描人物形象,而不重藻采修饰与渲染烘托的画法。这也决定了后世规摹之作的《九歌图》,无不以人物线条的勾画为主,而与李图一脉相承。如张渥的《东皇太一图》,主神像容貌完全同于李图,只是面向略异,身边侍女表情与方位不同。据《石渠宝笈》卷四著录周璕《九歌图》、胡同夏书词一册,图前副页有胡同夏识语云:“今得交周子湛园……出白描《九歌图》十二帧示余,其人物不逾寸许,而须眉状貌尽态极妍,神气飘扬,令人目眩心摇。至其用笔微妙,几令龙眠无处生活矣。洵希世之珍也。”胡氏因赞美友人“湛园”而轻抑“龙眠”,恰恰反证了其“白描”技法源自李图的奥秘。
二曰“择指意”。人谓李图作“骚图”而见“骚心”,从图画的呈象意义与技法来看,又往往通过选择创作指意以达成。例如李氏《少司命图》绘主神于中幅,副像(侍女)于右幅,贴身并立,侍女身背长剑,以应合《少司命》歌辞之“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的形象与心志,这也使图像通过白描勾画的重点提示,以强化语图互文的功效。传承其意,张渥同图则以主神手持纸卷为像,而未见佩剑,赵孟頫的图绘则以侍女背负长剑随行,陈洪绶的图绘虽仅画一主神背乘云车的身影,然横腰插剑,多同于李图所选择的指意。
三曰“隐逸气”。历代治骚学与制骚图者,固脱不开屈原“忧愁幽思”的“穷苦之感情”(刘一止《上越帅书》),而龙眠作图,却能撇开如此心境,呈现出一种仙气和逸气,这虽然与宋人尝损悲以自达的风气相关联,更在于李氏平生的隐逸的志行。当时名士交誉其“襟度超轶”,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可谓实录。对此,我们再参读苏轼的《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的一段文字:“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山庄图》系李氏隐居龙眠山时所绘,苏轼亲见其作画,谓之“天机”“意造”,其中正内含一种不同凡俗的隐逸之气。也正如此,我们读李氏《九歌图》,诸神面相皆飘逸自然,绝无“穷苦”之象,后世画师摹写衍绎,亦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