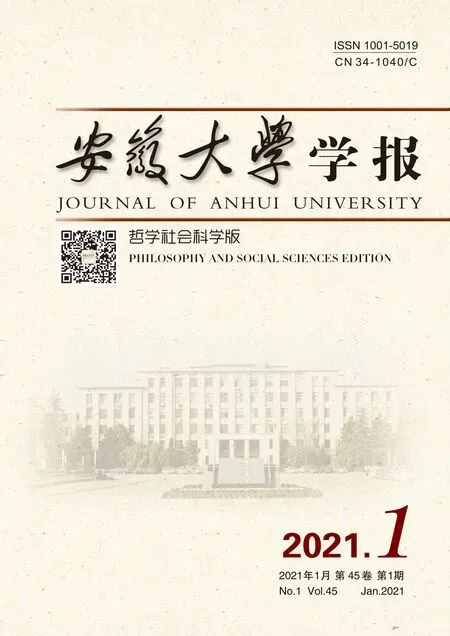主敬立本与穷理之基
——对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已知之理”的阐释
李健芸
朱子为《大学》“格物致知”条目所补的传文一般称为“格物致知补传”或“补格物致知传”(以下简称“补传”)。这段传文无疑是理解朱子“格物”思想的关键文本。学界对朱子的格物思想其实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概而言之,“格物”包含了“即物”“穷理”“至极”三层含义。然而,充分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对这段传文的理解不再存在可疑之处。在“补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意味着,在具体的即物穷理活动展开之前,心灵就已经拥有了某种关于“理”的知识,如此才能“因其已知之理”。但朱子在原文中没有对所谓的“已知之理”做出解释,学界也未对此处的“已知之理”给予足够的关注。于是留下的问题是:“已知之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果“《大学》始教”在于即物穷理,而在具体的穷理活动展开之前心灵就已经拥有了某种关于“理”的知识,那么,这种知识究竟如何呈现?以及,这种知识与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是什么关系?考察这些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要想澄清“已知之理”的内涵及其如何呈现的问题,就需要先澄清具体穷理活动展开之前心灵应当达到的状态,因为“已知之理”正是在这种心灵状态中才得以如其所是的呈现。在笔者看来,朱子对这种心灵状态的论说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在大学教育之前的小学教育,二在优先于具体穷理活动的主敬工夫。后者所揭示的意涵对于理解此种心灵状态更为根本。
一、穷理之先:小学之教中的“已知之理”
朱子在《大学或问》里详细论述了从“大学”之前的“小学”阶段进入“大学”阶段进行格物穷理的过程:
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
不同于《集注》“补传”中直接从大学始教开始论述,这里补充了小学之教的阶段。正如乐爱国教授所言:“强调在进乎大学、即物穷理之前,必须先‘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可见,小学之教是即物穷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但如此重要的信息为何没有出现在“补传”中?朱子的弟子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问:“‘格物’章补文处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学处做了。此处只据本章直说,不必杂在这里;压重了,不净洁。”
看来,朱子“补传”只是为了依从《大学》文本作解而避免烦冗,故而没有写入小学之教“习于诚敬”的部分。那么,如果要从整体上理解从小学之教中的“习于诚敬”、收放心、养德性到大学之教中的即物穷理,则应该依据《大学或问》的论述。在《大学或问》中也有“因其所知之理”一言,据此,学者所能够因循的“所知之理”必定在小学之教中已经拥有,对“已知之理”的探究就要在小学之教“习于诚敬”的脉络中进行。那么,小学之教中所谓“习于诚敬”具体指什么?
朱子写作《大学或问》时应当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成熟的思考,如果参考此前的一些讨论相关问题的书信,或许可以对此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在《答林择之》中朱子说:
古人只从幼子常视无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了。此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
在《答胡广仲》中也有类似的思想:
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
以上两条材料都说明朱子所谓小学之教的内容就是在对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的熟练过程中培养一种持守之心,以逐渐达到所谓“涵养纯熟”的内在品质基础,而这种基础是大学所以能够教之以格物致知的前提。显然,对洒扫、进退之类的日用之事的磨炼不仅是为了教授具体的实践行为如何做,更是为了培养一种心灵基础,即“涵养”,而“涵养”又不是空荡荡全无事做,而是就在日用之事的磨炼中自然纯熟。朱子进一步明确了涵养与日用之事的关系:
古人之学,固以致知格物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则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习而已。是皆酬酢讲量之事也,岂以此而害夫持养之功哉?(《答吕子约》)
在这里,朱子指出,小学之教的洒扫之事、礼乐之习,虽然都是日用酬酢之间的具体事务,但这些事务的磨炼不会妨碍“持养之功”。甚至可以说,所谓持养之功正是落实在对具体的日用酬酢之间的事务的打理中,即此就可以做涵养工夫。朱子所谓“涵养”是承自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教法,“涵养”与“敬”无疑密不可分,因而《大学或问》中所谓“习于诚敬”的小学之教,不是以“诚敬”为教习对象,而是在“涵养”中培养诚敬之心,教育的具体内容就是让童子、少年在日用酬酢的具体事务之操劳中涵养内在品质,从而培养一种由诚敬之心主导的处理具体事务的实践能力。
那么,在经由小学的涵养进入大学即物穷理的过程中,所谓“已知之理”是否就是在小学涵养之中习得的呢?朱子在《答吴晦叔》中如是论述了从小学涵养进入大学格物的过程:
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此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
在这段话中,从涵养践履到格物致知的过程与上文所论无异,但是有两点信息可以丰富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其一,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这意味着大学应该能够“知之深而行之大”,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应当同时包含“知”的推进与“行”的扩大;其二,大学的格物之教“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也就是说,所谓“即物穷理”所接之物,首先就是小学所习之事,即物穷理的范围首先在于“即”小学所习的日用酬酢之间的具体事务,“穷”这些事务之理。在《语类》中朱子做了更清楚的论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这里明确划定了“事”与“所以”的区别,正如朱人求教授所言:“小学只是追求‘所当然’,大学则应知晓‘所以然’。”如果借助这个区分理解在即物穷理过程中“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那么,所谓“已知之理”就是在小学的日用酬酢之间习得的处事行为的伦常规范,如事父事兄应当遵循的规矩,而“穷理”则是穷究这种规矩的“所以然之故”。
除了从“事”到“所以”的推进之外,由朱子在“补传”中对“穷理”最终效果(“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描述来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过程也涉及“知”的范围的扩大。对于这种扩大,吾妻重二先生认为:“在将已知的事项扩大适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它视为‘类推’的一种。”吾妻先生以“类推”理解“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种方法,那么所谓“已知之理”的范围就限于既有的经验之知。以上论述无疑符合从小学的“知”之浅、狭到大学的“知”之深、广的过程,然而,此中不能无疑。如果即物穷理所基于的“已知之理”仅指小学日用酬酢之间习得的伦常规范,那么这种“知”显然是一种经验之知,且其必定限于一个人早年的经验范围,但是就朱子的格物思想而言,“即物穷理”的范围无疑在理论上应当具有普遍性,且就“补传”的表达而言,“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显然,“已知之理”应当贯通在一切即物穷理的活动当中。因此,就一个人的经验和教育顺序而言,即物穷理所基于的“已知之理”固然可以在大学之教的初始阶段不离于在小学习得的伦常规范,但就其根本而言不能限于这一早年的经验之知。因此,要探究“已知之理”的根本,就必然要求对朱子的小学之教的理论再做深入讨论。
二、主敬立本与已知之理的呈现
上文已经标划出对小学之教中确立起来的“已知之理”的初步的理解,即不离于日用酬酢之间的涵养工夫,但又不限于已有的经验范围内的规矩,而是能够贯通在所有即物穷理活动之中的“已知之理”。但是,在上文引述的朱子的相关论述中,又存在这些表达:“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涵养纯熟”与“自然纯熟”,加上所谓“习于诚敬”之“习”,似乎表露这是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一个自然地、逐渐地养成习惯的过程。那么,即物穷理之前的“已知之理”是否应当理解为在这种逐渐养成的习惯中纯熟运用的伦常规范?确有学者按照习惯之养成理解朱子论述的从小学进到大学的过程。如牟宗三先生认为:“从此‘涵养将去,自然纯熟’,仍是空头的涵养,仍是习惯之事。”牟先生进而认为:“此是自然的不自觉的事,但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是风俗习惯中之好人,于此并无真正的道德行为。”因而,朱子所论述的这个过程“混教育程序与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工夫而为一,而不知其有别也”。在牟先生看来,由于涵养只是“空头的涵养”,也即没有道德自觉,不是道德主体自觉自主的行为,因而由此养成的人格只是习惯意义上的好人,没有真正的道德行为,这个进学过程只是教育次序,而非道德行为之奠基次序。牟先生的这个评论值得重视。如果认为“已知之理”就是在小学教育阶段通过习惯养成而纯熟运用的伦常规范,那么就会面临两个困难:其一,在风俗习惯中掌握的知识总是一种经验知识,经验知识不具有普遍性,而朱子为穷理活动设定的目标则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知识,那么经验性的“已知之理”是无法达成穷理活动的目标的;其二,这样的“已知之理”由于其根源是经验性的风俗习惯,而非自主自觉的主体,故而不能在根本上为人的道德行为奠基。然而,通过对小学之教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已知之理”并不局限于纯熟运用的习惯性的伦常规范,其根本上是随自主自觉的主体的确立而一同呈现的关于“理”的知识,那么,随着主体将一切事物之理纳入自身穷究范围,这种知识就随同主体普遍作用于心灵的穷理活动当中,而不依赖于风俗习惯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如此,以上两个困难实则不能成立。
其实,但凡对朱子的小学之教稍加留意都能发现,其中所主张的在日用酬酢之间的“涵养纯熟”,如果排除一切具体伦常规范等经验性的内容之后,其显露出的根本指向在于对“敬”的培养,而正是“主敬”工夫确立了人的各种具体活动得以恰当展开的根本的心灵状态。朱子在其《程氏遗书后序》中说:
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
这里是朱子关于主敬与穷理关系的著名表达。在朱子看来,“主敬”是“穷理”的根本,“主敬”为人的实践活动确立根本。“主敬”的思想显然承自程颐,朱子不仅本人多次有言,也多次借程颐之言指出“主敬”之于“穷理”(“格物”)具有奠基次序上的优先性。在《大学或问》中朱子引程颐之言而论之曰:
又曰:“格物穷理,但立诚意以格之,其迟速则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又曰:“格物者,适道之始,思欲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条者,又言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
从朱子所引五条程子语录可知,朱子所谓“涵养本原之功”就是主敬工夫,而“主敬”则是格物之本。主敬涵养本来是在小学之教中已经成就,但在朱子看来,当世的学者由于在年少时期未曾接受过古人的小学之教,故而即便到了应该进行即物穷理之教的时候,也需要补上涵养主敬的工夫,才能为即物穷理奠定根本。朱子在《答胡广仲》中说:
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论敬云:“但存此久之,则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圣贤之言,亦莫不如此者。
类似地,在《答林择之》的另一封书信中说:
疑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今人从前无此工夫,但见《大学》以格物为先,便欲只以思虑知识求之,更不于操存处用力,纵使窥测得十分,亦无实地可据。
在《答吴晦叔》中朱子指出如果缺乏涵养工夫而为格物之学的问题:
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则先知后行,固各有其序矣,诚欲因夫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则非涵养履践之有素,亦岂能居然以夫杂乱纷纠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
在上述材料中,朱子批评了当世学者忽视主敬涵养工夫,而专从事于格物之学,这会导致这样的格物之学由于缺失“敬”的工夫而失去根本的主宰,缺乏立根之处,也即“无实地可据”,导致心灵纷然杂乱,而无法有主宰地进行格物之学。唯有“主敬”才能确立格物之学的根本。因此,小学之教中的涵养工夫并非仅仅只是教育次序中的一个步骤,涵养工夫的目的在于培养“敬”,而这正是培养本原、培养主宰的工夫。
因此,朱子的“涵养”非如牟宗三等学者所谓的“空头的涵养”,而是“立本”的涵养,正如王健所论:“朱熹预设的‘存养之实’,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在日常‘洒扫应对进退’的活动中,所应保持的对天理良知的敬畏和自觉执行。”朱子也并非混淆教育次序与道德行为之奠基次序,其所谓“涵养”“主敬”不仅是小学之教的内容,也在人的行为奠基次序上处于奠定根基、培养本原的地位,且应该贯穿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始终。唯其如此,朱子才会强调“‘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答胡广仲》)、“大扺‘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答林择之》)。正是因此之故,朱子才在《大学或问》中说:
是其岁月之已逝者,则固不可得而复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条目,则岂遂不可得而复补耶?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朱子在此指出,虽然当世学者已经错过了小学阶段的涵养工夫,但“主敬”工夫仍然可以在为学的每个阶段加以弥补,这种弥补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因为 “敬”的工夫乃是“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
进一步,“主敬”何以能够“立本”?朱子论“敬”甚多,对于本文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敬”的醒觉之义,如:“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今人却块坐了,相似昏倦,要须提撕着。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只是常惺惺在这里。”“‘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无事时,且存养在这里,提撕警觉,不要放肆。”在“敬”中心灵能够达到真正的醒觉。因而,朱子也说“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可见,“主敬”工夫确立了道德主体或价值主体的自主自觉。但是,正如吴震教授指出,朱子这里的“自做主宰”就是“心的‘自存’义、‘自省’义”。因而,心“自做主宰”并不必然意味着由心灵活动所带来的道德行为的道德本原就是“心”,而只是说心在醒觉状态下使得真正的道德本原得以呈现,而这真正由心灵所呈现的道德本原就是朱子哲学的经典表达“心具众理”之“理”。关于“主敬”与“理”的关系问题,蒙培元先生认为:“持敬是以存养心中固有之天理为前提。”也有学者认为:“朱子注重知敬双修,认为敬是心集中、专一的体现,人常怀恭敬之心就能心地湛然、常明天理。”唐君毅先生认为“持敬”所以相较于格物致知具有“立本”的地位,在于“此工夫要在凝聚身心,使一切不合理之意念不得发,亦在自积极的存养此心之虚灵明觉,使超越的内在之性理,得其自然呈现昭露之门,而格物致知诚意之事,亦易于得力”。此说甚好。其实,不妨更简要地断言:“持敬”使得心中具有的天理的呈现得以可能。朱子本人就说:“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澈,方能察见几微、剖析烦乱而无所差□。”(《答彭子寿》)又说:“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可见,在朱子看来,“主敬”工夫就是要确立自存、自省、自觉、自主的主体,而心灵在这种状态下呈现的“理”就是“已知之理”。因此,“已知之理”随“主敬”工夫对主体的确立而一同得到呈现,其不依赖于小学教育阶段具体而有限的经验知识,而是普遍作用在心灵的一切活动中的关于“理”的知识。
如上所论,在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中,小学涵养的根本指向在于“主敬以立其本”,即通过“敬”的工夫确立心的自存、自省、自觉、自主,从而清理出一种使得心中“理”得以呈现的心灵状态。朱子所说的涵养不是“空头的涵养”,而是“立本”的“涵养”,因而这个为学过程不仅体现了教育次序,更在根本上体现了人的活动的奠基性次序,是培养本原的过程。以上就标划出了一个理解“已知之理”的基本方向。那么,在“主敬”工夫清理下的心灵中自觉呈现的“已知之理”的内涵是什么?“已知之理”与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的关系又如何?
三、 作为穷理之基的已知之理
固然,先已把握的“已知之理”和穷理之后所把握的“理”有所不同,但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补传”中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表明,“穷理”所要去“穷”的“理”就是先已把握的“已知之理”。在《大学或问》中朱子说:
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辩之际,以致尽心之功。
笔者认为,这段话对于理解“已知之理”的具体内涵非常关键。在这段话中,朱子指出,经由主敬工夫达到的心的自存状态是穷理之本,这一点上文已经阐明。进而,“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辩之际”,此处所谓“知有众理之妙”的主体必然只能是经由主敬工夫清理之后的“心”,“心”在“知有众理之妙”后,在学问思辨的过程中展开穷究。显然,心所要穷究的对象是“众理之妙”,但“众理之妙”本来自有,不待人“穷”之而后有,因而穷究“众理之妙”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真正的“众理之妙”的理解渐次深入的过程,是一个把“众理之妙”予以揭示、展开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本质上是“知”的展开与深化的过程。因此,先已把握的“已知之理”与“穷理”之后把握的“理”就其本质而言是同一的,只是随人心之“知”的浅深而有理解上的差异,也即是本质同一的“理”在“知”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的揭示。质言之,二者都是关于“理”的知识。因而,所谓的“已知之理”,即经由主敬工夫所达到的“端庄静一”的心灵状态中呈现的关于“理”的知识,落实到上述引文中来看,也就是对“有众理之妙”这一事实的知识。但这只是一种先于具体穷理活动而呈现于心灵之中的形式上的知识,这种知识只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只是抽象地领悟到所有存在的事物各有其理,但还没有具体的一事一物的“理”的知识充实其中,故而在“知有众理之妙”之后还需“穷之于学问思辩之际”。当弟子问到“已知之理”的“知”和“穷理”之后的“知至”之“知”的区别时,朱子与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
任道弟问:“‘致知’章,前说穷理处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且经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后。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穷之’,则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会,便是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着,便是知之端未曾通。才思量着,便这个骨子透出来。且如做些事错,才知道错,便是向好门路,却不是方始去理会个知。”
在此,朱子强调:“知先自有。才要去理会,便是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着,便是知之端未曾通。”这意味着,先已呈现于心灵当中的关于“理”的知识虽然缺乏具体事物之理的知识的充实,但已经有所朝向,而这个朝向为具体的格物穷理活动确定了方向。显然,如果缺乏先已呈现的有所朝向的知识,那么穷理活动就会陷入无头绪、无方向的混乱之中。那么,这种先于具体穷理活动而呈现于心灵中的关于“理”的知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理”的知识必定与朱子对“理”的理解有关,而在《大学或问》中朱子对“穷理”对象做过如下清晰的界定:“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显然,朱子将“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作为对“理”的界定。但是,杨立华教授通过详细分析朱子与弟子陈淳的书信往来证实:“朱子指出自己原来是讲了‘所以然’一句的,但后来发现‘所当然’才是真正关键所在,所以将‘所以然’一句删去了;其次,朱子强调,如果学者真地理解了‘所当然’的‘不容已’之处,则其它的各个层面也就自然默会于心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朱子对“理”的各种论述中,“所当然而不容已”应当居于首要地位。简言之,所谓“所当然而不容已”指的是每事每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这种具体的当然之则是普遍的天理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普遍的天理必定体现在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中,这样,对于心灵而言,要想获得关于“理”的真实而丰富的知识,具体的穷理活动就是必要的。在朱子这里,“穷理”意味着“知”的推进(“至极”)和对“所当然”的理解的具体落实。在“补传”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中,“表里精粗”指的就是“知”在步步推进以后达到极致,而“众物”强调的就是对每一事物的“所当然”的具体而丰富的理解。在《语类》中记载了一条关于“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讨论,可以提供参考:
问:“‘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极’,是因定省之孝以至于色难养志,因事君之忠以至于陈善闭邪之类否?”曰:“此只说得外面底,须是表里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尽,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尽,尤不可。须是无分毫欠阙,方是。”
在这里,弟子理解的“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指的是将事父、事君这类当然之理落实为具体的细节上的当然之事,而朱子的回答表明:只在当然之事上做好种种细节仍然只是“外面底”,只有小者大者都做尽做好了,才是“穷理”的理想效果。显然,“穷理”指向了将形式上对“所当然”的理解落实为在具体处事中对每事每物的内外、表里、大小的“所当然”的理解,也就是说,“穷理”所“穷”的是具体事物的当然之则。朱子与弟子在讨论“格物”时非常看重对事物之理的具体性的逐层把握:
问:“格物最难。日用间应事处,平直者却易见。如交错疑似处,要如此则彼碍,要如彼则此碍,不审何以穷之?”曰:“如何一顿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见得大纲,且看个大胚模是恁地,方就里面旋旋做细……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只管理会,须有极尽时。”
这里朱子强调穷理必须“一重又一重”理会,这意味着“穷理”必须经由细致的工夫历程才能达到,而这种工夫历程最终达到的对“理”的理解,不同于抽象的形式上的“所当然”,但也不是与形式上的“所当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理”,而是落实在具体事物中的具体的“所当然”,“穷理”指向对“理”的具体的真实的把握。
既然“理”指的是事物之“所当然而不容已”,而“穷理”的目标在于将关于“理”的形式上的知识落实为对每一具体事物的当然之则的真实把握,那么,在“穷理”之前就先已呈现于心灵中的关于“理”的知识就是一种尚未得到具体化和充实化的普遍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知识。这种知识为具体的穷理活动确定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具体而真实的理解。这一方向使得穷理活动避免了泛滥无归的知识追求的倾向,而只关心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同时,心灵具体的穷理活动充实了先已呈现于心灵中的关于“理”的形式上的知识,而只有具体的真实的每事每物的当然之则才是关于“理”的真知。这就是“已知之理”和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的关系。
最后还需考察的问题是,这种关于“理”的形式上的知识的根源何在?如果这种知识的根源外在于人的心灵,那就意味着这种知识在心灵中的呈现是具有偶然性的,也就意味着心灵有可能丧失这种知识(而非仅仅掩蔽了这种知识),而这样无疑就会动摇朱子格物穷理进程的根基。就朱子哲学的脉络而言,这种知识实则根源于人心固有之“理”。依朱子,“理”本具于“心”,但要在“知”的作用下才能发显出来。朱子说:“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万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这表明:首先,“理”不在“心”之外,但要在“知”的作用下才能发显,而“知”的作用则属于心的作用;其次, “知”与“理”不是二物,不是以一种“知”的作用达到另一种完全不同于这种作用的“理”,“知”就是心之理的体现。但是,真正的“知”的作用只有在经由“敬”的工夫清理之后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正当的发显,这种正当的发显就是上文已经澄清的对普遍体现于事事物物之中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知识。因而朱子说:“盖义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则自然发见明着,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尔。”(《答林择之》)这里朱子所谓的“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指的就是因“心”的已明之理而穷之,而“心”的已明之理实则就是人心固有之理的发显,也就是心的“所当然而不容已”的发显。质言之,心灵在“主敬”工夫清理后的理想状态下,按照它自身的当然之则,就能获得“事事物物上都存在当然之则”这一事实的形式上的知识,以此确立具体穷理活动的方向,这种知识并非一种根本上有别于心灵的知识附着在了心灵之中。就这种知识根源于心之理而言,由此知识确立方向的穷理活动也就有了主体方面的根基。
四、结 语
综上,“已知之理”作为在具体穷理活动展开之前已经被心灵把握的关于“理”的知识,其内涵需要从具体穷理活动展开之前心灵应当处于的状态入手探究。在朱子的直接表达中,在作为大学教育内容的格物穷理之前尚有一段小学之教,小学之教虽然以日用伦常中的具体应对规范为教育内容,但其根本指向实则在于“习于诚敬”。如此,“已知之理”就不能从纯熟运用的风俗习惯中的伦常规范方面来理解,而应理解为在“主敬”工夫培养的自存、自省、自觉、自主的心灵状态中呈现的关于“理”的知识。进一步而言,这种知识指的就是心灵对“有众理之妙”这一事实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理解还只具有抽象的普遍性,还没有具体的一事一物之理作为其内容,后者是格物穷理的目标。所谓“理”,就是事事物物中的“所当然而不容已”,也即每事每物依其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这样,“已知之理”就可以进一步界定为在心灵中呈现的有关事事物物中存在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知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知识不仅先于具体穷理活动,而且为穷理活动确定了方向,即穷理以穷究每事每物的当然之则为方向,而具体的穷理活动则使形式上的已知之理充实化、具体化,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心灵对“理”的把握真实而丰富。最后,这种关于“理”的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本就是心之理的恰当发显,因而这种知识只有可能在没有“主敬”工夫的情况下被遮蔽,却不可能丧失,这就为穷理活动的展开确立了根基。
“已知之理”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对“已知之理”的阐明将有助于澄清朱子格物论受到的误解。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时代的陆九渊和后世的王阳明等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恰恰相反,格物穷理以在“主敬”工夫清理下的心灵中呈现的关于“理”的形式上的知识为头脑,也就是以之为主导性的方向,具体而言就是以穷究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方向,这样的穷理活动避免了泛滥无归的知识追求的倾向,将心灵的探究集中到了所谓事事物物中的“所当然”上。这意味着朱子格物思想的旨趣在于揭示一种体现于事事物物中的普遍秩序,只有充分揭示这种普遍秩序才能充分理解人事的伦理秩序的根基,因为人事的伦理秩序就是普遍秩序在人事中的具体体现。就此而言,以普遍存在的“所当然”作为穷理活动的方向,体现了朱子试图将人事的伦理秩序奠定在本然的普遍秩序之上的努力,也就是说,人事上的“应当如此”其实是源于人的本来如此,只不过人常常处于失其本然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关于“理”的形式上的知识过于抽象、空乏,因而只具有方向指引的意义,很难提供具体处境下应当如何行动的知识,这也正是朱子很少停留在“主敬”工夫所呈现的关于“理”的知识上的原因。朱子也出于这一点而总是谈论能够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有丰富内容的格物穷理活动,或许正是因此才让朱子的格物论给人一种陷溺于追求具体事物之知识的印象。
An Interpretation of “Known Pattern” Presented through “Cultivation of Reverence”(主敬) and Utilized in Exploring Patterns Based on Zhu Xi’sCommentary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Extend
Knowledge
(格物致知)LI
Jianyun
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Zhu Xi’s theory about “investigating things”(格物), the concept of “known pattern” in Zhu Xi’sCommentary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Extend
Knowledge
(格物致知) necessitates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Known pattern”, known as the cont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before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patterns, refers to knowledge about patterns. “Patterns” can be understood as different regulations that things ought to obey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nature; thus “known pattern” means a formal knowledge about the regulations. But the knowledge could only be presented in the autonomous mind, attain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of reverence”(主敬). The knowledge presented in this way is prior to the particular activities of exploring patterns and designates the orientation to the activities. Besides, the knowledge is grounded in the pattern of mind, which sets up the foundation of pattern-exploring activities. But the knowledge needs to be embodied by particular activities aimed at exploring particular patterns, so that we can attain the true knowledge of patterns. An interpretation of “known pattern” shows that Zhu Xi’s theory about “investigating things”(格物) is not fragmented and unreasonable, as is criticized by the School of Mind.Keywords
: Zhu Xi; known pattern; cultivation of reverence(主敬); investigating things(格物); exploring patternsLI
Jianyun
, Ph. 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